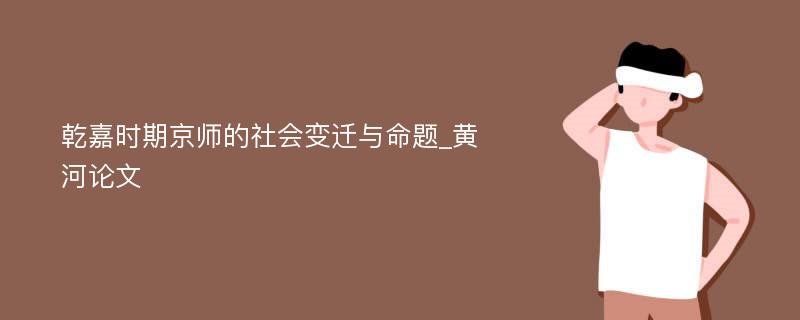
乾嘉时期的社会变化与经世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着转变并面临着选择的重要历史时期。清朝统治的由盛而衰,新的经济因素萌芽的出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使得传统的中国社会在陷入历代封建政权盛极而衰的怪圈的同时,又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这种盛衰转换,新旧交替,中外冲突所带来的各种变化,不仅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在号称朝廷大政的河工、漕运、盐政、铜政、人口等重要经济领域,也有或多或少的反映。许多为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和掌管有关事务的朝廷官员,以及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正是面对这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和经世主张。
一、河工
黄河的治理,始终是清廷首要大政之一。清代初年,承明末弊政之后,河道年久失修,黄水连年泛滥,仅顺治至康熙十六年(1677)的三十余年间,黄河大的决口即达八十余次,以至河南、苏北一带深受其害。康熙曾把河务视为首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之一,“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康熙十六年,清廷在平定“三藩”的战争中占据优势之后,始下决心治理黄河,任命靳辅为河督,主持治河工作。靳辅任用卓越的水利专家陈潢,全力堵塞黄河决口,大规模修筑、加固堤坝,使多年漫溢的黄河、淮河复归故道,安澜入海。同时,在黄河北岸开凿中河工程,使运河漕船得以避开黄河一百数十里之险,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自此而后,黄河安澜数十年,直至乾隆中期,虽有决口,但大多随决随堵,尚未造成太大的灾害。然而,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后,黄河漫决次数增多,决口长期不能堵塞,河患再次严重起来。对此,不少主持治河工作或关心河务的地方督抚和朝廷官员,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治河主张。
其一,疏浚河身,培筑堤坝。黄河常年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黄水挟沙,奔腾东流,一遇地势平衍之处,即水缓沙停,造成中下游河床淤积,河身垫高。而河身越高,水流越缓,淤沙愈积。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使得河患日趋严重。所谓“黄河斗水沙七,所过之处,无不淤垫”[1]。因此,传统治河之策,十分强调疏浚河身,培筑堤坝,以期“束水攻沙”,使河流通畅,安澜入海。乾嘉时期同样如此。乾隆二十一年(1756),大学士陈世倌上《筹河工全局利病书》,即以浚治河身为御灾急务之一,认为“黄河携沙而来,奔腾浩瀚,一往莫御,故坚筑堤岸,使水循堤直下,则势猛而沙随水去”,今“清口以上至徐州黄河数百余里河底高于内地丈许,皆成老淤,水势不能冲刷,自非大加疏浚之工不可”。否则,“大溜不能归中,河流不能迅捷,沙停河饱,为害滋深”[2]。针对疏浚河道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如“浮沙、途泥、滩河、浅水,一望弥漫,欲事畚锸,何所措手。少为开掘,水即随之,捞泥水中,焉能深广”[3],其治河工具若杏叶扒、铁扫帚、混江龙等又不尽合用等问题,陈世倌提出,“请铸大铁轴一具,约长六尺,上铸铁齿,长三寸而锐其角,一周凡三齿,共列五周,两端贯以铁锁,务使直沉至底。用船一只,夫四名,首横木梁,将铁锁分系木梁之上,用夫牵挽而行,沿路滚翻,每十船为一排,每十里置船一排”,“每日往回三次,十日当可深一寸,积一月计之,当可深二三寸,一年计之,可深二三尺矣”[4]。嘉庆四年(1799),时任河东河道总督吴璥覆奏黄河治淤情形,所言治河之策,仍“不外疏浚、堤防两事。疏浚以畅其流,堤防以束其力”。“是束水攻沙,诚为千古不易之论。以水攻沙,则必以堤束水。固知日渐培堤,计非尽善,而舍此更无束水之方”[5]。
其二,蓄清敌黄,疏通海口。海口即黄、淮入海处,位于江苏北部云梯关附近。由于其属黄、淮交汇之最下游,黄河所携大量泥沙,往往淤积于此,致使海口垫高,河流入海不畅,泛滥成灾。故需藉淮河及洪泽湖之清水,并力刷沙,以使海口通畅,安澜入海。而蓄清敌黄之关键,则在清口。清口系淮河注入洪泽湖后与黄河交汇之口,与运河之口相距亦不甚远。淮河及洪泽湖之水能否从清口畅出,直接关系到黄河、运河以及海口通畅与否的大问题。乾隆二十九年(1764),河臣高晋主张于云梯关外“旧堤上首作斜长子堰,约漫滩水,汇正河入海”,以使“尾闾宽阔,于就下之势益畅”[6]。乾隆四十一年(1776),因“海口逾远,近年黄水倒灌,致通湖引河淤垫,清水不能畅出。清江、淮安一带,运道停沙,清口以外,黄河两腮垫高”,河臣高晋、萨载奉谕查勘清口、海口情形,认为“惟有浚清口以内通湖引河停淤,使清水畅出,与黄河汇流东注,并力刷沙,则黄河不浚自深,海口不疏自治”。为此,二人特别提出:“于陶庄迤上积土之北,开引河一道,使黄水绕北下注,清水畅行,至周家庄会黄东注,不独可免倒灌,而二渎并流,攻刷黄河两腮浮淤及海口积沙,均可渐次刷深。下游深通,则黄河上游可免停淤”[7]。其后,陶庄引河工程完成,使黄河河身距清口移远5里,大大减轻了黄水倒灌,清口淤沙之患。总之,乾嘉年间“治河诸臣,总以蓄清敌黄为要务”。诚如嘉庆时河臣百龄所言:“黄河必得清水从中刷沙,始不停淤,淮水必得畅出清口,始不虞泛滥为害。盖淮水自西向东入湖,与周桥五坝遥对,黄河在洪湖之北,淮流入黄,其势不顺。是以靳辅疏浚五道引河,长至一千五六百丈,直插湖心,欲接其势顺向北行,使迤南之周桥五坝、高堰山圩不致吃重。又恐湖水力不敌黄,复于运河口门之外,筑磨盘埽分溜敌黄济运,又设立束清坝,钳逼清水,使之奋迅冲黄,以资得力。良以黄水具数千里之源,挟沙而走,其力甚劲,淮水仅百里之流,归湖之后,停蓄成渊,非有诸引河以领之,并加诸坝以激之,恐其力纡缓,不能敌黄而出也。又遇清水过大,则将束清坝口门拆宽,黄水过大,则将王营减坝封土启除,务令黄水减而不决,清水涨而不溢,由是黄水下行,得清流为之荡涤,滔滔入海,畅流无阻”[8]。
当然,这些治河主张,皆针对局部河患而言,尚非全局的、长远的考虑,因此,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嘉庆时河臣铁保勘查治河情形,曾概括当时各种主张:“有谓海口不利者,有谓洪湖淤垫者,有谓河身高仰者”。在他看来,这些都不足以为河大患,而他认为,治河之关键在于清口,“诚以清口畅出,则河腹刷深,海口亦顺,而洪湖不至泛滥,一举而三善备”。强调“为今之计,惟有大修闸坝,全复旧规,去新受之病,收蓄泄之利。则借湖水刷沙而黄河治,湖水有路入黄,不虞壅涨,而湖水亦治”[9]。铁保所言,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自“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10]。但铁保置河身淤高等诸多因素于不问,只强调清口一隅,未免“主持太过”,同样失于偏颇。
那么,黄河究竟有无根治的办法?事实上,18世纪中叶,一些有识见的大臣已经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解决河患问题。乾隆十八年(1753),吏部尚书孙嘉淦明确提出黄河改道入海的建议,即在黄河北岸开减河,引黄水北流入大清河,经山东入海。他考察历代河流情形说,古代江、淮、河、济四水皆“独行入海”,互不相涉。宋时河决,始分而为二,一由南清河入淮,即今之河道,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合济水正道入海。宋末以后,河遂南徙。此后,历元、明两代,河或北决,经大清河入海,或南流入淮,经今之河道入海。当时已有人认识到,中原地势“南高北下,宜顺水性,导之北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自明代以后,治河者皆“逼河使南行”。清沿旧制,以致顺治、康熙年间,河“决北岸者十之九,决南岸者十之一”。有鉴于此,孙嘉淦提出,在黄河北岸开减河,引黄水北流,经大清河入海。他说:“大清河之东南,皆泰山之基脚,故其道亘古不坏,亦不迁移”,即其下游所经之处,“不过东阿、济阳、滨州、利津等四五州县,即有漫溢,不过偏灾,忍四五州县之偏灾,而可减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并解淮阳两府之急难,此其利害之轻重,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减河开后,其至张秋,不过经两三州县之境,计其漫溢之处,筑土埂以御之,一入大清河,则河身深广,石岸堵筑之处甚少,约计所费至多不过一二十万,而所省下游决口之工费、赈济之钱米,至少不下一二百万。此其得失之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是则减河一开,所费甚少,为害甚轻,而决口可塞,积水可消,漕舟不误,其利甚大”[11]。此后,朝廷大臣裘曰修、嵇璜均提出过大致相同的建议,请令河流改归山东故道。这一主张,可以说抓住了治理黄河的关键所在。因为造成黄河灾害频繁的重要原因,除上游水土流失外,就是下游河床老化,日益淤高的河身已难以容纳奔腾东流的黄水,仅靠疏浚河身、培筑堤坝、开挖引河、疏通海口等局部治理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乾隆四十六年(1781),河决北岸青龙冈,黄水经赵王河,入大清河归海。这一路向,证明了孙嘉淦等人建议的可行性。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昧于时势,因循保守,不敢改弦更张,认为“黄河南徙,自北宋以来,至今已数百年。即以现在情形而论,其向北泛滥之水,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海者,祗有二分,其余由昭阳、南阳等湖南下者,仍有八分,甚至江南沛县城垣被冲,则南下之水较北更大。此时岂能力挽全河之势,使之尽由北流。且于山东、直隶运道往来,甚有关碍,岂容妄议更张。为今之计,惟有就事论事,救弊补偏,此外别无办法”[12]。因此,终乾隆一朝,乃至嘉庆、道光年间,黄河治理始终局限于堵决口、修堤坝、浚河身、通海口等传统的办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职此之故,数十年间河患不断,灾害严重,直至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黄河终于“东注大清河入海”。“盖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河病而淮亦病。至是北徙,江南之患息”[13]。可见孙嘉淦等人提出的黄河改道的建议,确实是有远见的正确主张。
除提出各种治河主张而外,一些正直的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还对河务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抨击。18世纪中叶以后,吏治逐渐败坏,朝廷大政之一的河务也成为利薮所在,主持河务的某些官员藉黄河泛滥之机中饱私囊,大发横财。嘉庆年间,百龄疏论河工,就曾指出,乾隆以后“在事诸君子,或以节省为见长,或以无事生觊觎,屡次纷更,旧规全废。况当天下承平,国家闲暇,借要工为汲引张本,藉帑项为挥霍钻营,从此河员皆纨绔浮华,工所真花天酒地,迨至事机败坏,犹复委曲弥缝”。甚而“河工诸员无一可信,以欺罔为能事,以侵冒为故常,欲有所为,谁供寄使,罚之不胜其罚,易之则无可易”,给黄河的治理造成许多人为的障碍。当然,终清之世,河工弊端始终是困扰统治者的痼疾,但是,清代中叶的有识之士能够直面这一矛盾,仍然表现了他们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以及传统的经世精神。
二、漕运
清廷定都北京后,为解决皇室食用、王公官员俸米、八旗兵丁口粮以及京师民食之需,沿明朝旧制,每年由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八省征收漕粮400万石,另于江苏、浙江两地征收白粮(即糯米)217472石,经运河运贮北京通州各仓,此即漕运定制。由于其地位十分重要,故而历来有“天庾正供”之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年间,社会经济发展,吏治民风整肃,漕运基本正常运行。至乾隆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日渐加深,吏治败坏,风气奢靡,漕政弊端丛生,形势日趋严峻。对此,一些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乃至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漕弊成为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漕运包括漕粮的征收、运输、入仓等诸多环节,本身即手续繁锁,关卡重叠。特别是贯穿南北数千里的运河一线,沿途需索,层层盘剥,致使各种损耗开销巨大,费用惊人,漕运也因之积弊丛生。诸如地方征漕加派各种杂项,州县任意浮收勒折,漕务官吏肆行榨取运丁,运丁则多方婪索州县,等等,不少官吏士子对此多有揭露抨击。王芑孙说:“国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生,老奸宿蠹,窟穴其中。通仓之需索,大累于帮丁,帮丁之需索,大累于州县。督抚以浮收暂纾州县,而州县卒未尝纾也。漕臣以帮费暂恤疲丁,而疲丁卒未尝恤也。通仓诸臣,奋然欲去经纪花户之需要,而卒未尝去也。经纪花户之盘踞于通仓者不得去,则尖丁之蚕食于州县者不能除。浮收岁甚,帮费岁增;帮费愈增,浮收愈甚”[14]。蒋攸铦也说,今“地方往往视收漕为畏途”,“盖缘丁力久疲,所领行赠钱粮,本有扣款,而长途挽运,必须多雇人夫,以及提溜打闸,并间有遇浅盘剥,人工倍繁,物价昂贵,用度实属不敷,势不能不向州县索费。州县既需贴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包户挟制”。“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积重无已之实在情形也”。又“从前帮丁贴费,每船不过百余,至二三百两不等。近来旗丁积累愈重,需费愈繁,且路费正用之外,或偿还旧债,或任意花消,或帮弁需索,皆所必有,亦非尽由于路费不敷。伊等知州县浮收,有加五六之多,遂得藉口多索,运弁奸丁,连成一气,州县惟恐误兑,不能不受其刁勒,是以帮费竟有递增至五六百两、七八百两者。……且州县既多浮收,则米色不能认真,帮丁既多贴费,则受兑亦不复深求。及至通州,贿买仓书经纪,通挪交卸,米色之潮杂不纯,率皆由此。此又官民交困,彼此挟持,南收北兑,流弊无穷之实在情形也”。
漕务种种弊端积重至此,理应“大加整饬,力挽颓风”,以“恪遵功令,严行示禁,升合不准多收,帮费全行裁汰”。但由于种种原因,漕弊“有不可不除,而又有不能尽除者”。如“帮丁长途苦累,费实不资,若竟丝毫不给津贴,则势必不能开行,若责令州县颗粒无浮,亦势必不能交兑”,等等。因此,乾嘉年间,一些大臣“不得不于无术万全之中,苦思酌中权宜之道”[15]。阿桂疏请申明粮船定式,“议定江浙漕船长八丈,深六尺,入水三尺四寸为度;江广漕船长九丈五尺,深六尺九寸,入水以三尺九寸为度。并将入水尺寸逐一量明分晰,横刊于浅板之上,俾得众目昭彰,易于查验。旗丁既不能于定制之外多带货物,即遇水小之年,船身入水不至甚深,亦可无虞稽阻”[16]。蒋兆奎认为:“办理漕运,要在恤丁”,提出将州县每石漕粮所浮收之七八斗内,“划出一斗,津贴旗丁,其余尽行革除。所出有限,所省已多,不特千万旗丁藉资济运,即交粮亿万花户,已沾圣恩无穷”[17]。蒋攸铦则疏请更定漕政章程,提出四条建议:第一,“每年秋成时,酌定收米准则,以免偏枯也”;第二,“旗丁各船帮费,应严定限制,以杜苛索也”;第三,“收米既有限制,则兴讼之粮,应委员验明上仓,以防积欠也”;第四,“州县预买恶米垫仓,勒收折色之弊,应严行禁革也”[18]。
由于漕运与运河畅通与否关系密切,而乾隆中叶以后,河患日趋严重,直接影响到淮河、运河,因此,一些官吏士子也开始考虑漕运的改革办法,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芑孙认为:“方今民困于浮收,官困于帮费,议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帮费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帮费,去帮费必先改漕法”。因而提出“酌古之制,权今所宜,取唐宋转般仓成法损益之”[19],即实行分段运送,沿途建仓的转般法,通过“易漕艘”、“建仓”、“造拨船”、“判职掌”、“优俸糈”等具体措施,除弊兴利,解决漕运问题。至嘉庆年间,有识之士更提出了改河运为海运的变革主张。嘉庆九年(1804),因“洪泽湖水低弱,力不足以刷黄,以致河口淤沙,七省粮船全不能渡”,时任浙江巡抚阮元曾“暗筹海运一法”,拟招募海船四百艘,“每艘可载米一千五百余石,略用兵船护出乍浦,即放大洋,其装卸之程、脚价之费,俱与之议立章程,以待不虞。交卸如速,一年可以往返三次,较河运省费三之二”。其后虽“以河道复通,遂不复用”,[20]但阮元仍作《海运考》一册,主张海运,以为未雨绸缪之计。嘉庆十五年(1810),因运河淤浅,漕船航行困难,皇帝谕令调查航海情形。一时之间,官吏士子多有持海运之议者。江苏士子高培源说:“我朝自江南以至直隶,沿海水师每岁放洋巡哨,海径曲折,兵弁类能谙熟。欲行海运,宜令熟识之将弁,携带商船伙长,从南至北,测水势,辨沙色,自某至某,凡岙套岛屿,可以泊舟,可以避风,先为标识,绘成一图。乃仿王宗沐、梁梦龙遗意,拨正兑十分之二三,按图试探,逮往返径熟,如先臣谷应泰所论,成山直沽,无异安澜,然后取岁运正额,法元人春夏二运之例,分番起运。将见峨舸巨艑,浃旬麇至,其视内河守浅,千夫纤挽,蚊负蚁行,则劳逸之不侔,固难以倍蓰计矣”[21]。高氏还就海道、雇船、脚价、丁弁、回带、赔豁等海运中的具体问题,一一作了探讨。苏州知府齐彦槐“陈海运策”,认为“驳海运之说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资盗粮;二曰重洋深阻,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另造,柁水须另招,事非旦夕,费更不赀。然三者皆可无虑也”。以“漂没”而言,“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其每岁漂没之数,总不过百分之一。今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且“沙船以北行为放空”,即“顺带南货,不能满载,皆在吴淞口挖草泥压船”。因此,齐氏提出,以各船“先载南粮至七分,其余准带南货,至天津卸于拨船。每南粮一石给水脚银五钱,上载时每石加耗米三升,卸载时以九五折收。合计南粮三百五十万石,不过费水脚一百七八十万两,曾不及漕项十之三四”。如此则“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价,而官费之省者无数。又使州县不得以兑费津贴旗柁名目,藉词浮勒,一举而众善备焉”[22]。就连身为“海角末商”的谢占壬,也对海运之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海运之所以难行,关键在于“官事民情互相参议”。由于“舵水人等之技,由身试而非师授,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而事外之人,悬询其情,自必语言矛盾,款要莫凭。况运粮规则,从未经历,尤不免畏难之心,纷扰于中”,故而“不能实情上达”。有鉴于此,谢氏以其“自幼航海经营,亲历有年”,于“运载成规,舵水约束,以及风波趋避,捍卫汛防,素经熟视”,因而,他从“古今海运异宜”、“行船提要”、“四时风信”、“趋平避险”、“防弊清源”、“海程捍卫”、“水脚汇筹”、“春夏兼运时日”等方面,详晰论证了海运的可行性及有关事宜,并将河运、海运二者加以比较,明确提出:“今如海船运粮,必先将官事民情通盘筹算。夫商船运货,一岁之中,重在春秋冬三季。其时北省豆粮丰熟,货足价廉,乘顺风运南,商贾获利较重,船户水脚亦增。夏季北省货缺价昂,商贾获利较轻,船户水脚亦廉。其时雇船,乘顺风运粮赴北,正可舍贵就廉,趋平避险。抑或权时赶运全漕,亦不妨春夏兼装,自可裕如。果能通融办理,不惟上下两无格碍,而且商船均有裨益。此海运头绪分明,海程今昔异宜之大略也。复思内河漕运情形,偶逢雨泽愆期,河湖浅涸,舳舻衔尾而来,进退有期,不能缓待清流,必至借黄济运;或逢雨水过多,湖、黄并涨,黄流倒灌,决坏运河。种种阻碍,在所未免。诚使乘此夏令,兼筹海运,以分其势,则河漕二务,均得从容,既可操引清激浊之衡,亦可定河下湖高之则,自不至有治黄不能顾运,利运不能治黄之弊矣”[23]。可见,海运与河运相比,优势显然。但由于一些地方督抚的阻挠,两江总督勒保和浙江巡抚蒋攸铦就曾疏陈海运必不可行者十二事,诸如“旗丁不习海洋,必责成船户,又非如旗丁有册可稽,且不能设官出洋巡视,必至偷卖缺额,捏报沉失,甚或有通盗济匪诸弊”;“元、明海运,米多漂失,到仓欠交者,每石自数合至一斗数升不等,今生齿日繁,人之所食浮于地之所产,岂堪再有漂失”;“京师百货之集,悉来自粮艘,若由海运,断不能多携货物,将来京地物价骤腾,亦碍生计”;“运丁所用兵工短纤等项,总计八九万人,穷民资以为生,若由海运,则须另募熟悉海道者,而此常年漕运之众,一旦失业,难保不流而为匪”[24],等等。因此,终嘉庆一朝,海运之事始终未能付诸实施。但是,诸多官吏士子对漕运的关注以及改革的设想,却仍然反映了他们的经世精神,并最终促成了其后漕政改革的实现。
三、盐政
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消费品,同时也是封建国家的专控商品,在国家税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盐法大体沿袭明制,除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外,内地共分为11个产盐区:“曰长芦、曰奉天、曰山东、曰两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四川、曰云南、曰河东、曰陕甘”[25]。每个产盐区均规定有相应的销盐区域,如长芦盐行销直隶、河南两省,奉天盐行销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山东盐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等等。盐的运销,则实行官督商销的纲引制度,由官府指定的盐商领取特许运销的许可证即“引”,按照指定的区域定额销售。这种官商结合的垄断经营体制,自清初至乾隆中叶的一百多年间,基本保持稳定,特别是18世纪上半叶,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数量增加,盐业产销两旺,既为封建国家带来了高额的盐税收入,又为盐商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随着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败坏和社会危机的出现,潜藏于盐业垄断经营体制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官与商皆视盐务为利薮,以官而言,凡与盐务有关涉者,上自官府衙门,下至胥吏衙役,无不欲从中染指,商人办理运销手续,所经各道关口,都需交纳所谓“公费”,受到层层盘剥;而商人为弥补漏卮,赚取利润,又往往将各种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造成官盐短斤缺两,质次价高的状况。私盐因之而兴,官盐滞销,国家盐课大量流失,弊窦丛生。对此,一些忧国忧民的官吏士子,纷纷起来揭露盐政之弊,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
缉私除弊,改革盐法,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清代盐法,“莫急于缉私,但有场私、有商私、有枭私,而邻私、官私为害尤巨”[26]。士子汪甡论盐法,即极言私盐之弊,认为“弊之大者惟在盐徒,而其为害,私盐夹带为尤甚。盖私盐多一引,则官盐壅一引,夹带多一斤,则正盐壅一斤。”[27]广西巡抚孙玉庭则直接指出了私盐屡禁不绝的原因:“盖场灶产盐,得利而售者情也。官买例有定价,售私则价重于官,场灶必卖私盐者,此其一。官商之盐有课,私贩之盐无课,无课则价轻,小民愿食私盐者,此其二。场灶必卖,小民愿食,私贩从中射利,而欲以法令禁之,此必不能,所由枭徒盛而拒捕多也”[28]。为杜私盐,为除积弊,不少官吏士子提出了变通改革之法。孙玉庭认为:“早思变计,莫如课归场灶”。即“于灶晒各户,具报产盐时,令场官查明确数,登记簿籍。至出售时,按照包数斤重计算,正盐每包应课若干,余盐每包应羡若干,抽收后即放令出场。其售之于商也,则令灶晒各户,合计成本饷项,共需若干,增价以卖,俾归本之外,尚有余息,不必问售之何商,任其自为交易。其商人转运,则凡粤盐应行口岸,皆听所之,但不侵淮、浙等处引地,则无所碍。如此变通改变,在灶晒之户,出课虽增,而得力亦赢,必所深愿。运商无需官设,则有赀本者,无论多寡,皆可货盐获利,熟不乐为。且无官商之名,则小民随处皆可买食,盐值必减,商民两便无过于是”。为使“课归场灶”之法易行,孙玉庭还制定了各项具体章程,如“宜合计每年引课共若干两,分别各场大小,匀派征收也”;“宜查核各场产盐数目,按包分摊也”;“各场盐价,应听灶晒各户,自行酌定销卖也”;“按包抽税,宜分别正余,以次征收也”;“征收课项,宜于场灶出售盐斤时,照数核收也”,[29]等等。
当然,由于各产销区域具体情形不同,一些官吏士子所提出的变通改革办法也不尽一致。如“河东盐行山、陕、河南三省,商力积疲,易商加价,俱无所济”。[30]乾隆五十七年(1792),冯光熊巡抚山西,疏请将河东盐课改归地丁。他说:“河东盐务积疲,惟有课归地丁,听民自运,既无官课杂费,又无兵役盘诘及关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请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陕西、河南课额,在于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属地丁项下摊征。”同时议定十条章程,主要有:“部引停领,免纳纸朱银”;“无许地方官私收税钱”;“盐政运使以下各官俱裁汰”;“移河东道驻运城,总管三场”;“三场仍立官秤牙行”;“盐政应支各款,各就近省藩库动支”等。经部议准,行之一年,大见成效,山西“自弛盐禁,民无摊课之苦,有食贱之利”。陕西、河南也都“盐充价减”。[31]其后,陕西巡抚方维甸亦奏请将汉中盐课改归地丁,“按里摊纳,与正项钱粮无异,并“拟于开征之前,将各县摊纳细数,刊入易知由单,并由司出示晓谕,务使各里周知,胥吏无从影射,自不至有派累闾阎情弊”。[32]但是,山西、陕西等地将盐课改归地丁,毕竟属于“因地制宜之道”,只可行于一时,而非长久之计。福建布政使裘行简即认为:“改归地丁之说,厚于富商,而薄于小民。”[33]甘肃按察使姜开阳更指出课归地丁之三大弊:“盖出课之民,不必皆贩盐之民”,贩者“于官课分毫无出,而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务本之农民,代之纳课,非重本轻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权不可以假人,今官不配盐,无人为之经理,游手无赖之徒,群集其中,趋利如鹜,是使之争也。急端既起,既不可以驱逐,又不易于稽查,积久生奸,必酿事变,其弊二也”;“甘省地瘠民贫”,若属“丰稔之年,尚可勉强催科,一遇水旱,流离转徙,正项钱粮,可以奏明蠲免,而盐课必不能减,将仍取之民,而民不能堪,将不取之民,而课无所出,其弊三也”。[34]因此,各地官吏在寻求更好的盐政改革办法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官府收税,听商民自贩的主张。姜开阳认为,当仿唐代刘晏治盐之法,于产盐之场灶设局收税,“一税之后,不论富商大贾、贫民小贩,听其随地售卖,除扣工本,得利甚多,人自乐为,脚贩日广,盐价日贱,无摊派之扰,无追呼之烦,无逋欠之忧,无赔垫之累,上不亏国帑,下不病闾阎”[35]。兰州知府龚景翰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认为“美意良法,莫善于此”[36]。福建布政使裘行简鉴于闽盐自乾隆末年以来,各项“正溢课银,悬欠至六十余万之多,催征筹备,皆属空文,徒有征课之名,而无收课之实,岂可不变通盐法,保卫民生”。因于嘉庆九年(1804)疏请复行收税法,“听民自晒自卖,自运自销,每盐一担,交税钱一百五十文,皆先纳课而后给单,凡商、鱼、船户,肩挑背负,俱任其在省南各府境内,毋论何场何地,自行售卖”。如此则“民无私盐之禁,场无商引之盐”,且“商课改为税课,私盐尽属官盐,无签商定地之烦,少缉私拒捕之案”,“于国课、官制、民生,均有裨益”[37]。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官吏士子提出的官府收税、听商民贩运的盐政改革主张,反映了18世纪清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试图摆脱封建桎梏的要求,不仅体现了他们对国计民生的强烈关注,而且为19世纪中叶的盐政改革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四、铜政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铜政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在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也不例外。乾隆五年(1740),以关于煤矿开采的讨论为契机,清初以来实行的矿禁政策开始松弛。乾隆八年(1743),大学士张廷玉奏称:“铜、铁、铅、锡之山,可以资民开采,供生民日用之需”,“请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除金、银之矿封固不准开采外,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以资鼓铸”[38]。自此而后,清代以铜矿为主干的矿业蓬勃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而达于极盛。特别是对铜矿生产,清政府采取减轻税率、提高官铜收购价、允许“一分通商”,即以产量的10%自行出售等措施,大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在铜斤主要产地云南,铜厂大者六七万人,小者亦万余人,铜产量也由乾隆五年的六七百万斤,猛增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一千二三百万斤。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矿业生产在极盛状况的背后,已然隐藏着危机,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吏治败坏,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云南铜政也开始陷入困难重重,入不敷出的境地。对此,一些地方督抚大吏不乏有清醒认识者。其中,尤以云南布政使王太岳所论为切中时弊。
乾隆三十六年(1771),王太岳出任云南按察使,次年擢布政使。在滇数年间,他目睹云南铜矿生产“官民交病,进退两穷”的状况,经过认真思考,于四十年(1775)上《铜政议》二篇,就云南铜政的现状、问题,以及改进的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太岳认为:“今日铜政之难,其在采办者四,而在输运者一”。在采办方面,“一曰官给之价难再议加也”。清代铜政定例,官给工本,招商、民承办,产量的20%作为课税无偿交官,其余80%由官府定价收购。其后为鼓励铜矿开采,清政府将税率降至10%,并允许以产量的10%自行出售。此即“每获铜百斤,准给商民通商十斤,抽课铜十斤,公廉捐耗铜四斤二两,余铜七十五斤十二两,给价收买”[39]。这些措施,初期确实促进了铜矿生产的发展。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府直接控制铜矿的生产和流通,矿业生产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以铜价为例,云南铜产量的绝大部分由官府收购,但定价却一直很低,初期每百斤仅银三至五两左右,其后虽经多次加价,亦不过六两四钱,远远不敷工本,造成云南铜矿亏本生产,负债累累,难以为继的状况。王太岳说,还在乾隆中,虽“各厂工本多寡不一,牵配合计,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兹峒路已深,近山林木已尽,夫工炭价,一皆数倍于前。而又益以课长之掊克,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来供亿,于是向之所谓本息课运、役食杂用,以及厂次路耗,并计其中,而后又有九两二钱之实值者。今则专计工本,而已几于此,厂民实受价六两四钱之外,尚须贴费一两八九钱而后足。问所从出,不过移后补前,支左而右绌。他日之累,有不可胜言者矣。夫铜价之不足,厂民之困惫,至于如此,然而未有以加价请者何也?诚知度支之藉制有经,非可以发棠之请,数相尝试也。且虽加以四钱、六钱之价,而积困犹未遽苏也。”其二,“曰取用之数不能议减也”。滇铜生产,自雍正以后,除例供京师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铸钱外,还供福建、浙江、贵州、广西、陕西等省局鼓铸之需。乾隆三十八、三十九年,滇铜产量达一千二百数十万斤,为“极盛之时”,“然而不能给者,惟取之者多也”。既有“京师之运额”,又有江南、江西以及浙、闽、黔、粤、秦、楚“诸路开铸”,造成云南铜矿所产愈多,“求之益众,而责之益急”的状况。他如大厂生产入不敷出,积欠累累,小厂地处僻远,难以统辖,再加上云南地区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都严重影响到铜政的正常运转。
针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王太岳在总结、参考前人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多筹息钱以益铜价也,通计有无以限买铜也,稍宽考成以舒厂困也,实给工本以广开采也,预集雇值以集牛马也”。特别是对铜价过低,京师及各省局取给铜斤过多的问题,王太岳指出,应适当削减各省局采买云南铜斤的数量,以裕滇铜;增加云南本省各局铸钱卯数,以铸息贴补铜价,即“以厂民之铜铸钱,即以铸钱之息与厂,费不他筹,泽不泛及,而此数十厂百千万众皆有以苏困穷而谋饱暖。积其吹呼翔踊之气,铜即不增,亦断无减。于以维持铜政,绵衍泉流”[40]。
此后,陆续有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觉察到云南铜政存在的危机,试图提出解决的办法。乾隆四十二年(1777),云南巡抚裴宗锡“疏陈铜务利弊”,集中提出了铜价不敷工本的问题。他说,每百斤铜价虽经加至六两四钱,然“取各厂人工、粮食、油炭时值逐款估计,折中牵算,矿沙积旺之厂,每铜百斤,犹少价银一两五六钱,若矿薄沙稀,则耗折更无底止。盖缘官买之初,定价本较他处最轻,而厂民不以为累者,当年岁需之铜,不过八九十万,后增亦不过三四百万,比于今日,十才一二。交官既少,私售必多,私铜既可肥家,官价自可不计。今官额日增,私售厉禁,厂民仅恃官本,势自不敷。原价既轻,虽叠加增,亦难给足,于是民则领后补前,官则移新掩旧,日积月重,遂成巨累”。对此,裴宗锡认为,与其采取现行“一分通商”的通融调剂之法,“不若明增价值”。即增云南本省各局鼓铸卯数,并将原“一分自售之铜”收回,“以作加卯,代为带铸”,将铸息一并分给各厂,如此则“大厂可增价一两五钱,小厂可增价一两。云南五金所产,生生不穷,厂户果能有利无累,获铜自可有增无减,厂欠可以永清,私铜可以永绝,散钱息以收铜息,厚厂利以清厂弊,计无便于此也”[41]。乾隆四十五年(1780),吏部右侍郎和珅赴云南查讯案件,回京面奏,亦曾言及铜价问题,谓“滇省铜斤,官价轻而私价重,小民趋利,往往有偷漏走私,地方官虽设法严禁,无如滇地山多路僻,耳目难周,私铜仍多偷漏,所以京铜缺少”。和珅认为:“向来定例,九成交官,一成通商。不若令将官运之铜全数交完后,听其将所剩铜斤,尽数交易,不必拘定一成。或商民知利之所在,竞相趋赴,丁多铜集,京运不致仍前缺乏”[42]。
上述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对铜政的看法和提出的种种救弊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国计民生和社会现实的关注。特别是关于铜价问题的议论,触及到了封建制度下矿业发展受阻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措施窒碍难行,致使云南铜政在乾隆末年以后,日形竭蹶,逐渐走向衰颓萎缩。但当时有识之士所作的思考,仍然给予后人以有益的启示。
五、人口
在封建社会里,人口数量的多少,可以说是衡量社会经济繁荣与否的标志之一。由于劳动力是古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土地耕种面积的扩大乃至社会财富的增长,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强调“养民”、“爱民”,重视人口数量的统计。据史籍记载,从西汉末年至明代晚期,我国人口数字一直徘徊在6000万人上下,增长幅度不大。清初经战乱之后,人口锐减,顺治八年(1652)为1400万人,十八年(1662)上升到1900万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全国在册人口也仅2460万人。此后直至雍正十二年(1734),除固定人口2460万人外,共“滋生人丁”1200万人,合计为3660万人,数字一直很低。乾隆五年(1740),一方面为了炫耀“盛世”,另一方面清政府开始觉察到人口增加的压力,感到需要掌握全国实际人口数字,以通盘筹划国用,因而下令各省查报户口实数与谷数。乾隆六年(1741)冬,“会计天下民数”,“大小男妇”达到1.4341亿,大大突破了历史上有书面记载的数字。对此,近年的研究者认为,我国明代以前的人口统计数字偏低,因为人们为了逃避赋税,采取各种方式隐匿人口。而清代乾隆以前的人口统计数,实际上是纳税人丁数,而非实际人口数,实际人口数应为纳税人丁的四至五倍。据此,有学者推测,明朝后期我国人口实际已达1亿以上,清代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数量已逐渐回升到明末水平,康雍年间约在1亿左右。至乾隆初年,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首次突破1亿大关。自此而后,人口增长速度一直很快,到乾隆六十年(1795)已达2.9696亿,远远超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人口的急遽增加,既反映了盛世时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力量的增长,也造成了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和不安定的因素。因此,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早察觉到人口问题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压力的,可以说是最高统治者康、雍、乾三帝。18世纪初叶,康熙皇帝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人口增长给国计民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于今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孟子曰:无恒产者无恒心。不可不为筹之也”[43]。在康熙看来,民生贫困,米价上扬,也都与人口增长有关。他说:“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朕洞瞩此隐,时深轸念”[44]。雍正在位期间,同样感到人口问题的压力,自谓其“临御以来,宵旰忧勤,凡有益于民生者,无不广为筹度。因念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欠,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45]又言“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余年,深仁厚泽,休养生息,户口日增,生齿益繁,而直省之内地不加广。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耳,而米价遂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望济于邻省。良田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此亦理势之必然者也”。[46]至乾隆年间,统治者更深刻地感觉到了人口遽增的严峻形势,乾隆说:“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日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朕甚忧之”[47]。不仅如此,乾隆还看到了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他在诗中写道:“谷数较于初践祚,增才十分一倍就。民数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48]。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问题,清代统治者相继采取了比较积极的对策,试图缓解人口增长给国计民生造成的压力。康熙根据“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的实际情形,于五十一年(1712)下令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进而推行“摊丁入亩”,藉以减轻广大民众的负担。康、雍、乾三帝都十分重视劝垦农桑,兴修水利,乾隆还开放矿禁,力图用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人口问题。
18世纪中国社会人口增长的实际状况以及统治者采取的一些措施,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思考,这就是洪亮吉和他的人口论。乾隆五十七年(1792),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洪亮吉被派为贵州学政。置身于民风淳朴的西南高原地区,目睹当地民众生计维艰的实际情形,忧国忧民的洪亮吉把自己对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他于次年撰写的《意言》一书当中。有关人口问题的看法和论述,可以说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洪亮吉首先对18世纪人口增长的情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人口增长的速度如此之快,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诸如耕地、房屋的增长却十分缓慢。洪亮吉以一个有屋十间、有田一顷的家族为例,对二者增长的不同情形作了比较分析,即“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十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则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已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即使“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据此,他得出结论:“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
洪亮吉还考察了人口增殖与物价的关系,认为人口越多,物价越高,民众生活越无保障。由于“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49]。为了解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问题,洪亮吉提出了两方面的对策:一为“天地调剂之法”,即“水旱疾疫”等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减员;一为“君相调剂之法”,“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50]。
当然,18世纪中国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对“盛世”时期人口遽增的社会现实表示忧虑之时,尚未能对此作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阐述,也还未能就解决人口问题提出更为有效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他们所指出的清代人口增殖的严峻状况,所论述的人口增殖与生产发展、生活资料增加二者之间不平衡的关系,却给予时人以及后世以有益的启示,并且在清代以及中国人口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乾嘉年间诸多有识之士对河工、漕运、盐政、铜政、人口等有关国计民生问题的思考,终于促成了经济之学的出现和经世派的产生,这就是陆燿及其代表作《切问斋文钞》。陆燿幼年家境贫苦,但他“奋励于学”,经举业入仕后,历任登州知府、山东运河道、按察使、湖南巡抚等职。幼时的生活经历和多年的仕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实际,了解民间疾苦。因而他既反对“闭户而谈天道,高座而说明心”的理学,又反对“揣摩应举,因循卑陋”的词章之学,对“挦撦细碎,抉剔幽隐”的汉学也持批评态度。[51]乾隆四十年(1775),陆燿以“立言贵乎有用”为标准[52],选择清初至乾隆年间“有关世道人心之作”,分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凡十二类,辑成《切问斋文钞》30卷。从而在18世纪下半叶明确树立一门经济之学,为嘉庆以后贺长龄、魏源等经世派的崛起以及知识界风气的变化,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综观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世主张,既是对盛行一时的汉学的反弹,也是对当时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反映。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然面临诸多问题,诸如汉学的狭窄,理学的陈腐,社会经济方面河工、漕运、盐政、铜政等大政的危机,以及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都使人们深切地感觉到,古老的中国社会内部,正积聚着空前的矛盾,酝酿着深刻的变革。正是这些或隐或显的矛盾和危机,警醒了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促使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救世的良方。经世主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与当时隐而复彰的今文经学以及方兴未艾的边疆史地学一道,汇成了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潜流。尽管它还十分弱小,也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它毕竟在学者面前重新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天空,为更多的学者走出汉学狭小的书斋,摆脱理学的束缚,直面现实,经世致用,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当然,由于社会的变化才刚刚开始,矛盾尚未激化,危机尚未爆发,因此,各种思想主张也未能十分成熟、系统,而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河工,或漕运,或盐政,或铜政,缺乏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看法,缺乏一种整体的、宏观的理论思考。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大多在传统的框架中徘徊,而较少提出扶植先进经济成分,因势利导,推进社会改革的方案。特别是乾嘉时期的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几乎都未能重视、倡导科学技术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陷。
注释:
[1]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100,中华书局1992年版,下册2440页。
[2][4]同上,2442页。
[3]同上卷98,下册2391页。
[5]同上卷99,下册2425页。
[6]《清史列传》卷23,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册1702页。
[7]同上,1705页。
[8]《清经世文编》卷99,下册2428页。
[9]同上卷100,下册2460页。
[10]《清史稿》卷127,中华书局本,第13册3770页。
[11]《清经世文编》卷96,下册2352页。
[12]《清高宗实录》卷1146,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3册16797页。
[13]《清史稿》卷128,第13册3803页。
[14][19]《清经世文编》卷47,中册1122页。
[15][18]同上,1099至1100页。
[16]同上,1139页。
[17]《清史列传》卷31,第8册2439页。
[20]《研经室二集》卷8,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上册578页。
[21]《清经世文编》卷48,中册1149页。
[22]同上,1160页。
[23]同上,1159页。
[24]《清史列传》卷34,第9册2636页。
[25]《清史稿》卷123,第13册3603页。
[26]同上,3609页。
[27]《清经世文编》卷50,中册1223页。
[28]同上,1251页。
[29]同上,1252页。
[30]《清史稿》卷358,第37册11337页。
[31]《清史稿》卷123,第13册3614页。
[32]《清经世文编》卷49,中册1203页。
[33]同上,1200页。
[34]同上,1198页。
[35]同上卷49,中册1199页。
[36]同上,1195页。
[37]同上,1201页。
[38]朱批奏折,转引自《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10页。
[39]上同,168页。
[40]《清经世文编》卷52,中册1283—1290页。
[41]《章学诚遗书》卷17,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161页。
[42]福康安《尚书额驸福手札》,转引自《清代的矿业》,上册160页。
[43]《清圣祖实录》卷240,第5册3209页。
[44]同上卷244,第5册3254页。
[45]《清世宗实录》卷6,第1册113页。
[46]同上卷64,第2册827页。
[47]《清高宗实录》卷1441,第29册21389页。
[48]《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四集》卷9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第7册703页。
[49]《洪北江诗文集·卷施阁文甲集》卷1,27页。
[50]同上,26页。
[51]《切问斋文钞·例言》。
[52]《切问斋文钞·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