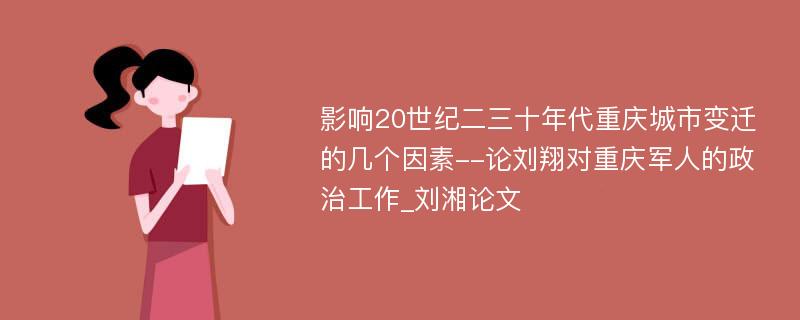
二三十年代影响重庆城市变迁的几个因素——论刘湘对重庆的军人干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几个论文,二三论文,军人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D67
二三十年代是重庆城市现代化历程极为关键的转型时期,笔者以学界较少关注的军阀政治与城市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认为20年代中期以后,重庆城市的地理区位优势因川江航运的发达而进一步凸现,城市商贸经济发展条件基本形成;刘湘军事集团对重庆的“军人干政”及其逐步实施的一系列颇具“现代”意义的城市建设,是重庆城市变迁的主要因素;21军在四川军阀中的绝对权威,使其驻防的核心基地——重庆得以在川军混战中享有近十年的相对“稳定”发展时期;卢作孚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觉醒及民生公司致力于沟通四川与外界的努力,震醒了“封闭”的川人,极大地冲击着四川军阀的“川人治川”政治理念。
一
对于20至30年代的重庆城市变迁和发展,“下江人”(注:“下江人”是抗战时期获得广泛认同的具有明显文化特征的社会群体。“下江人”以“上海模式”视野审视20、30年代的重庆城市景观的话语,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重庆城市发展变迁实况。)和西方人留下了较为丰富的话语。“下江人”说,“把成都和重庆比,恍惚等于把苏州与上海比”,“重庆是工商世界”(注:黄炎培.蜀道.第38页.上海开明书店,1935)。这个西南内陆独一无二的大商埠,其繁华程度“差不多可比上海的洋场”(注:黄九如.中国十大名城游记.第106页.上海中华书局,1941)。这里“中国大城市所有的洋货大概都有”(注:舒心诚.蜀游心影.第37页.中华书局,1939)。舶来品充斥市场,逐渐影响着市民的生活习俗,不仅“罐头之品,番餐之味,五方来会。烦费日增,欧酒巴菰输自海舶”,而且“城追西俗,级染市风,小食几遍通衢,远物以供日用”(注:向楚.巴县志.卷5.礼俗.1939(刻版))。
重庆城市“现代”意义的发展阶段始于1928年(注: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dit:Bniefs On Selected PRC Cities,Chungking.p.3.UnitedStates of Amenica,Washington:GovemmentPrinting Office.November,1975)。由此开始,兴建西部新城区,筹办城市的工业,改造和拓宽旧城区的街道等市政建设规划开始实施。随着邻近的江北、南岸区的城镇和乡村被划入新城区,城市空间突破了原来的城墙范围。与此同时,旧城区的市容为之改观,公路经过的地区,开始出现高层建筑,繁华区域逐渐由两江沿岸向公路两侧转移。重庆的进步“是如此的引人注目”(注:H.G.Woodhead edit:Yangtze And Its Problems.p.46-48,Shanghai:The mercury Press,1931),城市景观渐渐有了某些“现代性”的象征。经过扩建后的新市区“马路两旁十丈进深内之入口,已由二千余户增至五万余户,新建各式住宅,栉比连云,曾家岩一带,尤多军政大员富绅巨贾之别墅。汽车扬尘,顾盼其间,谁复念数年以前,此处犹为荒冢累累哉”(注:陆思红.新重庆.第22-23页.中华书局,1939),“近郊上清寺、曾家岩一带的清幽拔俗,实可与南京的鼓楼、陶谷媲美。于层峦起伏之中,大道四达,其间别墅如云,华楼掩映,一种壮丽阔大的气概,非寻常的猥琐都市所能及”(注:吴济生.新都见闻录.第14页.上海光明书局,1940)。抗战爆发后,重庆的都市气派十足,“诸如柏油马路,四五层的立体式大厦,影院,剧场,咖啡室,西餐社,油璧辉煌的汽车,如闪烁光芒的霓虹灯,凡都市所有者,无不应有尽有”(注:吴济生.新都见闻录.第15页.上海光明书局,1940)
30年代,重庆的新兴公用事业——自来水、照明、电话等建设也十分引人注目。1930年成立重庆自来水公司,次年向全市供水。1929年市政府极力筹划将电话办成公用事业,旋即筹集地方公债80万元,并与中国电器公司签订合同。由该公司提供设备和安装技工,到30年代中期共建成手动式和自动式电话3000余台(注:周勇、刘景修译编.重庆海关1922-1931年十年海关报告.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第36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1935年3月,成立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拥有1000千瓦发电机3部,日常发电约2000千瓦,基本满足了城市的照明用电和部分生产用电,“全市大放光明,顿成不夜之城”(注:吴济生.新都见闻录.第97页.上海光明书局,1940)。正因为有了“电力厂,自来水厂”,重庆“比成都现代化得多”(注:黄炎培.蜀道.第38页.上海开明书店,1935)。在“下江人”和西方人的话语中,一些“上海模式”的重要象征:高楼大厦、电影院、咖啡屋、西餐馆、崭新的轿车和新式的路灯等城市化物化指标在重庆都出现了。作为四川“最摩登折的”城市(注:葛绥成.四川之行.第30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重庆既“颇有沪汉之风”(注: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第164页.中华书局,1937),又“颇似香港”(注:庄泽宣.陇蜀之游.第166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简直可以说是“洋场十里俨然小上海也”(注:刑长铭.巴县及重庆实习调查日记.肖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39辑.台湾影印出版)。西方人称重庆“正在沿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注:Chungking News.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p.27.January,1929),“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新城市了”(注:Chungking Jottings.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p.40.June,1931)。
二
影响二三十年代重庆城市变迁主要有三大因素。
(一)川江轮船航运的发达使重庆在西南内陆的区位优势日益凸现,为都市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而民生公司为代表的川江航运业民族资本的成长与壮大又带动了重庆城市其他新兴产业的兴起。
四川省是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的相对封闭的区域,四周都是海拔1000至3000米的山地或高原。在这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区内,仅一线长江与外部沟通,重庆位于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嘉陵江为长江在四川境内最大的支流,四川盆地之中部及东部,尽为嘉陵江流域所经。长江上游(川江)以重庆划分为上下二段,重庆不仅是长江水系的交通枢纽,且“红盆最富庶地域这全部,皆为背后”(注: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343页.正中书局,1946)。重庆之西部及北部,属于川北丘陵地区,全部为白垩纪之赤色软质页岩所覆盖,夹以薄层之软质砂岩、水平重叠,此土壤,不仅生产力极强,且农业之盛,堪与成都平原媲美,“故其都市之繁荣,亦即应运而生”(注:袁著.重庆都市发展之地理的根据.四川经济月刊.第9卷5期.第55页.1938)。
“四川之交通,在铁路未兴起之前,当以川江为主要之大动脉”(注: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H1).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上海,1939),四川的物资可以通过与重庆通航的大小河流,源源不断地运到重庆,并由此输往长江中下游地区。民初,“蜀通”号成功开辟从宣昌到重庆的固定航班,迎来了川江轮船商业航运的新时代。二十年代中期,面对太古、怡和、捷江、日清等在华外资航业大资本,民生公司以颇有生气的管理机制与竞争活力,很快打破外资垄断川江的局面。1927年,民生公司的航线由渝合线驶入渝涪线,同年又增渝叙嘉线。第二年,增开渝合潼线,渝涪万线,不久驶入宜渝汉申线(注:四川月报.第1卷5期.第75页.1932),重庆成为川江航运水系的枢纽都市。1937年民生公司已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19182吨(注:重庆市档案馆.民生实业调查报告(1946年4月29日).档案史料与研究,1997年1期)。十年间,民生公司除以“发展航产以外,尚举办民生机器厂、三峡染织厂、合川水电厂,另投资于天府煤矿公司、固陵煤业公司、中华造船厂、四川水泥公司等事业”(注:高廷梓.中国航业.第2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民生公司以川江航运业带动城市新兴行业的兴起,推动了重庆城市现代工业的起步。川江航运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关系,客观上加强了重庆与周边腹地的经济联系,也扩大了四川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联系,正所谓“河流通航之距离既长,则都市附庸地之面积,亦随交通而得以扩展,盖贸易范围愈广,则都市之吞吐量愈大”(注:袁著.重庆都市发展之地理的根据.四川经济月刊.第9卷5期.第55页.1938)。川江航运业的繁荣还为重庆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1922年至1931年,川江上的蒸汽船航行大踏步地前进,占据了长江上游水运的重要地位。1936年,重庆共有中外轮船72艘,登记吨位为21666吨。以民生公司为代表的重庆民族资本的壮大与发展,也为重庆吸引长江中下游的资本、吸纳外地建设人才开辟了重要通道。
(二)刘湘21军对重庆的“军人干政”及其实施的一系列城市市政建设规划是促使重庆城市变迁的重要因素。
就政治学层面而言,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是转型社会权力均衡的统治范式。防区政治相当程度上填补了民初以来的四川政治权威真空;同时,20年代中期以后,刘湘集团在川军中的绝对权威又给重庆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条件。正如美国学者指出:“军阀时期既是混乱的时期又是有创造性的时期,在思想激烈斗争的背后隐藏着城市经济的增长和普遍的社会变革的进程”(注:(美)费正清,肖赖尔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第44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996)。刘湘自护国战争后迅速崛起,任川军第二师师长,驻扎川东九县,“跻身于四川军队一个独立系统的首领之列”(注:米庆云.刘湘兴亡纪略.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67页.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3)。1920年10月,四川督军熊克武与刘湘联合,进驻重庆。1921年6月6日,刘湘被川军各部将“推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注:川中将领通知推举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兼省长电.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2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不久就职重庆,开始“以重庆为事业基地”(注:吴祖沅.一、二军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36页)。20年代中期以后,刘湘凭借军事权威独占了四川“最具有战略意义”(注:Szechuan,Happy Military Hunting Ground,May Be United Shortly.By Harold R lsaacs,The China Weekly Review,Sep.5,1931)的防区——重庆市。1927年以后,四川的防区政治趋于稳定,军事冲突多发生在防区的边缘,重庆更是因刘湘集团的驻防而免于战乱,享有近十年的相对“安定”时期。
刘湘集团对于重庆的经济价值,早有认识,“查重庆位居长江上游,为西南巨埠,凡川省及康藏云贵所属商品,胥由此间出口运输,于国际市场颇著声誉”(注:重庆商务日报.1934-03-11)。刘湘的高级幕僚刘航琛指出,“重庆自不平等条约订立以来,已成为内陆一大河港,人口二十余万,相当繁荣。以万县为门户,设立分关,经济活动相当广阔,是四川全省经济的枢纽。贵州、湖南、陕南等地的物资,亦多在此集散。四川以此为应变根据地,甚属理想。刘湘得此良埠,兼控附近七十县市,如能扩大码头,加强设施,必可有为”(注: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第134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口述史料22辑.1990)。一位西方学者说,“重庆对于刘湘的主要价值在于税收”(注:Robert A.Kapp.Chungking as a Center of Warlord Power,1926-1937.In Mark Elvin and William Skinner edited: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p.156,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74)。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商埠,重庆为21军提供了丰富的商业税收财源。从成都到条约口岸重庆、万县,1933年280个沿河税收站,其中仅在重庆和沪县之间就有134个税收站(注:李明良.四川农民经济穷困的原因.四川月报.第2卷6期.1993)。重庆的地理区位优势,使刘湘得以对全省几乎所有的外贸商品征税。如四川的桐油产地主要分布在川东,其桐油出口率增加迅速,直接得益者是刘湘的21军;鸦片收入也是刘湘的重要收入,时川东的鸦片种植给刘湘带来特殊的经济利益;1930年鸦片税收占21军总收入的43.95%,1931年为32.57%(注: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第331页.商务印务馆,1936)。因此,有学者认为“刘湘的军队和驻地是建立在这个城市之上的”,来自重庆(也包括万县等其他贸易中心)的税收不仅使刘湘得以装备其庞大的军队,且可使其多变的部属始终忠于自己。如果没有武装占据重庆并增强势力,刘湘就不可能战胜其强大的竞争对手(注:Robert A.Kapp.Chungking as a Center of Warlord Power,1926-1937.In Mark Elvin and William Skinner edited: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p.17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74)。
正是重庆让刘湘集团获得了在四川其他任何地方无法享受到的个人投资和经营商业的利润,刘湘对重庆城市的治理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并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卷入了重庆地方政治经济建设。
第一,提高重庆的行政地位,将其作为21军“戍区首善地方”(注:陆军第二十一军司令部政务处.施政续编(止册).第51页.1934)。1921年刘湘决定以重庆为事业基地,设重庆商埠督办,重庆成为四川的次政治中心。重庆商埠督办公署的成立标志着重庆近代意义的市政机构的产生。此后,重庆的城市地位逐渐升级,1922年设市政公所,1927年改为市政厅,1929年正式建市,定为省辖市。重庆城市行政地位的升格,客观上为其发展准备了条件。
第二,采取“军人干政”的管理模式,以军阀政府的权威动员民间的资源进行城市建设。1928年21军成立政务委员会,开始了“军务、政务、财政”三点并重的干政模式(注:甘绩镛.如何改进今日之四川.四川月报.第2卷2期.1933)。刘湘军事集团直接以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身份控制重庆市政府,实现了对重庆市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权。战前十年间的重庆市最高行政首脑均为刘湘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1926年6月,唐式遵接任重庆商埠督办,7月,潘文华任重庆督办公署督办。1927年改重庆市政厅,潘文华任市长。1929年重庆建市,由潘文华任市长。1935年7月,张必果接任市长,第二年4月,李宏锟任市长直至抗战时期(注: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第563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这是典型的军人干政的政治构架。一位西方学者指出,“在1926年以后的十年中,是刘湘的权威在全省最高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重庆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的十年。刘湘和他的极有权势的部队下属深深地卷入了这些大多数的发展举措”(注:Robert A.Kapp.Chungking as a Center of Warlord Power,1926-1937.In Mark Elvinand William Skinner edited: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p.1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74)。为跟上“世界潮流”,潘文华任督办期间,商埠督办公署就委任对市政颇有研究的市政特派员“弛赴长江一带各大都市,详细调查市政之建设,及其发展,随时汇报回署,籍资借镜”(注:重庆商埠月刊.第9期.1927)以使“重庆市精神形式焕然一新,得与欧美各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上臻国际之光荣,下为各县之模范”(43)。从此时期重庆市政府发布的规章和实施情况看,其政策主要涉及:城市规划管理,如制订各种城市建设和合理布局计划;城市基础设施管理,如对住宅建筑、市政工程、公用事业的管理等;城市环境管理,如对清洁卫生、公厕设置、违章建筑、市场摊点的管理等;城市社会管理,如设施税救济、举办社会福利事业,对治安、消防、交通的管理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管理(注: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第53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在重庆市市政规划中,所有开辟新市区,拓宽城区老路,规划城区的公路系统,筹备电力厂,倡办自来水厂,及其他关于工程公有之规划,“均经先呈报陆军21军司令部核定”(注:廿四年度市建设计划.重庆商务日报.1935-05-09)可以认为,1929年的重庆建设市及其一系列市政建设的举措是“重庆开始了迅速地变迁和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注:J.E.Spencer.Changjing Chungking,The Rebuildof An Old Chinese City.The Geographical Review,p.47-50、29,1939)的重要因素。
第三,为获得军人干政的合法性资源,刘湘通过吸纳地方精英加盟军人政权,淡化军人干政色彩以增添其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同时加强与重庆城市金融界的联系,在相当程度上以民间资本参与重庆城市的经济建设。从某种意义讲,刘湘以政府的力量支持卢作孚统一川江航运业,是其获取军人政权合法性资源的举措关键。一方面,刘湘集团通过支持卢作孚民生公司为代表的城市新兴工商业部门,获得重庆绅商的广泛认同;另一方面,作为21军的重要官员,卢作孚、保北衡等人不仅“在社会地位上,其言论殊为军人所重视”,且“冀有以一洗四川各界陈腐昏庸之空气,而稍收脚踏实际之建设功效”,时人称“川者执政者有若卢君者五人而四川治,中央执政者有若卢君者十人者而中国治”(注:新世界.第58期第4页,1934)。可以认为,刘湘与重庆绅商的关系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刘湘集团的政治军事命运,刘湘在对重庆公众的演讲中,多次表达了其小心翼翼的谨慎态度,以避免引起民间社会对军人干政的“反感”(48)。实际上自进驻重庆后,21军实施提盐税的筹款办法已经激起重庆市工商金融界的强烈不满,为了在重庆建立稳固的统治,刘湘开始巧妙实施“枪杆子与洋钱的合作”政策。从1928年起,刘湘已经建立起与重庆金融界及商界的较为“和谐”的伙伴关系,重庆市总商会的会长及副会长赵资生、汪云松、曾禹钦、李鑫等人与刘湘集团都关系密切。刘湘说:“商人怕军人,因为军人有枪杆子。其实,军人也怕商人,因为商人有洋钱。商人没有枪杆的保护,便感到有生命危险,而军人没有洋钱,也就没有饭吃,同样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希望枪杆子与洋钱合作,把市面搞好,彼此都有利”(注:康心如.回顾四川美丰银行.重庆工商史料.第7辑.重庆5家著名银行.第34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聚兴诚银行在历次的军阀派垫中,成为重点搜刮的对象,1927年该行已为军阀垫支150余万元,超过该行登记资本总额的一倍半(注:杨氏家族与聚兴诚银行(未刊稿).第177页;存重庆市工商联,转引自唐学锋未刊硕士论文“刘湘与重庆财团的兴起”(1987年4月)第7页)。为了逃避军阀派垫,聚兴诚银行的总经理杨灿三曾将总行管理处迁至汉口。刘湘任用刘航琛实施财政改革后,杨灿三又将总行管理处迁回重庆,他说“重庆金融界和21军的利害关系太深,不妨暂与合作”,“在21军防区内作商民,实属万幸”(注:康心如.回顾四川美丰银行.重庆工商史料.第7辑.重庆5家著名银行.第34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当然,重庆绅商对于刘湘的实力也看在眼里,“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不愿意四川长期陷于内战,以致影响业务的发展,而刘湘当时在各路军阀中居于首位,又长期盘踞,我们希望也支持他统一四川,为他庞大的军费的缓急相通而效劳,我们也是愿意的”(注:康心如.回顾四川美丰银行.重庆工商史料.第7辑.重庆5家著名银行.第34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刘航琛道出了重庆市商民与刘湘集团的特殊关系,刘航琛说:“我的钱有许多应该是你的,因为你信任我,工商界人士均对我另眼相看,以为非我参加即无新事业兴起”(注: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第140页),“论权力,我虽无直接管理(向重庆市绅商征借钱款——作者注)之权,但有数万支枪为后盾。”(注: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第134页)因此,刘湘集团驻渝期间建立的军—绅关系,对重庆城市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三)三十年代中期的川人觉醒是重庆市重新走向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
川江航运沟通封闭的四川与外界的联系,同时也启迪了川人的觉醒。民初,川江轮船航运的开辟使“重庆已不再像从前只有依赖民船作为唯一的交通工具才能达到的遥远城市”(注:周勇、刘景修译编.重庆海关1922-1931年十年海关报告.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第33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重庆首先与长江中下游的城市联系密切。同一时期,重庆与四川各地的陆路交通也得到发展,尤其是30年代初期,航空运输的出现,成为重庆交通运输史上的里程碑,时“自沪赴渝可以直航,自渝至蓉又有飞机可乘,故不独迅速,且甚舒适,若不观三峡风景,则乘巨机由沪至蓉,朝发夕至,几如自沪至京一游,诚缩地有方,蜀道何难矣”(注:庄泽宣.陇蜀之游.第166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加之30年代中期开始川局较为安定的局势,川江“来往旅客日见增多,以前仅川人来往,外省者不及十分之一,今则各半”(注:庄泽宣.陇蜀之游.第138-139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交通革命打破许多观念,飞机之促进文化与政治,殊有不可思议之威灵”(注:季鸾.入蜀记.国闻周报.第12卷第19期.1935-05-20)。“外省人”、“下江人”开始进入四川,来自沿海的城市文明对重庆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无疑是对自民初以来“川人治川”军阀封闭自为的政治理念的挑战,于文化层面上启迪了川人的觉悟和地方精英的现代化意识,为重庆的城市现代化积淀了一定的素养。
在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的推进力量中,知识分子特别值得注意,“在一个传统社会中,与外部的现代性最早发生接触的往往就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见识与智慧,使他们对现代化挑战有更强的领悟力,同时也更清楚原有体制的缺点和弊病。因此,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知识分子往往成为现代化的最早呼唤者。”(注:孙力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2))卢作孚的现代意识是近代重庆人觉醒的突出表现,“中国当前的途径非常明了,不管是社会组织亦或是物质建设,只有迈步前进,追逐现代或更超现代,不然便会受现代的淘汰”(注:卢作孚.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1934年8月2日.卢作孚集.第242、4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显示了重庆人现代性意识的启蒙,而“到底如何才可以促起人们的觉悟?唯一的方法,便是拨开现局,使人们伸出头来,看看现局以外,还有一重天地,不误以为现局便是天地。如果人们长埋在现局中间,纵然觉悟了现局之坏,然而不知道如何才好,永远不会从现局中间自拔出来,跳到另外一重天地里去。因为他们从没有见过另外一重天地”(61)思想既是其毕生致力于沟通封闭的四川与外界商业行为的理论基础,又为重庆的城市发展指出了现实途径。可以认为,地方精英的现代意识对重庆发展具有深刻意义。
三
就后发展地区的现代化发展逻辑而言,现代化早期阶段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动员有限的现代化基础与资源,是必经的过程。刘湘集团以军人政府的权威动员民间各种资源,客观上推动了重庆城市的发展,显示了“权力政治”和“非经济因素”,在近代重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巨大超经济作用。但是,“中国近代军阀的军队不是现代国家的军队,军一绅政权也不是现代国家的政权”(注: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15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一方面,军人干政体制下的变革举措,以拥有充分集中的政治权威为后盾,以及享有这种权威的合法性为前提;另一方面,军人政权自身无法克服的转型特征,即封建性、掠夺性大大降低了其政权的权威合法性。刘湘21军对重庆工商业实施的苛捐重税,成为妨碍重庆发展的主要因素。据1930年的重庆海关报道,“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成为贸易发展的最大障碍,致使很多过去一直以重庆为转运中枢的货物逐渐转由他处运输。”(注:H.G.Woodhead edit:The China Year Book.p.203,Shanghai,1932)到1931年情况仍然十分糟糕,“整个天府之国正逐步受到货物运输过程中过分繁重课税的不利影响,……尽管商业团体一再请愿,过高而复杂的内地税制仍继续行之有效。”(注:周勇、刘景修译编.重庆海关1922-1931年十年海关报告.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第44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加之防区制度人为割断重庆与周边农村的天然经济倚靠关系,到1934年底,城市经济由于周边农村经济的崩溃而停滞不前,重庆城市原有的经济资源几乎消耗殆尽,重庆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