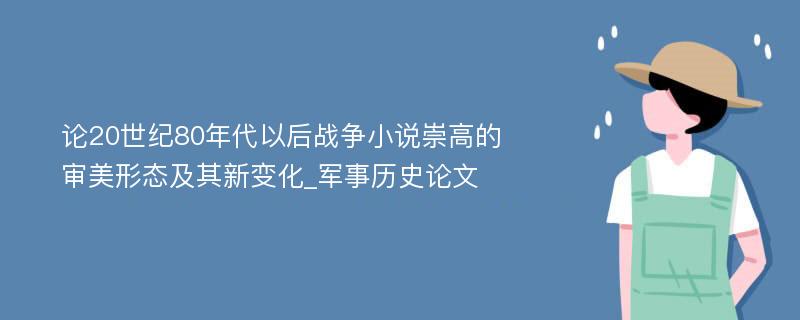
论20世纪80年代后战争小说的崇高审美形态及其新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崇高论文,形态论文,年代论文,战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10)04-0038-06
崇高是“十七年文学”的时代主潮,在共和国初期的战争小说中表现得更为鲜明,这也是由战争本身的特质及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所决定的。于战争中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取得战争胜利的最初时段里,必然要求其战争文学奏响出激昂的旋律、胜利的凯歌。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形态在战争小说中的位置及其内部的质素相应地发生了变更,产生了新变。
一、弱化战争场景,凸现人的心灵崇高感
对战争小说来说,气势恢弘的战争场景是构成崇高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与上世纪50-60年代的战争小说追求大构架、大情势相反,20世纪80年代后,战争场景趋于弱化。以李存葆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对战争的思考、对战争的态度变得比以往深邃、冷静,战斗过程、战争场面、胜负结果在小说中的比重已不那么重要,有的仅削弱为作家传达心智的一种背景。观念的转化是显见的:不再单纯地记录战争的场景、胜利的画面、欢欣的泪水,而是冷静地反思战争给人的情感与命运带来的影响,考辨战争与人之间那种复杂错综的关系,辨析战争历史与社会现实对人生历程的磨砺与变化。从强化战况的再现到弱化战争场景的描写,意味着战争小说视点的新变,意味着战争小说审美兴趣的调整与转换。
应该看到,战争场景的弱化并非是战争小说崇高艺术魅力的退化,而是更为灵动的深化。80年代后战争小说追求崇高主要从人的心灵中追求崇高感,这其中又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表现高尚而充满理性的崇高。崇高总是与高尚的精神境界同时又是与理性之光联系在一起的,高尚的精神世界常常激发起人们心中敬佩与崇仰的感情。《高山下的花环》中韩玉秀、梁大娘即使步行来到连队也要还清烈士的欠帐,即使自己再苦再累也要支持、理解梁三喜为部队、为国家所做的一切的崇高襟怀,使其获得了振聋发聩的艺术效应。《凯旋在子夜》重在描写童川、林大林在枪林弹雨、生死攸关之时,对军人的荣誉、国家的责任、自身的价值的感怀与思索。两人有情恨却又在临阵前成为上下级的战友,他们各自不同的坎坷经历,使他们的精神世界自始至终都充满着情感与理智、国家与个人的矛盾冲突。小说通过他们之间的彼此了解,传递互为内疚的精神世界,终于共同渡河执行任务,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的感人描写,告诉人们:战争检验人心,战场考验灵魂。在生死考验面前,往日个人的恩怨无足轻重,祖国的安危、人民的幸福、战友的生命才是维系于心的情怀。
这一崇高的情感,洋溢在作品的始终,强化了小说的崇高气势。国民党人士在我们的文学中一向是作为反面人物或者配角出现的,但在《战争和人》中作家王火完全以抗日战争作为背景、国民党民主人士作为主角,通过童霜威的人生历程与心灵的选择,形象地说明了“历史向人心生成”的必然趋势,流贯于全篇的不屈的崇高的民族精神,犹如一股暖流在作品中涌动。小说以战争为背景,将童霜威这样一个身世独特、经历复杂、性格别样的国民党高级边缘官吏,投入到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揭示他人生的苦闷、彷徨、徘徊、挣扎、探索之旅,通过他几经迷惘终于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向何处去、人民向何处去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选择了正确的符合历史走向的心路历程,雄辩地证明了人必将在时代中冶炼、在理性中锻造、在历史中升华这一崇高的主题。
由于地位与环境的影响,童霜威对于抗日顾虑重重,又怕军事失利,又怕生灵涂炭。有苟且偷生思想,却无决战决胜信心。他正直,也有正义感和爱国的感情,可又搀杂了世故和圆滑,常常妥协、迁就。尽管如此,坚守民族大义和做人的节操是童霜威毫不动摇的人生之本。他改名换姓做寓公,无论是汪伪集国威逼利诱还是日伪特务们绑架软禁,他一概不予理睬。童霜威虽未以投笔从戎的方式表达他对抗战的决心,但他以崇高的民族气节捍卫了人生中最可宝贵的精神情操。以自由之身、正直之心,走上了一条对国家民族和百姓有利的路。人生即选择。对于童霜威而言,人生即是自由,人生即是气节,人生即是民主,人生即是由历史生成、顺应时代走向、指向未来意蕴的崇高的心灵选择。
不过,20世纪80年代后的战争小说在表现人的崇高感时,人的崇高精神已从空中降落到人间,人物的思想境界丰富而可触,既展示人物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奉献精神,却又让崇高的品格滋生在现实的土壤中,萌生于生活中人的合理的需要与付出,以及人自身对合理利益的维护与索取上。同是奉献者,《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靳开来的精神境界和审美内涵与20世纪50-60年代已有显著的区别。梁三喜是背着沉重的经济包袱和家庭拖累而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的,那一尺见方的欠帐单及其处理方式,闪现出新时代传统型军人在家国同构的历史使命中,坚韧不拔的毅力,伟大高尚的胸怀。他“人死帐不能死”的崇高精神,宁肯自家受累也不肯增添国家的负担、损害战友的利益的高风亮节,虽也透出压抑与沉重感,但更激起人们崇高的敬意。童川上战场本是想转移生活的不幸,但在阵地上看见战友的牺牲后激起他仇恨的怒火,他开始思索他们这一代受过挫折的年轻人应该怎样捍卫祖国的荣誉,接受生与死的考验,而不应停留在个人的恩怨得失上。《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是个战神,但小说却从他与乌云的婚姻写起,将个人需要的必要索取与军人本职的崇高奉献结合起来,使崇高更具现实感。身为军人,国家需要就是个人的需要。丁贵(《师长向士兵敬礼》)、江涛(《穿越死亡》)等接到出征的命令后,毫不犹豫地肩负起祖国的重托。他们反复推敲作战计划,不仅争取打胜,更要争取打得漂亮,以最少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当然,也不必讳言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对高一级职位的渴望,他们全心打好一仗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肯定自身的价值、提升自己的职务增添更有分量的筹码,这是每个职业军人所应有的荣誉感与使命感。小说将与他们有着同样想法和能力的人拉到同一起跑线上,让他们共同为崇高的也是现实的目的而冲刺。这里有权谋,但不惟权谋,最终还是以战斗的结果为衡量的主要依据,尽管惊心动魄,但积极向上的美感,还是升腾起崇高的品格。
与现实的目的相联系,追求人的崇高心灵又向世俗化发展,即摈弃神化净化的崇高境界,既展示人的朴素而崇高的精神指向,也展示人的世俗情感、本真愿望等属于普通人理想的精神世界,敞开了丰富的人世化的美学境界,审美感受也大为丰富。人是现实中的人,即便是人的崇高的精神需求也必然呈现出复杂性。但在十七年的战争小说创作中,主人公往往是一架单引擎的“战斗机”,以“神”的身份起降在干巴巴的只供圣人降落的机场里。《上甘岭》中,战士徐成彬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表达的是对祖国的忠诚,张文贵看到徐成彬母亲和他弟弟一家的合影涌起的不是感伤、痛苦,而是鼓舞,是政治利益的伦理认同,是净化的崇高。20世纪80年代后,神的精神世界自然蒸发,人的精神世界日益敞开并趋向丰富,人的本性中那些人世化的高尚的精神质素得以自由飞翔。靳开来在献身前表达的是对妻儿的眷恋与告别,涌起的是悲情,是痛苦,是人之常情的自然释放。它一方面升至崇高的精神王国,一方面回归人世化的境界。这种形象产生的美感,既使人感奋,又催人泪下。它标志着人性中那些为了实现各种需要而潜在的崇高的质素,在作家笔下得到了真切的作答。兵团副司令秦震(《第二个太阳》)唯一的女儿白洁是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的情报员。在革命即将胜利之际,秦震得到了女儿被敌人绑架失踪的消息,这位见惯了流血牺牲的将军,虽然能够理解革命就意味着牺牲,但面对爱女的失去,依然抑制不住悲痛。小说写他那心如刀绞,冷汗淋漓,仿佛跌入了万丈深渊的感伤的心情,真实可信。读者对赵蒙生(《高山下的花环》)产生愤怒、理解、同情、支持、肯定等多重感受,就建立在他曾以“曲线调干”的方式下连队,而后又在临阵之际想充当逃兵,最后还是走上战场并以英雄的姿态出现在战场上的既世俗又崇高的“曲线”轨迹上。人们不会指责汉家女(《汉家女》)当兵先是为吃饭,后为调干,再为工资级别这一世俗而实在的人生理想,也不会指责她听说要上前线,满脸的无奈与宿命而没有丝毫的神圣与庄严的使命感,更不会指责她留给丈夫的录音和不幸成为遗书的信,说的全是儿女情长,枕边絮语,没有回肠荡气之势,但人们同样对这位手勤眼快、不知疲倦、默默奉献的女兵、母亲、妻子,献上诚挚的敬意。人们同样也不会指责父亲(《跪乳》)的愿望是儿子能够平安归来,临上阵前让儿子给菩萨磕头以保佑平安,归来后认为这是自己天天给菩萨说好话的结果的迷信色彩,更不会对母亲(《跪乳》)一生的理想就是儿子、孙子健康地成长,为此,含辛茹苦,终日操劳没有任何微辞,母亲平凡的一生是伟大而崇高的一生,她“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高尚情操,是人类最宝贵最瑰丽的品格,她给人的感受是愉悦,是心灵的激荡,是灵魂的共鸣。
二是表现一种亚崇高的心灵境界。所谓亚崇高是指人物追求的目的有崇高的一面,但人物思想行为的质地却显得较为复杂。这是战争小说崇高审美形态的一个新质。这一新质的出现是由小说《生命通道》中的苏原引发的。按照往常的模式,苏原为我方的医务工作者,不慎与妻子被日本鬼子抓获时,或者拼命反抗、或者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或者被游击队机智救出,如若不然则在狱中受尽折磨,宁死不屈(牟青的命运更为悲惨)。这样,苏原活下来时人们对他充满敬意,读者也觉得理应如此,释然于怀;牺牲则激起人们对英雄的景仰,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但一切都不是这样,一切预想的都没有发生,一切来自于人们惯性的审美期待与阅读心理不仅没有发生,而且几乎连发生的迹象也没有(偶尔出现的牟青逃跑时遭二名日本兵抓获正要施暴的情节,也因卜乃堂解救而化解)。应该说,现在人们对于书生苏原与他的妻子被日本人俘获时没有任何反抗,抱理解默认的态度了,这来自于对审美对象真实性的心理体验。由于理解也就产生同情,对他们遭受的委屈产生同情(牟青就曾为卜乃堂的一番汉奸理论流露出些许同情),仇恨心理竟不知不觉减弱并隐遁起来。奇怪的是,日本军医高田向苏原通报“生命通道”计划并让他看了证人后,人们反而希望苏原留下来协助高田一起执行“生命通道”计划,抱怨牟青不理解苏原的难言之隐,对他答应为地下工作者送情报感到宽慰,对他毅然决定与高田军医合作救老马的强烈、执著的意念,更予以支持,算是长出一口气——苏原总算是能为抗日战争做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工作了。无疑,苏原的追求是崇高的,是为抗日尽其力所能及的力量的。正当人们与苏原一起沉浸在抢救成功的喜悦中时,牟青的出逃又让人涌出惊诧与同情、无奈与怜悯之心来,毕竟苏原是为了牟青才放弃了无数次逃脱的机会的。这时人们强烈支持苏原单独逃跑,认为机不可失,但高田希望他为了老马再等半个月时,人们又祈祷时间尽快过去,成功尽快到来,对于苏原此时的痛苦再次寄予深深的同情。苏原最终被钉在汉奸耻辱柱上的结局,不仅未能释怀人们心中的快感,反而令人更感压抑,更感悲叹。苏原为抗日工作做了实事,甚至有功于历史,但没有佐证,只得在历史的帐册上留下无法洗清的恶名。对于苏原,人们无法用以往的审美观单向地投之以情感,而是在复杂的感受中不断地揣摩或修正应有的审美判断,恨时恨不起来,爱时爱不起来,高尚中潜存无奈,软弱中透着坚韧。更让人不知所措的是,这不是一部以悬念取胜的小说,你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无法松弛下来。这或许正是作者所追求的审美效应。
二、悲怆、凝重与复合多样的艺术基调
战争小说一旦终止了盲目的乐观与廉价的热情,走上痛定思痛的反思与创新之路后,崇高战争小说的审美基调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首先,作家们不再将小说的立意单独地集中在对胜利与新生活的向往和诗意的构寻上,而是多方开掘审美对象的崇高审美基调,在开放与多义性的主题中引发崇高审美基调的新变。崇高的审美基调就其根本来说首先出自作品的主题,多义的主题自然导致崇高审美基调的多向性。《高山下的花环》的题记含蓄而醒目,它既点出了指战员们的身份、地位、事迹,又表达了作者对英烈们崇高精神的敬意;既暗示出作品的主题,也奠定了全文悲怆而崇高的基调。但作者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由此深入,以人物的悲剧性强化作品凝重的色调,以人物灵魂的提升击响振奋的主旋律。于是,一曲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深沉而悲壮的崇高乐章,在读者心中轰然奏鸣了。“突然间,我似乎看见白昼上又加上了白昼,仿佛万能的神用第二个太阳把天空装点起采。”这是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中描绘他从地狱经过净界到达天堂后所看到的景象,它作为刘白羽《第二个太阳》的卷首语,准确地表达了刘白羽和无数革命者经历了从奴役到新生后涌起的激情,形象地表明了新中国屹立于世界后所放射出的璀璨的光芒。但是,当太阳还沉没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时,“历史受着磨难、生命受着磨难、太阳受着磨难。谁要承受最初一线黎明的欣喜,谁就不得不先通过炼狱的熬煎。”也只有经过炼狱之火,才能到达天堂之门,也才能博取最后的辉煌。这也是革命的哲理诗。小说以此交织着两种旋律:一是已看到胜利曙光的生命的律动,一是黎明前的黑暗的痛苦煎熬;一个预示胜利的来临,充满着欢乐,一个暗示革命的代价,充满着感伤。欢欣与哀伤相交织,喜悦与痛苦相震撼,悲喜相成的崇高美,构成《第二个太阳》的总基调。此外,《战争和人》、《红高粱》等也因多重的美学追求而显现出多样的崇高基调。
其次,作家们深刻的忧患意识也促动了崇高审美基调的新变。20世纪80年代后,国门再次打开,面对现实,人们不再用单一而纯正的崇高表达简明向上的审美基调,而是在崇高的心灵中铸入作家对历史的思索、对现实的忧患,使崇高的审美基调透出多样的色彩。日本侵略者曾给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欠下了累累血债,但几十年来他们却少有忏悔意识。中国远征军曾在缅甸英勇地抗击了日本军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但几十年来我们却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日本人不断祭奠他们的亡灵,中国人却一再淡漠英灵的存在。日本忠勇将士的后人受到优抚,中国浴血奋战将士的后代却遭到牵连,命运多舛。人们指责日本人不敢面对历史,实际上中国人更善于健忘曾经发生的一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正视历史意味着理智与觉醒。面对历史厚重的一帷,面对历史遮拦的一幕,《大国之魂》的作者邓贤试图擦亮曾被愚昧、麻木、疯狂和偏见锈蚀的心灵,让中华的精灵复活起来,让历史铭记一代青年曾用热血和生命谱写的中华民族的悲壮凯歌,让历史从这里走向未来。他要写出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写出中华民族锻造魂灵的脊梁,写出中华民族永不屈服、以血肉之躯迈向历史彼岸的“大国之魂”。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使作者在祭奠被遗忘的抗日战场时,庄严而神圣,敬仰而肃穆,谨严而客观。寓史于思,透力渗血,使崇高美显示出朴实遒劲又庄严肃穆的色彩。《跪乳》的作者岳恒寿系情思于历史,托历史以忧现实的创作思想,使作品在情浓意切中流露出对现实淡淡的忧伤,使崇高美糅进了古典的温柔敦厚的和谐美。作家对前辈充满敬意,但她更对革命造成人的个性畸形发展的现状忧心忡忡。她写英雄的伟岸,也写英雄的偏执;她写革命的崇高,也写革命的反崇高,她最终确定以悲剧性的崇高作为《英雄无语》全书的总基调,是她对人性、暴力、历史、现实更深刻的体悟。
第三,复合状的崇高品质的人物也分解了原有的单向的崇高基调。随着人世化美学境界的敞开,崇高美学的人物殿堂涌现了大量的现实中普通的带有亚崇高、悲剧性、优美态的复合型崇高人物。他们各自曲折多变的运行轨迹,自然使作品呈现出多色调的美学图式。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描写1948年秋,50名孕妇因不便与大部队一起行动,便组成了一支特别行动队——孕妇队,单独转战于渭河平原上。这些仅有15名战士做警卫的未来的“妈妈们”,在队长陈大曼的带领下,硬是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战胜了敌人的追杀堵截,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她们以牺牲全部警卫战士的代价,换来了50个与新中国同龄的新生命。小说的崇高寓意确实有些直白而功利,刀斧痕迹也很明显,但人物的塑造还是有其开拓之处。陈大曼13岁参加红四方面军,战争的砥砺和被俘的经历,打磨出她粗犷与直率的纹路,将其脱胎为一个男性化十足的女军人。敌人的虐待和凌辱,自己人的歧视与抛弃,更在她心里烙上了永生难以愈合的创伤。她变得冷酷而无情,甚至产生了畸形的心理:不再需要爱情,痛恨、仇视一切男人,她在集市上公然一剪刀剪掉布娃娃的“命根”,就是她畸变与仇恨心理的一次大爆发。但是,命运却让她再次接受炼狱的考验:为那些沉浸在爱和做母亲的自豪中的女神们,充当生命的“牧师”,为她们祈祷,为她们拨散战争的硝烟,何况她原来的恋人的娇妻孙志坚还在其中,这确实再一次刺激了她痛苦而如铁的心灵。其他如受出身牵连而遭受审查的刘雪鸣,牺牲了丈夫的李水莲,为革命失去两个孩子的“红色太太”冰姑,受封建裹脚之害的大脚婶等负重前行的女兵们,虽然她们都在战争的烈焰中升腾起崇高的精神之火,但她们多重而复杂的心灵煎熬与搏战,使小说的审美基调更为丰富。《红高粱》中“我爷爷”余占鳌“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原生态的多重属性,已非单一的审美基调所能指向。其他如梁大牙、靳开来、石二旺、高金豹、苏原、卜乃堂等复合状人物的出场,都使崇高审美形态的战争小说呈现出多重的审美基调。
最后,叙述策略与叙述视点的变化也带动了崇高审美基调的调整。以往,作者是以仰视的角度去烛照革命者的崇高品格,20世纪80年代后很少采取仰视角,而多是平视或俯视。如《我是太阳》、《英雄无语》等以审视的眼光摹写父辈的一切。这样,少了崇拜之情,多了平等之心;少了外在的激情,多了内在的潜流;少了冲动的宣泄,多了冷静的审视;少了行动的铺张,多了心灵的搏战;少了单一直观的呈现,多了复杂曲折的遮掩等等,不一而足。总之,20世纪80年代后的战争小说难以像50-60年代那样有大致相近的叙述策略与叙述视点,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有不同的叙述方略,读者也可从不同的角度产生不同的感受。也正是从这里,我们欣喜地感到,战争小说的崇高审美基调已走向多元、走向开放。
三、严正、庄重与富有力度、气势的叙述语言
崇高的美学风貌在语言上也有其相应的要求,即:严正、热烈与富有力度、气势的叙述语言。这一语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表现崇高的战争小说中颇为普遍,也形成相近的美学特征:语义庄重明晰,彰显阳刚之气;语汇刚性,富有硬度与力度;语态严正、热烈,凸现时代激情;语调昂扬、奔放,富有雄壮气势;语体富有宏阔之感,语言中洋溢着作家的仰慕和敬重之情,呈现崇高美的气象。
试比较以下几部代表性作品的结尾:
北方,万里长城的上空,突然冲起了强大的风暴,掣起闪电,发出轰响。风暴夹着雷霆,以猛不可挡的气势,卷过森林,卷过延安周围的山岗,卷过中华民族几千年征战过的黄河流域,向远方奔腾而去。——《保卫延安》[1]509
军首长们,许多指挥员们,红旗排、红旗班的英雄战士们,屹立在巍然独立的沂蒙山孟良崮峰巅的最高处,睁大着他们鹰一样的光亮炯炯的眼睛,俯瞰着群山四野,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崇高的、集体的英雄形象。——《红日》[2]537
站在大道边,站在毒日头下欢送部队的人群,个个喜眉笑眼地在欢呼,欢呼声震撼着碧绿的原野;欢腾的锣鼓声,有节奏地响着,响彻了蔚蓝的天空。排山倒海的铁的子弟兵团,排着三路纵队朝着正北,朝着保定城,朝着平汉铁路,朝着胜利,大踏步地前进!前进!——《敌后武工队》[3]481
也许是因为她(指徐芳)心情激动的缘故,今天的琴声显得格外激越和高昂,立刻又把大家带回到那严峻的战争年代。大家好像又看见漫天飞舞的雪花,交织着朝鲜战争上的火光。郭祥宛如处在战斗前夕一样,力量顷刻充满全身,恨不得立刻冲上前去,要求一项最繁重、最艰巨的战斗任务……——《东方》[4]1160
作品不同,语义相近:革命征程漫漫,任重而道远,真正的革命者永不满足眼前的胜利,他们将永远以饱满的热情,满怀信心地迎接新的挑战,他们将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语汇上:“冲起”“强大”“风暴”“掣起”“雷霆”“猛不可挡”“卷过”“奔腾”“屹立”“震撼”“响彻”“排山倒海”等一系列刚性的动词、形容词和具有大气象的名词的使用,使全段极富力度与硬质;语态上:充满着对正义之师锐不可挡的气势的热烈颂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极富时代感;语调上:激越、向上,欢快,结句落脚在重音字“去”“象”“进”“务”上,增添了壮美的气势;而整体上壮阔之感更使全段升腾起崇高的美的气象。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作家美学观及语言观的变化,小说的语言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绝大部分作家清醒地意识到语言是个性化写作的技术标志,是浸透着个人感觉的艺术体验,是作家主体创造能力的直接展现。因而在写作中,语法、语义、语式、语调、语态、语序等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也使得人们试图用某种固定的模式涵盖某类审美形态的语言模式就显得非常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语言走向本体与自由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正表明崇高美学形态的小说语言已进入觉醒与创造的时代。
人的审美感受是丰富多样的,对崇高美的战争小说也是如此。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与创新,崇高美的战争小说成绩可喜,变化显著,日渐丰富多彩,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创作中所暴露出的一些倾向,还是令人感到忧思。如战争场景的弱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作品出现虚化战争场景的迹象,无形中也模糊了题材的界限,虚化了崇高的意味。这是战争小说艺术视域的扩展还是矫枉过正,有待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又如,人世化精神世界的艺术探索,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俗化的艺术趋向,粗俗、粗鄙、原始野性等人的感性负分子,在“原状态”的旗帜下纷纷扩张,到了无粗不成文、无俗不成人,无陋不成形的地步,甚至认为英雄的本性理应如此。这种将原始野性与英雄性相混淆,将粗鄙粗俗与粗犷豪迈相混淆等走向事物反面的做法同样令人忧思。语言的个性化是文学的本性,但将语言运用到俗不可耐、粗俗直白,有哗众取宠之意,无精用创神之心,一味地迎合媚俗,也让人深感忧虑。人类的崇高毕竟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我们可以宽泛崇高的价值取向,可以认同多样的审美感受,但我们坚持认为,崇高与低俗还是格格不入的,给人以愉悦的情感,给人以净化的陶冶和美的启迪,才是崇高文学的正途,才是真正具有文学品味的艺术创造。
收稿日期:2010-0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