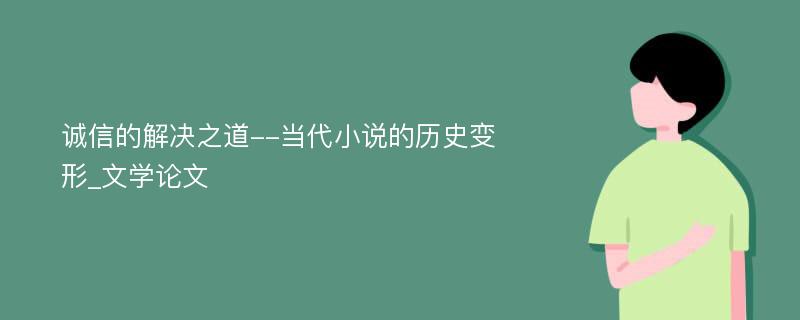
整体性的破解——当代长篇小说的历史变形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整体性论文,长篇小说论文,当代论文,历史论文,变形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准确地说,它是中国现代性发展到极富理 想主义时期的产物。长篇小说以它宏大的结构与广博的内容,可以概括更为丰富充足的 现实,表达人们更为深广的愿望,集中体现现代性的历史需求。尽管中国的现代性有着 更为迫切的民族国家寓言诉求需要表达,但在中国早期的现代性进程中,在茅盾、肖军 、萧红这样最典型的革命作家那里,民族国家的寓言与个人的经验还是相互渗透缠绕。 到了1942年以后,特别是50、60年代,中国的现代性有了更为明确的历史目标,对历史 与现实的认识更为坚定,个人的经验及其愿望被排除出写作领域。在50、60年代,几乎 是突然间中国的长篇小说有一个繁荣昌盛的景象,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叙事展现了一幅 又一幅壮丽的画卷。现实镜像被当成历史本身,并且成为现实存在的前提与保证。多少 年来,文学成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的强有力的证明,它的形象与情感的功能令人深信不 疑,可以有效地重建现实。关于现实的历史想象达到极致时,个人的经验、冲动被剔除 了。
50、60年代的长篇小说作为“历史化”的宏大叙事而产生意识形态的作用(注:有关“ 历史化”的论述可参见拙著《表意的焦虑》“结语”部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显然,人们依然迷恋这种状况,这是我们要关注的,而 且这种迷恋依然成为对当下长篇小说生产的外在的或内在的规范性支配。问题在于,其 一,人们只是从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而没有从现代性的意义上去理解它;其二,人们以为 抛弃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现代性在美学上的支配作用是一种更为 内在的和深刻的作用;因此,其三,它导致了人们对当下长篇小说生产的强烈不满,这 种不满奇怪地是以在理论上被人们意识到的意识形态超量写作为标准的,也就是说,对 当下的不满,经常下意识地援引那些过度历史化的作品为依据,以其强大的“思想性” 为参照,来表达对当下思想性薄弱的否定;其四,实际上,作家们的表达也依然迷恋完 整性和整体性的现代性美学规范,只有在完整性的表达中,当下长篇小说的审美表达才 会心安理得,才能如鱼得水。
由此说明了当下长篇小说的生产处于一种表里不一的张力状态。一方面在逃离“历史 化”,另一方面又渴望重新“历史化”。当然,这种逃离是一种有序的逃离,只是在某 种阶段它无法前行,它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当然,文学的道路就只是写作的道路,理论 是灰色的,理论所能做的,只是去看清历史真相,为未来提示可能性。
一、缝隙的开启:从超量意识形态到思想性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无疑秉承了50、60年代的美学规范,尽管“文革”后的文学 以反思“文革”及十七年“极左”路线为其出发点,但这种反思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 争,从“极左”到“反左”,其意识形态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但其思想方法则具有共 通之处。在文学方面,“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包含对“文革”和十七年的激 烈批判,但其美学规范并没有改变。那时在文学观念上打出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 口号,显然是要沿着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前进。在“拨乱反正”的纲领下展开的反思, 再次设想了一个“正”的历史,与其说回到了一种历史中,不如说重新建构了一种历史 。而另一种历史(“极左”的历史)则被排除在这个重新建构的历史之外。这种历史恢复 只是一种话语的恢复,只是在想象中完成了一种历史清除和一种历史建构,它只能是意 识形态的话语实践结果。投射在文学方面,整个80年代上半期的文学实践,其美学规范 并没有超出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章程。它当然在“人性论”和“真实性”这两点 上有所开掘,但这只是一项修复。
直到80年代中期,历史才敞开一道逢隙。整个80年代上半期,长篇小说的创作寥寥可 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戴厚英的《人啊,人!》(1980)、李国文 的《冬天里的春天》(1981)、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81),是这个时期比较出色的作 品。和同期的中篇和短篇小说相比,长篇小说的影响要小得多,前者与现实的紧密关系 ,使得后者更从容的历史含量变得无足轻重。除了戴厚英的《人啊,人!》与人性论和 人道主义讨论相关,并且与反思“文革”的时代纲领相一致,引发强烈反应,其他的长 篇小说并没有在现实中产生太大影响。但其小说观念与美学规范却可以清晰看出典型的 现实主义特征,其思考的主题以及思考的方式也没有越出“超量意识形态”的边界。也 就是说,一种相当明确和明显的“现实化”的意识形态主题贯穿作品的始终。
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长篇小说》发表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这显然是 一部蹊跷的作品。但在当时,因为王蒙的特殊地位,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相 反,它被作为当时的“现实化”的意识形态的佐证。王蒙一直处在时代中心,他被作为 引导潮流的人物而纳入当时的潮流,这同样是一件蹊跷的事情。事实上,王蒙在“文革 ”后的写作与当时的“伤痕文学”有所不同,甚至有着深刻的歧义:《蝴蝶》里的秋文 对张思远的拒绝;《春之声》中的结尾穿过那片乱坟岗,那并不是一个早晨,而是星辰 寥寥的前黎明时刻;《夜的眼》中关于民主与羊腿的假模假样的矛盾统一关系的论辩; 尤其是《布礼》中的那个叫做钟亦诚的人有着太多的怀疑……所有这些,都掩饰不住王 蒙对“文革”历史的一种忧虑与怀疑。他与大多数对“文革”史的重述主要是表示“忠 诚”信念的作家有着深刻的差异,他试图表达个人对历史的追问。也就是说,他是较早 具有主体意向的作家,这使他在“文革”后还是要与意识形态的超量化的编码做出区分 。但是,时代潮流需要王蒙,王蒙被卷入之后迅速被推到潮流的颠峰。王蒙的那种怀疑 与追问只能被隐蔽,不能被消除。《活动变人形》当然也可以看出当时意识形态可识别 的明显主题,例如,对人性的剖析,对中国现代的民族国家与个人命运关系的思考。但 对于王蒙来说,这些主题的处理已经带有更为深刻的个人视角。这个对历史反思的主体 ,有着个人的意向。政治化的主题转向了思想性的主题,其重心从政治的指令转向了自 我的思想。
80年代中期这样的历史潜在变化在迄今为止的文学史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说明, 这使人们对于90年代发生的变化显得茫然无措。正是因为这些中间或过渡的变化没有被 识别,人们不能理解随后的历史,也没有看清原来的历史。80年代中期,出现了“现代 派”和“寻根文学”,关于个人自主性的思想已经在文学中滋长起来,并且作家的自主 思考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思想性要素。作家(以及知识分子群体)思想与意识形态中心化功 能的分离,这对于文学叙事的变化是极为重要的。长篇小说对社会历史的表现不再是经 典现实主义规范之下的“本质规律”,不再是在民族国家背景上阐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而是开始融入了作家的主体意向性。其他文体因为与现实的思想演变关系密切,或者 本身就是现实思想变革的前导,率先地游离出主导意识形态背景。但长篇小说以其规模 和文体与民族国家的历史渊源,它显然不容易具有创新与变异。其内容的丰富与广博, 决定了它的文本体制与民族国家的想象天然一致。
对于80年代中期的长篇小说来说,从意识形态给定的本质转向个人的批判性思考,这 是一个值得强调的步骤。这种转向,由于其文本体制的关系,只能表现为视角方面的变 化。那些长篇小说在文本体制,在思想内涵,以至于在结构和修辞方面都依然带着旧有 的宏大体制的印记,但其视角出发点具有了个人性,或者具有了作家的主体性意向。这 一时期,数部长篇,张炜的《古船》(1986)、张承志的《金牧场》(1987)、铁凝的《玫 瑰门》(1988)、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1988)等,相继出版。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 作者个人对历史、人性的探究占据主要地位。同时期还有贾平凹的《浮躁》,但贾平凹 的这部长篇并未脱离当时的“改革”与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主题,贾平凹个人的文化底 蕴这时还并未显露出来。张炜的《古船》显然是一部宏大的历史叙事,两个阶级两条路 线被颠倒了两次,它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主导意识形态设定的思想向度,但它坚定 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书中对人性与宿命两个要点的表达,超出经典现实主义权威主题的 范围。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如此在结构和历史观念上承继了经典历史叙事的作品,也可 以融入作家的主体意向。张承志在80年代无疑是一个主导意识形态的作家,但他的《金 牧场》从时代主题中滑脱出来,明显具有了形而上的更为抽象的属于作家个人的思想。 当然,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是过分之作,就是放在王朔的作品系列中也显得走火入 魔。这是王朔对现代主义进行的戏谑,而他同时也被现代主义戏谑了。他稍后的《我是 你爸爸》则率先表达了市民社会的个人情感。在80年代中后期,意识形态规范已经很难 贯穿一致,这是历史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作家则是以其个体敏感性率先拓展了个人表 达空间。而在长篇小说这种历史化体制深厚的文本上表现出来,则可以看到最显著而深 刻的历史变异。
长篇小说显然是一个最保守最有力量的堡垒,它同时还是一个惰性十足的懒汉。其他 的艺术门类和文体屈于时代的创新的压力,都要进行各式各样的变革实验,只有长篇小 说,它要困守自己的规范,它的鸿篇巨制使它墨守成规就可以有所作为。这使它有可能 以坐享其成的方式来应对变化:它只要适可而止吸取当时的已有的思想与艺术变革成果 ,就能获得成功。长篇小说无不是短篇和中篇的倒退,特别是在先锋派作家那里,余华 、苏童、格非、孙甘露……所有在中短篇小说那里达到艺术高峰的作家,在长篇小说这 里,不得不放低姿态,不得不采取掺水行动。他们仅仅是在语言这点上,才保住了艺术 性的体面。长篇小说要么是意识形态化的,要么是大众通俗化的,这二者最容易磨合, 留给艺术的则是有限的空间。所有在长篇小说那里可以达到的艺术水准,在中短篇小说 那里都不过是雕虫小技。长篇小说仅仅是以其份量,以其对历史、现实以及人类生活的 广度和深度的涵盖而居于文学的中心地位。其艺术性最容易又最困难。最容易在于:它 只要有一定的容量就可以站住脚,人们对着几厚本用文字堆积起来的纪念碑很容易产生 敬仰之情和宽容之心;其难处在于:长篇小说要达到艺术上的创造相当困难,它需要与 传统与既定的规范妥协才能做得恰如其分。两相权衡,应该说,长篇小说的艺术性要达 到相当高的水准十分困难。
正如我们前面论述过的那样,在意识形态充分活跃的时代,长篇小说只要符合主导意 识形态规定的那种政治律令就能获得基本成功。在80年代中期,长篇小说开始降低意识 形态的内容,转向了具有作家主体性意向的思想意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根本性的转 折,它使随后的历史不可避免和顺理成章。
二、历史理性的缩减:生活质感的呈现
现代性携带强大的理性力量支配着文学,在长篇小说这里,历史理性找到最合适的家 园。理性与历史的合谋使长篇小说获得华丽的外衣和深厚的精神内涵,这种历史理性无 疑也是一种使文学屈服的力量。当然,文学也并不那么容易屈服,它以语言和生活的存 在可以抵御理性异化而保留文学品质。当语言与生活可以超出理性的支配,也就说明小 说叙事更多可能地获得了文学性的表达。80年代后期的长篇小说受历史理性支配的程度 在降低,而语言直接面对生活的那种叙述方式在起作用,它使长篇小说主要不是依靠理 性的思想主题来推动叙事,并且以此来获得阐释的意义,而是语言与呈现的生活使作品 获得文学品质。问题的关键当然还在于,文学—社会共同体接受这种文学,并确认了它 的存在价值。尽管在那个时期,人们对这些作品的阐释未提示明确的话语模式,但现在 可以在综合的语境中去重新认定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中的真正意义。
首先值得注意:迄今为止,莫言的创作依然保持旺盛的状态,多年来,莫言被人们过 度阐释,但他依然显得难以捉摸。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神秘感,或故作高深,而是他的存 在明明白白,但却从我们现有的语境中滑脱出去。这么多年,很多作家都随时代潮流的 撤退而退隐,只有莫言,依然故我,我行我素。根本原因,我以为就在于莫言不是跟着 一种被给定的时代精神写作,而是以自身对人类生活存在的理解和感受写作,他只是用 语言对准生活,一切都交付给直觉和语言,赋予他所表达的生活以最大的自由,一切思 想都在自明中,或者无须表白。当然,并不是说莫言的作品就没有可归纳的主题,而是 说在他的作品中语言透示出的生活质感,或者说生活呈现出的那种性状,显得更为重要 。他的写作是直接面对语言和生活的质感,是语言与生活质感本身的碰撞与起舞。莫言 自己就表示过对思想性的东西的逃避(注: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作过这样的表述 。),显然,仅仅用没有受过系统高等教育来解释莫言对思想理论的天然排斥是不恰当 的,同样的原因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莫言的才能表达在对语言的敏感上,表现在他 对生活的性状采取超常的幽默感和荒诞感加以处置。他无须求助思想性,更不用说宏大 的历史理性和意识形态。80年代后期,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被放在“寻根文学”的序 列底下来讨论,但实际上,莫言没有那么明确的历史意图,也没有对“文化之根”或“ 民族性”之类东西的迷恋,他只是根据个人的经验、根据民间记忆来写作。他的那些作 品是对乡土中国更为纯朴的生活样态的表现。在莫言所有的作品中,《丰乳肥臀》(199 5)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莫言可以凭着他的语言感觉、他对生活性状始终保持的那种幽 默感和荒诞感来展开叙事。读读这部小说的开头部分,就会对他能以如此随意的方式把 生活情境造得如此有声有色而感动不已。这个延续了整整十章的开头融合了上官鲁氏的 生产、驴的生产、日本兵的残酷杀戮、游击队的覆灭,最后以日本军医的救治完成这个 开头。
绝望与血腥,在莫言的叙事中就是生活本来的面目,他只关注语言往前推进,他是如 此不动声色,甚至在冷漠中还透着一点快感来书写这种生活。这一切都是存在本身,都 是发生着的事件,出生与死亡,希望与挣扎,开始与结束,是那么平常。莫言就是有这 种本事,他把任何惊天动地的事,都写得无足轻重。可是生活就像一种稠密的水流,抹 不开地存在在那里,既透明清彻,又不可理喻。莫言的书写是一种光的书写,就是时间 流向光亮中,一切都存在于此。他笔下的生活质感不是沉甸甸的那种,而是一种粘稠、 透明和光亮。
因为历史理性的退场,文学叙事完成了对生活的直接呈现,没有理性作为构架,也没 有更为深厚的思想性去探究,生活的事实和事物有一种更为纯粹的存在性出现于长篇小 说中。90年代初的中国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之所以“深刻”,在于它如此轻易就 完成,人们不知不觉,好像这一切只是延期到来的奖项,与其说这是历史的嘉许与恩惠 ,不如说是历史的债务,债权人已经麻木。历史的变异不再像80年代那么急迫,一切都 是延搁的可有可无的债务。一切宏大的思想体系,被现实的功利与需要替代,这是自在 自为的消解。90年代上半期,历史理性及其思想意向在文学作品中明显缩减,文学叙事 依靠语言和感觉展开。8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作家的主体意向也趋于弱化,作家依靠更好 的语言感觉,就可以把握生活的状况。那个时期在理论界和批评界,对当下的文学作品 的解释是“新状态”和“新表象”(注:这个时期有关的说法可以参见张颐武、王干、 张未民和笔者的论述。1992年左右的《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可见一斑。)。 事实上,正如“新写实主义”的平民主义的日常化叙事已经先于理论概括存在多年,对 这个时期的非深度化状况的描述,也早就露出端倪。回到长篇小说来看,长篇小说本来 在艺术上就趋向于政治性和大众化,当政治性缩减后,大众化的阅读期待就会起到更有 效的作用。既然历史理性已经难以起支配作用,那么作家只要在面对保守性的大众期待 再加入必要的个人化的艺术经验就能解决难题。事实上,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在艺术 上的主要困难,在于无法在艺术性与大众阅读期待之间找到平衡。其他的文学样式可以 忽略这一问题,发表于文学期刊的作品主要面对文学界,而长篇小说则要直接面对图书 市场,面对阅读。想象的读者经常成为写作焦虑的源泉。刚刚从历史理性中游离出来的 作家群体,乐于把读者群想象成是从洪荒时代走出来的狮身人面的感官享乐主义者。如 何降低艺术性则成为一个与读者沟通的简单草率的措施,就这一点,先锋派也不能幸免 。只是这种对读者与市场的期待,无意中完成了(或者加深了)长篇小说与思想深度分离 。通过对思想的逃避,当代长篇小说成为市场与读者的俘虏,这对于不同的作家,后果 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最低限度的思想性,如何与语言叙述结合在一起,这成为当代长篇 小说保证艺术性的赌注。
在这一转变的初期阶段,先锋派的长篇小说还是令人刮目相看。小说的难度在于,是 否有一种富有文学品质的语言能把握生活的性状质感。余华或许率先意识到这一转变过 程,使余华精疲力竭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没有激起文坛的响应,余华开始转向长篇 小说,《在细雨中呼喊》(1992,以下简称《细雨》)是最初的成果。只要看看《细雨》 到《许三官卖血记》的变化,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这个时代的艺术轨迹。《细雨》从先 锋派的语言实验破壳而出,但并未脱胎换骨。那种语言质感恰恰给生活的质感提供了家 园,余华可以不再去考虑形而上的思想性存在,也无须过分注重语言表达。他关注生活 的存在的状况,那种随时破裂的时刻,溢出边界的真实。《细雨》当然有可以归结的主 题,甚至可以在萨特式的存在主义意义上读解相当丰厚的思想意蕴,那种无依无靠的孤 独感,父亲的暴政与家的崩溃,怜悯与绝望中的欢乐等等,这些主题无疑可以在后现代 哲学纲领底下加以读解。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些思想如何成为那种生活存在的遗留物, 这里看不到思想硬性表达所需要的那些结构设置、反思性片断和主体意向。这部小说主 要依靠语言与生活质感的完美结合,它使表达具有一种纯粹性。很显然,同样是余华的 长篇小说,同时的《活着》(1992)与后来的《许三官卖血记》(1995)就包含了一些思想 的阴谋,因为余华放弃了语言接近生活存在性的那种努力,其被表现的生活则要依赖一 种预设的思想性来支持其存在性。我坚持认为《细雨》是余华最好的长篇小说,虽然这 有悖于余华本人梳理的他的写作的无限进步史。
格非在同时期的长篇小说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敌人》、《边缘》在当时的历史 境况中,思想动机的作用还是显得太重,格非没有在语言与生活本身的存在关系中,找 到好的叙述方式。长篇小说毕竟与中篇或短篇不同,对于后者,格非无疑是最出色的, 但长篇则要以更自由而又节制的方式去接近生活本身。《欲望的旗帜》几乎是力不从心 的作品,在90年代中期,这部小说无疑是少数回答了当时精神混乱的作品,但格非在一 个一元论思想崩溃的时期,偏执地要以他的思想来质问时代,他没有真正抓住这个时代 生活的外形——一种没有本质的外形,一种外形的外形。他奇怪地试图回到现代性的本 质主义家园,这在他的思想历程中有一种奇怪的恢复的格调,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的嘲弄 ,格非试图使他的作品成为一个“后—后”人文主义的宣言。一个时期的作家有他给定 的命运,曾经是子一代的叛逆的格非,突然间要充当起时代的精神之父——或者这个父 亲的代言人。他被父亲的阴影所迷惑,他是父亲魂灵在场的替代者——不管是从思想上 还是艺术上,这都不是格非所能胜任的。
90年代上半期出现贾平凹的《废都》(1993)和陈忠实的《白鹿原》(1993)这样的长篇 小说。前者讲述了一个欲望化的生活现实,在回望传统典籍的写作中,身体赤裸地呈现 ,给生活的本真性提供了绝对的基础。后者则依然要写出一种史诗,对民族国家的历史 进行重写和改写。《白鹿原》是最后的史诗,这就足以说明史诗的终结。随后同样的史 诗式的作品阿来的《尘埃落定》(1999),则选取了一个白痴作为视点,这个史诗已经没 有任何反思性意味,只有异域风光和一种生命存在的场景自我呈现。
90年代的长篇小说还有女性主义的探索。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1994)与陈染的《 私人生活》(1996)表达了女性对主流社会的疏离与逃逸。林白的小说依靠一种飞扬的语 言与现实拉开距离,使她的女性生活史的呈现具有不可屈服的倔强性。陈染的作品则更 偏执地回到内心生活,她只看到女性的身体,女性与女性的心理,以及丑陋的模糊不清 的男性形体。不用说,她们的怪模怪样的写作承继了残雪当年的女性叛逆传统,逃离了 父权制庞大的话语体系,日常、琐碎、怪戾的女性心理,不再需要深厚的历史理性作为 依托,更不用说适应意识形态背景了。
三、无法告别的父爱:性格与命运
当代长篇小说跟随着文学从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中走出来,它显得最勉强也最被动。 作家的主体意向一度给它注入了思想基础,但这些思想经历后现代主义以及知识经济和 全球化思潮的冲击,也难以摆脱“终极真理”的架构。尽管“历史终结”这种说法值得 怀疑,但它不绝于耳地流传,至少使人难以坚持历史绝对在场的观念。90年代后期以来 的文学场域被各式各样的话语碎片所覆盖,个人“力比多”开始起到更有效的推动作用 ,没有历史感和深度性的文本构筑成众声喧哗的当代现场。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文学崩 溃的场景,个人化的话语成为这个时期主要的表达方式,个人的“力比多”比任何时候 都充分而主动地得到表达,尽管压抑始终存在,但转向自我和身体的表达无论如何还是 有变形的表达途径。
从整体上来说,当代文学并没有在一个“历史终结”(我们姑且透支这个概念)的时期 找到最恰当和有效的表达方式:作为一种适应和直接的表达,它是卓有成效的;而作为 一种更积极、更有效地穿透这个时期并且展开新纪元式的话语创造,当代文学显得缺乏 创造的活力。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更显得力不从心。仅仅从艺术表现形式来看,长篇小 说的变化并不大,如果不是从更内在的深层的话语建构角度来看,长篇小说几乎岿然不 动。当然,背景与内在的空虚无论如何也不是外在的艺术形式所能掩饰得住的,长篇小 说依然要寻求新的内在性,寻求艺术表现的力度。当艺术表现的纯粹性力量不能支撑住 艺术本身的伸展时,它依然要回过头来寻求内在思想作为支撑。
艺术表现力与内在思想性这两个并不一致的问题,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场域中被 最大可能地混淆。本来个人的“力比多”的话语应该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但创造性与 生命底气的薄弱,使得个人的“力比多”话语流于表面和空泛。艺术想象力似乎已经枯 竭,它不能拓展新的场域,只有责怪当下的现实和迷恋过去。在这样的场景中,人们除 了怀念“父亲”的强大有力的统治没有别的想法,这依然是稚气未脱的想象。本来摆脱 了历史理性的文学,可以在个人“力比多”的驱动下,找到新的话语,但空泛的表象没 有真实的质感,人们止步不前,掉头寻找丢失的家园。“晚生代”作为一群离家的孩子 ,在90年代的历史空场中要夺取一条自己的道路显得困难重重。他们既不能沿着先锋派 的踪迹,更没有能力与“美女作家”的时尚姿态对垒。在重重夹缝中循序渐进,“晚生 代”不像先锋派那样是早熟和聪慧的一代,毋宁说他们是苦磨的一代。时间和经验使他 们成熟,使他们更容易与传统和现实达成妥协。“晚生代”能坚持下来并且凸显出艺术 实力,完全是以对传统小说的臣服为代价——尽管他们也加入了独特的领会和现实的需 要。
这个群体也许称之为“中坚群”更恰当(注:仅仅是为了把一批年龄和实力相近的作家 放在一起概括,而称之为“晚生代”。经历过90年代不温不火的磨炼,他们在艺术上趋 于成熟。由于这个群体已经步入(或接近)中年,并且也有泛化的趋势,他们已经成为当 下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因此,不如把他们称作“中坚群”——这个群体现在是那么壮 大,已经无法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开列名单。),这里只举出他们在长篇小说写作方面颇 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来分析。可以注意到,他们的长篇小说写作有一个回归传统现实主 义的倾向。这个倾向既没有任何思潮与运动的背景,也没有个人的刻意的努力。它是先 锋性创造姿态放低后文学常规化的必然后果。很显然,常规小说就是现实主义小说,只 是当今的现实主义显然与经典现实主义有明显乃至深刻的区别,这个区别并不是创作者 有意识的艺术行为,只是历史情境使之不得不如此的结果——它是“历史之手”完成的 作品。回到常规的现实主义也依然是在个人的立场上来完成表达。这批作家当然要把希 望寄托在艺术表达上,思想的穿透性(以及批判性)一方面被抑制住,另一方面也难以建 立。艺术表达就成为文本惟一的支柱。语言接近生活的那种先锋性表达显然有相当的风 险,有限的艺术性强调就落到在传统给定的要素上下功夫。因此,在荆歌、熊正良、鬼 子、董立勃、艾伟、刘庆等人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成为小说的艺术表 现用尽功力的地方。这种做法在中篇小说那里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长篇小说也如 法炮制,大有驾轻就熟之势。荆歌的《爱你有多深》(2002)、艾伟的《爱人同志》(200 2)、刘庆的《长势喜人》(2003)、董立勃的《白豆》(2003)等等,这些作品大都发表于 《收获》与《当代》,都是广受好评的上乘之作。
这些作品都是通过主要人物的命运发展推进故事,线性的时间是命运增值与力量呈现 的必要通道。这些作品里的人物总是命运多舛,坎坷多变,一步步走向生活绝境,几乎 所有的苦难都让主角碰上。苦难炼就了命运之不可抗拒的历程,造就了性格向着极端化 的方向挺进。在这里,苦难、性格和命运是三位一体的一种力量,它们在互相碰撞和铰 合中凝聚在一起,使小说叙述变得坚韧有力,使语言显示出了品质。因为叙述行进在不 断被强化的苦难和命运境遇中,人物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怪异和极端,它除了把事件推 向最坏的境地、迎来生活的崩溃外,别无选择。当然,也可以利用外部环境,像刘庆的 《长势喜人》和董立勃的《白豆》,因为写作年代具有历史的强大压迫机制,可以通过 历史环境给人物命运施压。但荆歌的《爱你有多深》和艾伟的《爱人同志》就面临困难 ,在压抑机制不那么明显的年代,外部历史的力量没有强大到成为绝对的压力(也许存 在这种压力,但这两部作品,以及现在所有的作品都没有能力去发掘),只有借助于人 物性格,通过把人物性格扭曲,使生活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导致命运失控而走向极 端。在命运崩溃的时刻,使文本获得力量。也是在这样的推进中,小说叙事和语言始终 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即使是表面上松驰自如的叙述,也因为内在隐含着走向生活绝境 的那种趋势,从而有一种整体性的力量。在这里,对生活的表面、对存在真理的追踪, 实际上变成对艺术表现力、对小说叙事的力度的追求——这里以美学的形式重现了伟大 “父亲”的身影。性格与命运成为小说艺术表现的同谋,而不是像经典现实主义那样, 成为政治信仰或历史思辨的助手。但它对时间线性发展的依赖,它寻求的整体性和单方 面不断强化的艺术手法,它的叙述主体在场的那种目的论,都表明它是对现代性美学的 回归和强调,它是在美学上对“现代性之父”的重新臣服。那种命运的力度达到极端,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美学规则和趣味,关键是把握住结构、整体和方向。这是对由来已久 的父爱的眷恋,也是以美学的形式对“现代性之父”的虔诚颂扬——它是美学意义上的 父爱的欢乐颂。艾伟的《爱人同志》最后让刘亚军放火烧了那幢房子,他也完成了自我 终结,而文本也完成完整性的终结,张小影也解脱了,一切都解脱了,一个完整的结束 。真是圆满啊,无懈可击的圆满——在父亲的圆满怀抱里,子一代成熟了。当然,没有 任何理由认为对完整性的认同就是当今长篇小说叙事的天敌,仅仅是说,过分追求完整 性,形成完整性的惯性,这就抑制了当代长篇小说写作的更多的可能性。它本来可以破 壳而出,但它没有。
尽管在当代长篇小说发展到这种状况的前提下,这种小说叙事卓有成就并且也推进了 常规现实主义的发展,但它的驾轻就熟和老道,只能表明常规现实主义走到顶端,而不 能表明当代小说叙事已经无路可走。事实上,这几位作家的几部长篇小说已经处在冲破 整体性的边缘:荆歌对荒诞感的把握,对语言的那种欢乐般的张力的寻求;艾伟可以对 性格心理进行多方透视,他能穿过生活的不可能性,能够把绝望的时刻写得淋漓尽致; 刘建东对多元视点运用得相当自如,把生活的荒诞性与反讽结合在一起,让生活变形和 变质,看到存在的局限性。只要往前走一步,就可以预计更有冲击力的东西出现。
四、转向逃逸:文本敞开的可能性
有必要看到的是,另一部分作家向经典现实主义提出挑战。长篇小说并不是单纯恢复 历史存在,而是重新给历史编码,给语言提供更大的场域。90年代依然出现了当代长篇 小说最极端的作品,这就是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1998),这个人倾注了六年时间 ,写作了一部四卷本的长篇小说。一次对经典的冲动和梦想,却转变为对经典的全面颠 覆。刘震云的反抗同时带有胡闹的嫌疑。但整整六年,一个如此智慧的作家的行为,不 能不看作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部作品对乡村和城市进了双重解构,不再是单向度地批 判城市或现代文明,而且对乡土中国也进行了无情的嘲弄。这部作品令人惊异地以最彻 底的方式解构了父权制文化,“父亲”在这里被完全戏剧化了,他是欺骗、无耻、无赖 的综合体。同样包含着对整体性和历史理性的嘲弄,刘震云的叙述颠三倒四,没有时间 的自然行程,父权制的强大的线性时间被任意割裂,置放进杂乱的后现代场域。在这里 ,语言的快感、反讽和幽默、戏谑与恶作剧构成叙事文本的主要元素。当然,在这部作 品中依然有一种肯定性的价值,那就是“姥娘”所表征的母系文化的人伦价值,那是一 种来自传统深处的“孝道”之类的精神家园的根基。对于刘震云来说肯定性的价值并不 明确,也不刻意求证,那是回到乡土中国生活本真性的一种有限价值。没有理由认为刘 震云的如此过分的行径可以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夺取一条宽广的道路,但作为实验 性的文本,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它表明什么道路可行,什么不可行。在刘震云之后,没 有人走这样的弯路。
张炜在新世纪之初出版《能不忆蜀葵》,以强烈的抒情意味和对现代主义场域的迷恋 展开叙述,一种灵魂和肉体的撕裂也撕扯着文本的叙事,但张炜能凭借过人的才华做到 游刃有余,他的批判性或反思性已经不再是障碍,而是叙述的动力机制,在这个意义上 ,张炜的虔诚几乎愚弄了现代主义。
河南人在当代小说方面的大胆,直到阎连科的《受活》(2003)才让人幡然醒悟。事实 上,两年前李洱的《花腔》(2000)就令文坛吃惊不已,那是一部相当结实的作品,对历 史真实性的怀疑,导引着对历史的重新书写,小说叙述以如此自由而有穿透力的形式推 进。阎连科的《受活》对现代性的革命史进行了独到的描写,使这段历史的呈现显示出 极为复杂的意味。很显然,这部小说在文本结构、叙事方法以及语言方面,显示出倔强 的反抗性。这个文本是怀着对乡土中国,怀着对革命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命运的宿命式 的关切来展开的,因而,阎连科试图回到乡土中国残缺不全的历史中去。在这里,革命 史与乡土史是同样破碎的地方志。小说不断夹杂“絮言”于正文叙事中,这些“絮言” 是对正文的补充与解释,然而,这本身说明,一旦回到乡土中国的生活状态,回到它的 真实的历史中,那些东西是如何难以理解,没有注释,没有说明,现在的阅读完全不知 其所云。这是对被文化与现代性培养的阅读的极大的嘲弄。乡土中国是如此顽强地自我 封闭,它的语言,它的那些说法,难以被现代性的叙事所包容。当然,更重要的是,阎 连科的这部小说中大量使用了河南方言,特别是那种叙述语式。这种文本带着强烈的乡 土气息,带着存在的倔强性向当代社会扑面而来,真是令人措手不及。很显然,“絮言 ”同时具有文本结构的功能,对一个正在进行完整性叙事的文本加以打断,插入另外的 表达。阎连科的这部对残缺生活书写的作品,也使之在结构上变得不完整,变得残缺不 全。那些“絮言”的补充结构,并不说明把遗漏的遗忘的和被陌生化的他者的历史全部 补齐。相反,它意指着一种不完全的书写,无法被概括和表达的乡土中国的历史。尤其 令人惊异的是,小说采用中国旧历来作为叙事的时间标记,所有的时间都在中国古旧的 黄历中展开,现代性的时间观念,革命史的时间记录,在这里都消逝在古老的黄历中。 诸如“阴农历属龙的庚辰年,癸未六月……”,“庚子鼠年到癸卯兔年……”,“丙午 马年到丙辰龙年……”,甚至柳县长在回答地委书记关于列宁的生卒年时,也用“上两 个甲子的庚午马年家历四月生,这个甲子的民国十三年腊月十六日死”这种老黄历加以 表述。这些莫名其妙的时间标记,顽强地拒绝了现代性的历史演进,革命历史在这样的 时间标记里也无法被准确识别。
过去,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只有在写城市或者写历史时才能促使文本开放 ,其语言则是在现代主义的审美感知的氛围中来加大修辞的表现力。现在,阎连科居然 在回归乡土,回到方言和口语中,文本却具有极大的开放性,文本洋溢着顽强的解构活力。就这一点而言,阎连科的这部小说为当代小说的本土性所具有的先锋意义,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最具本土特征的小说,也有可能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性,具有解构历史及其现代性象征体系的顽强的力量。
这里勾勒的只是当代长篇小说历史变异的一个侧面,这是一个并不富有诗意的历史变 形记,毋宁说它充满苦难、狡诈和诡异。当代长篇小说还有另一种历史,还有宏大的历 史叙事在展开——那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历史保存史。对于我来说,更愿意看到一种可能 性——一种逃离的可能性,一种始终创造和逃离的可能性。看到这种可能性,于是,我 们可以豪迈地说,汉语长篇小说依然具有创新的活力,逃离了“现代性之父”,子一代 有自己的出路,在历史破碎的间隙,他们灵巧的身姿可以躲闪,可以诡异多变,因为不 再被一种力量支配,也不再向一个目标进发,长篇小说的叙事可以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 ,这正表明,本文的探讨只是一个开端,一种历史的终结和写作零度的开端。这是一个 重新写作的时代,一个写作全面更新的时代。
标签: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莫言作品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细雨论文; 余华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