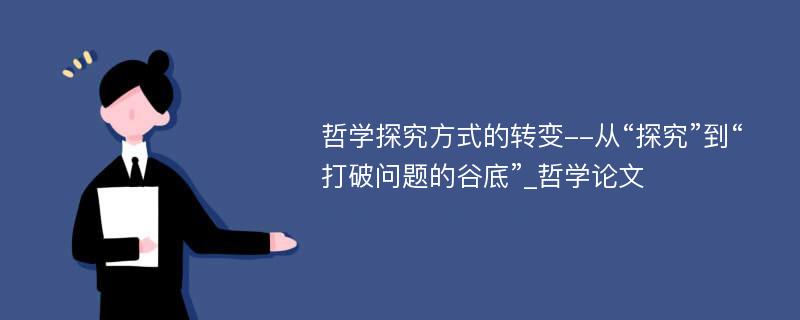
哲学探究方式的转变——从“追根究底”到“把底问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追根究底论文,哲学论文,方式论文,底问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爱智范式:一种“追根究底”的哲学探究传统
哲学的追问,是人对自己本质的追问。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本质,便如何进入一种哲学性质 的不倦的追寻之中。千百年来,哲学的一个伟大的梦想,就是寻求一种绝对“真”的语言, 把握最终极的实在,进入超历史永恒和超感性绝对的“真正的世界”,建构一个无所不包的 形而上学体系。哲学的追问,在这种伟大的梦想推动下,遵循着一种“追根究底”的“爱智 范式”。对这一哲学探究方式的评估,是整个20世纪哲学消解、反叛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 出发点。我们如何看待传统哲学遵循的这种爱智范式呢?今天的哲学思考前所未有地面对这 一问题的困扰。特别是在20世纪哲学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进行了全面反叛之后,该问题对于 21世纪哲学发展的方向而言尤其重要。
众所周知,传统哲学的核心是由“爱智慧”予以定向的。“爱智慧”作为对智慧和真理的 永无止境的追求,作为一种对世界人生“追根究底”的探问,它本身就包含了这种“爱”的 “理想性”乃至“梦想性”的一维,同时也包含了“爱”的“过程性”或“历史性”的一维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两个方面在人的人性本质中都有根源,就会看到,爱智慧作为一种哲学 追问,其实是人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的表现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人追求真理、认识世界 和认识自我的理性映现。因此,如果说哲学“爱智”是一种“梦想”,那它也是人类曾经有 过的并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的一种“梦想”。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 否认这种“爱智范式”的哲学探究方式对人类社会进步以及人类知识增长的重要历史意义。 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伟大的梦想”,始终引导人类从封闭的前现代社会进入高度开 放的急速变动的现代社会。然而,历史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恰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 特所说,“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当我们今天反省现代性困境的时候,就会看 到那从根源上构造西方现代性的“爱智梦想”,实际上使得现代性的所有建构无不隐蔽着重 重危机。对这些困境和危机的关注,必然引发人们对以往哲学探究方式进行置疑或清理。
爱智范式的哲学探究方式是把“智慧”作为“爱”的对象。这根本不同于单纯响应“智慧 ”并进入一种“与智慧和谐一致”的生命感悟和历史感性。由于它直接指向对智慧的“欲求 ”与“占有”,因而是一种将“智慧”或“最高智慧”对象化的探究活动。在这种哲学探究 方式中,“爱智慧”总是不断地从人无法达到的、不可认识的彼岸世界寻求对问题的终极诠 释和终极见证,人被看成是同属两个世界的“公民”,而我们全部的探究活动都是为了在感 性的、现象的、变动不居的世界与理性的、本质的、永恒不动的世界之间架设一座相通的“ 桥梁”。传统哲学的这种探究方式,在“搭桥”活动中,确立了一种“知识论”的传统构架 ,并在基本的理论思维前提上预制了一个永恒在场之物的存在,即一个最终的“底”的存在 。张世英指证它是一种“有底论”,大致是不错的。这种哲学探究方式,奠定了西方哲学形 而上学的基本框架,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黑格尔(海德格尔也说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的西方哲学都是在一种“爱智范式”下发展和演进的。
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在这种“追根究底”的“爱智范式”的探究中获得的“伟大成就”是毋 庸置疑的。不说它构成了哺育和滋养各门科学的母体,曾经有“科学的总汇”和“科学之科 学”的荣耀。也不说它在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中一直居于最高主宰地位,甚至由于它的构造 作用,西方传统文化被称为“哲学文化”。单从它对一种理性主义思想文化传统的不断塑造 ,对人的主体性精神的弘扬,对人性的提升和人的自我认识的强调,就可以说,今天人们面 对的已经融入到生活世界之中的所谓“西方现代性”,实际上导源于这一哲学传统。然而,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行伟大之思者,必入伟大之迷途”。西方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在成就 其“伟大”、“崇高”之时,是以对“最高”的价值主宰、“最终”的真理权威、“最真” 的世界根据的不倦探寻进行的。它在哲学探究的前提上,早已预设了种种不可究诘的、毋庸 置疑的“根据”( “底”)的存在。对此“根据”之追寻,不可能在感性的、相对的、有限的 、生成流变的领域获得结果,于是便走到了超感性绝对和超历史永恒的“彼岸幻影”之中。 这种“根据律”往往又逻辑地成为形式化、概念化的体系架构原则,构成了“追根究底”的 哲学探究样式的基本建构策略。
这里产生出来的很多问题是传统形而上学家未曾意识到的,这些问题表现为今天西方哲学 和文化经历的重大危机。追究起来看,危机的根源其实就是那一直隐蔽在西方人“爱智慧” 之中的“人与智慧的分裂”。它是现代人经历的种种“两极对立”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紧张 的根源。当代德国学者勒内·豪克不无忧郁地说:今天,“无论在西半球还是在东半球,‘ 主观’的人愈来愈无家可归。焦虑变成绝望,导致对麻醉品的享用。程度不同的精神病是我 们时代基本的世界性病症。逻各斯信誉扫地。”[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主 观”之人的孤离无根,更深的缘由乃在于造成此种“根基之丧失”的“追根究底”的哲学探 究方式隐蔽着的“底”之“无”。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建构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爱智范式之间的内在关 联,就会看到那给人许诺希望的现代性梦想实际上来自哲学领域的爱智梦想。今天人的苦闷 、焦虑甚至绝望,在于人在“科学技术”、“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社会正义”、 “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等“现代梦想”中,看到人类更深重的灾难。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 阿多尔诺曾经说过,“奥斯威辛之后不再有哲学”。实际上,人们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一 千多年来人类的“爱智”之标,原本是人的一种错觉式的(对“底”、“根据”)价值设定。 当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以一种急速运转的形式将几个世纪人类的“梦想”实现出来的时候, 那曾经隐蔽在柏拉图哲学王国背后的“专制陷阱”,也就由“思想”变成了“现实”。现代 人确实如卢梭所描绘的那样,他知道自己是“生而自由的”,但同样也痛苦地意识到自己“ 无处不在枷锁之中”。“爱智慧”本来是人的自由生命的无尽追求,然而这种追求由于忽略 了人的生命前提,总是从分裂人和人的世界出发,从人与存在的对立出发,把人置入“两个 世界”相互敌对的境地。这种导致人自身的灵肉分裂、人的世界的多重分裂(人与自然的分 裂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分裂)的因子,是现代人经历的精神分裂的始作俑者。
自19世纪以来,当科学、进步和理性在资本主义世界广泛地建功立业的时候,欧洲的许多 知识分子开始敏锐地发觉“理性的光芒”和“进步的神话”并不能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一 种 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开始出现,它要追问那种实现在现代科学中的“爱智慧”究竟将人类引 向何方。这一时期,哲学要求摆脱对自然科学方法典范的效法,要求抛开那些被认为是“绝 对真理”和“最高智慧”的东西,更多地关心人和人类的处境。因此,诗人的吟唱、文学的 叙事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写作,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变得愈来愈重要,并且逐渐取代了以往“ 牧师”的位置。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境况下,要求哲学坚持它以往孜孜以求的那些“爱智梦想 ”( 例如它要求成为严格科学的主张)的任何主张,就变得非常可笑。哲学领域中出现的这一变 化,既是哲学探究的视野的转变,同时也是人的自我理解的视野的变化,它表明生活世界的 问题在哲学运思的层面上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实际上,一旦“爱智慧”被诸科学分解为对各种认识对象(物)的知识探求,传统哲学寻求 一种终极知识的爱智梦想便破灭了。这意味着爱智哲学的终结。整个20世纪都沉浸在终结 哲学、告别哲学的深深的忧虑之中。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对以理性、正义和真理之名实施的 杀戮有了切肤之痛的亲身经历,使人们对启蒙运动以来有关进步和解放的神话有了更清醒的 认识。毫无疑问,人类追求真理、热爱智慧,是为了摆脱谬误和愚昧,为了使人类获得自由 和解放。然而,“爱智慧”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福音”,却使得现代人前所未有地陷入深深 的两难境地。可以说,20世纪是哲学爱智慧的梦想无可挽回地遭遇到破灭的世纪。这个世纪 特有的忧虑在于,对形而上学的反叛和消解其实是向一个伟大传统的告别。在这种告别哲学 的一系列思想运作中,首先是一种自18世纪以来就不断地得到强化的现代梦想的幻灭,它同 时也表明一种更深远的根基的丧失。我们以往在一种爱智范式中一直被看作是毋庸置疑的“ 根”和“底”现在变得有了问题。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幻灭。我们需要认真地思考20世纪哲学经历的这种幻灭。我们看到, 从哲学探究方式的转变中,我们多少能够切中问题的要害。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虽说是一句老生常谈,但它却为我们揭示出“变化了的时代”和“变化了的时代精神”的 地质学路标:在哲学和哲学探究方式的转变中,我们可以见证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
二、哲学的两种探究样式:从“有底”探究到“无底”探究
毫无疑问,“爱智慧”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演进的历程中,展开了一条“哲学之路”。这 是一条伟大的哲学探索之路。但是,这条满怀“希望”、洒满“光明”的爱智道路,却又是 一条布满陷阱、充满迷途的运思之道:它遗忘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并通过对作为终极之“ 底”的“存在者”的追寻,遗忘了“存在”自身的问题。由于此遗忘,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 发展到顶点(同时也是终点),必然回转到它的超始处或开端处。人们从对智慧的欲求、占有 和追寻(以人与智慧的对立为前提)回转到重新思考人的生命与智慧的和谐一致,就是一个必 然的进程。
“爱智慧”的人充满希望。而且,这是一种对追寻的结局不抱任何怀疑的期望。期望的问 题在形式上就是“有”的问题,是“是”的问题,或者“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总得“ 有”个“什么”,人们才期望,如果什么都“没有”,也就根本谈不到“期望”。因此,“ 爱智慧”的视野是一种关联着“有”的视野,它甚至把一切渺不可及的“终极之有”涵盖在 内。这里面有一种不言自明的“信心”。爱智哲学的基本思路是从“有”追问到“有”,从 “存在者”追问到“存在者”。这种追问是一种“有底论”的追问。由于它总是从存在者深 入到“底”,这样就在“有”之间或者“存在者”之间区分了层次、确立起“深度”。以这 种方式,它设定了一种最终的存在者,而哲学的追问就是要达到这个“底”。因此,“爱智 范式”的哲学家好像在做一场“挖掘”游戏,他们的目的是要比赛看谁挖掘得更“深”。这 种深入到“底”的哲学追问没有触及“无”的问题,更未触及从“无”到“有”的问题。 因此,它关注的核心不是“生”(创造或创生),而是“知”。人的生命或生活的主题往往以 一种扭曲的形式表现在爱智范式的知识论的追求中。这种哲学追问,从一种理性自识的意义 上理解人的本性,最终把人理解成为“认识者”、“求知者”、“理性的动物”和与“客体 ”相对而立的“主体”等等,它不大可能理解人的自为本性中那种“从无到有”的权力性和 创造性特质。所以,后来西方哲学凡是涉及到人的“从无到有”的创造性本质的地方,都由 “神”或者“神性实在”来加以解释。这是爱智哲学始终走不出超感性绝对和超历史永恒的 广袤疆域的缘由。
“爱智慧”确立了一种追寻初始本原、充足理由、最终同一性、最高价值原理和永恒抽象 本质的哲学探索的道路(人们通常称之为传统本体论)。这种哲学爱智达到顶点,必然不满足 于只是不停地更换“最终基础”或“最后根据”( “底”),一旦哲学的追问在爱智范式中出 现了把“底”问“破”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哲学爱智梦想的幻灭。“把底问破”的探究样式 是在“消解智慧”或“弃绝智慧”的视野上展开的。与“爱智慧”孜孜于“有”(期望)相反 ,“把底问破”的哲学探究样式走到了希望的反面而碰到“无”的问题。在这种“无底”的 探究样式中,一切预定的“和谐”、“完美”、“真的世界”、“永恒的正义”、“最高的 智慧”等都不再具备建构性的作用。这种探究方式并不指向某种不变的“最高智慧”,也不 设计什么最终的“根”“底”来供哲学家追寻,情况却是它总要求人们尽力祛除各种“最高 智慧”所造成的蒙蔽。哲学探究方式的转变,实际上呈现出从“爱智慧”到“祛除智慧”的 裂变。西方哲学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经历了一次转折,此后17世纪形而上学和18世纪的启蒙运 动都基本上是在这次转折的基础上用“人”、“主体”或“理性”作为“最后根据”来取代 “神”的位置。然而“神”并没有被废黜,它只不过改换了一幅面孔,以“人”的形象出现 在哲学的追问之中了。因此,近代出现的哲学转折并没有改变传统哲学的方向,它是传统哲 学原则的进一步展开,是其终极可能性的展现。当这种可能性达到极致的时候,“有底”到 “无底”的转折就呈现出来了。
事实上,哲学爱智梦想的幻灭,必然表现为哲学之“问”出现了把“底”问“破”的情况 。这意味着不再有一个终极存在(超感性领域)给人的生命意义提供最终保证。这样一来,作 为“底”(超感性绝对和超历史永恒)的“上帝”就被取消了,“上帝死了”。紧接着的问题 必然是,人如何穿过无际的“虚空”?或者,面对“无底深渊”的人如何才能活下去?陀思妥 也夫斯基的类似问题是:“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如何活下去?”这些问题使“生命意义”的 追问成为哲学的主题。而“生命意义”的主题化在理论前提上必然通过“一切价值的重估” 表现为“把底问破”,从而进入生命之“无底深渊”,惟有如此“生命意义”才成为“问题 ”。
与“无”的遭遇,提示出西方现当代思想经历的从“追根究底”到“把底问破”的探究方 式的转折。19世纪末和整个20世纪处于这个转折时代之中。转折时代的特点,可以用这个时 代三个代表性的思想家的判定词来表达,这就是“上帝死了”(尼采语)、“哲学的终结”( 海德格尔语)和“人之死”(福柯语)。尼采代表了从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维度带来的转折。他 选取的视角是“上帝死了”。海德格尔则是通过宣告“哲学的终结”而从存在“意义”和“ 真理”的界面上遭遇“根”“底”之丧失。尤其是他在后期思想中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实际 上是在“哲学的终结”这一点上面对“无”的问题的,他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是指那种 “从有到有”的形而上学的终结。福柯对尼采的解释完全不同于海德格尔对尼采所作的解释 ,他认为尼采的“上帝死了”说的是那杀死上帝的“人”的死亡。他沿着尼采开辟的道路, 对各种形式的看起来有智慧、有价值的思想提出了质疑。这些思想产生的重大影响,标志着 20世纪西方思想处于“把底问破”的“无底深渊”中。20世纪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在 现实生活中面对的无尽的迷惘、痛苦、焦虑、乃至绝望,都可从这种哲学探究方式的转向中 获 得解说。
三、希伯来寓言的启示:“通天塔”,还是“巴别塔”
一则古老的希伯来寓言讲述了“通天塔”是如何变为“巴别塔”(争吵之塔)。这个寓言有 如“咒语”一样,描绘出人类精神建造活动的“伟大”及其隐蔽的“陷阱”。
西方哲学经历的从“追根究底”到“把底问破”的哲学探究样式的转向,是不是同样遵循 了从“通天塔”到“巴别塔”之转变的“宿命”呢?在哲学爱智的伟大梦想破灭之后,在哲 学出现了“把底问破”的情况之后,哲学将走向何方呢?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对于21世纪 哲学的创建而言,必不可少。也许,我们从这则古老的希伯来寓言中,能获得某种启示。
我们知道,建造“通天塔”需要的智慧是一种伟大的知。我们相信这种智慧或知的伟大, 在那里人们彼此理解,但由于语言的混乱,到最后拆掉塔顶的时候,他们才真正彼此理解了 :这是一座“巴别塔”(争吵之塔)。巴别塔没有建成,它最终倒掉了。我们建立一个体系, 甚至设想一种关于各个系统的一般理论,作为能达到终极触到天的一般的普遍理论,并试图 用这理论来重新理解“巴别塔”,可是,“这种体系如今已经衰败了”[2]。人类建造哲学 形而上学理论体系的活动,与这里所说的建造巴别塔的活动,具有类似的历史命运。或者说 ,它本身代表了对人类试图重建“通天塔”的各种思想文化运动所隐蔽的前提的揭露。
我们看到三个因素在发挥作用:一种最高形态的知识理想;它所具有的诱惑;以及它所隐 蔽的无知或虚无。人们用概念、用思想、用想象等来建造,开启出伟大之知的“通天塔”的 建构工程。这种到达伟大的知的努力,使人在知的决断中进入爱智慧的建造活动之中。然而 ,这 种诱惑最终却使原始的和谐倾塌,于是我们面对曾经被灿烂的外表蒙蔽住的伟大而令人震惊 的“无知”。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塞尔在《万物本原》一书中谈到这一寓言的时候说道 :“我们就是带有嘈杂声的各种语言的百衲衣。一座塔加上噪声,一种体系加上喧嚣与躁动 ,一些建筑精美的墙垣,加上一些哭墙,那里的呻吟、呜咽和悲泣声可以使已经断开的石头 碎裂。这时我们明白了。历史开始了。”[2]我们同样可以说,只有在爱智哲学范式终结 之际,在“追根究底”的哲学探究样式被一种“把底问破”的哲学探究样式取代之际,哲学 才真正地回到生活世界。——“这时,我们明白,历史开始了”。
“通天塔”是同一性智慧的象征;而它一旦变成了“巴别塔”,则是同一性的智慧最终解 体的象征。哲学家并不建塔,吸引哲学家的是那种建塔的智慧,和那种拆除“巴别塔”的智 慧,是那种伟大的建构和伟大的解构。我们由此进入历史吧!我们可以在哲学家爱智慧的历 史旅程中看看“通天塔”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变成了“巴别塔”(争吵之塔),于是,“爱智 慧”也就变成了对最高智慧的弃绝!
“巴别塔”彻底倒掉了!“底”已被问“破”!“通天的路”消失在荆棘丛生的废墟中!20世 纪哲学经历的转折,在告别全部形而上学的伟大梦想和不朽的建造活动中,似乎一脚踏入到 “虚空”之中。我们从西方当代思想尤其是种种后现代主义哲学标举的“反叛”路数中,完 全能够见证到这种当代思想裹挟着的普遍的世界情绪。不论是取消深度、拒绝同一性、向整 体性开战、解蔽在场、颠覆主体性,还是破除起源幻像、祛除形而上学的怪影、重写现代 性,哲学探究方式总已经面临着深层次的范式转变,即将已往被视作“通天塔”式的建造活 动看做是一种“巴别塔”式的“散落”。于是,出现了尼采所说的“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 的论题。形象一点说,这一转换就是为爱智梦想提供充足理由或者根据的“底”的破碎。不 论人们称之为“上帝死了”、“主体性完了”(即所谓“主体性的黄昏”)、“哲学终结了” ,还是称之为“历史终结了”、“自然死了”、“自然终结了”、“人死了”,说的都是同 一件事,即一种悠久“根基”的丧失,一种可供我们伫立于其上的“底”的碎裂。这些令人 触目惊心的句子绝非哲学家的故弄玄虚,它表达了20世纪人类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根本觉悟。 人和人类又一次面临决断:一切伟大的知的背后,必定隐匿着伟大的无知;一切“终极”之 “底”无非是人类思维的一种预设,它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漆黑无边的“无底深渊”;“通天 塔”,换一个角度看,就是“巴别塔”。然而,谁将承担起这样的使命,将沉浸在慷慨豪迈 的不朽伟业中的人唤醒呢?当隐蔽的虚无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喧嚣声漫过了我们的眼睑,我 们还能看到什么呢?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一种“有底探究”的对象化运作中构筑种种爱智梦想 。然而,当这种梦想已然幻灭而“底”已不复存在之时,思之任务如何能够承担起“无底探 究”的重任?我们从建塔人的伟大希望开始,我们就置身其中,我们的父辈散落在大地上的 开始就是我们的开始。问题的关键是:在爱智梦想的幻灭处,我们如何为人类的这种希望辩 护?我们今天更紧迫地面临着这问题的困扰。
西方哲学经历的“哲学的梦想”的幻灭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是因为这里隐蔽着“人的奥 秘”和“哲学的奥秘”,表达了“人的命运”和“哲学的命运”。“爱智慧”确立的“追根 究底”哲学探究样式,反映了那种需要抽象永恒本质、需要绝对最高主宰、需要在一种自我 异化或对象化中认识人自己的“人的处境”。然而,爱智范式的哲学并非一无是处,它是人 类在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推动文明的发展、知识的进步和理性的累进的伟 大的探索活动。在科学尚不发达,人类生产力水平较低,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主体能力极其有 限的情况下,它对于提升人类理性的威力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它确立的一种“主客二分”的知识论框架以及在一种对象意识中对知识确 定性的不倦的追寻,对“根据”、“理由”和“底”的究极式的追问,使得它成了滋养和哺 育诸科学的母体。
然而,当分工越来越细密,社会结构的分化越来越向纵深展开,科学越来越演变成了一种 全面的技术统治,滋养和哺育诸科学的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也就在纷纷独立的诸科学那里完 成了自身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家们意识到传统哲学追求的爱智梦想的虚妄本性,因 此 消解或弃绝传统爱智范式的哲学所设计的“最高智慧”就成了哲学家们共同面临的一个主题 。
爱智梦想的幻灭就是哲学-形而上学的幻灭。哲学-形而上学的幻灭也就是人对一个超感性 绝对和超历史永恒的知识领域和真理领域的信仰的幻灭。这是发生在当代人身上的一件大事 。20世纪哲学以自己独特的运思,揭示了“通天塔”成了“巴别塔”的“形而上学的命运” 。哲学从“有底”探究向“无底”探究的转变是当代思想的一个基本趋势,它表明新世纪哲 学必须在人与存在的内在相属关系中放弃一种虚妄的究极性梦想,这要求哲学必须在与人的 生命的一体性关系中进入一种“无底”运思。
我认为,哲学惟有坚持此种“无底”运思,才能真正回到人的生活世界。我们只有在“无 底”“棋盘”的搏奕中,而不是在“有底”“建构”的预设中,才能理解人的实践本性,才 能 以一种真正的“彻”“底”(即“把底问破”)的方式领会人的自由生命本质。“无底”探究 之“无”,是人的生命境界之一无蔽障、一览无遗的自由澄明境界;在这种“无底”运思中 ,哲学不再是与人的生命存在无关的、与人的生活世界相脱离的“世界外的遐想”,不再只 是一种孜孜于人不能到达、不能居住的“抽象概念大厦”之建造的思维活动,与之相反,哲 学必须从人与存在的内在相属、人与世界的内在一体、人与智慧的和谐一致关系中进入“时 间”、“历史”、“现实”。这种哲学的“无底”探究,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前提批判,它 不仅能历史地看待“通天塔”式的形而上学体系建构之为“巴别塔”的“实情”,而且能够 在一种“无底”之“无”的生命感悟和历史感性中审视一切“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这样 看来,哲学探究方式的转变(从“有底”探究到“无底”探究的转向)其实是思想谱系的转变 。对此谱系的揭示将使我们清楚地辩识出21世纪哲学的主题及其方向。哲学的谱系,说到底 ,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谱系,而哲学的命运其实是和人的命运紧密联在一块的。这命运要求 哲学的探究和人的探究必须在一种内在关联中回到人所生活的现实生活世界,要求哲学的追 问同时也是人生命自身的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