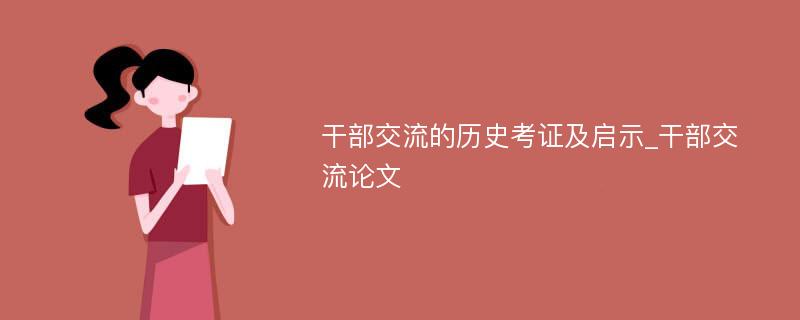
干部交流的历史考证及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迪论文,干部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政权组织的主体,干部队伍历来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其交流问题也始终是我们党干部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对中外历史上的“干部交流”进行考证,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建立具有新时期特点的干部交流制度,对于促进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使之充满生机和活力,对于提高干部素质,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加强干部队伍的整体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干部交流并非始于今日,历史上早已有之。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比较有作为的君主为加强封建统治就曾有过尝试。
战国时期体现皇权的玺印制度、上计制度就已蕴含着以君主的意志调动官吏易地做官的思想。
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皇帝总揽全国军事、政治、经济、司法等一切大权,“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秦王朝为维护统治秩序,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叛乱,也采用过易国封侯的办法。
汉朝初期,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强化了对文官队伍的管理,建立了客卿、察举、易地任官等制度,广开才路,多方谋人,求贤任能。为防止官吏任职期间亲族的攀扰,规定七品县令,必需脱离家族,离家三百里异乡做官,且为官期间发现有弊立即易地,重者惩处。
隋唐任官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对官吏的监督,同时,任官交流也较为定型和完善。官吏在一个地方任职多年,即使清廉无过,也要调往异地。
在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历代王朝除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易地任官的思想外,还采取一种仕宦谪迁措施。尤其是明清时期,不仅承袭了这一政治遗产,而且把它作为官员交流的主要政策措施。
仕宦谪迁是随着社会政治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处罚性官职调离手段,是处罚性的交流,通过对不称职的官员贬降异地,“俾历艰难,省躬悔过”,促使其克勤克谨地谋求政治前程。谪迁不仅可以惩戒有过者本人,亦可达到警醒百僚的目的,为官员提供宦辙前鉴,让他们心玩忽职守相戒,以勤廉任职互勉。
谪迁本来只用于惩处那些有过错的官员,但明清两朝出于政治生活的需要进一步发展了它。一些并无过失但亦无政绩的官员也常被谪迁。这虽失之于苛,但对于惩治贪官污吏,维护明清两朝的政治秩序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纵观历史,不仅中国历代君主体制都非常注意任官的交流,作为现代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官员交流也为世界各国政府所普遍关注。虽然社会制度存在着差异,但在官员轮换、干部交流上的主张都是比较一致的。
南斯拉夫政府,从主席到各部部长、副部长,任期都是四年,一般只能连任一次。这种限制任期与定期轮换的规定有利于防止执政官员的职业化、官僚化和长期垄断某项工作。
联邦德国的一些科研机构已经形成不成文的制度,每隔七年,就要大批吸收年轻人进来,原来的人员除了确实出类拔萃的骨干以外,一般都要离职,到其它部门去工作。联邦德国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明确规定:所长必须从外单位聘请,任期五年,到期无论有多大的成绩也必然换掉,以防止墨守成规。日本东京大学原子核物理研究所除少数技术人员允许固定外,行政人员和研究人员一律都不固定,每人只准工作五到七年,到期必须离开。
七十年代初,日本部分国家公务员中连续发生受贿事件。为此,日本内阁会议作出关于严肃官厅纪律的规定:“原则实行同一职员在任不得超过三年,对任期三年者,将进行适当调换。”避免这些实质性的职务权限集中于特定职员。
以上是中国历史和当今世界某些国家关于官员交流的简要情况。当然,由于阶级属性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无论是我国历史上的任官易地,还是世界各国的官员交流制度都与我国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不能否认,这种任官交流对于澄清历史上的吏治、惩治现实中的腐败、激发官员任职期间的向上心理,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应该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政治生活有所启迪。
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久握权力会使人腐化……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阿克顿也指出:“权力必致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这些论断,已被社会主义以前所有社会的政治生活实践所证明。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它们是否还保持效力?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固然有其崭新的东西,但它并非天外之物,仍不可避免的留有“旧社会的痕迹”。共产党人固然有其特殊的品格,但任何干部,包括领导干部都不是神仙。而是生活在一定亲族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人。这样,加之长久的居一岗执行公职履行公务,就很难摆脱旧习惯势力的影响和侵袭。因此,应该承认,权力对共产党人同样具有腐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干部交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各种干扰、腐蚀减少到最低限度,或使干部从可能造成腐化的羁绊中解脱出来。
消除中国社会现今党政机关存在的某些腐败现象,加强廉政建设,有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进行思想教育,二是强化制度建设。从历史的经验看,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要使执政党消除腐败、保持廉洁,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忽视,这是由商品经济的两重性决定的。
商品经济既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又容易诱发人们去接受一些消极、腐朽的思想观念,而消极、腐朽的思想观念一旦冲破我们某些干部的思想防线滋生起来,仅靠单纯的思想教育就不能完全奏效了。因此,在进行思想教育“软约束”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依靠纪律和法规“硬约束”的力量。
建立和实施干部交流制度,就是用法规性的“硬约束”手段,从时间空间、亲朋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联系上割断某些久居一岗的干部走向腐败的途径,以条件、环境或职务上的变迁根绝他们滋生腐化的可能性,以制度的限制提高防止他们蜕变的安全系数。这个道理就如同工业生产中为了保证人身和作业安全,对在有害条件下工作的人员,明确规定工作期限一样,因此,安全系数是很高的,而安全系数高,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就小。同样的道理,既然我们承认权力对共产党人也具有腐蚀作用,就应该将安全系数原理引入到我们的干部制度中,通过限制任期和定期交流,保证我们干部队伍的机体不受侵蚀。
当然,决不能说干部长年久居一岗就一定滋生腐败现象,但即使不是这样,也容易出现思想僵化、满足现状、守摊吃饭、不思进取的情况。尤其是取得了一定政绩、有了相当职位以后,更容易产生一种“安全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什么改革呀、创新呀,能戴住头上这顶“乌纱”享清福就行了。除非周围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动不行了,否则,决不对外部世界和改革者的意见作任何反应。长此下去,在客观环境的限制下,只能是墨守常规、安于现状。
而实行干部交流,给久居一岗多年的干部换一个新环境,他必然要经过一段适应期,然后才能进入具有创造性的自由王国。在这段适应期里,他要冷静的观察、思考,调整自己的心理适应能力,按照新岗位的要求,学习和构筑新的知识结构理论体系和能力素质。这段适应期是锻炼干部的最佳时期,能使许多人增长才干。
任何一位新官上任,面对新的岗位、情况、信息,既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认真分析什么原因使前任干部工作出现滞局,什么是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什么是当前稳定全局的主要因素;又不可能把适应期拖得太长,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期望,迫使他必须加紧开拓新局面,尽快做出决策和新的选择。这种新选择是他取得主动的基础,同时也是对他能力素质的一个考查。如何理顺自己高度紧张的情绪,忙中有闲、乱中取静,自觉地依靠群众,调查研究,摆脱“心理眩惑”,取得首任效益,从暂短的无序走向逐渐的有序,这是对新任干部适应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的锻炼和考验。
俗话说,静能生智。干部走上新的岗位,利用“静”的机会在新的环境中对原岗位业已平衡的各种心理素质予以内省、调整和重新组合,逐步实现新的心理平衡和构成,以尽快明确和接受新岗位所赋予的期望。这是一个心理素质自我调整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使相对稳定的个人心理素质趋向新的社会心理素质要求,进而削弱直至消除不适于新的社会环境需要的个人心理品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由于是社会环境对个人的检验,无疑会使干部本人克服掉以往一些不良的东西。由于环境的变化,习惯看问题的视角,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都要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这就给新到岗的干部提出一些新的课题,迫使他们必须进行新的学习和思考,这无疑在客观环境的限制上为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和条件,这些条件的获得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得到实现,而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通过在交流中个体素质的提高也就自然优化了。因此,建立并实行干部交流制度,是造就一支优秀干部队伍的重要战略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