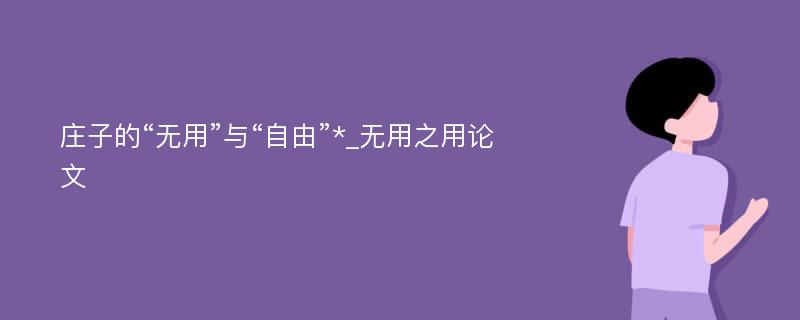
庄子的“无用”与“逍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逍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庄子深谙世人只知“有用之用”而昧于“无用之用”,在先秦诸子里最先也是最深刻地辨析了“无用”、“不材”等理论问题。笔者注意到,现学界多从生态哲学角度阐释庄子的无用之用,但生态哲学毕竟是因当今生态危机直接威胁到人及万物的生命存在而产生的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物的意义与价值的现代思潮。生态危机应当并不存在于庄子之时,生态伦理的问题谅也不会进入两千多年前庄子的视界,庄子不会为了解决所谓生态问题而提出无用之用。那么,什么是庄子倡言“无用”的初衷呢?“逍遥者,无用之大用也”(潘基庆《华南经集注》,见严灵峰,1972年,第12册,第63页)——“无用”之论盖从多层面透显出“逍遥”之意。
一、言的无用与逍遥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擁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塗,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遥遊》)①
这段文字置于《逍遥游》之末,自当关乎逍遥。惠子以无用之树讥刺庄子之言“大而无用”,那什么是惠子所责于言的“用”呢?惠子现实上重政治事功,自许有“全国家,安社稷”(《说苑.杂言》)之能,理论上重视思想对于现实的实际作用,自视其言无小用而有大用,②其“历物十事”作为“自然哲学”(韦政通,第232页),旨在藉名言分析和逻辑推论,研求天地万物之理,认为一切时间空间以及事物异同的区分俱非实有,从而推出“天地一体”之说,确立“泛爱万物”(钱穆,第214页)之义。“泛爱万物”或许是惠子之言对于现实的“大用”。庄子之言吞吐宇宙、凌迈俗情,荡佚于逻辑名理之外,非规矩绳墨所能限范,连“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秋水》)的名家巨子公孙龙,面对庄子的言说时亦不禁茫然自失,难以置喙;此等杂出无绪之言在惠子看来迂阔而不切实际,不能产生具体的现实效用。此“无用”乃是从现实功用层面对庄子之言的否定。
庄子则以大樗自喻“其言虽无用于世,而可以逍遥自得”(王叔珉,2007年a,第36页)。庄子旨趣不在析分万物之理,而在追求有限人生的逍遥游放;不像惠子那样要从理论上认识万物一体,而是要实际经验物我一体的境界。(参见冯友兰,第154页)在庄子看来,惠子囿于形器而不达大道,究心物理辨析而忽忘生命德性的修持;只关注物理世界(参见朱前鸿,第82页),不重人的心智情慧(参见钱穆,第214页)。庄子深察世间种种“大言”、“小言”皆生于言者的“成心”。“成心”即偏狭的是非分别心,言起则是非生,是非生则离析万物、遮蔽大道;道无是非,言有偏失。故此庄子《齐物论》在破拆儒墨各家是非之言的虚妄之时,连自己的言说也一并扫除。庄子对“言”更有深刻的反省:言只是达意的工具,言不可把握大道,大道不可言说,体道悟道的生命经验难以言诠,出神入化的技艺和人生体验难以言说,可见言在本质上是无用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最高的境界是无言。
既然无用,为什么又有庄子的言说呢?庄子有寓言、重言、卮言,其中卮言最显庄子的真机微旨;一定意义上,寓言重言也可涵括于卮言之中,如此则庄子全书“无一不是卮言”(张默生,第16页)。卮言是自然无心之言。当儒墨囿于各自偏狭立场,彼此奋其私智,自是而相非之时,庄子则“不谴是非”(《天下》),游心于道,倾听万物的言说。“倾听”非感官意义上的“听之以耳”(《人间世》),而是以虚灵明澈之心朗照万物。万物有其自然的分际,各是其所是,不是其所不是,庄子顺任万物,只是把所听到的万物的言说如其所是地说出来;惟其言出无心,故庄子虽有言说,不过是万物假庄子而显身,因而庄子的“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归根到底还是万物自己的言说;庄子虽言实未尝言。纵使庄子终身不立一言,万物仍旧以各自的方式言说生命的真意。庄子委曲顺随自然分际的卮言对于万物自身来说,真可谓有之无所增益,无之无所亏缺,确乎一种无用之言。庄子知天下沉浊,至言不止于众人之心,俗言大行于时,面对惠子的“无用”之嘲,自甘其言于无用之地。无用于世也就不为世塗所范限,与物无迕,无所困苦。更重要的是无用之言可以逍遥自适。“无何有”、“广莫”以喻道之本乡(参见潘基庆《南华经集注》,见严灵峰,1972年,第12册,第63页),也可视为以空间的虚旷无垠来表象心灵之逍遥遊放的四达并流状态。“树之无何有之乡”正是无待(参见叶秉敬《庄子膏肓》,同上第16册,第22页),无待方可通向逍遥。庄子言说大道,对于道的言说超世迈俗,固不可以寻常小用相责求,正如大若垂天之云的斄牛若强其执鼠则大谬一样。大樗不合规矩绳墨而无用于惠子,庄子用于规矩绳墨之外。人与无用之大樗逍遥彷徨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象喻庄子以其无用之言与物逍遥,逍遥自适正是庄子无用之言的大用。西晋郭象既批评庄子之言虽当于理而无用于现实,又认为读庄可以使人“游惚怳之庭”(《庄子序》),也就是无用之言可以任人逍遥游放于自由之境,可谓遥契庄生之旨。
如果庄子的无用之言仅仅停留在“汪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层面上,不免有退回心灵的无何有之乡、逃避现实困苦之嫌。然而,要看到“庄子非避世者,乃入俗而超俗者也”(王叔珉,2007年b,第112页),在另一层面上,庄子之言以其无用的形式深刻介入现实人生。《外物》云: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墊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
足之所践为有用之地,足所未及为无用之地,无用之地并非拙象的存在,它就在有用之地的周围并延伸开去。容足之外的无用之地正可任足自由行走,这便是无用之地的发用。如非无用之地的支撑,则向者容足之地亦难成其用。有用是在场的、显在的、有限的用;无用则是不在场的、潜在的、无限的用;无用之中不断涌现出有用之用,赖有广大的无用之地,方使有用之地得以成其用。祛除有用之用对于无用之用的遮蔽,才能察识有用之用何以可能。
无用之地以比无用之言。《天下》说:“百家众技”,“时有所用”,然此百家之言有用于世,其小何异于容足之地。庄子之言不专于一技一艺之用,故此无用。无用之言非但可以逍遥自适,更为现实人生因应世务的天府。庄子言说大道,栖神体道悟道的境界,旁涉心、性、命、知、生死等等问题;这些与外在物质需要无关,与个人功利目的相分离,不关直接的当下世用。凡此看来离人最远的无用之言,却在讲述人生最本己的问题。寻常人等囿于当下,拘于实用,对此了无自觉。殊未见庄子这些无用之言正作为远离当下实用的人生智慧,从超越的层次上关怀人生:必先深刻领悟生命中的这些所谓无用的事情,才能奠定有限人生的真正意义。相反,眼光仅限于当前的物用功利,就会“心为物役”,使生命的天机受到物欲的斫削,所谓“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宗师》),从而丧失对于人生意义的深刻领悟。《天下》称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与天地精神盘桓逍遥,游心于道,人不见其用,故谓无用。然而,惟有超越现实物用,才能领悟天地的真相,安顿有限的人生;“与世俗处”正是庄子的无用之言在现实人生层面上的发用。庄子揭示儒家的仁义礼与人的自然性情所存在的深刻矛盾,暴露人的各种价值观念、判断标准、是非之争的片面性和非真理性,警醒世人当持守性命之真而不被世俗价值和文化传统所异化;以心斋所达到的心体的虚灵妙应来调御暴虐之君,以乘物游心的心上功夫,因情顺势,处理复杂的邦国外交事务;以生死泯一于化涤除凡众对生死的缪见,融化生死关隘,把有限的个体融入万化之中获得无限的意义;以自然命定的思想揭示万物自然性的差异、人之生死的不可测度、人生遭逢际遇的不可知性的根源,让人洞达命理,安命顺化;以万物意义均等,在源始的意义上揭示人与万物一体共在。庄子更以道为生命的大宗师,逍遥游放为人和万物应然的存在方式。凡此在惠子看来是无用之言,最终莫不结穴于生命之中,在更高的层次上成为人生世用的源头活水,人生的出处行藏皆受其沾溉涵养。如同无用之地容人自由行走一样,无用之言所启导的智慧可以引领人生因应物情世事的万端变化,寄迹世途而游心物外,从而逍遥于天地间。自唐韩愈至近人钟泰,次第有以庄学出于儒门之论,此于史料和学理上固不足征,然其用意不外揭橥庄书隐含的淑世思想,将庄子的无用之言引入世用,开显无用之言的大用。
二、人的无用与逍遥
人的无用缘于庄子的忧生之思。“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至乐》),忧患与生俱来,成为生命本己的规定。因为忧患,生命才有免于忧患、追寻逍遥之境的内驱力。在庄子看来,当此人世背离了大道,大道遗弃了人世,生命存在失去了真理性意义。处身昏上乱相的人间世,尘网重重,免于刑戮已是幸事,而如何安顿必有一死的短暂人生、达至生命的逍遥境界,成为庄子“无用”之论的深刻追寻。前人早已看出《人间世》“匠石之齐”章“发明大木无用之用,与逍遥意同”(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九引赵以夫注,见《正统道藏》第25册,第20148页)的旨趣。
人的“无用”表现为生命对成为工具的拒绝。人唯有无用于世人,才能免于被谋划为工具,《人间世》从匠石只知有用之用而昧于栎社树的无用之用,经南伯子綦领悟大木的无用之用,到支离疏作为无用之人的大用,层层推进,其忧生之思归结为如何免于世患,全生保真,成就生命的大美。“世间所有困苦,惟以待用而起”(张栩《庄子释义》,见严灵峰,1972年,第30册,第43页),有用之材如柤梨橘柚等莫不以其材用而伤损自己的生命,中道夭于斤斧,不能尽其自然年寿。以人而言,颜回往说卫君、叶公出使齐国、颜阖将傅蒯瞶等等,例皆以其能苦其生(李贽《庄子解》,见严灵峰,1974年,第18册,第113页),“有用”竟成生命的祸患。“有用”固然取决于使用者对于物的看取,似无关物自身,但人、物自身似不为无失。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祸由自取。比干剖心,关龙逢被诛,或以仁义之言炫示于暴人之前,或以操行之高洁映衬出他人的污浊,“以出乎众为心”(《在宥》),卒致为世所嫉。全生保真,免于世患就必须韬晦其材,藏身于“无用”之地,“无用”即拒绝沦为物用工具。
“匠石之齐”章的栎社树不是一般的物,而是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有灵性的生命,是远祸全生之人的象喻;庄子以树说人,让树向人讲述无用对于生命的意义。栎社树不同于《逍遥游》中的大瓠,大瓠是被惠子目为无用之物,栎社树的“无所可用”是其自身努力探寻的结果。生命被谋划为物用工具,诸如作为舟船、棺槨、门户等等,具有多种可能性。成为工具即是对生命的伤毁:成为工具的多种可能性,意味着生命受到显在与潜在的各种谋划,具有受到当下或未来的多种可能的伤害毁损。要全生保性,就必须拒绝成为任何一种工具。面对每一种成为工具的可能性,必有与之相应的拒绝方式,于是对于物化为工具的拒绝成为守护生命的智慧。诸如以易沉于水拒绝成为舟船,以速朽拒绝成为棺槨,以易遭虫蛀拒绝作为梁柱,这些都是栎社树长久探寻所得的种种拒绝方式。拒绝了种种被物化为工具的可能,栎社树不在可用之数,遂成无所可用,无所可用也就无有伤害。无所可用之物才真正作为生命自身而存在,正是无用于成为工具才成就了栎社树的“大”,这个大是生命充分实现其自然性的一种美。“观者如市”,匠石弟子慨叹“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便是激赏生命的大美,也是对无用之用的惊赞。栎社树无所可用而天完具足的生命免于作为工具,这便是生命的逍遥。“庄之逍遥,在无所可用而已”(钱澄之《庄子诂》,见严灵峰,1974年,第30册,第41页)。栎社树作为不材之木,不同于远离人世、远在“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的大樗。大樗超然人世之外而与人逍遥,栎社树就在人间世,且寄托为社,正为人物聚集之地。在人物聚集之地,展现生命之大美,以无用而获无所为而为的观赏,正像喻了生命寄迹世途,藏身于无用,甘居不材之地,韬晦自全,在人间世作逍遥遊。
然而,无用是否一定免于祸患?天下之物以无用而速祸者不乏其例,盖缘材与不材、有用无用都是人从自身需要出发对物对人的一种衡定。需要因人因时、因地因世而异,对于人、物的材与不材、有用无用的衡定各各不同。“在一时一地一事无用……在异时异地异事则可以有用”(曹慕樊,第11页),无用于甲者或为乙者所用,向者之不材或成异日之大材。同为不材,《人间世》中的大木以其无用而存,《山木》中的雁以其不材而亡;同为材,《山木》中的文木以其合乎材用而夭于斧斤,雁则以其合乎材用而见存。看来人的有限心智无法料测何时当处乎“材”来避害,何时当处乎无用以远祸,专于材与不材、有用与无用俱不免于系累。原因在于材与不材对举而成,有用与无用相待而起,俱涉形迹,均未造乎至极。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可否双遣材与不材之累呢?庄子以为不然。“材与不材之间”貌似超越了材与不材的对峙,实则泥于“之间”,犹是执此“之间”以与材、不材相对待。可见无论材与不材以及二者“之间”总落入彼此对待之中,总受制于其所待,俱非绝对的全身之地,不能实现闲放不拘的无待逍遥。
于是,庄子超越有用与无用、材与不材及其“之间”的分别,使生命不至以其有用而遭损毁,不可因其无用而被伤害,世人“既不得以无材而弃我,而又不得以有材忌我”(陈懿典《南华经新解》,见严灵峰,1974年,第14册,第527页),由此达到绝对的无用之境,因应人情世事的莫测变化。这种绝对的无用之境体现为“乘道德而浮游”(《山木》)。乘道德即顺自然(参见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见周启成,第300页),顺乎物之自然性,也顺乎自己的自然性,遨游于“万物之祖”的大道之中。道体虚无,不涉两端,亦非中央。游于大道,既不专于材,又不专于不材,也不专于材与不材“之间”,这样虚以应物,与时消息,泛然不系,不为物累。俗情对此无法作出材与不材以及材与不材“之间”的任何衡定,先前材与不材、有用无用可能招致的一切祸患皆不能加。既不会如大瓠以无用而遭剖击,也不会如栎社树因无用而让人叹美,如此世人“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老子》五十六章)。相形之下,栎社树、支离疏等藏身于无用,而此则藏身于大道。材与不材、有用无用之迹俱化,因而较之前者更进一层。这种置身绝对的无用之境、遨游于大道的生命才真正消解了任何对待关系,消除了任何世患,俯仰自得于天地之间,回到自身独特的存在之中。
三、物的无用与逍遥
庄子的物兼万物及人自身,成玄英早将庄子关于物的无用之论溯至老子(参见郭庆藩,第936页),但老庄的分别当予廓清。《老子》十一章不否弃物的实有之于人的利益,然其用心不在器物的有、无两方面之相须为用,而是有见于寻常只知器物之实有方面助益于人,而器物中空无部分的成物之功多被忽焉不察,故而纠偏救弊,祛除器物实有方面对于器物空无部分的障蔽,开显器物有中之“无”的功用。至于物的无用之用,老子并未涉及。
庄子所研求的不是物的有中之无的功用,而是实有之物的无用之用。《逍遥游》云: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庄惠之辩实为庄子“明无待之义”(王叔岷,1988年,第38页),“自叙其逍遥之趣”(沈一贯《庄子通》,见严灵峰,1974年,第9册,第33页),以显无用而能逍遥。
要理解物的无用与逍遥,先须检视庄子对于人与万物关系的基本看法。一般意义上,庄子并不否认物之于人的利用价值:《在宥》认为物虽轻贱,人不可不赖外物以维持生命的存在;《达生》提出养护形体首先当凭借饮食衣物一类资生之具。利用外物自必对于外物有所作为,庄子循天道重无为,却不可因其“既言无为,则不当更言有为”,庄子“未尝有薄人道而不为之意”(钟泰,第243页)。庄子并不一概否定人对外物的作为,而是主张人为应以物的自然性为根据,应当因顺物的自然性而为。人对于物的作为应当“本乎天”(《秋水》),“天”就是自然生成不假一毫人为的物之自然性,此所谓“天在内”(同上);人为则是人出于自己的目的加于物之上的方面,此所谓“人在外”(同上)。“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在宥》),拂逆物性的断不可为,顺物之性的则为于其所当为。“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秋水》),络马穿牛固属人为,人为首先当洞察物的自然性,诸如牛可负重,马可致远,负重致远是牛马的自然性所使然,人皆因循之;因循物之自然性作为人为的最高原则,协调人与物的关系。因循物之自然性就是尊重物的主体性,人为必以物之自然性所能容受的范围为其界限,使得人的作为不至伤害物之自然性,不妨碍物自身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在绝对意义上,人为决不可逾越物之自然性所能容受的限度。越过这一限度,就是“以人灭天”,以人的作为毁损物之所受于天的自然命限,从而淆乱天地自然之经纬,悖逆万物之实情本性,导致“鸟乱于上”,“鱼乱于水”,“兽乱于泽”(《胠箧》),灾及草木昆虫之类。更重要的是,人为最终要消融于物之自然之中,使得虽由人为,却如同物之自为一样,此所谓“人伦万物,莫不自然”(成玄英《庄子疏》,见郭庆藩,第694页),这才是庄子有关人对物之作为的精义所在。但是,在这个层次上,尚未进入物之逍遥的境域。
进而再看庄惠的根本分歧。惠子其心量囿于实用,与大瓠只在单纯的实用层次上照面;实用之外,惠子对于物的意义了无所见。惠子是用物的主体,大瓠只是被量度具有何种实用功能的对象。惠子从自身需要出发,对于大瓠次第给出盛水浆和作瓢两个实用尺度,只要满足其中任何一个尺度,大瓠就成为有用的用具。作为用具,大瓠与其它任何能盛水浆、作瓢的用具无甚区别;大瓠之为大瓠就此消失于用具之中,在惠子那里已不再作为大瓠自身而存在。一当大瓠不能满足惠子的实用之需,便被视为“无用”之物。“无用”则意味着物没有存在的意义,惠子击破大瓠,实为以“无用”为由来否定物的存在。因而,惠子和大瓠在实用的层面上构成“有所待”的关系。“有所待”则相互对峙,相互制约;陷于其中的惠子只是实用层面上的人,大瓠只在实用的领域才显身于惠子,二者双双失去自身的完满性和丰富性,不能自在自得、逍遥遊放。
庄子对单纯以物用需要来衡定物之意义加以反省与批判。物的意义绝不止于满足人的物用需求,《马蹄》认为粘土树木虽以其材性合乎人的物用尺度,可用来制陶作器,济人所需,但粘土树木和人的物用尺度并无源始的一致性,更不是为了符合人的物用尺度而存在。物的有用性只是物遭遇人的需要而发生的实用价值,不是物的意义的全部,更不是物之于物自身的意义。物的意义决不在于满足人的物用需求,在物用之上之外,物还有更重要的属于自身的东西。
庄子戏惠子“拙于用大”,似乎意味着自己善于用物之大。拙于用大和善于用大都落脚于“用”。庄子在惠子的盛水浆、作瓢之外,为大瓠找到了浮遊江湖之用,这个“用”是超越现实物用之上的无用之用,即所谓逍遥遊放于自得之场。庄子以虚灵之心面向物,看到古之体道圣人从不以同一种才能去要求万物,也不以同一种标准去度量万物。万物皆有各自独特的功用,也有各自不具备的材性。顺着万物之所可、之所是的方向来看,万物皆有其所可,皆有其所是,都有存在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来自人的给予,而是来自人与物所共同的本原之道,道通万物而为一。从道的立场看,万物无贵贱之分,人与万物意义均等,故应因循物的物性,任物各是其所是。庄子批评鲁侯“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至乐》)的养鸟方式,把自以为善美的东西强加于物,全然无视物的物性,只是以其自养之法来养鸟,而不是以鸟的自养之法任鸟自养。鲁侯爱鸟未尝不深,但这种爱实为奴役物性以快己意。适合于人的,未必宜于物;人有适于人的存在方式,也应该听任万物各自获得适于自身的存在方式,诸如鱼以处水为宜,猿猴以腾挪于树木为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跳出人自身的单极立场,以道眼观物,“兼怀万物”(《秋水》),物各付物。
庄子不从自身需要出发先行给大瓠设定尺度,此所谓“无己”,也就是祛除了偏私的功利心,把自我对于物的狭隘的物用尺度虚掉了。“用大”之用似涉人的作为,但人的作为在这里体现为纯任自然、因循物性,让大瓠是其所是,无有造作施为,因而是无所为而为。所以,庄子的“用大”不是惠子的“以己用物”,而是“以物用物”(参见王夫之,第8页)。顺大瓠之大而以之浮遊江湖,便是虚己以应物,顺物而不失己。浮遊江湖遂成大瓠的无用之用,用物的无用之用便是庄子“用大”的精意,如此“不设成心,随物为用,乃能尽逍遥之趣”(张之纯《庄子菁华录》,见严灵峰,1974年,第41册,第9页)。因而,人与物的彼此对峙、相互约束涣然冰释,游离于实用之外的人与物皆“无所待”,由无己而无所待就是逍遥。这样,“无用”实际上是人的与物为娱,与物为娱成为逍遥的发生地,将人和物带入逍遥之境,“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游》),呈现了人与物的一体共生的逍遥图景。物的逍遥就是物的自在自得,“自在”就是物以本己的方式存在,物始终存在于自己的本性之中;“自得”就是物各得其本性,得其本性才是物各成其为自身的“得”。
可见庄子所讲的逍遥并非限于人自身,而是涵括天地万物,将人的逍遥游放与万物的自在自得并置而论。人作为一物,与万物没有绝对界限,皆是气之聚散。“化”是人与万物的存在方式,万物万化,人与物只是以不同的形相委蜕嬗变于天地之间,人所称美的视为神奇,人所厌弃的视为腐朽,殊不知“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知北游》),如此万物齐一,意义均等。贵己贱物,是人囿于自身而对于物的歧见,设若物也取人的偏执立场,必然贵物而贱人,自会导致人、物相贱而自贵,终至贵己者必遭他物之贱视,如此“相刃相靡”(《齐物论》),势必造成人、物的紧张关系。庄子更重视物我一体,在对于“至德之世”这一远古氏族时代的史影描述里,蕴涵了庄子关于人与万物一体逍遥的怀想与憧憬。人有人的规定性,物有物的规定性,人作为一个族类“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人之与物各各是其所是,人不因物失去人性,物不因人失去物性,此时“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雀之巢可攀缘而窥”(同上),人与物各自持守自己的本性,人在“鼓腹而游”(同上)的同时,与万物共同嬉游于天地之间,卒至人忘其为人,物忘其为物,“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山木》),这是人与万物一体逍遥的景致,是生命自在自得的初始图像。
人的逍遥不能离开物的逍遥而独存,当人把物仅作为利用对象时,人与物俱梏于实用。人受制于物欲,物依赖于人的需要,“人支配了物”,“物也支配了人”(彭富春,第52页),如此人与物两两对峙,俱不能逍遥遊放。在人对于物的无所为而为、物对于人的无用之用的状态里,人与物双双顿开利用的系缚,人不为物累,物不为人役,人与物各各回到自身,物尽其物性,人尽其人性,各得其所,于是人与物相契于春和一样的境域,处在“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大宗师》)的逍遥之中。人逍遥游放于天地之间,物也闲放不拘于天地之间,个中蕴含的深意在于:物的逍遥与人的逍遥是一体之两面,没有物的自在自得,人的逍遥终究只是一种幻象;一旦人妄作妄为,破坏了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逍遥,人的所谓自由终将因失去潜在的基础与前提而幻灭。
*本文实就《庄子》全书展开论述,为行文之便而称庄子者,均指庄书而言。
注释:
①文中所引《庄子》均据郭庆藩《庄子集释》,引时只注篇名。
②据《吕氏春秋·应言》,白圭认为惠子之言如同“市丘之鼎”,虽大且美,但并不实用。惠子则以鼎可以为饥饿的三军作蒸食的炊器,自喻其言无小用而有大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