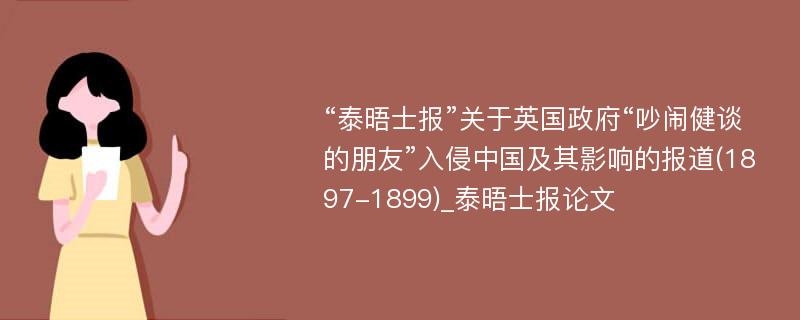
英国政府的“一个吵闹而多嘴的朋友”——《泰晤士报》对列强侵华活动的报道及其影响(1897—1899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政府论文,泰晤士报论文,列强论文,朋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 )02—0086—06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争夺的一个焦点。作为当时英国影响力最大的非官方报纸,《泰晤士报》对列强在中国的争夺进行了及时深入、形式多样的报导,是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道本身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该报的报道和主张不仅经常成为欧洲各国间外交涉的依据,而且作为有代表性的舆论力量,也是影响英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在初步梳理《泰晤士报》1897—1899年有关列强侵华报道的基础上,分析其史料价值,进而探讨这些报道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
一、《泰晤士报》有关列强侵华报道的史料价值
长于报道海外事务,追求独家新闻,言论有力,不为当局所左右,这是19世纪中叶全盛时期的《泰晤士报》的主要特点。到1898年前后,英国的报业竞争已经使该报一家独大的地位有所动摇,但这些特点仍体现在该报对列强在华行动的相关报道中。我们试做如下的归纳。
(一)持久追踪,频繁报道。《泰晤士报》对列强在华利益争夺的关注程度从报道的数量上即可见一斑。从1897年11月16日第一篇关于德国进犯胶州湾的报道开始,该报关于中国事务的报道数量急剧增加。最初几个月中,几乎每天都有相关的文章,有时甚至一天有来自不同渠道的多篇报道。据初步统计,到1899年底之前,仅是标题中包含“中国”或“远东”的新闻就将近600条。 此外其他相关新闻以及重要演说、社评、读者来信当中内容涉及中国者数量也相当可观。这些报道中,除少量涉及中国的维新运动、地方叛乱、疫病以及风土等内容外,绝大多数都与列强的军事、外交和商业争夺有关。许多报道常常包括来自驻中国和世界各地记者发来的多篇电文。如1898年4月6日第7 版题为“列强与中国:法国的要求被认可”的一组报道中,就包含了该报记者和路透社记者发自北京、横滨、圣彼得堡、柏林、巴黎、维也纳的9条消息,还附有对法国刚刚租借的广州湾的一个简介。[1](Apr6,1898) 此外第15版还载有一篇题为“俄国与德国在中国的地位”的长篇读者来信,这样当天有关报道就使用了大半个版面,共达5000多词。
(二)形式多样,来源广泛。如上所述,《泰晤士报》有关列强在中国的行动的评述,使用了新闻、社评、通讯、特写、要人演说、议会辩论记录以及读者来信等多种报道形式。该报庞大的记者队伍和广泛的消息来源构成了一个遍及世界的信息网络,保证了其报道的全面与深入。我们知道《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莫理循和驻上海的濮兰德(J.O.P.Bland)① 是完成前方报道的主要人员,他们的报道相当重要,但还只是该报涉华报道的一小部分,其派驻欧洲、美国、日本各主要城市的记者以及在英国国内的记者编辑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驻外记者发回的电稿,一部分是自己采访搜集的最新消息,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当地报刊的摘要或综述,文中往往还夹杂着记者自己的评判和对英国下一步行动的建议。而在英国国内的记者,则密切跟踪外交部、议会等有关机构的最新动态。此外,政商各界领袖在各种场合的言论也会被他们及时刊载出来。比如首相索尔兹伯里的几乎每一次重要演说都可以在《泰晤士报》上找到原汁原味的记录。经常刊载各界人士的来信,也是《泰晤士报》的一大特色,他们常常在重大问题上以专家或当事人的身份建言献策、左右舆论。社论则是《泰晤士报》自己立场和观点的鲜明展示。社论中常常极力鼓吹攫取在华利益,并积极出谋划策,对于保守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则不时冷嘲热讽,甚至激烈批评。
(三)新闻及时,大致准确。与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19世纪末已堪称“信息时代”。1841年在中国的璞鼎查接到发自英国国内的训令要数月之久,而此时电报的使用已使记者可以把世界各地的新闻即刻反馈到国内,发达的报业又使这些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公众当中。由于有遍及世界的记者网络,加上莫理循等记者的巨大活动能力,当时《泰晤士报》能及时得到有关中国的新闻并予以报道,甚至比英国政府的情报还早,而且它刊登的大多数消息最后都能得到证实。莫理循短时间内就在北京建立起庞大的情报网,其能量“甚至连最有进取心的情报人员都望尘莫及”。② 事实上,驻其他各地的记者在报道有关消息时也不逊色。 以德国在胶州行动的有关报道为例,《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11月15日就发回电讯,称德国在东亚的舰队接到命令向山东海岸进发,以要挟得到对两名传教士被谋杀事件的补偿,[1](Nov16,1987) 第二天又发回德国军舰已经在胶州湾登陆的消息。[1](N0v,1897) 而英国政府迟至18日才接到驻华公使窦纳乐的电报,确认了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报道。[2](P18) 不过,由于当时记者的情报并不是在得到官方证实之后才报道,因此也有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被刊载出来。如该报在1897年12月10日报道说德国近期将放弃胶州湾,转而占领福建的三沙湾,遂引起各国的关注。最后德国官方专门就此发表声明,称《泰晤士报》的有关报道是“完全的捏造”。不过《泰晤士报》倒也不避讳,德国政府的声明和舆论的指责也都照登出来。[1](Dec13,1897)
《泰晤士报》的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报道,涵盖了列强瓜分中国行动中的方方面面,为这段历史保存了不同于各国官方文件的另一套文本,因而颇具价值。
首先,该报对事实的及时披露和紧密追踪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史实。大众媒体对事实的及时报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实录当代史,而且往往比任何官方文件都全面丰富。由于它的记录以天为单位持续进行,我们可据以充分还原时人了解和应对每一次行动的过程,甚至确证或订正一些史事。如法国强租广州湾(及雷州湾)的谈判,学界一般采用翁同龢日记中的说法:在1898年3月7日法国提出“补偿”要求后,经过多次谈判,法国在4月9日提出照会底稿,宣称“不准动一字,限明日复”。总理衙门被迫屈服,于第二天(即4月10日)交出复照两件, 答应了法国划定势力范围、强租广州湾等要求。[3](P67—69) 但《泰晤士报》记者早在4月5日就从北京发回电稿,称中国已答应法国的要求,并且指出法国同意保留英国在九龙拓界的权利。[1](Apr6,1898) 由此可以推断,总理衙门的屈服,应该是在4月9日之前, 而所谓的“限明日复”的照会底稿及第二天的复照,看来不过是既定的程序而已。此外,《泰晤士报》还通过摘编各国报章报道而详细记录了每次重大事件之后各主要国家的舆论反响。比如,德国的《科隆日报》、《北德宪报》,法国的《时报》(TEMPS)、《辩论报》(DEBATES),以及俄国、奥匈帝国、美国、 意大利等国的影响较大或代表官方立场的报纸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言论经常被转载在《泰晤士报》上,这是其他档案文献难以做到的。
其次,该报的大量言论及对新闻背景的分析和介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时人的心态,进而理解史事发展的动因与方向。在报道重大新闻的同时,《泰晤士报》常常发表社论或读者来信,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各方的动机、目的,下一步的走势等,然后阐明该报的立场,并对英国的行动提出建议。这些言论传递着时人的观念,反映了支持扩大侵华的英国工商阶层的态度,因而对现今的研究者而言,亦弥足珍贵。
该报的新闻背景分析与介绍一部分体现在适时刊登的所谓“中国通”们的读者来信当中,一部分则是该报记者配合新闻报道而撰写的许多长篇综述性文章,其中有的是对重大问题的阶段性总结,有的则就某一方面热点问题做综合评述。这些综述为英国人了解关于中国的事务提供了详尽的背景知识,为当局制定下一步侵略政策进言献策,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也不乏参考价值。
当然,在利用这些材料时,必须注意其明显的倾向性。《泰晤士报》虽然标榜不受英国官方左右,但这远不意味着它的报道已经做到了客观公正。相反,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商报之一,加上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各大公司的工商广告,《泰晤士报》常常毫不避讳地站在工商界的立场上为之摇旗呐喊。尤其在19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膨胀的背景下,该报更是成为了英国对外扩张的吹鼓手。它奉自由贸易为神圣信条,一方面把英国描绘成中国唯一的真正的朋友,另一方面又时时称中国为“半文明”甚至“野蛮”的国家,声称对付不愿全面融入其经济体系的清政府只能使用“炮舰”政策,由于清政府不能阻止其他列强攫取特权,从而破坏了英国在中国的商业优势,因此必须牺牲中国的主权而做出“补偿”。只有把握这一背景,我们才能对该报的报道和评论形成正确的判断,进而批判地加以甄别利用。
二、《泰晤士报》有关列强侵华报道的影响与作用
当然,我们重视《泰晤士报》的报道,不单纯因为它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作为当时在英国甚至全世界影响最大、辐射最广的报纸,该报代表的公众舆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在相关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泰晤士报》的报道是大众甚至政府的信息来源,客观上充当了当局的耳目,有时甚至起着喉舌的作用,许多报道和评析还成为英国与他国外交交涉的基础。对于该报涉华报道在英国的影响,莫理循的上司曾经不无夸张地说,“你发来的电讯在伦敦被视为权威。即使你编一个完全的谎话人们也会相信,因为它是出自你手。”③ 虽然首相索尔兹伯里经常把《泰晤士报》的报道斥为“报纸的谣传”,但从英国外交部与驻各国使馆的往来公文可以看到,当时很多重要情报英国官方确实是首先从《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得悉的,然后它才下令其外交人员予以查实或采取应对措施。
1898年3月7日,《泰晤士报》以“列强与中国:俄国的要求”为题,率先报道了俄国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湾的消息。索尔兹伯里从该报获悉这一消息后,3月8日即致电驻俄国公使欧格纳,指示他向俄方询问消息的真实性。欧格纳当天就约见了俄国外交大臣莫拉维耶夫伯爵,“向他读了《泰晤士报》的有关内容”,然后问他内容是否属实,对方回答确有其事。[2](P60、61、63)
此后不久英俄关于旅顺大连签证问题的交涉,更凸显了《泰晤士报》的影响力。1898年5月12日,《泰晤士报》刊登如下消息:俄国驻天津的领事知会其同僚, 外国人要进入旅顺和大连湾,必须持有经俄国领事签证过的护照。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强烈地反对这项决定,因为总理衙门曾明确地通告其下属,这两个港口应与其他商埠同等对待。[1](May12,1898) 索尔兹伯里看到这条消息后,当天即命驻华公使窦纳乐查实此事。13日得到窦纳乐的确认后,翌日他又致电驻俄公使欧格纳,要其就签证一事向俄国提出抗议,理由是此举违反了《天津条约》有关规定。欧格纳在16日回电报告说,俄国外交大臣已答应就此事进行解释。20日又报告说,俄国已下令收回签证的命令,并称那是其驻天津领事擅自采取的行动,俄国外交部并没有下达要求签证的命令。但据窦纳乐22日的报告,俄国领事说自己确实是按照外交部的训示行事的。[2](P188、190、192、198、202)
英国政府的交涉显然不能令《泰晤士报》及在华的英商满意,而且实际上俄国驻天津领事也并没有收回签证的要求。于是,《泰晤士报》在23日又刊登消息:“英国政府看来默认了一项通告,即没有由俄国领事签署的签证,英国人和任何外国人都不能登陆大连湾和辽东半岛。这一通告被认为是限制大连湾外国通商自由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并提出“显然有必要在大连湾任命一个英国代表以维护英国利益。”[1](May23,1898) 英国外交部在舆论压力之下继续交涉,终于使俄国有所让步。窦纳乐在6月1日报告说,俄国的最新规定是,前往这两个地方必须持有护照,但是否由俄国领事签证则自便。索尔兹伯里回电说,要求护照也不符合《天津条约》第9条的规定,只有进入非通商口岸的内地才要求外国人持有护照。 之后窦纳乐和欧格纳分别在北京和圣彼得堡多次与俄方交涉、俄国最终仍坚持前往旅顺必须持有护照,而大连湾则“暂时”不会要求护照。[2](P218、219、226、237、238、267、277)
正当这些交涉进行之时,神通广大的《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又从“完全可以信赖”的渠道弄到了中俄关于租借旅顺和大连湾的协议,并立即全文刊载出来。[1](Jun3,1898) 英国政府发现这个秘密的协议中有更多“破坏”其在华利益之处。于是,首相索尔兹伯里又赶紧命令驻俄公使欧格纳向俄国政府提出抗议,指出这个协议违反了俄国曾向英国做出的保证。[2](P226)
(二)《泰晤士报》与各国主要报纸间的新闻战,已成为列强之间对华权益争夺的一个重要战场。当时,列强虽然都垂涎于中国,在特权和势力范围的争夺上互不相让,但各国政府在表面上还尽量保持着矜持的姿态,避免彼此间爆发直接冲突。于是,各国的“非官方”报纸就成为相互试探并进行暗战的武器,各报常常指责对方的行动破坏了本国的利益,违反双方已有的谅解,进而建议本国政府要采取某种行动以谋求补偿。《泰晤士报》虽然不受政府支配,但作为商界的代言人,它在这场争夺中甚至比英国政府更加卖力。该报不但发表了很多言论,也积极转载其他各国大报的观点。
比如在报道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消息时,《泰晤士报》专门配发了社论,强调胶州据闻已经被中国许诺给俄国,因此德国不大可能永久占领。[1](Nov16,1897) 德国报纸马上予以反驳,并指责《泰晤士报》是试图鼓动俄国反对德国的行动。[1](N0v18,1897) 之后德国报纸又声称,德国的整个行动是在俄国的同意下进行的。甚至有德国报纸说本国的行动在俄国可能很受欢迎,因为选择德国人在亚洲做邻居,无论如何要比与英国为邻好。《泰晤士报》记者在转述这些报道后称,这些报道明显有官方授意之嫌。[1](Nov23,1897) 在法国强租广州湾期间,《泰晤士报》与法国报纸之间进行了论战。
有时,当各国分赃已毕,政府也会出面制止各报之间继续争论,甚至使报纸成为互相示好的工具。如俄国在霸占旅顺之后,马上向所有报纸发出禁令,不许发表任何关于德国在中国行动的攻击性文章和评论。它们被提醒要记住俄国与德国的关系是“最友好的”。[1](Dec24,1897) 德国外交大臣毕鲁(Herr von Bulow)在胶州湾问题上与英国达成谅解之后对记者表示,德国在中国的行动没有造成与包括英国在内的任何大国的冲突。“如果有时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的话,事实上也不能代表英国政府,而是出自个别的英国媒体,它们的看法并不符合事实。”[1](Feb9,1898)
(三)《泰晤士报》的报道已成为影响英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它积极为英国的侵略扩张进行鼓动,使政府的行动得到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它也把政府置于舆论的压力之下。虽然英国政府在这场争夺中机关算尽,捞到不少好处,但对于一心只想保持本国在远东的霸主地位的《泰晤士报》来说,索尔兹伯里领导的政府显然做得还不够,而该报的消息灵通也恰恰反衬了政府在外交情报搜集上的闭塞和迟钝。这一时期的《泰晤士报》对当局的嘲讽与指责几乎从未间断。英国政府常常被迫回应《泰晤士报》的指责,为自己的行动辩解,时而也对该报的多嘴多舌反唇相讥。而私下里,官员们又不得不承认报界的压力,张伯伦在1898年2月3日写信给巴尔福说,“如果你读了最近的报纸,一定会同意我的感觉,那就是政府如不在中国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将面临很大的麻烦。”[4](P65)
长期以来英国在外交事务上由首相索尔兹伯里大权独揽,几乎达到了“独裁”的程度,外交部的次级官员们在重大决策中也无足轻重。[5](P59) 他还规定外交次官可以拒绝回答下院的提问,于是外交部变成了“像坟墓一样”难以渗透的部门。[6](P[863—868)
但是,《泰晤士报》却大有破坏这种外交“独裁”之势。当时该报已经不接受政府的资助,当局无法凭借经济控制来操纵它,通过扶持官方报纸打压《泰晤士报》也以失败告终。同时,言论自由的传统使英国政府又无法对本国报纸的报道强行控制。因此,《泰晤士报》不但把英国的外交行动传播给公众,而且为许多反对派提供了发表见解的舞台,这样就在客观上把英国的外交事务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了。面对这种局面,就连索尔兹伯里政府也毫无办法,只好勉强应战。
《泰晤士报》对索尔兹伯里外交政策的批评由来已久。1897年10月该报驻上海记者关于英国对华政策的回顾与总结中,直截了当地说,过去的30多年里不但在突破中国与世界之间的阻隔方面几乎毫无进展,而且英国通过“鲜血和金钱”换来的许多权利也任之丧失。[1](Oct18,1897) 俄国派遣一支舰队在旅顺港“过冬”后,《泰晤士报》随即发表社论批评本国在德国占领胶州后行动迟缓。随后,它又借助一封读者来信批评索尔兹伯里在对华贷款谈判中优柔寡断,浪费了“对英国最好,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1](Dec28,1897) 不久,英国在俄国的抗议下从旅顺撤走军舰,放弃开放大连湾的要求,并且在对华贷款谈判中再度受挫。借此机会,《泰晤士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或转载各方的评论,批评政府的外交屡次被俄国挫败,对英国的利益和地位极为不利,[1](Feb1,1898) “英国人在大陆的形象再次受损”。[1](Feb4,1898)
显然《泰晤士报》低估了英国政府在华掠夺的决心和能力,其实它早已在为获得“补偿”而对清政府软硬兼施了,只是索尔兹伯里信奉秘密外交,认为这样既得好处,又不得罪其他列强。因此,“蒙冤”的英国政府也会抓住机会攻击《泰晤士报》。比如政府指责说,俄国之所以插手贷款谈判,阻挠开放大连湾,就是因为《泰晤士报》的报道泄密所致。1898年1月17日,《泰晤士报》披露了英国贷款谈判的进展,指出英国的条件之一是增加大连湾、湘潭、南宁三个通商口岸。[1](Jan17,1898) 结果,俄法公使马上提出反对英国新开口岸的要求。[1](Jan18,1898) 面对官方的指责,《泰晤士报》认为政府孤陋寡闻,过高估计了清政府官员保守机密的能力。事实上在每次重要的秘密会谈之后,消息灵通的外国公使和中国官员都能知悉会谈的进程。[1](Feb9,1898) 不过,《泰晤士报》这样说显然是要嫁祸于人, 因为莫理循在1月17日曾写信给濮兰德,承认他的消息得自汇丰银行, 而非清政府的官员。④
官方与《泰晤士报》的交锋达到白热化,是在1898年5月初, 此时德俄法均已在中国攫取了各自的特权和势力范围,英国也取得了威海卫,并把长江流域据为势力范围。但是,在商界和反对派看来,别国的特权都是在破坏了英国利益的情况下取得的。尤其是4月初出版的《英国议会文件:关于中国事务的通信》(俗称蓝皮书)中提供很多交涉细节印证了人们的这一印象,因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大增。于是,一场针对政府对华政策以及索尔兹伯里本人的激烈攻击由《泰晤士报》发动了。[7](P145) 4月30日,该报发表评论,指责政府在华政策是彻底失败,并声称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首相大权独揽造成的。[1](Apr30,1898)
5月4日,索尔兹伯里在保守党的樱草花联盟(primrose league )集会上发表了演说。这次演说因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生机勃勃的国家将医治或宰割奄奄一息的国家”的论调而经常被史家提及,④ 事实上这次演说中索尔兹伯里在为自己的远东政策进行辩护的同时也对媒体的插手表示了不屑。他说外交问题只能通过结果来评判,公众舆论不可能通过在结果形成过程中的个别状况来做出正确的判断。他认为,目前英国在远东的外交结果“不是很令人失望的”,因此他不能理解一些中间环节何以造成那么大的激动。针对英国已经失去了在远东的威望的指责,他说,“一般而言,当外国报纸说英国丧失了威望的时候,那意味着这些国家希望我们帮他们火中取栗。”[1](May5,1898) 与此同时, 支持政府的一位议员也在当天的一个宴会上翻出《泰晤士报》泄密的老帐,指出由于该报的不谨慎,英国与清政府以开放大连湾为条件而贷款的谈判才以失败告终,“一个经常宣称只关心商业问题的报纸,在把本国政府的底线暴露给全世界前,一定要考虑再三才行。”[1](May5,1898)
当然,《泰晤士报》对官方的辩解与指责并不买账。在刊登索尔兹伯里演说的同一版面,它首先刊登了一位自由党议员的演说。对于政府在远东的表现,他总结为最初高调威胁,但没有行动,然后步步退让,结果颜面尽失。接着又刊登了一封署名为“一位托利党议员”的读者来信。该议员认为英国在远东“耻辱的失败”明白地显露在蓝皮书中,也展示在全世界眼中,无法通过一场辩护来掩盖。[1](May5,1898) 在制造了索尔兹伯里已经“众叛亲离”的印象后,《泰晤士报》用一篇社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它说指责《泰晤士报》泄密是试图转移视线,也是毫无用处的。索尔兹伯里担任首相的同时长期把持外交部,已经造成日益增加的不安。首相的演说丝毫没有能够缓解这种感觉。[1](May5,1898)
官方与报纸的争论一直持续,索尔兹伯里继续为他的秘密外交辩护,要求媒体闭嘴。一个多月后在联合俱乐部(the United Club)的周年晚宴上, 他仍要求人们对外交不要妄加评论。他说他现在不断收到驻外人员寄自世界各地的电报,提出同一个请求:“你越多地保持沉默,我们的工作就会越顺利。”“他们感到最难以忍受的,就是英国大臣和政治家们的能言善辩——也许我应在这里加上报纸的多嘴多舌。我常常在想,现在与别国斗智的英国外交人员的处境,就像是一位扑克牌玩家的身后站了个吵闹而多嘴的朋友,不断地大声议论他手中那些牌的大小。而同时他的对手们却完全肃静,完全没有过分好奇的朋友,只是安静地实施他们的计划。”[1](Jun30,1898) 索尔兹伯里的抱怨不无道理,媒体不可能知悉外交活动背后的真实交易与谋划,比如晚近的研究者利用解密的文件证明英国租借威海卫意在遏止德国而非俄国,[8](P1157—1179) 这是当时人们不可能了解到的。不过,无论这位首相多么不自在,《泰晤士报》这位“吵闹而多嘴的朋友”都没有丝毫安静下来的迹象,其影响也不容小视。
以上的分析虽然只涉及《泰晤士报》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事务的大量报道中的一小部分,但已能显示该报当时产生的重要影响。作为英国工商界的代言人,《泰晤士报》毫不掩饰自己报道的倾向性,公开站在英帝国扩张主义者的立场,处处强调本国的权益,积极鼓吹参与列强争夺,扩大对华侵略,使我们多少看到了英帝国侵略者隐藏在官方“矜持”外表之下的真实形象。虽然该报经常不满政府的表现,不时抨击官方的政策,但是我们从双方的论争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侵略策略不同的反映,在侵略和扩张的本质上并无二致。该报更多地扮演着当局侵华的耳目、参谋和吹鼓手的角色。它虽然“吵闹而多嘴”,但终究是英帝国一个“小骂大帮忙”的朋友。
注释:
① 濮兰德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秘书,兼任《泰晤士报》驻沪通讯记者。Lo Hui-Min ed.,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1,p.48.中译本第59页。
② Lo Hui-Min ed.,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1,p.41.中译本第50页。
③ Lo Hui-Min ed.,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1(1895—1912),p.127.中译本第156页。
④ Lo Hui-Min ed.,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1,p.62.中译本第76页。
⑤ 见[英]菲利浦·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胡滨译,立人校,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11页;[英]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刘存宽、张俊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