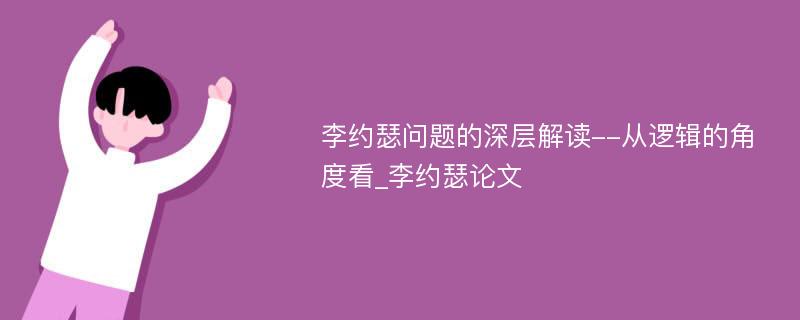
“李约瑟问题”的深层解读——从逻辑的观点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观点论文,李约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2)01-0018-04
“李约瑟问题”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一经提出,它便一直困扰着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学术界。由于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人给出过满意的解答方案,而且由于它牵涉到一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学界又称其为“李约瑟难题”。
一般讲来,“李约瑟问题”可以这样表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即在古代和中古代,中国人对于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发展,究竟做出了什么贡献?虽然自从耶稣会传教士在17世纪初叶来到北京以后,中国的科学就已经逐步融化在现代科学的大熔炉之中,但是,人们仍然可以问:中国人在这以后的各个时期里有些什么贡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又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1]?简而言之,“李约瑟问题”的大意是:大约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西方,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却诞生在西方,而没有诞生在中国呢?
国内许多学者为了解决“李约瑟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探索,并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有的学者从对“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入手来阐发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李约瑟先生所说的“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科学技术”,是指在文艺复兴后的16、17世纪中国没有出现诸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力学这样的科技成就,而这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用西方人的观点、方法和成就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若就此而论,李约瑟所说的“在16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就完全站不住脚,因为事实上,在16世纪以前,中国只是在技术和在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在自然科学方面从来没有走在过世界的前列,甚至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独立的、系统的自然科学理论。按照这种观点,“科学”应当是由概念、定律、定理、公式和公理等要素组成的具有逻辑自洽性的知识体系。而若以此而论,中国历史上的《墨经》、《徐霞客游记》、《九章算术》、《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等著述,或者是对自然现象进行的较为细致的描述,或者是对经验的较为系统的总结,或者兼而有之。但它们都不能算作是自然科学著作。这样,“李约瑟问题”的表述应修改为:16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在许多方面都超过西方,但后来近代技术为什么诞生在西方而没有诞生在中国呢?而且中国为什么一直未出现过任何自然科学体系呢[2]?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主张“中国古代没有科学”。
有的学者不同意上述看法,反对“中国古代无科学”的主张,他们认为中国古代不是只有技术而没有自然科学。在这种观点看来,经验的总结,并将其系统化,提出一种假说来概括这些经验,就是科学。就此而言,前文所列著述均在科学之列。他们认为,之所以产生“中国古代无科学”的看法,原因是:(1)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人们研究不够,却用西方的科学模式来衡量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2)欧洲中心主义者故意不提中国的发明创造;(3)中国古人没有专利的观念,所有发明创造都没有署名;如此等等[3]。
笔者认为,学界的这些争论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这种意义并不在于是否能够提出“李约瑟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而在于提示我们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再思考。这些问题包括:(1)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2)为什么中国的近代科学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实际上这也正是“李约瑟问题”的系统表述中所包含的两个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两个问题是紧密关联着的,对其中一个的解答也就是对另一个的解答。
按照本文的观点,“李约瑟问题”的表述本身的确存在着概念的混淆。李约瑟先生没有对“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给予明确的界定和清晰的区分。正是由于在这一点上认识的不明确,才导致了学界许多误解的产生,从而大大妨碍了对“李约瑟问题”实质的把握。
关于“科学”与“技术”两个概念的界定和区分,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至少有一些是应该成为共识的,即科学是一个理论体系,科学的本质特征在于理论化、体系化。相比之下,技术则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它具有更多的实际应用性。科学的任务是解释和认识自然,“求知求真”。技术的任务在于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经世致用”;科学研究的成果是抽象的理论,而技术发明的成果是具体的物质产品。技术以经验为直接基础,“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4],然而,技术毕竟是人类用以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手段和方法,不能总是停留在“知其然”的水平,还必须“知其所以然”。并且,也只有“知其所以然”,才能更新原有的手段和方法,使技术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知其所以然”,也即认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这恰恰是科学的本质。可见,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那么,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呢?爱因斯坦曾经指出,西方的自然科学是建立在两大知识体系——几何学和形式逻辑之上的,它们是发展科学的主要基础[5]。几何学指的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由于欧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的演绎方法基础之上的,所以,这里实际上涉及到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是逻辑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逻辑学与科学之间是有着天然联系的,科学真理的力量决不仅仅来自各学科的具体内容,也来自其依托的逻辑的力量[6]。逻辑学不仅是一门工具性学科,而且是支撑人类思维大厦的基础性学科,它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意义上“器”的层面,而且还表现在“道”的形而上层面[6]。对科学而言,逻辑学不仅提供了建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塑造了科学事业得以进展的“求真”氛围。科学的特点在于“求知求真”,而逻辑的力量也正是源于对纯粹真理的不断追求。所谓的“科学精神”即为纯粹的求真精神。正因如此,笔者认为,逻辑学是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支撑。离开逻辑学谈科学,所谈的必定是残缺的、畸形的科学。
亚里土多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他创立的以三段论为核心的演绎逻辑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门真正的演绎科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演绎法被后来的欧几里得继承和运用,构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门成型的科学——几何学。欧几里得“从少数被认为是空间的不证自明的特性的公理出发,按照逻辑原理,推演出一系列奇妙的命题”[7],这正是演绎式科学方法的基本特征。欧几里得本人“也许没有为数学增添一项具体的新发现,但他从几条公理出发,就构造了一个雄伟壮观的几何体系。他的严密的逻辑,完整的体系,不知使后世多少个科学家着了迷,一直被认为是科学理论逻辑结构的典范”[8]。到了近代,牛顿仿效欧几里得,用公理方法把前人的力学知识加以系统化,形成了一个逻辑体系,牛顿的经典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由许多定义、定律、推论组成的。后来的拉格朗日的力学著作,克劳胥斯的热力学著作,斯宾诺莎的哲学著作,也都是用类似方法写成的,而且欧氏几何的逻辑明晰性、可靠性给12岁的爱因斯坦造成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印象[8]。从中我们对逻辑学对科学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可窥见一斑。
然而,作为科学发展主要基础的形式逻辑和几何学这两大知识体系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少的。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形成可与亚氏逻辑、欧氏几何相提并论的科学体系,即使在被李约瑟先生称为“中国科技的领先时代”的中世纪的中国,像《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农政全书》、《本草纲目》等著作中,多的也只是关于技术的描述性记述,或者零散的科学思想,而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建构。也就是说,这些著述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闻名于世的四大发明也仅仅停留在对经验的总结之上。它们的实用价值较大,理论价值较小。通俗地讲,它们只告诉人们“是什么”和“怎么做”,而很少涉及“为什么”。而且众所周知,我国至今也没有创造出像相对论、宇宙大爆炸理论、耗散结构论等这样的世界级的科学理论迄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
可见,严格讲来,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且中国的近代科学更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那么,这一切究竟根源何在呢?笔者认为,中西对比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乃根源于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别。
“科学是一个从个体层次向文化层次的认知发展的延伸,是一个传统的文化知识之上的发展生长物,而且是一个文化进化之特殊化的认知变异体和延伸。”[9]西方自然科学之所以领先于世界,是有其内在根据的。虽然在西方文化源头时期的古希腊也并没有系统的自然科学,但正如前文所述,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以三段论为核心的演绎逻辑学却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门真正的演绎科学。亚氏逻辑学不仅提供了建构完整科学体系的基本方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为西方科学理性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西方的文化模式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其逻辑传统,也即分析传统。亚氏逻辑学和欧氏几何学作为西方文化的两大基石,经过两千多年的积淀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塑造出的是一种重分析、纯求真的理性思维方式。而这些正是发展科学的主要基础,是西方自然科学在近代以来得以取得重大成就的必要条件。
然而,自先秦时代起,中国文化就表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经世致用”。学者们重视人生,讲究实用,漠视各种与人生无关的自然知识或抽象理论。在他们看来,任何学问必须有利于社会人生才有价值。于是“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而学问”成为根本的学术目的。应当肯定,中华民族不乏“求知求真”的精神,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压倒一切的价值目标是追求一种理想的道德境界和实际的社会利益。这一点极其顽强地贯穿于学者们的“求知求真”的活动中:为了“经世致用”,才去“求知求真”!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未能处理好“求知求真”与“经世致用”的关系,过于强调“经世致用”是“求知求真”的归宿,相对忽略了“求知求真”是“经世致用”的基础,因而构成了在科学认识上的误区。比如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就是出于几何学乃“众用所基”、“其裨益当世,定复不小”的目的。这种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科学观,使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一度在世界上领先的“科学”,实质上是以技术和工艺为表现形态的科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纯粹为了实用而去求知求真,难以保证对科学发展自身规律的遵从,难以使学者始终保持相对独立性和通过冷静的观察和实证的研究去建构严密的、公理化的演绎系统[10]。梁启超曾尖锐地指出:“科学所要给我们的,就争一个真字”,“中国人因为始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所以,50年前很有人奖励学制船,学制炮,却没有人奖励科学。”[11]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实用理性”文化,它与西方的“科学理性”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它过于注重对人际关系的处理,而忽视甚至漠视对自然界的深层次的探索。然而真正的科学乃是根源于对自然界的“纯求真”式的探索,它是绝对不能以“追求实用”为直接目标的。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出的是一种“求善”思维,而不是“求真”思维。西方古代先哲对于看似毫无实用价值的问题仍苦苦求索。而中国先哲却对这类问题不屑一顾。究其原因,乃在于后者缺乏前者那样的非功利、纯求真性的认知型思维倾向,而这正是近代科学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诞生和发展的文化基因[12]。正如罗素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先哲缺乏古希腊人那种“对真理沉思之至上的内在价值的感觉”[13]。正因如此,笔者认为,逻辑传统的缺乏是造成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和近代科学落后的关键因素。“实用理性”的深刻影响,使整个中国社会对没有直接实用价值的“理论”产生了一种消极的漠视心理,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真正的“科学”又怎么可能产生呢?正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承中“逻辑基因”的缺乏,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科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当然,不容否认,“实用理性”给古代中国带来了技术的高度繁荣。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之内,社会是稳定的,这有利于技术的产生,人民的安居乐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的广泛使用,这又推动了技术的进展。而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人民的言行举止受到宗教教义的严格限制,这就严重阻碍了技术的进步。所以,在16世纪之前,中国只是在实践经验的总结即“技术”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而并没有产生有利于“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然而西方并不是因为缺乏产生技术的土壤而是由于社会原因才在技术上落后于中国。我们应该认识到:科学的理论发现和它的实际应用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差距,理论探索也许暂时无用,但它孕育着未来的实用成果。科学研究只有远离立竿见影的期待,才会有更多新的理论发现,从而给技术带来强大的后劲。事实证明,西方社会正因为有了发达的近代科学作为坚实的基础,所以才有了发达的近代技术。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可以和古希腊相媲美的名辩之风,产生了较为丰富的逻辑思想,这是系统的逻辑学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然而,“实用理性”的大行其道导致许多有着逻辑闪光点的思想,由于在政治、伦理上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受到批判、抑制。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意识十分薄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逻辑发展处于“中断”状态。已故著名逻辑学家殷海光先生曾经指出:“在文化的规范、美艺、器用、认知四种特征中,中国文化的规范特征过于发达,特别是自汉以降逐渐成为文化价值取向的主导力,由此导致‘在价值的主观主义的主宰之下,益之以美艺的韵赏和情感的满足,认知作用遭到灭顶的惨祸’。”[14]这是对中国社会思想状况的准确概括。逻辑学根本上属于认识论范畴,认知特征的不发达必然导致逻辑系统研究的不发达。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大憾事。这样,由于逻辑研究的“中断”,在中国,科学就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生长点,科学理性在实用理性之前完全的劣势最终导致中国科学落后的现状。中西比较告诉我们,逻辑学的昌盛是科学事业发展和发达的一个必要条件。
收稿日期:2001-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