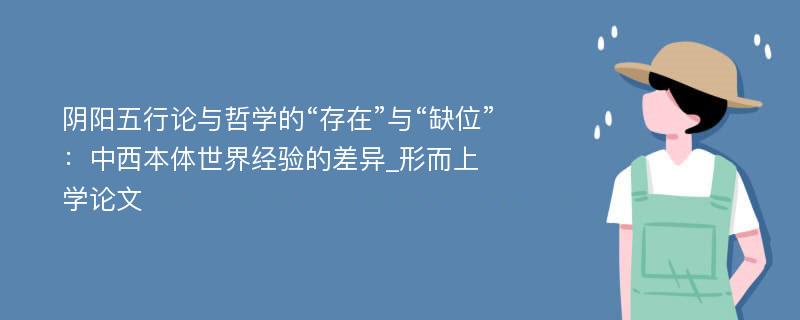
阴阳五行学说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中西体验本体世界方式的差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中西论文,阴阳论文,差别论文,不在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1)01-0051-005
中西对于本体世界的体验在方式上存有显著的差异。西方哲学的一贯意图在于要超越当下现象去挖掘背后的终极本体,于是便有“知性形而上学”的生发与滥觞,而中国的思想却从不在乎这种超越,即使有一定程度上的理性提升,也总与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相联结,表里相即、内外兼融,形成所谓“性情形而上学”。中国哲学的诸家各派中,真正能够在纯哲学本体意义上与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相对待般配的,当首推阴阳五行之学。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阴阳与五行的观念一经形成,就没有中断过对中国社会的国家政治、意识形式及个人生活发生实际的作用和影响。一直到今天,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在中国人的行为取向和思维方式中,总不难发现这一学说所留下的印痕。透过文化与生活的表层结构,阴阳五行之学似乎颇能说明中国哲学对本体世界所做的独特体验。(注: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一书中,对阴阳与“在场”、“不在场”问题曾作过富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探索。)
一
西方人体验本体世界的方式的形成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在古希腊,从赫拉克里特的“逻各斯”(logos),到毕达哥拉斯的“数”,到巴门尼德的“存在”,到德谟克里特的“原子”,哲学家们都力图透过眼前的感性事物,到它的背后去寻找世界的本质,追求绝对的、统一的、本源性的基础。但真正为西方哲学体验世界确立起固定模式的是柏拉图。海德格尔说过:“综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1-p70]柏拉图以为,我们的感官所感知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因而都是不真实的,“真正的实在”应该是绝对的、永恒的、不变的“理念”。这个“理念”是独立于事物和人心之外的实在,是一切现成事物的根底。所有的理念构成一个独立存在的、唯一真实的世界,亦即“理念世界”,而我们感官所接触到的具体事物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幻象世界”。柏拉图学说一出,西方哲学的航程就开始朝着纵深的方向行驶了,感性中的物事、经验中的具体必须上升、提高到理性抽象中的普遍和一般,才是可以被认知、被理解、被验证的,真实存在着的东西并不是人们感官的对象,而是我们理解中的东西。此后,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围绕着“逻各斯”这个中心而展开,实体、本质、超越、验前、纯粹、形式等概念和真理、第一因、实在、本体、结构、终极意义等观念,经由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内容和形态上都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长足的发展。这样,建立在理性论证与逻辑推理基础之上的形而上学,一方面,成为西方哲学领会世界的独特路径;另一方面,也在东西方交流、沟通中滋生出许多隔膜和误解,即使在今天,东方人要对其作准确的把握与理解,还显得十分困难。
西方人之所以执著于“在场”的观念,是因为在他们的哲学体验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即世界一定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一种在人们确定实在、真理、至善、理性、知识时可以作为最高、最后本体依据的永恒的、终极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一切知识和所有人生的“阿基米德点”,哲学的目标和任务就在于要发现这个基础,探究出这个基础是什么,同时还要用理性为这种发现和探究的“合法性”作辩护,阐释出这个基础的意义。笛卡尔就是这种“基础主义”(Fudndamentalism)的典型代表,在他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一书中就有关于这种“基础”的“隐喻”,包括认识论和本体论在内的“形而上学”好比一棵大树的树根,而“物理学”(关于自然界的学说)和其它各门具体科学(主要指医学、力学、伦理学)则分别是这棵大树的树干和树枝,形而上学的使命就是要为“树干”和“树枝”提供确实而自明的“知识原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是为这一庞大知识体系的根基的论证提供服务的。笛卡尔强调,惟有理性思维才能够认识外部世界的真实本性,确实的真理总是被清楚明晰地认识到的,知识不可能产生于感觉,感觉不能表明事物本身的状态,只表明事物如何影响我们,颜色、声音、气味并不归物体本身所有,我们关于物体的真正的知识来源于我们头脑所固有的、天赋的或先验的基本概念和一般原理。认识的原则、理性的规范总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不过只有在经验的过程中,只有当头脑进行思维的时候,才变得明显起来。所以,“我思”就是一种现成的“给定”(given),是永远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东西,是确凿的、肯定的存在,是在场的,因此也就成了一切基础的基础,存在着的一切都必须放在绝对的理性尺度上加以校正。至于“我思”如何进行、如何才能达到事物本身,笛卡尔的哲学便无能为力了,笛卡尔发现了事物显现出来的一面,却无法转回到另一面去挖掘出能够建立整个知识的根本信念的理由。
在西方,对“基础”的渴望几乎主宰了整个笛卡尔以后时代的所有哲学,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前赴后继地寻找着这个超验的“实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也不可能跳出“在场”形而上学的巢臼。在他看来,我们不能如实地认识事物本身,只能认识事物呈现给我们的表象,我们不能越出理性而拥有关于超感性的存在——自在之物——的知识。而如果我们硬要用理性去认识非现象世界里的东西,必然会产生“先验幻象”。因此,人类不可能产生关于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关于自在之物的形而上学。这样,以追求“在场”为鹄的形而上学,对于“真实的世界”而言,完全成为一种虚构的神话和假托的寓言,对于事物的本身来说,完全是毫无裨益的。与康德不同,黑格尔总试图用“绝对精神”包容“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囊括存在世界的一切。黑格尔是“辩证法大师”,特别强调抽象概念的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即正反事物或事物中对立两面的统一与转化,但实际上这种概念的演化不过是达到终极理念的一个过渡,历史的过程不过是精神运动的无足轻重的工具,惟有“绝对精神”才是最后的、最真实的根底,一切对立都会在这里消融和保存下来,“绝对精神”变成了一个普遍的、永恒的“在场”,最高实体背后的、潜涵着的世界永远从我们的理解中隐退。至于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分析哲学的“语言”,则应该看作是追求“在场”的哲学史在当代的残留和延伸。
二
如果说西方形而上学侧重对具体感性事物进行抽象加工,运用概念进行纯粹的思维,而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却不容许这种超越和分裂,主张获得对世界的体认不能离开感性物事的“物象”,要求在经过抽象和概括而获得普遍意义的直观“意象”中领会事物本身,即所谓“观物取象”。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概念思维,“阴阳之象”、“五行之象”之类的“意象”表现出中国哲学思维活动的独特方式和鲜明特色。在体验世界本源的方式上,古希腊人似乎总立足于一种固定的事物如水、火、原子或数,而中国的阴阳观念则倾向于从现成事物的运转、活动中去把握世界总体的根本。阴阳观念起源于对现象世界的观察,不仅天道物候的天地、山川、昼夜、寒暑、晴雨、枯润各为阴阳,而且人事生活的男女、君臣、尊卑、贵贱、刚柔、强弱、成败、得失也可判为阴阳,整个世界的行止、动静、分合、生灭、正反、进退皆能分出阴阳。从宇宙总体到日用纲常、从自然存在到人情世事都与阴阳之道相契合,所以《易传·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老子》中则说:“万物负阴而抱阳。”“阳”是事物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当下方面,而“阴”则是决定“阳”、生发“阳”面的根源和背景。董仲舒以为“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从表现形态和内在性质上看,阴阳正反有似于西方哲学的“在场”和“不在场”,任何一个事物呈现于我们面前的那一面,即我们所看到的一面是事物的正面或“阳”的方面,而尚未呈现于我们面前的那一面,即我们暂时所没有发觉到的一面是事物的反面或“阴”的方面。活着的人总是当下时空中的存在,他不可能真正地看到还未呈现于他眼前的任何东西,“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即便他能够意识到、想象到这种东西的存在。因为在事物的阴阳两面中,虽然有一面被呈现出来,是出场的,但总有一面被遮蔽着,是尚未出场的。“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阴和阳总处于相互对待、彼此印应的状态之中,二者不可能同时出场,或同时成为一种性质的存在。“阳出而前,阴出而后。”(《春秋繁露·天道无二》)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作、一开一塞、一起一废,其规律都是一致的。
从表层看,“五行之象”所表达的是感官能够获得的金、木、水、火、土,但它们已不仅仅是作为可以被人类利用的具体物质材料了,即“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昭公十一年》),而毋宁更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抽象化或理性提升后的带有“类”特征的普遍性的“意象”,有如《易传·系辞下》所说“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五行之象,在天可以为五星,在地可以为五位,在人可以为在五脏,在物可以为五材,在岁可以为四时,在政治和历史中则可以为五德始终,……取意比附,开物成务,永无止竭。
哲学的产生源自人们对形而上者的思考。但是,同为追求形而上学,西方人和中国人的路径却迥然有别。由于理性主义精神的极大突出,西方哲学极善于把本属于事物本身的概念、判断从事物自身中剥落出来,构成一个绝对形式化的、纯粹的逻辑系统,概念成为这个系统里思维运作的唯一可以依靠的符号和工具。西方哲学的这一思维品质经过两千年的发展所形成的最直接的现实结果在于:一方面,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与日益昌明,“工具理性”的异常发达,但另一方面,系统之外的感性、经验、直观、潜意识,非概念的直觉、体会、顿悟、想象,在很大程度上被拒绝、被贬低,从而导致哲学远离了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道德教化、情感体验、文化艺术及富有实践意义的日常生活世界,人的“交往理性”发育相对不足。而在包括阴阳、五行在内的中国哲学中,概念思维的色彩很淡漠,倾向极不明显。“名”是中国哲学的概念形式,但其形成、运作和发生功效总是与“象”纠合在一起的,从来都不是纯粹抽象的符号。如,《周易》之“易”,或涵指日月,或取象蜥蜴;老子之“道”,或喻之“惟恍惟惚”,或譬以“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这些具有丰富“象”的内容的名相,虽然没有西方哲学概念所具有的那种明晰性、确定性、逻辑性和系统性,但却避免了人为地把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主体意识与物质对象、自在之物与主观表象及在场之物与不在场之物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危险。
在中国哲学,无论“阴阳之象”,还是“五行之象”,从来都不是静止、平面或一维的,从来都不会把意之所指仅仅停留、固定或局限在某一当下的存在和状态之上。阴与阳总是相伴相随、互反互成的,它们总在对立、依存、渗透、互补的状态中实现着自己。“几物必有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春秋繁露·基义》)中国的阴阳学说并不象西方形而上学那样追求某种超现象的本质,它一般都否认有超感性的理念,以为世界就是相反的具体事物及其阴阳两面的相互转化。呈现出来的、在场的一面总以未呈现的、不在场的一面为根据、为依托,但决不存在谁超越谁、谁决定谁的问题。“天之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之道是也。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出则阳入,阳出而阴入,阳右而左阴,阴左则阳右。”(《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阴和阳之间是一种对等、平齐、互存的关系,谁都不是对方的主宰,谁也不会被对方所占有,并且二者都处于某种动态的、规律性的交替运行之中。与阴阳之变相类似,五行学说中也有“相生相胜”之观念。《洪范》九畴,首列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折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无论“润下”、“炎上”、“曲直”,还是“从革”、“稼穑”,所象征或隐喻的都有运动、转化、变异、播藏、分合之意义。现存文献中,《吕氏春秋·应同》较为完整地记载了“五德始终说”的内容,从黄帝、夏禹、商汤,到周文王、秦始皇,历史的演进是按土、木、金、火、水之气的运行规律为底本的,并且“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在自然世界里、在人类社会中,“可通约性”普遍存在,同类的东西具有相同的属性,并且还可以互相感应,即所谓“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其实,也正是这一“感应”才孕育出中国哲学的“性情形而上学”。五行之间存在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其一般规律为“比相生,间相胜。”并行的五材之间,一方面可以相互衍生,相互创设,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另一方面又可以相互接换,相互更变,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五行之中谁都有其盛,谁都有其衰,世界在五行的轮流、交替之中实现着变化,金、木、水、火、土循环运行,往复始终,但大家都是平行对等的,都是五材之一种,从根底处看,不存在谁支配谁、谁领导谁的问题,更不可能发生如西方形而上学中谁超越谁、谁高于谁的矛盾。
三
总的说来,西方对本体世界体验的方式都是一维的、线型的、单向度的。在理性中心主义那里,最具普遍性的概念是哲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只有“绝对”才是永恒的“在场”,连时间也被抽空,脱离了生活世界的具体存在状态。而在基督教的思想中,只有“上帝”才是永恒的“在场”。人永远只是“奴仆”,人从一开始就是有罪的,人生的历史不过是向上帝不断赎罪的过程,世界的发展是有尽头的,即那个不可挽救的“末世”。这一切都跟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易传·系辞上》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出场的东西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也并不永远都在场,相反,变化不息才是永远不可否定的。世界的图景日日增新,时时更善,“原始反终”,永无穷尽。眼前的世界永远不可能向我们呈现出它的“根底”,《易传·序卦》曰:“物不可以穷,故受之以未济终焉。”亦即世界是无根无底的,要寻求绝对的“在场”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哲学与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倒是相通的。
后现代哲学不屑于追求传统形而上学的终极本体,而力倡回到真实世界本身,以为“在场”的东西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它总是与“不在场”的世界相联系、相统一的。所谓永恒的“在场”,从本质上看,无外乎是人类对外在表象世界所作的总体化的努力,是人类在自己证明自己、自己肯定自己的基础上,为世界所设定的一种固定的、僵死的程序。“世界”不是它自己本身,而是主体的“再现”,世界成为一种被阐释的、纯粹的、赤裸裸的“给定”,成为一种等待被整合的主体化了的“内容”,因此,正如早期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不变者,实存者和对象是一个东西。”[2-p28]然而,对象构成着世界的实体,对象不应该是我们主观中的复合物。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形而上学的命题只能解释事物是怎样的,而不能表达事物是什么。海德格尔也曾怀疑过:“大地上有一尺度吗?”为我们理性所一直追寻的永恒的“在场”真的存在或真的能够达到物自身吗?他说:“毫无疑问,一切所显现的描述,在所显现和作为对象与对立意义上,从没有达到了物作为物。”[3-p149]伽达默尔直接指出,在现代科学中,这种把认识主体附属于认识客体之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并没有“合法性”,难道物理学的世界果然是一个真实的、自在的世界?它真的超越了一切此在的相对性,而关于它的知识则可以被看作是绝对的科学?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物理学的世界完全是主体自己产生的现象、表象甚至就是假象,在这里,人们遵循着一种抽象的思路,而在这个思路的尽头则是一种人工语言的理性结构。在形而上学的思维中,我们犯了一个前提性的错误,即我们思维着的理性从一开始就被置于“绝对的完善性”之上了,所有的认识、所有的“演算”都得按照它的模式进行。然而,真实、自在的事物一直是独立于我们的愿望和选择的。从根本上来说,要想“达到事物本身”、“拥有世界”,就必须“对世界采取态度”(sich zur Welt ver-halten),这种“态度”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同由世界而来的相遇物(Begegnenden)保持距离,从而使它们能够如其本来面目那样地出现在我们之前。”[4-p566]可见,事物本身或真实的世界并不直接就是我们的理性和形而上学中现存的“给定”,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必须承认,解构主义大师J.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摧毁最为彻底。他以“延异”(differance)、“痕迹”(trace)概念和“增补逻辑”(logic of supplement)为工具,对在场追求的起源、过程、形态、目标都进行了无情的解构。德里达以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在场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因为我们的认识和理解都是通过符号系统来完成的。这样,对象的在场总会被无限地“推迟”或“拖延”,形而上学所孜孜以求的、纯粹的在场概念最终变成为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幻象。人们关于在场事物的认识只有在把本属于不在场概念的特征给与在场的概念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才能达到对在场之物的把握。古希腊哲学家的“飞矢不动”之所以成为悖论,就是因为人们对在场概念的过于执著。如果我们将特定的、瞬间的现实预设为永恒在场的东西,那么就必然会产生出悖论。因为惟有在每一瞬间先已打上过去、未来的痕迹之后,方可想象运动的在场。一方面,两实的瞬间不再是一个绝对之物或一个给定的概念,而应该是它与过去和未来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作为在场的、现时的瞬间本身就已包含了不在场即过去和未来。于是,在场便具有了它的对立面——不在场的成分、特色和属性。不是在场规定不在场,而是广义的不在场涵盖着有限的在场。差异之前和差异之外都不在场,“延异”从不显现它完整的意思。“延异是一种在在场和不在场两者相对立基点上所无法设想的结构和运动。延异是各种因素相互关联的差异、痕迹和分离体系的游戏。”[5-p27]在场之中有延异的不在场的“痕迹”,甚至在场与不在场都是“延异”的结果。世界上并不存在纯之又纯的绝对统一的“本源”,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在场或不在场的。“痕迹”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写下来又被抹去的东西,它总是半隐半现、半有半无的,痕迹的在场与不在场永远无法确定,它是一种不在场,但又总在在场之物中证明和宣告自己的在场。而这与阴阳学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观念又是相一致的。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注:周敦颐《太极图说》,见朱熹、吕祖谦《近思录》,第3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北京)《易传·系辞上》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已把这种本体论的体验上升到神乎其神的境界了。德里达还认为,我们的世界存在着一条无限的“增补之链”,如教育是对自然的增补,书写是对语言的增补。由于在场与不在场的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来说,谁都不处于支配和主宰的地位,谁都不具有驾驭、超越的优势和特权,所以“增补”和“被增补”之间的绝对区别、明确界线正在被消解和破除。不仅在场之物需要补充,不在场之物也需要补充,“增补”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外物,而是需要补充之物赖以存在的先行条件。所以,德里达得出结论:“总之,在场并不是原始的,而毋宁是被建构的,它并不是绝对的”,尽管不存在纯粹的、现存的在场,且它作为概念性的东西并不与事物本身相符,但它却成为形而上学不可避免、难以克服的主题,还驱使着我们去追求;更为甚者,“不论在形而上学还是在科学方面,这种追求无疑是唯一让我们精疲力竭的东西。”[6-p212]德里达对形而上学所作的反思的确是非常深刻的,他的摧毁和解构当然也是极有力度而又富有成效的。
四
董仲舒所说“相反之物,不得俱出”的“天之常道”,在后现代的视角主义这里亦可引起共鸣。梅洛·庞蒂的“立方体之喻”颇能说明一些在场、不在场及其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按常规解释,立方体应有六个面,但实际上从没有人能够同时看到它们,它的六个面永远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我们面前。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立方体”的时候,我们所归属到它身上的东西远多于我们所看到的,此间,过去的或未来的经验一直在起作用,立方体隐藏的方面的存在是我们假定和想象的结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给我们提供意义的事物,永远不可能完全地显露出来。所以,似乎也可以说,真正的立方体并不是在场的“立方体”,它存在于我们的感知和“我思”之中。梅洛·庞蒂说,拥有六个面的立方体不仅是不可见的,而且也是不可思议的,立方体只有对它自己来说才是立方体。[7-p178~179]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综观中国哲学的整个历程,无论易、老、玄学,还是宋明新儒学,都无一例外地要在阴阳五行尤其是阴阳问题上开展一番论说,为什么这一学说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其中原因恐怕要归之于这一学说本身所展示的本体论意义。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生命,没有本体论的哲学就象没有神灵的宗教,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在客观上可以弥补诸子之学缺乏本体论的不足,从而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建构提供可靠的基础,并通过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形成汉民族独特的思维传统。春秋时代,处于观念发生阶段的阴阳与五行,从一开始就强调了本体世界的多元性和真实感,并扬弃了对事实存在的分离与割裂。战国以后,阴阳与五行的合流又使得中国人的本体世界更为充实、饱满,更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深广的可变性。董仲舒认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阴阳与五行的结合可以把宇宙天地、世间万物的构成解说得更加符合本体的原来面貌。五行之所以能够“比相生”、“间相克”,之所以有“始终”、“转移”,就是因为有阴阳作为两种彼此依存、相互补充的矛盾力量在其中作不断的运行、推动。[8-p161]只要阴阳消长不息、对待不止,五行图式的周转就不会间断,当然也就不会使现存世界停留、限制在某一“给定的”存在上,纯粹的、绝对的“在场”就不可能找到站稳脚跟的基础。世界在流变,在场的东西注定是暂时的。“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其实非独阴阳也,然而阴阳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春秋繁露·天辨在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阴阳与五行已经相即相融、汇为一体了,正如戴震所说:“举阴阳则赅五行,阴阳各具五行也;举五行即赅阴阳,五行各有阴阳也。”(《孟子字义疏证·天道》)另一方面,阴阳、五行之中,任何一者都不容许也不可能独立行事,“独阴不生,独阳不生。”谁都离不开谁,大家都有一种“本体论上的平等”(ontological parity),谁都是真实的,谁都不比谁更具有真实性或缺少实在性。在这个开放的、动态的、无边际的系统或结构中,大家都得施展职能、发挥作用,都必须“相与一力而并功”。
[收稿日期]199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