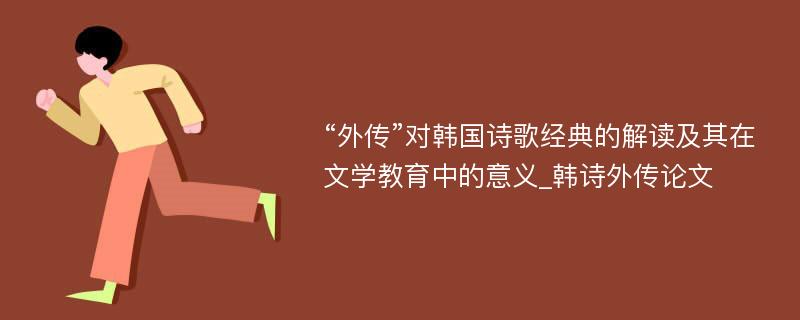
《韩诗外传》解经方式及其文学教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传论文,意义论文,方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1)01-0155-04
汉代十分重视对《诗经》的解说与传授。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说中,《韩诗外传》非常特殊,显著区别于三家诗的是其解诗方式。《韩诗外传》解诗注重激发研习者自己对作品的联想和领悟,本文名之为启悟式解经。
《韩诗外传》解《诗》,不注重探求诗人的情志及诗之本义,也不就具体某一首诗所具有的文学性(修辞、表现手法、美学特征)加以研究、揭示,即不注重诗作的表现方式、表现技巧,不注重诗人是如何言说其怀抱的,而是特别关注诗所言说于研习者有何相干,对研习者有何启示。《韩诗外传》的解经方式,重在从《诗经》中寻求一种思想上的体悟与发现,重在激活研习者的联想,富于启示性,是一种独特的启悟式解经。具体而言,其启悟式解经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故事解说诗句,二是对同一节诗,做多角度解说。
一、以故事说《诗》的解经方式
《韩诗外传》共十卷310章,据笔者统计,以故事(包括对话)形式来解《诗》的,有146章,占全书近一半的比例。以故事形式解《诗》,是其最鲜明的特色,具体而言有以下四种情形。
1.把抽象的道德品质故事化。卷二第十四章解说“彼己之子,邦之司直”(《郑风·羔裘》),并没有像毛诗及后来的朱熹那样探求诗人之意是刺还是美,而是把阐释的重点放在“直”的含义上。先讲了一段故事。楚昭王时,石奢做负责刑罚的官,其父杀了人,他抓住父亲。回到朝廷,自认为有亏于忠孝之道,最终自刎而死。叙述完故事,引孔子所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1]48《外传》把“直”这种道德品质用讲故事的方式加以阐释,把抽象的品德行为化、故事化了,限定了直的含义是像孔子所说的、石奢所作的“子为父隐”。
卷九第十章和十一章也解说“邦之司直”[1]314-316。分别叙述了两个故事。颜斫聚为齐景公掌管鸟却让鸟飞走了,景公要杀他,晏子劝止了景公。解狐向魏文侯推荐自己的仇人荆伯柳做西河守。荆伯柳向解狐道谢,解狐回答公私不同,虽举荐他,但仍有私怨,并张弓射荆伯柳。晏子和解狐的言行,在解说者看来,属于邦之司直。
类似的解说颇多。卷二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解说“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伐檀》),第十九章讲殷纣王时大臣商容在周武王得胜后,不受三公之命,解说者赞赏他能“内省而不诬能”,以此来解说诗句的含义。[1]53-54第二十章讲晋文公狱官李离的事,他过听杀人,向文公请罪,伏剑而死。讲述者认为李离“忠矣乎”,用李离的事迹,用忠于职守来解释“彼君子兮,不素餐兮”[1]54-56。
卷四第八章[1]136、卷七第二十一章[1]264-265、卷八第二十六章[1]297-298和第二十七章[1]298-299,都解说“好是正直”(《小雅·小明》),都是举具体的人物言行来阐释“正直”的涵义。[1]136卷六第十八章和第二十章,解说“柔亦不吐,刚亦不茹。不侮矜寡,不畏强御”,也是举人物言行来阐释诗句。[1]221-222,223-224.
2.用故事解说抒情性的诗句。《外传韩诗》所选择加以解说的诗句,在我们今天看来,极少有诗意。我们今天各种选本所选的诗篇,《韩诗外传》极少涉及。就是那不多的抒情的诗句,也大多被解说者以故事来阐释。卷一第二十六章和第二十七章,解说“亦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诗句出自《邶风·北门》,本来是一个小官吏抒发无可奈何的情感。《韩诗外传》完全抛开诗句本来所抒发的情感,而是讲了两个人物的故事,阐释儒家的概念。一个是申徒狄反对当世,抱石沉于河。一个是鲍焦认为廉者易愧而轻死,于是立槁于洛水之上。而认为这两个人可谓廉,但称不上仁。[1]26-27,27-29
卷四第一章和第二章,解说“昊天大怃,予慎无辜”(《小雅·巧言》),诗句本来是抒发一种极度痛苦、质问天命不公的情感。《韩诗外传》并不分析诗句所抒发的情感,而是分别讲述了比干劝谏商纣王和关龙逢进谏夏桀均遭囚杀的故事来解说诗句[1]129,129-130,意即比干和关龙逢二人就是那无辜之人。
3.用故事解说描述性的诗句。卷七第二十六章解说“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小雅·白华》),讲了一个故事。孔子鼓瑟,曾子在门外听出瑟声有贪狼之志、邪僻之行。后孔子解释,鼓瑟之时,见狸欲捕鼠而未得,致有此音。[1]269卷八第八章解说“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大雅·卷阿》),讲述黄帝治天下,修德行仁,问凤象于天老,后致斋于中宫,终于迎来凤凰蔽日而至的故事。[1]277-279
4.将叙事兼抒情的诗句,演绎成故事。最典型的要数卷一第三章,解说“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周南·汉广》)。《韩诗外传》叙述孔子南游适楚,在阿谷之隧,遇见一女子佩璜而浣衣。孔子三次让子贡去与之交谈,女子均答之以礼。[1]2-5故事篇幅较长。第九卷二十三章解说“彼美淑姬,可与晤言”(《陈风·东门之池》),讲述北郭先生听妻子之言,不受楚庄王之聘的故事。[1]327-328
这种以故事解说经典的阐释方式,与《荀子》的引诗为证判然有别,也有异于汉代通常解经的问答体、论说体及章句体。故事化的解说,无疑富于形象性、生动性,具有文学色彩。
二、多义共存的开放式解说系统
《韩诗外传》多有几章对同一节诗进行解说的情况。具体而言,有三种。一是在同一卷顺序相连的二章、三章或四章解说同一节诗,共计有98章对39节诗加以解说。二是在不同的卷中解说同一节诗,共有16章解说7节诗。三是同一卷相连的几章解说同一节诗,在其他卷中,也有对这一节诗的解说,共有5章。总计有119章对46节诗进行解说。《韩诗外传》共有310章,这种情况值得重视。那么它们有什么意义呢?
1.对同一节诗含义的解说相同,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卷三第二十八章和第二十九章,都解说“帝命不违,至于汤齐”(《商颂·长发》)。两章解说的中心都是“古今一也”,即诗句表达的意思是古与今情形相同。[1]113-114第二十八章重在针对“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异道”的观点进行驳斥,引出“圣人以己度人者”的论点,从而解释为什么古今一也。第二十九章则举舜为东夷人,文王为西夷人,以地域及时代论,都相去甚远,可是他们的政治行为,却如出一辙。从而推出“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的观点。这是从实证角度加以举例论证。两章论古今一也,相同,角度则不同。
卷四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都解说“如蛮如髦,我是用忧”(《小雅·角弓》),都把这句诗的意思解释为“言语之暴与蛮夷不殊”,则为人所忧。[1]151-153第二十三章论的是君子和小人禀持不同个性,处不同情绪、不同处境时的不同行为,这是对比之中标举君子之行。第二十四章论的是何谓仁义礼容,以及四者于治乱生死的重要性,从而批评现实之无道。两章对诗句的解释相同,论述则不同。
其他如卷一第四、五两章解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鄘风·相鼠》)[1]5-7,八、九、十连续三章解说“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风·柏舟》)[1]9-13,卷四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连续三章解说“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小雅·白华》),卷五第三十二、三十三两章解说“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商颂·长发》),卷十第六、七、八连续三章解说“辞之怿矣,民之莫矣”(《大雅·板》)[1]341-345,都是此类。
2.对同一节诗含义的解说相同,举不同的事例加以阐释。卷三第二章和第三章解说“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周颂·我将》)[1]80-81,81-83,第二章讲述商汤时有穀生于廷,商汤听伊尹之言而行仁义于国,七日穀亡,国家昌盛。第三章讲述周文王时病重,五天后地震,地震的范围不出国郊。文王听臣下之言,修行礼义,没多久病愈。地震后四十三年去世。这两章分别讲述了两代明君对待妖异现象的做法,用意相同,只是事例不同而已。
卷四第一章和第二章解说“昊天大怃,予慎无辜”(《小雅·巧言》)[1]129,129-130,第一章讲述王子比干因谏纣王作炮烙之刑而被杀,第二章讲述关龙逢因谏夏桀作酒池而被杀。两章事例不同,用意很明白,都是为忠诚诤谏之臣鸣不平。
其他如卷三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连续三章解说“载色载笑,匪怒伊教”(《鲁颂·泮水》)[1]105-110,卷六第十二章和卷十第二十四章解说“人亦有言,进退惟谷”(《大雅·抑》)[1]216-217,362-364,卷八第二十三、二十四两章解说“日就月将”[1]293-295,第二十六、二十七两章解说“好是正直”(《小雅·小明》)[1]297-299,卷九第一、二两章解说“宜尔子孙承承兮”(《周南·螽斯》)[1]306-307,均为此类。
3.对同一节诗多角度、多层次加以解说,而不是从同一角度反复强调,这是《韩诗外传》解诗突出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韩诗外传》对同一节诗提供了多种解说,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多义性共存的解说系统。与前两种比较,这种解说方式尤其富于启示性。卷一第十三、十四、十五连续三章解说“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邶风·雄雉》),角度各不相同。
传曰:喜名者必多怨,好与者必多辱。唯灭迹於人,能随天地自然,为能胜理,而无爱名。名兴则道不用,道行则人无位矣。夫利为害本,而福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不求福者为无祸。《诗》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第十三章)[1]14-15
传曰:聪者自闻,明者自见。聪明,则仁爱著,而廉耻分矣。故非道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故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远而名彰也。《诗》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第十四章)[1]15
传曰:安命养性者,不待积委而富;名号传乎世者,不待势位而显。德义畅乎中,而无外求也。信哉,贤者之不以天下为名利者也!《诗》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第十五章)[1]15
第十三章论的是具体不求什么,不求名、利、福。第十四章论不强求非己所有的,第十五章的观点是不向外求德义,强调内在的修养。连续三章从不同角度解说如何才是“不忮不求”,如何才能“何用不臧”,解说的内容全然不同。
卷一第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都解说“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1]23-25(《邶风·旄丘》),两章都把诗句当作一个问题加以解答,第二十三章论述的结论是:情行合名,祸福不虚;无为,能长生久视。第二十四章论述的结论是:君子具备三种品质——衣服容貌得,言语应对逊,就仁去不仁,则可以久。两章从不同方面解说何以能久,何以自处。
卷三第三十一章和三十二章及卷八第三十章至三十三章共六章都解说“汤降不迟,圣敬日跻”[1]116-118,301-303(《商颂·长发》),其中卷三第三十一章与卷八第三十一章言辞大同小异,论述的都是谦德的重要性,其他四章则各不相同。卷三第三十二章记孔子教导子路之言,中心是言行要慎重、诚实,才是既知且仁。卷八第三十章述汤作护,其宫商角徵羽五声具有不同的教化作用;第三十二章述田子方束帛赎道所见老马的故事,而穷士人知所归心。第三十三章述齐庄公以挡其车轮的螳螂为勇士人,回车避之的故事,而勇士人归之。可见,《外传》对“汤降不迟,圣敬日跻”的解说,主要是围绕“敬”的含义,分别从谦德、诚慎、音乐的教化作用、仁爱及于马则致穷士人、敬“知进不知退”之螳螂精神等五个角度展开。对同一节诗,有这么多角度的阐发,真是启人心智。
这类情况还有很多。卷二第五章和第六章解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1]36-38(《卫风·淇奥》),卷二第十、十一、十二连续三章解说“执辔如组,两骖如舞”[1]42-46(《郑风·大叔于田》),卷三第四、五、六连续三章和卷八第十九章都解说“明昭有周,式序在位”[1]84-88(《周颂·时迈》),卷四第六、七两章解说“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1]134-136(《小雅·大东》),卷四第二十七、二十八两章解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1]158-159(《小雅·隰桑》),卷六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连续三章解说“王猷允塞,徐方即来”[1]228-233(《大雅·常武》),卷九第十、十一、十二连续三章解说“邦之司直”[1]314-317(《郑风·羔裘》),卷十第一章、二章和三章解说“济济多士人,文王以宁”[1]334-338(《大雅·文王》),等等,都是对同一节诗,从多种角度进行阐发,赋予诗句以丰富的意义。
三、《韩诗外传》解经方式的文学教育意义
班固对《韩诗外传》解诗的评价是“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汉书·艺文志》)班固对《韩诗外传》的解经方式持否定态度,认为没有解说出《诗经》的本义。的确,《韩诗外传》解经不重诗本义、诗本事,大多数并非《诗》的正解,而是别解,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别解却有其特别的文学教育意义。
以故事解说经典,并非仅《韩诗外传》采取这种方式,《韩非子·喻老》篇就是有选择地用故事解说《老子》某些语句,以事解经的方式实是战国以来流行的一种传统。对《诗经》,人们尤其重视博依之学。《礼记·学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注:“博依,广譬喻也。”不能够广譬喻,则不能安于诗。《学记》又曰:“古之学者,比物丑类。”郑玄注:“比物丑类,以事相况而为之。”比物丑类,即以事明理。孔颖达疏曰:“古之学者,比方其事以丑类,谓以同类之事相比方,则学易成。”以同类之事相比方,则容易取得好的学习效果和教学效果。孔疏进一步申明了以事说经方式的文学教育意义。《韩诗外传》正是如此。解诗者将抽象的道德品质及情感,用富于形象和情节的故事加以解说,把诗句故事化的解经方式,产生了诗句以外的丰富的联想意义。从研习者角度而言,在学习这种解经方式的过程中,会加强他们思索故事与诗句之间的联系,激活了研习者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重联想,重形象,可以视为文学教育。
《韩诗外传》对《诗经》多义共存的解说系统,其实也是通往战国以来大学教育最高理想的一种途径。《礼记·学记》:“古之教者……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古代理想的大学教育要九年而达到“知类通达”境界,何谓知类通达?郑注:“知类,知事义之比也。”张子曰:“知类通达,比物丑类是也。”朱子曰:“知类通达,闻一知十,而触类贯通也。”《韩诗外传》对同一节诗多所引申、多角度解说,不正是知类通达之教吗?也不妨说,《韩诗外传》对《诗经》的解说重启悟不重考索,实源自孔子诗教。《论语·学而》记孔子与子贡论诗,称赞子贡:“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为政》记,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教弟子学诗,看重的正是《诗》可以兴的作用,赞赏习诗者的是其“告诸往而知来者”举一反三、知类通达的能力,并非对《诗》本事的探究。
[收稿日期]2010-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