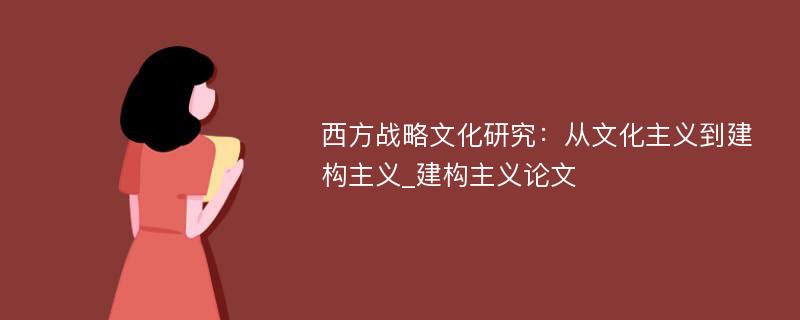
西方战略文化研究:从文化主义到建构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主义论文,战略论文,建构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4)03-0046-50
问题的提出:国家安全决策与战略文化
如何制定国家安全政策?战略决策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不仅是战略决策者们直面的问题,也是国家安全研究领域学者们探讨的永恒议题。西方传统的战略学一般认为战略决策是基于“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考虑,决策者以客观环境为归依,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做出判断,进而制定适当的国家战略。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一直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主流理论范式。
新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假定,国家在功能上是追求效用最优化的无差别实体,而效用一般定义为以能力和资源所代表的权力。因此,只要资源和条件许可,国家的行为就是要不断扩大其能力,以求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取得相对有利地位。国家的战略决策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这些非历史、非文化的客观变量,如地理、能力、威胁,特别是由物质能力分配而构成的国际体系结构。(注: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尽管在战略决策研究中,有一些文献讨论了决策的知觉(或知觉错误),(注: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但这些总体上只是对新现实主义分析框架的补充,新现实主义基本上没有为战略决策的战略文化方法提供理论空间。(注:See 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3,p.4,pp.12-15,p.18.)决策精英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基本上只考察国家的能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能力分配,这种能力是物质的,由这种物质能力分配构成的国际体系结构也是物质的。结果,观念、文化类因素在新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中完全忽略。
随着70年代以后国际安全环境的相对缓和以及国际政治理论本身的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领域出现的“文化”现象一样,文化研究也渗透到国际安全和国际战略领域,战略文化方法因此应运而生。研究战略文化的学者们认为,战略决策的产生不只是一个以客观物质环境为归依的理性取向,而是决策者受文化传统、历史因素局限之下的行为体现。正如美国学者伊萨克·克莱因所指出的,战略决策是对战争的一种主观判断,因此不同的军事组织、国家或民族对待暴力、战争的方法都各有不同,而形成战略思维多元化的现象。(注:Yitzak Klein,“A Theory of Strategic Culture”,Comparative Strategy 10:1,pp.3-24.)军事决策者们赖以制定战略之种种不同风格的信念,就成为战略文化的研究目标。从事“战略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战略文化”可以对不同国家、军队的战争行为提出更全面的分析。一般来讲,战略是政略的延续,但文化的因素就像藏在决策思想中的一面三棱镜,对客观环境加以分析,透过光谱将军事与政治目标相联结,演化出适当的战略。(注:曾瑞龙、郑秀强:《20世纪90年代的“战略文化”理论:一个拓展中的学术领域》[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24卷,第4期。)
战略文化方法在冷战结束以后的发展与新现实主义本身不能有效解释、预测国际社会的变化有关。冷战结束以后,新现实主义曾经预测,美国可能凭借它作为惟一仅存的超级大国地位重新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俄罗斯可能会由于权力的衰落而一蹶不振,中国可能会崛起而成为挑战美国霸权的对手。特别是,新现实主义预测冷战时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德国和日本,必将在后冷战时期根据自己的权力确定的战略利益,自信地调整其外交政策,实现它们的所谓外交正常化。(注:See Jeffrey S.Lantis,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ucrity,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Issue.1,2002,p.89 note 6,note 7.)例如,德国学者米切尔·斯图莫尔认为,冷战后欧洲的发展把德国置于欧洲大陆地缘战略的核心位置,诱使德国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强调目标的明确性和手段的可预测性。(注:See Jeffrey S.Lantis,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ucrity,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Issue.1,2002,p.89 note 6,note 7.)但是,经过冷战结束后10多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新现实主义根本没有正确预测主要事件(如体系变革),也没有在一个变化了的新的国际体系中描述国家安全政策模式。例如,美国尽管在后冷战时期、特别是布什政府时期单边主义有新的发展,但总体上还没有完全放弃多边制度框架,基本政策取向还是通过利用现有的多边、双边制度维护美国的霸权;俄罗斯尽管权力衰落,但从没有放弃作为世界大国的抱负;中国虽然权力不断增强,但无意于挑战美国的霸权,强调要和平崛起,做负责任的大国。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冷战的结束虽然在内政、外交政策上有所调整,但德国仍然坚持在欧盟框架内发展自己,坚持“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的身份,日本更是不断巩固和发展冷战时期确立的“美日安保机制”。所有这些,新现实主义无法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必须寻找新的理论范式作为替代,战略文化方法就是一种兴起于冷战时期,并在冷战后呈现积极发展态势的新的理论范式。
二、战略文化研究的议程:历史的考察
根据美国著名的战略文化研究专家江亿恩的划分,西方的战略文化研究经历了三代。(注:See 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3,p.4,pp.12-15,p.18.)以下本文以此为线索,侧重于从战略文化的起源、战略文化的功能来考察战略文化研究的历史演变。
1.第一代研究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所谓“决定论”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战略文化研究的重点是解释美苏两国核战略不同的原因,认为战略文化是固定不变的,美苏战略文化的不同是美苏两国不同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最早对战略文化进行直接研究的是斯奈德对苏联有限核战争学说的研究,他第一次提出“战略文化”的术语。斯奈德认为,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决策者对于核战略指令或模拟所共有的整体概念、制约性情感反应和习惯行为模式的综合。(注:Jack Snyder,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Implications for Nuclear Options,RAND R-2154-AF (Santa Monica,Calif:RAND Corporation,1976),p.9.)通过借鉴斯奈德的研究,这一代研究的其他学者,如格雷、洛德和琼斯也对战略文化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国家的战略文化主要是由历史经历、政治文化、地理位置等变量的独特性引起的。格雷提出,战略文化的输入因素包括更古老的先辈,更深的历史和文化根基,美国的历史经验影响着其对于武力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促使主导其战略选择的一套独特信仰的产生,而这一信仰又导致形成了美国独特的核战略。洛德认为,战略文化是根植于历史的、有时候无意识的、无系统的关于战争的本质、战争的必要准备以及战争方法的观念。琼斯认为,一国战略文化具有三个层次:它的基本因素来源于地理、民族文化和历史变量;社会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及政治文化,这些变量的互动产生了一国的战略文化。(注:See Jack L.Snyder,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Implications for Nuclear Options (Santa Monica,Calif.:RAND Corporation,1977);Colin Gray,“National Styles in Strategy:The American Example”,International Security 6,No.2(1981),pp.21-47;Colin Gray,“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tyle”(Lanham,Md.:Hamilton Press,1986);Carles Lord,“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Comparative Strategy 5,No.3 (1985),pp.269-93;David R.Jones,“Soviet Strategic Culture,”in Carl G.Jacobsen,ed.,Strategic Power:USA/USSR,pp.35-49(New York:St.Martin's,1990).)
如果对第一代研究者的观点进行解读,可以发现斯奈德与其他学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区别之一是关于战略文化的功能。斯奈德没有把战略原则绝对化,认为战略文化只是包含着一种“认知倾向”,而第一代的其他学者认为战略文化可以严格限制战略选择,走向了一种“机械决定论”。区别之二是关于战略文化的起源,斯奈德并没有把战略文化作为植根于历史-文化经验的产物,而是最近的历史经历、意识形态、高级政治、组织利益以及地理的混合因素导致的。
江亿恩认为,第一代研究在概念、方法论和经验研究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注:See 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3,p.4,pp.12-15,p.18.)从概念上看,第一代研究者所定义的战略文化的构成因素过于复杂,因此,其作用也非常有限。技术、地理、组织文化和传统、历史战略实践、政治文化、国家属性、政治心理、意识形态甚至国际体系结构,都被认为是战略文化的输入变量。但问题是它们本身就能够,事实上已经对战略选择做出独立解释。如果战略文化作为复合变量包含这些独立输入因素,那至少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怎样评估这些不同输入变量的作用。因为不同变量的作用大小可以解释不同的战略文化形成战略选择的作用。而第一代文献没有评估这些不同输入变量因素的作用。第二,战略文化这一复合概念不能证伪。如果战略文化是所有相关解释变量的产物,那么就没有概念空间解释非战略文化。与此相关的是,这一代的研究文献没有表明,一个国家的战略倾向何时产生足够性的变化,以致一个统一的战略文化不复存在。这一代的研究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一个社会根本不存在战略文化或者存在多种战略文化的可能性。方法论上问题涉及到战略文化和行为的关系。战略文化包含了历史行为作为关键渗入因素。也就是说,在前一段时间的行为应该是后一段行为的解释变量。后一段行为是植根于某一时段或者几个时段,那么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哪一时段的行为作为考察变量,应该怎样评估最近的历史经历与过去历史经历的不同影响。另外,这一代几乎没有或者很少文献讨论战略文化的工具性一面。在经验研究上,几乎很少文献讨论战略文化是如何传播的,无论是广义的文化过程(如教育、大众媒体、政治社会化)和狭义的战略文化过程(如军事教育、军事史的建构等)。
2.第二代为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的所谓“工具论”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战略文化研究有了深入发展,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国家内部的战略决策,认为战略文化是战略决策领域政治主导权拥有者手中的工具。(注:Main literature include:Bradley Klein,“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se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4(1988):pp.133-148;Robin Luckham,“Armament Culture”,Alternatives 10,No.1(1984):pp.1-44.)与“决定论”不同的是,“工具论”认为战略文化与实际的战略行为存在根本的断裂,战略文化无非是政治精英们模糊或掩饰他们的战略选择的工具。其目的是给他们所实施的战略赋予文化或法律上可以接受的合法性,并以此消除或误导可能出现的政治挑战。例如,布莱利·克莱因就认为,美国对外所宣称的战略,实质上是政治精英们为了使他们实际施行的战略被接受和消除潜在政治挑战力量的工具。(注:See Bradley Klein,“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se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4 (1988),pp.133-148,p.136.)这一代的研究仍然关注超级大国的战略文化,但采取的是葛兰西式的(Gramscian)视角。军事战略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反映了一种政治霸权秩序。“战略文化涉及到暴力的可能的倾向以及国家合法使用暴力反对潜在敌人的方法……研究战略文化就是研究国家有组织的文化霸权。”(注:See Bradley Klein,“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se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4 (1988),pp.133-148,p.136.)
克莱因的“战略文化”尽管是工具性的,但它并非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他强调战略文化的起源还是一种历史经历。由于不同的国家这些经历不同,因此不同的国家展示的战略文化不同。由于在战略文化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断裂,由于行为是国家利益或者是霸权集团的组织利益的反映,因此,战略选择应该受这些利益的限制。因此,尽管国家说的是不同的战略文化语言,但采取的往往是类似的战略行为。
“工具论”在这一代其他学者那里有一定的变化。以罗宾·洛克汉姆关于“武器文化”的研究为例。与其他战略文化学者不同的是,洛克汉姆认为战略文化并非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全球历史过程的产物。他把战略文化定义为一种武器崇拜论,这种崇拜论在现代化武器、军事优越性以及安全之间建立起实质性的因果关系,渗透到文化和心理的各个方面。人类意识包含了武器—安全的联系性;并且承认在战争体制中要改变这一点是不可思议的,承认武器竞赛、核遏止的合理性。这样的武器文化是为它的制造者服务的,这些制造者包括战略家、政治家、士兵以及武器制造商。从此意义上理解,文化是工具,但它是跨国性的工具。它不具有种族文化体系的独特性,它的独特性体现在全球层次上的工业化、军事化以及资本化。(注:Robin Luckham,“Armament Culture,”Alternatives 10,No.1(1984),pp.1-2.)
第二代战略文化研究文献的问题存在于象征性话语(即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工具性”意味着主要精英可以超越甚至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战略文化限制,但最新关于领导的研究预示着在战略文化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辨证关系。(注:See 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3,p.4,pp.12-15,p.18.)精英们被自己建构的战略文化社会化,结果自己也受到了这些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前辈的战略文化的限制。这就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精英们受制于他们建构的战略话语。结果,战略行为上的跨国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话语上的跨国不同。也就是说,战略文化也有可能真正影响战略选择。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第二代研究成果实际上陷入“工具性”与“功能性”的矛盾之中。
因此,从分析层次上看,第二代的研究既包括克莱因的着眼于国内层次的“战略文化”理论,也包括洛克汉姆的在全球体系层次上的“武器文化”理论。从“战略文化”的功能看,“工具性”是主流,但它没有从经验上考察战略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挥功能性作用。
3.第三阶段为90年代以来的所谓“干预变量”时期,即认为战略文化既不是决定因素,也不是工具,而是一种“干预变量”(有的学者使用了军事文化、政治军事文化或组织文化的概念)。
在这一时期,战略文化研究侧重于“利益决定论”所无法解释的战略选择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避免了第一代的“决定论”,认为战略文化是可以变化的。例如,“干预变量论”主要代表列格罗就认为,由于战略文化根植于最近的经验,而不是历史,因此战略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化的。二是注重理论的检验以及与不同理论的对比。例如,列格罗检验了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组织文化论对制约战争的解释。另一“干预变量论”代表人物科尔则将结构现实主义、官僚组织理论与战略文化论进行了对比。
由于在后冷战时期,这一代学者的研究范围突破了超级大国,而关注更多中小国家,研究的领域也更宽广。例如,科尔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英国不同的军事学说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两国军队不同的组织文化导致了不同的军事学说。(注:Elizabeth Kier,“Culture and Military Doctrine:France between the Wars,”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No.4(1995),pp.65-93.)这些文化是由三个层次的观念、信念和规范组成。第一层次涉及到对国际政治和战争本质的评估,第二层次涉及到军队、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第三层次涉及到国内组织、技术和官员与士兵的关系。列格罗把组织文化定义为“一种假设、观念和信念的模型,它限制了一个团体如何适应其外部环境而进行内部结构管理”,并且对二战中使用潜艇攻击商船、轰炸市民以及使用毒气有不同层次的限制。(注:Jeffery W.Legro,Cooperation under FireL Anglo-German Resraint during World War Ⅱ (Ith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
以彼得·卡赞斯坦为首的学者们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集体著作《国家安全的文化:国际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进一步确认“战略文化”的内容,把行为规范与国家认同视为影响战略决策的决定性变量。(注:Peter J.Ka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本书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探讨了两方面主题:第一个方面是探讨战略决策中的文化、制度背景,其中涉及对各种行为规范的讨论。另一方面则集中讨论国家、种族的认同对战略决策的影响。本书的作者们认为,规范是一个在群体生活中产生的行为准则或风俗习惯。其作用也有两种:其一,规范可以建构一个国家新的认同。其二,规范也能进一步确定一个已经存在的国家认同。本书另一个主题是对认同的有关研究。本书视“认同”为国家建构中的主要变量,进而认为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是此种认同的确立过程中造成的现象。事实上,本书的作者们普遍地认为“文化”既是一套评价标准(evaluative standard),也是一种认知准则(cognitive standard),而不同种类的“规范”以及“认同”就是在这个广义的文化平台上运作,其存在决定了各个国家、群体该在何种制度下生存、社会制度怎样运作、如何规范与其它群体的关系等等。根据本书的观点,规范与认同实际上限制了决策者可运用的手段,战略决策不可能脱离文化体系而存在,“战略文化”应该被确立为研究国防决策、战争战略的主要方向。
从第三代、特别是《国家安全的文化》中我们可以发现,战略文化研究已经超越了单位层次上的国家,而试图从体系层次上,探讨国际规范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而且,从功能上看,国际规范不只是限制国家的行为,而是通过改变国家的认同,重新建构国家的利益,最终根据新的国家利益采取新的战略行为。
三、文化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研究路径
通过对战略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战略文化研究基本采取的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两种路径。
文化主义与建构主义都是用来描述安全研究的观念转型的两种研究方法,关心的都是规范对国际安全的作用,包括限制作用和建构作用。规范不仅可以作为行动的“路径图”(road map)而限制行为体的行动,而且本身就可以塑造行为体以及行为体有意义的行动。二者在核心概念和基本思想上存在着相当大的一致性。
文化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存在明显区别。一般认为,文化主义起源于比较政治学,而建构主义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理论方法。约翰·杜费尔德认为建构主义是一种宏观理论框架,而文化主义则更关心的是安全研究中“文化的本质、原因和结果”。(注:John Duffield,“Political Culture and State Behavio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No.4(19991),pp.765-804.)
文化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更多的可能集中于分析层次上。建构主义趋向于关心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国家行动的社会结构。对于建构主义来说,国家做它们认为最合适的事。尽管建构主义对于考察规范如何塑造世界政治结构感兴趣,但大部分著作还是集中在处理国家间冲突和国家使用暴力的规范基础。(注:参见亚力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Janice E.Thomson,Mercenaries,Pirates and Pirates and Sovereign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而文化主义考察的是在国内层次上的规范如何塑造国家的安全政策。早期文化主义著作的目标是理解美国敌人的特殊的军事属性。(注:For discussion on this early culturalist literature in security studies,see Alastair Iain Johnston,“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No.4(1995),pp.36-49.)最新的文化主义著作显示有关国家军事行动是由决策者和政治精英的集体信念(战略文化)以及军队指挥官(组织文化)塑造的。
分析层次上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化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世界构造的更深刻的内涵。(注:Theo Farrel,“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Issuel,2002.)建构主义认为国际规范塑造了国家的形式和行动的相似性,而不管国家的物质能力。例如,所有国家无论权力大小,都相互承认主权。而当文化主义者关注国内规范对国家形式和行动的影响时,往往导致了国家行为的差别。结果,建构主义者和文化主义者对国家行为往往进行相互冲突的预测。以核问题为例。建构主义者预测新的核国家通过模仿旧的核国家的行为方式而确定他们的身份;而文化主义者往往预测所有新、旧核国家由于各国文化差异则对核力量的态度呈现国家和组织差异。
如同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可以交叉一样,建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也并非不可融合。有些建构主义者意识到需要对国际规范的国内起源进行研究。这就要求对国家内部进行观察,看国际规范如何同地方行为体(local agent)建立联系。(注:Jeffrey T.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orld Politics 50,No.2(1998),pp.340-342.)这方面研究特别有意义的是建构主义对人权规范传播的研究。与此相对的是,一些文化主义者在研究中也开始发现,一些在国内军事结构中制度化并且体现在军事实践中的规范,往往起源于该国以外,来源于国际规范。(注:Theo Farrell,“Transnational Norms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Constructing Ireland's Professional Arm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No.1(2001),pp.63-102.)
作为研究方法,文化主义和建构主义实际上为西方战略文化研究提供两种研究路径。根据前面对西方战略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战略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从文化主义到建构主义的演变。
第一代研究基本上遵循文化主义研究路径。尽管第一代研究成果变量的多少、远近以及战略文化的功能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基本上都认同国家内部因素,如历史经验、政治文化、地理位置等因素塑造了一国的战略文化,从而决定一国的战略选择。在第二代研究成果中,有部分成果采取的是文化主义研究方法,如克莱因的研究。但罗宾·洛克汉姆关于“武器文化”的研究,则是建构主义方法,他认为战略文化并非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全球历史过程的产物。在第三代有关战略文化研究的大量案例中,国际规范通过“社会化”进程,内化为国内合法性规范,从而建构国家新的认同,影响、塑造国家的战略决策。
两种路径反映了战略文化形成的不同的进程。在文化主义路径中,战略文化研究只考虑国内变量,国际社会中观念、文化和规范对一国战略文化形成没有影响,各国战略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各国国内变量的独特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独特性的战略文化必然带来战略决策的差异性。但在建构主义看来,各国以国内规范为代表的战略文化并非完全是一国内部的产物,国际社会的规范可以通过社会化过程改变、甚至完全取代国内规范,从而改变一国由自己的历史特殊性而形成的独特战略文化,使得各国(至少在某一领域)的战略文化呈现趋同现象,导致国家的战略决策也趋同。
收稿日期:2004-0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