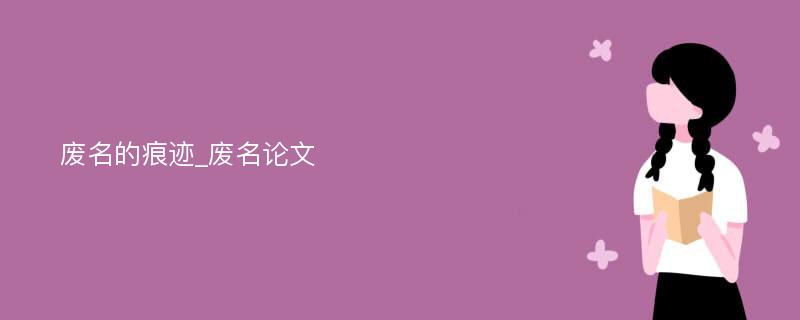
废名的踪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踪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史家通常既把废名视为京派小说的鼻祖,同时又把他定位为自成一家的小说名家。废名的小说尤其以田园牧歌的风味和意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他的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长篇小说《桥》等都可以当作诗化的田园小说来读,这些小说以未受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冲击的封建宗法制农村为背景,展示的大都是乡土的老翁、妇人和小儿女的天真善良的灵魂,给人一种净化心灵的力量。他的这类小说,尤其受传统隐逸文化的影响,笼罩了一种出世的色彩,濡染了淡淡的忧郁与悲哀的气氛。因此周作人在给废名的《桃园》作跋时说:“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一种悲哀的空气中行动,“好象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在这一点上废名君的隐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势力”。 这种朦胧暮色所笼罩的田园牧歌的所在地就是废名的故乡——湖北黄梅,这也是他寓居北京时期时时回眸的地方。废名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5)、《桃园》(1928)、《枣》(1931),长篇小说《桥》(1932)、《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等——也大都以自己的故乡作为题材抑或背景。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集中创作的一些散文中,也每每向故乡的童年生活回眸。这些别致的散文所状写的儿时旧事,完全可以与小说中的乡土事迹进行比照。这是一个有着独特的文学之美的乡村世界。30年代的沈从文对废名作品中作为文学世界的故乡有如下描述: 作者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乡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的活到那地上。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的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论冯文炳》) 同样在文本中建构了另一个乡土田园世界——湘西边城的沈从文,是从“乡村空气”的角度进入废名的文学创作的,这种视角与周作人不谋而合。两个论者都从废名的作品中嗅到了某种空气,沈从文的“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说法更贴近废名营造的原生态的、质朴而淳厚的乡野气息,而周作人则捕捉到废名小说中淡淡的悲哀的色彩和氛围。如果说沈从文看到的是一个令他感到真实而亲切的乡土,那么周作人所表达的,则是对这一乡土世界必然失落的怅惘的预感。周作人把废名的田园小说,推溯到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背景中,因而看出废名的田园世界笼罩了一种出世的色彩,从而也就纠缠了一丝淡淡的忧郁与悲哀。废名大部分以故乡为背景的创作,都能印证周作人的上述论点。 如果说,《竹林的故事》、《河上柳》、《菱荡》等短篇小说中更令读者嗅到“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那么,长篇小说《桥》中则更浸透着一种世外桃源般隐逸的空气。 《桥》于1925年开始写作,前后延续了十余载,所以人们说废名“十年造桥”,《桥》由此也成了废名最为精雕细刻的作品。这部小说没有总体上的情节构思和连贯的故事框架,通篇由片断性的场景构成。男主人公小林和两位女主人公琴子、细竹虽然构成了经典的三角恋爱模式,但彼此间的关系远没有《红楼梦》中宝、钗、黛三人间那么复杂,小说每一章写的几乎都是读书作画、谈禅论诗、抚琴吹箫、吟风弄月,每一章独立成段落。这一切使《桥》逸出了经典意义上的小说成规,因此,评论家都从诗化特征的角度分析这部小说,如灌婴称“这本书里诗的成分多于小说的成分”,朱光潜也认为“《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①。 而《桥》的隐逸色彩则表现在它有一种田园牧歌的情调,使人联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30年代即有评论者称它是“在幻想里构造的一个乌托邦。……这里的田畴,山,水,树木,村庄,阴,晴,朝,夕,都有一层缥缈朦胧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这本书引读者走入的世界是一个‘世外桃源’”②。但废名倾情讲述的毕竟不是真正的桃花源故事,小说中的田园视景尽管不乏诗化的韵味与出离尘寰的格调,却同时也像沈从文所说的那样混合了牛粪与稻草的气息,或许这才是令废名魂牵梦绕的真实的乡土。流泻在废名笔下的,就是那浸透着牛粪与稻草气味的,既零散又无序的儿时乡土的断片化记忆。 废名以乡土为题材的小说中也留下了废名自己的成长痕迹。小说《桥》中的小林的形象就拖曳着废名童年的影子。《桥》中写到的“万寿宫”就是主人公小林儿时经常光顾的地方。 万寿宫在祠堂隔壁,是城里有名的古老的建筑,除了麻雀,乌鸦,吃草的鸡羊,只有孩子到。后层正中一座殿,它的形式,小林比做李铁拐戴的帽子,一角系一个铃,风吹铃响,真叫小林爱。他那样写在墙上,不消说,是先生坐在那里大家动也不敢动,铃远远的响起来了。(《桥·万寿宫》) 小林写在墙上的,就是“万寿宫丁丁响”这几个字。关于这几个字,作家汪曾祺曾有过如此发挥:“读《万寿宫》,至程林写在墙上的字:‘万寿宫丁丁响’。我也异常的感动,本来丁丁响的是四个屋角挂的铜铃,但是孩子们觉得是万寿宫在丁丁响。这是孩子的直觉。孩子是不大理智的,他们总是直觉地感受这个世界,去‘认同’世界。这些孩子是那样纯净,与世界无欲求,无争竞,他们对此世界是那样充满欢喜,他们最充分地体会到人的善良,人的高贵,他们最能把握周围环境的颜色、形体、光和影、声音和寂静,最完美地捕捉住诗。这大概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仙境’。”③ 汪曾祺因此说废名的小说“具有天真的美”,这反映了废名本人也是个大有童心之人,而这种天赋的童心才是废名得以进入儿童世界并从中发现童心之可贵的真正原因。在《万寿宫》这一章中,小说叙述者称,如果你走进曾被用作孩子们的私塾的祠堂,“可以看见那褪色的墙上许多大小不等的歪斜的字迹。这真是一件有意义的发现。字体是那样的孩子气,话句也是那样孩子气,叫你又是欢喜又是惆怅,一瞬间你要唤起了儿时种种,立刻你又意识出来你是踟蹰于一室之中,捉那不知谁的小小的灵魂了”。这种“有意义的发现”正是儿童世界的发现,在“孩子气”中有“小小的灵魂”。废名称童心“无量的大”,这种童心的发现获得了近乎发生学的本体性意义。这是对儿童心灵的自足性的确认,其中既有人类学的意义,也有诗学的价值。它显示了一种儿童的认知方式以及儿童观察和感觉世界的视角,为人们展现出一个非常别致的世界。 1937年抗战的爆发改变了当时作为北京大学讲师的废名象牙之塔里的生活。按规定,北京大学只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才有资格去西南联合大学,废名则回到了老家湖北黄梅。经历了多次挈妇将雏弃家“跑反”的流徙,终在1939年,凭借从亲属那里借到的三元钱旅资,辗转到了一个乡村学校——金家寨小学教国语。半年后又赴临时设在五祖寺的黄梅县中学教英语,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重返北大任教。1947年,应《文学杂志》的编者朱光潜之邀,废名创作了以自己故乡避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从1947年6月到1948年11月在《文学杂志》连载,于是,就有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以下简称《坐飞机以后》)的面世。 当年第一次读《坐飞机以后》之前的心理期待,是预期看到一部乡土乌托邦的图景,看到乱世中难得的世外桃源般的时光,正像废名的《桥》勾勒的田园牧歌的理想国图式那样,或者像出自废名对自己在北京西山居住经历的摹写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传》(1932年),描画的是一种出离尘寰般的隐居生活。然而,废名在《坐飞机以后》中的变格,着实令我吃惊。小说中的“莫须有先生”的形象当是《莫须有先生传》中的传主形象的赓续。而1932年版的《莫须有先生传》中的莫须有先生形象是一个颇有点儿像堂吉诃德的喜剧人物,“对当时的所谓‘世道人心’,笑骂由之,嘲人嘲己,装痴卖傻,随口捉弄今人古人,雅俗并列”④。废名创作这部小说时带有几分“涉笔成书”的游戏态度,尤其大肆玩弄即使在21世纪看来也有超前性的先锋叙述,但它除了叙述和文字的快感外,在内涵方面是较为空洞的,称《莫须有先生传》只是一部语言游戏和叙述游戏也不过分。所以到了20世纪40年代,连莫须有先生本人对当初的自己也表示不甚满意,在《坐飞机以后》的“开场白”中莫须有先生即表示“我现在自己读着且感着惭愧哩”,《莫须有先生传》是自恋的镜像,是孤独的呓语。鲁迅当年称废名“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只见其有意低回,顾影自怜之态”⑤,是大体准确的评价。1947年的废名还称《莫须有先生传》中的“事实也都是假的,等于莫须有先生做了一场梦”,而《坐飞机以后》则“完全是事实,其中五伦俱全,莫须有先生不是过着孤独的生活了”。当然,40年代的莫须有先生依旧像《莫须有先生传》中一般自鸣得意,夸夸其谈,自我膨胀,但是这部新小说总体上看的确是废名极力声明的一部写实性的“传记文学”。除了莫须有先生这个名字是“莫须有”的之外,小说更接近于信史而远离虚构作品,基本上可以当作废名故乡避难生活的传记来看。而充斥于小说中的莫须有先生的长篇大论也值得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认真对待,小说由此堪称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历经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涯的另类心史,是废名在小说中一再提及的“垂泣而道”之作,在某些段落可谓是忧愤之书,甚至可以说是像当年鲁迅那样忧愤深广。废名极力使读者改变对30年代那个疯癫癫的莫须有先生的印象,以期引起读者对小说中的宏论的充分重视,正是因为小说中表达的是废名在整个抗战期间避难乡间而从事的思考,其中的思想大多关涉国计民生、伦理教育、生死大义、道德信仰,是从底层和苦难生活中逼出来的活生生的念头,而非象牙塔中的凭空玄想。我以为废名在故乡过着隐士般生活的预期压根儿就是错的,正如小说所写:“莫须有先生现在正是深入民间,想寻求一个救国之道,哪里还有诗人避世的意思呢?”抗战阶段归乡避难反而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考察乡土民生和社会现实的历史机缘。小说由此呈现了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传达了深入民间之后的沉潜的思索。我正是从一个作家的心灵历史和思想自传的角度看待这部小说,而这也恰恰符合废名对读者的要求。他一再声称“本书越来越是传记,是历史,不是小说”,读者也需要调整阅读心态,把莫须有先生的诸多惊世骇俗之论,看成肺腑之言与庄重之语,是战时废名潜心思索的如实传达。其中的观念取向有些是当时知识界普遍共享的,有些则颇不合时宜,是独属于废名的观念和思想。虽然这些思想从形态上讲无疑是小说家言,既显得另类,又显得驳杂,并无系统性,但仍不失为考察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一个案例。其历史价值尚不在废名所标榜的“它可以说是历史,它简直还是一部哲学”,而在于它的真实性。当我们把小说当成作家真实经历和思想的“写实”性纪录,并从观念和价值层面进行观照,《坐飞机以后》就构成了40年代中后期中国知识分子多元思想取向的一部分,展示出颠沛流离的战争生涯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的复杂的历史视野。 战争带给废名一家最直接的经验首先是“跑反”。废名故乡的“跑反”堪比汪曾祺描述的在大后方昆明的“跑警报”,却更多一些久远的历史。“跑反”这两个字“简直是代代相传下来的,不然为什么说得那么自然呢,毫不须解释?莫须有先生小时便听见过了,那是指‘跑长毛的反’。总之天下乱了便谓之‘反’,乱了要躲避谓之‘跑反’。这当然与专制政体有关系,因为专制时代‘叛逆’二字翻成白话就是‘造反’,于是天下乱了谓之‘反’了……而且这个乱一定是天下大乱,并不是局部的乱,局部的乱他们谓之‘闹事’。‘闹事’二字是一个价值判断,意若曰你可以不必闹事了。若跑反则等于暴风雨来了,人力是无可奈何的。他们不问是内乱是外患,一样说:‘反了,要跑反了。’”废名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解释“跑反”及“反”与“闹事”的区别,并不是热衷于辨析词义及其沿革,而是揭示一个在民间有长久积淀的语汇其历史内涵的丰富性。“跑反”已经成为民间的持久记忆以及战乱年代的恒常的生存方式,甚至蕴涵着乡民的生存哲学和智慧。在废名的描述中,跑反的不仅仅是人,相反,“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头牛,其次是一头猪,老头儿则留在家里看守房子,要杀死便杀死”,反而有一种豁出去了的镇定,倒是跑反者每每谈“跑反”而色变。当然,跑得次数多了就也并非总是惊慌失措,农人们在跑反的间歇依旧聚众打牌,或者在竹林间谈笑自若地纳凉,令莫须有先生很佩服他们的冷静。莫须有先生的儿子纯,就是在一次次跑反的经历中伴随着“牛的沉默猪的惶惑”一点点长大起来,逐渐也不用爸爸抱着,而能自己跑反了,最终则学会了把跑反当成新奇的“探访”,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避难,都感到兴奋和喜悦。当然,孩子们更多获得的是“避难人的机警,不,简直可以说是智慧”。至于莫须有先生的逃难生涯则使得作为新文学作家的他神经更为敏感,脑细胞也特别活跃。逃难的过程中大脑里往往比平时充斥着更多的奇思异想,同时也激活了他的历史感,觉得“写在纸上的历史缺少真实性”,而真正的历史是在眼前获得现实印证的历史。莫须有先生在跑反的路上,就把自己同民族历史真正联系了起来: 眼前的现实到底是历史呢?是地理呢?明明是地理,大家都向着多山的区域走。但中国历史上的大乱光景一定都是如此,即是跑反,见了今日的同胞,不啻见了昔日的祖先了。故莫须有先生觉得眼前是真正的历史。 这种把空间(地理)时间(历史)化,并在“今日的同胞”中晤面“昔日的祖先”,都是一种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特殊体验,只有借助战乱的经历才能获得。 前引《桥》的《万寿宫》一章中“先生坐在那里大家动也不敢动”的一句描写,揭露了废名小时候私塾教育的冰山之一角。抗战爆发后,废名回到老家,直接在乡间从事小学教育,这种教书的经历构成了废名在《坐飞机以后》中对教育问题屡发宏论的资本。 废名对教育的反思是从乡土儿童教育开始的:“莫须有先生每每想起他小时读书的那个学塾,那真是一座地狱了。做父母的送小孩子上学,要小孩子受教育,其为善意是绝对的,然而他们是把自己的小孩子送到黑暗的监狱里去。”废名因而得出了“教育本身确乎是罪行,而学校是监狱”的论断,这与福柯在诸如《规训与惩罚》等著述中阐释的思想何其相似乃尔。莫须有先生称自己“小时所受的教育确是等于有期徒刑”,并将他小时读《四书》的心理追记下来,则“算得儿童的狱中日记”: 读“赐也尔爱其羊”觉得喜悦,心里便在那里爱羊。 读“暴虎冯河”觉得喜悦,因为有一个“冯”字,这是我的姓了。但偏不要我读“冯”,又觉得寂寞了。 读“鸟之将死”觉得喜悦,因为我们捉着鸟总是死了。 读“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觉得好玩,又讨便宜,一句抵两句。 莫须有先生以孩童在“狱中”无法压抑的童趣反衬“监狱”的黑暗,让读者认同所谓“小孩子本来有他的世界,而大人要把他拘在监狱里”以及把旧时代的儿童教育看成“黑暗的极端的例子”的说法。然而时至今日,乡土儿童教育依旧看不到光明。抗战期间,当莫须有先生归乡之后,依旧体验着“乡村蒙学的黑暗”,看着孩子们做着“张良辟谷论”之类的八股文题目而不知所云,感到“中国的小孩子都不知道写什么,中国的语言文字陷溺久矣,教小孩子知道写什么,中国始有希望!”他自己则身体力行,贯彻自己的新的教育主张。一方面引进新的语法教学,一方面革新作文理念,大力提倡“写实”,让孩子都有话说。他让“小门徒们”写荷花,写蟋蟀,读到一学生说他清早起来看见荷塘里荷叶上有一只小青蛙蹲在荷叶上一动也不动,“像羲皇时代的老百姓”,就“很佩服他的写实”,称“这比陶渊明‘自谓是羲皇上人’还要来得古雅而新鲜”。 在这个意义上,似乎还可以把《坐飞机以后》看成一部关于乡土教育的论述。 类似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美育也构成了废名教育理念的一部分,并使他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人生审美化的理想。废名往往把审美情绪和审美经验引入日常世界,实现着审美和人生的统一。因此,《坐飞机以后》虽然以长篇大论为主导特色,但是依旧充盈着大量富于审美情趣的乡土日常生活的细节。废名在叙述乡居生活、逃难生涯、患难之际的天伦之乐、乡亲之谊时,也是趣味横生,童心依在。譬如小说中关于莫须有先生的两个孩子——慈和纯——“拣柴”的描写: 冬日到山上树林里拣柴,真个如“洞庭鱼可拾”,一个小篮子一会儿就满了,两个小孩子抢着拣,笑着拣,天下从来没有这样如意的事了。这虽是世间的事,确是欢喜的世间,确是工作,确是游戏,又确乎不是空虚了,拿回去可以煮饭了,讨得妈妈的喜欢了。他们不知道爸爸是怎样地喜欢他们。是的,照莫须有先生的心理解释,拣柴便是天才的表现,便是创作,清风明月,春华秋实,都在这些枯柴上面拾起来了,所以烧着便是美丽的火,象征着生命。莫须有先生小时喜欢乡间塘里看打鱼,天旱时塘里的水干了,鱼便俯拾皆是,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落叶,风吹落叶成阵,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河水,大雨后小河里急流初至,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雨线,便是现在教纯读国语课本,见书上有画,有“一条线,一条线,到河里,都不见”的文句,也还是情不自禁,如身临其境,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果落,这个机会很少,后来在北平常常看见树上枣子落地了,但其欢喜不及拣柴。明月之夜,树影子都在地下,“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多”,见着许多影子真个独自多了起来,但其欢喜不及拣柴。 拣柴这一在乡土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场景被莫须有先生赋予了过多的美学和生命意蕴,而即如看打鱼,看落叶,看河水,看雨线,看果落,看树影,都是对寻常生活的审美化观照,表达的是生命中的惊喜感。 废名擅长的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这里面体现的是一种观照生活的诗性倾向,同时融入了一种诗性的哲思,这一切,恐怕深深得益于废名对待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拣柴的乡土细节中,充分表现了废名的艺术人生观。工作与游戏合一,背后则是审美观照,是诗性人生、欢喜人生,所以这里充分体现了废名对尘世的投入。废名的小说让我着迷之处正在于他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化观照。一旦把生活审美化,世间便成为废名所谓的“欢喜的世间”。这种“欢喜”,荡涤了废名早期淡淡的厌世情绪以及周作人所说的“悲哀的空气”。小说中也每每强调莫须有先生“是怎样地爱故乡,爱国,爱历史,而且爱儿童生活啊”,这当然是废名的夫子自道,莫须有的形象在此昭示的是一个欢喜而执着地人世的废名。《坐飞机以后》中记录了莫须有先生在除夕前一天进城采办年货而冒雪赶路,见一挑柴人头上流汗,便在道旁即兴而赋的一首白话诗: 我在路上看见额上流汗, 我仿佛看见人生在哭。 我看见人生在哭, 我额上流汗。 从艺术角度上看,这首“流汗”诗有游戏之作的意味,但是却表达了一个为他人的辛苦人生而感同身受的废名,一个如此贴近了乡土日常生活的更真实可爱的废名。 历经战乱的废名,其笔下的乡土记忆已经不再像“略带稻草气味”的早期那么纯然,已经又多了几许生之欢喜以及生之沉重,从而愈加丰富了中国的乡土记忆。 从文体学层面上说,从30年代的《桥》到40年代的《坐飞机以后》,都表现出废名卓尔不群的艺术品格。批评家刘西渭曾经这样评价废名:“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很少一位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遂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自有他永生的角落。成为少数人流连忘返的桃源”⑥。这个让“少数人流连忘返的桃源”,就是废名精心建构的别开生面的小说世界。鹤西便称赞《桥》说:“一本小说而这样写,在我看来是一种创格。”⑦朱光潜把《桥》称为“破天荒”的作品:“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没入心灵深处,颇类似普鲁斯特与伍而夫夫人,而实在这些近代小说家对于废名先生到现在都还是陌生的。《桥》有所脱化而却无所依傍,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先生的特创。”⑧《桥》之所以是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的文章,朱光潜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的故事逻辑,“实在并不是一部故事书”。当时的评论大都认为“读者从本书所得的印象,有时像读一首诗,有时像看一幅画,很少的时候觉得是在‘听故事’”。因此,如果对废名的小说追根溯源的话,废名可以说接续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几千年的诗之国度的诗性传统,他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诗性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废名堪称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鼻祖,从废名开始,到沈从文、何其芳、冯至、汪曾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能够梳理出一条连贯的诗化小说的文体线索。而废名作为诗化小说的始作俑者,为现代小说提供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破天荒”的创作。 如果说《桥》是“破天荒的作品”,那么在《坐飞机以后》中,废名发明的也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体——一种兼具哲理感悟和浓郁政论色彩的,以史传为自己的写作预设的散文体。以往偶尔涉及《坐飞机以后》的评论都倾向于以“散文化小说”来定位《坐飞机以后》,唐弢即称“要说‘五四’以来小说散文化,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⑨。废名自己也称: 莫须有先生现在所喜欢的文学要具有教育的意义,即是喜欢散文,不喜欢小说。散文注重事实,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只求写得有趣,读之可以兴观,可以群,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好;小说则注重情节,注重结构,因之不自然,可以见作者个人的理想,是诗,是心理,不是人情风俗。 废名在《坐飞机以后》中可谓是自觉地实践“注重事实,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只求写得有趣”的“散文体”的写作。 但是,废名的散文体又不同于现代其他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文体。为了承载史传功能,废名把散文体向更散的方向作去,以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散漫无际的大杂烩文体。可以说,借助这种大杂烩文体,他把自己抗战期间在乡下避难的全部思想,甚至战时写的那本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的断片,都一股脑儿塞到这部小说中了。也正因为他试图表达自己的议论和思想,如实记录避难生涯,所以以往如《桥》那样的小说的诗化框架和情节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他了。《坐飞机以后》的大杂烩文体就给了他最大的自由。废名堪称找到了一种集大成的写作方式,集历史、文学、宗教、道德、教育、伦理于一炉,小说的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史论、诗话、传记、杂感、典故、体悟、情境……都因此纳入小说之中。废名不仅超越了以往的自己,也超越了文学史,不仅为20世纪40年代,也可以说为整个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种他人无法贡献的文体形式。 废名的诗在现代新诗史上也是自成一格。在史家眼里,废名是30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群体的一员,但却被视为现代派诗人群中最晦涩的一位⑩。这与周作人的说法也恰相吻合,周作人当年也称“据友人在河北某女校询问学生的结果,废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懂”(11)。不过,比起文章来,废名诗的晦涩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多少影响了废名在诗歌史上的声誉。或许可以说,废名作为一名诗人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他的具有诗化特征的小说的烘托。卞之琳在80年代曾指出:“他应算诗人,虽然以散文化小说见长。我主要是从他的小说里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而不是从他的散文化的分行新诗。”(12)30年代评论界对废名小说《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也多半是由于在小说中读到了更多的诗境,评论者似发现废名“到底还是诗人”(13),不过这个结论却是基于他的小说而推导出来的。这恐怕与废名公开发表的诗作较少也不无关系。 废名的诗与小说有相得益彰的地方,都表现出哲理的冥想的特征。其诗歌中也每每有出尘之想。1927年废名卜居北京西山,从此开始长达五年的半隐居式的生活,其生活情境在《莫须有先生传》中可以略窥一斑。同时,废名也集中创作了一批新诗,诗中经常出现的,也正是一些“遗世”、“禅定”、“隐逸”等绝尘脱俗的意象。深山中禅定的形象,也堪称是废名的自画像,正如废名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一首诗《灯》的开头一句所写,“人都说我是深山隐者”。又如这首《泪落》: 我佩着一个女郎之爱 慕嫦娥之奔月, 认得这是顶高地方一棵最大树, 我就倚了这棵树 作我一日之休歇, 我一看这大概不算人间, 徒鸟兽之迹, 我骄傲于我真做了人间一桩高贵事业, 于是我大概是在那深山里禅定, 诗人“慕嫦娥之奔月”,结果到了一处出离人间、只有鸟兽出没的“顶高地方”,并把这种“深山里禅定”视为“人间一桩高贵事业”。诗人自我设想的形象,正是这种“深山里禅定”的形象,一如朱光潜当年评论《桥》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参禅悟道的废名先生”(14)。朱光潜也正是从“禅”的角度论及废名的诗歌:“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更惊叹它真好。有些诗可以从文字本身去了解,有些诗非先了解作者不可。废名先生富敏感的苦思,有禅家道人的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背景。”(15)这个“深玄的背景”,或许正是禅悟的背景、理趣的背景,它同时也构成了理解《莫须有先生传》和《桥》的背景:“《桥》愈写到后面,人物愈老成,戏剧的成分愈减少,而抒情诗的成分愈增加,理趣也愈浓厚。”(16)这种“理趣”的追求发展到诗歌创作中,就有了“深山里禅定”的诗人形象。而且,这种“禅家道人的风味”在诗中不仅仅体现为深玄的背景,它构成了诗歌的总体氛围,透露着诗人的审美理想,同时又具体地制约着诗中所选择的意象。 废名小说《桥》中的出世情调和彼岸色彩在他的诗中也得到了更充分的印证,体现为作者对一个梦幻般的想象世界的营造:“时间如明镜,/微笑死生”(《无题》),“余有身而有影,/亦如莲花亦如镜”(《莲花》),“太阳说,/‘我把地上画了花。’他画了一地影子”(《太阳》),“梦中我画得一个太阳,/人间的影子我想我将不恐怖,/一切在一个光明底下,/人间的光明也是一个梦”(《梦中》),“我见那一点红,/我就想到颜料,/它不知从那里画一个生命?/我又想那秋水,/我想它怎么会明一个发影?”(《秋水》)这些诗每一首孤立地看,都似乎很费解,但放在一起观照,诗中的“镜”、“影”、“梦”、“画”、“秋水”等等,就在总体上编织成了一个“镜花水月”的幻美世界,一个理念化的乌托邦的存在。用周作人评价废名小说《桃园》的话来说,即是“梦想的幻景的写象”(17)。从这个意义上说,废名的诗歌语言,是一种幻象语言。在一系列幻美的意象背后,一个幻象世界应运而生。到了1936年创作的《十二月十九夜》中,这个幻美的世界更臻佳境: 深夜一支灯, 若高山流水, 有身外之海。 星之空是鸟林, 是花,是鱼, 是天上的梦, 海是夜的镜子。 思想是一个美人, 炉火是墙上的树影, 是冬夜的声音。 这首诗堪称“意象的集大成”,诗中几乎所有的意象都是具体可感的,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的美好事物,然而被废名串联在一起,总体上却给人一种非现实化的虚幻感,似乎成为一个废名参禅悟道的观念的世界。一系列现实化的意象最终指向的却并非实在界,而是一个想象界,给人以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缥缈感。所以,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称这首诗“洋溢着凄清夺魂之美”(18)。诗人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编织幻美世界的诗艺技巧。 从营造幻象以及观念世界的角度总体上理解废名的诗作,可能不失为一条路子,并且有可能把握到废名对中国现代诗歌史的特出贡献。倘若单从诗歌体式上讲,废名诗歌的不足还是比较显见的。卞之琳的评价最为到位:“他的分行新诗里也自有些吉光片羽,思路难辨,层次欠明,他的诗语言上古今甚至中外杂陈,未能化古化欧,多数场合佶屈聱牙,读来不顺,更少作为诗,尽管是自由诗,所应有的节奏感和旋律感。”(19)尤其是废名的诗歌语言过于散文化、白话化,打磨不够,有时尚不及小说语言精练,则是更明显的缺失。除却上述不足,废名诗歌独特的品质却是他人无法贡献的。这种特出之处可能正在于他为现代诗坛提供了一种观念诗,一种令人有出尘之思的幻象诗,一种读者必须借助禅悟功夫才能理解其深玄奥义的理趣诗。 朱光潜在评价废名的小说《桥》时曾这样说:“‘理趣’没有使《桥》倾颓,因为它幸好没有成为‘理障’,因为它融化在美妙的意象和高华简练的文字里面。”(20)“理趣”之所以没有使《桥》“倾颓”,可能不仅仅因为“它融化在美妙的意象和高华简练的文字里面”,更因为《桥》在读者期待视野中毕竟是小说,是“小说性”制约了“理趣”,使它没有极端化。那么,在废名更为纯粹的观念诗中,“理趣”有没有成为把更多的读者挡在门外的“理障”呢?这恐怕是废名诗歌值得思索的另一个问题。 ①孟实(朱光潜)《桥》,载《文学杂志》1937年第1卷第3期。 ②灌婴《桥》,载《新月》1932年第4卷第5期。 ③汪曾祺《万寿宫丁丁响——代序》,见《废名短篇小说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 ④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 ⑤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⑥刘西渭《〈画梦录〉——何其芳先生作》,《李健吾批评文集》第132页,郭宏安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 ⑦鹤西《谈〈桥〉与〈莫须有先生传〉》,《文学杂志》1937年8月1日第1卷第4期。 ⑧孟实《桥》,《文学杂志》1937年7月1日第1卷第3期。 ⑨唐弢《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 ⑩参见蓝棣之《现代派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11)周作人《〈枣〉和〈桥〉的序》,收《苦雨斋序跋文》,天马书店,1934年。 (12)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13)鹤西《谈〈桥〉与〈莫须有先生传〉》。 (14)孟实《桥》,《文学杂志》1937年7月1日第1卷第3期。 (15)朱光潜《文学杂志·编后记》,1937年第1卷第2期。 (16)孟实《桥》,《文学杂志》1937年7月1日第1卷第3期。 (17)周作人《桃园·跋》,《苦雨斋序跋文》,天马书店,1934年。 (18)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第202页,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年。 (19)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20)孟实《桥》,《文学杂志》1937年7月1日第1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