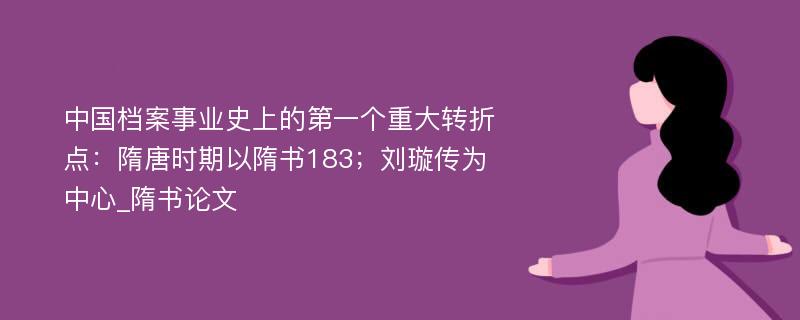
中国档案事业史上第一次重大转折:隋唐之际——以《隋书#183;刘炫传》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唐论文,史上论文,中国论文,事业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的发展与整个中国档案学的学科成长、内涵提升并不完全同步,尤其是最近的二十来年,除了郑州大学王金玉教授的宋代档案管理制度史研究外,鲜有其他具有范式意义的重大成果。这一方面,固然与本学科在整个档案学中学科地位相对边缘化,从业人数有限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教研人员缺乏敏锐的学术意识,对相关文献史料的发掘、勾陈与分析、理解能力尚有不逮,即使对一些已经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文献解读、阐释能力明显存在欠缺有关。就本学科而言,一些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的课题还基本未予展开,以致我们的某些教研人员对本学科的基本结构、主体框架、内涵、范围的界定等问题认识也存在偏差,如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分期问题、历朝(唐、明、清等朝)档案管理制度研究、近代档案学传入问题研究等。其中对中国档案事业史分期问题的探讨,多数的论著还停留在参照、沿用中国通史的分期方法,未能从本学科的专门史特点——有针对性地从自古至今的档案与档案工作产生、发展、成熟乃至定型、档案工作内涵的时代转型、变迁的内在演化规律出发,将中国档案事业史构建成一门具有专业史特点、又具有一定文化传播史、文明传承史内涵的档案专业基础课之一。事实上,某些专业或学科的历史分期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或脉络并不完全同步、重合甚至错位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并不奇怪,也不必强求一致:人文、思想领域内的发展转型(包括统治集团内部个别政治家的思想)往往要比整个社会转型或历史变迁先行一步,成为时代先声,相反作为国家机体中的某些上层建筑领域的观念、惯例、技术等则往往相较社会生产力及历史发展要滞后一些。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发展、演进就属于后者。
笔者以为,中国档案事业史的研究要取得档案学其他学科地位如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提升学科研究的层次与内涵,就需要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目前大多数研究成果还局限于介绍历代的文种及文书工作、档案管理制度史的微观视野,更要追求一些就本学科而言具有一定形上色彩的论题且属于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类似于八十年代关于档案起源问题的讨论,这是学科发展与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内在逻辑。本文利用两则史料就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分期(古代)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同行指正。
《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
(牛)弘尝从容问(刘)炫曰:“案《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对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复治,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炫对曰:“齐氏立州数十,三府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1]
案,牛弘,隋安定人(今甘肃泾州)。本姓尞,因其祖父允居高官而赐姓牛。文帝初年,迁秘书监(主管图书、文献、档案管理及著作之官),上任不久,就仿西汉初年的文化政策,向文帝上表建议“请开献书之路”。文帝极为赞赏牛弘的主张,并纳其言。后官至吏部尚书及光禄大夫(散官,从二品)。刘炫,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北)人。儿时以神童著称。有文献记其“左画方,右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并举”。成年后声名日隆。时适值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投机思想发作,想一夜成名、暴富,遂伪造数百卷“古书”以进,结果被人告发留下污点。其后虽为朝廷也贡献过若干正确主张,但均因前科而籍籍无名。开皇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征辽声,独刘炫以为不然。征辽战事失利后,人们逐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牛弘与刘炫的关系也开始渐渐走近,经常就朝廷之事相询于他。
上文对话是其中的一次。这段看似十分平常、随意的对话,却揭出了中国档案事业史上第一次大变革的史实。
汉时文书档案工作人员称令史。牛的第一问是“今令史百倍于前”的原因,刘炫用对比的方式回答了隋唐前后文书与档案工作业务内容及形式的巨大变迁;牛的第二问是令史工作为何“魏齐之时”还十分“从容”,而今令史职责却“不遑宁舍”,原因在什么?刘炫准确分析了发生这种巨大变迁的客观历史原因。
毫不夸张地说,这段文字是中国古代档案事业史上极其稀见的珍贵文献。《隋书》作者借刘炫之口阐明了:古代的档案与档案工作演进至隋唐之际出现了明显的分水岭这一基本史实。隋唐之前,“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需要强调的是,“案不重校”之“案”,应指文案、文书。隋朝统一之前,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南朝与北朝),大多是管辖范围极其有限的地区性政权,“魏、齐”是如此,宋、齐、梁、陈也是如此。文书工作的基本态势是“文书行下,不过十条”,规模和数量均十分有限。相反,隋朝重新回归统一以后则大相径庭。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对地方尤其是边陲地区要实现有效统治与管理,文书这一工具不可或缺。各级政府也一刻离不了制度设计。中央王朝需要颁行(以皇帝名义或以中央政府名义)大量的政务文书,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文件是普发性文书。由于传统制作文书基本手段是手抄方式(明清时期有极少数文书,其制作手段采用印刷术,如明代的户贴便是由明朝户部统一刊行且盖有户部大印,上留有若干空格以便各户据实填写。近代以后,才将印刷术较大范围地施行于文书制作,但还有大量文书继续沿袭手写的习惯,两种制作方式并行),这就意味着每一份同样内容的文书需要制作——手抄数十份乃至百余份文书。为了保证文书内容的准确、有效,必须履行严格的校对程序。文献记载中也频繁提到各级官府中设有“楷书”这样的文书膳写人员。缮写文书,难免有差错的情况发生。这就是唐朝贴黄制度(公文改错制度)产生的原因。“文不繁悉”之“文”,当然还是文书、文案,“悉”者,“细微”之谓也。隋唐之前,文书内容不需要面面俱到,繁复而冗长,也不是任何细微之事皆须“文书行下”。因此,相应地,文书档案工作的从业人员其本职要求仅是“掌要目而已”,且大多是兼职(由他官而兼)。然而,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多民族封建大帝国后,则完全是另一番情形了:“今之文簿,恒虑复治,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征百年旧案”。笔者以为,“恒虑复治”四字,蕴含极其丰富内涵。用我们今天的术语说,文书通常是单数用法,这里的“文簿”却是复数用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档案”,此处语境也只有是“档案”说才能“恒虑复治”,也即处于文书办理完毕以后第二阶段的工作,其性质才与此处的“复治”二字相吻合。“锻炼”者,“管理”之谓也。档案管理业务某环节的工作处理如若不系统,不周严,不细致,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万里追征百年旧案”,直接影响档案利用工作的开展,可谓立竿见影。“老吏抱案死”描写的则是经年甚至数十年专门从事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令史”(吏的一种)境遇。从事文书工作尤其是其中直接从事文书撰写者的身份与地位则要优渥得多。
本段文字的第二部分是分析引起这种档案、档案工作形式、内容及档案工作人员地位巨大变迁的历史原因。文书与档案工作的繁复,其终极原因是地域辽阔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帝国体制再次恢复与重建、国家机构及其职能的膨胀、拓展与政务分工的不断细密化所致。本段内容采用反复比较的方式,不厌其烦说明导致隋唐前后档案工作发生巨大转折的根本原因。“齐氏立州数十”,而“今州三百”;官员的职数,“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随员,“每州不过数十”,因是“长官自辟”,也没有多少相应的人事任命或考核等文书及档案材料产生。各级政府衙门(州、郡、县)的官吏总数从数人、十数人到数十人就可以包打天下了。而今,随着科举制度的诞生及全面实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的官员总数成十几或几十倍的速度激增,“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隋朝开始,在中央王朝确立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基本官僚体制,以礼部因科举考试而形成的举子铨选材料和以吏部与考功司为主的官员人事管理部门形成并积累了数以万计、甚至是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官员任命与考核材料(唐朝则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用于管理、考核和任命官员或准官员依据的“甲历”档案)。古代,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全部档案构成主要不外乎包括以记录君主活动为中心内容的所谓“皇家档案”、官府运行类(上行与下达)文书档案、在任官员与科举考试合格士人(准官员)的甲历档案、因管理社会事务而形成的包括民政、司法系统在内的户籍档案(历代封建王朝财政收入获取的凭借和依托,也是数千年编造史从未中断。户籍的职能从来就不仅仅是人口与户籍管理的依据,它还承载着众多人口管理以外的功能,这种制度设计一直延续至今)及诉讼档案(自古至今诉讼档案的保管具有特殊地位,通常需要永久保管,古代称作“常留”类[2],这种传统具有普遍性和继承性)等有限的几个门类,它们无不与上文所述的国家机构管理职能的全面拓宽与分工细化相关。当然,专门从事档案管理工作的令史地位的下降还与选拔标准的下降存在对应关系。隋唐之前,档案管理工作大多属于兼职,汉代的司马迁、班固其本职主要是史官,各有名垂千古的著作传世,但他们又都是兼职的档案管理官员(司马迁:“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后上丞相”,小小的太史公府积累从全国各地报给汉代中央政府的全部计书材料——类似于今天的统计数据报表,甚至还是文书的正本;更不用说,班固还是东汉明帝直接遴选的“兰台令史”,而兰台更是汉代最大规模、最有影响的中央王朝档案典籍收藏机构,其著作《汉书》的完成便是他利用这一得天独厚、无人能及的身份地位与文献获取优势的结果),其社会地位主要是通过史官身份及著作成就取得的。但是,隋唐以后,作为专职的文书档案工作管理人员大多籍籍无名,“无名氏”是隋唐以后所有档案工作从业者的统一无奈别称。宋代千文架阁法的创立者周湛不是因为他的转运使身份,历史上也不太可能留下他作为档案工作创新者的名字。即使宋代有些早年曾经从事过文书档案的管理工作,后期获取很大声名的官员,其政绩与功名也大多是因为后期的非档案管理职官的身份及影响所及。
但是,刘炫在这个问题上颇为消极。他不是一个与时俱进者,用他的话说:“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虽然病因找到,但药方是错配的。牛弘自然“甚善其言而不能用”,因为历史不可能开倒车,也不可能回到“魏齐之时”,从前那种“府史之任,掌要目而言”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这不符合历史及社会发展的趋势,从机构设立到职能设置都不允许档案工作如此定位。档案工作的发展趋势必然是越趋专职化,具体表现为出现专职的档案工作人员(甲库令史)以及专门化的档案工作机构(甲库)。这种变化不是点滴,而是全方位的,是结构性、制度性的变化,完全称得上中国档案事业史的第一次转折,也完全有理由断言:宋代出现的大批量的、专门性的古代档案工作机构——架阁库是隋唐时期档案工作制度化框架确立的逻辑结果。隋唐时期的档案工作基础与成就为古代档案工作的发展至两宋时期的定型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与技术条件。
这是一则涉及宏观层面的古代档案事业史的史料,很好地阐述、说明了隋唐前后档案工作形式与内容的巨大变化与历史变迁。
还必须说明的是,《隋书》成书于唐初,由魏征等人奉唐太宗李世民之诏编纂而成。因此,这段史料中描述的情形也客观上包括唐初的档案工作状况。
无独有偶,有关唐代的档案事业史的史料,不仅有宏观层面的材料,还有一件十分难得的、具体涉及档案整理、管理及保护的微观细节史料。那就是唐元和八年(813年)任吏部侍郎(主管官员考选及甲历档案管理)的杨于陵曾向宪宗建议:
臣伏以铨选之司,国家重务,根本所系,在于簿书。承前诸色甲敕等,缘岁月滋深,文字凋缺,假冒愈滥,难以辨明,因循废阙,为弊恐甚。若据现在卷数,一时修写,记其功值,烦费甚多。窃以大历(代宗年号,766-780)以前,岁序稍远,选人甲历,磨勘渐稀。其贞元(德宗年号,785-805)二十一年以后,敕旨尚新,未至讹谬。纵须论理,请待他时。臣今商量:从大历十年至贞元二十一年(775-804),都三十年,其间出身及仕宦之人,要检覆者,多在此限之内。且据数修写,冀得精详。今冬选曹,便获深益。其大历十年向前甲敕,请待此一件修毕,续条贯补辑。臣内省:庸薄又忝选司,庶销涓矣。以俾朝典,谨具量补年月及应须差选官吏,并所给用纸笔杂功费用。[3]
笔者将这段史料中涉及的文字及档案工作史实也略作梳理:(1)档案及甲历档案对朝廷、国家的管理作用。在杨于陵看来,所谓“国家重务,根本所系,在于簿书”。作为主管吏部考选的官员,一刻也离不开甲历——唐代官员在铨选、任用过程中形成的人事档案。如对文武官员的定期考核形成的考课材料。史载,刺史崔邈对属下桂阳令袁嵩的考辞:“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见任”。按照当时的规定,刺史对属下的考语也需向吏部归档。顶头上司对袁嵩因“妻管严”而做出的“考下”评语直接成为吏部“解见(即“现”)任”的依据。可见甲历档案在人事管理、选举制度中功能的不可或缺性。(2)档案管理及整理的必要性。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已经形成并归档的材料,几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以后,以普通纸张为载体的档案材料不可避免地存在“文字凋缺”或纸张破损的情况,由此引发“假冒愈滥,难以辨明,因循废阙”的弊端。档案管理、整理及保护的业务需求很自然的提上议事日程。但这项工作必须考虑轻重缓急以及经济或技术上的现实可行性。“若据现在卷数,一时修写,记其功值,烦费颇多”。假如要对收藏在各甲库中所有的甲历、甲敕——“现在卷数”全部“修写”,完全没有必要。文中“请待此一件修毕”中“一件”应作“一批”解。因为在这里显然不是单数,而是集合名词。这一史实在《新唐书》杨于陵传中也有述及。“请修甲历,南朝置别簿相检实,吏不能为奸。”[4](3)这次整理的重点是“从大历十年至贞元二十一年(775-805),都三十年”间(距上奏之年前八至三十八年前的材料)形成的甲历。由于利用——文中也称“磨勘”频繁的官员甲历、甲敕大都在这一区间,所谓“其间出身及仕宦之人,要检覆者,多在此限之内。”而“大历”之前的甲历及“贞元二十一年以后”的甲敕不是利用较少,就是“敕旨尚新”,没有必要挤在这一时间段内作为此次整理的重点对象。(4)“修写”一词的含义。笔者以为,此处“修写”二字,实则今日之重抄,它道出了古代档案整理一以贯之、沿用千余年的基本做法,即重抄、缮写。“修”与“写”的关系可以理解为通过重抄、缮写获取与原件信息内容完全一致的新材料,以达到所保存的材料内容真实、准确的目的,从而实现档案整理的目标。换句话说,通过“写”(缮写)这种渠道达到“修”(修复,注意:是信息内容的修复,不是原件修复)的功能。当然,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份材料了,而是与原件信息内容完全一致“新档案”。有人将“修写”二字理解为古代直至今天书画作品保护技术中普遍采用的修复、修裱技术,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这种理解只能是以今律古的产物,是今人恣意的想象,是我们对前人思想观念与做法不能做到“同情之理解”的结果。由于中国古代尚无档案原件概念,档案管理与整理的标准、目标定位在信息内容的真实准确性上。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档案管理与整理(也可以说保护)必然选择重抄这种既经济、实用,技术上又可行的办法。这种办法直至明、清时期尚无改变。如,明代规定,“凡天下臣民实封入递,即于公厅启示,节写副本,然后奏闻。”[5]清代更是如此。从嘉庆十年起规定,“凡清字、汉字之档,岁久则缮,清字档每届五年,汉字档每届三年,均由军机大臣奏明另缮一份。”[6]有清一代,都把缮写、录副、会抄作为档案整理与管理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原因其实也并不复杂。中国古代的修复、修裱技术在保护书画作品中确实起到了无可替代又行之有效的作用。但是书画作品与普通的文书档案最大的区别是:书画作品的价值是与特定作者联系在一起的,王羲之亲笔的《兰亭集序》(假如存在王的真迹)与后代其他人临摹的同题材作品,其价值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假如诸葛亮亲笔写成的《出师表》还存世,其价值也必然连城。而档案的名义作者往往是机关或机关负责人,但文书档案的实际作者(起草者或书写者)则往往是“无名氏”(上文已提及),即使是内容极其重要的文件材料,往往也假手于“无名氏”。在此思想、观念指导之下,档案整理与管理(包括保护)采用经济实用的重抄手法就不难理解了。且也为后世的史实所证明。(5)离开文本再举一则颇为极端的例子。据《文昌杂录》卷二记载,宋元丰官制初行时,尚书省六部诸司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接收到了十二万三千五百余份文件[7],这还仅仅是中央政府若干职能部门的两个月的收文量,还不包括这些部门的发文数。由此也不难推断,古代档案整理或保护中实行托裱修复技术的不可能性与不可行性。
尽管上述两则材料在学界早已发现,但在笔者看来,并没有真正重视并发掘出这些材料在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中——尤其是在档案事业史历史分期研究中的重大史料价值和丰富内涵。两则材料,前者属于宏观材料,回答的是隋唐前后档案工作体制、规模及其实践内涵的历史变迁以及隐藏在这种变迁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后者则属于典型的微观材料,具体针对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一批档案材料的整理、保护的工作的对象、细节与实施途径。就目前材料而言,应该是最早阐述特定时期档案整理的对象、重点、方法与路径的经典文献,都是不可多得的档案事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至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专门档案机构——唐三省甲库,系统的档案管理律令制度、完善的档案信息征集制度(即著名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确立的史料征缴制度)等唐代档案工作史实更为学界耳熟能详,在此不再赘述。但是,笔者还想就这个阶段古代档案利用工作的认识及有关情况说几句。无论古今、中外,档案利用目的及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政务利用,二为修史之用(广义的学术利用,实质也是历史研究之用的延伸)。但是对于后者而言,谁在用,为谁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却是存在差异的。隋唐之前,为我们档案界津津乐道的司马迁、班固作为古代档案利用——编史修志之用的楷模、代表,与隋唐以后的修史之用有一显著区别,前者表现为利用者与管理者的重合,即利用者往往是管理者自己,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明代学者凌稚隆从著述质量的角度对班固的《汉书》的评价不无微词,“孟坚掇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耳。”[8]从侧面理解,可能《汉书》中的“抄录”或移录的档案文献比重过大了,从而不无降低文章本身“独创性”价值的嫌疑。但是,隋唐以后,管理者与利用者明显分离了,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班、马的档案管理者与利用者双重身份合一的情形了。那些为史家撰著一代国史或以弘扬帝王文治武功为主要目的的实录的编纂,提供档案材料的“档案工作从业者”们则完全淹没在“故纸堆”中,称为历史上的“沉默者”、“失踪者”了。应该说,这也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必然,也是档案事业史发展变迁的内在规律。
当然,各类档案材料的大宗利用毫无疑问在于政务,上文提及并分析的杨于陵关于甲历档案的整理建议,问题缘起也在于“国家重务,根本所系,在于簿书(即甲历)”,即甲历的现实政务利用功能。这种官员甲历、甲敕是组织部门(吏部等)考核、任用的直接依据。细分一下,这种利用应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集中(定期)利用,如甲历;一种是不时之用。通常是:如若政务管理或运行中遇到一些一时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遂寻求于政务实践活动的副产品——既往档案材料(历史上将这些材料称为“故事”。“故事”者,顾名思义是“过去之事”,但史书中涉及“故事”者,往往又特指“过去的文件”、“过去的档案”、“过去的事例”规定等,均与已经办理完毕的文书或已转化为档案的文字记录有关),以此作为解决这类疑难问题的途径、线索、依据等。这种利用材料在历代史书中,从绝对数量来说,肯定不乏其例。但这种利用又属于政务实践、运行的惯例之事,不是值得正史大书、特书的所谓“盛事”,所以相对地说,也不一定常见、频见。这里,笔者将《隋书》上检索到的一则材料供大家参考。
现存《隋书》相对简略,档案利用的直接例证也较少。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隋书》卷八志第三记载了一个故事:陈永定三年(559)七月,武帝驾崩。新任尚书左丞庾持主持皇帝丧礼。他当着满朝文武说,晋宋以来,皇帝驾崩丧礼按惯例必须先到太庙告祖,然后进哀册(如今悼词)奉谥,从灵柩上车起对先帝即呼“某谥皇帝”,但晋宋以前,情况有异。先帝在未入土前任何时候只能称“大行皇帝”。孰是孰非,朝廷需加“详正”。于是朝廷上下各抒己见,各执一端。时任国子监博士沈文阿记起宫中曾有一批萧氏梁朝的礼仪文书档案。他通过“检梁仪”,仔细查阅了梁朝有关皇帝丧礼的礼仪档案,得出如下结论:“自梓宫将登辒辌,版奏皆称‘某谥皇帝’登辒辌”。意为:自先帝灵柩登灵车起,哀册上即可用“某谥皇帝”语。现在既然谥号已定,哀册已宣,就不能称大行皇帝了。他的意见为众臣所接受。这就是历史上“依梁仪称谥以传无穷”典故的出处。[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