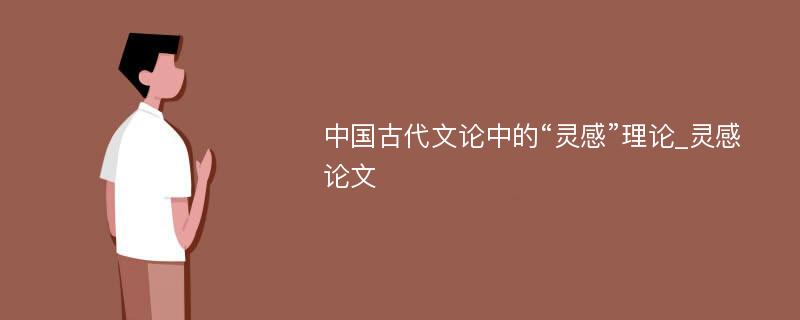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灵感”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灵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1(2000)03—0067—08
“灵感”一词在希腊原文中的意思是“神的气息”,转用到诗人或艺术家的创作上,是指感受神的灵气而代神立言。在西方,最早提出“灵感”说的是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他说:“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①对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加以发挥而作出比较系统阐说的则是柏拉图,柏拉图认为艺术创造并不是凭借技艺而要得到灵感,凭技艺,不会分出高下,凭灵感,则必定有成功和失败之别。柏拉图所说的“灵感”,实质就是艺术家受灵感动而代神说话。他在《伊安》篇中说:“诗人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话。”可见柏拉图把艺术创作活动视为神灵附体,以创作主体为媒介而直接传达神谕的活动。
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并没有“灵感”这个术语,但古代文论家对于艺术创造过程中有关作家灵感突发现象的描述及其理论阐释,则是自晋代陆机以来文学创作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古人对灵感有“感兴”、“天机”、“妙悟”等多种称谓,它们均是指作家被客观现实中某一偶然机遇触发创作冲动,突然出现文思泉诵的最佳创作状态。同西方古代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灵感”说一样,我国古代文论也十分重视作家的创作灵感,并把它视为艺术创作成功的关键,认为文艺创作不能专凭技艺,还必须要有灵感,并且每每在阐述二者的关系时将灵感放在创作条件的首要位置上。但是,我们这里所谈的中国古代的“灵感”说。是集历朝历代诸家关乎创作灵感问题的批评言论而成的。在中国古代,尚未有一个理论家对灵感问题建立起系统的学说体系,他们至多也只是在某一种批评场合,或结合作家、作品的评论,或总结作家的创作经验而旁及灵感现象,因此,他们的观点还是比较零散的、多角度的,并未形成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的探讨。同时,历来的古代文论研究也对古人论作家创作灵感的问题缺乏系统的研究,依笔者所见,专门从历代文论中抽绎并概述古代灵感说的专题研究尚未有出现过,这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灵感说的概貌,至今也未能清晰地显现在人们的面前。笔者有感于此,从所搜检的材料中,围绕着古人论灵感的本质、论灵感的特征和对灵感生成的主客体条件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略加概述,试图对古人论文艺创作灵感问题的主要观点作一个大体上的梳理。限于笔者的识见,文中不足之处尤其是所使用的材料有欠准确或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一、古人论灵感的本质
从心理机制上来讲,灵感是创造性思维过程中认识发生飞跃的心理现象,但人们大脑的创造思维,又并非无中生有地空自运作,而是对大脑意识中已有的事物进行加工改造,破除旧联系,建立新联系,形成新的创造物的运作过程。这是自近代以来逐渐发展的心理学提供给人们对灵感现象的本质的认识。然而在古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灵感现象都被蒙上了神秘的外衣,其本质属性未能得到科学的、准确的揭示。在西方,公元十二世纪以前,灵感一词的含义一直在“神性的着魔”意义上使用,是指诗人或艺术家通过某种高于他本人的媒介,吸入了神的灵气,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超凡的魅力。因此,灵感的实质就是被灵所感,诗人或艺术家有神灵凭附,就得到了神性的感动,而凭借灵感的艺术创作,就能散发出神的气息,从而给人以诗性的启悟。同古代西方的神赋灵感说一样,中国古代作家或文论家对他们每每切身感受过然而又不得其解的灵感突发现象,常常也归之于神灵的赐予。如《南史·江淹传》中“江郎才尽”的故事,曾植“感甄”而作《洛神赋》的传说,钱起夜闻空中吟诗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而作《湘灵鼓瑟》诗等等。但是这类故事传说,尚不属于自觉的理论批评,它只能反映出人们对灵感现象的朦胧的认识。用神赋灵感的说法来加以附会,是对灵感最省力而又最权威的解释,而这样的解释也正是对灵感现象无知的表现,它并不代表我国古代文论的灵感学说。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灵感说,从理论内涵来看,重在揭示心与物的关系属性,视灵感为人心之感于物的心物际会的产物,具有唯物主义的认识倾向。从阐说方式来看,古人对灵感问题的分析,一般都是结合作家、作品的评说来进行的,至多也只是属于作家的创作经验谈,因此它总是紧贴作家的创作实际,解释作家创作中文思开塞的现象,用以指导人们的写作,而不像西方的古代文论家那样把灵感问题纳入通灵观念之中并作系统的形而上的抽绎和阐发。在我国古代,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学创作中灵感问题的是西晋文论家陆机,他在《文赋》中用了较多的笔墨,细致地描述了作家创作构思中“天机骏利”的灵感袭来和“六情底滞”的文思滞涩的现象。陆机在这里所说的“天机”即指灵感而言的。“天机骏利”也就是思维敏锐、激情迸发、浮想联翩、下笔不能自己的灵感勃发状态,而陆机把这种灵感突发现象称之为“应感之会”,也就是“感物而动”、“应物斯感”的意思。
陆机的这种观点本之于先秦以来的“心物感应”说。《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淮南子·俶其训》也说:“且人之情,耳目应感动,心志知忧乐。”可见,陆机所提出的“应感之会”的灵感现象,它是心物感应的机缘,是诗人应物色之召而产生的创作感兴。陆机之后的梁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也是从心物感应的角度揭示创作灵感本质的。《文心雕龙·物色》篇专论作家创作与自然景物的关系,强调“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物感说的观点。认为作家的创作灵感和艺术情致是由色彩纷呈的客观事物所引发的,在艺术家的心灵世界与客观物质世界之间有一种物我的对应关系,因此诗人流连万象而感物联类,“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在刘勰看来,“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作家的创作运思,必得之于“江山之助”,才会富有艺术情韵。这样就从心物关系的应物斯感的角度揭示出了作家诗兴即创作灵感产生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论从心物关系角度揭示灵感现象发生的原因,表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而较少有唯心主义的玄论。但是这还不是对灵感本质的揭示,在“物感”论的认识基础上,古人还进一步指出艺术灵感尽管有其飘忽无定,倏起倏落的特点而难以被人们所把捉,但是它并非是玄奥不可解悟的神秘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它无非是作家在长期的生活积累及艺术实践中覃思经久而一朝感悟的思维飞跃现象。葛立方《韵语阳秋》中谈到必感物方有诗兴:“自古工诗者,未尝无兴也。观物而有感焉,则有兴。”诗歌创作的灵感往往是偶然产生的,但灵感偶然地产生又绝非是凭空地产生。诗人观物而有感,首先还在于他平素的日久积思,以对某一个问题的积极思维为前提,这样就形成了心理上对外界事物的有意注意,一旦遇上了相应的客观环境的激发,偶有感触,即荡文思。这正如苏轼在《书蒲永升画后》评蜀人孙知微画山水所说的那种状态:“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艺术灵感是创造性思维中认识飞跃的现象,就其表现形态而言,它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但实际上,这种偶然性之中却包含着必然性,它是建立在艺术家长期不懈的艰苦探索基础上的思维突进,因此它才常常发生在有意思维过程中的间歇阶段。唐代的皎然在《诗式》中指出只有经过艰苦的艺术构思,才有可能“坐致天机”,这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认为“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皎然在此把“先积精思”和“意静神王”的关系解释得十分清楚,不仅说明灵感与平日的积思有同方位的指向,而且也说明灵感是平日积思的质的飞跃。灵感具有偶然性的特征,它突发于触物感怀之际,但就创作主体内在因素来说,作家内心必先有所怀而后才能触物生感,所以古人指出:“深思之久,方能于无思无虑中忽然撞著。”(《宋元学案》卷十五黄百家按语)“深思”就是作家胸中有所怀,它是灵感产生的内在前提条件,倘若没有作家萦绕脑际的悬想,没有对特定目标的执意追寻和深邃的思索,那么,再有纷杂的物色相召引,也不会撞击出思想的火光。宋人吕本中对此作了譬喻性的说明。他说:“悟人之理,正在功夫勤惰间。”吕本中所称的“悟人”,即指洞悉奥妙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与灵感同义。这是强调作家必须积学以储宝,富有艺术实践的积累,这样有储于中才能易感于外。吕本中举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顿悟草书笔法的事例来说明这一原理:“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如张者,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故能遇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观剑,有何干涉?”(《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吕本中的这段话里包含着关于灵感本质属性的两个要素。其一,创作灵感把艺术家带入“迷狂”状态,它似乎失去了理智而受下意识的支配,但是它并非真的迷狂。也就是说,灵感并不是无意识活动,而是有意识的思维活动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思维状态。灵感的这种“迷狂”状态不仅表现为灵感爆发后的如醉如痴的强烈冲动,其实在此之前,它还表现为艺术家对确定的创作目标长时间地沉溺其中、执迷不悟的苦苦思考。如张旭于草书笔法的营求,已达到“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的程度。倘若没有这种专注的思考,那么公孙大娘的剑舞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他顿悟笔法的契机。其二,从艺术活动的创作构思来看,灵感并不是创作的起点,而只是这一思维流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状态,它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思维成果基础之上,是这一思维活动成熟的标志。
我国古代的“灵感”说,不仅指出了创作灵感是在作家学识积累和创作体验的基础之上,历经长期思考而一朝文思开塞的现象。同时还指出:灵感只不过是思维过程中闪现出来的思想火花,它飘忽而来而又可能转瞬即逝,它可以照亮人们的思维路向,却不能代替创作构思本身。灵感虽然具有新异性、独创性的特点,但它还需要进一步地作学理性的思考和技巧性的锤炼,这样才能创造出艺术精品。如果仅靠抓取灵感来写作,则又势必流于笔轻手滑,轻率浮泛。清人陆桴亭说:“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燃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不灭。故悟亦必继之以躬行力学”。(《思辨录辑要》)同吕本中相比,陆桴亭不仅指出灵感是学业积累和艺术实践的升华,它来自作家的勤奋学习和实践。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获致灵感之后还要“继之以躬行力学”,认为这是与灵感同一路向的思维延伸。这就是要求作家要以深刻的理性思考来坐实灵感思维所闪现的思维灵光,修正灵感中的某些偏颇,也就是强调艺术创作的锤炼之功。很明显,陆桴亭是把灵感作为创造思维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来看待的,在灵感出现之前,它需要深厚的功夫积累,这样才能像石中取火那样必有坚硬的质地,才能敲击出火花来;而灵感出现之后,作家还需要冷静地思考和精心地研磨,这样才能把灵感之光所照亮了的思维内容完善地表现出来。陆桴亭的这种看法是深得创作三昧的经验之谈,我国古代许多作家的创作实践,便直接说明了这个问题。如唐代诗人李贺锦囊盛诗,而创造出一首首精美的作品来。这样的创作过程正如陆桴亭所揭示的那样,灵感于其中只是起到一种催发的作用,它既非创作的起点,也不能独立完成艺术构思。对此,清人许印芳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灵感在创作中总是形诸挥洒淋漓的意兴,灵感袭来后,作家“兴酣落笔,如黄白合冶,大气鼓铸”,待到成篇之后,则还要费以“细检瑕疵”的“熔炼之功”:“平者易之以拗峭,板者易之以灵活,繁者易之以简约,疏者易之以缜密,哑者易之以铿锵,露者易之以浑融。”(《与李生论诗书》)许氏的这番话是从创作后期的文章修改方面着眼来谈它对创作构思的深化作用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就谈到作家临文之际“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总感到才气倍盛,然而“暨乎篇成”,则又’半折心始”,文章效果还不曾达到预想的一半。刘勰解释说这是因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就是说作家在创作灵感的催发下,创作构思极度活跃,但是作家的语言表达却总是难以详尽达意的,这就需要在不断研磨、反复锤炼的文章修改的过程中来深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并丰富作家的艺术构思。即便是下笔千言而辩才无碍的天才,也不可能总是落笔便好,因此古人早就作出这样的写作箴言:“文字频改,工夫自出。”(吕木中《吕氏童蒙训》)我国古代文论家的这些论述,把作家的灵感定位在创作过程的起始阶段,认为它以创作主体的实践积累为基础,又需要以躬行力学的创作实践对它加以延伸和定型,从而对灵感的本质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这样,对灵感现象的本质,已经揭明它是建立在实践积累基础上的创造性思维的质的飞跃。
二、古人论灵感的特征
作家的创作灵感是心灵睿智的显现。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状态,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突发性、迷狂性和形象独创性这三个方面上。灵感现象的这些形态特征,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也都早有揭示,而这些揭示,大多都是结合作家的创作体验所作出的形象性的描述。
首先,谈灵感的暂迅性。灵感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在于它不受创作主体意识的控制和支配,从表现形态上显现出无意识性。这正如别林斯基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作家对灵感“只能听命于它,因为它包含在他里面,但却不受他的支配。”作家对于灵感,只能静心地等待,“却不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②创作灵感的这种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它在作家还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降临,即所谓“来不可遇”;另一方面它往往又在作家尚未及经意的情况下悄然离去,即所谓“去不可止”。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勒惠思二僧》一诗中有句云:“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说的就是创作灵感的突发而易逝的特点。这也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一个灵感不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两次,而同一个灵感更不会在两个人身上同时发生。灵感的暂迅性特点,其原因即在于灵感思维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中运行的,它不受主观意志的支配,是一种潜思维,是由于人脑中一部分潜藏的信息突然受到外界触发而被沟通,建立起新的神经联系,因此就出现了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的灵感突发的现象。又由于灵感思维是在潜意识中运行的,主体的意识对它不能把握和控制,因此作家常常会出现“疑此江头有佳句,为君寻取却茫然。”(唐庚《春日郊外》)的灵感顿失的现象。古人对灵感,虽然不能从心理机制上作出科学的阐释,但是他们对灵感暂迅性特征的描述则无疑是准确的,指出“诗在境会之偶谐,即作者亦不自知,先一刻迎之不来,后一刻追之已逝。”(许学夷《诗学辨体》)明代谢榛则称诗之“天机”须“待时而发”,就是说灵感需要作家受到外物的感召之后“触物而成”,它绝非“幽寻苦索”的人力所能为。至于那些“属对精确”的妙句,自有作家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力为底蕴,但它们常常是“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四溟诗话》)这正是对艺术灵感不期骤得的非自控性的准确说明。
其次,谈灵感的迷狂性。灵感通常出现在高度紧张的思维过程中的间歇阶段,它往往伴随着强烈的精神亢奋而进入创作的迷狂。此时,作家的意识似乎不再受理智的支配,任凭“下意识”的推动,奇思妙想,奔涌而来;惊人妙语,不招而至,其才智似乎超出了平时能力的极限。这就是绝大多数作家都曾亲身经历过的创作迷狂。据载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在写作《上林赋》、《子虚赋》时,就出现过“意思萧散”,“忽焉如睡,焕然而兴”的精神状态。而现代诗人郭沫若在写作《地球,我的母亲》之时,就曾赤着双足,率性地倒在路上,“直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③受到这种诗情的鼓荡,他便快捷地完成了该诗的创作。
作家在灵感袭来后所处的迷狂状态,有如清人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中所描述的那样:“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这首论诗诗揭示出诗人的创作迷狂的主要特征是强烈的感情冲动和意外的惊奇感,对创作对象深度痴迷和脑海中奔涌着各种形象乃至幻象。陆机的《文赋》谈及作家在“文思开塞”之后所处的思维状态说:“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藏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以盈耳。”这就是作家在物我感应的机缘下,灵感袭来,创作冲动勃发的情状。此时作家感情像潮水一样涌至,眼前万象竟萌,视通万里,耳边充溢着清越动听的乐音,全身心地沉浸在他所追逐的艺术情境之中,这就是伴随着情感冲动的创作迷狂状态。明人谭元春《汪子戊己诗序》说:“夫作诗者一情独往,万象俱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即手口原听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测,即胸中原听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强,而“因以候于造化之毫厘,而或相遇于风水之来去。”这段话不仅指出灵感袭来时,诗人进入了“口忽然吟,手忽然书”的不能自己、诗兴勃发的状态,而且还指明了诗人的这种创作迷狂是“一情独往”之所致。在这种状态下,诗人的手口之所动,听凭’胸中之所流”,而诗人心胸涌动的情感又得之于风水相遭之际,与自然造化相侔。谭元春的这段评论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诗人的创作迷狂,乃是作者专注于特定对象而出现的高度兴奋而忘却自我的精神状态,最终进入了移我情于外物、物我合一的境界。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古代文论所讲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其中就包含着作家的创作迷狂状态在内。庄子的“至乐无乐”是一个哲学命题,其核心是强调清静无为、无知无欲,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与“道”合一的境界,它与庄子的文艺美学思想是相通的,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意境”理论。“意境”的基本构成在于情景交融,它包含着客观的生活形象和作家的主观精神态度这“二原质”,无论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都是主客观相融合的产物。意境的创造,往往也就是在作家融情入景的迷狂状态中完成的,其最高境界,也就是泯除了物我界限,超越了世俗尘想,诗人自我完全沉浸于外物之中而与物合一,即如王国维所说的“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12]
其三,谈灵感的形象独创性。灵感是人类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它一般出现在创造实践过程中创造性和效力最高的一顷刻,所以,独创性是灵感思维的最基本的属性。文艺创作活动需要运用形象思维,因而在艺术创造过程中所产生的灵感,总会伴随着鲜明而独特的艺术形象,形象独创性是艺术灵感的最鲜明的特征。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常常用“神化”、“妙悟”、“灵眼’、“灵手”等概念来说明灵感的独创性。如《西京杂记》记载扬雄评司马相如的赋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金圣叹评《西厢记》时说:“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被灵眼捉住。”这些都是指灵感的独创性特征而言的。
古人论灵感的形象独创性特征的言论,一般都是与创作技巧、规程相比照而提出来的,因此它常常与艺术理论中强调神似,反对形似,主张天然化成,反对人工雕琢的观点相关联。唐代李德裕《文章论》说文章“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他在所作《文箴》中也说:“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淡而无味。琢刻藻绘,弥不足贵。如彼璞玉,磨砻成器,奢者为之,错以金翠,美质既雕,良宝斯弃”。这里就把“惚恍而来”的“自然灵气”即具有独创性的灵感同“杼轴得之”的轧轧抽思相对比,认为文章写作应该摒弃模写古人和雕饰藻绘的作法,而要熔铸新意,如亘古恒悬的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并把它视作“为文之大旨”,体现了论者反对模拟形迹,提倡独创出新的文学发展观。明代的剧作家汤显祖承续李德裕的观点,对此阐述得更为明确。他说:“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常物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形象宛然。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证圣。”(《合奇序》)汤显祖观点与李德裕同旨,但他对灵感独创性的揭示,是从突破技艺常规而追寻意趣神色的创作主张中引伸出来的。汤显祖的戏剧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强调作者一任性情所发,超轶格调之外,为了充分表达剧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不受曲律的束缚。在这样的理论主张之下,必然重视作家的灵气,注重抒发性情而反对按字模声和步趋形似的因袭风气。其实不仅在汤显祖是这样,在文学批评理论上,凡是主张师心自用,独抒性灵一类观点的人,都必然注重性情与灵机的有机融合,强调任性而发,师法自然而音合天籁。这样的理论主张里面也必然包含着与灵感说相通的理论内容,如明代李贽、三袁及清代袁牧的文学理论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作家的创作灵感问题。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是针对复古派而提出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学主张。然而他们所提倡的“性灵”,其实质也就是一种即景生情的抒发,是情境偶触荡起的文思。用江盈科的话来解释,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敝箧集序》)江盈科的解释可谓探得了性灵的本质。
三、古人论灵感生成的条件
我国古代文论在对灵感的本质作以揭示和对灵感的特征作以描述的同时,对灵感产生及如何培养并获致灵感的条件也作出了较深刻的阐发。古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古人论灵感现象,指出作家必须备有生活实践、艺术实践和学识的积累,才有可能触物生感,爆发出思想的火花。这是从创作主体的主观内在因素方面找出的灵感生成的原因。如前所述,我国古代文论对灵感本质的揭示,基于具有唯物倾向的认识之上,以人心之感于物为天机触发的契点,把灵感视为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受阻而又一朝解悟的思维飞跃现象,因而就必然把作家平素蓄积的生活体验和学识经验作为灵感生成的先决条件,用古人的话来说,这就叫做“有诸中”。古人对灵感与创作主体实践积累关系的揭示,早在先秦时期的庄子那里已萌其蘖。庄子论艺所提出的技艺神化说,注重完全天然的艺术而反对人为造作的艺术,他所讲的一系列寓言故事如疱丁解牛,轮扁斫轮,梓庆削木为鐻等,都贯穿着这样的思想。然而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技艺效果呢?庄子认为要使人们虚静、坐忘以致“物化”的境界,才能“以天合天”,即主客体物我为一,这样的创作自然就和天工造化相一致了。庄子的这种学说,看似神秘玄奥,同时又带有排斥人们的能动认识和实践的意味,但是,它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神化的技艺来自于实践活动的积累,也就是主体驾驭客体的能力在反复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演进而终臻神妙。如“佝偻承蜩”故事中的累丸致巧,“吕梁丈夫蹈水”故事中的日与水没,都讲出了神化技能出于实践练习的道理。庄子的技艺神化说并不是针对文艺创作而言的,而技艺的神化也并不指灵感现象,但是它所阐发的道理则与文艺创作中作家灵感突发现象的原理相通。神化技艺本是一种实际操作能力,而不是一种思维状态,它一经形成便具有恒定性,也不像灵感那样的不可重复。但它与灵感的相通之处主要在于,它们都以实践活动的积累为生成的前提,就其本质属性而言,它们也都是人们实践活动的质的提升和飞跃。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认为庄子的技艺神化说,包含着对创作灵感的本质和产生根源的认识。后世的古代文论家对灵感本质的揭示,更明确地从它的实践属性方面,阐明它与实践积累的关系,这样,就正确地抓住了灵感现象“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本质属性,其实也就正确地指出了灵感产生的前提条件在于作家平素的内在积累。
作为作家创作灵感产生条件的内在积累,不仅包括他的艺术实践活动,而且还包括他的生活实践的积累。因此古人论灵感,还指出了灵感现象之所以能在某一个作家身上发生,从内在生成因素方面来分析,它与该作家的个体生活史也有极密切的联系。因为人们的生活经历不同,所形成的生活积累,也就会影响他对客观事物的情感反应,同样作为信息源的外界事物,对于有不同生活经历的人来说,所能唤起的感受是不同的,因而发生在触物之际的创作灵感,并不是飘忽无根的不可测度的现象,而是作家所经历的客观生活以主观情感的方式在某种契机引发下的灵光闪现。对此,清人魏禧《宗子发文集序》中的一段阐述说的十分清楚。他指出“人生平耳目所见闻,身所经历,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虽市侩优倡大猾逆贼之情状,灶婢丐夫米盐凌杂鄙亵之故,必留深思而叹识之,酝酿蓄积,沈浸不轻发。及其有故临文,则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地之不可御。”这里所谈的就是作家的生活积累有如江河之水之蓄势待发,一旦临文,即触类生情,形成滂沛无滞的文思。我国古代诗话中曾记载不少“一字师”的故事。所谓“一字师”常常并不能以一字说明学问的高下,而取决于为师者的生活积累。如据载初唐诗人宋之问一次在杭州踏着月光游览灵隐寺,面对银光笼罩下的寺中殿阁和鹫岭偶发诗兴,不禁吟道:“鹫岭郁苕荛,龙宫隐寂寥。”然接下来便难以为继,虽苦吟良久也未得佳句。这时走过来一老僧为他续作两句:“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这两句诗把灵隐寺开阔的远景一下子给鲜明地展示出来,显得气象非凡,确为诗中警拔之句。然而我们能看出,这两句写的是灵隐寺的远景,而不是诗人的眼前景。宋之问夜游灵隐寺,此时既看不到沧海日出的景象,也没有依门倾听江潮的生活体验,所以他纵使才高八斗也作不出这样的诗句,而寺中的老僧平素有这样的生活积累,才能脱口吟出如许佳联。
古人在论述灵感生成的主观条件时,还十分注重作家的学养对灵感的先决作用,清人袁守定借用韩愈的话把这称作“有诸中”。他在《占笔丛谈》中说:“文章之道,遭际兴会,抒发性灵,生于临文之顷也。然须平日餐经馈史,霍然有怀,对景感物,旷然有会,尝有欲吐之言,难遏之意,然后拈题泚笔,忽忽相遭,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这段话是从作家平素的学识积累的角度来说明灵感产生的前提条件的。袁守定以“探珠于渊”、“采玉于山”为喻,说明诗人的创作灵感终归是诗人内在积学蕴思的光华闪现。
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其自身的自然生理条件也是制约灵感生成的重要因素,相对于主观精神条件而言,我们可以称它为主体物质条件。古人认识到,作家的创作状态与他的身心状态是相关联的,而作家创作灵感的出现,在作家身心状况方面而言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寻找如何调适身心状态以利灵感闪现的规律,便是文论家所毕力以求的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求,最早可以溯源至庄子的“虚静”说。致虚静、守敬笃,是庄子所强调的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它要求人们“心斋”、“坐忘”,废止人的官能知觉而进入到无知无欲的空明状态,以虚静的状态来排除世俗尘杂的干扰,这样才能对至道进行观照,从而进入“大明”的境界。庄子把虚心静默地体悟宇宙万物的本质和规律作为认识客观外在事物的途径,使主体与自然相融为一,这样也就能够保持涵虚待物、专一而静的状态,有利于洞鉴事理、探赜发微。庄子的“虚静”说不是针对艺术创作提出的,但其原理则与艺术创作对作家摒除尘俗之想,专心凝虑在审美境界中展开想象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作家创作伊始的沉思虚静的状态何以有利于驰骋神思、捕获灵感泥?这个问题在梁代文论家刘勰那里,从原理上给予了相当科学的解释。刘勰认为,作家写作应当依循志意,顺乎自然,做到“率志委和”,以使作家的文思“理融而情畅。”相反,如果一味地搜索枯肠而“钻砺过分”,则就会“神疲而气衰”,导致文思艰涩、窒碍难通。刘勰把作家“率志委和”和“竭情殚虑”两种精神状态视为创作成败的先决条件,认为它们劳逸程度是悬差万里,所产生的效果也就有天壤之别。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刘勰指出其原因即在于一个人的“器分有限”。这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才分总会有偏长和限度,而精神活动的范围却是没有边际的。作家如果以有限的智力去强求超乎才分的文辞之美,这就如同庄子所说的有“以有涯随无涯”的困窘,势必会使自己“精气内销”而“神志外伤”。
刘勰的“养气”说,从人的生理条件着眼,说明作家保持心气平和、神清气爽的状态,文思才不会壅滞。他论养气旨在探求如何调适身心状态,从而在主体方面创造文思条畅的条件,这实际上也就是创作灵感产生所需要的主体物质条件。刘勰的“养气”说同庄子的“虚静”说有内在的关系,而且同《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提法相表里,都是为了打通郁结的文思枢纽而要求保持内心虚涵澄彻的状态。但刘勰所强调的“养气”,并不侧重在静穆罄澄的虚心照物上,而主要强调作家要依循自身的生理规律,清和其心,条畅其气,培护一种旺盛的创作意兴。为此,作家不仅仅要孤身静默地去玄览或畅想,更主要的是要在生活中创造各种“逍遥”和“谈笑”的环境氛围,在这样的情境中,作家的创作意绪才能舒卷自如,创作灵感也才会频频闪现。刘勰认为这种在生活中逍遥情志、得意舒怀的调适身心,同胎息养生之术一样,都是养气的一种方法。作家的创作只有在意气高扬的情绪状态下,文思才不会受阻,这就为创作灵感的出现打开了通路,也就是说为灵感的产生创设了自然条件。
如前所述,古人对灵感本质持有唯物倾向的理解,因而他们对灵感现象发生的前提条件的认识,也从心物契合的关系着眼,指明客观事物的感发作用是灵感生成的客观外在诱因,它不仅包括作家受自然景物的感召而触物生感,而且也包括作家面对各种社会生活情景而感事生怀。这样,古人就从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对作家心灵感发的角度,揭示出了灵感产生的客观外在条件。从理论上来阐述这一原理的,当以钟嵘的《诗品序》为全面而又明确。钟嵘一方面指出“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的四季景致,会感动诗人,生发诗情。另一方面,钟嵘更注重各种社会生活情境所感发的怨情对诗人创作欲望的催动作用,如“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魂逐飞蓬”等,它们以各种生活情状“感荡心灵”,滋生灵感,形成诗人创作的内在动因。但概括地说,作家不管是面对自然物色还是生活情景,创作灵感的引发,总要有一个主客观相融汇的契合点,那么,这个契合点也就是灵感产生的适时机缘,它所包藏的客观外在诱因即客观景物或生活情景在这里就成为灵感突发的主导因素了。
总之,灵感现象是创作主体与客观外物机境偶触的产物,这是就其爆发的契点而言的。作为灵感产生的条件,也必须具备主客体双重因素的原因,古人论灵感生成的条件,从主体因素方面指出了主观精神因素和主体物质因素共同构成灵感生成的内在条件,而自然景物的物色相召和社会生活的感荡心灵,则是激发创作灵感的外在条件,它作用于作家的耳目,调适作家的心境,焕发出作家高昂的创作情绪,从而为灵感的生成铺设了通途。古人的这种认识已形诸明确的理论阐述,这说明我国古代文论中的灵感说,不仅对神秘的灵感现象作描述性的揭示,而且能进一步从它的生成原理上作出了具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的说明,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文论的灵感说,虽然阐说方式尚嫌零散而欠系统性,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理论深度,已届科学认识的水平。
[收稿日期]1999—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