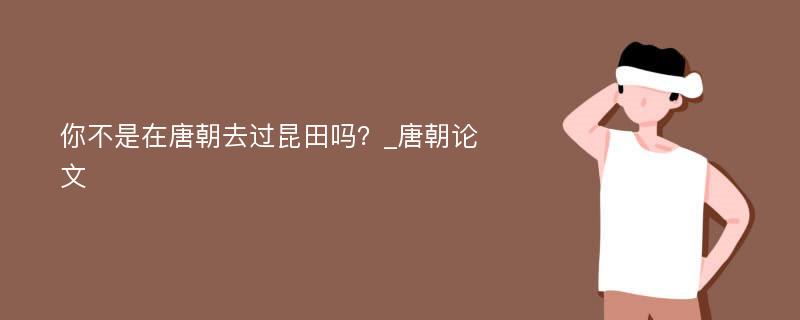
唐代未行均田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田论文,唐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历史上,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种非纯粹的土地国有制度。它始于北魏,历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以及隋朝,至唐代是否继续推行过这一制度呢?傅筑夫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以下简称《经济史》)中说:“唐代的均田法令根本就是一纸空文”①。这就是说,在唐代虽多次颁布过均田法令,但实际上从唐朝建立之日起,自始至终就根本没有实行过这一制度。此论笔者难以苟同,因它与唐代在实施两税法以前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
一
《经济史》的作者在该书论述北魏实行均田制时,认为是具有推行均田制的客观条件的。他说:“它(指北魏)在当时实具有推行这一制度的客观条件,因为实行计口授田的先决条件,是土地相对过剩,而北魏王朝正是建立在长期战乱和人口大量死亡之后,政府掌握了大量的无主荒田。”以此来看唐朝,笔者认为初唐不仅同样具备这一客观条件,而且其条件并不比北魏差。
先从可供均田的荒田来看。众所周知,唐朝是经过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和大规模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起来的。早在隋朝后期,由于隋炀帝“转输不息,徭役无期”,其时,“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这茂草”②。紧接着又爆发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其参加的人数之多,波及的地区之广,是唐朝以前所未有过的。所谓“十分天下,九为盗贼”,其言实不为过。凡起义军所到之处,地主阶级无不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使形成于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势力,基本上趋于崩溃。史载:山东地区,农民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③。江淮地区,农民军对隋官,“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河西地区,农民军“杀尽隋官,分其家产”④。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没落,不少田庄,“通庄并溃”⑤,因而在唐初便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田。如河南、山东一带,至贞观六年(632年),魏征还上书说:“自伊洛以东,暨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⑥。甚至直到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河南地区依然是“此间田地极宽,百姓太少。”⑦至于秦陇一带,贞观时,也是“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⑧。以此观之,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建立的唐朝,在其初期,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供唐政府实行均田制的抛荒土地,(包括熟荒地),比之没有经过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北朝和隋朝,就数量而言,无疑要多得多,此是不言而喻的。
再从授田人户的数量来看。隋朝在全盛时期,其户口总数为890余万户,4600余万口,后经隋炀帝的大兴土木,东征西战,徭役、兵役繁重,已经造成人民大量死亡、流散。以后在隋唐之际,经各地的农民起义,时间长,地区广,或战死或因无食至饥饿而死者,为数也不少。到唐初,户口因之而锐减的情况,十分明显。据《通典·食货志》记载:“大业所有八百余万户,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万户。”这就是说,在唐高祖李渊刚建立唐朝的武德年间(618-626年),户口只及隋大业中的四分之一。至太宗贞观初年,户口虽略有增加,仍不及三百万户”⑨,只及隋大业中的三分之一。直至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距唐建国已有30余年,根据户部尚书高履行奏称:“隋开皇中有八百七十万,即今现户三百八十五万”⑩,其户总数仍不及隋开皇中的一半。可见当时实行均田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荒田不足分配,而是可耕的荒田有余,垦荒的劳动力却严重不足。这除了根据上述的户口统计数字外,还可以从当时唐政府所实施的增殖人口的政策中找到答案。
贞观时(627-649年)唐政府实施的人口政策,主要有两条:“一是,赎回外流人口。由于隋末的战乱,不少内地和沿边居民,或避乱北上,或为戎狄所掠”。唐太宗为争取这部分居民尽快回乡务农,在即位后,便立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或令突厥颉利可汗“归所掠中国户口”,或“以金帛购中国人”。如贞观三年(629年),“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次年,又“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同年,“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11)总计前后被赎回的外流人口不下200万人。二是,奖励生育。早在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就下诏:“劝勉民间嫁娶”。明文规定婚龄为男二十,女十五。鳏夫寡妇凡丧期已过者,“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12)至贞观三年(629年)又规定:凡“妇人正月以来生男者,粟一石”(13),以资鼓励。同时为了督促地方官认真贯彻执行增殖人口的政策,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14)以此作为考核地方官员,决定其升降的依据。若问唐政府为什么要采取上述增殖人口的政策,那不就是为了设法解决当时荒田有余,而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实际问题吗?
既然如此,那又如何解释初唐农民受田不足的问题呢?如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幸灵口,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15),尚不及法定应受田数的三分之一。笔者认为,这只是属于京畿地区人多地少的狭乡,它和隋朝在始行均田制时的狭乡地区的情况是相似的。史载:隋文帝“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16)但这种情况,在初唐与隋初一样,就全国范围而言,并不具有普遍性。
何以见得?因当时离京畿不远的河南道就存在着“田地极宽,百姓太少”的大片宽乡。唐政府为使受田不足的京畿百姓得到土地,早在唐太宗贞观十八年便下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至宽乡”(17)。以后,在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还鼓励“移至宽乡”的农民,尽力开垦荒地,“庶尽地利”,对“占田过限”者亦不追究。此在《唐律疏议·户婚》中就有规定:“若占于宽闲之处不坐,谓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以上事例,不仅说明了初唐具备了实行均田制的前提条件,而且还证实了此时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均田之制。
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史》作者的立论,前后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肯定北魏王朝在刚建立时,实具有推行均田制度的客观条件——“在长期丧乱和人口大量死亡之后,政府掌握了大量的无主荒田”。另方面却又无视同样具备了上述条件——荒田有余而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初唐,武断其颁发的“均田法令根本就是一纸空文”。这怎么能自圆其说呢?
二
那末,唐代历史发展到中唐的“全盛时期”,是否可以认为:“因为人口早已增多,而土地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实行均田制的条件是不存在的”(18)呢?笔者的回答也是否定的。诚然,唐朝在进入“全盛时期”,其实际情况确与初唐不同。当时“人口早已增多,而土地相对不足”,也是事实。但“土地相对不足”,造成农民受田不足,不仅唐中期是如此,纵观历史上实行过均田制的朝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不存在农民受田不足的问题。有的甚至在一开始问题就很严重,如北齐在实行均田后,“肥饶之年,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19)。我们总不能以此为根据,断定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实行过均田制,把先后颁发过有300年历史的均田法令,一概视作“一纸空文”吧。
其实中唐农民之所以会造成普遍受田不足的状况,究其原因,与以前实行过均田制的朝代,大致是相同的。此乃在于:
其一,用作均田的土地,并非是所有的土地。历来实行的均田,都不是剥夺权贵豪富的私有土地,以均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而是在不触动他们原已占有的土地的前提下,来推行均田之制的,唐朝当然也不会例外。如唐臣于志宁就直言不讳地说过:“臣居关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址不坠。”(20)于志宁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的于谨之曾孙,他家自魏周以来,经隋朝到唐代,尽管朝代一再更换,但其原已占有的土地,并不因新王朝再次实行均田而受到丝毫影响。以此可见,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说的:均田制“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21)。此言是可信的。正因如此,这就决定了唐王朝可以用来推行均田的土地,主要是那些无主荒田,而并不是所有的土地,其数量相对来说,本来就是有限的。更何况每一次还授,每丁都有二十亩留作永业田。既是永业田,当然也就由国有土地转变成为私有土地了。于是可供政府用作均田的土地,必然会越来越少,农民受田不足的情况,随之就会越来越普遍。
其二,相对有限的荒田,还要留下相当一部分,用来作为国家的屯田以及供皇帝赏赐贵族勋臣之用。唐承隋制,其屯田的规模比隋代还大,既有工部屯田郎中所管的屯田,也有司农寺以及州镇所管的屯田。仅工部屯田郎中,就“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大者五十项,小者二十项。”(22)据日本学者的统计,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以前,全国军屯总数有1147屯,若每屯以50顷计算,则军屯土地就达57000余顷(23)。皇帝赏赐给贵族勋臣的土地,为数亦不少,如唐高祖一次赐给裴寂的良田就达千顷。再如,唐太宗赐给徐进的良田亦有50项。这也势必要减少用作均田的土地。
其三,均田制名曰“均田”,实际上并不均。历来给贵族官吏所受之田,大多远超过农民的受田额。按唐代均田法令的规定,其受田之制是:
农民受田,“丁男中男以一顷,老男笃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为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24)
贵州官吏受田,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100顷递降至5顷;职事官从一品到九品,受永业田60顷递降至2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旗尉、武骑尉,受永业田30顷递降至60亩(25)。此外,官员还受职分田(地租作官吏的俸禄),外官多则12顷,少则2顷,折冲府官多则6顷,少则80亩。公廨田(地租作官府的费用),多则40顷,少则1顷(26)。
这就是说,农民受田每人最多不超过一顷,其中永业田仅仅只有20亩。而贵族官吏,除职分田和分廨田不属官吏的私田外,永业田皆可传子孙,或为官吏的私田,并以官爵的高低定永业田之多寡,官爵愈高,所受的永业田也就愈多。少则60亩,是农民(丁男和中男)的3倍,多则100顷,为农民的500倍,而这些都是用相当一部分的荒田来进行分配的。
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对土地兼并的加剧(此问题下面再谈)和人口的增加,实行均田制的前提条件,自比之初唐要差多了。就人口而言,唐高祖武德时,只有200余万户,到天宝十三年(734年),增至900余万户,5200余万口,比之唐建国时增加了四倍有余。在此情况下,农民受田不足更为普遍。不仅“京畿地狭,民产殷繁,计丁给田,尚犹不足”(27),即使是地处西陲的敦煌和吐鲁番等地,农民同样是受田不足。这是均田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实行均田制的朝代都是无法避免的。
即使如此,但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根据史籍的记载,唐政府仍没有停止过实行均田之制。此可从以下史实中得到证实:
一是,根据唐代敦煌均田户籍残卷的记载:
(则天后)大足元年(701年)
户主张玄均年叁拾肆岁 上柱国子 课户见不输
母薛年陆拾贰岁 寡
弟思寂年贰拾肆岁 上柱国子
柒拾伍亩已受三十亩永业
合应受田贰顷叁拾壹亩三十五亩口分
一顷五十六亩未受
(唐玄宗)天宝六载(747年)户籍:
户主阴承光载贰拾玖岁 白丁下下户空 课户见输
婆 袁载柒拾叁岁 老寡空
敦煌郡 敦煌县 龙勒乡 都乡里 天宝六载籍
母 齐载伍拾陆岁 寡空
妻 侯载贰拾肆岁 丁妻天宝四载账右漏附空
弟 永俊载贰拾伍岁 白丁空
妹 惠日载贰拾岁 中女
肆拾玖亩已受 三十亩永业 七亩口分 二亩居住
合应受田贰顷陆拾贰亩 园宅
二顷一十三亩未受
仅据上述残卷的记载,便足以证明,不论是户主张玄均家,或是户主阴承光载家,其户籍应登记的项目,应受田的数额,以及该不该承担租税等等,无不与唐代均田法令相吻合。若是在此期间,唐朝没有再继续实行均田制,那在敦煌地区出土的文物中,怎么会有当时记载均田的户籍残卷呢?难道此是假的不成?
二是,据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年)的诏书载:“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28)如果唐朝在此期间没有再实行均田,何以还要在诏书中提及“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牵及到均田制的条文呢?
三是,其时唐王朝还通过行政手段,采取了多种措施,以维持已趋于崩溃的均田制。或将国家价括之田,分受给少地和破产流亡的客户。如开元九年(721年),唐政府将“(宇文)融检括剩田以授客户”(29),使一部分已失去土地的客户,又重新按均田法令,分得了数量不等的永业田和口分田。或移民至宽乡,垦辟国有荒地。如开元十六年(728年)十月,唐玄宗诏令:“诸州客户有情愿,属边缘利者,至彼给良沃田安置,仍给永年优复(千里外,复三年;五百里外,复二年;三百里外,复一年)”(30)。此从“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亦满”(31)的记载中来看,其时确有不少客户由狭乡徙至宽乡,通过均田分得了永业田和口分田,从而使“高山绝壑”的国有荒地,才得以大量垦辟。
史实表明,唐代不仅在初唐,而且在“全盛时期”的中唐,仍继续维持着均田制度。所不同的只是原先实行的并不彻底的均田制,至此更加不彻底罢了。但不彻底与根本就没有实行过,毕竟不是一回事,此是常识问题,无需多费笔墨。因此,以“人口早已增多,而土地相对不足”为理由,断定“中唐以前全盛时期,根本就不可能实行均田制度”的论点,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至于谈到唐代的均田法令,对土地买卖限制的放宽,“不仅由国家授与的口分田和永业田,可以用各种借口自由买卖,而且连赐田和勋官永业田亦可以自由买卖”,便认定“唐代的均田法令根本就是一纸空文”。其理由笔者以为也是不够充分的。诚然,唐代的均田法令,有关土地买卖的规定,比之以前实行过均田制的任何朝代都宽,究其原因,并不象《封建史》作者所说的那样,“这实际上是在立法时即故意网开一面,为土地自由买卖大开绿灯,这显然不是由于立法人思虑不周,留有漏洞”(32),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在推行均田制后,由于农民或多或少得到了土地,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赋役负担,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这就必然会使社会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就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加强各方面的经济联系,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土地私有化和商品化的进程,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唐政府在均田法令中,放宽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是顺应了商品经济和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规律,而决不是“在立法时故意网开一面,为土地自由买卖大开绿灯”。因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33)退一步说,即使是唐政府“故意”所为,那也不可能使均田制朝立而夕坏。因为,任何事物由发生、发展到消亡,都有一个过程,均田制当然也不会例外。关于这个问题,因限于篇幅,在此不能详述,留待另文再论。
三
唐代实行过均田制,这一历史事实,我们还可以从唐政府前后施行的两种不同的赋役制度(“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和“唯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得到佐证。
按唐朝开始时的赋役法规定:“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即二丈五尺),输绫绢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两旬,无事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34)这种赋役征课之制,是以人丁为本的,它是按人丁受田为基础的。由于田有口分、永业之别,所以每丁每年必须负担缴纳国家规定的租调(租粟二石;绢或绫、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麻三斤)和必须服力役杂徭(二十日,如无事不服役,按日三尺绢折纳)。正如陆贽所说的:“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35),就是这个意思。其所以如此,就是实行均田制给民以受田为依据的。
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地主阶级凭借着改治特权和经济实力,大肆兼并土地。他们或通过“借荒”、“置牧”的手法,把熟田说成是荒地,任意侵夺,或无视政府均田法令中,有关限制土地买卖的各种规定,违法买卖,置设庄田。史载:“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36)从而使以庄田形式出现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得以显著地发展,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除了逃亡他乡,“多去平籍,浮食闾里”(37),成为流民外,更多的则是被迫向庄田主“贷其种食,赁其田庐”(38),成了庄田主的庄客佃户。正由于地主庄田的发展,使曾经对社会经济起过进步作用的均田制度,到唐玄宗时便日益遭到破坏。如唐人杜佑所说的:“虽有此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逾汉成、哀之间”(39)。
而安史之乱,造成社会秩序大乱,则进一步加速了均田制的破坏。一方面是人民或惨遭屠杀,或四处逃亡,人丁随之大幅度减少。据统计: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有户890余万,口5200余万,到乾元三年(760年),只剩下户190余万,口1700余万。天宝十四年,唐政府课口820余万,到乾元三年,只剩下230余万。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户口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课口还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唐人李瀚说:遭安史之乱,“编版之户,三耗其二,归耕之人,百无其一。”(40)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另方面,有权势的富豪和官吏,他们乘安史之乱的混乱局面,更是肆无忌惮地掠夺农户的田地,并把死亡或逃亡农户的田宅并入自己的田庄,致使“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41)。因而在“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42)的情况下,要维持以租庸调征收赋税的旧制,已根本不可能了。
然而,赋税“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43),任何政府如果不解决赋税的征收问题,都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在此情况下,唐王朝不能不面对已发生变化了的客观实际(作为封建国家已丧失了均田的条件,原有的大量均田农户已失去土地成了庄田主的庄客佃农),以适应不可逆转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必然趋势。到唐德宗时,就不得不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放弃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改行征税“唯以资产(主要是田亩)为宗,不以人丁为本”,“其租庸杂调悉省”,分夏秋两次交纳的两税法。
其所以会如此,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个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当基础发生变化时,那末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之而变化。当产生新的基础时,那末也就会随着产生适合于新基础的新的上层建筑。在封建社会里,作为上层建筑的赋役制度,主要是由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发生变化时,就会随之产生适合于它的新的赋役制度。唐朝的赋役制度,由租庸调制演变成两税法,决不是一时的偶然现象,而是以庄田形式出现的地主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破坏了均田制的结果。我们的古人虽不可能了解后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他们从了解社会变动的过程中,也已经意识到,由均田制的租庸调制,发展到土地兼并,形成均田制破坏后的两税法,这是势所必然的事,并对其相互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论述。宋人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食货志》中说:“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亦说:“(唐)中叶以后,法制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卖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必欲复租庸调之法,必先复口分、世业之法,均天下田,使贫富等而后可;若不能均田,则两税乃不可易之法矣。”以上论述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租庸调法是以“口分、世业”的均田制为基础的,要实行租庸调法,就必须先“均天下田”,实行均田制,若“不能均田”,那就不可能复“租庸调之法”。由于“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即均田制的破坏和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于是两税法就成了“不可易之法矣。”由此可见,完全否认在唐代实行过均田制的观点,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注释:
① (18)(32)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卷,第224页。
②《隋书·杨玄感传》。
③《资治通鉴》卷183。
④《旧唐书·李轨传》。
⑤《续高僧传·释慧琏传》。
⑥《旧唐书·魏征传》。
⑦《通典·历代盛衰户口》。
⑧《旧唐书·高昌传》。
⑨《新唐书·食货志》。
⑩《唐会要·户口数杂录》。
(11)《旧唐书·太宗本纪》。
(12)(14)《全唐文·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
(13)《全唐文·赐孝义高年粟帛诏》。
(15)(17)《册府元龟·帝王部·惠民》。
(16)《隋书·食货志》。
(19)(25)《通典·田制下》。
(20)《旧唐书·于志宁传》。
(21)《文献通考·田赋考》。
(22)《旧唐书·官职志》。
(23)(日)王井是博《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512页。
(24)《唐六典·尚书户部》。
(26)《通典·职田公廨田》。
(27)《唐会要·内外官职田》。
(28)《册府元龟·田制》。
(29)《文献通考·田赋三》。
(30)《册府元龟·帝王部·务农》。
(31)《元次山集·向进士三》。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页。
(34)《唐六典》卷3。
(35)(38)《陆宣公集·均节赋税恤百姓》。
(36)《册府元龟·邦计·田制》。
(37)《新唐书·宇文献传》。
(39)《通典·食货典·田制下》。
(40)《全唐文·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
(41)《唐会要·逃户》。
(42)《旧唐书·杨炎传》。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