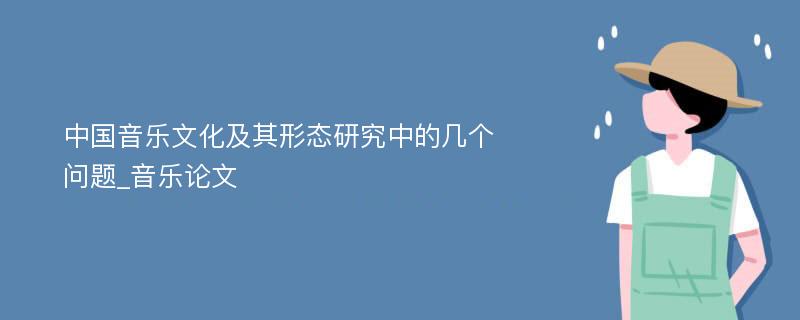
多元一体的中国音乐文化及其形态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音乐论文,形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音乐研究》2000年第一期发表了澳籍华人杨沐的《中国音乐形态理论建设与汉族中心论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杨文”),文中称中国音乐学界基本上是用“汉族音乐形态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指责“中国学者们相当一致地认为这种理论涵盖了整个中国各民族的音乐形态”,并说“虽然学者们都知道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事实,但却似乎没有人意识到上述做法的大汉族主义心态”。笔者也想对这些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众所周知,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族名,同时56个民族又有一个共同的族名,即中华民族。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经过多年研究后指出:中华民族“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注: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北京)。)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只注意各个民族的多元性,看不到它的一体性,是不全面的。
具有一体性的中华民族,在民族特征方面也有共同性。关于这一点,谷苞先生发表了两篇论文加以论述,他不仅列举了中华民族在语言、经济生活、地域方面的共同特征,还分析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许多共同文化事象,如共同的神话传说、共同的乐器、共同的节日、都崇拜龙、都用12生肖纪生年和纪年等。(注:谷苞《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上引书第37-71页。)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只研究每个民族的特性,不研究这个多元一体民族大家庭在文化方面的共性,也是不全面的。
在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民族学家们还指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汉族一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在众多民族之中,始终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注: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第58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成都)。)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目前的实际状况。研究中华民族文化,不尊重这一历史事实,不面对这一实际,不是科学的态度。
中国的音乐学家们不仅都清楚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事实,也了解它所具有的一体性,不仅关注各民族音乐的个性,也看到了它们的共性。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汉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汉族音乐对其他各民族音乐产生影响的事实。也就是说,我国音乐学界和与民族学界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在对中华民族文化研究过程中,取得了共识。我相信每个懂得历史、尊重事实、正直的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音乐的时候,都会注意到我国学者经过长期研究所取得的上述共识,都会尊重我们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
也许因为我是在多民族杂居地区长大的,从小又喜欢音乐,所以很早就意识到各民族音乐的不同及其共同之处。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我开始在各民族地区采风,到80年代初,我已在北方所有民族中进行过田野工作,并对一些南方民族的民间音乐进行了调查。在对采风中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和其他材料进行比较研究时我注意到,在除俄罗斯族民间音乐之外的所有各民族民间音乐中,都采用无半音五声音阶,都广泛运用“摇声”,都采用散板这一独特的节拍形式,都以单声部为主要织体形式。把具有这些特点的民间音乐作品和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的一部分民间音乐作品加以比较,后者和我从小就学习的欧洲古典音乐在形态方面更为接近。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吉克族的大部分民间音乐作品与上述两种音乐风格又有很大不同,和伊朗、阿拉伯以及中亚一些民族的音乐在形态上相近。经过这样的比较,我在1983年写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音乐体系浅析》一文(注:杜亚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音乐体系浅析》(《中国音乐》1984年第1期)。),把中国民间音乐的形态归纳为中国、欧洲、波斯—阿拉伯三大音乐体系。“杨文”指责这篇文章“把实质上是汉族音乐形态的体系命名为‘中国体系’,将其运用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形态分析”,不符合实际情况。我是在研究中国各民族民间音乐,主要是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形态后,才提出:“中国音乐体系”这一概念的。我把汉族民间音乐置于这一体系之下,而不是凌驾于这一体系之上。“杨文”中说“中国学者们相当一致地认为这种理论涵盖了整个中国各民族的音乐形态”也不符合事实。在我的文章中除了列出“中国音乐体系”外,还把一部分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维吾尔族和锡伯族民间音乐作品归纳为“欧洲音乐体系”,指出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吉克族尚有大量属于“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的民间音乐作品。对中国民间音乐的形态采用这种三分法来归类,恰恰是为了避免用“汉族音乐形态的理论”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分析,表现出对少数民族历史、语言、传统及其音乐文化的尊重。我那篇文章是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乐教研室编写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课讲义绪论中的一节,当时参与这本讲义写作的还有王耀华、张鸿懿、李文珍、陈铭道等诸位先生,大家一致认为不能用汉族音乐取代中国音乐,我们正是为了解决以往民族音乐教学中少数民族音乐所占比重较小的问题才动手编写这本讲义的。
“杨文”中还指责把“中国汉族的古典音乐宫调理论用于维吾尔族音乐的形态分析”的做法。首先,把中国古典音乐宫调理论看成由汉族所独占,完全是错误的观点。我国古典音乐的宫调体系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不只属于汉族。别的不讲,在隋唐时代的十部乐中,只有“清商乐”是汉族音乐,而“龟兹乐”、“高昌乐”和“疏勒乐”都是维吾尔族先民的音乐,没有创作、表演这些音乐的实践,哪来的宫调理论?况且,那时中国宫调理论也不是由汉族一个民族创造的,许多少数民族音乐家参与了这一工作。当时在乐律学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苏祗婆是龟兹音乐家,他在宫调理论方面的贡献至今被维吾尔族人民和音乐家引以为荣。今天用维吾尔族的先民参与创造的中国宫调理论去分析维吾尔族的民间音乐作品,有何不可?其次,如果杨沐对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稍有了解,便可知道维吾尔族民间音乐中的许多作品在宫调关系方面的确继承了古代西域音乐的传统,为此,维吾尔族人民和音乐家也感到骄傲和自豪。杨沐指责中国音乐学家们有“大汉族主义心态”,可他连什么是“大汉族主义”也没有搞清楚。“大汉族主义”是“汉族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国内民族关系上的表现。”“在历史上的主要表现为: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限制和剥夺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平等权利”。(注:见《民族词典》第45页,陈永龄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上海)。)杨沐想要剥夺少数民族拥有中国古典宫调理论的权利,是不是有“大汉族主义”之嫌?
“杨文”中问:“根据曲调形态的相似而将其他国家的音乐也划入‘中国体系’”是不是“大汉族主义、汉族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的表现”?杨沐可能是指我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音乐体系浅析》一文中提到前苏联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少数民族、匈牙利族和其他一些民族也采用中国音乐体系的观点。这里限于篇幅,暂不讨论前苏联少数民族和其他民族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匈牙利的情况。
在历史上有不少民族从我国西迁,其终点都是地处欧亚草原西端的匈牙利平原。公元376年,从我国西迁的匈奴人到了这里,(注: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刊《匈奴史论文选集》第120-145页。林干编(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公元568年,柔然人也到了这里。(注:周伟洲《敕勒和柔然》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据历史记载,西迁的匈奴人还把他们的音乐带到了匈牙利平原,在东罗马帝国供职的希腊历史学家普利斯库斯(Priscus)在其笔记中便记录了匈奴人在匈牙利唱歌、演剧的情况。(注:冯家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刊《匈奴史论文选集》第155-170页。林干编(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20世纪初,匈牙利音乐家已经注意到该国民间音乐和中国民间音乐之间的联系,柯达依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论匈牙利民间音乐》一书中便用中国的宫调理论分析匈牙利民歌,(注:柯达依《论匈牙利民间音乐》第20页,廖乃雄、兴万生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北京)。)他还在这本著作中指出:“马扎尔族(即匈牙利族)现在是那个几千年悠久而伟大的亚洲音乐文化最边缘的支流,这种音乐文化深深地根植在他们的心灵之中,在从中国经过中亚细亚直到黑海的诸民族的心灵之中。”最先把匈牙利民间音乐和中国音乐相联系,用中国的音乐理论分析匈牙利民间音乐不是我,而是柯达依。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搞清历史,和“中国中心论”或“大汉族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如果有人指出,日本人和韩国人现在用的方块字是“汉字”而不是“日本字”和“韩国字”,也可以称为“大汉族主义”吗”
音乐形态学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之上,一般都要通过对记录下来的乐谱进行分析才能完成。“杨文”中说:“中国的‘民族音乐理论界’或‘民族音乐形态学界’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基本上是纯理论案头工作者而不是立足于田野工作的音乐研究者”,这等于否认了我国音乐学界进行音乐形态学研究的基础。他还问:“中国的音乐工作者对采录到的音响所作的记谱有多大的准确性和可信性呢?”他说:“某些实际演唱(奏)中的音高跟已知的汉族律制的音高很不相同”,“而有的记谱者则是没有听辨出音高上的不同,而认为他们跟汉族音阶中的音高是一样的”。杨沐还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资料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提出质疑,并得意地说:“除了我本人的著述以外”,好像还没有人就此进行“研讨”。按照杨沐的说法,大部分中国音乐学家不做田野工作,记录的乐谱又不准确、不可信,在此基础之上,中国音乐学界所进行的音乐形态学研究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进行科学研究的首要条件便是尊重事实。以主观想像代替客观事实,不是科学态度。如果中国音乐学界的“相当大一部分人”都不立足于“田野工作”,请问杨沐,有一百多卷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中的资料是谁搜集来的?都是由中国音乐学界中搞田野工作的“相当小一部分”人搜集的吗?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家中有多少人立足于“田野工作”,有多少人不搞田野工作,你统计过吗?如果统计过,请将数字发表出来。如果没有统计过,只凭主观想像发表议论,这是哪家的“学术规范”?又是什么人的“文风”和“文德”?
杨沐对中国音乐学家记谱的准确性和可信性提出质疑也非常不恰当。中国音乐学家是一个群体,其中有的人记谱的水平可能较高,有的人也许不太高,不能一概而论。杨沐这样提出问题,一方面表现出他对中国音乐学家这一群体及其学术成果的不尊重,同时也暴露了他对记谱方面的许多问题的无知。
虽然不能只依靠乐谱进行音乐形态学的分析和研究,但它毕竟是进行此种研究的重要材料。我们知道,乐谱是人们用来记录音乐和符号,既然是符号,它就不是、也不可能是音乐本身。人们在用不同的记谱法记述音乐时,不必要、也不可能记下音乐中的一切,总是要略去次要的东西、记下主要的东西。这里就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什么东西是应当记录的?什么东西是应当略去的?对此,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类型的音乐,也会有它所强调的不同方面。如减字谱只记弹奏手法,不记音高和节奏;央移谱只记音高和节奏,不记音色;锣鼓经只记总体效果,不记个别乐器的如何演奏,等等。从减字谱的观点来看,五线谱的准确度和可信性就不高,从反过来也一样。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文化中的记谱标准来要求另一种文化中不同乐谱的准确度和可信性?
用一种谱式记录一种音乐文化中的音乐作品,哪些方面应详尽,哪些方面应忽略,也要根据其研究目的来决定。如巴托克在用五线谱记录匈牙利民歌时,常常为了研究其特征,首先极为详尽地记录一遍,因为记得非常细致,所以不便阅读。当记完这一行后,他还要用较为简略的方法重新再记一行可供阅读的乐谱。巴托克常把这两种乐谱平行并列发表出来,以供不同的人参考。(注:可参看Balint Sarosi所著Folk Music-Hungarian Musical Idiom一书67页第45例(Corvina出版社,1986年,布达佩斯)。)我们能根据他记的较简略的第二行谱来批判巴托克记谱的准确度和可信性吗?显然不能!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研究者对其调研对象尚不太了解,记录可能会力求详尽,反过来,如果研究者对其调研对象已经相当熟悉,则可能会采用比较简略的记谱法。如今天匈牙利一些音乐学家记录的匈牙利民歌乐谱,往往比巴托克记录的第二行谱还要简略,他们称巴托克的第一行谱为照相式谱,第二行谱为画像式谱,他们自己记的却是只勾出轮廓的、漫画式谱。潮州音乐用的“二四谱”不在“重三六”和“活五”乐曲中写微降、微升号。如秦腔、陇剧等西北地方戏设计唱腔的作曲家,也常不把“苦音”中"si"和"fa"两声上代表微降、微升的箭头标出来。一个真正懂记谱的内行是不会对所谓“漫画式谱”的准确度和可信性提出疑问的,提出疑问的往往是不了解这种音乐、不懂记谱原则的外行人。
另外,用记谱的方法来记述音乐,要受乐谱记述可能性的限制。音乐学家现在还不能像语言学家那样拥有一种比较完善的、可以用来记录各种语言的符号——国际音标。目前我们采用五线谱和简谱记谱,并不是因为它们具有最高的准确度和可信性,而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两种记谱法,另一方面也实在是还没有找到更好办法。目前,世界上许多音乐家都在为此而努力。我相信用这两种谱式记录传统音乐的人都会感觉到记谱像是要把一只活生生的小鸟强行装进一个有固定尺寸的笼子中一样困难。这也许是近30年来,国内外民族音乐家发表的研究报告中乐谱的分量越来越少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记谱几乎是民族音乐学家介绍其采集品的唯一方法,而今天他们却可以通过唱片、盒式录音带和激光唱盘直接地诉诸听觉,无须借助乐谱。依笔者之浅见,在对中国音乐学家们所记乐谱的准确度和可信性提出疑问之前,首先应当质疑的是简谱和五线谱这两种谱式本身的准确度和可信性。
记谱总是要受人主观听觉的影响,受耳朵的敏感程度和人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也会受个人对记谱法掌握程度的影响。因此,民族音乐学家一直在设法用客观的机器代替有主观性的人来记谱。即使我们以后可以用机器记出极为准确的乐谱,由于乐谱本身的特征和局限,只凭它还不能进行音乐形态学的研究。就像不接触本人,只通过看照片便想了解一个人一样不行。因此,音乐形态学的研究一定要建立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之上,音乐学家们一定要通过采风,才能真正对他进行形态研究的对象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杨沐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中所搜集资料的可信性和准确性提出质疑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的编选工作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集成中的资料都是经过多次筛选、在层层把关后才入选的,而且每一卷都经过数次严格的审查。我们不能说因此它就十全十美,一点问题也没有了,但也绝不会像杨沐污蔑的那样连“可靠性和可信性”都成问题。杨沐讲这样的话,除看了一百多首黎族民歌外,还做过什么调查?根据“杨文”所说,这些谱例还只是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编选工作准备的材料,既不是海南省的分卷,也不是最后的定稿,更代表不了全国集成工作的水平。如果没有对全国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便发表这样那样的议论,又是根据哪家的“学术规范”?这种事其他的音乐学家大概不会去做,恐怕此种“文德”也只能归杨沐个人所有了。
另外,杨沐所用的音乐术语似有规范的必要。何谓“汉族律制”和“汉族音阶”?除了杨沐自己之外,大概没有人清楚。汉族传统音乐运用五度相生律、纯律等律制,现代音乐还运用十二平均律,这些律制许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乃至外国音乐也在运用。在汉族音乐中运用的各种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在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中也能发现。生造出此类名词除了不符合目前的“学术规范”之外,是不是也有“大汉族主义”之嫌?
“杨文”还列表对中国“民族音乐理论”或“民族音乐形态学”的主流和当代音乐人类学(其实是西方音乐人类学界)的音乐形态研究的性质进行了比较。虽然杨沐宣称比较的目的“绝不是要否定或肯定其中一者的价值、作用或必要性”,但在具体的论述中他又总是对西方的音乐人类学者使用的音乐形态分析描述方法加以肯定,对中国音乐学家的做法则加以否定。如他在表中说中国人的音乐形态分析描述“基本上应被认为是‘主位’(emic)路向且应用范围有限”,而西方人的音乐形态分析描述“基本上应被认为是‘客位’(etic)路向且应用范围较广”。还说西方“无人会用”“汉族的调式体系来解释蒙古民歌”,“或是用汉族古典宫调理论来解释十二木卡姆和维吾尔族歌舞的音乐形态,这似乎是比中国的某些民族音乐理论家在认识上略胜一筹之处”云云。
其实,"etic"和"emic"在民族学和民族音乐学中都是记述人类行为的方法,只是立足点有所不同而已。"etic"是指设定一定的基准,对所有的文化进行描述的方法;"emic"则是依据某一文化固有模式的概念进行研究的方法。因此对一种具体的文化来说,"etic"的方法一般是外来的分析者所采取的立场,是以旁观者、局外人的身份进行观察,始终坚持客体性来对待调研对象的态度。而"emic"则是力图身临其境,欲使对象主体化的态度,一般是局内人所持的立场。我想中外民族音乐学界在分析音乐形态时采用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侧重点,主要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应用范围”广与不广的问题。另外,主位和客位、局外和局内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统一、相反相成的一对概念。每一个民族音乐学家都会以某种文化为基础,他总在受自己母文化的影响,在进行音乐形态研究时,要获得纯粹“客位”的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要完全用“主位”的观点来看问题,除非自己本身就属于这种特定的音乐文化,在这种音乐文化中出生和成长,否则也不可能。由于以上原因,民族音乐学家在研究工作中总是置身于连接有“主位”和“客位”两端的线的某一个点上。至于究竟在哪一个点上,则随着研究问题的不同和主、客体关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在对某一音乐文化的形态进行研究之初,不管自己是否属于这个文化,都应采取“客位”的态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了调研对象,就可以逐步地转向“主位”的态度。但当自己对这种文化相当了解的时候,恐怕又要逐渐地转向“客位”的态度。即所谓“钻进去”、“走出来”。不“钻进去”,不了解这种文化不行;不“走出来”,不和这种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也不行。这里也没有什么“应用范围”广与不广的问题。杨沐把“主位”和“客位”对立起来,并把它们和“应用范围”相联系,说明他对这一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应当努力学习才是。
至于杨文中所说的西方学者比中国学者“略胜一筹之处”,我看倒是他们不如中国学者的地方。中国学者懂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性,了解中国音乐文化不是汉族一个民族创造的,而是中国所有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一事实,从来不把中国古典宫调理论看成是汉族一个民族独有的财富,也从来不把汉族民歌采用的调式体系看作是汉族独有的。另外,蒙古族和汉族有许多共有的民歌,如“漫瀚调”(亦称“
蒙汉调”)。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两个民族共有的调式理论对它们共同创造的民歌进行音乐形态的分析呢?
杨沐借批判“汉族中心论”和“大汉族主义”为名,处处以执学柄者自居,对中国音乐学家和他们所进行的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研究肆意指责,而他所依据的据称是所谓“当代音乐人类学总体思想”。从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不要说“当代音乐人类学总体思想”,对民族音乐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他自己还处在一知半解的阶段。杨沐口口声声宣称的所谓“当代音乐人类学总体思想”,不过是他用来为其“霸道”行径所做的幌子罢了。
对多元一体的中国音乐文化及其形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界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相信经过努力,我们一定能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我们欢迎外国同行参与这项工作,也希望他们对我们的研究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宝贵的意见。然而,我们也希望外国学者能尊重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成绩,我们并不需要从外国请回什么人来当文宗。
笔者认为,在对中国音乐文化及其形态的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须要牢记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只注意各个民族的多元性,看不到它的一体性是不够的。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更多注意了各个民族的多元性,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似应加强对其一体性的研究。这不是“汉族中心论”,更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恰恰相反,这种研究正是为了肯定各少数民族对中国音乐文化的贡献,从而也是对“大汉族主义”最有力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