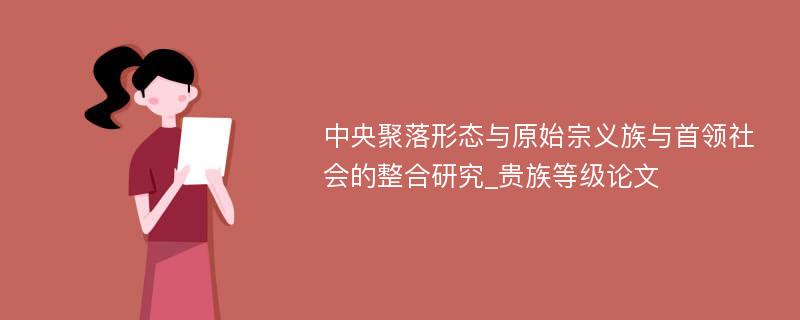
中心聚落形态、原始宗邑与酋邦社会的整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聚落论文,形态论文,原始论文,社会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4)04-0005-10 “中心聚落”“酋邦”和“原始宗邑”是笔者用来描述中国上古时代由原始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阶段所使用的三个概念。对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长处与不足,笔者也曾进行过一些分析[1]6-7,167-173,并提出“以聚落形态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通过整合可以达到“互补互益”[1]7的效应。但是,如何把这种整合体现于具体的研究之中,又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密切相关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梳理一下中心聚落,原始宗邑和酋邦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对中心聚落、原始宗邑和酋邦社会之间共性与个性的分析概括,进行整合方面的尝试。 一、宗邑、原始宗邑及其与中心聚落和酋邦的关系 所谓中心聚落,就是在具有亲缘关系的聚落群中出现一个权力相对集中、有能力统辖其他聚落、集中了贵族阶层或者高级手工业生产者的聚落。这里所说的中心聚落是从聚落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提出的一个一般性概念。由于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总是具体的,并时时展现出自己的个性特色,为此,笔者曾联系我国商周时期的历史特点把中国史前社会的中心聚落称之为原始宗邑[1]125,133-137,140-154。也就是说,原始宗邑是笔者把周代的宗邑概念引申到史前社会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或者说原始宗邑是中心聚落形态在中国史前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 周代的宗邑即宗庙所在之邑。《左传·哀公十四年》曰:“魋(桓魋)先谋公,请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杜预注:“宗庙所在。”这是说宋国的桓魋先欲图谋宋公,请求用鞌邑交换薄邑。宋公断然拒绝,杜预注说它是“宗庙所在”地。可见宗邑的标志之一即宗庙所在地。在春秋时期,对于有先君宗庙之邑又名为“都”。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在讲到卿大夫普通的邑与都的区别时曾明确地说:“凡邑有先君宗庙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 周代宗邑的另一特征在于它乃宗族宗主权力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是宗族统治的基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曰:“崔,宗邑也,必在宗族。”这是说崔地乃齐国崔杼一族的宗邑,因此一定要掌握在宗主手中。这是宗邑的又一特点,即宗邑是与宗族及其宗主联系在一起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骊姬使人对晋献公说:“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埸无主,则启戎心。”这一记载也见于《国语·晋语一》。曲沃为晋桓叔之封地,桓叔是晋献公之始祖,其封地曲沃是晋宗庙所在,故为宗邑;宗邑必有宗主。在采集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战国时期秦的《宗邑瓦书》,为陶制,其刻铭有“子子孙孙以为宗邑”。对于宗主来说,若能世世代代保持宗邑,就会使得自己的后裔既能一直以本族社稷宗庙的代理人自居,又可长期获得宗邑的收入,使得宗族统治有一个世袭稳定的基础。 周文化传统中的宗邑并非始自周代。《诗经·大雅·公刘》在描写周人祖先公刘带领族人由邰迁徙到豳地后举行宴饮时曾写道:“食之饮之,君之宗之。”这里的“君之宗之”,毛传曰:“为之君,为之大宗也。”朱熹《诗经集传》解释说:“宗,尊也;主也;嫡子孙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为主也……以饮食劳其群臣而又为之君为之宗焉。”因此,“君之宗之”说的是君统与宗统的统一,也就是说,在公刘时代,周人就出现了最高酋长与大宗宗主合一的组织结构。“宗之”是从宗法和族长的角度,统一在宗族和宗主的旗帜下;“君之”是从部族和聚落群的社会权力的角度,统一在最高酋长及其中心聚落的周围。这是当时宗族组织及其权力关系的反映。有趣的是,《诗经·大雅·公刘》第四节文字所描写的那种盛大而有秩序的宴会场面,完全可以与人类学著作中经常提到的酋邦酋长们所举行的盛大宴会相比拟,它体现了财富的相对集中,也是酋长及其家族对其所占据的社会地位的炫耀,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分层和权力相对集中的情景[2]254-264。既然周人的宗族组织以及宗权与君权的合一可以上溯到周族史前社会的中心聚落形态或酋邦阶段,那么周代宗邑的原始形态难道不就是史前社会的中心聚落或人类学上的酋邦吗?为此,从宗邑入手引申出原始宗邑这一概念,当然就有了文献和逻辑的依据,原始宗邑是中国史前社会中心聚落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这样的命题,显然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二、中心聚落、原始宗邑与酋邦社会的共性特征 如果我们将中心聚落、酋邦与原始宗邑加以对比,可以看到许多共同之处。 第一,三者在外在特征和内在功能上是一致的。例如,最早提出酋邦这一概念的美国人类学家卡莱尔沃·奥博格(Kalervo Oberg)就将酋邦定义为:在一个地域中由多村落组成的部落单位,由一名最高酋长统辖,在他的掌控之下是由次一级酋长所掌管的区域和村落[3]78-80。对酋邦理论有所发展、并提出“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概念的美国考古学家厄尔(Timothy K.Earle)也认为:酋邦最好被定义为一种区域性组织起来的社会,社会结构由一个酋长集中控制的等级制构成,它具有一种集中的决策机制以协调一批聚落社群的活动[3]146。我们知道,史前社会中心聚落的外在特征就是在一个聚落群或一组聚落中处于统领地位的大型聚落。所以,一般而言,中心聚落的规模面积要远大于其他普通聚落,而其内在特征则是它在聚落群中所具有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中心地位与作用,处于聚落群等级的顶端。 就聚落的规模而言,如前所述,作为中心聚落,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第四期聚落主体部分面积达50万平方米,河南灵宝西坡村遗址现存面积约40万平方米,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约50万平方米,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50多万平方米,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80多万平方米,安徽含山凌家滩约160万平方米。聚落的规模大,在聚落群中统领着其周围从属于或半从属于它的其他普通聚落,在聚落等级中处于较高的地位,这些也都是周代宗邑的基本属性,当然也是原始宗邑所应具备的。 中心聚落的内在特征表现为聚落功能的几个集中性,即宗教祭祀功能、管理协调功能和军事调度功能的集中,亦即所谓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中心地位与作用。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殿堂及其广场,以及湖南澧县城头山、河南郑州西山等中心聚落时期的城邑,就强烈地表现出管理协调、军事防御与指挥以及宗教祭祀等方面的中心地位的功能;红山文化中牛河梁的女神庙、积石冢、祭坛以及东山嘴祭地(社神)的祭坛和祭天的祭坛遗址,则把这种宗教祭祀中心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宗教祭祀文化的圣地;安徽含山凌家滩墓地、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以及这一时期其他遗址的墓地中,那些非常富有的贵族大墓所表现出的集军事与宗教于一身的特质,同样也强有力地说明中心聚落所具有的政治、军事、宗教诸多方面的集中性和中心地位。前文已讲到,宗邑一方面是宗庙所在地即宗教祭祀的中心,另一方面也是宗主权力的基础,是宗族政治和宗教祭祀的中心。因此,无论是外在特征和内在功能,中心聚落、酋邦与原始宗邑都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中心聚落、酋邦与原始宗邑中共同的权力特征主要是神权政治,也有的表现为神权与军权并重,可视为古代中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前身和雏形。 在中心聚落诸项集中性的功能中,宗教祭祀的中心是突出的,而且对于史前社会来讲,这种宗教祭祀的功能就是政治功能。甘肃秦安大地湾第四期聚落中901号多间式的大房子,前有辉煌的殿堂(主室),后有居室(后室),左右各有厢房(东、西侧室),在房前还有一个广场,广场上,距前堂4米左右,立有两排柱子,柱子前面有一排青石板。其殿堂,从行政角度讲,是当时酋长首领们集会议事、布政之地;从宗教祭祀角度论,又是人们举行宗教祭祀活动的中心庙堂。房前的两排柱子,可能是代表各氏族部落的图腾柱,也可能是悬挂各宗系旌旗的立柱,而两排柱子前面的那排青石,则可能是贡献牺牲的祭台。至于以901号庙堂大室为中心而形成的广场,当然也是举行重大的集体活动时使用的神圣空间。在这里,“殿堂—族氏的旌旗立柱(或图腾柱)—广场”这一组合设施,凸显的就是一种神权政治。当然,从大地湾901号屋内出土的一套量粮食的量器和在后室发现的3件用作储存谷物的大陶瓮[4]79-80,似乎透露出该政治中心(即权力中心)是包含着对公有经济的分配权在内的。 大地湾遗址之外,在社会发展的复杂化程度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安徽蒙城尉迟寺聚落遗址,在聚落中心偏南部的18号建筑基址(F68-F71)以南和以东位置,也有一处面积约为1300平方米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处因经常举行祭祀活动或篝火晚会留下的圆形火烧遗迹,在广场边缘还出土有被发掘者称为鸟形“神器”的特殊器物,也显示出宗教祭祀是该聚落突出的政治生活。 神权政治最突出的是红山文化中宗教圣地的出现。神权政治可以说是中心聚落形态与酋邦和原始宗邑的共性,表现为规模宏大的宗教圣地却属于红山文化的个性特征。红山文化中有两处大型祭祀中心:一处是位于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群,在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40多个遗址点,其布局以女神庙为中心,北部有用石砌的墙相围的巨大平台,西南关山的地方有大型的祭坛,两侧附近分布着许许多多的积石冢,这样以女神庙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方圆50平方公里的宗教圣地;另一处是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祭祀遗址。根据我们的研究,东山嘴的方形祭坛是祭祀社神的社坛,方坛内竖立的平底尖顶的长条石头是以石为社主的“石社”[5];而方坛南部约15米处的圆坛,则是祭祀天神的祭坛[6]77。 红山文化的女神庙和积石冢相互关联,女神庙里供奉的是久远的祖先,积石冢中埋葬的是部落中刚刚死去的酋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死去的著名酋长,也会逐渐列入被崇拜的祖先行列。所以,红山文化中的女神庙和积石冢表现出浓厚的祖先崇拜观念。而喀左县东山嘴祭祀遗址呈现出的则是祭祀天地社稷的自然崇拜。 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在远离村落的地方专门营建独立的庙宇和祭坛,形成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场,这绝非一个氏族部落所能拥有。而对其宗教祭祀规模和文化所达到的高度,苏秉琦先生主张它所代表的政治实体是“古国”,“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7]130-138。在我们看来,红山文化所表现出的宗教祭祀规模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恰好是中心聚落形态或酋邦社会的神权特征,因而从凌源到喀左横跨几十公里的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等遗迹是一个部族或部落群崇拜共同祖先和祭祀天地的圣地。由于这些大型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代表着当时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具有全民性的社会功能,所以,在原始社会末期,各地方酋长正是通过对祖先崇拜和对天地社稷祭祀的主持,才使得自己已掌握的权力进一步上升和扩大,等级地位更加巩固,神权政治在这里得到极好的说明。 中心聚落中神权与军权并重,还可以安徽含山凌家滩墓葬为例。在凌家滩墓地中,1987年发掘的87M4[8]和2007年发掘的07M23[9]是两座墓葬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的贵族大墓。87M4随葬145件器物,其中有玉器103件;07M23随葬器物330件,其中有玉器200件。两座大墓主人的富有程度在整个墓地首屈一指。从墓葬的规模、随葬品的丰富和精美程度以及一些特殊器物来看,这两座墓主生前应为酋长。这两座墓相距很近,当属同一家族。由于07M23墓发现的陶器等资料有限,还不能与87M4墓进行比较,无法判定二者在时间上是否有先后,因而也无法判断两个墓主生前是前后继承关系,还是同时并存关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座大墓都随葬有用来占卜的玉龟,也都随葬大量玉钺和石钺。其中,87M4号墓不但随葬一副玉龟,而且在玉龟的背甲和腹甲之间夹有一块表示“天圆地方”和“四极八方”等宇宙观的玉版。07M23号墓则随葬1件玉龟、2件玉龟状扁圆形器。在石钺、玉钺方面,87M4随葬玉钺8件、石钺18件;07M23随葬玉钺32件、石钺44件。这两座大墓也随葬一些生产工具,表现出其对生产领域的重视。但这两座大墓主人的富贵主要在于他们都是以执掌着宗教占卜祭祀为主,也兼有军事之权的酋长之类的人物。这种最高酋长集宗教与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情形,体现的就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政治性格和权力特征。 凌家滩聚落对原始宗教的重视,并非孤立地体现于87M4和07M23两座大墓。例如在98M29墓中随葬有3件玉人,在87M1墓中随葬有3件玉人,有学者认为这些玉人是原始宗教法器,这两座墓主人是专职巫师。笔者认为这些玉人有可能表现的是祖先崇拜。从发掘报告中可以看到,每件玉人手臂上都刻着七八条臂镯纹样;而在07M23墓主人双臂位置,左右各有一组10件玉镯对称放置,是套在手臂上的臂镯,其情形与98M29和87M1墓出土的三件玉人手臂上刻的臂镯是一样的。对此,笔者推测07M23墓主人为刚死去不久的有作为的酋长,他是可列入祖先行列的重要人物;而玉人则是“高祖”或“远祖”之类的祖先形象,由此才使得07M23墓主人双臂各有一组10件玉镯与玉人双臂刻的七八条臂镯纹样高度一致。双臂上套有众多的臂镯,这大概是作为宗教领袖人物的一种装饰或身上法器的部件。如果说玉人是祖先崇拜的反映,那么凌家滩98M29号墓出土玉鹰则属于动物崇拜,再从87M4号墓出土表示“天圆地方”“四维八方”宇宙观的玉版,以及87M4和07M23两座大墓都随葬有用来占卜的玉龟和玉龟状扁圆形器等特殊器物来看,凌家滩中心聚落的原始宗教和祭祀已十分发达,其神权政治也是突出的。 在凌家滩聚落墓地中,表现出极明显的尚武风气。1987年到1998年三次发掘的44座墓中[8],随葬玉钺的墓有11座,占总墓数的25%;随葬石钺的墓有30座,占总墓数的68%;玉钺和石钺二者合起来,占总墓数的93%。11座随葬玉钺的墓共出土玉钺26件,30座随葬石钺的墓共出土石钺186件,玉钺与石钺相加,40座随葬玉钺和石钺的墓共出土玉、石钺212件。大量随葬玉钺和石钺是尚武的表现,在这样的风气中,87M6号墓主人原本是专职石匠,但他在随葬22件石锛的同时也随葬32件石钺;98M20号墓主人被认为是专职玉匠,他在随葬24件石锛、111个玉芯和4块磨刀石的同时,也随葬有6件玉钺、16件石钺。大量随葬石钺玉钺所表达的身份地位显然与军事和军功有关,在当时的贵族行列中,有些贵族应当是军功贵族。 在人类学的实例中,摩尔根曾指出易洛魁人的“大战士”就属于军事酋长[10]141;恩格斯则把这一时期称为“英雄时代”,他说: 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赛,巴赛勒斯,狄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其所以称为“军事”,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劳动获得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深壕宽堑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实行以来,就逐渐变为世袭制,他们最初是耐心等待,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11]164 此外,在卡内罗(Robert L.Carneiro)所举例的哥伦比亚the Cauca Valley酋邦社会中,其贵族有三种,即血缘贵族(nobleza de sangre)、军事贵族(nobleza de cargo)如战争首领以及基于财富的贵族(nobleza de riqueza)。诚然,这三种贵族之间并非截然不同,贵族的身份原则上靠继承获得,然而实际上更多的是直接靠战功获得[12]246。这些军事贵族当然包括恩格斯所说的“最高军事首长”和“下级军事首长”。由于当时正处于由原始社会向国家社会转变中,部族与部族或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普遍存在,因而当时神权政治的权力系统中必然含有军事首领的权力,并成为这一时代的社会特征。 除了战争因素外,中心聚落形态阶段即酋邦阶段的权力因素既是血缘性的亦为宗教性的这一特征,也是人类学家们经常强调的。如卡莱尔沃·奥博格(Kalervo Oberg)在提出酋邦概念时即认为,酋邦的政治权威基于部落对共同渊源的认同。这是把祖先崇拜与血缘关系合为一体的一种认知。保罗·基希霍夫(Paul Kirchhoff)在描述酋邦的“圆锥形氏族”特征时,也强调该社会中每个成员的地位取决于他和“氏族—部落”祖先之间血缘关系之远近。而所谓氏族部落之祖先已属于神化了的祖先神范畴,是与祖先崇拜和宗教祭祀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提出:马耳他诸岛屿的神庙和巨石墓文化、复活节岛的“阿符”祭坛和巨石雕像、塔西提岛金字塔式的高坛等,都是酋邦社会中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有许多是为了纪念酋长之死而建造的。这些祭坛、雕像的存在,既说明在酋长支配下雕刻神像的神官和工匠之类的专职人员的出现,也说明酋长本身就是兼职的祭司,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和权威性[13]162-167。 第三,中心聚落、酋邦和原始宗邑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其氏族部落社会中的不平等。其中,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在不同的土著民族或集团中各有差异。有的表现为保罗·基希霍夫所说的“圆锥形氏族”(又称为“尖锥体形氏族”)。在这种圆锥形氏族—部落社会中,整个社会通常相信是自一个始祖传递下来,每个成员的地位取决于他和直系始祖之间血缘关系之远近,高血统的人与“氏族—部落”祖先的关系最近。在这里,社会地位大部分依据其出身而定,所谓与直系始祖之间血缘关系的最近者,也就是与现实的最高酋长关系最近者,亦即在直系世系上和酋长最近者,可获得较高的地位,从而形成圆锥体形的分阶等的社会系统。如果这种不平等(即阶等)只是以其出身而定,并不具有经济意义,那么笔者认为,这样的酋邦在社会发展序列中就处于“简单酋邦”的位置,也就是弗里德(Morton H.Fried)所说的“阶等社会”(rank society)。在考古学上,河南灵宝市西坡村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墓葬就有这种现象。在该墓地所划分的大型墓中,那座随葬有3件玉钺的11号墓主人是一位年仅4岁的小孩,而玉钺无论是作为武器或者是作为斧类工具的象征物,都不是一个4岁小孩所真正能从事的工作,这似乎告诉我们这位4岁的小孩原本是要成为巫师的,却不幸夭折身亡,故而其死后随葬的器物不但在数量上与那些被划分为大型墓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在品质上有玉钺等玉器。由此可见,该墓地中的不平等并非完全是由其生前的个人能力之类的因素决定,而是由其血缘身份之类的因素决定,当然也是世袭的。这一情形与酋邦模式中的尖锥体形氏族按照人们和酋长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确定其身份地位的原则,以及人类学者弗里德所说的“等级社会”中的“等级”(或译作“阶等”)的产生,有相似之处。对于这样的中心聚落,笔者将之列为中心聚落形态的雏形阶段。 酋邦社会的不平等,也有的表现为弗里德所划分的“分层社会”。这种社会分层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弗里德说是“相同年龄和性别的成员在获取基本生存资料的权利上存在差异”。对于史前的社会分层,欧美人类学者之间尚有分歧。除弗里德提出史前已出现社会分层之外,塞维斯(Elman R.Service)不认为社会分层属于酋邦阶段,而厄尔等人则认为分层存在于酋邦之中。史前社会即国家形成之前有社会分层,这无论是人类学上还是考古学上都是有资料证明的。例如,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莒县陵阳河遗址、莒县大朱家村遗址,江苏新沂花厅以及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墓所表现出的颇为悬殊的贫富分化,就属于具有经济意义的社会分层。因而,若比较没有社会分层的酋邦与含有社会分层的酋邦,笔者主张前者可归为简单酋邦,而后者则可归为复杂酋邦;而若将中心聚落形态也与之相对应的话,则前者属于初级阶段的中心聚落,后者属于发达的中心聚落。前者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要低于后者。换言之,初级阶段的中心聚落相当于简单酋邦,亦即“阶等社会”;发达的中心聚落相当于复杂酋邦,属于“分层社会”。 史前社会复杂化过程所呈现出的不平等也是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的史前中心聚落形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原始宗邑形态,其中的“家族—宗族”结构是一项重要特征。由于这样的社会结构使得这一阶段的社会不平等就可划分为:既有聚落内部的不平等,也有聚落与聚落之间的不平等;在聚落内部又可分为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不平等和家族内部父权家族长与其他家族成员间的不平等。例如我们一再指出的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莒县陵阳河遗址、莒县大朱家村遗址、临沂大范庄遗址、茌平尚庄遗址、邹县野店遗址,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以及安徽含山凌家滩的墓葬中,都可以看到大墓与小墓在墓穴大小、有无棺椁葬具、随葬品的数量、种类和质量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悬殊。这种差别,若从家族墓群和家族组织内部的视角看,当然可以划分出父权家族长与其他家族成员之间的不平等;若从宗族墓地内诸家族茔地的划分来看,有些家族富有的大墓较多,有的较少,这就属于宗族内部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不平等。尤其是在莒县陵阳河遗址中,大型墓和中型墓葬主要集中于河滩旁的第一墓区,而小墓一律埋葬于其他三个墓区,可见宗族内家族间的贫富分化已经相当严重。而宗族与宗族之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聚落与聚落之间,即中心聚落或曰原始宗邑与其周围普通聚落相比存在着不平等,如:大汶口、陵阳河、大朱家村、花厅、凌家滩等中心聚落的居民无论在财富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比那些普通聚落为高,表现出普通聚落从属或半从属于中心聚落,普通聚落被中心聚落所支配的情形,这当然属于聚落与聚落之间的不平等,亦即原始宗邑与从属于它的普通村邑之间的不平等。 第四,在史前社会晚期的血缘性问题上,中国史前社会的中心聚落阶段即原始宗邑阶段表现出的是“家族—宗族”组织结构;酋邦则是原始社会中血缘身份与政治分级相结合的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类型,用张光直先生的话来说,即“酋邦的主要特征是其政治分级与亲属制度相结合”[14]。的确,无论是酋邦,还是中心聚落形态或原始宗邑形态,其血缘性的结构形式应该说是形形色色的,它既可以表现为“圆锥形氏族”形态,亦可以是中国上古社会所表现出的“家族—宗族”形态。然而,它们的共性是在血缘的纽带中以血缘亲疏这一自然形态来作出身份和政治上的等差,成为史前中心聚落形态、原始宗邑和酋邦等社会类型的族共同体的组织结构和政治基础。 正像周人的宗族组织出现于先周时期一样,史前社会的原始宗邑即中心聚落,也是以家族与宗族组织结构为基础的。在笔者的一些相关研究中,曾列举了大汶口文化刘林墓地、大汶口墓地[1]136-138,151、陵阳河墓地中的“家族—宗族”墓地所反映出的社会组织结构;也论述了大河村、黄楝树、尉迟寺等遗址中房屋建筑所反映出的“核心家庭—大家庭—父系家族—宗族”的社会组织结构[1]146-149。对于这种以家族和宗族为社会组织结构、并处于最高级别的中心聚落,我们称之为原始宗邑,这应该说也在揭示中国史前社会中心聚落的特点。 说到宗族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笔者认为,从史前社会后期到西周春秋时代,宗族组织结构不断重复着从家族到宗族的繁衍分合的衍生模式。在周代的宗法中有大、小宗之分,这是宗族组织长期发展的结果。史前社会也许没有周代那样的宗法,但史前社会后期宗族组织中有强大宗族(强宗)与弱小宗族(弱宗)的分化,从而必然要导致主支与分支的出现。与大体平等的氏族部落结构相比,史前社会后期的父权家族和宗族的形态使得宗氏谱系变得清晰而有连贯性。在这里,每个宗族的祖宗是明确而实际存在过的,各个家族及个人与祖宗的关系和在宗族谱系中的位置都是确定和有序的。这样,各家族及其成员在宗族中的地位也是一定的。而在同姓的宗族与宗族之间,那些人口兴旺、经济繁荣、军事实力雄厚的强大宗族,很容易被视为与传说中的氏族部落始祖或部落神有直系的血缘渊源,即直系后裔,从而确立其主支(即后来的大宗)在部落乃至部族中的领导地位,其宗族长即为最高部落酋长或部族酋长。我国历史上颛顼、帝喾、唐、虞、夏、商、周、秦八代国族的谱系就与其部族始祖或部族神直接相联系。这样,在宗族内部,依据与宗族祖宗的血缘亲疏关系而确立各家族及其成员的社会政治上的和宗教祭祀上的等次性;在宗族与宗族间,也因和现任部族酋长即居于统帅地位的强宗族长间亲疏关系的不同,而形成主支与分支之间的等次性。这就必然使得聚落与聚落间出现中心聚落与半从属聚落即原始宗邑与村邑的组合关系。特别是在伴随有战争的情况下,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之间的主从和不平等关系将会越来越被加强和发展。残酷的战争使父权家族和宗族所具有的独立性受到限制,人们不得不团结在居于统帅地位的强大宗族的周围,联合本部族众多宗族力量共同对敌。这样,只能使强宗即现任部落或部族酋长所在宗族的地位不断巩固,而它所在的聚落也得以膨胀和发展。强宗一旦被视为是部落乃至部族始祖或部族神的直系后裔,就握有本部落或部族的最高祭祀权,在其所在地建立宗庙,主持祭祀大典,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握有部落或部族最高祭祀权和军事指挥权的主支宗族,在行政上的发号施令就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其族谱的正统性、其所在地的宗邑性,也就不可动摇了。总之,中心聚落与从属或半从属聚落相结合的形态,亦即原始宗邑与从属于它的普通村邑相结合的形态,在史前的出现,既是聚落内外发生不平等的结果,也是中国父权“家族—宗族”形态的产物,它是中国由史前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重要途径。 中国史前社会中心聚落(即原始宗邑)形态中的贫富分化、不平等以及社会上的权力关系和祖先崇拜的意识形态,都是与“家族—宗族”组织结构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家族和宗族都属于血缘组织,因而这样的不平等当然也是一种血缘身份与政治分级相结合而产生的不平等。这种带有身份特征的不平等,始现于简单酋邦,也延续、滞留于复杂酋邦之中。只不过是在简单酋邦时期也即中心聚落形态的初级阶段,它还不具有弗里德所说的社会分层的意义;而到了复杂酋邦阶段,即典型发达的中心聚落阶段,其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深,已萌生属于经济权力不平等的阶级和阶层,亦即已进入弗里德所说的社会分层。也就是说,上古中国,典型、发达的中心聚落形态,它所呈现出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复杂化的演进,以及在聚落群或部族中中心聚落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文化的中心地位与作用,原始宗邑的个性特征和神权政治等方面,都是十分突出的,这些社会现象共同构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国家社会转变的时代特征。 三、中心聚落、原始宗邑与酋邦社会的个性表现 中心聚落、原始宗邑与酋邦社会之间的个性问题,往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作为中心聚落,在聚落的外在形式上,有的依旧是环壕聚落,有的则演变为城邑。这种修筑城墙的中心聚落,在南方,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邑遗址可作为代表;在北方,则有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城邑。正如笔者曾指出的,对于史前城邑的性质,判断它究竟是中心聚落时期的中心聚落还是早期国家时的都城,是需要附加一些其他条件进行分析的,而不能仅仅依据是否修建了城墙,是否出现了城。这样的条件,我们以为:一是当时阶级产生和社会分层的情形;二是城邑的规模、城内建筑物的结构和性质,例如出现宫殿、宗庙等特殊建制。这是因为,只有与阶层和阶级的产生结合在一起的城邑,才属于阶级社会里的城邑;而只有进入阶级社会,在等级分明、支配与被支配基本确立的情况下,城邑的规模和城内以宫殿宗庙为首的建制,才能显示出其权力系统是带有强制性质的。而权力的强制性则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依据这样的条件,我们判断城头山和西山等城邑属于中心聚落,特别是与龙山时代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早期国家的都城相比,问题是清楚的。至于在中心聚落形态阶段,各地是否修筑有城墙,则属于中心聚落形态的多样化问题,而不属于中心聚落与酋长社会的普遍原则。在中心聚落阶段,某些地方修筑城邑,这既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加强的标志,这大概是人们对自己的聚落群内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祭祀中心非常重视,大力保护的缘故。 在中心聚落形态阶段,也可以看到某些遗址属于专业性生产点,例如在甘肃兰州白道沟坪发现专门烧制陶器的场所[15][16],在湖北宜都红花套发现石器制造场[16]。白道沟坪位于黄河北岸,是马家窑文化马厂期的遗址。该遗址中间是居住区,西边是墓地,东南边是一个很大的陶器制造场。在陶器制造场中除了发现许多泥坯、研磨颜料用的磨盘和分格的调色陶碟等原料和工具外,还发现被分为四组的12座陶窑。由于这些陶窑及其周围已受到破坏,假如每组都能像中间那样保存完好,四组当有20座陶窑。为此,严文明先生指出,如此大规模的陶器制造场,其产品绝对不单是为自身消费的需要,而主要应是为交换而生产,由此可以说“这个聚落的居民是以制造陶器为主要生业的”[1]146-149。红花套位于长江西南岸,紧靠江边。它利用江边大大小小的砾石,建立了许多石器作坊,同时也有不少住房,可见它不是临时的石器制造场,而是从事石器专业化生产和交换的经济中心。此外,从红花套发现大量管钻留下的石芯而很少发现管钻的完整器物,其他类型的完整器物也很少见,最多的是些残次品和废料;相反在红花套周围数百公里内的一些遗址中,则有许多与红花套石质相同、制法和类型相同的完整器物,而不见半成品、残次品和制石工具。这说明红花套石器是供许多地方使用的[1]146-149。 对于像白道沟坪和红花套这样的专业化生产,可以判断其为一种商业性生产,而无法将其视为塞维斯所谓“酋邦具有再分配机制”这一假说的实例。在塞维斯的酋邦“再分配机制理论”中,酋邦兴起于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由于资源的差异,出现地区分工和交换,在这种特殊的地方,进行生产分工与产品再分配的需求很大,导致控制中心即酋邦的出现,使酋长成为再分配者。然而,在中国史前社会的中心聚落形态阶段,各地区的生产、消费和生活在总体上和基本方面都属于自给自足,根本不属于由于生态和资源的关系而使酋长组织各个聚落从事生产的地区分工。所以,酋邦也不是由于再分配机制兴起的。白道沟坪和红花套这样的用于交换的专业化生产,在中心聚落形态阶段出现,反映出此时各个聚落社会的生产可以有多种样式,但由于这样的材料凤毛麟角,因而它只属于不同的聚落乃至不同的中心聚落的个性表现,而不能视为中心聚落或酋邦社会的一般特征。至于社会发展到下一阶段即早期国家阶段,这种专业化的生产是否开始纳入邦国内再分配体制之中则当别论。 以上我们通过对中心聚落形态、原始宗邑以及酋邦社会中共性与个性特征的分析,对三者进行了整合。其整合的原则是以聚落形态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远古社会,需要以远古社会遗留下的聚落遗址材料为建构理论框架的基础。这正像我们所说的三重证据法中,地下的考古资料是基础,地上的文献是血脉,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材料是辅助和旁证一样。现存的人类学资料虽然有“活化石”的作用,但它在时间上距离远古已经很久了,在环境上也与远古社会各地区的聚落环境大不相同,因此可以借助于它解释远古社会的一些现象,而它本身并非远古的史实。这是我们在使用人类学资料和三重证据法时必须注意的问题。由于我们是以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为主来对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进行整合,因此可以说,这样的整合实际上也是对重建中国上古社会历史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