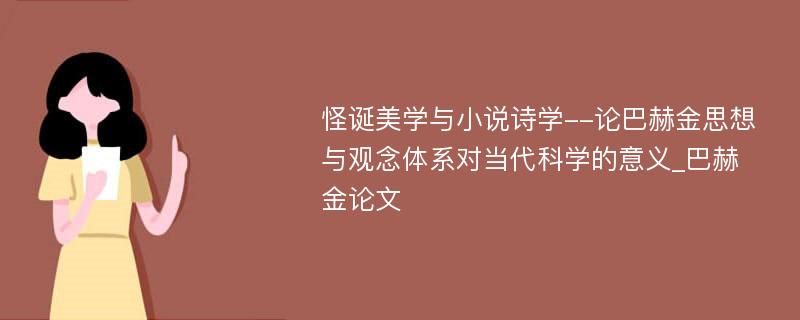
怪诞美学与小说诗学——论巴赫金的思想与概念体系对当代科学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诗学论文,怪诞论文,美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5)02-0017-04
众所周知,巴赫金创立的怪诞形象观,是与考察这一问题的传统方法完全矛盾的。
从传统观点来看,怪诞是各种艺术形式构成的体系,这些形式偏离于形式创作的某种思想范式或者与之相对立,它们旨在展示由各种类似手段所描绘的事物及人物与“一如生活的范式”大相径庭(注:参看工具书、洛谢夫与舍斯塔科夫的《美学范畴史》一书、尤里·曼与汉斯·冯特的书、洛特曼的《在怪诞与哲学的世界中》一文。)。巴赫金相反,不说这是对范式的偏离,而说是两种地位平等和彼此补充的审美规范(经典)许多个世纪以来同时共存于文化中。
虽然巴赫金的这个理论也像其他理论那样广为人知(注: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论巴赫金所建立的文学、哲学、美学的专著中却对他的怪诞理论未加讨论。参看:Freise M.Michail Bachtins philosophische ? sthetik der Literatur.Frankfurt am Main,1998.),但在实践中传统方法却独霸科学。这种方法在文艺学研究中而不是在文化学研究中(试比较:一方是论果戈理、谢德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论著,另一方是利哈乔夫与别人合著的论笑在古代俄罗斯的书)尤为突出。
之所以形成了这种状况,在我看来,原因是巴赫金的方法首先被“固定”在了对历史上很遥远的材料的研究上。学者虽然提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和果戈理的部分创作中存在着与文艺复兴、中世纪甚至希腊化时期的怪诞传统的一些交叉点,但这些关系总归让人觉得过于大胆和直接,似乎感觉得到缺乏某种必要的中间环节。我认为,这同样也有其缘由:在巴赫金思想的总的体系中怪诞观念和小说理论之间的联系至今没有得到阐明。
不妨把为什么作者本人没有明确这种联系的问题搁置一边,我要探讨的是一些事实,证明这种联系存在的一些事实。不考虑到巴赫金思想的这两个方面的相互联系,就无法真正理解学者对这两个问题——无论是怪诞还是小说——的任何一个的阐述,于是也就无法有效地把他的思想运用于当代文艺学中。
1.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双体性身体(двутелое тело)”和“双声性话语(двуголосое слово)”两个术语(参看我的书)的外在相似性这个事实。每个术语对于我们所比较的怪诞理论和小说理论而言几乎具有核心的意义。第一个术语指怪诞诸形式中的这样一种形式,它最明显地表达出怪诞身体作为生育的身体(后面专门细述)的特点。第二个指三类散文语言中的这样一类,它能够决定小说修辞的特色。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相应的理论框架中可以区别开(1)形式的基本原则和(2)这样的一种个别情况,这种情况就是上述原则的极端表现。一般来讲,怪诞身体形象是以身体界限的转换为基础建立的,而古典身体形象则是以局限性、封闭性和自足性为基础建立的;从这个角度看,双体性身体便是一种极端情形。在双声性话语领域情况也同样如此,这种话语及其所有的变体(让我们回忆一下,如故事体、仿格体、讽拟体、对话语轮)都是以不同意识以及不同主体意向的界线转换为基础建立的。这里也有一个极端情形,这就是具有内在对话性的话语,换言之,是这样的一种双声语变体,在一个话语里同时兼有多种意向,这不只是不同的意向,也是对立的意向,而且还是地位平等的意向。
最后,如果说巴赫金把怪诞身体形象与特殊的时间观和生成思想联系在一起,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他也完全以类似的方式阐明了界限开放的话语是如何参与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的,而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指出了对长篇小说体裁具有代表性的内在确信的话语与这一过程的有机联系,这种话语不同于非长篇小说体裁的话语,后者是凝固了和不参与正在流逝的现实生活的权威话语。
2.与“双体性身体”较为相近的还有另一个巴赫金小说话语理论中的术语“语言混杂”。如果“双声性话语”是从内部描述话语,从如何形成它的各种意向的角度描述话语,那么第二个术语则描述了话语外部的面貌,即从外部观察时呈现出来的话语形象中语言肉体的(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明显的异质性。
假如使用巴赫金的术语,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作者把小说的各种主题谱写成“管弦乐曲”的要素,而是“风景画风格”(参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展示,这种风格的基础是消除作者话语与人物话语之间的界线。至此我们在巴赫金那里再次看到了“普通类型的”结构与它的极端变种的区别:在“风景画风格”的框架内可以出现被称之为“语言混杂”的各种异质话语的完全结合。
不难发现,类似的极端情形不过是小说修辞领域中的怪诞诸形式。
3.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术语“小说的意在言外”。此术语的地位不同于术语“双声性话语”和“语言混杂”。
首先,“小说的意在言外”所指的概念是小说语言形象的概括性特征,它是与作为象征的诗歌语言形象的特征并列的,按照巴赫金的观点,诗歌语言形象同样具有普遍性。
其次,这个概念同时指长篇小说中的话语(参看《长篇小说的话语》)和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参看《论时空体形式》一文)。
让我们对“小说的意在言外”与“象征”的关系作一考察。在《长篇小说的话语》的研究中,巴赫金区分了作为个别情况的“狭义的诗歌形象”——纯语言形象(“比喻形象”)和作为任何艺术形象的本质特征的象征:“在狭义的诗歌形象(即语义辞格所表现的形象)里,所有事情(言语形象的运动)都演绎在言语(包括其一切因素)和对象(也包括其一切因素)两者之间”;“而且,艺术象征(如隐喻的展开)所要求的正是统一的语言,与自己的对象发生直接关系的语言”[1](P91-92)。在其他论著中我们可以找到相同的逻辑:“最后,尤为困难的是小说的意在言外,也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隐喻(虽然与诗歌隐喻完全不同),它是由它们(骗子、小丑与傻瓜形象——笔者注)带入了文学的,并且对它而言甚至没有恰当的术语(“讽拟”、“笑话”、“幽默”、“微讽”、“怪诞”、“漫画”等等,只是它的一些变体和情调)[1](P315)。
如果我们记得,在演说术传统上讽刺实际上是纯语言形象或者手段,而巴赫金那里的讽拟是双声语的一种,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小说的言外之意是与双声语有关系的,就好像象征与比喻形象有关系一样。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语言形象的类别与人物类别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散文,准确地说是对长篇小说具有特殊性,这一点对于巴赫金的读者而言显得有些意外。研究长篇小说修辞一文的第4章被称为“小说中的说话人”。同样是与《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中与“小说的言外之意”相联系的那三类人物,既是被表现的言外之意本身,也是说话人:“这些人物的存在本身不具有直接的意义,而具有转义,因为它们的外表,它们的一切言行,不是具有直接的意义,而是具有转义,有时候是具有相反的意义,不能对它们进行字面上的直接理解,它们不是它们表面上出现的那种东西;它们的存在是某种别的存在的反映,而且还不是直接的反映。”[1](P309)
散文的语言形象是在各种不同的意向、各种社会的和民族的语言的交叉中建立的,而在这种交叉中“言语仿佛活跃于自己的语境和他人语境的边界上”[1](P97),这种语言形象和上面提到的长篇小说特有的人物形象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这些人物同样活跃于自己的语境和他人语境的边界上,这些人物的意义也如同双声语的意义那样,是由各种不同的语境地位平等地相互映照中生成的(此处即指“这里的存在”和“别的存在”),但若单面地阐释,它们的意义就会消失。
小说的言外之意与杂语发生关系并不是偶然的,而象征相反,与统一的语言发生关系。如果我们说巴赫金对象征的论述是以俄罗斯象征主义者所创造的、后来在洛谢夫的研究中获得了严格的逻辑形式的那个观念为出发点的,那么这种说法不太可能会错,而且这样的说法中确信“象征中具有的那种共同性已经隐含了一切被象征的东西,尽管这种东西是无穷的”,也确信象征“就是同一,就是所指之物和能指此物的思想形象的彼此渗透”,但同时也是“一系列有限的或者无限的合乎规律的个别情况”。[2](P65-66)
显然,在这样的一种象征观念中,象征的统一而惟一的描绘因素或者象征因素(巴赫金那里是语言)具有预先就确定了的界限这种思想,与等同自身、同时被象征或描绘的对象的无尽性这种思想,是结合在一起的。
小说的言外之意正相反,它是开放的语言的双重性和异质性,意义和事件的双重性和异质性,无论语言的形象还是人物的形象都是以绝对不等同自身和各自界限的转换事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巴赫金认为,在长篇小说的渊源中不仅有骗子、小丑与傻瓜的原型,而且还有各种“民间的面具”,这些面具的固有特征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同于自身”,以后的小说的主人公也“不与他的命运和他的身份完全等同”[1](P478-479)。
关于类型上同源的两对对应的范畴,一对是诗歌象征与小说的言外之意,另一对是古典的审美规范与怪诞的审美规范,现在完全清楚了。需要指出的只是在长篇小说中,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小说中,作为主体的主人公不与自身重合,不与那个作为角色的自身(其中也包括起着情节作用的语轮)相重合。这正是巴赫金论主人公与其情节不相重合的意思之所在,这同样也是巴赫金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或者大于自己的命运或者小于自己的人性的意思之所在。
这一说明使我们能够转而探讨如何把巴赫金关于怪诞的思想运用于小说历史诗学研究中的问题。
以对怪诞的传统理解为基础研究各种文学作品的论著,要么只涉及文学作品中的物化的领域(各种怪诞的物质形象和各种完全客体化了人物)(注:有代表性的如我们最新的百科辞书论怪诞的条目中,所有的例子只说明主人公及其世界的各种不同的特征。参看《文学术语与概念百科辞典》第189条,莫斯科,2001年版。试比较:Loicq A.Grotesque//Le dictionaire du Littéraire.Publié sous la direction de P.Aron,D.Saint-Jacques,A.Viala.Paris.2002.P.255.),要么力图把对物的描绘与有关整个描写的特殊情调的模糊思想结合在一起。谈这种特殊情调时,借助“宇宙性的”、“幽默的”、“极度奇怪的”、“荒诞不经的”、“荒谬的”(有时候还是“可怕的”)、“充满幻想的”诸如此类的范畴(注:参看:Wilpert G.von.Sachw(rterbuch der Literatur.Stuttgart,1989.C.353.))。采用这种方法,被强调的已经不是物,而是作者对它的评价,这种评价是直接以描写的方法被表达出来的。越承认符合真实物的事物比例遭到破坏是怪诞的主要特征,这一点就显得越自然。
在第一种情况下,研究文学怪诞的对象,可以是很大数量的属于所谓的古典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样的物质形象和人物形象可以在诸如屠格涅夫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找到,由于这个原因,在他们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可以发现对讽刺手法的局部使用。第二种情况,即有关审美情调的观点,恰好相反,几乎只属于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以及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颓废文学。
关于文学中的怪诞主体的问题,以及所讲述的事件的各种形式(情节结构)与讲述本身这一事件的各种形式(特别是叙述结构)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直到近期依然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注:这种传统在塔马尔钦科与别良采娃合著的《文学作品中的怪诞主体》中遭到了破坏。参看塔马尔钦科、别良采娃、鲁契尼科夫、福克松:《文学作品:理论与分析问题》,克梅罗沃,2003年版,第6-61页。)只要问一问,“怪诞”、“怪诞形象”这些概念只属于背景人物呢,还是还属于主要主人公,属于叙述人,只属于情节结构呢,还是还属于叙述本身,就会明白,在许多古典作品中各种怪诞原则是与姑且称之为非怪诞的各种原则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这些非怪诞原则恰恰是对立于它的边缘现象的艺术体系的核心。
我们一点也不否定各种混合情形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的意义,我只提醒一点,那就是要揭示这些情形的本质特征,需要以认识各种“纯粹的”形式和各种“对立的”形式为基础。然而,传统的怪诞理论缺乏的正是研究这些形式的适当方法,因此可以说,是这些形式真正体现出纯审美的规范,而不是展示出对这一规范的偏离。
各种“纯粹的”怪诞形式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非诗歌艺术中具有以下突出特点:(1)文学主体的形象(主要主人公和/或叙述人)是以各种不同的意识之间边界的转换——直到每个意识的载体丧失同一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2)统一的和直接的描绘法让位于逆向的描绘法或者被它所取代;(3)在修辞学领域,在各种“双声性”话语的变体中,具有“内在对话性”(与“双体性身体”完全类似)的话语形式占据主导地位。
收稿日期:2004-0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