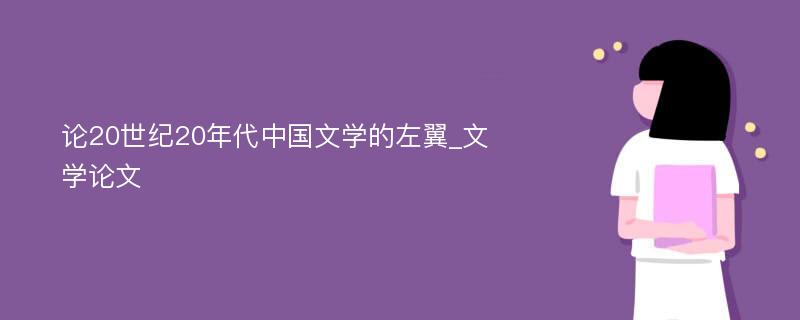
论1920年代中国文学的左翼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五四”文学到左翼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断裂。“五四”文学是在“人的文学”的思想视野下追求个性解放、表现个体的心理世界与精神冲突、反对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人道主义文学,塑造的农民形象是愚昧的、病态的、奴性的;左翼文学是在“阶级性”的现代性思想视野下对革命群体中的人进行审美想象和建构,表现的是阶级对立下经济矛盾和政治冲突。“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不仅存在着对立与差异,而且也有着内在的精神勾连,二者之间有着一道隐秘的精神桥梁相通。“从文学‘自身’来说,左翼文论与五四以来以人性解放为旨归的文学思想和兼容并包的创作状态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断裂,但还是隐伏着几个方面的历史联系,例如,五四的‘思想革命’的主张已包含着社会革命的意向;五四作家普遍的平民意识和偶或出现的‘劳工神圣’的口号可以通连左翼‘文学大众化’的提倡;五四虽有多种创作流派,而其中较多倾向于真实反映现实的朴素的写实主义,好像是为左翼强调‘现实主义’作了铺垫。到了左翼文论的后期,由于鲁迅、茅盾、冯雪峰、胡风等左翼作家和理论家的努力,更逐渐自觉地与五四文学传统相接续,并在演进中深化。”①
以“文学革命”为口号的现代“五四”文学,本身包含着革命的质素。“五四”文学左翼化早在1920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创造社的“革命性”话语大大遮蔽了文学研究会的左翼化转变。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提出了“血和泪的文学”,在思想倾向和创作姿态上已经蕴含了左翼文学的精神内涵。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着内在精神联系的。后期创造社对“革命文学”的倡导,加速了1920年代文学左翼化的生成流变过程。1920年代后期,文学左翼化的过程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其焦点在于对乡土中国和农民形象的不同思想认知与审美建构。对1920年代中国文学左翼化的回顾与反思,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当时不同文学流派的审美差异、挖掘其内在精神联系和理念交融,而且对新世纪阶级性叙事缺失的文化语境提供了来源于历史的审美启示。
一、文学研究会的左翼化
“五四”以后,随着时代形势的发展,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对探寻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巨大。在各种现代性思潮中,宣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渐渐深入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在“五四”时期文坛上两大主力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中,许多作家的文学观念随着时代转折而发生重大变化。以往的研究多数从创造社的后期转变来叙述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但是,事实上,文艺界最早倡导左翼革命文学的是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的。对此,田仲济先生在《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思想》一文中有过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我们一直以为最早提出的是创造社或太阳社……实际上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就有人提出,‘第四阶级者要想扭断这条铁索。非将现在底经济组织推翻不可,非特无产阶级者联合起来,革第三阶级的命不可’。从而提倡血泪的、革命的、自然主义的文学,以这样的文学来推动进行俄国式的革命。”②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初的宣言中就明确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③可见,文学研究会作家所秉持的文学观是一种严肃、客观、真诚、为人生的观点。文学研究会同人观点的相近,并不说明他们之间没有差异。相对于周作人的人道主义人性观之下的“为人生”的文学,郑振铎的文学观点与他拉开了明显距离。1921年,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6期发表《血和泪的文学》,提出:“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吧:‘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诚然有时能以天然美来安慰我们的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然而在此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上,我们的被扰乱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恐总非他们所能安慰得了的吧……记住!记住!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④提倡为人生的、客观的、表现“血和泪的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五四”文学走向左翼文学道路上贯通的精神血脉。
不仅如此,文学研究会的一些作家在文学对社会的能动作用上,也有着与中国左翼文学一致的认同:1921年,郑振铎在《文学的使命》中提出文学的效力问题,认为文学具有“在哀微的时期,作家于时代精神以外,同时须具有改造时代精神的思想。不仅是无杵的表现与解释他而已”;在感性方面,“我以为文学中虽重要的元素是情绪,不是思想。文学所以能感动人,能使人歌哭忘形,心入其中,而受其溶化的,完全是情绪的感化力”。⑤叶圣陶在《创作的要素》中也提到了文学的效力:“到了尽能做到的时候,文学就有一种神异的力,他一定能写出全民族的普遍的深潜的黑暗,使酣睡不愿醒的大群也会跳将起来。达到这个时候的迟早,全视创作家的努力如何,创作家努力!”⑥1921年,耿济之在《〈前夜〉序》中,对文学改造社会、人生的功用与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换言之,文学作品的制成应当用作者的理想来应用到人生的现实方面。文学一方面描写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另一方面从所描写的里面表现出作者的理想,其结果: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这才是真正文学的效用。”⑦为此,耿济之详细分析了《前夜》的作者屠格涅夫所具有革命倾向性的写作姿态,他认为,屠格涅夫实在是厌弃白尔森涅甫和苏宾两人学问和艺术的事业,而推崇段沙洛夫这种切志救国、铁肩担道的精神。然而屠格涅夫并不是反对学问和艺术的事业,他也知道这种事业在社会上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俄国“当时”所最为需要的并不专是这种事业,却是需要实地改造的力量和精神。他在自己小说里不但对于白尔森涅甫和苏宾表示蔑视的意思,并且否认与他同时的各种人。他说:像放沙格夫这种人现在是没有的了,所有的只是喧嗓者,鼓锤子,和从空虚移到虚空的人。这句话真是骂尽俄国当时的人,形容尽俄国当时社会的情形!所以这篇小说实在是俄国青年的兴奋剂,凡读着这本书,便明白自己的责任并不在于空虚飘茫的言论,而在于实地去做改造社会的工作。此书一出,俄国不少青年男女都觉悟过来,争着学段沙洛夫和叶林娜,大张“争自由”“谋解放”的旗帜,以做各种民间的运动,而促成社会的改革。由此可见文学与社会和人生实在是很有关系的。⑧
耿济之对屠格涅夫的写作姿态和精神追求的分析极为精辟。屠格涅夫的这种思想意识是被时代青年和后来的异域翻译家所理解、响应的,文学的确起到了无比巨大的改造人生、社会的作用。耿济之所引进的屠格涅夫的遗弃“学问和艺术的事业”、“切志救国,铁肩担道”的精神,与后来的中国左翼文学家宁肯牺牲文学的艺术性,也要追求文学的革命性宣传效果的文学理念,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耿济之的主张与阐释,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文学研究会与左翼作家在文学的工具价值理性方面的精神联系,而且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屠格涅夫”们和左翼文学提供了一面基于更高的利益、更高的理想,趋向终极性价值的镜子。
正是因为文学研究会与左翼文学有着这样相同的血脉和精神联系,所以在时代大转折的时候,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向左翼作家的转化、提倡革命的文学就显得自然而然,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乡土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的自然发展。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创造社的“革命性”话语大大遮蔽了文学研究会这种左翼化转变。
二、“革命文学”的发生
“革命文学”是192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左翼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词汇。因此,对“革命文学”词汇生产过程的分析,就为我们昭示了一个1920年代文学左翼化的生成流变过程。事实上,这个词汇最早并不是创造社作家提出来的。早在1917年3月,李大钊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一文中就提出了“革命文学”。李大钊说:“俄国之文学,人道主义之文学也,亦即革命主义之文学也。其思想家、著作家有所评论、有所创作,莫不以人道主义为基础,主张人性之自由发展,个人之社会的权利,以充丰俄罗斯国民生活之内容……而赫尔金之《谁之罪》,俾善士奇之《贵族之领地》,则又关于改善家庭问题者也。就中尤以赫尔金、伯伦士奇二氏为革命文学之先觉。”⑨李大钊“革命文学”的提出,对1920年代文学左翼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中国文学关系的探索下,与左翼革命文学血脉相通的文学研究会作家也提出了“革命文学”的主张。
早在1922年4月,之常在《文学旬刊》第35期发表《支配社会底文学论》,在文学界最早提出具有阶级意识的“革命的文学”的主张。“侵害第四阶级底铁索,传统思想固然是一部分,现在底经济组织的确是主要的成分。第四阶级者要想扭断这条铁索,非将现在底经济组织推翻不可,非将无产阶级者联合起来,革第三阶级底命不可……文学是人类活动底结晶,传达感情底利器,新时代底指导者,鞭策者。国民文学底功用是将一人底热情传达他人,站在新时代底莅临底前部。时代蜕变,思想和环境种种变迁,文学当然也是生长的,与时代俱变的……总之,今日底文学是人类活动底结晶,新时代底先驱,为人生的,支配社会的,革命的。”⑩之常不仅最早在文坛上提出了革命文学的主张,更为可贵的是他运用马克思阶级对立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对革命文学进行阶级性的现代性思想审视。这使之常的主张具有了真正的革命文学性质。尽管之常的“革命文学”主张发出了新的文学时代的召唤,但是文学研究会等团体的大多数作家距离真正认识、倡导“革命文学”还有着一段时间。
1923年12月,茅盾发表《“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一文,敏锐地发现反对“吟风弄月”的恶习、“醉罢;美呀”的所谓唯美的文学和有颓废倾向的文学,是当时文坛上常常听到的论调。对此,他从社会政治趋于黑暗、中国知识阶级中了名士思想的毒以及唯美派作家也没有产生好作品等方面分析了文坛发生变化的原因,大力主张“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的现代“活文学”,大声呼唤“我希望从此以后就是国内文坛的大转变时期”。(11)
1924年11月,茅盾留苏的弟弟沈泽民发表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是中国左翼文学一篇极为重要的理论文章。沈泽民在文中明确指出:“就是在现在,我们显然看出,在文学方面象在各种方面一样,已有诞生一种新的精神的必要了。一个极大的变动正在涌起;社会的全组织正在瓦解,旧的阶级已自己走到他的灭亡的道路,新的阶级正在觉悟起来凝聚他自己的势力……一个革命的文学者,实是民众情绪生活的组织者,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在这革命的时代中所能成就的事业!”(12)沈泽民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明确指出了文学的新时代风貌以及对作家的革命召唤,而且具体点明了作家创作革命文学的途径、革命文学的本质特征。他指出:“真真的革命者,决不是空谈革命的;所以真真的革命文学者,决不是把一些革命的字眼放在纸上就算数……因为现代的革命的泉源是在无产阶级里面,不走到这个阶级里面去,决不能交通他们的情绪生活,决不能产生革命的文学!”(13)
亲身参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是作家获得真正的革命意识、革命思想的唯一正确途径。真正的“革命文学”决不是作家在革命的幻想中产生的,而是在革命实践中造就的;也不是仅仅“外面敷着血和泪的文章”即可成为革命文学的。“血”和“泪”不是所谓的革命文学的装饰品,它们真正昭示的意义是“文学的阶级性”。至此,革命文学的本质特征——阶级性——已经被清楚地揭示出来。这是沈泽民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的新认识,其中凝聚了苏维埃俄国的文学革命实践,也包含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的思想成果,对中国文坛的左翼化产生了重要作用。
1925年5月到10月,茅盾连续在《文学周报》上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的系列文章。茅盾清晰地梳理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源头、发生条件、内容、形式,为无产阶级文艺做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阐释。1920年代初期、中期的文学左翼化理论和“革命文学”词汇的提出,在很大意义上为后来的“革命文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规定了其精神内涵和审美指向。
三、后期创造社的左翼化
在创造社前期,郭沫若等作家反对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坚持主观表现论的唯美主义文学观。1923年5月20日,成仿吾也在《新文学之使命》中全力主张“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因而呼吁“我们要追求文学的全!我们要实现文学的美!”(14)
但是,郭沫若在1923年5月27日第3号《创造周报》上发表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描述了“野兽般的武人之专横,被廉耻的政客之蠢动,贪婪的外来资本家之压迫,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泪排抑成黄河扬子江一样的赤流”的“中国的政治生涯几乎到了破产的地位”,因而鲜明地主张“我们现在于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种新的运动,我们于文学事业中也正是不能满足于现状,要打破从来的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现”,对“五四”文学提出了否定性的批评:“四五年前的白话文革命,在破了的絮袄上虽打上了几个补绽,在污了的粉壁上虽然涂上了一层白垩,但是里面的内容依然还是败棉,依然还是粪土。Bourgeois的根性,在那些提倡者与附和者之中是植根太深了,我们要把这根性和盘推翻,要把那败棉烧成灰烬,把那粪土消灭于无形”。(15)虽然郭沫若已经在文学上喊出了“无产阶级的精神”的字眼,但是“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也标明了郭沫若的文学观并没有真正完成从“五四”文学的人性意识转变为阶级意识。
不仅郭沫若如此,此时的创造社大将们同样缺乏阶级审美意识。1923年12月17日,作为创造社主将之一的郑伯奇在《国民文学论》中,认为“阶级文学在今日的中国还太早,中国所要求的,正是国民文学”。(16)1926年6月,创造社的另一主将成仿吾在《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中认为,“文学的内容必然地是人性”,在经过一番分析后,得出了一个公式:(真挚的人性)+(审美的形式)+(热情)=(永远的革命文学)。(17)可见,“无产阶级精神”的革命文学并没有真正成为这一时期创造社同人的共同思想认识,创造社还处于从“五四”文学向左翼文学的转变之中。
从社会阶层的新变化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乡村社会中的农民阶级日益分化,贫雇农无产者渐渐成为革命的“第四阶级”主要力量。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已经在政治上指出了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位置,看到了中国农民所蕴藏的巨大的积极革命力量,第一次发现了中国农民。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革命性的发现,推动了作家的左翼化。到1926年,郭沫若等人的左翼化转变渐渐走向自觉。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从法国大革命谈起,认为现在进入了“第四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而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地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地,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地。除此以外地文艺都已经是过去的了。包含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都已经过去了。”(18)
1928年1月1日,由一群青年文艺者创办的《太阳》月刊问世,引发了“革命文学”从酝酿期走向高潮期。《太阳》月刊创刊号的卷首语高呼要“向太阳,向着光明走!”为了正义和光明,要求文学“开辟新的园土”、“栽种新的花木”——“革命文学”。1928年,创造社后期的干将冯乃超、李初梨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一起推动了中国左翼文学高潮的到来。1928年2月1日,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表达了创造社作家左翼化的思想转变,提出明确的“革命文学”要求:“换一句话,我们今后的文学运动应该为一步的前进,前进一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1928年2月15日,李初梨在《怎样建设革命文学》中提出了革命文学的阶级性概念。至此,革命文学的阶级意识已经成为创造社内部左翼化作家的共识。对革命文学的艺术形式的探索,李初梨提出了“讽刺的、暴露的、鼓动的、教导的”四种形态的革命文学。
四、农民形象:“革命文学论争”焦点
为了扩大革命文学的影响,彻底击溃“五四”文学的传统,创造社作家在提出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立场、观点的同时,还对革命文学的艺术形式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而这种具体分析是建立在对“五四”文学的主将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人作品的批评基础之上的,其中对鲁迅的攻击尤为激烈。透过对鲁迅等人的攻击,我们不仅会看到创造社等左翼化作家的革命文学主张,而且还可以反观出他们对乡土中国社会、对中国农民的不同思想认知与审美建构。
1927年,许幸之的《艺术家与农民革命》提出了艺术家如何在“农民向贵族资本家革命的时代”,以艺术的形式参加农民革命、创作“农民文艺”的问题:“亲切的农民来告诉我们,你们艺术家们,你们莫要再替贵族和资产家们做宣传工作了。他们在社会上已经作了许多不可掩饰的罪恶,现在是我们平民是无产阶级向他们革命的时期……你们诗人文学者,你们画家雕刻家必须参加我们的农民革命,你们的诗和小说,画和雕刻,也必须描写我们农民的生活,必须以我们农民的风俗习惯来做你们艺术的题材,你们描写出来的诗和小说,绘画和雕刻,也必须教我们农民们都能了解。”(20)许幸之的呼吁是切中时弊的,因为新兴的左翼文学思潮虽然一味强调“第四阶级”、“工农大众”,但是相对于乡土中国国情、具体的文学创作来说都是泛泛而谈,没有真正深入中国农民、体现农民生活的革命文学作品。
虽然左翼作家已经意识到了阶级性的现代思想意识,但是怎样表现阶级意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确立起来,都处于探索之中。乡土中国的国情使左翼文学理论涂抹上了一层乡土色彩,即左翼理论的探索在涉及文学艺术形式的时候,都指向了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21)真正具体到文学内部对乡土中国社会、中国农民及文学中的中国农民形象进行理论思考和审美观照,是1928年后革命文学高潮的时期。
1928年1月冯乃超对叶圣陶、鲁迅、郁达夫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反映的是“负担没落的运命的社会”,“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在一种否定性的批判中建构了一种积极的阶级性审美想象。1928年2月,蒋光慈在《关于革命文学》中对革命文学的阶级性想象进行了理论阐述:
旧式的作家所表现的,何尝不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过他所表现的,是旧的倾向,是反动的一方面,而忽略了新的,能够创造光明的力量。革命的作家不但要表现时代,并且能够在茫乱的斗争生活中,寻出创造新生活的元素,而向这种元素表示着充分的同情,并对之有深切的希望和信赖……
革命的作家不但一方面要暴露旧势力的邪恶,攻击旧社会的破产,并且要促进新势力的发展。视这种发展为自己的文学的生命。在实际社会的生活中,一切被压迫群众不但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是创造新社会的主人。(22)
蒋光慈已经清晰地阐述了左翼化文学对中国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形象的审美想象与建构方式,即由过去的“暴露”、“攻击”、“批判”转向为对“新的,能够创造光明的力量”、“新生活的元素”的寻找、发现、促进,由对愚昧、落后的被压迫者形象转向为“反抗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是创造新社会的主人”的新形象的塑造。在具体的文学审美想象方面,蒋光慈提出了反个人主义,表现集体主义和群众力量的文学创作原则:“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所谓个人只是群众的一分子,若这个个人的行动是为着群众的利益的,那么当然是有意义的,否则,他便是革命的障碍。革命文学的任务是要在此斗争的生活中,表现出群众的力量,暗示人们以集体主义的倾向。”(23)
基于这种革命文学新思潮的要求,钱杏邨在承认《阿Q正传》是一部伟大的创作、是“代表中国人的死去了的病态的国民性的”时代力作的前提下,指出了新的第四阶级文艺思潮中的农民变化:“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象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并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象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智识已不象阿Q时代的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明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24)在这种新型农民观的审美观照下,钱杏邨得出了一个鲜明的结论: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
钱杏邨对阿Q形象的批判引起了许多作家的批评。1928年6月11日,青见在《语丝》上发表《阿Q的时代没有死》,对钱杏邨立论的基础“阿Q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农民已经变化了”进行反驳:“在北方——东三省,直,鲁,豫……的农民,不但幼稚而且还可以说没有严密的组织,对于政治还待认识;也不了解‘革命’,更没有‘革命性’。知识呢,只有那祖传的一点。举例来说……在乡间是有‘真龙天子出世’的传说。此外则普遍的钟表都认不得!”因此认为“钱先生说中国农民如何如何,倘是指全中国而言,我敢说:‘错了!错了!第三个错了!’”(25)青见的批驳是非常有力的。中国农民在北伐战争后的农民运动中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大多数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民还是处于原先的旧秩序之中,阿Q式的农民思想、精神面貌并没有多大的改观,因此,钱杏邨批判鲁迅思想过时论是不确切的。1929年5月12日,茅盾对钱杏邨等人的批评做了进一步的反驳,认为“《呐喊》所表现着,确是现代中国的人生,不过总是躲在暗陬里的难得变动的中国乡村的人生;我还是以为《呐喊》的主要调子是攻击传统思想,不过用的手段是反面的嘲讽……再如果我们是冷静地正视现实的,我们也应该承认即在现今,中国境内也还存在着不少《呐喊》中的乡村和那些老中国的儿女们”。(26)
鲁迅对农民的文学想象基于“人的真理”的思想基础,是客观性很强的现实主义想象“人的文学”。钱杏邨提倡发掘中国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优点,塑造觉醒的乃至走向革命的新农民形象是左翼文学具有革命性质的文学审美转向,是一种对农民的阶级性革命想象。鲁迅的这种想象是指向“立人”思想的终极目标的,其中也已经包含了“革命”的因子,阿Q也是要求革命的,即鲁迅的“人的文学”与钱杏邨的“革命文学”之间是有一种相通的精神联系的。但是,钱杏邨等只是一味地要求表现革命的积极性因素,而把暴露黑暗的客观性很强的现实主义文学想象视为革命文学的障碍,非要宣布阿Q的死亡不可,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杜荃等人对鲁迅的攻击同样体现了这一“左倾”幼稚病。
在鲁迅、茅盾等人的批评下,创造社等“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所在,及时调整文艺路线,并取得了鲁迅等人的理解与支持。在这个阶级性的思想共识和审美原则的一致性基础上,1930年3月2日,鲁迅、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蒋光慈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成立使“革命文学”从狭隘中走向更为宽广的“左翼文学”,在承继和断裂中使“五四”文学发展为具有新型性质的“左翼文学”。在“左翼文学”的审美想象中,中国农民具有了新的性格特质:由“五四”文学中的落后、愚昧的形象转化为新的革命阶级意识觉醒者。
从“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愚昧、落后、不觉悟者,到革命文学中的觉醒者,乃至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中的反抗者、革命者,中国农民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现代化的客体到革命的主体、从“老中国儿女”到新中国主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翻身解放,获得了生命尊严和平等权利。但是,随着新时期以来社会的再次剧变,中国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当代人民文学、底层文学如何进行审美书写,如何艺术表现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等新弱势群体,成为新世纪文学审美想象一个无法绕开的中心问题。新世纪中国文学应从1920年代中国文学左翼化的历史审美镜像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启示,批判性地继承其所昭示的文学叙事伦理、政治倾向性和极为宝贵的“头朝下”底层意识。
注释:
①王铁仙《绪论:中国左翼文论的是非功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第2—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田仲济《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思想》,《文学研究会资料·中篇》第74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周作人等《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资料·上篇》第1页。
④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文学研究会资料·上篇》第73页。
⑤郑振铎《文学的使命》,《文学研究会资料·上篇》第71—72页。
⑥叶圣陶《创作的要素》,《文学研究会资料·上篇》第156页。
⑦⑧耿济之《〈前夜〉序》,《文学研究会资料·上篇》第75、77页。
⑨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卷》第346—34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⑩之常《支配社会底文学论》,《文学研究会资料·上篇》第80—82页。
(11)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文学研究会资料·上篇》第113页。
(12)(13)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文学研究会资料·上篇》第127—128、128—129页。
(14)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社资料·上册》第4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15)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社资料·上册》第46—47页。
(16)郑伯奇《国民文学论》,《创造社资料·上册》第80页。
(17)成仿吾《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8)郭沫若《文艺家的觉悟》,《创造社资料·上册》第122页。
(19)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社资料·上册》第169—170页。
(20)许幸之《艺术家与农民革命》,《创造社资料·上册》第151页。
(21)在左翼作家之外,郁达夫于1927年9月在《农民文艺的提倡》一文中提倡一种新型农民文艺:“文艺是人生的表现,应当将人生各方面全部都表现出来的。现在组成我们的社会的分子,不单是游惰的资产阶级,凶悍的军人阶级,和劳苦的工人阶级而已。在这些阶级之外,农民阶级,要占最大多数,最大优势。而我们中国的新文艺,描写资产阶级的堕落的是有了,讽刺军人的横暴残虐的是有了,代替劳动者申诉不平的是有了,独于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感情,农民的苦楚,却不见有人出来描写过,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的新文艺的耻辱……我希望大家能够格注意分一点出来,来提倡这泥土的文艺,大地的文艺。”参见《郁达夫文集》第5卷第282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
(22)(23)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第143、1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4)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第192页。
(25)青见《阿Q的时代没有死》,《“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第494—495页。
(26)茅盾《读〈倪焕之〉》,《“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第849页。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研究会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1920年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艺术论文; 阿q精神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鲁迅论文; 创造社论文; 读书论文; 革命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