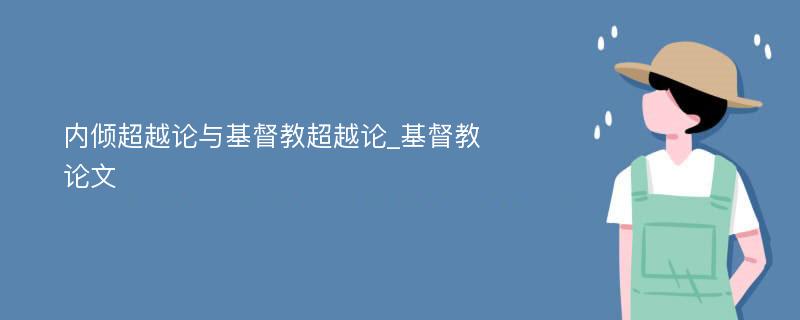
“内向超越”论与基督教超越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圣经·路加福音》4:4)在基督教看来,作为被造物的人必须靠与创造主有密切联系的关系而生存,一旦隔断了这种联系,人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也不会获得真正的满足感。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面对上帝创造的无限空间会产生无比敬畏,引发人心对上帝那无穷的追求,他由此反省到人心深处也确有一空处,惟有作为无限者与至圣者的上帝本身才使其得到满足。①然而,人对无限者上帝的追求却绝对不可能使人变成上帝本身,因为有位格性的上帝不能混同于内蕴于人的某种超越性境界或某种神性因素,这就使基督教超越观迥然有别于中国文化传统下的超越追求。新儒家就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超越方式为“内向超越”,而基督教的超越路向为“外在超越”,他们批评“外在超越”观使“一切的‘道’、‘理’都在上帝、耶稣、圣徒那边,都是外在于人的,而人心之内则充满了情欲和罪恶”。②
新儒家拈出“内向超越”论来概括中国文化传统的超越方式可谓精当,但对基督教超越方式的概括并不准确,其评价也失之于偏颇,下文对此展开论述。
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向超越”论及其特点
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向超越”论,是新儒家很推崇的说法。中国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境界被他们解释成“人天合一”式追求,对人可以达到“人之神(圣)化”境界有着很高期许,不妨称之为“人神”精神,与基督教文化传统的“神人”(道成肉身)精神有着深刻差异。这是借用俄罗斯神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说法,他用“人神”和“神人”概括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差异,③用在这里倒也一目了然。
用“人神”式的“内向超越”论来概括中国文化传统的超越追求仅仅是贴了漂亮的标签,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种超越追求的特点。笔者把这些特点总结为如下三点:
首先,中国文化传统追求超越和突破的出发点是从自然、宇宙(天)与人的神秘感应出发,正如葛兆光指出的,“宇宙是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来源”。④这里的“宇宙”就像中国古代的“天”,并非指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天,而是有情有义、化育万物的神性之天,从而方可与“君子”之心产生神秘感应,鼓励着君子进行不屈不挠的超越追求,所谓“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
其次,这种超越追求其实预设了人性可被教化乃至人可以成神的理念,这就是新儒家所谓对人性的“光明意识”,最终,向上和向外的超越追求收回和落实于人心。
新儒家大师钱穆对此解释说:“性善亦便是仁,便是人心之相互映发相互照顾处。故孟子又说‘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一切宇宙人生,便都在此人类自身的心上安顿。从人心认识到性,再从人之心性认识到天。如此便由人生问题进入到宇宙问题,这里便已到达了西方哲学上所谓形而上学的境界。”⑤钱穆的弟子余英时极为欣赏这种“内向超越”论,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突破’以后,超越性的‘道’已收入人的内心;因此先秦知识人无论是‘为道’或‘为学’,都强调‘反求诸己’、强调‘自得’。这是‘内向超越’的确切意义”。⑥
既然一切都要返回自我人心,“内向”确实是做到了,不过“超越”如何落实?其思路从“四书五经”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学》说“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诚”就成为连接“天道”与“人道”的天梯,心“诚”则灵,天道、人心交相呼应,自我意志通达宇宙生生大德,自救者“天”救之。
因此,就有了第三个特点:中国文化的超越追求就像中国文化史本身的“超越的突破”(transcendent breakthrough)一样最为温和,海外学者史华慈认为这和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超越与突破相比应算为“最不激烈”。⑦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中庸》),宗教道德化,超越追求人间化、生活化。冯友兰对此大为激赏,其解释也最精妙,他说日常生活的吃喝看似平常其实都是“道”,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这一大道,“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充分觉悟到事实是如此”,因此“教”的作用就是告诉人其实在不同程度上遵循了“道”,要对此有觉悟,此一觉悟说白了就是超越。那么,“为了达到与天地参,是不是需要做非常的事呢?不需要。仅只需要做普通而平常的事,做得恰到好处,而且明白其全部意义。这样做,就可以达到合内外,这不仅是人与天地参,而且是人与天地合一。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出世,而同时仍然入世”。⑧
“内向超越”论反思
“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出世,而同时仍然入世”——至此,中国文化的超越追求实际上取消了这一追求,一变而为觉悟,人靠己力感应自然神性,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神”境界。
就中国文化的内容来说,儒、墨、法这三家关怀社会,强调积极入世;道、玄、禅这三家关怀自然,强调消极出世,二者指向截然不同,很难合并在一起来说。但在超越追求的形式上,这六家却都蕴涵着“天人合一”式追求,其预设前提都相信人性可被教化,人亦可自我教化,个人在修身养性的过程中不断觉悟到“道不远人”的境界,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种觉悟内化为人格修为,就给自强不息的追求撑开了一片天地。这正是新儒家的“光明意识”,因着对人性可被圣化持有极为乐观的期许而大受赞扬。当然,“光明意识”并非一味摒弃“人性恶”而信奉“人性善”,而是相信哪怕原先属于“本恶”的人性,在后天不断学习和修炼中仍可抑恶扬善,从而达致美好境界。说到底,“光明意识”是一种深刻觉悟到的“道德意识”,这种主张认为哪怕再顽劣的本性,仍可以道德努力去完成自我圣化这一过程,如西晋周处斩蛟射虎,发愤改过,终成忠臣名将一样。
这就是新儒家另一位大师梁漱溟所谓“走向以道德代宗教之路”,也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泛道德化特点。⑨对“泛道德化”如何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泛道德化固然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点,究其实又暗含着很大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就证明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简单化约成个人道德问题,“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困境不是单靠提高某个人乃至某些人的道德修养就可以得到解决的。
不过,笔者认为,“内向超越”论和“泛道德化”的最大问题还是出在其人性预设上,对人性过于乐观的预设使“内向超越”和“泛道德化”论者过于忽略了人性的幽暗面。
通行的论调认为基督教文化强调“人性恶”,中国文化则强调“人性善”。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并不确切。中国文化中并非没有“人性恶”论,只不过这种“人性恶”论的提出是为了提醒后天学习和修炼的重要,还是回到对人可被教化的“光明意识”上来。基督教文化传统强调“幽暗意识”不假,但也没有完全排斥“人性善”论。《圣经》认为人为万物之灵长,盖因人之被造与万物不同,人按上帝形象被造,人像上帝,这便使人性得到极大尊崇,因此美国《独立宣言》才宣称“人人被造而平等”而不该误译为“人人生而平等”。但《圣经》又强调人的原罪和堕落,强调人与上帝的绝对距离,此乃对人性采取某种“幽暗意识”。师从美国神学家尼布尔的中国学者张灏在《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总结“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阴暗面和人类社会中根深柢固的黑暗势力的正视和警惕”,⑩也就是说,“幽暗意识”的要旨在于否决人变为神的一切可能,对人自我圣化的能力保持高度警觉,拒绝用道德意识化解人性危机,断然拒斥人在死亡和罪孽问题上的自救力,对基督教来说,才有了圣子道成肉身之代赎。人的堕落和沉沦在《圣经》中被认为是不争事实,也是原罪和本罪在人性中泛滥的结果,根源正在于人的自我中心和自我神化之举。而处在原罪和本罪阴影下的人,还能像上帝吗?还像,否则连神化的冲动都不会有,他们并没有完全失落上帝形象,还拥有真、善、美、圣、爱的碎片。但问题是人无法靠己力把真、善、美、圣、爱聚成生命整体,无法在废墟上重建“巴别塔”。
在批评基督教所谓“外在超越”观过于悲观前,我们先要反思“内在超越”论是否过于乐观了?从社会层面来说,人凭着理性和道德教化真能在地上建立天国吗?为什么那些宣称已经进入了天国的人们最终都会在地狱般的梦魇中醒来?从个人超越追求层面来看,君子“依自不依他”,“诚于中,形于外”,完全依靠这依稀连接“天道”与“人道”的“诚”之天梯,并没有一个作为“绝对的他者”的真理监督,万一陷入“真诚的自欺”并“自欺”到自以为“真诚”怎么办?或者,干脆看开了,认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不超越为超越”,那何必还追求?因为“不追求就是追求”,为何一定要“非如此不可”?于是,“内向超越”论的“内向”就有吞噬掉“超越”的危险。毕竟,超越就像爱情一样,不可能仅仅在个体内心深处自我完成,“超越”就意味着既要“向上”又要“向外”。
从根本上来说,对人性的这种“光明意识”对人性和人的升华能力寄予了太高期望,时刻以天人合一境界来要求人自己,表面看有劝其修身养性的作用,但一方面会带来骄傲或焦虑,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伪善。“内向超越”论的保证、落实若仅以君子的诚实为尺度,就有流于虚妄的危险。中国文化精神有极高的道德追求,旨归还是在人间,理论上可以“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中庸》)。但在实际操作上很容易使“天命”被“率性”淹没,“高明”被“中庸”消解,神圣被凡俗解构。成官泯就看到了中国文化这一症结所在,才批判中国文化精神说:“神圣和世俗的界限和张力,正是基督教文明的核心所在,属世的一切只有通过超越才能得其意义。否则,吃喝闲逸,乃至烟花柳巷,都成了文化之精深,妙道之至境,崇高神圣的维度安在?现实生活中果圣俗无碍了,所谓德行安在?”(11)
基督教超越观辨析
因为强调“向上”和“向外”的超越追求,基督教超越观常被新儒家讥评为“外在超越”观。下边,我们就通过《圣经》来考察一下“外在超越”观这种说法为何失当。
《圣经》认为上帝照自己的形像造人,人选择背叛上帝,始祖亚当代表人类犯罪堕落,从此,人就无法再合乎上帝造人时定的神圣标准。于是,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在十架上作为羔羊献祭牺牲,死后三天复活,打通救赎通道。但这还没有结束,《圣经》又记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圣父和圣子差遣圣灵从天而降,感动人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代赎,人在认信和接受后,被上帝称义,开始其今世成圣之旅。这种成圣不是自我圣化,而是受圣灵感化。因此,基督教认为没有抽象的人性,必须把人置于“创造-堕落-救赎-成全”等四种不同状态中来讨论,基督教超越观也因其状态不同而有不同特点:处于“堕落”层中的人,只能模糊感知“创造”层的真、善、美、圣、爱,却不能靠自己成就“救赎”。“堕落”层中的人无法向“创造”、“救赎”和“成全”状态产生突破,惟有领受“救赎”后才能开始真正的突破和超越。而领受“救赎”后的超越则是圣灵内住下的超越,人以其“肉身”践履“圣道”,和“堕落”状态下的自我超越方式并不相同。
为了把这种超越方式说得更清楚,《圣经》干脆以“重生”来说明。《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犹太大学者尼哥底母深夜造访耶稣,叩寻人生在世的超越真谛,耶稣直接抛出“重生”二字来回答其征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人的重生不是靠再进母腹生出来,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须仰仗圣灵能力。圣灵成为人超越之必需。外在圣灵进住人心,超越就从“外在”变成了“内向”,于是对基督救赎事工的认信就不再是对外部信条的认信,而是与基督产生一种内在生命的连接,这是神学家们一再声明的,也是基督徒一再强调的,因此帕斯卡尔才在神秘的“火之夜”写下“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这样的句子。神学家卡尔·亨利也说:“未曾重生的自我需要属灵及道德的恢复,它应该回到对上帝的爱和事奉中。在《圣经》中失去的自我是指人与上帝和其他人的疏离(《圣经·马太福音》16:26);因此正确的出路并非失去自我,而是自我被基督救赎。但耶稣也说,我们的死是结出果子及得永生的路:‘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圣经·约翰福音》12:25)。”(12)
圣灵作为神圣位格的引入,就使得基督教谈论起超越来,即如温伟耀这样的基督教学者认为的那样,指的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境界式超越”,而是基督教的“对话式超越”。(13)“对话式超越”的根本就在于人与上帝生命关系的恢复与重建。
基督教信仰可从两个层面来言说:一是指个人与《圣经》所宣称的耶稣基督建立救赎关系,重在信“谁”;二是指认信教义,即创造论、“原罪”说、救赎论、教会论和末世论等,重在信“什么”。英文钦定本《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后半节到十三节,保罗对提摩太讲得很清楚——For I know whom I have believed,and am persuaded that he is able to keep that which I have committed unto him against that day.Hold fast the form of sound words,which thou hast heard of me,in faith and love which is in Christ Jesus.中文和合本《圣经》译为“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规模”一词在《圣经·提摩太后书》的希腊原文中有“概略”之意。这两节经文表明,信仰既是关系,又是命题。从基督教超越观来看,其超越追求关键在于人与上帝的对话与交往关系。首先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超越追求,其次才是文化论意义上的超越观念。用德国神学家马丁·布伯的话说,超越追求是“我与你”的关系而非“我与它”的关系。英国文学家路易斯在《纯粹基督教》中干脆说基督教的超越追求不是“传递”“一套观念”,而是“注入”“生理的或超生理的”新生命。(14)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干脆认为基督教超越观是基督教超越追求的敌人,真正的基督教超越重在爱的关系中活出新生命,把个人从“我们”式的“拉平”(或译“平夷”)中脱离出来,直接面对造物主从而获得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15)超越就是生成个体的过程,也是受苦中与人连接的过程,但其本根在与上帝的关系,其次才是关乎生存的观念和命题,言说观念和命题要力求表达鲜活的生存本身,不是为概念在体系中找位置、贴标签,而是促使人去爱,去相信,去行动,去“道成肉身”,爱和知识在践履中合一,教义成为立身实存的生命意识。
因此,用“外在超越”观概括基督教超越方式并不恰当,相反,基督教力求避免把立身实存的“对话式超越”外化为抽象的观念和教义认同,也力求不因高举上帝的真理性和美善性就贬低人的超越追求。基督教贬低的不是人的超越追求,而是拒绝相信人能变成上帝从而为“堕落”状态下的人性扩张立一道界限。处于“救赎”状态中的人,依靠圣灵内住开始其超越追求,弃旧从新,依靠的不是文化论意义上的超越理论,而是靠与有位格性的真理交往。《圣经·创世记》三十二章就记载了雅各和上帝摔跤的故事,经过这一事件之后,雅各就成了一个新人,他的生命更新与突破之所以发生,与其说来自于雅各自身的努力,不如说是来自上帝亲自的发动和成全,不过这种成全确又是借着他的努力追求来完成的。所以,雅各才惊呼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圣经·创世记》32:30)
基督教否认处于“堕落”状态下的人靠着理性和道德就能找到真理完成超越,这一点饱受新儒家批评,认为把人贬低得太厉害,使人失去了超越的信心和基础。但从基督教超越观来看,这种对人性的“幽暗意识”恰为迎候真理的突入提供了新的契机。于是,真理来寻找人,把人迁移到“救赎”状态,圣灵内住于信徒内心也就保证了超越追求从“外在”到“内向”的转化。
总之,“内向超越”论说起来头头是道,但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新儒家常攻击基督教超越观为对象式思维,实在是没能看到真理作为卡尔·巴特所谓“绝对的他者”的庄严、威严和尊严。“内向超越”论如何避免一切都是自说自话的陶醉而持守“外在超越”路向下的谦卑,这是非常要紧的问题,关乎人立身实存的精神命运。而且,到底如何从“内向”开出真正的“超越”?说法很多,却难有真正落实。对君子诚实人格的过高期待,形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自圣精神,和基督教文化传统下的忏悔精神迥异。
批判首先应该对自身进行批判,反思最好先对自我进行反思。“内向超越”论者为何常常难逃林毓生所说“我族中心主义”情结,为何缺少一份“谦心”、“仁心”和“公心”?“我们在忧愤之余,要切实体认我们的文化危机的确是既深且巨的。任何未经深思熟虑的反应都势将无济于事。”(16)毋庸讳言,不管中国传统文化目前受到多大青睐和重视,若其超越方式的内在难题不解决就照搬于今肯定是行不通的。
注释:
①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1页。[Blaise Pascal,Pascal's Penssees(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85),101.]
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18页。同时参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18页。[Yu Yingshi,Shi and Chinese Culture(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ress,2003),618; also see Yu Yingshi,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Nanjing:Jiangsu People's Press,2004),14-18.]
③梅列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杨德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38页。[Dmitry S.Merezhkovsky,Tolstoy and Dostoyevsky,trans.Yang Deyou(Shenyang:Liaoning Education Press,2000),37-38.]
④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页。[Ge Zhaoguang,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2001),51.]
⑤钱穆:《灵魂与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页。[Qian Mu,Soul and Mind(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4),9.]
⑥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617页。[Yu Shiyiing,shi and Chinese Culture,617.]
⑦Benjamin,I.Schwartz,"Transcendence in Ancient China",Daedalus,Vol.104,No.2(1975):57-68.
⑧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1-153页。[Feng Youlan,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6),151-153.]
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6页。[Liang Shuming,The Substance of Chinese Culture(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ress,2005),96.]
⑩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59页。[Zhang Hao,The Consciousness of Darkness and Democratic Tradition(Beijing:New Star Press,2006),59.]
(11)成官泯:《独语录·译序》,见奥古斯丁:《独语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Cheng Guanmin,"Preface to Translation," in St.Augustine,Monologium(Shanghai: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1997).]
(12)卡尔·亨利:《神、启示、权威》(四),康来昌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7年),第286页。[Carl Henry,God,Revelation and Authority,vol.4,trans.Kang Laichang(Taipei: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1997),286.]
(13)温伟耀,《“境界性超越”与“对话性超越”——基督宗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排他”与“兼容”》,收录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编《“文化研究与神学研究中的公共性问题”——2005年暑期国际研讨班论文集》,第6页。[Wen Weiyao,"Realm Transcendence and Dialogical Transcendence:The Exclusiveness and Inclusivenes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Context." This is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5 Summer Institute of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held by School of Liberal Art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4)C.S.Lewis,Mere Christianity and The Screwtape Letters(Harper San Francisco,U.S.A.2003),64.
(15)Kierkegaard,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ed.and tran.Howard V.Hong etc.2 volum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344; Kierkegaard,Two Ages:The Age of Revolution and Present Age,ed.and tran.Howard V.Hong etc(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86.
(16)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389页。[Lin Yusheng,The Creative Trans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88),389.]
标签:基督教论文; 儒家论文; 圣经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内向论文; 人性观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人性论文; 中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