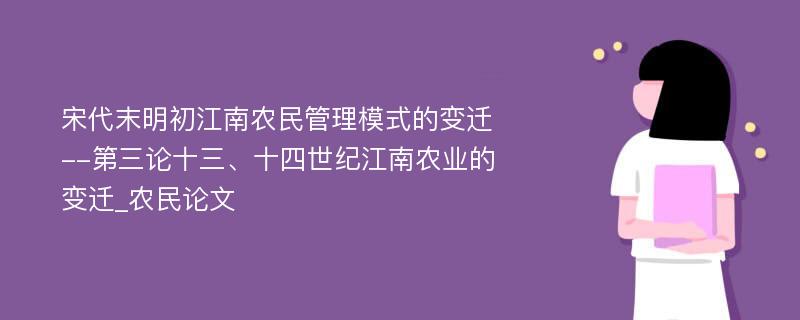
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之三论文,农民论文,方式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十三、十四世纪,在人口、耕地和技术发生变化的同时,江南农民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个变化涉及众多的方面,例如租佃制度、商业化、农村工业,等等。在这里,我们仅挑选其中的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这两个方面就是农民的经营规模和农田的生产能力。之所以挑选这两个方面,一则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经营方式的主要内容;二则也因为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对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比较忽视,而且还有一些错误的看法。
(一)经营规模的变化
虽然经营规模问题是农业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奇怪的是,在过去关于江南农业经济史的研究中,尽管许多著作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专门讨论的论著却不多。因此,尽管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或倾向于认为自南宋以来江南农民经营规模狭小(有的学者甚至将经营规模狭小视为宋以后江南农业停滞的主要原因),但事实上这种看法并未经论证,只是一种假设而已。
至少自唐代以来,江南的农业生产就是以单个的小农家庭为经营单位,因而一个农场也就是一个农民家庭所耕种的田地。尽管由于土地所有权的不同,有大地产与小地产之分,但从经营方式来看,大地产上的佃农与小地产上的自耕农,都同样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并没有太大差异。因此我们在讨论农业中的经营规模问题时,没有必要对农民的身分作出区分。
宋末、元代和明初,江南一个农户平均耕种多少田地?首先,我们先根据官方人口和耕地数字,来作一个粗略的估计。然后再根据其他文献中的记载以及今日学者所作的各种推测,来作进一步分析。
梁庚尧收集了南宋一些地方户均耕地数字,其中有关江南者如下(表1)。
表1.
地点 时间户均耕地
常熟县
1174—1236
45亩
华亭县
1190—94 48亩
江阴军
1228—33 20亩
建康府
1260—64 37亩
江宁县
1260—64 38亩
上元县
1260—64 41亩
溧阳县
1260—64 28亩
句容县
1260—64 40亩
溧水县
1260—64 12亩
*原户均耕地数字中的小数点后部分,已据四舍五入原则略去。
梁氏并总结说:在属于丘陵地区的江阴军,户均耕地较少;而在属于平原的平江府、嘉兴府及平原、丘陵各半的建康府,户均耕地较多,在30余亩至40余亩之间。(注: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4年,第100~106页。不过,梁氏说江阴属于丘陵地区而建康属于平原、丘陵各半地区并不符合事实,因为从大的地理范围来看,江阴虽属于长江沿岸高田地带,但仍然是江南平原的一部分;建康则属于宁镇丘陵地区。)。
元代有关数字很少,这里我们仅能根据至顺《镇江志》中的数字,算出镇江府的户均耕地数(表2):
表2.
田地数 户数 户均耕地数
3,431,509亩 100,065户
34亩
出处: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与卷5总属。田地数系中的“田”与“地”数之和,户数系“土著户”之数。
明初的情况比较清楚。根据从翰香使用的明初官方人口与耕地数字(注:见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刊于《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据该文所列出的数字, 江南各府的人均耕地面积为:(单位:亩/人)应天府:6.09、苏州府:4.18、松江府:4.20、常州府:10.28、镇江府:7.36、杭州府:5.90、 嘉兴府:3.88、湖州府:7.55。),并依据后文所言,明初江南一户平均约有5口,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知明初江南每户平均拥有耕地的数量为(表3)。
表3. (单元:亩/户)
地点户均拥有耕地 地点 户均拥有耕地
应天府
31
苏州府 21
松江府
21
常州府 51
镇江府
37
杭州府 30
嘉兴府
19
潮州府 38
说明:所得户均耕地数字中的小数点后部分,已据四舍五入原则略去。
对比表1、表2和表3,我们可以看到:在宋、 明都有数字的建康(应天)府,宋末与明初户均耕地数变化不大,仅有轻微下降。但在华亭(松江),自南宋中期到明初,户均耕地数竟减少了一半多。而在镇江府,从元代中期到明初,户均耕地数反而有轻微上升。这些情况,如与《探讨之一》的表1、表3和表5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况相比较, 可以看出人口变化与户均耕地数变化趋向是大体一致的。
当然,由于官方人口与耕地数字不完全和不可靠,我们还须参照其他文献进行研究。在这方面,宋史学者们已提出了不少看法。但是由于各位学者所用资料和观点的不同,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常常相互矛盾。例如,傅宗文估计宋代江南一个劳动力可以耕种水田20—30亩(注: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6 页。)。但柳田节子和草野靖却认为宋代稻农一户最低经营面积为30亩(注:柳田节子:《宋代乡村の下等户にへいて》,《东洋学报》40卷2号, 1957年。草野靖:《宋代民田の佃作形态》,《史艸》第10辑,1069年。)。漆侠认为宋代两浙路大部分农民的耕地数在19.5—25亩以下(他未说明是北宋还是南宋,不过看来是南宋)。但是在同书的另外一个地方,他又估计南宋江南一户农民通常种田30—50亩(注: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218~219页。)。而他所引用的一些例子,还表明一些农民种田之数大大超过此数(注:漆氏所引用的例子如:常熟农民过氏一家种田60亩,嘉兴佃农钮七种早稻80亩,等等(同上书第331、1204页)。)。 梁庚尧则认为:“南宋时期一个农人有能力经营30亩的土地,而事实上许多农民所经营的耕地面积,远小于此一数字”。少到多少呢?他又说:“在人口集中的江、浙、闽、蜀等地区,……一户所经营的土地甚至只有数亩或十余亩”(注: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129、155页。)。不过这个看法显然与他前面表列的情况及结论相互冲突。综观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南宋后期的江南,每户农民平均大约有耕地30—50亩之间。取其中数,每个农民平均有田40亩左右。这个数字,应当是较为接近实际的。
元代情况较为不清。据有限的记载来看,在江南平原上,农民实际户均种田面积比南宋有所减少。据宋末元初方回的记述,在嘉兴一带,“一农可耕今田三十亩”(注:方回:《续古今考》卷18《附论班固计井田之入》。)。而稍后人袁介《踏灾行》诗(注:见于陶宗仪《辍耕录》卷23“检田吏”。),在十四世纪初的松江高田地带,官田上的佃农,一户种田也正好是30亩。若与该地(宋华亭县)在南宋中期户均耕地数48亩相比,尚不及后者的三分之二。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农户平均耕地面积在缩小。
到了明初,尽管元末人口的减少应当使得户均耕地增加,但江南平原上农户平均种地数量减少的趋势却变得更加明显了。例如,据明代官方统计数字,1393年苏州府每户平均有田地21亩,因此每个农户平均种田应在20亩以上。但是在占苏州耕地70%以上的官田上,佃农每户种田数却在20亩以下。洪武时,政府授予太仓8,986户人民以官田,标准是“见丁授田十六亩”(注: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收于《明经世文编》卷22。)。1398年将常熟县官田分给军士屯种,“每军受田一十二亩或一十五亩” (注:况钟:《况太守集》卷8《请军田仍照例民佃奏》。)。一户佃农佃种官田数量的上限,政府规定最多为30亩(注:《明世宗实录》卷27。)。从现存的个别实例来看,农户平均种田数量也确实在减少。例如,按明初的官方统计数字,松江府每户平均有田地21亩,而洪武初年松江华亭县农民孙慎一,一家四口,所种全是官田,共19.8亩(注:见《孙慎一户贴》(收于天启《平湖县志》卷10风俗)。),刚好达到此平均水平而仅及元代同地官田佃农种田数的三分之二。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宋末至明初,尽管人口和耕地的数量及其比例变化不一,但江南平原上的农民户均种田数量确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上面的估计,可知在江南平原上一个农户平均种田的数量,南宋后期约为40亩,元代中期约为30亩,而明初则约为20亩。与此相对照,在江南西部的丘陵山地,自宋末至明初,农民户均耕地数变化并不很大,看来都在40亩上下。例如,至顺时镇江路每户平均有田地34亩,与相邻的建康府在南宋时的平均数相差不太多,因此估计在宋末和元末之间变化不很大。而明初该府户均耕地数为37亩,相差也不很大。建康府(应天府)的户均耕地数,宋末到明初从37亩降到31亩。较之江南平原上的变化,这个减少幅度也颇为有限。由此可见,这两府的户均耕地,自宋末至明初,都是30—40亩之间。如果除去城市人口和乡村中不劳动的人口,那么每个农户平均有田数,肯定要高一些,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大约在40亩上下。黄震说:“浙右之地,滨江皆山,如镇江、江阴及常州之晋陵、武进,循江而东,岗脉隆起,地硗而多干”(注: 《黄氏日抄》卷73《申省控辞改差充官田所干办公事省札状》。)。因为这个地区水土状况及农作方式等变化不像低田地带那样大,所以每个农户平均耕地面积比较稳定,是可以理解的。这里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江南平原上农户的经济规模会出现缩小的趋势呢?
导致普通农户种田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家庭规模的变化,另一是农民生产能力的变化。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变化。
第一,农民的经营规模与其家庭规模有密切关系,因此在讨论农民经营规模变化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弄清一个普通农户的家庭规模有多大。一般而言,一个普通的小农家庭,一般仅包括一对夫妇及其未成年(或未成家)的子女和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父母。但是农民家庭规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户家庭规模究竟如何?是否发生过什么变化?都还须讨论。
由于宋代的户口统计通常只涉及“丁”(男丁和女丁),所以南宋江南官方户口数字中人口数字,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人口。一户平均到底有多少人?一些宋史学者进行了考证。其中,何忠礼认为:一般地说,宋代每户约有2个“成丁”,加上“不成丁”,男口约有3人;再加上女口,总人数约有5—6人(注:何忠礼:《宋代户部人口统计问题的再探讨》,收于《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出版。)。但是据何氏所引史料,江南每户口数大大超过这个全国平均数。例如北宋中期的常州晋陵县,有户2万,丁10万,平均每户有丁5人,加上其他(不成丁、女口等),一户当有10人以上(注:胡宿:《文恭集》卷35《常州晋陵县开渠港记》。又据苏颂《苏魏公集》卷10杂事:苏颂之祖,雇得一婢,自云其家有十人。)。而在毗邻杭州的明州慈溪县,南宋后期平均一户有7.5人(注:宝庆《四明志》卷5、卷16引胡榘《奏状言明州慈溪县户口》。) 。梁庚尧认为:南宋农村每户口数大约多在4—10口之间。 但从该书第80—81页表6所载胪列的13个数字来看,临安府饥民每户平均人数(6人),高于大多数江南以外的地方饥民每户平均人数(注: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82页。)。因此江南每户口数应当在4—10 口的范围内居于偏上地位。傅宗文则认为:宋代农民家庭人口数有增加的趋势,一家十口是常情。而在其所引史料中,关于南宋江南的农家者又居多数(注: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第305页。)。因此,大体而言, 在南宋后期的江南,一个普通农户的平均人口在5口以上。 而其中的成年男女劳动力,大约有3人。
因史料缺乏,元代的情况很不清楚。从王逢描写松江乌泥泾棉纺织业的诗句“十口勤劳指头直”来看(注:王逢:《梧溪集》卷7 《半古歌》。),农户的规模仍然普遍较大。据至顺《镇江志》卷3 户口中的数字计算,每户平均有6.1人(土著户)和5.7人(民户)。从这些推测,元代江南每个农户的平均口数,可能与南宋后期相差不多。
到了明初,情况变得比较清楚了。据官方统计数字,苏州府1371年每户平均有4.15人,1376年有4.32人;松江府1391年每户有4.82人,同一年常州府有4.36人,杭州府有3.78人。因此明初江南每户人口,大体上在4—5人之间。也就是说,江南一个普通农户的总人口,约为五口。这种规模,在明清和近代江南没有多大变化。所以在江南,所谓“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实际是从明初才形成的。其中主要的农业劳动力,就是这个家庭中的丈夫和妻子(注: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载《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农民家庭规模的变化(特别是家庭中主要劳动力人数的变化),对农户的经营规模(即一个家庭农场的规模)的变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农作技术未有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三个劳动力耕种田地的数量,当然比两个劳动力要多。如前所述,南宋后期江南平原上一个农户大约种田40亩,元代30亩,而明初20亩;明初数仅为南宋后期数之半。如果以每个劳动力计,那么南宋后期应为13亩,明初为10亩,大约减少了1/3。元代则介乎其中。
第二,决定农户经营规模的又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户的耕作能力。各种特定的生产方式,都要求相应的经营规模。反过来说,某一特定的经营规模,是由农民在某一耕作方式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
如前所言,直到明代后期,江南平原大部分地区仍实行水稻一年一作制。而在这种耕作制度下,一个农户(有夫妇两个劳动力)如果无牛,可种稻25亩上下;若是有牛,则所能种者还要更多。但是在水稻与春花轮作的“新一年二作制”下,一个成年男劳力只能耕种10亩上下。如果超过了10亩,农民就无力耕种,只好将超出的部分出租(注:李伯重:《明清江南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载《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 《“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载《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因此农户耕作能力的上限, 决定了其经营规模的上限:在水稻一年一作制下,是20亩以上;而在水稻与春花的一年二作制下,则是10亩左右。宋末至明初江南一个农户平均耕田20亩以上,是符合当时农民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来看,南宋江南一户农民一般种田40亩左右。到了明初,家庭规模变小,同时也由于稻麦复种制比以前进一步普及,一个普通农户平均种田数减少到20亩或20亩略多,是符合逻辑的。至于处于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元代,农户耕田数也应当介于其中,因此方回才会说“一农可耕今田三十亩”。到明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清代),随着妇女之转向手工业和蚕桑业,大田农作越来越变成男子的专业,因此农户的经营规模也逐渐只与男子的耕作能力有关。在此情况下,农户的种田面积进一步缩减。作为其结果,“一夫十亩”遂成为江南农户的标准经营规模模式(注: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载《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从本质上来看,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户平均种田数量逐渐下降的现象,表现了农民对最佳经营规模的追求。我们知道,只有在最佳的经营规模下,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在研究农业经营规模的问题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首先,任何一种既有的农业经营规模,都是各种特定的条件的产物,因此所谓“最佳经营规模”,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相反,由于各种条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最佳经营规模”的标准也因时因地而异。其次,即使是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商业化水准较高的江南地区),农民为了获得最理想的经济效益,也在不断地努力追求某种最佳经营规模。“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从此意义上来说,每个时期和地区农民的经营规模,相对于其所处的特定条件而言,都可以说是在向“最佳经营规模”靠近。简言之,一种经营规模之所以能够出现和普及,最根本的原因,是其经济上的合理性。
(二)亩产量的变化
判断农民经营规模是否合理,最重要的标准是农民一年中生产的产品数量是否增加。在农户种田数量减少的时候,只有通过提高亩产量,才能增加总产量。因此亩产量的问题,对于研究江南农业生产的变化来说至为关键。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宋末至明初江南水稻亩产量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非常薄弱的方面。
关于南宋江南稻米亩产量,研究者较多,但彼此意见分歧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是2石左右。例如余也非估计南宋江南亩产量为2石米(注: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吴慧认为亩产2石应是中等水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梁庚尧认为南宋最高亩产量为3石,而浙西地租也多在0.6—1石之间。 如按一般的计算方法(即产量为地租之倍),则浙西稻米亩产为1.2—2石之间(注: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145页。)。 斯波义信对大量的亩产量记载进行了分析,也认为南宋末期和元代为2石(注: 斯波义信:《宋代の消费、生产水准试探》,载于东京都立大学《中国史学》(东京)第1号,1991年。并参阅其《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第90~91、137~141页。)。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在2 石以上。例如闵宗殿认为南宋太湖地区稻米平均亩产2.5石(注: 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中国农史》1984年第4期。)。傅宗文估计这一地区亩产3石米(另有1石麦)(注: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第310页。)。漆侠的估计更高:江浙稻米亩产量, 南宋初期为3、4石,而南宋中后期则达5、6石,而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地区,更达6、7石之高(注:漆侠:《宋代经济史》,第2、26、138页。)。
在做出这些估计的学者中,余、傅、漆三人并未提出有力的证据以支持其说(注:例如,余也非赖以做出其估计的依据,只有一条史料。傅宗文主要依据的史料也只是周弼《丰年行》中的诗句“长田一亩三石收”,而此诗所说的是丰年产量,而且地点时间也不明确。而依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44《桂阳军劝农文》所说:“闽、浙上田,收米三石”,即使是丰年,亩产3石也应是好田的产量,而非普通田地平年的产量。漆侠关于“亩产五、六石”的结论,所凭的只有高斯德《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中说到的“(浙间)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 六石”一条史料。而天野元之助已指出此条史料所说的是谷而不是米;如果折为米,只有2.5—3石,与王炎、陈傅良等人所说相同(天野天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增补版),御茶の水书房(东京),1979年版,第256页)。其所说“亩产六、七石”(漆氏未列出处。 实则为明州记载),则是宋代史料中亩产量的最高记录,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条这样的记录。用这样的记载作为普遍情况,我们认为是不妥的,况且对这条记录来说也存在着天野所指出的问题。)。闵、吴二人所用史料基本一致,但史料数量颇为有限,难以说明普遍情况。因此,比较有说服力的,是斯波氏和梁氏的估计。不过,梁氏没有做出直接的估计(上述1.2—2石的平均亩产量是我们根据梁氏对地租的估计而得出来的), 唯一可靠而又明白的估计,应是斯波氏的估计。不过,正如斯波氏所指出的那样,每亩2石左右的平均产量,看来只能是普通亩产量的上限。 斯波氏根据1237年的139个常熟学田地租数字进行了亩产量分析, 结果是亩产量在0.62石以下者占53%,0.62—1.20石者占27%,而1.20—2.25石者占20%。而全部114个事例的平均亩产量,只有0.65石(注: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91、142~143页。)。学田地租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并非偶然。我近来从《重修琴川志》卷12“役”所收张攀撰《归政乡义役记》(撰于嘉定三年二月初二日)和刘宰撰《义役记》(撰于嘉熙二年正月十五日)二文中发现的材料,有力地证明了亩产2石确乎不是普遍情况。据张文,在南宋后期的常熟县归政乡,438亩义役田的平均亩产量为1.36石;而据刘文全县50都的义役田地51,310余亩,平均亩产量为1.0石。这两个数字虽然高于上述学田的平均亩产量, 但仍然大大低于2石的亩产量(注:亩产量以地租之倍计。 全县的产量包括麦在内。)。我们知道,常熟是江南重要的水稻产区,早在唐代,就因收成通常都较好而得“常熟”之名。北宋人沈垌说:“姑苏之北有大邑焉,曰常熟,山长而水远,泉甘而土肥,民富物庶,人乐其业”(注:《重修琴川志》卷13“道”所收崇宁5 年沈垌撰《乾元宫兴造记》。)。而南宋人程公许更说:“浙居东南隘,水逾于地,引以为田,厥土衍沃。姑苏产甲两浙枝邑,常熟复甲姑苏,即名可知也”(注:《重修琴川志》卷12“役”所收淳祐9 年程公许撰《常熟重开支川记》。)。由此可见,常熟的亩产量在整个江南是中等或中等以上。而一般来说,学田、义役田在当地田地中也应属于中等或中等以上(注:例如,宋代中国最高的亩产量记录,是吴县学田的4.52石(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38页。)又, 漆侠也指出:“中等水平的田地在两浙学田中占优势”(漆侠:《宋代经济史》第363页)。)。如果常熟的学田和义役田的亩产量只是在0.65—1.36 石之间,那么说整个江南的平均亩产量为2石或者2石以上,看来是难以成立的。因此,我们比较有把握的是:南宋后期江南的稻米平均亩产量,应当远低于2石,很可能只是1石多些而已。
我们这个较低的估计,是否与南宋文献中那些亩产2石或2石以上的高产记载相矛盾呢?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在地域上,这些高产记录多数集中在苏州、嘉兴以及湖州,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仍然可看到不少1石以下的低产记录。在此外的地区,亩产少有达到2石者(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38、140~141页。)。 特别是在建康、镇江以及常州等地,亩产更低。例如黄震说:“常、润渐北,则地渐高,而土渐硗,所收亩多止五大斗或四三斗”(注:黄震:《黄氏日抄》卷84《与叶相公西溜》。)。南宋交租有的地方用“大斗”,1 斗大约相当于1.3常斗(注:漆侠:《宋代经济史》,第375页。)。亩租最多5 大斗,即亩产量最高为1.3石。若是亩租3—4大斗,则亩产量为0.8—1 石。南宋初期镇江的亩产量,又还大大低于此(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一九:绍兴6年(1136)10月10日攀宾言条, 诏令江南东西路与镇江府所属县份,“有不成片段闲田,委官逐县自行根据见数,比民间体例,只立租课,上等立租二斗,中等一斗八升,下等一斗五升,……召人耕种”。固然为鼓励开垦,租额可能较低,不过镇江等地整个地租水平低下,也是可以肯定的。)。其次,有些江南高产之说,出于一些官员之口。他们在江南之外一些地方劝农时,往往以江南作为榜样来劝导当地人民努力耕作,力争像江南农民一样获得高产(注:关于南宋的劝农文,参阅宫泽知之:《南宋劝农论——农民支配のイロキ—》,收于中国研究会编《中国史像の再构成——国家と农民》,文理阁(东京),1983年。)。这种劝农文字,既然意在劝诱,自然要将榜样尽量说得好些,因此不能把文中所说的情况完全当做真实。
元代江南水稻亩产量,记载很少。李干认为“两浙地区亩产一般为三、四石以至五、六石,个别地区达到七、八石”(注: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9页。)。 但是他既未标出所说产量到底是谷的产量还是米的产量,也未说明他依据什么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这个估计实际上只能是一种猜测而已。余也非、吴慧估计为米2石,与南宋相同(注: 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166页。)。他们所引用的证据, 主要是《黄金华先生文集》卷10“义田”、方回《续古今考》卷2《计佃户岁入岁出》、 《两浙金石志》卷14《湖州路报恩光孝禅寺置田山碑》三条材料,并从地税进行推测。但是,在现存文献中记录元代江南田租数字最为具体可靠的《西湖书院增置田碑》和《西湖书院义田记》,他们却未涉及。据这两个文献,西湖书院在各地的田产,每亩平均收租数量如下: 杭州1(?)——0.29石,仁和县——0.8石,乌程、昆山县——0.65石, 杭州2(?)——0.78石,宜兴县——0.48石。全部田产2,182亩共收租1,271石,平均每亩收租0.58石(注:《西湖书院增置田碑》,见于《两浙金石志》卷15;《西湖书院义田记》,见于《黄文献集》卷7。)。 亩产量以地租之倍计,则平均亩产为1.16石。由于该书院田产分布较广,因此可以说其上的地租和亩产量更有代表性。据此,元代江南水稻亩产量可能与南宋后期大致相同,都是1石多一些(注: 在元朝江南仍然沿用宋代度量衡制(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165~166页),因此我们可以把以上数字直接作比较。)。
明初江南水稻亩产量的记载也很少。因此之故,我们未见有人对此做出估计,遑论专门的研究。我们认为:较为可靠的做法,是根据官田赋税来进行推求。明初江南官田数量巨大,因此其情况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注:在除杭州外的江南7个府中, 官田在全部耕地中所占的比例如下:最高的松江府为85%,其次苏州府为63%,接下去镇江府为32%,应天(江宁)府为29%,嘉兴府为27%,湖州府为24%,常州府最低,为15%。森正夫:《明初江南の官田について——苏州、松江府にぉけるその具体像》,载于《东洋史研究》(东京)19辑3号,1960年; 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27页。)。官田的赋税, 通常是私租的50—80% 。这里姑以70%计(注:1425年,周干等人在对江南八府进行了半年调查之后,进奏明宣宗说:“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宫,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其八也”(《明宣宗实录》卷6洪熙元年闰七月丁巳条)。尽管这里所说的是“抄没田”, 但据森正夫《明初江南の官田にへいて——苏州、松江二府にわけめの具体像》,“抄没田”与“宋元官田”在官田中所占比重相近,共同构成官田的主体,而二者的税额是相似的。又,《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则说:“凡为民国平田佃种者率完租米一石,官田重(者)至七斗。其高低民田佃种者率完租七八斗,官田轻至四斗。其视佃民田者,已属轻额矣”。)。赋税最重的苏、松二府,明初每亩官田平均负担的赋税分别为0.44石和0.31石(注:前引据森正夫文。)。据此,则此二府一般亩产量应为1.3石和0.9石。嘉兴府及该府属下的海盐县官田最高租额分别只有0.5石和0.7石,而常州府武进县和宜兴县官田的一般租额分别为0.4和0.3石,应天府上元县更仅为0.2石(注:伍丹戈: 《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第18页。)。如用同样的办法推论,那么这些地方的亩产,应当也大致与苏、松相近或更低。因此,尽管有些记载说明初江南一些地方地租额很高(注:例如弘治《吴江县志》卷6风俗说: “每田一亩,起租一石至一石八斗”。但此说是否可靠尚待考证,因为后来的嘉靖《昊江县志》卷13风俗在谈到地租时说:“农田计亩索租,下自八斗,上至一石八斗而止”。即使所说属实,在江南也应是极端的例子。),但就整体而言,江南水稻一般亩产大致在1石上下或1石略多。就上面曾经谈过的常熟而言,直到明代中期的嘉靖时代,“大率亩之所入,上农以二石计,中农以石有赢计,下农以石计”(注:嘉靖《常熟县志》卷4 食货。)。我们可以将此视为明初江南亩产情况的缩影。
尽管明初江南水稻亩产量看上去与元代乃至南宋后期相差不多,但是由于度量衡制的变化,实际已有相当大的差别。南宋、元、明江南亩积变化不大(1宋元亩约等于0.98明清亩),可以忽略不计, 但量制变化却很大。大体而言,1宋石=0.66市石,1元石=0.95市石,而1 明清石=1.03市石(注: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12~13页。)。换言之,1宋石大约等于0.69元石,或0.64 明清石。考虑到这些变化,南宋的1石/亩,大体上等于元代的0.7石/亩,或明清的0.6石/亩。或者说,元代的1石/亩,大体上等于南宋的1.4石/亩或明清的0.9石/亩;而明清的1石/亩,则相当于南宋的1.6 石/亩,或元代的1.1石/亩。因此,尽管从表面上来看, 宋末至明初江南水稻亩产量似乎变化不大,但实际上已经增加不少(注:具体的例子如常熟,南宋后期亩产量在0.65—1.36石之间,取其中数为1石, 以明制计为0.6石;明代中期亩产量为1石多(中农之田),姑以1.3石计。 较之前者,增加了一倍。)。
正是因为亩产量提高,所以江南的田亩赋税自宋以来一直在上升。位于西部的杭州、江宁、镇江三府的税粮,从南宋至明初,分别从12~13万石、15~21万石和9~13万石增至25万石、32万石和24万石, 大约增加了一倍(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154~155页。)。位于东部的苏松二府增长幅度最大。南宋苏州税粮虽然号称沉重,但实际不过在28~39万石之间,元代增至88万石。元末张士诚据苏州时,赋粮一度超过百万石。到了洪武12年(1379),仅秋粮中的正耗粮,竟已达到215万石,洪武26年(1393)又进一步增加到281万石。虽经宣德时期两次削减之后,仍一直保持在200万石左右的水平(注: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154~155页表7;并参阅范金民、 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松江的税粮,南宋时期为6~11万石,元代增至20万石, 明初则暴增至88万石。苏、松二府分别增加了7倍和9倍之多。江南全地区的税米总数,在南宋时期大约在123~145万石之间,明初则上升至559 万石,增加了4倍之多(注:据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第154 ~155页表7中各府税粮的计算而得。)。固然明初江南重赋有各种原因,不过其中最重要者,还是如范金民和夏维中所指出的那样,是由于这里经济的发展,从而方使重赋成为可能。至于明太祖对此地区的个人好恶,并不重要(注: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因此,宋末至明初江南水稻亩产量有相当大的增加,应是无可置疑的。
如果将上面我们对南宋后期、元代中期和明代初期江南平原上一个农户平均种田数、户均劳动力数和亩产量的估计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农户的稻米总产量和每个劳动力的产量就如表5所示:
表5.
户数田数 亩产量* 户总产量 户劳动力数 每个劳动力产量
南宋
40亩 1.3石 52石3人17石
元代
30亩 1.8石 54石3人18石
明初
20亩 2.1石 42石2人21石
*说明:三个时期的亩产量,均以当时的“1 石余”计(此处都以1.3石计),然后又据上述折算标准折为宋制。
可见,尽管农户种田数减少,但由于农民家庭规模的缩小和亩产量的提高,每个劳动力的平均产量却在增加。此外,如果再加上后茬作物(麦、豆、油菜),这个增加的幅度还会更大一些。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此时期,江南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处在缓慢的提高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