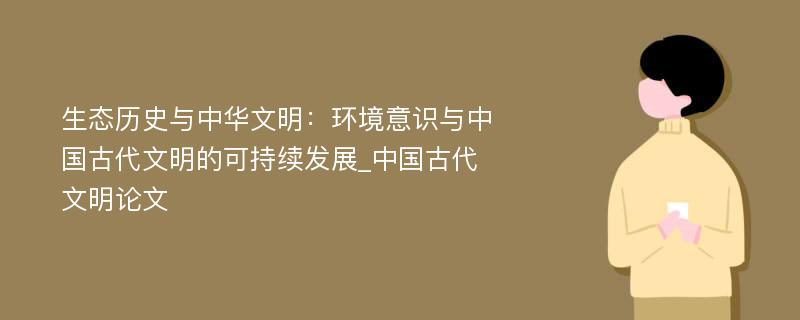
生态历史与中华文明(笔谈)——环境意识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中华文明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12-0105-05
中国古代文明为何能够保持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持续发展,并创造辉煌的文明成就?以往人们多从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儒家文化的特质等方面进行讨论和认识,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发展问题进行诠释,获得了许多富有启示意义的认识成果。文明的持续发展实质上是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只有文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文明的发展才能长期延续。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上的环境意识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意义①相通契合,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效防止了人的过度物化,抑制了人对自然毫无节制的掠夺,确立起以代际平等为基础的资源利用原则,从而在环境和资源方面保证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效防止人的过度物化
在对人类发展的深刻思考中,学者们已清楚认识到人的物化问题。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生产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物质资料,在劳动和创造中感受生存的幸福和生命的意义。但是,随着物质资料生产和财富的积累,这些物质资料会不断侵蚀人类的心灵,刺激人类物质欲望的膨胀,逐渐扭曲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导致人与物错位,真正的人在物的面前消失,人逐渐被物化。
人被物化的后果极其严重,其一,人的物化往往会使人局限在狭隘的分工范围内,留恋眼前利益的获取和物质欲望的满足,从而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失去未来的方向。其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的物化使人完全彻底地从自然界中剥离出来,以一种超自然物的意识和身份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成为自然界的主宰者,加剧人与自然界的对立。为了攫取更多的物,人以盲目和野蛮的行动将自然界作为肆意蹂躏和征服的对象,从而使人类逐渐失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之中。[1]因此,如何有效地防止人类的物化,就成为人类社会是否可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但他们基于天人合一理念,在处理人—社会—环境关系上,充分注意到人的欲望与人的物化之间的相互关联,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抑制人对自然界掠夺欲望的膨胀,有效地防止了人被完全物化,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因为对自然的掠夺而使中国古代社会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关系到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关系到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方式方法和利用程度。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哲学家就以朴素的形式阐述了这个问题。尽管说法不一,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人与自然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超自然物。周代有天、地、人“三才”[2](《说卦》)的表述,认为天地人是统一的整体。《易传》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2](《系辞下》)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故强曰之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3](第25章)老子强调的是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他还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第42章)强调“道”不仅是人的本源,而且是天下万物的本源,是宇宙的普遍规律,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观点的另一种表述。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4](《韩称》)程颐也指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5](卷2上)王阳明在《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中说:“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显然,王阳明不仅强调人与自然为一体,而且倡导人与万物的诚爱无私,和谐相处。
人作为一种自然物存在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也是现代环境伦理观念的哲学基础。恩格斯多次强调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统一”,反对“把那种精神和物质,人类与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6](P159)现代环境伦理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要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依存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意识与现代环境伦理观念是相通契合的。
人作为一种自然物,人的自然力、生命力和能动性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中国古代哲学家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肯定人类具有超出万物的生命价值和赞助天地之化育的能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把人视为自然的“征服者”,人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服从自然法则。[7]《易》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2](《乾·文言》)强调人要发挥能动性,必须依照自然规律。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8](《天论》)老子在认识到“道”为万物的本源之后,进而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道家把顺应天道自然而为称之曰“无为”,而把违背自然规律的行动,称之曰“有为”。儒家虽然对自然规律问题没有做较系统的理论阐释,但通过对禹和鲧的行为做不同的评价说明顺应自然规律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禹所以能治水成功,是因为他顺应了水势就下的自然规律,采用了疏导水流使之注入大海的办法;而鲧治水遭到失败,是因为他违背水势就下的自然规律,采取垒坝堵水的办法,使人与自然仍处于对立之中。《大戴礼记·易本命》云:“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由自夭而不寿,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息。”正是基于对自然规律的这种观察,其后的许多思想家都对人怎样符合规律性而实现目的性的问题做了有价值的思考。如《淮南子·修务训》说:“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这里的“人必事焉”、“人必加功焉”,实际上是对人类能动的主体性地位的肯定,也蕴涵着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统一的意义,只不过它更强调由规律性而达到目的性、由利用自然规律来展示人的自觉能动性。这种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尊重客观规律,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的思想,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9]
二、仁民万物,珍爱生命,抑制人类对自然的欲望膨胀
基于对人与环境的伦理关系和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两大问题的不同理解,形成了许多内涵不同的环境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是自然界万物进化的最终目的,只有人类才是衡量生命实体能否存在的唯一价值尺度,因此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时,应该将人类的利益置于首要位置,自然对人类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一种观念认为自然不仅仅对人类有工具性价值,还具有独立于人类存在的内在价值,人类应该承认自然及其万物像人类一样拥有道德地位并享有道德权利,人类应该尊重自然及其他生命,对它们承担起道德义务和责任。[10]
显然,前者虽然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发展出发,也重视人与环境的和谐,主张对人类生存环境进行保护,但这种保护是为了从自然界获取更多的功利性保护。而且人类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个人或集团的私利,往往把自然界作为可以无穷索取的资源库和无限容纳废弃物的垃圾场,对自然进行疯狂掠夺,导致环境破坏,损害大多数人和后代人的利益。在社会实践层面上,保护环境成为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空话,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不可持续的局面。后者认为人类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拥有其内在价值,只有人类从自然的整体利益出发,把其他自然存在物也当作具有独立于人的主观偏好的内在价值的对象来加以保护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完整才能真正得到保护,人对环境的保护才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安全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才会更安全、更稳定、更可持续。这种观念把道德义务的范围扩展到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把平等地关心所有当事人的利益这一伦理原则扩展应用到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身上,真正使人类对自然的关爱和保护成为自觉,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具有了实在意义。
中国古代哲人在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把天地万物视为和谐的整体。老子道家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强调“道”的运动是自身使然的(即“无为”),其最终意义就在于确证自然体系之结构的完美及其和谐性。儒家对万物共生共存的相互依赖关系观察得要更细密一些。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1](《尽心上》)在孟子的观念中,君子之“爱”是有层次的。从对亲人的亲爱,到对百姓的仁爱,再到对一切自然物的珍爱,各有不同的内涵,表现为由近及远的扩展。而这几种爱之间又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亲亲必须仁民,因为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才能使亲人的幸福得到保障;仁民又必须爱物,因为只有珍惜作为生存资料的自然物,才能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他将仁爱的道德规范延伸到爱物的领域,从而把珍惜爱护自然万物提高到作为君子的道德职责的地位。荀子认为天地万物的存在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一个有序的整体系统,即“天地以合, 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8](《礼论》)正因为世界是一幅和谐有序的图景,故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8](《王制》)荀子又说:“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8](《非相》)宋代张载则认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4](《乾称》)
与人和自然和谐的观念相联系,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主张“兼爱万物”,把爱护生物,尊重一切生命的价值提高到衡量人们行为善恶的高度上。《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将“生”作为天地之间的至德。道家以无为、无执、无处的心态对待“物欲”,无疑已包含化解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寻求一个适合人生存的客观环境的意向。儒家由于重视人伦日用的道德实践,强调按照由近及远的程式将“仁德”及于人,推及于物。孔子不仅主张以“仁”待人,也主张以“仁”待物,即《论语·述而》中所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礼记·祭义》记载: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显然孔子把道德伦理行为推广到生物,认为滥伐树木,滥杀禽兽是不孝的行为,把保护自然提高到道德行为的高度。
在孔子“仁物”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术”说。所谓“仁”,即指把人的“不忍人之心”推及于禽兽,亦即“恩以及禽兽”。宋代程颐更强调说:“生生谓之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种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5](卷2上)宋代学者朱震在《汉易传·说卦》中不仅认为人对草木禽兽应当珍悟保护,而且把滥伐树木,滥杀禽兽的行为斥为“不孝”,他说:“万物分天地也,男女分万物也。察乎此,则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体。是故圣人亲其亲而长其长而天下平。伐一草木,杀一禽兽,非其时,谓之不孝。”
正是由于对自然生物系统具有同情心,所以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11](《梁惠王上》)荀子也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鳌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财也。”[8](《王制》)这些思想尽管是朴素、直观的,但已说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不只是一个技术手段控制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有道德的参与。[9]
三、重视社会发展的代际平等,强调自然资源利用的合理性
从时间层面说,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对待自然资源利用的问题上,坚持代际平等的发展理念,即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考虑后代生存和发展的需求,遵循当代社会的发展不以损害后代的发展为代价,顾及人类发展的未来。
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以农业为主要形态的文明,它的发展及其可持续性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密切关联。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代思想家基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仁民爱物,反对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既肯定在不违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为人类造福,又强调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性,以保证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强调自然资源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应该进行开发利用。荀子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8](《王制》)显然荀子把山林泽薮等自然资源作为国家财富,是“国家足用,财物不屈”的物质基础。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不管是主张仁民爱物,保护环境,还是反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终极目标还是要让百姓“有余食”、“有余用”和“有余材”,落脚点还是民生,还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礼记·曲礼》认为:“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地有余而不足,君可耻之。”[12](《杂记》)
但是,利用而不是滥用,这是中国古代环境意识的基点。我们的先人很早就认识到“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13](《主术训》)认为要想利用自然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适时地开发和利用,反对不合时宜地过度开发,特别是破坏性的开发利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保护山野薮泽是富国富民的保证。《管子·立政》篇中讲到富国立法有五,其中第一条就是“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将山泽防火、草木生殖置于富国之道的首位。《逸周书·文传解》中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管仲认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伐必有时。”[14](《八观》)孟子把是否能够对自然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提升到“王道”的高度,体现了中国古代环境意识的鲜明特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对动植物的捕获狩猎砍伐作出了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在此过程中又采取了取大留小、用壮护幼的方法,以保证幼小动植物的生长。夏历的春三月和夏三月正是树木生长、鸟兽鱼鳖孕育生长的大好时机,所以古人严禁在这一时期内田猎鸟兽、网捕鱼鳖。《礼记·月令》记述上半年孟春正月到季春六月均有保护林木鸟兽龟鳖等生物资源的禁令。从孟春“禁止伐森,毋覆巢……”,到仲春“毋竭川泽,毋漉陂坡,毋焚山林”,再到季夏“树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从《礼记·月令》看,几乎每个月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都有明文规定。
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关系方面,目前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过分强调保护,反对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哪怕是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环境保护成为空谈而失去实际意义。一种是过分强调利用,不重视保护,从而走向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则既肯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又强调这种利用应该适时适度,强调利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基于环境保护的开发利用,既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满足了人们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需要,也为子孙万代留下了可供长期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这正是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意识。
注释:
①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和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在《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两个权威文件,可持续发展应该有三层基本含义:在时间上,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强调当代社会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要顾及人类发展的未来利益;在空间上,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发展,强调同时代人之间应该有公正、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在对自然的认识和资源利用的态度上,社会的发展应该在不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的前提下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强调人类应该保护生态环境,并与自然和谐共处,反对人类对自然物产的毫无节制的征服、掠夺和挥霍,以免产生灾难性的环境后果,危害人类生存。从可持续发展的这些应有之义看,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终极目标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不仅强调可持续性,而且特别强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