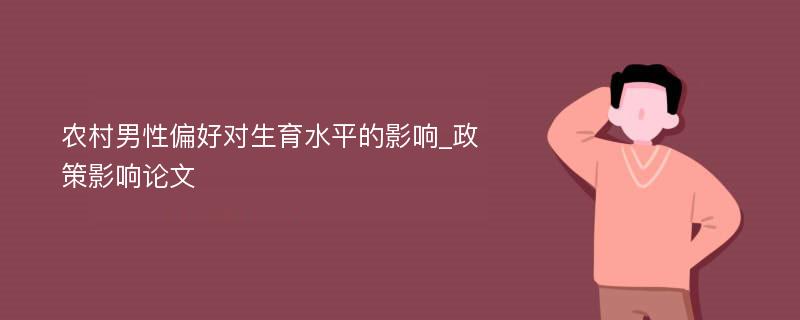
生男偏重对农村生育水平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平论文,农村论文,生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0年代,中国开始进入人口转变阶段,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都在逐步下降。到1995年,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意味着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水平。但是,有两个事实不容忽视:一是人口的整体规模仍在持续扩大;二是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出现,是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而不是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所阐述的那种自然转变(注:Easterlin,R.A.,1966,“On Relation of Economic Factors to Recent and Projected Fertility Changes”,in Demography 3(1):31-53;Coale,A.,1979,“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in L.Chao & K.Koboya Shi(eds.),Fertility Transition of the East Asian Population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目前,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少生或节制生育还没有真正成为人们的心理需求和意愿;自觉自愿地控制生育以及小家庭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注:陆益龙:《生育分析的社会人类学框架》,《人口学刊》1998年第6期。)。尤其是,农民的生男偏重心态,仍会驱动他们选择多胎生育。因此,维持和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还需要从均衡乃至转变农民的生男偏重心态入手。本文主要根据笔者在皖东农村社区的田野考察的经验材料,分析和探讨农民生男偏重心态的形成原因及其对生育水平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均衡农民生男偏重的策略选择或制度安排问题。
农民生男偏重的成因
生男偏重属于生育心态的一种。所谓生育心态,是指育龄夫妇及其他家庭成员或亲属对于生育行为结果的认知、评价、态度和偏好,主要包括个人和家庭成员对生育孩子数量、性别结构、生育时间的态度、评价、偏好和倾向。譬如,对于生还是不生、早生还是迟生、生男还是生女、多生还是少生等问题,任一家庭都会有一个基本倾向。当前,中国农民的生男偏重心态,主要表现为一个家庭倾向于或特别看重甚至追求至少生一个男孩。
生育行为虽然由育龄妇女执行,但对生育选择产生影响的因素还来自于其他家庭成员以及重要亲属。家庭和重要亲属关系中的不同成员都可能从不同的侧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最终的选择。所以,生育心态的最终倾向,则是家庭中各种价值、理念、态度和意愿以及偏好相互影响、相互较量后的均衡态势或最终结果。同样,生男偏重也是家庭对生育选择的综合评价及最终的倾向。
从农村的田野考察中,笔者发现农民生男偏重现象主要表现为:在现行政策背景下,较多的农民家庭在有了一个男孩之后,他们的心态相当平衡,生育第二胎的意愿和动机并不强烈,对只有一个孩子的小家庭现实能够较为满意地接受;但是,如果年轻夫妇第一胎生育了女孩,那么,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的心态是极为不均衡的,而且父母心态的失衡程度远远超过育龄夫妇。这种失衡心态主要反映在:(1)家庭成员情绪低落甚至反常,家庭气氛渐渐紧张起来;(2)家庭成员各自盘算以后的生男计划;(3)布置和逐步实施生男计划;(4)当生男计划受到阻碍或挫折时,他们极容易与相关机构和人员产生较为激烈的摩擦和冲突。
从偏重的程度来看,当前农村生男偏重主要存在三种状态:一是生男即满足;二是生女再努力;三是不生男孩不罢休。第一种状态反映,一些农村家庭在第一胎生了男孩之后,在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下,他们已经相当满足了,能够接受控制生育或不再生育;第二种状态特点是,适度地追求生男,即在追求生男过程中,当困难和成本越来越大时,他们会适可而止,放弃追求,接受现实;第三种状态是一种强烈生男偏重现象,他们常常不顾任何阻力和代价,甚至会采取极端对抗的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生男愿望。
农村为什么存在生男偏重的现象呢?或者说,农民家庭为何希望家有男孩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
(1)农业生产方式决定论。这一类观点认为,由于当前农村主要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依赖于强体力劳动,离不开男性劳动力,因此,农民家庭追求生男孩,是出于农业生产需要考虑的。
(2)传统文化决定论。即把“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看作是当前农民生男偏重的根本动因。这类观点似乎认为,传统的文化观念是难以改变的,它对人们的行为始终会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无形而又深刻的。
(3)家庭效用最大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任何家庭的生育选择,都属于理性选择,因而都在追求生育效用的最大化。人们之所以有生男偏好,是因为人们认为生男对家庭具有更大的效用(注:参阅贝克尔《家庭经济分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叶文振:《孩子需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以上观点或理论解释虽然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解释了农民生男偏重的原因,但是,它们又各自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持这些观点的人可能并没有从农民真实生活中去客观地探寻农民生育选择行为的动机。所以,笔者以为,要真正揭示和解释农民生男偏重的原因,需要把主位研究(emic approach)和客位研究(etic approach)结合起来(注:陆益龙:《生育兴趣:农民生育心态的再认识——皖东T村的社会人类学考察》,《人口研究》2001年第2期。)。引入费克所说的“现实的模型”(model of reality)和“为现实的模型”(model for reality)(注:Fricke,Tom,1997,“The Uses of Culture in Demographic Research”,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4(4)825-32.),深入农民的现实生活,体验乡土文化,探寻农民认为哪些东西对他们更为重要,哪些制度和政策对他们是有效的。惟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生男偏重的内涵及其原因。
按照这一方法论原则,通过对现实经验材料的解读和归纳,笔者发现,撇开人们喜好男孩的心理因素不论,目前,导致农民生男偏重的社会文化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村落文化背景下的趋同压力;二是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与实践导致农民生活现实连续性的断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男情结这一特殊精神现象。
首先,生男偏重是在乡土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因此它与乡土社会和“村落文化”中多种因素相联系(注:参阅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受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如社区的历史传统、地理生态、生活兴趣、民风民情以及在村落聚居中形成的趋同行为所构成的压力等等(注:参阅刘世定、胡冀燕《趋同行为与人口规模》,中国人口出版社1993年版。),都对生男偏重或追求生男产生极大的作用。
正如费孝通所说,乡土社会是一种礼俗社会,也是人人都“顾面子”的社会(注:参阅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生活在同一个村落里,人与人之间彼此熟知,直接互动,同处于一个生活单元之中。在这种情景中,他人的评价和自我的“面子”,几乎对每个人或每个家庭来说,都相当重要。在这种生活氛围里,人们甚至把维护“面子”看得比什么都更加重要。所以,当生男在村落中得到较高的社会评价时;当现行的相关政策安排及其实施,又进一步强化和突出这种价值评价时,生男也就成为村落中重要的价值目标,直接关系到各家或个人的“面子”问题。因此,生男已超越了农民的物质需求,而成为一种精神追求。
所以说,农村出现生男偏重现象,并非由笼统的传统文化所致,而是具体的现实文化所为。
其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生男偏重的形成与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践有着一定的联系。计划生育的实施,打断了农民长期维续的生活现实连续体,改变了农民原有的生活惯习和格局,干扰了农民家庭的生活周期,从而诱发了农民更加明确、更加强烈地追求生男的心理倾向的形成。此外,作为一项政策,计划生育首先表现为国家的意志和要求,这种要求相对于生活在较为封闭的村落居民来说,则意味着外在力量的嵌入和干扰。当他们的意愿与这种要求不一致时,相对剥夺感也就容易产生,随之便形成逆反心理和追求满足或补偿的动机;当行政的强制措施压抑和阻碍他们的欲求实现时,这些欲求就可能在农民的潜意识里构成巨大的情绪冲动。潜意识的能量驱使着有些农民直接与政府对抗,有的采取逃生、偷生,有的采取溺婴、引流等措施来追求生男价值的实现。所以,并不能把农民的生男偏重简单理解为理性选择的倾向,或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无论从心态还是从行为的角度看,生男偏重都具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
生男偏重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影响生育水平的直接因素就是生育主体选择多生还是少生的行为,如果选择多生,就会导致生育水平提高;如果选择少生,那就会导致生育水平下降或维持低生育水平。多生还是少生,又与生育主体的这样几种行为选择相关,那就是晚婚、避孕、节育和绝育等等。那么,人们会不会选择这些行为呢?是自愿选择还是被迫选择呢?这些问题最终也就关系到生育主体的基本心态,也就是他们的价值、态度、意愿和驱动力。
所以,根据生育影响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民生男偏重对农村总和生育率或生育水平的影响,也就是通过家庭生育主体的各种可能影响到生育数量的选择倾向和行为而得以实现的。
实现和维持低生育水平,关键因素就是生育主体自愿选择或被迫接受少生,而影响和决定少生的次级因素主要包括晚婚晚育、婚后避孕、采取节育措施以及接受绝育手术等等,至于婚后及产后不育等非人为因素,通常影响不大,所以可予忽略。家庭或个人是否接受那些次级因素的要求,则受到生男偏重的直接影响。
从逻辑上看,生育主体愿意接受计划和控制生育措施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种:一是自觉自愿地接受计划生育和主动接受节育措施;二是在外在政策和制度的制约和限制情况下,勉强接受或被迫接受计划和控制生育。除愿意接受外,还有一种不同意接受甚至反抗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他们既不愿意接受控制,也不顾任何限制,极力追求多生(通常指三胎以上)。
第一种态度反映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以及“小家庭”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内化了的价值取向。很显然,这种心态对促进生育水平的转换以及维持低生育水平和人口平稳增长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第二种态度是在外在力量强制下形成的,其结构具有不均衡的特点,因而也是不稳定的。当外在的强制力量发生变化时,或其他因素发生变动时,其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例如,当计划生育政策管制松动时,他们就可能改变对生育选择的态度,转而选择多生。第三种态度是超生和多生的直接动力,与计划和控制生育背道而驰,也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最主要障碍。
生男偏重使得上述农民对待计划生育的三种心态都产生不同的影响。首先,生男偏重对第一种自愿节育态度构成负面影响。因为,当生男的愿望得不到实现时,农民自然就不会自愿接受计划生育原则。其次,生男偏重影响到计划生育措施对农民行为选择的边际效应。生男偏重提高了农民对生育控制措施的压力效应的阈限,也就是说,具有生男偏重的人,对控制措施的压力作用反应较为迟缓。在有男孩的情况下,他们能够接受生育控制。但当他们的生男愿望与控制措施不一致时,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超生以追求生男。最后,生男偏重对不愿接受甚至反抗计划生育控制措施产生直接的影响。从实地考察的情况来看,多生虽已不是多数农民的生育目标,大多数农民对生育孩子数量已经没有更多要求,但是,他们对生男的要求则相对更加强烈了。对较多农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家有一个男孩(注:陆益龙:《生育兴趣:农民生育心态的再认识——皖东T村的社会人类学考察》,《人口研究》2001年第2期。)。
总而言之,目前农民的生男偏重仍对维持和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产生负面的影响,农民对生男的追求,是他们运用各种策略来回避政策制约甚至与政策相对抗的最为重要的动因。所以,农民与计划生育政策、农民与基层计生干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农民的生男偏重。
均衡生男偏重的政策选择
人口规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会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变数之一。因此,控制人口增长,推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对稳定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关键是如何更加科学地、合理地推行计划生育,这就需要对更为具体的问题加以更细致的研究。
从生育水平转变规律来看,目前中国农村地区尚未达到人口自然转变的条件,也就是说,稳定低生育水平,政府的干预和政策调控因素仍起决定性作用;农民对待计划生育的态度大多属于第二、三种,即在政策或制度限制和控制的情况下,能够接受控制生育、节育和少生,而部分农民在没有男孩的情况下,极力追求多生直至生男。
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尚未把少生、控制生育以及小家庭观念作为生育选择的偏好;而且,生男偏重的心态仍将驱使部分人超生或多胎生育。由此看来,一旦政策或政府控制力度降低,农村生育水平和农村人口将会有较大幅度回升或提高。
因此,维持农村现有的低生育水平,在战略选择上,仍需要继续推行和加强计划生育;人口规模过于庞大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人口控制的重要性,管制和调控的松懈,将对中国社会协调发展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科学合理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的基本方针不宜变动。有些学者主张在经济发达地区放松生育控制,这种主张忽视了一项政策的推行可能产生的负面社会心理效应。很显然,在一个地区或城市里放松控制,必然会刺激和拉动另一地区的农民生育需求的变动。
至于农民的生男偏重观念,需要辩证地、全面地分析和认识。一方面个别意志的累加并不等同于集体、公共利益和合理性所在;另一方面还应认识到,农民的生男需求及偏好,具有可交换性和可替代性。对某些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他们要求生男,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有关,如果公共选择要求他们少生,那么就需要在其他利益分配上给予相应的补偿,以弥补他们的相对损失,平衡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同时,如果帮助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及消费结构,也将转变他们以往的观念、需求和偏好。
因此,新时期的人口转变,不是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是转变计划生育工作的内容和方式。需要把医学化、行政化的计划生育工作转向以利益调整、社会服务和文化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上来。改革现行的城乡利益分配格局、建立和健全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制度,制定合理的优惠和补偿政策,促进农村女性成就机会的提高,特别是对农村地区的在校女生的升学和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加大支持、补偿和优待的力度,促使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此外,加强公民人口与环境意识的教育,让人口、资源和环境意识深入人心,让公民树立个体超生行为的外部性意识,并把自觉实施计划生育或在更替水平以下生育作为一项社会公共准则。
总之,人口问题属于公共领域里的问题,维持中国农村低生育水平,政府的干预和政策的调控仍将占主导地位,社会经济因素的自动调节作用仍很微弱。政府的政策调节要注重创建良好的制度和生活环境,以便于促进人们生活水平和精神结构的转变,最终达到人口的自然转变。
标签:政策影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