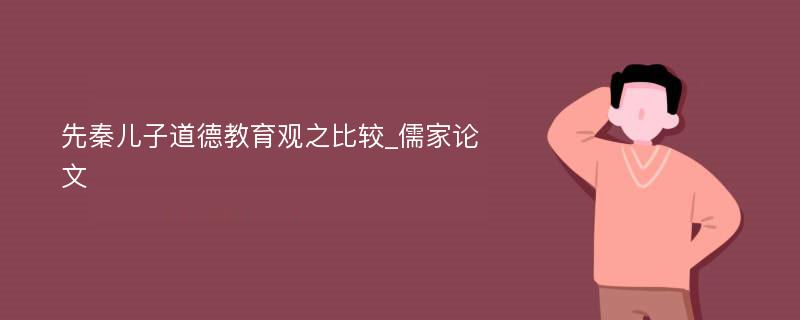
先秦诸子道德教育观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诸子论文,道德教育论文,先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秋时期是中国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学术 下移,养士用士,百家争鸣。百家之中,又以儒、墨、道、法四家为最。故今人探讨先 秦诸子,多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代表。
从对后世道德教育的影响来说,无论在当时或在后世,在国内或国外,诸子百家中又 以儒家影响最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经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潜移默化于中华 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准则、精神支柱和传统习俗,构成有别于西方传统 的中华文明的典范文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方其他国家,并远及欧美。尤其是 儒家在道德教育领域创立的许多思想、方法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行为的典范。
几乎与孔子同时的墨家——墨子、道家——老子及产生时间稍晚的法家——商鞅、韩 非子,与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他们对道德教育没有严密、系统的思想,但是 他们的政治、思想主张和教育实践对道德教育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道德教育的目的 、内容、方法上都有一些独到见解,值得后人认真加以研究。
一、四大家在道德教育目的上的差异
儒家的教育目标是仁智合一的“贤士”。孔子继承了西周“敬德保民”思想,主张以 “德政”治国安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论语·为政 》)德政是要由人来实施的,所以培养修己安人的贤士就是教育的唯一目的。他的教育 内容有四种,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德行的教育列于各科之 首。他教诲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 学文。”(《论语·学而》)认为学生首先要学习德行,做一个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 其次才是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所以在其整个教育中,道德教育居于首要地位。 孔子对学生的评价,也是把德的标准置于才能之上的。他认为颜回好学,不是说他的知 识丰富,才能高超,而是指颜回的品德比别人高尚。[2]一个人的知识才能再好,如果 没有好的品质,也是不足道的。孔子认为,道德的价值高于人的知识才能,在各种教育 中,道德教育处于第一位。孟子进一步提出“大丈夫”理想人格的修养目标。他将人的 道德境界分为六个层次。“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 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章句下》)神圣之人非常 人可达,美、大、信、善之人则人人可为。被称为“别宗”的荀子认为,尽管人性是恶 的,但通过自己的学习,也可以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因此在道德教育的内容和作用上, 他认为对“礼”的学习是道德教育对人性本恶的唯一补救方法,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 “化性起伪”的作用。所以,荀子教育目的起点是培养既懂“礼”、“法”,又行“礼 ”、“法”的“卿相士大夫”,最高目标是使人成为“圣人”。[3]
总之,儒家认为道德教育是对个人本性的改良或提高。对社会而言,道德教育应以改 造国家、改良社会为目的。用孔子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己立”、“立人”、“己达” 、“达人”。立,含义有站立、成立、创建的意思,在《论语》中出现了25次;达,有 通达、顺利、闻达、完成的意思,在《论语》中出现了20次。这两个字同时出现在《雍 也》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 是孔子回答子贡问仁时说的话。简单翻译就是:仁者,自己要立得住脚,便要让他人也 站得住脚。自己想达,便也帮助他人能达。能够从近身的一点一滴做起,并推行开去, 可以说是行“仁道”的方法了。
相对于孔子道德教育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目的论,墨子虽然没有明确的“立人 ”主张,但是在道德教育目的上,他也主张培养“贤士”、“兼士”。他兴办私学,广 招学生,以“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4](《墨子· 尚贤下》)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把培养实践“兼相爱、交相利”的“贤士”、“兼士 ”作为自己的使命。以上两家区别在于:儒家尤其是孔子的道德教育目的可概括为“内 圣外王”,含有个人、社会目的的两层意思。对个人而言,道德教育是对于个人本性的 改良或提高。对社会而言,道德教育则以改造国家、改良社会为其目的的。所以在目的 的达成上也有两个层次的选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章 句上》)墨子是一个“摩顶放踵”、热心救世、为民兴利除害的社会活动家,认为凡是 “利人”、“利天下”的行为,就是“义”,凡是“亏人自利”、“害人”、“害天下 ”的行为就是“不义”。所以墨子的行为准则是:“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 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墨子 把“仁义”作为一种至善的道德追求而不是虚幻的言论,是为实现天下人的现实利益服 务的实践,为义的“贤士”、“兼士”。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必须“有力者疾以助人 ,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给他人、天下人带来实际 的利益,使“天下和庶民阜”。
老子把“无为”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最高原则和人的至善品德。他说:“道常无为而 无不为。”他认为,人人做到“无为”即朴素无欲,无所作为,即能“天下将自定”( 《老子·为政第三十七》)。老子宣扬“无为”的道德教育观,目的是实现“其政闷闷 ,其民醇醇”(《老子·顺化第五十八》)的道德理想,看上去他的道德教育似乎是无目 的的、无作为的,其实不然,道家同样有自己的道德教育目的。撇开历来的争论,我们 基本可以确定老子思想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其特性是自然、 无为、虚静、柔弱、不先、不争,人应当效法“道”,清静无为,绝圣弃智,放弃争斗 ,以柔为贵。老子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以大道自然的精神来治理社会,使人心归真。道 家也有自己需要养成的理想人格,就是“神人”、“真人”、“至人”等(皆为庄子语) 。这几种理想人格并不是如孔子为理想划分的不同层次的目标那样,而是从不同的角度 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神人”是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逍 遥游》)的完全超脱社会、超越生死的精神、绝对自由的人格境界;“真人”是一种“ 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渔父》),即使身居俗世,也不为俗累,不以 心背道,“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的独立人 格;“至人”是一种“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的化解物我差异,具有虚己无我的精神境 界(《庄子·人间世》)。可见,道家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天人合一、自然归真的独 立人格。当然老子与庄子各自对理想人格有不同的表述,老子重隐藏自我,以无为而无 不为;庄子所求的不是以利国利民为己任,而是人的个性解放与独立,这一点到了玄学 更加得到发展与提升。
法家的道德教育目的从表面上看是培养顺民。法家主张以法为本,以君王的是非为是 非,反对开启民智,对普通人的道德教育不重视,故儒家的道德教育目的受到法家空前 的批判。因为法家认为:教育开启民智,增长知识,使人性中恶的本性进一步扩大,破 坏了君王刑、法、术、势的强硬统治。他们认为儒家的仁义德教是“暴之道”(《商子 ·开塞》),使人“偷乐而后穷”(《韩非子·六反》)。其实,法家的道德教育目的也 有一定的层次性,除了顺民之外,法家也有自己或君主需要达成的人格目标。法家不赞 成道家的无为、隐世,认为这样的人完全无用,“有民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 之世,将安用之?”(《韩非子·说疑》)法家对儒家所赞扬的“杀身成仁”、“舍生取 义”的“志士”、“君子”也不赞成,因为他们对生活没有策略。法家所要达成的人格 目标是“耿介之士”、“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其中“耿介之士”最为法家看重 ,因为统治阶级需要一批忠贞耿直的能臣智士,韩非子说:“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 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尔。”(《韩非子·五蠹》)这样的“耿介之士”、“智 术之士”、“能法之士”利国利民,有实用价值的。另外,法家理想人格中还有一种“ 全大体者”。这种人虽受制于外部,却能有限度地提升自我,顺应外部,“因天命,持 大体”,“名成于前,德垂于后”(《韩非子·大体》),完成自我使命,这是法家理想 人格的最高层。
从另一个角度看,墨家与儒家的德育目的论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应具有献身精神。不 论“君子”、“圣人”,还是“兼士”、“贤士”,都是愿意献身于社会、国家或他人 的理想人格,他们的道德教育目的基本属于社会中心论。道家特别是庄子的道德教育目 的更倾向于精神自由者,在儒家“内圣外王”目的失落的时候,常常为广大知识分子所 接受。法家理想人格是利国利民、有所作为的强者形象,这在许多掌握国家政治权柄的 知识分子身上时有体现。相比较而言孔子设计的“君子”、“圣人”人格是符合社会生 活实际的,其道德教育主要致力于主体理想人格的塑造,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具有 较强的生命力。而道家的“神人”、“真人”、“至人”形象常常作为儒家人格的补充 而发挥作用。
总起来说,四大家道德教育目的的核心都是在讨论人的主体性如何开发的问题,不论 “仁”、“兼爱”、“道”或“力”,他们的目标不外三种:一是个人人性、道德的改 良;二是个人通过道德教育增进知识、能力;三是形成社会公德、提升治国安邦的水平 。对个人人性、道德的改良来说,儒、道两家从不同的角度深入下去,提出成人、立人 的不同标准;墨、法两家更注重实际运用能力,但都有自己的方法达成这三种目标。相 比较言之,儒家的道德教育目的更切合现实生活,也具有灵活性。
二、四大家在教学内容上的异同
从道德教育内容上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仁”。提倡 “仁”的根本目的是要塑造能建立和维护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所需要的理想人格—— “君子”。君子的理想人格,应当是“智、仁、勇”的统一。“智者不惑、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因此, 其主要教学内容是除了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外,孔子更是精心为 学生编成《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教材,内容涵盖了文 学艺术、政治文献、历史、哲学、礼制、音乐艺术以及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教学 中尽力发挥教材对人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情操的陶冶作用。《诗》教人心意畅达,体切人 情;《书》教人通晓历史,明辨是非;《礼》教人知道规范,举止有节;《乐》教人净 化心灵,品性善良;《易》教人深察事理,达观为人;《春秋》教人交往得体,行为有 原则。
相比较而言,墨家、道家、法家多偏重于某一个方面,如墨子道德教育的核心是以“ 兼爱”代替“仁”。与儒家的重礼乐、崇宗法不同,墨子针对“诸侯兼并、杀人掠地” 的局面,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 葬”、“节用”、“非乐”和“非命”等十论,其思想反映了当时中下阶层的愿望。在 教育内容上更提出学生要注意对生产技能、军事知识、论辩才能的培养,反对“博闻” 杂识[5],强调以约驭博。同时墨子十分重视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在论辩才能上主张 “察类明故”的逻辑思维,与孔子的“触类旁通”、“知类通达”的主张是一致的。墨 家把对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看成是“兼士”、“贤士”的必备条件。
老子的道德观与孔子、墨子的道德观有明显的区别。老子的思想核心是“道”,在伦 理意义上,道指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德指人类的本性或品德。他说:“圣人之道,为 而不争。”(《老子·显质第八十一》)“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老子·修观第五 十四》)即道德教育的内容就是寻求道德观与自然的相通。人类生活中的道与德,应当 以自然界的道与德为依据,而不是以儒家所说的“仁义”为依据,因为“仁义易其性” (《庄子·骈拇》),不符合“道法自然”的主张。庄子也一样关心人的道德的修养,提 倡“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庄子·德充符》)。
法家的道德核心是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在道德问题上,法 家并不是不要“仁义”,而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人们的道德生活及其规范,以及怎样去 确立和实行伦理道德规范的问题。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如何使人获得实力,因为法家 认为“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只有拥有了“力”,才能“述仁义于天下 ”(《韩非子·靳令》)。所以他们鼓吹以力致功,在耕战中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 又由于主张历史进化、时代变化,在道德教育内容上坚持不断前进、更新,适应发展的 社会政治,提倡道德教育内容的不确定性,“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 礼之循”(《商子·更法》)。相对说来,各家的道德教育内容中,儒家的道德教育内容 更广泛、丰富,具有实现个人、社会双重道德目标的知识基础,更适合开发人的主体性 。
三、四大家在教与学方法上的异同
(一)对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上的异同。
四大家在道德教育方法和策略的选择上都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墨家的人性观与 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判断接近。墨子明确提出人的本性或品德本来并没有善恶 的区别,而是后天“所染”: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 色亦变,五入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所染》)他对孔子自相矛盾的 德育环境论、“天命”观提出了彻底的批判。认为孔子既主张学习重要,又承认“唯上 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的观点,是既让人裹头发又让人脱去帽子一样的矛盾 。[6]墨子把“有道者劝以教人”看作是教育的第一要义,而把“隐匿良道,不以相教 ”视为“天下之乱,若禽兽然”的一个突出表现。(《墨子·尚同》)而道家的人性观则 以“朴”为主,如最新发现的战国简帛竹书《老子》中“视素保朴,少私寡欲”。“朴 ”,即是自然原始状态,“同乎无欲,是谓素朴”(《庄子·马蹄》)。庄子甚至认为失 去这种自然性,人就失去了生命力。《应帝王》中“倏”、“忽”对“浑沌”的故事, 就是一个明证。(注:《庄子·应帝王》载:“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 帝为浑沌。倏、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 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故而他认 为保留人的独立性和个别性是必要的,反对“人为物役”,由此道家在道德教育方法的 选择上主张以恢复人性“朴”的本来面目为主要目标,实现“无为教育”。即教育者要 顺应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和个性特征进行因材施教而不妄为、不横加干涉、不要求 千篇一律,以无为的教育态度来实现“有为”的教育。与孔子的“无言之教”具有明显 的不同。“无为教育”就是顺应教育规律,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按其自身的要求去 做,以“无为”的态度去作为。老子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 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忘知第四十八》)
法家的人性观以人性恶、“人性利己”为主。如商鞅就认为:“名与利并至,民之性 ”(《商子·算地》)。韩非认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韩非子·难二》)。因此 ,在道德形成上主张“德生于刑”(《商子·说民》)。而在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则主张重 术势,重外部制约。“耿介之士”最为法家看重,因为统治阶级需要一批忠贞耿直的能 臣智士。与孔子不同,出于政治考虑,法家认为一旦百姓掌握了过多的技巧和文化,会 带来动乱,难以管理,“乐则淫,淫则主佚”(《商子·开塞》),主张“朴农”(《商 子·耕令》)。以法为本,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反对开启民智,对普通人的道德教育 不重视,教育内容除了法律,就是“耕战之术”。法家对孔子的道德教育目的大加指责 。因为法家认为,教育可以开启民智、增长知识,使人性中恶的本性进一步扩大,破坏 了君王刑、法、术、势的强硬统治。他们认为儒家的仁义德教是“暴之道”(《商子· 开塞》),使人“偷乐而后穷”(《韩非子·六反》)。但法家同时又强调人若要为我所 用,就须用“隐栝”之术改造之。[7]
(二)对发挥教师主导性方面的异同。
在发挥教师的主导性方面,孔子讲究在潜移默化中通过教育来影响学生。他在自己的 长期教育实践中,处处以高尚的品行给学生示范,以真诚恻隐的人格熏染学生,深受弟 子和后人的崇敬和赞叹。颜渊曾由衷地称赞孔子的道德人格:“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论语·子罕》)孟子叹服孔子“出于其 类,拔乎其萃”。(《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孔子率先倡导的教师以身作则,在我国漫 长的教育史上,为历代教育家所推崇,并逐步演化成为我国学校道德教育的一项原则。
墨子对人性可塑性的认识更清醒,因而更重视教育对人性的影响、熏染作用,也更强 调教师用怎样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来教育学生,以达到直接影响学生道德是非观念和 个人品质的形成。所以他非常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不像孔子“叩则鸣,不叩则不鸣” ,而是主张“强说人”、“行说人”的主动教育。在当时社会混乱、道德沦丧的现实之 下,他深知进行道德说教不易。他指出:“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 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之也。”(《墨子·公孟》)说明要人接受从善 之道不易,要奋力而为,循循善导才能奏效。虽然墨子在谈到教与学的关系时说:“唱 而不和,是不学也。智少而不学,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适息。” (《墨子·经说下》)主张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应构成和谐的关系。但墨子教育思想更强 调教师的影响、熏染作用而忽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从“尊天事鬼”的道德规范出发, 墨子还企图借助“天”、“鬼”等超自然的力量威慑或督促人们践行道德要求。同时, 由于墨子主张“尚同”,在他设计的贤人执政下,要求人们有统一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人 们的思想行为,要求人们以“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 》),积极采取“上同而不下比”的示范教育法,才能获得一定的效果。但是他以“天 子”(最大、最正确的教师)的是非为是非,实质上让学生放弃了道德判断,没有了自主 选择,与他的环境论中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一样,表现了墨子对道德教育中学生主体性 的忽视和矛盾性。
道家看重的往往是直觉和无意识,所以道家认为教育者要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 位,让受教育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发展,同时也应尊重教育者即教师的主体地位。 他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养德第五十一》道家认为道 之所以受尊重,德之所以被人珍贵,就在于它不施加影响,而让万物顺其自然。“是以 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老子·守微第六十四》)因为道对于万物来说只是居于辅助立场。所谓辅助,只是依 照万物本来的状态去发展,所以圣人也应是辅助百姓的发展而不加以制约。教与受教者 之间应建立在平等和合作的关系基础上,而非统治与被统治、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基础 上。这种平等和合作的师生关系,对学生主体精神的充分发挥,主体人格的丰富与完善 以及学习积极性、主动性的有效激发都有重要作用。庄子更注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他 在《外物》中“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的教学境界,就是一种教者有意设教而 让学生在无意之中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性格和本然状态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成长发展 方向的最佳教育状态。道家要求学生自己领悟真理,教师就应当遵守后发性原则,“感 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庄子·刻意》)这虽然说的是为人之道,用于 道德教育也无不可。教育要后发起人,不宜先入为主,要承认人的教育过程,保证道德 教育的主动性和准确性。
法家在道德教育上强调借助政治的强势力量,主张以刑、势来压服人们人性中的“自 为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视民如婴儿”(《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 》),“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强调吏(教师)的威严。而对于学生(或者 是“民”)则处于被动受制的客体地位,这与孔子倡导学生主体性的教育方法大相径庭 。法家道德教育中把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道德在这里处于政治的附庸地位。从积 极的方面看,这样借助政治的强势,有助于营造道德教育的良好环境。因此他们不重视 个别教育而重视全方位的效应,主张“用众舍寡”。不是探究受教育者的个性特征,而 是“因之人情”。所谓“人情”,是普遍的“人情”,韩非子解释为“民之所有者也, 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所以主张君王(最大的道德规则制定者)以赏使利,以 誉使荣,顺应人情,引导人心,最大限度地规范道德行为,也就是控制人心。(《韩非 子·制分》)即使有重视个体主体性倾向的韩非,也只提倡“人主”个人素质的提高, 掌握“御臣”的技巧。而对臣民有选择的教育,服从就是美德,“尽力守法”即是忠臣 (《韩非子·忠孝》),因为教育是使人人成为为国为君有用的人,成为统治阶级需要的 忠贞耿直的“耿介之士”而不在于个人的道德修为是否成功。这当然不是说法家完全不 重个人道德教育。韩非子就曾体会到教育的困难性,他说:“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 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 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韩非子·说难》)韩非子认为:道德教育要深刻理解受 教育者的心理,找准切入点,才能达到德育的目的。正是因为法家过分强调环境对人的 作用,才会忽视人的主体性,忽视人对社会、他人的责任。
总而观之,由于四大家人性观的不同,导致他们在道德教育方法的选取各有不同。儒 家重主体性,主张以教化为主、自修自养;道家认为“道”是一种“本无”,是超于任 何感觉和认知的,不是可以冠以任何名称的东西,所以,人要教化自己,就要“我无为 民自化”(《老子·淳风第五十七》)。只有在儒家“陶心淑性”的教化基础上,这种“ 自化自正”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显示出它的意义。因此也可以说它是对儒家教化后的再 教化,是对儒家教化思想的补充。而墨家和法家都过分强调环境的影响作用,在对人的 主体性上有不同程度的忽视。
四、四大家在学、行关系上各有侧重
孔子倡导学、思结合与知、行联系的原则。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孔子认为“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即学习不加思考,就容易受书本的 欺骗;相反,脱离实际的空想,不认真体会前人积累的知识,也是危险的事。在“知” 和“行”的联系上,孔子强调“多闻多见”是知识的基础。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 ,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就 是知识要在“多闻、多见”上狠下工夫,然后择善而从,识别真伪。同章中孔子还说: “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孔子认为:书本上的知识,我和别人 差不多;但在生活实践中做个君子,我还没有能做到。可见他对知、行关系看得很重要 ,而且对知识分子,特别强调“躬行”。
孔子很注意道德的实践——行。他说:“力行近乎仁”(《中庸》)。他的弟子子夏也 说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 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可见,在道德培养上,他是相当重视实际行 为的。当然,孔子所谓的“行”的内容只能是践履躬行他所倡导的道德规范。
孔子坚持学、思、知、行的教学原则,要求“学思结合”,坚持“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的原则(《论语·述而》),运用“叩竭法”[8],实行“因材施教”,注意发挥学 生的主体性,给学生以思考的空间,通过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使知识真正为自己所拥 有,并且通过实践来印证。所以学习、思考、获得真知、实践印证便是教师教学的全过 程,也是学生学习的全过程。
孔子学、思结合与知、行联系的教学原则,后来被他的孔子子思发扬光大。子思在《 中庸》中有这样一段话:“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 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 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 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里提出学习要做到学、问、思、辨、行;同时还 要做到学要能,问要知,思要得,辨要明,行要笃,这样就会“人一己百,人十己千” ,其结果就会使愚笨的人聪明起来,柔弱的人刚强起来。
墨子更重视经验的积累,强调认识始于新知,终于“智知”。他提出著名的“三表法 ”,即要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以为刑政,观其 中国家百姓之利”的“本之”、“原之”、“用之”。(《墨子·非命》)在如何获得经 验的问题上,墨子强调学习的意志是关键,指出:“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 》),把“自苦而为义”(《墨子·贵义》)作为对学生的基本要求。要求他们“自苦而 为义”,“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要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为正义事 业而勇于牺牲的精神,并通过这种精神学得的理论还要通过“用之”来检验。所以在学 与行的关系上,墨子主张“行为本”,要求学生在道德实践上要“强力而行”,提倡君 子的自我修养,并主张在实践中不断增强修行最终达成君子之道。[5]墨子自己就是一 个实践家,同孔子一样,他重视以身作则的身教,反对“坐而言”却不“起而行”者。 同样,判断人是否有仁义,墨子不是看他是否懂得“仁”的概念,而是看他的行为上是 否能够正确从善去恶。他说:“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 ,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 也其取也。”(《墨子·贵义》)所以在道德教育的评价上,墨子强调用“合其志功而观 ”(《墨子·鲁问》)的评价方法,主张把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作为评价道德是非的一条 原则。
孔子和老子因对人性的看法各异而导致他们不同的治国主张。孔子着眼于后天的“习 ”,主张用“仁内礼外”兼治的方法来达到政治清明;老子则认为人性素朴自然,统治 者当效法天道“无为而治”。庄子与老子一样主张道德教育要顺遂人性,不要“乱天下 之径、逆物之情”(《庄子·在宥》)。乍看上去,庄子是既不要“学”,也不要“行” ,更无从谈其“学”与“行”的关系。其实庄子是主张人要靠自己来领悟和探究真理的 。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 知北游》)既然教师的教育要后发起人,要承认人的教育过程,保证道德教育的主动性 和准确性。那么个人领悟、探索的过程当然包括学习和实践环节。老子也说:“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象元第二十五》)即人可以在大自然中学习 到一切,这里的“法”就有“习”、“效”的意思在里面。
法家德育目标很重要的一点是“以力致功”,主张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以实力服务社会 、建功立业。所以在道德教育实践上主张积蓄力量,依仗“气力”获得实绩。对于那些 “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商子·画策》)的不劳而获者以及使“治乱之功 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韩非子·孤愤》)的空言误国者是深恶痛绝的。当然 这些“力”的积蓄,必然有学习的过程,即“修其身”、“执一以静”(《韩非子·扬 权》),虽受制于外部,却能在学习中有限度地提升自我,顺应外部,完成“以力致功 ”的使命。“学”是“功”的起点,“力”是“功”的保障,最终是为了“至德”、“ 大功”。
总之,由于四大家道德教育目的的不同,对待“学”与“行”的关系也多有不同,各 有侧重。孔子为达到“学以致用”、“学能大用”的目标,主张“学”、“行”、“思 ”的结合,强调学习是一个反复实践、“下学上达”的辩证过程,需要道德教育对象的 思维与具体行为上的积极参与,需要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墨子为实现其为“天下之 利”的目标,主张“学”与“行”的统一,以“行”为本。道家主张为保证道德教育的 主动性和准确性而后发起人,靠道德教育对象自己的力量自化自正。法家主张“以力致 功”,反对空言。这些理论对我国的道德教育重视言行一致、学以致用优良传统的形成 ,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标签:儒家论文; 道德教育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法家论文; 人性观论文; 道德论文; 教育的目的论文; 先秦诸子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人性论文; 墨子论文; 韩非论文; 墨家论文; 道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