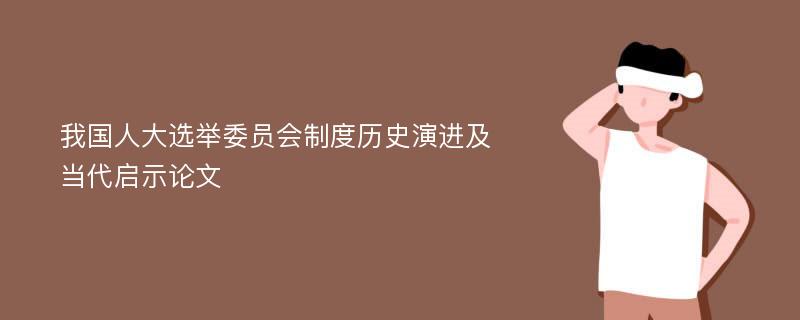
我国人大选举委员会制度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陆 强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1953年《选举法》框架下的选举委员会作为办理选举事宜之临时机关,负责监督、指导《选举法》的执行。这一时期的选举委员会地位高、行政权属性特征明显,成员代表性强且不实行回避制度,工作任务存在层级性差异。1954年《宪法》确立了新的国家权力架构,选举委员会的地位和功能开始弱化,选举管理权力的重心由中央下放地方。1979年《选举法》在县乡级人大选举中恢复了选举委员会的建制,并在其职责、组织及运行机制等方面作了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逐步强化选举委员会在人大直接选举中的作用。
关键词: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委员会;选举法
2015年《选举法》[注] 1979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简称。 第六次修正,就选举委员会等选举机构的职责作补充规定。时隔五年,选举机构相关议题再次引起最高立法机关的关注[注] 2010年《选举法》修正恢复了1953年《选举法》有关选举机构的专章规定,对县乡级人大代表选举委员会的产生、回避、职责和工作要求作了较为“完整”的法律阐述。 ,凸显选举机构在新时期人大选举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县乡级人大代表选举的主持机构,选举委员会居于选举机构体系的最前沿,对于选举法律规范的执行作用重大,直接决定人大代表民主选举活动的法治化水平。本文以《选举法》第六次修正为契机,就我国人大选举委员会组织建构及相关制度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以期对选举委员会的良性发展和运行有所助益。
一、 1953年《选举法》 [注] 本节所称《选举法》,如无特别说明,仅指 1953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的体制初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并没有立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中央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地方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3-14条。 。尽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称《共同纲领》)已经确定国家未来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关于会议召集时间却迟迟未定。直至1952年10月,党还曾想通过召集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推迟全国人大会议的召开时间。然而,斯大林出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和对敌斗争的需要,建议中国共产党于1954年进行人大代表选举和制定宪法[注] 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63-69.。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第20次会议决定于1953年召开由人民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在谈及选举的目的和作用时指出:“为了发扬民主,为了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要办选举”[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20.。由此可见,1953年的人大代表选举有着深刻的反帝斗争的国际政治背景,对于选举的民主化、规范化、制度化有较高技术要求。会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席、邓小平等23名委员[注] 1953年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包括中共、各民主党派及各方面人士,分别为:安子文、李维汉、李烛尘、李章达、吴玉章、高崇民、陈毅、张治中、张奚若、章伯钧、章乃器、许德珩、彭真、彭泽民、廖承志、刘格平、刘澜涛、刘宁一、邓小平、蔡廷锴、蔡畅、谢觉哉、罗瑞卿。 组成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选举法》,就选举委员会性质、产生、成员构成、任务等内容作了专章规定,为我国人大代表选举提供有效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4月3日,新成立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根据《选举法》之规定,发布《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中央选举委员会1953年指示”),对基层选举委员会组织及选举工作的具体展开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在《选举法》以及中央选举委员会1953年指示的框架下(即“一法一指示”),选举委员会制度初具雏形。
(一)办理选举事宜之临时机关
《选举法》第35条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选举委员会为办理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宜之机关”。邓小平在1953年《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亦指出:“为了监督和指导选举法的确切执行……应迅速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的选举委员会”[注] 邓小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J ].安徽政报,1953(3):26.。由此可以确定,选举委员会为办理选举事宜和《选举法》监督、指导之执行机关。选举委员会《选举法》监督、指导机关的功能定位,对于切实推进《选举法》的贯彻落实具有实质意义,这也是我国现行《选举法》最稀缺的法律品质。基于选举工作阶段性、周期性的因素考量,这一时期的选举委员会采取临时机构模式。关于选举委员会的成立时间,邓小平在1953年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的一份电报中指出:基层选举委员会不应马上普遍成立,而是采取哪里开始进行选举才在哪里成立的办法[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099.。其他层级的选举委员会在基层选举委员会成立前即宣告成立,以便于对下级选举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指导。《选举法》第41条规定:“选举委员会的工作全部完成后,选举委员会即行撤销”。由此可见,作为临时机构的选举委员会,于选举进行时成立,选举结束后即行撤销。
(二)机关行政权属性特征明显
《选举法》第35条同时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选举委员会,应在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下成立。中央选举委员会由本级人民政府任命,地方各级选举委员会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任命。邓小平在1953年《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进一步指出,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级选举委员会的工作[注] 邓小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J ].安徽政报,1953,(3):26.。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制度采取议行合一的模式,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担负“议”和“行”双重职能。1954年宪法明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相当于宪法草案规定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注] 阚珂.1954 年制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转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N ].法制日报,2015-06-11(3).。有学者甚至认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中央人民政府不仅仅是“议行合一”的,而且是“议、行、军、审、检”五权合一[注] 周永坤.议行合一原则应当彻底抛弃[J ].法律科学,2006,(1):57.。与中央人民政府不同,在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权力混合色彩逐渐淡化,回归行政权本位。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依据1953年《选举法》成立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权力来源带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混合色彩,地方各级选举委员会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任命,及其与本级人民政府工作上的领导关系,则使地方各级选举委员会的行政性色彩更加浓厚。
(三)机关地位高成员代表性强
中央和地方各级选举委员会各设主席1人,委员4~28人不等[注] 参见1953年《选举法》第36条。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任命刘少奇为新成立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彭真、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李维汉等28人[注] 中央选举委员会其他19名委员分别为:李四光、何香凝、沈雁冰、胡耀邦、高崇民、马寅初、马叙伦、陈叔通、章伯钧、习仲勋、程潜、程子华、刘格平、刘澜涛、刘景范、邓子恢、邓颖超、赖若愚、谢觉哉。 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从成员构成上来看,中央选举委员会堪与政务院比肩[注] 中央选举委员会29名成员包括5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共6位)、3名政务院副总理(共5位)。另外,彭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950年陈云递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候补书记仅剩彭真1人),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 ,具有较高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为其独立履行职权提供组织保障。在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中,代表性是国家机关组织、构建正当性的传统考量因素。为树立中央选举委员会中立、公平、公正形象,中央选举委员会汇集了来自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方面的人士。中央选举委员会这一组织模式,对于地方选举委员会的组织具有直接参照意义。
1979年《选举法》的制定以及选举委员会组织系统的恢复,与我国新一轮地方国家权力结构调整相伴而行。就在新的《选举法》正式交付表决3天前,全国人大会议对通过仅一年的“七八宪法”作了再次修正。根据新的宪法修正决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务委员会,取消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亦不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人民委员会),设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地方人大和政府由1954年宪法设计的议行高度合一的模式开始实现初步分离。宪法修正决议同时规定,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范围向上延伸到县一级(包括县、自治县)[注] 参见《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第2-3条。 。1979年《选举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新的选举机构制度设计。
因此现在还不能武断地说,某些产业就不适合网络协同,可能要从更长的时间段,在更大的产业范围内来思考这个问题。
为选举委员会配备“豪华”的成员阵容,有利于提升选举委员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对于其保持履职独立性、自主性具有积极意义。但成员间较高比例的交叉任职,容易使选举委员会被其他机关“渗透”,在其他机关的“围城”中丧失自我。成员代表性的过分强调,使选举委员会工作能力得不到有效保证,不利于选举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成员资格条件有特定要求
作为统一的机构组织系统,选举委员会的任务具有同一性,但层级不同面临的具体任务也会呈现一定的差异。一般而言,各级选举委员会任务主要有:(1)监督选举法在辖区内的执行;(2)受理选举违法行为的检举和控告并作出决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选举委员会仅限于选民名单事项;(3)公布本级当选代表名单并颁发当选证书。中央和省、县、设区的市选举委员会还负有如下两项任务:(1)指导地方各(下)级选举委员会的工作;(2)登记本级人大当选代表。此外,作为国家处理选举事宜最高层次的选举机关,中央选举委员会还负有如下职责:(1)指导《选举法》在全国范围内的执行,解释《选举法》,依法发布指示和决定;(2)规定选举相关表格、证书格式和印章型式。而作为承担代表直接选举工作的最基层选举机关,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选举委员会,有着一些与中央和省、县、设区的市选举委员会不不一样的选举任务:(1)登记、审查和公布选民名单;(2)登记和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3)按照选民居住情况划定选举区域;(4)规定选举日期和选举方法,召开并主持选举大会;(5)分发选民证;(6)计算票数,确定本级人大当选代表[注] 参见1953年《选举法》第37-39条、第66条。 。选举委员会工作任务上的层级性差异,与不同层级选举委员会的功能和定位直接相关。高层级选举委员会的任务具有宏观性、指导性特征,低层级选举委员会的任务则更为微观和具体。保持选举委员会组织机构体系的完整性,有助于选举委员会保持主体地位,提升专业化水平。
在逆城市化趋势下,从事简单劳动的进城务工人员被机械化所代替,面对高昂的居住成本和消费水平,从事简单劳动的务工人员将开始返乡之路。为了将这批返乡农民工妥善安置,政府不得不提前开始进行农村、乡镇及中小城市建设,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和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劳作条件,大兴农田水利,提供更多工作机会,这也正是目前大规模进行新农村建设目的所在。而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阶层,面对大城市越发激烈的竞争和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乡镇日益增加的工作机会,也会有相当一部分选择乡镇的静谧与安逸。
根据《自卸车液压系统技术条件》规定,液压油温不得超过80 ℃。但在夏季环境温度较高,铰接式自卸车液压系统多次出现油温报警,液压系统温度最高时甚至达到了100 ℃以上。因此有必要分析研究铰接式自卸车在环境温度40 ℃,油液温度30 ℃条件下的热平衡特性。
1956年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和镇第二届人大代表选举[注] 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第一届人大选举从1953年开始,1954年上半年结束。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选举从1954年上半年开始,至1954年8月结束。根据1954年9月21日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地方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5条之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因此,至1956年人大换届选举仅限于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的主持机构为本级人民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任命的主体机关降格为在本级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建立的办理具体选举工作的机构[注] 〔32〕周恩来.国务院关于1956年选举工作的指示[J ].国务院公报,1956,(22):504.。中央不再单独设立选举机构,1953年4月曾对基层选举工作发布指示、1954年4月与政务院联合发布对于召开省市县人大会议问题决定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已不再发布指示或决定,取而代之的是依据1954年《宪法》成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务院。在省、自治区层面,“选举委员会”被“选举工作办公室”〔32〕所取代。及至1958年人大代表选举时,《国务院关于1958年选举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仅提出“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应该成立选举工作的领导机构”[注] 国务院关于1958年选举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J ].国务院公报,1957,(53):1108.,对于“选举工作领导机构”的名称、形式并未予以明确。有的省份仍以省选举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选举实施方案,如《江西省选举委员会关于1958年选举工作的实施方案》;而有的省份虽然成立了省选举委员会,但却以省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布指示,如《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1958年选举工作的指示》;有一些省份则以中共省级党委、省人民委员会发布指示,如《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关于1958年选举工作的指示》。
绿色矿业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序列之一,绿色矿山则是实现绿色矿业的中心环节和主要载体。绿色矿山的实施主体是矿业企业,绿色矿业实施主体一般包括政府主管部门、矿业企业、矿业协会、社区组织等,比之前者涵盖范围更广。如果说绿色矿业是矿业发展的“线”的维度,那么绿色矿山则是这一线条上的“点”,也即绿色矿山是绿色矿业的基础经营单位,绿色矿业是绿色矿山的成果集成和延伸。
(五)工作任务呈层级性差异
选举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体性政治活动,选举委员会人员构成影响人民对于选举的公共观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举活动,对于选举委员会人员构成也会具有特定要求。关于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条件,邓小平在1953年《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专门指出:“鉴于全国各地情况不一,而我们又系初次进行这样全国性的选举”,“任务繁重”,“无论领导方面或群众方面都还缺乏经验”。“如果选举委员会工作能力不强,是无法胜任的。所以挑选一批为人正派、办事公道而又联系群众的人到选举委员会工作,是办好选举的关键”[注] 〔21〕邓小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J ].安徽政报,1953,(3):21、26.。中央选举委员会1953年指示亦特别强调:“必须慎重选择为人正派、办事公道、能联系群众且有一定办事能力的人充任”[注] 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J ].安徽政报,1953,(4):3.。由此可见,1953年中央和地方各级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条件首重人品,且对工作能力有特别强调。
(六)机关行为责任难以追究
依据《选举法》之规定,选举委员会为临时性机构,选举工作结束后即行撤销。选举委员会撤销后,因职务行为产生的责任归属问题,《选举法》无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选举委员会分别由本级和上一级人民政府任命,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级选举委员会的工作。《选举法》第40条亦明确规定:“选举后,各级选举委员会须将关于选举的全部文件,送交各该级人民政府保存,并应迅速向上级人民政府和上级选举委员会作选举总结报告”。因此,选举委员会撤销后因履行职权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本级或上级人民政府承担。由各级人民政府代选举委员会承担责任之法律逻辑,不利于选举委员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容易在工作中滋生怠职或滥权现象。选举委员会的临时性,容易使相关部门疏于对选举委员会成员职务上违法犯罪行为的监督和责任追究。作为各级人大执行机关之各级人民政府,为免于承担法律责任,可能会为选举委员会开脱。
1953—1954年人大代表选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具有普遍意义的人大代表选举。除中央和地方各级选举委员会外,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地方人大主席团[注] 1953年《选举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选举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之”。 在选举中也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地方人大主席团主持上一级人大代表“大会选举”[注] 为与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的“选举大会”作区分,此处的“大会选举”主要是指间接选举中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对上一级人大代表的选举。 的做法,为1979年《选举法》接受并延续至今。选举委员会法律监督执行机关地位的确立,上一级人民政府对地方各级选举委员会的任命,选举委员会上下级工作指导关系的确立,县市对于乡镇等基层选举委员会主席的派任,对于提升选举委员会的工作能力,保障选举法律规范的实施,具有积极意义。
二、 1954年《地方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注] 1954年《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简称。 的结构调整
(一)选举委员会地位和功能弱化
1954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确立了新的国家权力架构,人大选举机构体系也随之作了调整。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地方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将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交由本级人民委员会主持[注] 1954年《地方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第28条规定:“县级以上的人民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二)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乡、民族乡、镇人民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二)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1954年《地方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选举的“主持”,与1953年《选举法》的规定不同。1953年《选举法》关于选举的“主持”,仅限于主持选民参加的“选举大会”或代表进行的“大会选举”[注] 参见1953年《选举法》第39条第6项、第54条第2款。 。1954年《地方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选举的“主持”,是指对代表选举活动的总体规划和安排[注] 1979年《选举法》同时在这两种意义上使用“主持”一词,参见该法第7条、第31-32条。 。我们通常所说的“选举主持机构”,即是从后一层意义上来说的。
关于选举委员会成员任职资格问题,《选举法》没有规定。邓小平在1953年2月28日的电报中指出:凡属担任选举委员会委员的人,一般地应是可能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人[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098.。因此,选举委员会成员人选的任职资格与代表候选人资格一致,并无其他特殊要求。关于选举委员会成员回避问题,邓小平在1953年《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认为没有回避的必要,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大代表选举主要是间接选举,间接选举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大会投票方式完成,“大会选举”由大会主席团主持,不是选举委员会;二是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虽然由选举委员会主持,但基层选举委员会的工作是在上级选举委员会派出的工作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因此亦没有回避的必要〔21〕。事实上,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间接选举中相关选举委员会承担监督、指导、受理检举和控告等职能,选举委员会仍难以摆脱“做自己案件法官”的窘境。直接选举中上级选举委员会派出工作组[注] 上级选举委员会派出工作组与基层选举委员会主席存在人员交叉。 监督、指导基层选举,并没有否认选举委员会“做自己案件法官”的现状,关于选举工作组监督、指导功能的强调恰恰凸显了选举委员会成员回避的必要。
(二)选举管理权力重心由中央下放地方
选举委员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与选举管理权力配置的调整密切相关。1953年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具有开局意义,因此成立专门负责“选举事宜”之中央选举机关,统筹全国选举事务。人大代表首次全国普选后,选举工作确立了基本的活动规则和程序,积累了实践经验,后续的选举有先例可循,中央选举机关的存在就没有首次选举时那么迫切。由于当时的选举主要是间接选举,只有基层人大选举采取直接选举模式,将选举管理权力下放省级人民委员会,由省级人民委员会负责处理辖区内的选举事宜,可以减少选举管理层级,便于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采取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对于中央和地方选举管理权力关系的这种变化,内务部长谢觉哉在1956年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进一步解释称,对于选举工作中的问题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就地解决,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问题等特殊情况,由省级人民委员会权宜决定,报中央备查;其他一般性的地方问题都由各省级人民委员会负责处理。内务部主要负责全国选情的掌控,总结交流经验等具体选务,组织中央有关部门统一研究相关问题并提出意见,报请国务院决定[注] 谢觉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关于1956年基层选举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意见[J ].陕西政报,1956,(12):517.。中央与地方选举管理权力的这一配置模式为1979年《选举法》沿袭。
1954年《地方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选举主持机构的地位,与当时我国地方人大仍保持高度“议行合一”的政权制度模式密切相关。人民代表大会并不是常设会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只有在开会期间才行使权力,绝大多数闭会的时间里,其权力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人民委员会行使,选举事项的管理亦不例外。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主持本级人大代表选举,客观上限制了各级选举委员会的权力,降低了选举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弱化了选举委员会的功能和作用。在扩大省级人民委员会处理地方选举事务自主权的同时,直接导致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取消,省、自治区选举委员会也开始被选举工作办公室取代。1953年《选举法》设计之选举委员会制度,经过第一次人大代表选举之后产生的重大变化,与《选举法》相关制度设计时间仓促[注] 从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议成立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到同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选举法》从起草到通过不到1个月时间。 有一定关系,更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时代背景以及1954年国家权力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从1954年开始,全国人大先后经过1958年、1964年3次代表选举,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被虚置,地方各级人大和人民委员会被各级革命委员会所取代。尽管全国人大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曾一度恢复活动,但具有时代开新意义的人大代表选举还要等到1979年《选举法》通过之后。
三、1979年《选举法》恢复和发展新时期
关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选举委员会主席、委员如何产生问题,邓小平在1953年2月28日的电报中指出:选举委员会主席可以由同级党委中政府行政首长正职之外的负责同志担任,政府行政首长副职亦可担任。选举委员会委员可以在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人民武装部队中选择[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098.。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1953年指示,乡、镇等基层选举委员会主席由县或市选调干部派任。派至乡、镇等基层单位指导工作的干部,3至5人组成1个工作组,领导1至3个乡、镇。选举委员会“要有妇女参加”,“境内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应吸收其代表人物参加”[注] 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J ].安徽政报,1953,(4):2-3.。
2016年,十四团建团五十八周年,这一年十四团团史馆正式开馆,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一颗巨大的红色五角星镶嵌在天花板的正上方,十四团的前世今生在环形的大厅中一一展现,行走在这其中,有两鬓斑白的老者、有风华正茂的青年、也有刚刚学会走路的孩童,当问起其中的一位老军垦,这个博物馆建得怎么样,老人用朴实的语言回复我“好、好、好”,随后,在一盏老马灯前陷入了沉思。
与1953年《选举法》相比较而言,1979年《选举法》在立法理念上更为开放和稳健,《选举法》有关选举委员会的规定呈现出大轮廓、粗线条的特点,为选举机构保留进一步发展的法律空间。从立法技术上来看,1979年《选举法》并未就选举委员会制度作集中的专章规定,有关选举委员会性质、产生、职权等问题散见于《选举法》各相关条文。1983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代表直选若干规定》),就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委员会的组织、职权作出具体规定。直到2010年第五次修正,选举机构才开始作为独立一章在现行《选举法》中出现。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法一规定”的框架下,选举委员会进入初步恢复并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一)选举管理权力分散主体多元
从组织框架上来看,1979年《选举法》基本承袭了1953年《选举法》有关选举委员会的建构思路,但在组织结构上作了较大调整。中央、省、地市级选举委员会不再保留,地市级及以上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持,地方人大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的会议由大会主席团主持,代表选举的具体工作交由人大或其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完成。在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过程中,维持了选举委员会的框架机制,将其明定为县乡级人大代表选举主持机构。除选举委员会外,《选举法》还将省、地市级人大常委会确定为县乡级人大代表选举的指导机构,将县级人大常委会确定为县乡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领导机构。虽然法律、法规对选举主持机构、领导机构、指导机构的职权作了一般性规定,但实践中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想象中那般清晰。人大代表选举管理权力分散、主体多元的局面,是1954年《地方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结构调整的继续,仅有的不同在于间接选举中地方人民委员会的职权被地方人大常委会取代,地市级及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在直接选举中的领导、指导职能在《选举法》中得到进一步明确。
(二)法律保留机构常设化改制空间
在县乡人大代表选举中,选举委员会维持了1953年《选举法》临时机构设置的做法。与1953年《选举法》明确规定不同,1979年《选举法》并未就选举委员会临时机构的特质作出规定,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直选若干规定》也未予以明确。“代表选举期间(时)”设立选举委员会;选举工作结束后,选举委员会“即行撤销”“自行终止”“即行终结”“自行解散”的规定,主要见于省级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注] 〔38〕陆强.选举委员会常设化研究——以县乡级人大代表选举为视角[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53-54.49.。选举委员会的临时性设置固然有现实因素的考量,但总体而言它不符合选举事务管理权力连续性和整体性的要求,不利于选举委员会职能履行和责任追究,影响选举委员会功能的良好发挥〔38〕。就此而言,选举委员会作常设化改制符合选举发展的规律和内在逻辑。从《选举法》的规定上来看,选举委员会放弃临时机构的做法无任何法律障碍。
(三)机构职责日趋明确精细化
选举委员会职责是其活动的主要内容,选举委员会功能的发挥关键在于其职责的完善。选举委员会职责这一提法,是2010年《选举法》修正后才有的正式的法律表述。1953年《选举法》使用的是“任务”,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直选若干规定》使用的则是“职权”。采用选举委员会“职责”这一表述,反映选举委员会在强调职权能动性的同时,开始关注职权履行过程中的责任担当。1979年《选举法》制定时并未就选举委员会的职权作明确列举,有关选举委员会的职权散见于《选举法》相关条文,涉及职权约11项[注] 参见1979年《选举法》第7条第2款、第24条、第25条、第28条、第31条、第35-36条、第39条。 。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直选若干规定》开始就选举委员会职权作一般性列举,涉及职权11项[注] 参见《代表直选若干规定》第2条第1款。 ,其中新增职权6项。2010年《选举法》修正时,正式将这些列举上升到法律层面,并作了进一步地补充和完善。除一般性列举条款外,《选举法》以及《代表直选若干规定》其他条款还就选举委员会的职责作特别规定,《选举法》历次修正对此均有涉及。截至2015年《选举法》第六修正,选举委员会现行有效的职责条款涉及职权约28项[注] 参见《选举法》第10条第1款、第26条第2款、第27条、第29条第2款、第31条第1款、第33-34条、第36-37条、第41-42条、第58条,《代表直选若干规定》第2条第2款、第5条、第10条第2款。 。选举委员会职责日趋明确精细化,对于充分发挥选举委员会功能,完善选举制度意义重大。
(四)选举管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并重
“自己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基本要素之一,它要求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理涉及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务或裁决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争议时,应主动或应当事人的申请而回避[注]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六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75.。在人大代表选举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主要体现在选举委员会成员被推荐为人大代表候选人时的回避问题,这在我国长期以来存在重大分歧。2010年《选举法》修正肯定了选举委员会成员被推荐为代表候选人应辞去选举委员会职务的做法,具有时代开新意义!它以法律的执行力改变了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使选举委员会的公共观感得到进一步改善,将我国的选举管理从“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并重”的方向转变。诚然,如所有开新的制度一样,选举委员会成员回避制度是不彻底的,在选举委员会下设机构(办事机构、派出机构、选区工作机构)、乡级选举委员会成员,以及选举委员会会议回避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地检讨和完善[注] 陆强,陈伯礼.论我国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委员会制度的完善——兼议2011—2012年县乡人大代表选举[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30-131.。然而,这些瑕疵并不影响该条款在我国选举体制革新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如前所述,大量研究发现了身体活动与成功老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研究者更倾向于做身体活动对于成功老化的促进作用这一方向的解释。但是前人研究有很多是非实验研究,因此,对于身体活动与成功老化之间关系方向的解释似乎证据不足。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成功老化者似乎有更多的锻炼参与。因此,未来需要更多的实验研究和纵向追踪研究来进一步探讨身体活动与成功老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为老年人身体活动促进以及成功老化促进提供科学依据。
四、余论
作为较早践行民主选举的国家,美国在总结联邦选举法律规范实施的经验教训时发现:在诸多缺陷中,最为重要的是没有一部法律能够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机构去管理和执行法律的规定[注] See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Thirty Year Report ,Washington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 2005. P .4.。“尽管一个失败的候选人可以在联邦法院或国会一个委员会里就某种违法行为攻击他的对手或对竞选结果提出异议,但是并没有一个常设机构来调查对不正当行为的指控。两院的选举委员会以及调查竞选支出的专门委员会,在特殊情况发生时确实也进行深入的调查,但它们几乎都是党派性质的,主要只关心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注] [美]查尔斯·A .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册))[M ].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3.。“国会调查竞选运动财务管理问题的各种调查委员会,一向都是调查特定选举的各种特别委员会。它们没有工作班子,没有专门的会计技术或财力,以持续进行必要的工作”[注] [美]哈罗德·F .戈斯内尔、理查德·G .斯莫尔卡.美国政党和选举[M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274.。结果,这些条款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于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相对独立、拥有一定规则制定和司法裁判权的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简称“FEC ”)应运而生[注] See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Thirty Year Report ,Washington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 2005. P .5.。
选举委员会是选举法律规范执行和监督的法定机关,居于选举活动的最前沿,具体推进选举活动的进程。选举委员会的性质、组织、功能和作用,与一国的政治体制、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1953—1954年第一届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选举时,我国成立了体系完备、代表性强、地位颇高的中央和地方各级选举委员会,对顺利完成我国第一次人大代表选举发挥了重要的监督和指导作用,为选举法律的执行和具体操作规则的制定作了开创性和引领性的工作。1954年《宪法》确立新的国家权力架构,中央和地方选举委员会的地位和功能开始弱化,中央选举委员会等相继被取消、取代,直至各级人大被虚置、取代,不再召集会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生活步入正常轨道,定期性的选举开始恢复。然而,选举委员会的机构建制仅在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中得到承袭,全国、省、地市级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则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下级人大主席团及有关工作机构来完成。
选举管理是一项专业性要求较高的政治活动,在强调活动政治属性的同时应保障选举技术能够充分表达选民意愿,实现党的意志和选民意志的和谐统一。选举管理机构体系的分散性和选举委员会的非常设化组织建构,使选举法律的实施得不到有效保障。“选民民主意识教育和民主素质养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选民切身体验和感悟,需要选举委员会长期规划、系统安排和专业设计”[注] 陆强.选举委员会常设化研究——以县乡级人大代表选举为视角[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53.。选举委员会的附属性地位,更让其难以肩负应有的社会担当。《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向世人宣称:“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定期的、真正的选举需要选举法律的制定,更需要独立、专业、稳定的选举法律守护机关维持国家选举活动的周期运行。我国应逐步恢复建立中央到地方的选举委员会组织机构体系,在解释法律、制定规则、确立标准、指导工作、解决纠纷、监督选举等功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保障公民选举权利,提升选举法律规范的实施水平。
Locking J3-J7and reconfiguring the dynamics model of the manipulator,L1=Lais the active link,and links L2-L7 are locked together as the passive linkLp.Theposition vectors of the centroid relative to the coordinate Rpfor each link Li involved in Lpare shown asm,m,m,rp6
On the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and Systematic Evolution of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in China ’s People ’s Congress
LU Qiang
(Law School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China )
Abstract :The legal provisions of China’s Electoral Law (1953) stated that electoral commissions at all levels were authorized to monitor and instru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Electoral Law , as well as deal with issues concerning with elections of People’s Congress of different levels. Electoral commissions of the time behaved with distinct identification of executive power and high status. Electoral commiss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took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commission members with wide representativeness practiced no avoidance system. In the year of 1954, Chinese Constitution has clearly put forward a new 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to mitigate electoral commission’s responsibility and then limit its competence. The emphasis of election administration power is shifted from the central to local. While China’s Electoral Law enacted in 1979 restored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electoral commission in the election of deputies to People’s Congress at the towns and counties level, the law also made extensions and improvements to the duties, organizations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electoral commissions. Thus, electoral commissions could progressively exert an active effect on the direct election of the deputy to People’s Congress.
Key words :People’s Congress; electoral commission; Electoral Law
*收稿日期 2018-12-05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9年2月25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选举机构模式选择及制度完善研究”(项目编号:17CFX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陆强,男,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行政法学。
中图分类号: DF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69X(2019)03-0028-08
DOI. 10.19510/j.cnki.43-1431/d.20190225.001
标签:人民代表大会论文; 选举委员会论文; 选举法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