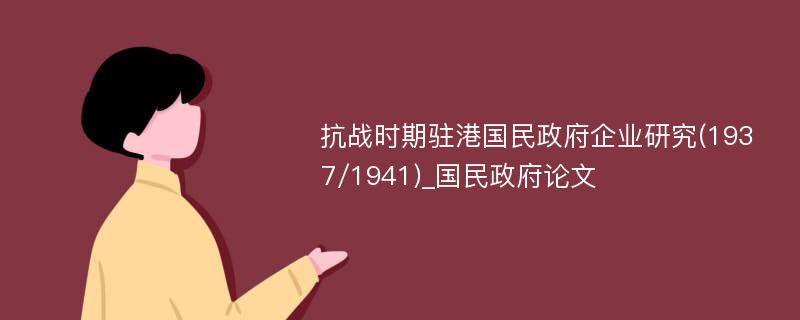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研究(1937-194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国民政府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前期,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所属的金融、外贸、运输等企业亦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使香港成为战时对外转运、国际贸易及外汇基金运筹的总基地。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企业调剂金融,沟通对外贸易,输出大量国产品,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外汇,同时又得以购进急需的军事战略物资,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持久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随着抗战史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关注到战时国营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并对其作用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如王相钦和吴太昌主编的《中国近代商业史论》第8章《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商业》第2节《国民党政府的贸易、物资管制及国家资本的商业垄断活动》中,提及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简称贸委会)“为维持债信、出口大量农矿产品,是做出了巨大努力的,对此应该予以肯定”。同时亦揭露了该会下属的3家国营贸易公司实行农产品管制、苛扰商民等经营弊端。①又如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第9卷第5章《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经济》第1节《外债与对外贸易》中,肯定了贸委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并提及该会所属的3家国营贸易公司。②郑会欣著《统制经济与国营贸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较详细地考察了抗战后期复兴商业公司的情况,肯定贸委会及其属下的国营公司在寻取外援、争取物资、调剂金融、促进运输、增加出口诸方面都发挥过积极作用。③按这些并未具体涉及抗战前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的经营活动,因此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一 香港在中国战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抗战爆发后,中国外贸中心逐渐向华南转移。尤其是在粤汉、广九两路接轨后,长江中游及西部各省之客货出入,大部趋向省港。沪宁失守后,长江下游之经济交通,概被日本破坏或把持。据海关1938年贸易报告书表明,上海出口总值下降,而广州及华南各口岸出口总值上升,该年沪粤对外贸易一升一降之差别,极为显著,俨然有以粤汉铁路代替长江航运,以香港取上海而代之的趋势。
1937年9月,香港进出口货物激增,主要原因即原运沪货物多改在香港起卸。如汉口因长江口被敌封锁,所有以前集中该埠转往上海出口之大批物资,均改趋省港外销。这年香港入口货物中,由中国大陆运来者价值为2.11亿余元,约占当年香港进口总额的34.2%。④
就对外输出入货物的内容而言,香港从大陆进口的主要是桐油、矿砂、茶叶、药材、蚕丝、猪鬃、瓷器、牲畜及农副产品。如1938年桐油经香港输出额超过由国内直接出口达1倍以上,钨砂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3强,茶叶则几乎全部经由香港出口。⑤从香港转输内陆的货物主要是军用物资和工业制品。当时,中国政府向欧美各国大量订购轻重工业机器、铁道器材及其他军需物品,主要是靠广九、粤汉两路输运入口。据估计,抗战初期中国70%的军事战略物资都是经过广九铁路从香港运到广东的。⑥当时英国方面认为:“保持该线路(指香港通道)开放对中国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下去,香港继续起转运中心的作用是一个关键因素。⑦日本侵略者也认识到:“中国事变发生后,香港对于中国承担了日益重要的任务。”在“香港港湾仓库里的军需物资堆积如山”,因此,香港是“重庆政府与列强保持联系的唯一门户,同时作为援蒋物资的中转基地或宣传、谋略基地,更加处于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⑧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香港与华南的正式交通路线被切断。不久,华南沿海重要城市亦相继陷于敌手,但内地货运尚能与香港保持经常接触,特别是香港通过澳门及广州湾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大为增进。1939年末,第一次粤北大捷后,广东战局趋于稳定,以惠州、淡水和西江南路为主的东西两翼与香港的贸易十分活跃,广州沦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快即淡化。在华南方面,中国政府开放惠州、淡水至大亚湾畔沙鱼涌的门户与香港通商,大量物资运往内地,粤战时省会曲江一跃而成为物资集散中心。
故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香港仍保持着重要的战略贸易地位。当时日本曾作分析,认为随着七七事变的发展,英国不得不从华北、华中退却,香港逐渐成为对日经济战的前沿阵地。它作为英美对日封锁、对蒋介石援助的据点,愈加意义深远。美英中经济会议多次在香港举行,三国为维持法币而成立的汇兑平衡资金委员会的本部也在此。英美还支持香港与内地国统区的秘密贸易,使国民党政权能通过香港维持战时财政。故对于重庆方面来说,“香港真正是抗战经济的中心”。⑨尽管日本舰队对中国沿海实行封锁绞杀,妄图切断中国的外援之路,但其阴谋却难以得逞。其中原因,除了中国军民(包括港澳爱国同胞)的顽强抗争,华南沿海海岸曲折、河汊纷歧、地形极为复杂外,还因英属殖民地香港的存在,日军无法阻止第三国(特别是英美)的船只往来,故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进出口业务源源不绝。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香港始终发挥着中国战时对外贸易主渠道的特殊作用。
二 战时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的分支机构
抗战爆发后,由于香港在中外贸易和交通运输中所处的特殊重要地位,国民政府国营企业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
(一)金融企业。广州、武汉陷落之际,国民政府所属中、中、交、农四行的一些机构于1938年10月20日迁移到香港。⑩翌年,四联总处为调整并加强各地分支处之机构起见,订定改组各地四联分支处办法,规定业务重要区域设立分处,次要地域改设支处,并限令各区于1940年1月1日改组成立。依限陈报成立者,计有包括香港在内的15个分处和17个支处(广州湾支处原属香港分处管辖,当香港沦陷后,于1942年初改为直辖支处)。(11)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早在战前即已设立了香港分行,现又将总管理处主体部分迁港,并仍与陷于“孤岛”的上海分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上海中行还在香港设有办事处。(12)
中国国货银行为官商合办股份有限公司,1929年11月创办于上海,为国民政府指定的经营外汇银行,由孔祥熙和宋子良分别任董事长和总经理。香港分行于1938年3月29日开始营业。(13)
上海沦陷,国民政府西迁,中央信托局因对外接运物资,于1937年底将主力撤退至香港。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派其子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可以说在此之前,中央信托局的首脑部门并不在陪都重庆,而是设在英国控制下的香港,业务行政由孔令侃在香港遥控指挥。(14)
此外,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原设于上海,抗战爆发后,先是一部分迁往香港,一部分迁往昆明,直至1940年时全部迁往重庆。(15)该局易货处总处原设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于1942年4月迁移重庆。(16)
邮政储金汇业局于战时设立了驻香港办事处,不久便感到该处人员不敷支配,应予以充实。为增加工作效率起见,遂将本局干部陆续迁港,“惟于名义上仍作为设在上海,以免敌人或有另设总局之企图”。(17)
(二)外贸企业。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加外汇收入,巩固财政,实行统制对外贸易,于1938年2月成立了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负管理之责。不久,中国战时贸易特别是官方出口贸易完全经由贸委会之手进行,其经营的货物包括桐油、茶叶、猪鬃、生丝、羊毛、苎麻、肠衣、各种动物皮等,业务繁多,范围极为广泛。贸委会下辖富华贸易、复兴商业及中国茶叶等3个公司,以利统制战时贸易。(18)这几家公司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且都在香港建有分公司。
富华贸易公司成立于1937年,总公司设在重庆,总经理席德柄,协理缪钟秀。下辖香港、云南、西北、陕豫、苏皖、江西、湖南、浙江、四川等分公司,均设经理和襄理。其中香港分公司经理为吴清泰,襄理为孙纯一。(19)
复兴商业公司成立于1939年2月,总公司设在重庆。董事长由孔祥熙兼任,总经理董承道、席德柄(后),协理周苍柏、沈士华。下辖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浙江、香港及仰光分公司,均设经理和襄理。其中香港分公司经理为林荣森,协理为周辨明。(20)
中国茶叶公司成立于1937年5月,总公司初设上海,后迁重庆,经理人为寄景伟、吴觉农、朱钱农等,在香港及内地各埠广设分公司。(21)
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植公司)是以经营植物油为主、官商合办的大型企业,隶属于国民政府实业部,1936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吴鼎昌、周诒春曾先后担任中植公司董事长,张嘉铸为总经理。上海沦陷后,特在香港九龙加设厂处,以便继续桐油出口贸易(22),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
(三)运输企业。轮船招商局早在19世纪70年代成立之初,即已在香港设立了分局。抗战爆发伊始,该局总经理蔡增基率员撤迁香港,成立办事机构,另由副经理沈仲毅领衔组织长江业务管理处,负责内河军公运输业务,各分支机构也先后进行了调整。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蔡增基逃往澳门避难,总局职权无法继续行使。直至1943年4月,招商局奉国民政府交通部令在重庆恢复总局。(23)
粤汉、广九两条铁路于1937年8月23日正式接轨通车,次年初,香港至广州的公路顺利开通并投入使用,粤港间公路与广九铁路并驾齐驱,成为抗战初期中国最重要的补给线之一。1937年10月1日,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因军运保密简称西南运输公司)在广州正式成立,担负繁重的国际运输任务。这是抗战前期中国政府所属最大的国际运输机构,有员工不下2万人,汽车约3千辆。(24)在香港、河内、新加坡及内地广设分处(香港先设办事处,1938年2月改为分处),形成一个对外联系香港、越南海防,对内联系中南、西南各省的铁路、公路、水路的综合运输网。1938年5月,又“奉命对于各机关在(香)港起卸之货物运输全权负责办理”,并设“关于铁路主持之机构,专一筹运”。(25)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贯通华南沿海与内陆的港粤国际交通线遂失去效用。西南运输处总处已于此前(9月)迁往昆明,并饬令香港分处于新加坡设分处,以便接转自香港疏散及承收向欧美订购之物资拨运仰光。次年2月,香港分处迁往昆明,并入总处,但仍留有交代清理人员,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才告结束。(26)
由上可见,战时国民政府驻港企业,除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轮船招商局系原在香港即有分行分局外,其余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才新建的。
三 战时驻港国营企业的经营状况
(一)金融机构的经营。国民政府所属中、中、交、农四行等在港机构的主要任务是调剂金融、管理外汇、平衡汇兑及维持法币。中央银行于1938年3月15日在香港设立通讯处,主要从事经营管理外汇(含侨汇)、口岸汇款和印制、转运法币钞券等业务。央行在海外印制的钞券“均以运抵香港为终点,而本行之加印签章事务,亦由中华书局在港设厂办理”。(27)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驻香港机构的业务和中央银行相似,主要也是经营管理外汇及印制、转运法币等。
中国银行把在内地汇往上海的款项先汇到香港,由香港中行出面联系上海的收款人,转由在香港的其他机构或商号,代为取款或转汇上海。直至1941年下半年,港英当局宣布限制提取法币条例,内地以法币汇港转沪这种业务才告结束。(28)
由于战时法币需求量大增,印制、转运法币是四行重要的经济任务。出于钞券的安全和质量考虑,国民政府一般委托国外公司印制,香港是四行印制法币的重要基地,直至1941年时,四联总处还曾“嘱各行在香港方面与各印制钞公司洽印钞券,计中央银行向中华书局接洽订印,中国、交通两行向商务、大东两家订印,中国农民银行向大业公司订印”。(29)
1939年2月至1941年6月,中美签订了4次易货借款,中英签订了2次信用借款,可购买各种急需物品,其中不少是利用香港输入的。中央银行口岸汇款七八成是购买战时用品,解款最多之处为香港,1940年达3600余万元法币,上海次之,为1530余万元。(30)
本来国民政府为防止资金逃避维护外汇市场,对口岸汇款除党政军及“国营”事业机关必要汇款核明承汇者外,限制特严。但1940年后,我国经济进入困难阶段,农业歉收,物价猛涨,通胀严重,外贸及国外物资供应日减,国家财政更为拮据。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经济问题上升到了重要地位。鉴于后方各地所需机器原料和日用必需物资,大部分仍须由口岸内运,口岸汇款之需要始终未减,四行总处于1941年提议开放港沪商业汇款,并决定“以便利后方商民为主要对象,售出外汇购运货物,以能运入后方者为原则”。平准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光甫复函云:“兹为鼓励上海或其他任何地方之物资内运前往自由中国,以调整上海与后方各地间之法币差价,并谋改善中国之经济情形起见,应由本会筹议种种办法,期与中中交农四行切实合作……今后尤宜加倍努力,增加中国物资供给。”(31)据四联总处的报告,1941年下半年重庆14家商业银行共汇往沪港7695万余元法币,其中香港为821万余元;由沪港汇入6079万余元,其中香港为2228万元。同期后方各地官方四行承汇港沪款项共计5297.5万元,其中香港为3351万余元。(32)
中央信托局的任务与四行有所不同,该局总部于1940年2月1日在重庆正式办公,但仍在上海和香港分地办公。驻港部门有中央储蓄会、购料处、易货处及信托处港处等,其主要业务是采购物资、吸收存款、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对外易货贸易。由于国内物资短缺,国民政府颁布集中采购令,规定国家机关一切采购物资事宜均委托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办理。当时中信局的采购处、所分布于香港、上海、昆明、重庆、海防及仰光等埠,而以香港为其枢纽。“港处因系自由港口,各项外货输入,均堪便利,现货供给较内地充足而齐备,即向国外订货,亦以商行林立,洽商方便,是以各机关托公案件多于此集中办理”。(33)据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驻香港通讯处负责人1939年1月16日致总处函称:该处由国外直接运往越南海防的材料,由香港中信局通知,一共已运10批(截至此函止),各批原提货单及材料清单、保险单等件,均由香港中信局直接寄往海防分局,转交本处。另该处还托西南运输处驻香港机构办理海防至昆明段之运料事宜。(34)又如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但凡购买仪器设备,多向香港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办理,据双方往来函件统计,仅1941年3至11月间,即共计42件,涉及仪器、绘图材料、书籍、测量仪器、车辆、现货等。(35)
(二)贸易机构的经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1938年以集中物资换取外汇为中心工作,办理各种农副产品对苏易货及外销业务。1940年因行政业务划分,1月首将全国桐油购销业务划归复兴商业公司办理。4月,中国茶叶公司改隶贸委会后,所有外销茶叶之收购易货外销等业务,均由其负责办理。6月,富华贸易公司接办贸委会桐油、茶叶以外出口物资的购销业务。(36)
富华贸易公司出口的猪鬃一直经由滇缅公路转运香港输向欧美。复兴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收购和运输桐油等农副产品,人事调配权都集中于总公司。抗战初期,总经理席德柄住在香港,公司的业务由协理缪钟秀主持。(37)
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以驻港机构为据点,开展桐油的国外贸易。数年间,营业额达1.24亿元,其中外销占70%。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该公司的国际贸易业务才完全中止。(38)
(三)运输机构的经营。西南运输处初期的路线一经香港至广州,一经越南海防至镇南关,并在省、港置有仓库设备。香港分处自1938年2月开始办理进出口物资运输,设有运输科,分铁路、水路、公路、仓库、装卸等5个股及九龙事务所。由于铁路运费低廉,时间快,故该处物资主要经铁路装运。这年2—10月,由铁路输入物资约13万余吨,达预期之半数,其中军需品占1/4,其余为五金材料、油类、机件等物。水路运输因轮船舱位有限,每月不过千吨,都是五金、电料等普通物品。公路运输则利用在香港装卸之新车驶入内地时,随时配运。至广州沦陷前,共驶入卡车1201辆,但带运物资仅600余吨,此项业务随广州陷落而告中止。
广州沦陷后,该处进出口物资改由航运至海防及仰光,再转入国内。因越南政府未许军用品通过,格于禁令,所运物资亦为五金、原料及汽车机器等项。仰光线则有军用品配运。此两线一年输入之物资约有1.6万余吨。由香港输往欧洲货物,托交英国、苏联籍轮船运送出口者,均为矿产,如钨砂、纯锑、生锑、锡、锌等,平均每月1次,历时10个月,共运出矿产12640吨。(39)
(四)香港沦陷时驻港国营企业损失殆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营企业驻港机构或被迫撤离,或被敌人没收和查封,损失惨重。
在金融业方面,日本占领香港后,对原有各国银行进行清理。1942年4月11日,日本总督宣布将在香港的英、美、荷、比等国13家银行和中国4家银行作为“敌产”而没收,存款被冻结,并授权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清算这些银行的资金。(40)除了国民政府中央所属的4行外,同年6月占领当局财务部又勒令广东省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4家官办金融机构停业,并令清算一切账目。(41)
在外贸业方面,香港沦陷后,国民政府财政部贸委会设在香港的3个分公司仓库均被日本占领当局查封,公司职员20余人撤退至广东惠阳。(42)
抗战开始时,富华贸易公司运往香港的货物,除准备在香港就地销售者外,一俟整理妥善,即随时尽速运转欧美,但1941年底时,美国船只驶往香港者甚少,以致待运之货舱位难得。当日本突向英美宣战后,香港航运骤断,富华贸易公司存于港埠的货物遂无法运出。据香港分公司于当年11月29日最后发出的存货报告称:计有猪鬃3860担(海关担,下同)、肠衣190担、山羊皮1393担、羊毛160担、羊绒161担、生丝955担、苎麻595担,以上货物收购成本价估计为962.4万余元,加上运费估计约409.1万余元,总共计约值法币1371.5万元。(43)
另据国民政府财政部贸委会档案记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复兴商业公司在香港的仓库存有桐油约1500吨,并有存款约20万港元、100万元法币和一些美金。日本入侵后,公司经理林荣森已失去自由,企业被日军政部兴亚机关接管。富华贸易公司香港分公司在香港存有杂货约4000担,也被敌接管并运走。另还有存款约150万港元、美金15万元和数目不详的法币。公司经理吴清泰亦失去自由。中国茶叶公司存茶约有10万箱,但存款数目不详。(44)可谓损失不赀。
从战后财政部编制的贸委会所属机关损失统计资料,亦可测知富华贸易、复兴商业及中国茶叶公司香港分公司3个单位损失之惨重。因为该会所属机关的损失主要为直接损失和商业机关的损失,直接损失占损失总计的99.38%,间接损失仅占0.62%;商业机关的损失占损失总计的97.42%,行政机关损失仅占2.56%。(45)
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植物油料公司香港分厂业务停顿,至日本投降后才恢复。(46)
在航运业方面,战时招商局不仅船舶遭受了巨大损失,江海各埠的分局(或办事处)也绝大多数被日军侵占或破坏,仓栈遭焚,码头被炸,营运被迫停业,香港分局的码头仓栈和上海、广州、天津等分局一样,只剩下一堆堆残骸。据1945年招商总局与27个分局(或办事处)的统计,该局在抗战时期财产直接损失达5827万元(法币原价)。(47)
四 战时驻港国营企业经营活动之评析
战时国民政府在港企业的经营管理尽管存在着一些漏卮,但主要方面是对抗战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驻港国营企业机构经营的弊端。
在近代中国国营企业中,官僚衙门习气和封建宗派作风历来是兼而有之,抗战时期当然亦不例外。如轮船招商局的管理机构受到战乱巨大的冲击,发生了自创办以来罕见的经济大案,经营管理一片混乱。1938年,招商局总经理蔡增基将随迁到香港的“海元”、“海亨”、“海利”、“海贞”等四大海轮出售给英商怡和洋行,索价34万英镑,“海云”轮也同时在香港出售。蔡氏令人将卖船收入、营业收入及其他经济收入均存入汇丰、广东等银行,数额颇巨。日本占领香港后,蔡增基遁居澳门,存放于香港的招商局档案、账册、财产契据等全部散失。据蔡氏事后称,他在香港沦陷前提出港币34万元,除少量开支外,余下30万元收藏在寓中,不料突被日军侵入,洗劫一空。招商局在这次案件中损失巨款,为开局以来所罕见,蔡氏在此案发生前后行动诡秘,疑窦甚多。国民政府交通部等有关当局对这一案件的审理,延宕数年之久,而当事人最终竟未受到任何的惩处。(48)
又如孔令侃在香港主持中央信托局的工作,因而有了发财的机会。他将亲信人员先后调港,利用香港是自由商港,大量进行私人进口买卖,赚取外汇。(49)
(二)战时国营企业在港经营的历史作用。
香港是抗战前期大后方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均在香港设立网点,如财政部贸委会驻香港机构、四联总处香港分处、香港中国银行团、中美英汇兑基金平衡委员会香港办事处、广东省战时贸易管理处香港办事处等,这些机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首先,金融业方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所属金融机构四行二局通过设在香港的分支行处,经营管理外汇,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资金的外流,增强了外汇储备,有利于汇率的稳定,保证军政机关的外汇供给;印制及转运法币钞券,解决了战时所需法币钞券供应不足的困难,保证了军需供应;采购急需物资、对外易货(中央信托局重点在香港专办接运军火转口越南海防、河内通过滇越铁路内运事宜,同时继续向欧美洽购军火),粉碎了敌人破坏我金融之阴谋,稳定了经济局势。
出口结汇政策亦使国民政府赚得巨额外汇,根据中国银行年度业务报告,1939年度按银行牌价结进港币92.4万余元,1940年度为373.9万余元,1941年度(截至11月底止)近1639万元,增幅大且远远高出英镑、美金及越币的款额。(50)
其次,运输业方面。西南运输处既是抗战时期国内战场急需的外援军需物资的主要承运者和供给者,又是中国主要战略矿产品和农牧产品的主要输出者。在广州沦陷前,利用铁路、水路和公路并驾齐驱,抢运物资。日军攻占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后,运输大动脉广九铁路中断,中国向英美等国订购运抵香港的各种物品,在货仓里堆积如山。中央政府“电饬留港办理人员,迅将趸存于港中之各种物品,转道输运返国。各专员奉命后,即开始规划,审查品物之先后急需,设法次第转运”。(51)其中西南运输处香港分处等所起之重要作用自不待言。
第三,外贸业方面。在战时收购和运输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为维持债信,出口大量农矿产品,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初期农产品中之茶叶、桐油、猪鬃、生丝及一部分皮张等产品均在香港或仰光交货,矿产品也大多在香港、仰光等地出口。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海运被阻,这种情况才改变。(52)
财政部贸委会是中国战时出口贸易国营化之官办商业机构的核心,竭力奖励土货,增加产量,扩大外销市场。并会同中国植物油公司、中央信托局、中国茶叶公司等,收购全国重要外销土货,集中香港出口,准予免税,故办理颇有成效。(53)
1938-1939年间,中苏签订了3次易货借款合约,苏方向中国提供了总值2.5亿美元的信用借款,用以购买苏联的军用物资,中国需以农矿产品输苏偿还。抗战前期,中国交苏偿债农矿产品大都是在香港交货的,对苏贸易逐年增加,1937年度总值600万港元,1938年度1500万元,1939年度达3000万元。以茶叶占首位,次为桐油、猪鬃等。(54)当时,中国的茶叶出口主要用于对苏易货贸易。为了保证交苏茶叶顺利输出,贸易委员会决定“将东南各省所产之茶,全部运抵香港交苏”。由驻港富华贸易公司合同苏方办理。(55)根据历年在香港交苏偿债茶叶货单记载:1937-1938年度为57765关担,另3200箱;1939-1940年度为12.4万市担;1940-1941年度达27万市担。(56)大量农产品从香港源源输往苏联,换回了重要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
抗战前期,美国是向我国提供贷款的第二大国,根据1939年2月签订的中美桐油借款合约,美国向中国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中国须于5年内用桐油偿还。战时桐油经国民政府确定为国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议决自1940年1月起,将全国桐油指定由复兴公司专营,购运出口以偿还外债。桐油运美偿还外债,对于国际信誉至为重要,国民政府为履行美国借款合约,收购、储运桐油,由内地分途源源输往香港,以复兴公司香港分公司为“转运枢纽”。虽受日本严密封锁,外销量仍逐年上升,如1939年合计由香港运往美国为1.8万余吨(单位:美吨),1940年合计运入香港有2.2万余吨,1941年增至3万吨左右。(57)由于复兴商业公司的出色工作,使中国在1942年就提前还清了全部贷款,“博得美国朝野的同情与赞赏,树立了我国债信,将来于对外借款上关系甚大”。(58)中国用桐油借款从美国购买了大量急需的工业制成品,增强了抗战能力。
评析国营企业的对外贸易统制政策及其作用,不能脱离战时具体的历史背景。有谓战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是国民政府,它实行外贸管制,对出口贸易,不仅严格管制,而且直接经营。特别是贸委会所属的几家机构,几乎垄断了主要出口产品的收购和运销。但亦应看到,这些外贸公司在出口口岸自行开盘和开价,最初曾一度使外商操纵出口产品价格的局面有所改变。(59)曾在香港担任富华公司协理、著名的茶叶专家吴觉农评价道:“茶叶自统销政策执行以后,第一步就是由上海迁至香港,这不但在业务的执行上对苏能够直接易货,对英美能够直接交易,而且把过去洋行买办制度垄断之下的一切陋规……一概取缔,使茶商不合理的负担,统予减除,这样在中央、地方与茶商各方面通力合作集体力量的奋斗之下,三年以来,已经替中国茶业开辟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的康庄大道。”(60)连当时日本侵略者亦承认:“中国土产出口,原属国际资本主义之地盘,掌握于……外商之手。是故对外贸易国营化,不仅为贸易形态之变更,且含消灭国际资本主义之势力及排除国家经济中殖民地性质之意义。换言之,并非简单的贸易政策之问题,而为与社会基础的构造有关系之问题。”(61)况且,往昔茶叶、桐油、猪鬃等中国农产品运到香港以后,都由外商转销各国,不分敌我,甚至大量流失到日本。3个国营贸易公司成立后,在香港统制农矿产品的出口业务,有目的地向友邦出口,有效地遏制了重要物资资敌状况,也支援了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
国营企业驻港机构还发挥了其他方面的重要作用。如当日本宣布封锁香港后,1940年7月5日,贸委会致电香港富华贸易公司,饬令查明最近香港货运情况。越日,该公司即复电称:“封锁只限沦陷区运香港之食品,其余尚无影响,沙鱼涌仍通,但夫缺,可运货甚少。”(62)次年5月,富华贸易公司香港分公司还节译了日本对我抗战贸易设施的调查报告,呈报贸委会,受到高度重视,并复电要求其“嗣后续有所得,仍宜随时密呈。”(63)香港中信局经多方设法,暗设秘密电台,与重庆和上海方面联络,通报关于财经、与敌私谈和平以及日伪情报等信息。孔令侃并在香港创办《财政评论》杂志,由贾士毅负责。另又组织了一个香港银行业联谊会,从事宣传组织活动。(64)
这些努力,对于中国坚持对日经济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01、630页。
②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90—791页。
③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26—146页。
④《一九三七年香港对外贸易概况》,《中行月刊》第16卷第3期,1938年3月。
⑤《经济新闻》,香港《星岛日报》1939年2月6日。
⑥译自《南支经济丛书》,东京:福大公司1938年再版,第380页。
⑦引自余绳武、刘蜀永主编:《20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⑧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香港作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页。
⑨译自秀岛达雄:《香港·海南岛の建设》,东京:松山房1942年版,第116页。
⑩《倪文钰致副经理函(1938.10.27)》,上海市档案馆藏盐业银行档案,档案号:Q277—1—273。
(11)重庆市档案馆等编:《四联总处史料》上册,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29页。
(12)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
(13)中国国货银行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38年3月25日。
(14)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15)中国保险学会编:《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4),第385页。
(18)满铁调查部编:《支那经济年報》,东京:改造社1942年版.第520页。
(19)《富华贸易公司各地分公司工厂及各办事处一览表(1941年11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档案号:309—517。
(20)《复兴商业公司暨各附属机关主管人员一览表(1941年11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档案号:309—517。
(21)《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直属机关一览表(1941年10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档案号:309—517。
(22)《华资名厂产品介绍》,《香港商业录》,《香港商业年鉴》,香港新闻社1949年版,第45页。注:袁剑秋认为,中国植物油料厂在香港所设的是办事处,1937年9月成立,专办外销业务。见其著《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23)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496—497页。
(24)龚学遂著:《中国战时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9页。
(25)夏兆营:《论抗战时期的西南运输总处》,《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第85页。
(26)龚学遂著:《中国战时交通史》,第88—89页。
(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3),第307页。
(28)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第209页。
(29)重庆市档案馆等编:《四联总处史料》中册,第113页。
(3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3),第307页。
(31)重庆档案馆等编:《四行总处史料》下册,第38页。
(32)重庆档案馆等编:《四行总处史料》下册,第74页。
(3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4),第256页。
(34)《经济部工矿调查处内部来往函件(1939)》,重庆市档案馆藏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档案,档案号:0020—2—1。
(35)《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函稿(1941年)》,重庆档案馆藏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档案,档案号:0075—1—78。
(36)《本会所属各公司历年营业概况及盈亏概况表(194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20。
(37)王慧章著:《猪鬃大王——古耕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58页。
(38)袁剑秋:《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34—39页。
(39)龚学遂著:《中国战时交通史》,第88页。
(40)《中国经济年鉴》,香港:中国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8年版,第133页。
(41)重庆市档案馆等编:《四联总处史料》中册,第500页。
(42)《贸易公司广东办事处致贸易委员会电(1942年2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档案号:309—545。
(43)《富华贸易公司总经理席德柄致贸易委员会电(1941年12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档案号:309—545。
(44)《太平洋战后各处报存港沪物资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档案号:309—9634。
(45)《贸易委员会所属机关抗战损失统计表(1945年11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档案号:309—2—181。
(46)《华资各厂产品介绍》,《香港商业录》,《香港商业年签》,香港新闻社1949年版,第45页。
(47)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第484页。
(48)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第498页。
(49)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240—241页。
(5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3),第477、490页;重庆档案馆等编:《四联总处史料》下册,第160—161页。
(51)《港闻》,香港《星岛日报》1938年11月6日。
(52)李琴芳选辑:《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对苏易货偿债相关史料》,《民国档案》2006年第2期,第31页。
(53)《港闻》,香港《星岛日报》1939年2月10日。
(54)《经济事项纪要》(1940年3月),《经济统计月志》第7卷第4期,第80页。
(55)尹在继:《中苏茶叶贸易史记(上)》,《茶叶经济信息》总第284期,第23页。
(56)李琴芳选辑:《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对苏易货偿债相关史料》,《民国档案》2006年第2期,第45—47页。
(57)《复兴商业公司香港分公司致陈董事长(1942.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档案号:309—942。
(58)孔祥熙:《财政部三十年度重要工作之检讨与今后之改进办法》,《财政评论》第7卷第4期,1942年4月,第109页。
(59)王相钦、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商业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页。
(60)吴觉农:《茶叶统制与湘茶前途》,《湖南农业》第1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第16页。
(61)《香港分公司译呈敌人对我抗战贸易设施之调查报告(1941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档案号:309—1047。
(62)《敌人封锁香港后货运情形(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档案号:309—5732。
(63)《香港分公司译呈敌人对我抗战贸易设施之调查报告(1941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档案号:309—1407。
(64)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89、241页。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法币论文; 外汇公司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营企业论文; 桐油论文; 银行论文; 中央机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