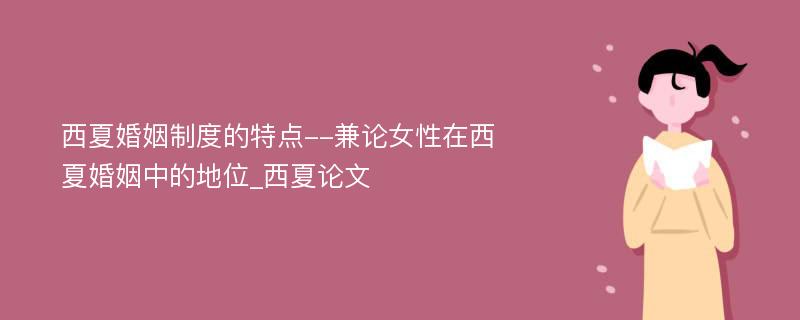
西夏婚姻制度的特征——兼论女性在西夏婚姻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婚姻论文,特征论文,地位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3;C91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3)05-0081-04
从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和社会婚姻实践分析[1],西夏婚姻有一些在党项社会中有重要影响的特征,现探讨如下。
一、姑舅表婚盛行
在中国古制中,称姑母的子女为外兄弟姐妹,称舅父、姨母的子女为内兄弟姐妹。外为表,内为中,外兄弟姐妹与内兄弟姐妹之间互称为中表兄弟姐妹,他们之间的婚姻为中表婚,亦即通常所称姑、舅、姨表兄弟姐妹婚。历史上很多民族都盛行过中表婚。甚至现代一些民族,如凉山彝族仍存在舅姑子女优先通婚的习俗。据人类学家考证:交表(或中表)婚是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优先婚姻形式,是因为这一制度既维持和加强了上一代产生的亲属关系,又巧妙地维护了外婚的原则。如果在母系继嗣社会中,姨母的子女与己身同属一个继嗣集团(家族或氏族),故不能互为婚姻;在父系继嗣社会之中,父之兄弟之子女,又与己身同属一继嗣集团,故亦不能通婚,唯有舅父之子女、姑母之子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均与己身分属不同的继嗣集团,所以符合外婚的原则,可以互相联姻。
从理论上讲,交表婚有三种形式,即双边交表婚、父方交表婚和母方交表婚。实行双边交表婚时,一个男子既可以娶舅父之女为妻,也可以娶姑母之女为妻。实行父方交表婚时,一个男子只能选择其姑母之女为妻;而实行母方交表婚时,则他只能与其舅父之女结婚。冯汉骥根据《尔雅·释亲》等文献资料证明在古代中国的汉族先民中,交表婚不但是优先的,而且也是指定的[2](P117-134)。然而中表通婚毕竟是一种近亲结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渐渐不再被提倡,甚至在一些民族中被明令禁止。到唐、宋时期表婚已在法律上被禁止。《宋刑统》规定:“中表为婚,各杖一百,离之。”然而,在当时社会上对表兄弟姐妹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并不完全排斥,政府也听之任之。西夏《天盛律令》中没有规定限制中表婚,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中表婚十分盛行。
党项族盛行姑舅表婚,从其语言中可窥见端倪。在西夏语中“舅”、“甥”两个称谓经常连用,“舅甥”和“为婚”两词语音完全相同,说明在党项族社会中舅父之女和外甥之间存在着一种优先缔结婚姻的权利[3]。党项族的中表婚应是双边交表婚,即一个男子既可以娶舅父之女为妻,也可以娶姑母之女为妻。同一家庭的子女在双边姑舅表婚下,男性的岳父、女性的公公和他(她)们的舅父应是相同的称谓;同样,男性的岳母、女性的婆母和他(她)们的姑母应是相同的称谓。西夏亲属称谓正反映了这一特点[4](P203-204)。谚语“亲上亲甥妇坐姑上,热上热设帐向南晒”、“天热去照日,亲眷加亲眷”、“善亲胜戚,大婚重婚”等都反映了党项人姑舅表等亲属联姻的习俗[5]。
姑舅表婚在西夏上层统治集团中,特别是在皇族中多有记载。如西夏第一代皇帝景宗元昊娶舅父之女卫慕氏,第二代皇帝毅宗谅祚娶舅父之女没藏氏,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娶舅父之女梁氏。当然这种典型的中表婚除了反映西夏社会的一般婚姻习俗外,还有政治联姻的需要。卫慕氏、没藏氏都是党项望族,梁氏则是两代掌握朝柄的国相之家。皇室的中表联姻对社会上保持中表结亲无疑会起到提倡和强化的作用。
二、妇女地位较高
西夏党项族因自原始社会末期发展至封建社会时间较短,只有几百年,所以一些反映原始社会的习俗有所保留。在婚姻方面妇女地位较高就是原来传统习俗的遗存。
《辽史》记载:西夏习俗“喜报仇……力小不能复仇者,集壮妇,烹以牛羊,具酒食,趋仇家,纵火焚其庐舍。俗曰敌女兵不祥,辄避去。”[6]女兵报仇,敌人躲避不战,是古代女权的一种表现,是对妇女的尊重。至近代,有的民族内部冤家械斗时,若妇女站出来制止,冤家械斗即可停止,这与古代西夏党项族的习俗十分相近。西夏时期还有女兵参加作战。女兵,西夏语称为“麻魁”。西夏有女兵在当时各王朝中也是很有特点的,这也应看作是妇女有一定地位的表现。
在西夏婚姻制度中,妇女在婚权上比宋朝妇女有较多的自由,寡妇改嫁也比中原地区宽松。
《天盛律令》中对主婚权有明确的规定:“诸人为婚嫁女顺序:亲父母可嫁,祖父母、伯叔、姨、兄弟、嫂等其他节亲不许嫁。”“若无亲父母,则祖父母及共居庶母、女之同母兄弟、嫂娣及亲伯叔、姨等共议,使往所愿处为婚。”[1]可见,在西夏社会中婚姻行为的主婚权属于父母亲,在没有父母亲的情况下则由其祖父母、共居庶母、同母兄弟、嫂娣、亲伯叔、姨等共同商议。西夏婚姻应属于父母或期亲包办婚姻。《天盛律令》还对违反主婚权条律的做法作出了处理规定:无父母时,“若不共议而嫁时,六个月期间可上告,当接状询问。祖父母、伯叔、姨等嫁女者不治罪,兄弟、嫂娣嫁则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因未共议,婚姻当改过”。从中不难看出,西夏对婚姻的缔结是比较严格的,同时在父母以外的亲属中,又有不同的层次,祖父母、伯叔、姨的主婚权比兄弟、嫂娣要大。《天盛律令》还规定:“诸人已为婚,婿未往,或男死或女死等,一律当罚有主婚价,女当嫁情愿处。”[1]男女订婚后,若女婿未往迎娶,或男子已死,女子则可嫁至“情愿处”。这也表明西夏妇女的婚权相对较多,和中原地区完全漠视女子的意志是有所不同的。
西夏许寡妇改嫁。《天盛律令》对寡妇改嫁有具体规定:“寡妇行三年孝期满,有公婆则不许随意出。若公婆情愿放,有欲赎出者,则有无子女一律当听赎出。无公婆,则愿住即住,愿往乐处即往,夫主之畜物勿取。”寡妇改嫁要待丈夫死后3年孝期满后才可以,要征得公婆同意,无公婆则自己作主。
由于西夏对外的战争较多,被敌人俘获者的家庭婚姻便成了应特别处理的问题。对此《天盛律令》作出了专门规定:“为敌人俘获者之妻子,有子女则(待)十年,无子女则(待)五年,未迎娶而住父母处则三年以待丈夫。逾期不来归,则有公婆者许与不许随意出,依各自实行。若无公婆而欲往随意处,则当告往随意处。”丈夫被俘,长期不归,妻子应根据有无子女、是否迎娶分别等待一定年限。过期限则可以改适他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妇女的权益。
结论:
(一)西夏婚姻中妇女有一定的主婚权。由前述已知西夏婚姻制度规定的主婚权属于父母亲和期亲,是典型的包办婚姻。但从《天盛律令》对婚权的规定中,还可看出女子本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主婚权,“若无亲父母,则祖父母及共居庶母、女之同母兄弟、嫂娣及亲伯叔、姨等共议,使往所愿处为婚”。即在无父母时,由其他至亲共同商议,但还需要女子本人“往所愿处”,若本人不愿去,婚姻仍不能成立。这可能是西夏党项族过去婚俗的遗留或影响。
(二)唐宋时期也允许寡妇守丧期满后改嫁,但宋朝受理学精神的束缚,寡妇改嫁往往受到非议。《唐律疏议》(亦作《唐律疏义》)、《宋刑统》只是规定对强迫寡妇改嫁的处罚,而《天盛律令》还规定了寡妇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改嫁,使寡妇改嫁比较容易,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寡妇的再婚权。
(三)西夏婚姻中有妻妾之分,子辈有嫡庶之别,但西夏的妻妾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尊卑严格,嫡庶之间的差别距离也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大。《唐律疏议》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7]宋代也有类似的规定。可见在中原地区妻、妾、婢女的尊卑位置规定得十分清楚,若违反要受处罚,而在《天盛律令》中还没有这样严格的规定。这也表明地位低下的妇女在西夏的待遇要好一些。
三、对非婚性行为和非婚生子女相对宽容
过去党项族的婚恋比较自由。文献记载,西夏党项族原来“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8]这种行为和社会对这种行为的认识,是与当时比较原始的社会形态相一致的。当然这种自由的婚恋是不适应封建社会制度的。在私有制确立并发展以后,男子为了确保自己的继承人在血统上无可怀疑,就特别要求妻子保持贞节。西夏的私有制早已确立,男子在家庭中也早已占据主导地位,男女的自由婚恋也被买卖婚姻所取代。尽管如此,仍然能够在某些方面发现党项族传统习俗的遗留或影响。
西夏法典对男女的“非礼”行为,也要进行处罚,但处罚较轻。如《天盛律令》规定:“寡妇及未嫁女与人行淫时,男人罪:是寡妇则(徒)一年,是未嫁女则三个月。女人:十杖。”与有夫之妇通好处罚稍重,“诸人与人妻一处寝宿被捕时,徒二年”,但强调当时捉捕并有知证[1](P189)。
《天盛律令》卷八“夺妻门”用一门的篇幅专门对抢夺他人妻子作出规定,共有10条之多,可见当时确有抢妻之风,而且严重到要以法律的形式专项作出处理的程度。这与中原地区是很不相同的。如该门规定:“诸人欲与人妻行奸,以女人不愿,密谋持抢时,徒四年。女人能举报而不举报,心悦愿往者,徒三年。”[1](P187)对抢未嫁女者处罚很轻:“诸人女在未嫁,父母不允,不许随便抢亲受礼。违律而父、兄弟告时,前抢亲受礼者,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女人情愿则笞三十,不情愿则不治,归还父母,依愿嫁之。”[1]一些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民族至近代仍有抢婚习俗。
封建社会对非婚生子女都采取歧视的态度,西夏也不例外。如:“诸人与大小侄妇混房所生子,不许袭抄、官、军。”“诸人之妻与他人通而生杂子,不许袭丈夫之抄、官、军,勿得财物,依次当注册。”[1]但相比之下,对非婚生子女显得宽容。《天盛律令》规定:“诸人娶妻子,后与他人行淫乱而怀有杂女子者,不许取状寻问。”这一条律保护了非婚生子女,并进一步对杀害非婚生子女作出了处罚:“已产出而为父母所杀时,为母所杀与杀己子罪相同,为父所杀则杀一人徒六年,自二人以上一律徒八年。”[1](P185)
四、女嫁不从夫姓与女子以身先荐国师
西夏文文献《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中反映了西夏婚姻制度中有女子出嫁不从夫姓的现象。《西夏文天盛二十二年(1170年)卖地文契》(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记录一寡妇卖地二十二亩,值骆驼四匹;全齿骆驼二,双峰骆驼一,代步骆驼一。契约末尾详述所卖牧地坐落四至。立约人除寡妇本人以外,尚有二子附署,所延请中人多至四名。契约有“立文契人耶和氏宝引”,“其商约者子没罗哥獐,共商约者(子)没罗口鞭”。契文一方面表明西夏牧地私有,可以自由转让;另一方面表明,卖主有二子姓没罗,而卖主寡妇姓耶和氏,证明女嫁不从夫姓[9]。
党项人有一种特殊风俗:“凡有女子,先荐国师,而后敢适人。”[10]元人马祖常《河西歌》亦云:“贺兰山下河西地,女娘十八梳高髻,茜根染发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10]这应是喇嘛教传入西夏后,在党项族内形成的习俗。由于喇嘛教在西夏地位极高,故出家者甚多,当时即有“河西土俗,大半僧祗”之说[11]。僧人在西夏享有盛誉,党项女子以身先荐国师,这同西藏风俗大致相同。当然,党项女子愿以身先荐国师,与他们本民族性关系较为自由之俗有关。
五、西夏党项人的择偶标准
从《新集锦成对谚语》、《圣立义海》、《碎金》等文献中可以反映出西夏人的择偶标准。
《碎金》有“为婚是旧仪,亲戚从今非。媒人奉承美,集体问姿容。贫富福高低,吃穿处处至”[12]。其中,“集体问姿容”,一句表明“姿容”是择偶的主要标准。又如《圣立义海》“美妇名义”中认为“世间人之最上者,乃色美,其次为意智、言语之美”[13](P89)。姿容固然重要,但是妇人内在的美,对丈夫的忠贞更为重要。如《圣立义海》“丑妇名义”讲了:“外丑内聪,妇人要有才艺,内心聪明,如仅具外在的美,则多招灾祸,诗中云:‘男智察妇行,愚人重外表。’”[5](350条),谚语“禄贱,对官事忠,妇丑,对丈夫贞”;“大喉主中口爱味,贱女人中夫择妻”[5](61条)等,也说明西夏社会对妇人美与丑的再认识。党项族尚武,故勇敢者也能获得美满婚姻。如西夏谚语有“勇(年年),美姻连”,“勇禽美禽择爱”[5](242、352条)。同时婚姻还依靠经济实力来决定。如《天盛律令》“为婚门”中对于婚价的诸条规定以及《文海》中对“婚价”的解释,“婚价也,结婚取女价,向亲戚叔、舅等馈物之谓”,这种“馈物”实际上是男女方索付之价格。《碎金》中“贫富福高低,吃穿处处至”也反映了西夏婚姻观念中对于经济因素的重视。
党项族原本是从事畜牧业的游牧民族,北迁以后才开始接触并学习农耕。党项政权建立后,党项人在农区从事农耕,在宜于放牧之地仍从事游牧。从事农耕则更接近汉族,接受中原地区的文化更多;而从事游牧则保留本民族传统习俗更多些。西夏婚姻制度上这些特点,多与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传统婚俗有关,但却反映了西夏社会特别是党项族当时的一些婚姻特征。
[收稿日期]:2003-0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