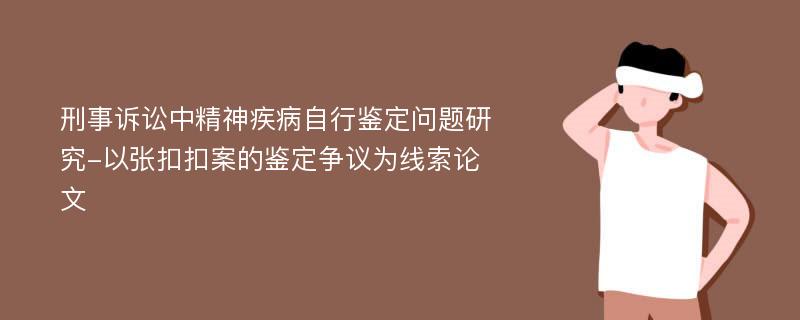
鉴定制度
刑事诉讼中精神疾病自行鉴定问题研究
——以张扣扣案的鉴定争议为线索
叶 青,盛雷鸣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摘要: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未对关于当事人自行进行精神病鉴定有明确规定,但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存在自行鉴定的空间,实践中也有自行鉴定的合理需求。自行鉴定的鉴定意见具备作为证据的资格,是对控诉的合理怀疑,印证的方式也不能直接予以排除,应当纳入公安司法机关审查的范畴。为规范自行鉴定存在的问题,应当从程序上优化当事人的鉴定申请和参与的权利,提高鉴定人素质和强化责任追究,完善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出庭制度,最终减少自行鉴定。
关键词: 司法精神疾病;自行鉴定;公安司法机关审查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一直是刑事司法中的热点问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有逃避惩罚而装病的可能,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也担心被不当追诉,被害人担心鉴定不准确而让罪犯“逃之夭夭”,社会公众希望“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公安司法机关也担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冤枉或被放纵。这就造成是否启动鉴定,无论是初次鉴定还是补充鉴定、重新鉴定,都受到了案件当事人、公安司法机关乃至社会公众的强烈关注。
2019年4月,因杀人动机特殊而引起广泛关注的陕西汉中张扣扣杀人案件的二审再次成为舆论的热点。上诉人的近亲属在一审后自行委托北京正慧科鉴咨询服务中心进行鉴定,并由后者认定张扣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辩方律师以其向二审法院申请对上诉人进行精神障碍程度的鉴定,并要求通知鉴定的专家出庭,但法院在听取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后驳回了鉴定与出庭的申请,也没有采信这一自行鉴定的意见材料[1]。由此引发了不少争议:一是刑事诉讼中当事人能否自行委托鉴定?二是自行委托的鉴定意见应当如何对待?三是如何平衡诉讼中的鉴定需求?
1 刑事诉讼中精神疾病自行鉴定的必要性
1.1 刑事诉讼对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启动的规范
作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启动与否的主要依据,《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颁布以来,历经三次修改,已明确赋予了当事人申请补充鉴定与重新鉴定的权利,但当事人能否自行鉴定的相关规定一直付之阙如。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是我国第一部刑事程序基本法。在该法侦查章节中单独将“鉴定”作为一种措施,并明确“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关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虽然该条款并没有明确拥有“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的权力主体,但侦查是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侦查机关的职权,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鉴定”,也可以根据当事人和辩护人的申请“重新鉴定”。为此,这个主体应当是不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当事人在内的,一方面当事人“指派”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不可能,他们没有“指派的权力”;另一方面,该节随后的条款中明确规定,“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应当告知被告人。如果被告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如此,被告人若有权自行鉴定,告知鉴定结果应当就没有必要。该法1996年修订的主要内容是增加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诉讼代理人在审判阶段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也即,再次鉴定的申请权主体得到了扩大。2012年与2018年的修法并没有就鉴定的此项内容作改动。
近30年来,宽甸县的降水量、气温和日照时间呈周期变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宽甸县降水量偏多;2016年开始,宽甸县的气温开始回升;日照情况较好,有利于作物生长。
实验组患者的TC(血清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terol)、TG(甘油三酯Triglyceride)、LDL-C(血浆中低密度脂蛋白LowDensityLipoprotein)以及ApoB(载脂蛋白apolipoproteinB apoB)均高于对照组,其中对照组的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以及ApoA(载脂蛋白apolipoprotein A apoA)高于实验组。见表1。
由此可见,法院的裁决理由只有一点能直接与《意见书》的内容相对应,但该点理由显然也不足以否决《意见书》确认的张扣扣精神障碍问题。更为关键的是,作为是否有精神疾病这一专门性事实问题,法官是不具备认定能力的,这也是鉴定存在的原因,法官、鉴定人根据各自的专长,各司其职可能是更为合适的立场。
虽然庭前会议的报告中提及合议庭可对《意见书》进行质证,但在庭审中并没有直接提及[9]。从法院的宣判词中也可以发现,针对《意见书》的不适用,最直接的理由可能是鉴定的委托不合规,并没有对《意见书》本身的内容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查及质证③ 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五节,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作了详细的规定。从张扣扣案件庭审的相关文字报道看,并没有进行审查与认定。 。
1)听力理解能力弱。每年的四六级考试,听力环节都是中国学生最大的障碍。在听不懂的情况下,衍生了各种“听到什么选什么”“选中间长度的”“不懂就选C”等等所谓“听力策略”。过后一对照听力原文,几乎没有生词,完全看得懂,但就是没听懂。
由此可见,《刑事诉讼法》只是明确了公检法在诉讼中采用鉴定这一侦查或核实证据的手段,当事人可以通过向公检法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而利用这一措施,但当事人初次鉴定申请权和自行鉴定权并不明确。从公安司法机关的规范性文件看,当事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申请初次鉴定的权利,也即在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或审查起诉阶段的案件,辩护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的理由而申请进行鉴定。从有关学者的调研看,公检法机关似乎也基本都不否定申请初次鉴定的权利[2-3]。考虑到对当事人而言,申请权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仍然需要国家机关的审查批准,所以,在赋予当事人更多程序性权利的同时,公安司法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当事人在启动鉴定程序上的被动性。
1.2 精神疾病自行鉴定的合理需求
“我特别喜欢听盛老师讲课……”笔者走进七师高级中学,说出“盛庆余”的名字时,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满口称赞。
不过,在民事特别程序中,法院并不拒绝当事人的自行委托鉴定①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法院可以对申请人提供的鉴定意见进行审查,自然是以不反对其自行鉴定的。 ,民事诉讼的相关证据规则也明显承认当事人的自行鉴定。从调查取证权看,辩护律师进行的自行委托鉴定,收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主观方面的情况,既是其辩护权行使的需要,也不需要经过公安司法机关的批准② 目前《刑事诉讼法》只规定,在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取证时需要经检察机关或法院的同意(第四十三条),也可以在需要时向检察机关或法院申请调取证据,但并非调查取证都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法院的批准。 。
一是作为对国家司法权行使的一种监督或限制,公民有批评、建议、申诉或控告等权利,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刑诉法中虽然没有明确公民以自行鉴定的方式来监督司法权的行使,但也不能否认这种权利的宪法依据,总体上具有合法性。二是在涉及人身自由与生命等重大利益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坚持自行鉴定以获得进一步救济的可能,具有必要性。三是自行鉴定在申请人自行支付相关费用的情况下,活动本身并不对国家、社会或其他公众等公私利益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害,至多只是刑事司法中的当事人自行寻求的一种辩护的策略,具有合理性。四是无权利则无救济。在当前申请鉴定权利没有复议、复核或上诉等进一步救济的情况下,自行鉴定虽不是法定维护利益的手段,但至少可以作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一种合理补充。
其次,从刑事司法实践视角看,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启动、意见的作出及采信中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给予当事人自行鉴定予以救济。医学研究表明,精神疾病的形成原因既包括社会原因也包括病人自身原因,涉及的学科至少包括医学、遗传学、行为学、心理学等具有跨学科特点,精神疾病的鉴定也成为较为公认的难题。从鉴定错误率来看,国外有研究发现,在67个再审程序中的精神疾病案件,有错误诊断结果的,第一次有48%,有发现错误结果的,第一次有60%,第二次仍有24%[4]。从多次鉴定下的结果看,多次鉴定的结果不一致较为普遍。2001年度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437例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其中69例为重新鉴定。结果发现,重新鉴定的案件中有40例鉴定结论存在差异,其中诊断不一致的占25%,法律问题评定不一致的30%,两者都存在差异的占45%[5]。甚至在个别地方,多次鉴定出现前后结果不一致的占到100%[3]。尽管目前的部分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都得到了法院的采信,如有的地方达到了98%以上[6],但重新鉴定率低,由此避免了多次鉴定可能产生的结果不一致问题,并不能反映鉴定意见本身的科学性。
一些研究发现,鉴定的启动、鉴定意见的作出、采信受到较多非科学性因素的影响。如有学者在实证的基础上提出,除了被告人或其近亲属有无精神疾病史、行为是否异常、是否吸食毒品以及申请人的证明材料是否确实充分外,法官是否启动精神疾病鉴定还会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如果被害人较多或属于法律上特别保护的人群,社会影响比较恶劣的,法官启动鉴定就较为谨慎[2,7]。一旦初次鉴定结果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时,公安司法机关一般会以理由不充分或证据不足等驳回重新鉴定的申请;如果公安司法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异常”,即使辩方提出一定的证据线索也难以获得他们的支持而启动鉴定。鉴定意见的作出也有不少类似于综合权衡的结果而不是依据专家的知识,如被害人与作案人之间的关系较为亲密的,多评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反之评为限定责任能力的较多;法官在多个鉴定意见的采信上也是如此[3]。实践中的上述现象可能不具有普遍性,但至少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法官的采信也没有完全遵守科学性的要求,更没有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如此,在鉴定活动及采信过程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司法救济仍不完善的情况下,否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行鉴定将对其人身自由、生命等重大权益形成威胁,也有损司法的威信。
当事人对精神疾病自行鉴定的相关规范不明确并不代表自行鉴定的不合理,更不代表实践中不需要。
最后,从法律规定视角看,精神疾病自行鉴定并不需要作为诉讼权利由法律明确规定。刑诉法既可以作为一部对公安司法机关的限权法,也可以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法,其主要是通过对公安司法机关的权力限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赋予来实现的。权力限制与权利保障是相辅相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实现需要公安司法机关对自身权力的适当限制以及通过权力予以保障。自行鉴定不需要规定为一项诉讼权利,一方面,当事人进行的鉴定并不需要公安司法机关的保障,完全可以自己委托进行。以国家级鉴定机构看,虽然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统一受理办案机关的委托,但鉴定机构接受公众委托的情况也不鲜见[8]。以与刑诉法规定相似的民诉法及其实践看,虽然启动鉴定也是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鉴定,或法院认为需要鉴定的,由法院委托鉴定。
首先,从程序正当性视角看,精神疾病自行鉴定是当事人申请鉴定的合理补充。根据当前法律的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在先前没有鉴定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初次鉴定;当事人的申请需要公安司法机关的批准,鉴定才可能实施,也即公安司法机关完全可能出现不批准实施鉴定、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问题。此时,按照当前的刑事法律规范,当事人将不能再申请(当然,当事人在不同诉讼阶段可以分别提出上述的申请),也没有就公安司法机关作出的决定提起救济的途径。鉴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在刑事司法中的重要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因密切的利害关系,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相对熟悉,在申请公安司法机关鉴定得不到批准、公力救济途径受阻的情况下,寻求私立救济的途径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认可。
另一方面,当前法律并没有完全排斥自行鉴定的结果。当事人通过自行鉴定寻求自力救济并非没有考虑鉴定结果可能对司法产生的影响,毕竟自行委托鉴定获得鉴定意见只有正式进入公安司法机关审查的范围,这种自行鉴定才有实质意义。前述的民事诉讼特别程序及有关的证据规则都明确了民事诉讼中的自行鉴定结果可以被纳入到法院的证据审查范围中,刑事诉讼的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对自行鉴定也处于一定程度容忍或默认的状态,自行鉴定意见也得到法院的重视。以张扣扣案为例,对于辩方律师提交的自行鉴定的结果与三名鉴定人出庭的申请,法院在听取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后予以驳回,但法官在宣判词中仍然对不采信这一结果进行说理[9]。虽然法院排除了这一材料的适用,但对辩方而言,这无疑可以起到加强辩护,并引起法院慎重考虑的目的。
2 自行鉴定的意见应当纳入公安司法机关的审查范围
2.1 张扣扣案二审法院对自行鉴定意见的处理评析
张扣扣案件中,其家属在一审后自行委托3名精神疾病专业专家对张扣扣进行精神状况鉴定,并由受托单位北京正慧科鉴咨询服务中心出具《正慧科鉴中心(2019)咨字第5号法医精神病学书证审查意见书》,认定张扣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二审过程中,上诉人及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上提出由法院对张扣扣进行精神疾病鉴定的申请,理由包括张扣扣属于偏执型障碍,作案时的控制能力稍弱,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一审驳回鉴定申请的程序不合法,理由不能成立。检察机关则建议驳回,理由包括张扣扣整个作案过程思维清晰,精神状况正常,辨认、控制能力没有问题;张扣扣父系、母系亲属都没有精神疾病史,张扣扣本人也没有既往病史。法院经评议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驳回了鉴定的申请,但同意在庭审中由辩护人出示意见书并进行质证。在庭审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确认,在听取了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后否决了上诉人提出的3名专家出庭申请[1]。
自行鉴定并不需要公安司法机关的权力保障,是辩方自我救济的重要措施。《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法庭应对自行鉴定意见进行审查。从张扣扣案件中庭前会议上也可以看出法庭也同意就该鉴定意见的出示与质证。基于此,笔者认为,自行鉴定取得的结果应纳入公安司法机关的证据审查的范畴,而不是直接予以排斥,可能是更为合适的立场。
公安部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对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具体情形作了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形式,加强了对鉴定意见的审查,要求鉴定意见必须符合法律、有关规定,而违反规定鉴定程序的鉴定意见将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不过,无论是公安部的规章还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都没有对何种情况下可以启动初次鉴定、特别是当事人的申请鉴定作出规定。
不过,从法院裁决的其他四点理由看,可能既难以否决《意见书》的内容,也无法确定张扣扣精神是否有障碍、是否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笔者认为:(1)张扣扣没有精神疾病家族史和既往史,这个较为容易确认。不过,没有精神疾病家族史并不能说明张扣扣本人是否患有相关疾病,而其没有既往病史,也无法说明张扣扣近期及实施犯罪时是否有精神疾病。(2)对作案过程的回溯性认识,难以准确反映作案当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作案过程的认识大多来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也有部分来自犯罪的客观方面,但这些认识也只能是辅助性,由此对作案时精神状态的推理与判断难免出现偏差或错误[10]。(3)庭审中的表现只是对当前精神状态的展示,并不能表明作案时的精神状态。
公安司法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对鉴定的程序进行了完善,但仍然没有明确当事人能否就精神疾病问题进行自行鉴定。鉴于改革开放伊始,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也是刚刚确立,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只有公安部在1987年发布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其规定,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的,由县以上公安机关发给聘请书,或者直接由县以上公安机关刑事技术部门或者其他专职人员负责进行;被告人在“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应当进行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也即,一方面明确地排除了被告人自行鉴定的可能,另一方面对被告人的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提出了“合理”要求的限定。1996年修法后,公安司法机关都颁布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有部分突破。即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鉴定费用由请求方负担,告知当事人鉴定结论,可以不告知过程只告知结论;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或近亲属可以犯罪嫌疑人有患精神病可能而申请检察院进行鉴定,费用由申请方负担。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底修订了该规则,除了增加在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情况下检察院承担费用的情形外,还将以患有精神疾病可能为理由的申请鉴定提前到自侦阶段。从对患精神疾病可能而申请鉴定的相关规定看,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此时已有相关的精神疾病鉴定意见,但是被排除了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的可能,当事人不认可这一鉴定意见而申请再次鉴定;二是申请启动精神疾病的初次鉴定,此时侦查机关、检察机关都没有对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甚至对其精神状况都没有怀疑,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或近亲属认为犯罪嫌疑人可能患有精神疾病,需要鉴定。
2.2 对自行鉴定意见的应有立场
从最后的宣判词看,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精神疾病鉴定的申请及没有采信北京正慧科鉴咨询服务中心出具的《意见书》,理由包括:(1)张扣扣没有精神疾病家族史和既往史;(2)作案的过程反映其有完全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3)一审庭审中的表现正常;(4)二审庭审中未发现其精神异常;(5)刑事司法精神疾病鉴定应由司法机关决定提起,辩护人提交的《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案参考[10]。
首先,自行鉴定意见具有证据资格。从调查取证权来看,律师自行调查取证是我国刑诉法赋予辩护人独立地位的重要体现,其不仅可以向司法机关申请调查取证,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在涉及案件有关专门性事实问题,需要有专门知识的人协助收集有关证据,辩护律师委托有法定资质的鉴定人进行协助应当属于调查取证的必要内容。从我国证据要求的“三性”来看,辩方提交的自行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关联性是毋庸置疑的,是鉴定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精神状况进行检查鉴别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客观性,与案件最终处理也具有关联性。
至于合法性,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排除,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这种自行鉴定;即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内容看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五节“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 ,可能影响自行鉴定意见作为定案根据的主要问题就是“鉴定程序违反规定的”⑤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八十五条的规定,鉴定意见被排除的情形有九种,第一、二、六、七项都是鉴定机构及鉴定人问题,只要委托人选择正规的鉴定机构,一般都不是问题。至于第三、四、八项,只要委托人规范委托,并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应该也可以解决;而且鉴于刑事案件中自行鉴定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希望鉴定意见被采纳或考虑的心态,委托人一般都会确保排除这三项影响鉴定意见被作为定案根据的因素。 。无论是从《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还是《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看,涉及违反规定的可能是与“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统一受理办案机关的司法鉴定委托”不完全相符。不过,从前述的民事诉讼相关法律规定、司法实践看,事实上现在是允许非国家机关委托鉴定,刑诉法也没有明确禁止自行鉴定;无论是当事人委托还是律师委托,委托行为本身并不影响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在影响自行鉴定结果真实性、公正性的程序性要求被排除后,如果不能从内容上对自行鉴定意见进行实质性审查就予以直接排除适用,既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坚持的基本理念不符,也与刑事司法所追求的目标相悖⑥ 以最新两高三部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看,无论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还是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直接排除自行鉴定意见都没有依据。学者大多也认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构建的一般原则应以违反基本权利和追求案件真相相结合,自行鉴定对这一原则也不构成任何违反。 [11-13]。
他清贫的生命,又是那般丰盛和富有,超过一切帝王和富翁。在他的衣服上拍一下,鞋子里抖一下,就抖出一片春天。
其次,自行鉴定意见可以形成对控诉的合理怀疑。对精神疾病的自行鉴定,大多是在检察机关认为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或法院认为被告人精神无异常的情况下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进行的;通过这种自行鉴定获得的结果,可以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形成合理的怀疑,从而削弱、甚至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后果。在我国,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且需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被告人并不需要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还受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保护,但其有自行辩护和委托或接受律师协助辩护的权利。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并不对犯罪主体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而是在没有异常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无病推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精神状况的查明是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责,这也是当前初次鉴定以及再次鉴定的决定权都由国家机关垄断的重要原因。
不过,这种无病的状态只是一种推定,本身是允许质疑和推翻的,一方面公安司法机关通过鉴定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辩护人也可以收集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减轻,甚至不负刑事责任的证据,如犯罪主体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公安司法机关在没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而又拒绝鉴定申请的,或初次鉴定认为应当负刑事责任而拒绝重新鉴定的,此时意味着控方认为对犯罪主体主观方面的证明已经完成。也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此时辩方自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事实上是收集质疑的证据。在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精神障碍并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下,自行鉴定意见就是对控方证明的削弱,可能形成并达到对指控的合理怀疑。此时,检察机关、法院应当对该证据材料进行审查,以确认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否需要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通过个别审查与全案证据的综合判定,确认案件事实。
最后,相互印证的方式不能直接排除自行鉴定意见。从既有的一些研究看,公安司法机关不启动鉴定或拒绝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思路大多是相关证据印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状态无异常,如邱兴华杀人案件中“杀人目的明确”,杀人后的表现正常;回答问题切题,思维清晰等。云南马忠富杀人案件中马忠富在审理期间的意识清醒。湖北随州熊振杀人案件中熊振无精神疾病家族史,作案过程缜密,讯问交代合理等……[3]。张扣扣案件中,检察机关的意见与法院裁决的理由也与上述的案件相类似。的确,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基本模式,印证证明具有较高的证明要求,还具有易把握与可检验的优点[14],但这种证明模式忽视对单个证据的审查,更多关注印证事实,忽略心证功能[15]。在对精神状态自行鉴定的结果没有进行审查的情况下,以其他证据来证明精神状态的无异常,这种典型的印证模式忽视了鉴定意见本身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关联性。这种印证缺乏对个体证据的心证审查,其他证据与该证据材料也无法绝对一致,由此得出的印证结论不能、也不应具有排除自行鉴定意见的效果。
SGSN1在昨天以后就基本没有出现GTPC的闪断告警了;SGSN2和SGSN3闪断次数也明显降低,剩下的告警和某些基站断链有关。
3 尽量减少刑事精神疾病的自行鉴定
刑事诉讼中精神疾病的自行鉴定具有必要性,对这种鉴定的结果也应积极应对,由专家辅助人和法官进行审查再确定效力及是否要重新鉴定、补充鉴定。但鉴于刑事诉讼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审查的困难,对方当事人可能不服及由此可能引起多次鉴定、重复鉴定等效率与公正的问题,实践中,应尽量减少自行鉴定现象从而预防前述情况的出现应当成为程序公正的首选。
3.1 优化当事人的申请鉴定,明确鉴定参与权
优化当事人的鉴定申请权是减少自行鉴定的程序性保障。公安司法机关职权控制下的鉴定启动权有利于防止社会资源的浪费,更利于提高当事人双方的接受度。在当事人对职权鉴定的公正性存疑的情况下,赋予其程序性救济是现代诉讼公正性的基本要求。当事人的申请鉴定与自行鉴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自行单方鉴定存在可能难获对方当事人、公安司法机关承认的缺陷,在能够获得较为公正的鉴定保障下,当事人应当会尽量减少自行鉴定。目前公安机关对申请补充鉴定、重新鉴定有规定,对申请初次鉴定没有规定;司法机关还没有对申请鉴定的具体情形或考虑因素作出较为具体的解释。笔者认为,一方面可以将公安部规定的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情形适用于整个刑事诉讼各个阶段;另一方面,明确申请初次鉴定的情形,可以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有精神疾病家族史、既往病史,日常行为或作案前后行为怪异,作案手法、动机或一些表现难以解释或不同常人,以及有其他可能对精神状况引起合理怀疑的线索或材料的,公安司法机关都应当启动鉴定。
鉴定不仅是一项查明案件真相的侦查措施,也应当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16]。诉讼的参与性是公正性的基本要求,在不对案件的效率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下,通过让当事人一定程度的参与,使得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以凸显,更有助于鉴定程序的公正和鉴定意见的可接受性。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本身与案件的办理是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的,包括可能的尽快结案、避免社会压力、多次鉴定的费用问题以及在多个鉴定之间的选择难题等[9]。为此,无论是依职权进行还是依申请进行鉴定,通过当事人一定程度的参与鉴定都有助于减少对公安司法机关公正性的质疑、赢得当事人的信服。出于侦查阶段保密的需要,当事人申请参与的可能性较小,不过在侦查的后期、审查起诉及审判阶段,征询当事人对鉴定机构、鉴定人的意见,不仅是回避权利的体现,也有助于减少后续阶段对鉴定意见的争议。已有部分案件实现了当事人选择鉴定人[17],最终鉴定的效果也较好。笔者认为,可以参考《民事诉讼法》中的协商鉴定人的办法,在根据申请决定启动鉴定的情况下,无论是补充鉴定、重新鉴定还是初次鉴定,都应就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选择征询案件当事人的意见;在依职权进行鉴定的情况下,条件允许也征求当事人的意见,最终以程序的充分参与减少后续多次鉴定的可能性。
双顶径是指胎头两个顶骨隆突间的距离。位置约为两侧太阳穴上方最宽处骨头之间的长度。随着孕周的增加,胎儿双顶径逐渐增大,孕足月时平均值约为9.3厘米。在分娩的过程中胎儿的头部通过产道的最大径线就是双顶径。
“参与比率低”,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的是目前所开发的再就业培训项目缺乏足够的价值,以致无法对失地农民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使得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出“参与”再就业培训的选择。尽管这类培训的学费都有政府专项资金补助,无须个人支付任何费用,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选择“参与”再就业培训这一选项,对于每个个体而言,结果的意义、价值及实现的可能性都是不一样的。
3.2 提高鉴定人素质,强化鉴定责任追究
鉴定人素质是鉴定意见准确的实质性保证,提高鉴定人的相关素质是减少鉴定需求的关键。目前鉴定人执业的核心要求是具有相关专业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长期的工作经历等。虽然精神疾病的鉴定主要涉及医学、心理学等,但不同于一般诊疗中的精神状态判断,精神障碍程度的鉴定涉及公众的人身自由与生命安全,显然要比一般出于治疗目的的诊断更为严格、谨慎。也即除了从事医学的精神疾病诊疗的资格外,应当对精神疾病的鉴定确立更为严格的鉴定标准,包括鉴定人的准入资格限定。虽然有建议鉴定人应当学习法律知识[7],但笔者认为,鉴定人主要是对精神障碍程度的评定,不应对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等法律相关问题进行评判,这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应当不影响其对精神障碍程度的判定。由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状态鉴定类似于医生的诊断,鉴定人首先必须有长期的从业经历,从而才可能有丰富的经验以判断各种可能的精神障碍表征,为此,建议鉴定人的资格上应当适当延长从事实务的年限,并禁止单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担任。其次,鉴定人应当采用统一培训或统一考试的形式来规范其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一致性。当前精神障碍程度鉴定的一致性低,不仅与精神疾病相关学科的发展不成熟有关,与鉴定人本身的理论素养也密不可分。这方面的培训或学习内容至少可以包括对最新的精神病学相关理论研究、精神障碍程度鉴定的科学流程、技术标准等。
责任追究是鉴定人公正执业的保证。当前《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对鉴定人的法律责任有规定,有些地方也有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如《上海市司法鉴定管理实施办法》、《江苏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和《云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等,但制定类似上海的《关于严格司法鉴定责任追究的实施办法》、专门规范追责的地方并不多。不仅如此,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司法实践中的多次鉴定不一致情况也普遍导致责任追究的困难,如何合理、科学地追责,同时又不致于将这种认识问题完全归咎于鉴定人,做到对鉴定人的不枉不纵仍需要不断地实践与探索。此前有报道存在明显虚假鉴定的案例,但对处理的公开报道则很少[18]。故笔者无法揣测是否对这些错误鉴定进行了追责,但一旦存在追责,则应当予以公开,促成在全社会形成良性的舆论监督氛围,为我国的鉴定制度良性发展提供社会支持。
3.3 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确保有专门知识的人自愿出庭
鉴定人和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是减少自行鉴定的必要补充。除了申请补充鉴定、重新鉴定外,对精神障碍鉴定意见的质证不仅是当下庭审实质化的必要内容,也是保障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权、增强鉴定意见可接受性的重要途径。由于精神障碍鉴定意见的专业性,当事人及其律师、司法人员除了进行形式性的审查外,对鉴定意见的实质内容也难以判断。通过完善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制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增强控辩双方的参与,也为法官的证据审查提供指引。当前的鉴定人出庭基本完全由司法机关掌握,但可能混同了国家机关的职能、有违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的趋势也不一致,有必要放宽鉴定人出庭的规定,除法院依职权认为需要出庭外,公诉人与当事人任何一方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并提出合理理由的,法庭都应当通知鉴定人出庭。除此之外,对鉴定人的人身安全、经济补偿保障的完善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9]。
将外耳道清洗干净后,用医用无菌棉签拭干,再用盐酸洛美沙星滴耳液(规格为5 mL:15 mg/瓶)治疗,6~10滴/次,患者的患侧耳道朝上,外用滴入,2次/d。治疗7 d为1个疗程,共1个疗程。
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出庭与鉴定人不完全相同,其在出庭前一般与案件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也没有义务必须出庭;不过,考虑到有专门知识的人对鉴定意见质证的重要作用,有必要重点从经济补偿和人身安全等方面确保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意愿。在当前控辩双方都可以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基础上,还应考虑法庭依职权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协助提供对鉴定意见或控辩双方意见的专家意见,避免控辩双方可能的抵触心理和担忧法官审判权的被剥夺,为法庭查明案件事实提供参考[19]。
4 结语
人权保障理念和刑法谦抑理念是我国当代刑法应当遵守的基本理念[20]。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鉴定为不负刑事责任或限制刑事责任,其应当获得刑罚上的减免;刑法任务的关键不在于惩罚,而在于教育并促使罪犯最终的回归社会。为此,刑事司法的过程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障碍鉴定持开放态度,无论是申请鉴定还是自行鉴定。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不确定时,通过正当的程序尽力确保实体的公正,不仅是人权保障的要求,也是司法公正的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鉴定为不负刑事责任、限制刑事责任,一方面反映了其自身失去或部分失去对行为辨认、控制能力的现状,国家、社会也有义务帮助其治疗;另一方面这种鉴定并不意味着其可以轻松逃脱惩罚,强制医疗及社会的标签效应不可避免,从轻处罚甚至不予宽宥也是常见的处理,但至少保障了程序正义的底线。
参考文献:
[1] 卫佳铭.张扣扣案二审,庭前会议报告:驳回精神障碍程度鉴定申请[DB/OL] .(2019-04-11)[2019-06-07]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87358.
[2] 陈卫东,程雷,孙皓,等.刑事案件精神病鉴定事实情况调研报告[J] .证据科学,2011(2):193-215.
[3] 郭华.精神病司法鉴定若干法律问题研究[J] .法学家,2012(2):121-136+179.
[4] 张丽卿.鉴定证据之研究[Z] .1994.
[5] 张钦廷,黄富银,管唯,等.精神疾病重新鉴定分析[J] .中国司法鉴定,2004(2):51-52+35.
[6] 朱大凤,罗国志,阮俊,等.宜昌地区333例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案例分析和随访调查[J] .中国民康医学,2012(7):829-831.
[7] 陈邦达.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实证研究——以382份刑事判决书及案例为样本[J] .法律适用,2017(23):59-65.
[8] 陈海锋.鉴定人出庭的认识误区与规制路径——以刑事诉讼为主要视角[J] .法学,2017(8):174-183.
[9] 张成杰,郑朝渊.张扣扣案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原判[DB/OL] .(2019-04-11)[2019-06-1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84930.
[10] 陈卫东,程雷.司法精神病鉴定基本问题研究[J] .法学研究,2012(1):163-178.
[11] 陈光中,曾新华,刘林呐.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J] .清华法学,2012(3):7-19.
[12] 卞建林,谢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发展——以《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之颁布为视角[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5):15-22.
[13] 杨宇冠.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点与完善[J] .法学杂志,2017(9):93-96.
[14] 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J] .法学研究,2004(2):107-115.
[15] 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J] .法学研究,2017(2):149-167.
[16] 霍宪丹.鉴定权是公民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兼析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现状与发展方向[J] .中国法医学杂志,2004(2):125-128.
[17] 杨尚峰.哈市警察致死案尸检结果公布 死者系外力作用致死[DB/OL] .(2008-11-06)[2016-07-26] 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8/11-06/1440373.shtml.
[18] 柴会群.女子以身试药拷问法医鉴定[J/OL] .(2009-07-15)[2016-07-19] .http://www.infzm.com/content/31493/0.
[19] 陈邦达.美国法庭聘请专家证人的实践与启示[J] .证据科学,2017(6):698-708.
[20] 陈兴良.当代中国的刑法理念[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3):136-150.
Discussion on Self-initiated Psychiatric Judicial Appraisal in Criminal Cases—Taking the Disputes on Appraisal in Zhang Koukou Case
YE Qing,SHENG Leim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42,China)
Abstract s: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China,there is no explicit provision on the parties'self-initiated appraisal of mental illness,but there is room for self-initiation in relevant normative documents,and there is a reasonable demand for self-initiation in practice.The opinion of self-initiated appraisal is qualified as evidence,and is a reasonable suspicion of the accusation,and the way of verification should not be directly excluded bu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judicial organs'examination.In ord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self-initiated appraisal,we should optimize the parties'right to apply for and participate in the appraisal procedure,improve the quality of appraisers and improve accountability,improve the system of appearing in court by appraisers and persons with expertise,and ultimately reduce self-initiated appraisal.
Key words: psychosis in criminal justice; self-initiated appraisal; examination by police and judicial organs
中图分类号: DF73;DF795.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671-2072.2019.04.001
文章编号: 1671-2072-(2019)04-0001-08
收稿日期: 2019-04-20
作者简介: 叶青(1963—),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诉讼法学研究。E-mail:yexsu@sohu.com。
(本文编辑:沈 敏)
标签:司法精神疾病论文; 自行鉴定论文; 公安司法机关审查论文; 华东政法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