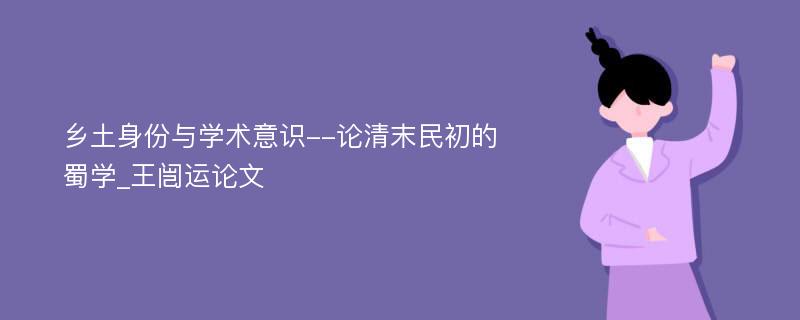
地方认同与学术自觉:清末民国的“蜀学”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民国论文,自觉论文,学术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0)06-0034-17
中国文化中地域意识的兴起甚早。先秦典籍如《诗经·国风》按国别编纂诗歌,《尚书·禹贡》注意到各地风土物产的差别。秦汉以后,各地区的文化多样性更受关注。《礼记·王制》明确提出各地文化不同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汉书·地理志》更注意到不同的历史经验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提示了自时空两条线考察地域文化的思路。这一意识在学术史中主要体现为一系列以地名加“学”字构成的名词,如宋代的“关学”、“洛学”、“闽学”及清代经学中的“吴派”、“皖派”等。它们常常成为“不证自明”的分析范畴,在学术史中使用甚广。
从实际运用看,某地之学中的“学”字,包含有学校、学风、学术以至文化等多层意谓,其指向须视上下文而定。一般学术史提到此类概念,则多着落在具有地方特色的学术层面上。但这种所指仍是模糊而宽泛的,所谓地方特色,或指某些学科,或指某些学派,或指某种学术路数,或数种涵义兼而有之,但有时也不过就只是代表了一个地域范围。显然,这类名词基本上是一开放的表述,其意涵处在不断波动中,而又多少指向一个相对统一的内核。
作为此类概念中的一个,“蜀学”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这可从既存研究对此概念的语义演变的梳理中看出一斑,兹不赘言①。需要指出的是,现有成果虽已多少注意到蜀学概念的开放性,而仍多倾向于将其视作一个清晰的实体,或依据个人看法为其划出一明确的疆界,进而努力讨论其特色所在。问题在于,为概念下个准确的定义,固然可能使研究对象清晰化,但也不无时代错位的危险。因此,怎样尊重历史中人对蜀学一词的理解,仍是蜀学研究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蜀学一名至少应有两个层面。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化学术实体的层面,这也是既存研究处理较集中的层面。其次,它也是一个被“表述”出来的对象。在此层面上,不论其作为一个实体是否存在以及具体面貌如何,此称谓的提出都反映了人们对四川学术文化状况的认知(有时或是“理想”)。对四川学者而言,此名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区域学术的自觉,而其中又寄托了超学术的关怀。清末民国一些四川学者对蜀学发展脉络的历史考察,一方面反映了蜀学内部彼此歧异的学术立场,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他们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大体类似的问题意识。这既与近代四川地方观念的形成有关,也是整个中国近代学术典范转移大运动的一部分。对这一学术传统建构过程的考察,无疑有助于我们对蜀学研究若干立场的反思。
不过,这两个层面虽有不同,又不能截然区分。表述要以一定的事实为基础,而一个概念一旦被表述,特别是被概念所涵盖的人群有意识地采用和阐发,也就反映了表述者的心理自觉,这又会成为一种塑造力量,对“现实”产生影响。一般认为,19世纪80年代以后,四川学术异军突起,影响力明显提升,成为近代“蜀学”勃兴的表征。此说延续既久,今日仍被学界接受,然实有不少事后追想成分,值得清理。不过,这些追想也建立在若干事实上,且正是晚清以来四川学术的实际发展,刺激了蜀中学人的“蜀学”自觉(此一称谓在历史上即存在,但近代学者采用此概念,自有特色),并试图对其重新诠释。本文意在结合近代四川地方社会和全国学术风气转移的大背景讨论四川和外省学人对蜀学的认知,基本集中在第二个层面,惟在此过程中,仍要兼顾“实”的层次。
一、近代蜀学兴起诸说检讨
一般认为,清代四川是移民社会,移民中多农、商,少士族,故其文化水平在全国长期落后。这一看法在清代就已存在。乾隆《雅州志》云:“蜀于献贼兵燹之后,又继以吴逆,疮痍未起,流亡未复,或有不耕不读之人。”[1]嘉庆《定远县志》云:“国初兵燹之后,家少藏书。士大夫子弟担簦负笈,远道从师。贫乏者教授生徒,兼营耕读。”[2]类似记录在有关文献中俯拾皆是,几成套版②。不过,至迟到了嘉庆时期,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已恢复,文化也继之复苏。同治《仁寿县志》谓,当地“入国朝二百余年”,儒风仍“未大畅”。直到道光八年才开始有了大的改善[3]。这一时间与道光《岳池县志》所述相近:“近日经学隆重,生儒皆知学古。研经茹史,颇多博洽之儒。数十年来,科名亦盛。”[4]虽都是印象式的描述,但既不约而同,亦应道出几分实情。
科举考试情况虽不能反映学术状况,但某地文风盛衰也关系着当地学术水平的高下,惟一般学术的兴盛当略晚于兴学。关于近代四川学术,学界多追溯到同、光时代的尊经书院,张之洞与王闿运则被视为两大助产士。黄崇麟说:“有清二百年,蜀学暗黮,恒不逮他行省。”直到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以经史词章之学倡导后进,而湘潭王壬甫先生为之师,于是文雅彬彬,比于江浙。”光绪初,吴之英、廖平、杨锐、宋育仁、胡延、张祥龄、吕翼文等“辐辏并出,颉颃上下,于是号称极盛”[5]565,566。吴虞也说:“蜀中文献,明末以来澌灭殆尽。”直到张之洞“建立尊经书院,蜀中人士始通古学,比于齐鲁”[6]36-37。
张之洞常被视为尊经书院的创办者,其对近代四川学术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清代正统汉学一线的引入,这特别体现在他为尊经书院学生编写的《书目答问》一书。虽然在此之前四川并非全与汉学绝缘,但张氏对此风气在川中推广功不可没,影响直到20世纪20年代不绝。其时曾就读于成都高师的姜亮夫说,林思进就要求学生“各备《书目答问》一册”[7]。陶亮生也说,向楚“见我所执注疏为叙府本,曰:‘此陋甚,当购南昌本有阮氏校勘记者,行间圈识最重要。’”[8]此法亦出于《书目答问》“十三经注疏”条下:“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四川书坊翻刻阮本,伪谬太多,不可读,且削去其圈,尤谬。”[9]
不过,张之洞本不以学术名家,且不久就离任了,故谈及清代四川学术,通常更重视王闿运。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列廖平、吴虞于王闿运后,云尊经学子“廖平治公羊、穀梁《春秋》,戴光治《书》,胡从简治《礼》,刘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师法,能不为阮元《经解》所囿,号曰‘蜀学’,则闿运以之也。”[10]78、622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于四川大学的萧印唐曾云,他在大学时,“闻师友说湘绮王氏。湘绮于逊清长尊经书院,自来蜀中,学风蔚盛焉。”[11]按此应在20年代中后期,彼时师友尚争说王湘绮,可知其影响之大。四川内外学人均把王闿运作为近代蜀学的开山祖师,实视蜀学为其余脉。
按照黄崇麟和钱基博所列名单,近代蜀学可谓彬彬多士。不过,一般学术史往往只提廖平,且每不忘称其为王闿运弟子。梁启超说,王闿运乃“文人耳”,于“经学所造甚浅”,而“平受其学,……知守今文家法”[12]56。说王闿运学问甚浅,又谓“平受其学”,则对廖平学术评价不高,仅许其“守今文家法”而已,未必真懂廖平③。然廖平学出湘绮,却是时人共识。章太炎在《訄书》初刻本中说:“闿运弟子,有井研廖平传其学,时有新义。”[13]8
清季四川学术在国内名声,泰半系于廖平一人,而一般认为廖平主今文学,故提及四川学术,多把其放入今文经学统系中,勾勒出一条从湖南到四川再到广东的传播路线。刘师培云:“湘中前有魏源,后有王闿运,均言《公羊》,故今文学派亦昌,传于西蜀、东粤。”[13]152川人庞石帚并不以廖平经学为佳,但也说:今文经学经庄方耕、刘申受等人“先后推阐”,王闿运“遍注群经”,廖平“尤善别今、古,益为闳肆,穷高极深,沦于不测。余论沾被,以启南海康长素,成其《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之说。于是微言大义,始自毗陵,流衍于吴、越、湖、湘,上溯于蜀,反注于粤,浸淫遍天下焉”[14]212。四川学术上承湖南王闿运,下开广东康有为,全副精神,似都在今文一线。
这样,在学者心目中,晚清四川学术确已获得全国性声望。其中评价最高者似为钱基博:“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10]562钱氏自不慊于此“疑古非圣”之风,惟蜀人对清季以来学风转移出力甚大,廖平为其枢纽,吴虞则集大成者,不管钱氏褒贬,蜀学地位已甚高。
不过,近代四川学界实不仅廖平一家独秀。在经学之外,小学、文学、史学皆可观;在经学之内,与廖立场不同者有吴之英等,自有风格。但这些在外省学者所著学术史中却少有提及。自然,虚名与实际往往颇有距离,外边的人不提,并不等于不好,但也说明尊经诸子真正获得全国声望的并不多。即使是廖平,也多是作为今文学二传手的形象出现,在通论性文字中,多附于王闿运后,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将其附于康有为章。至于世俗声望,廖平更无法和康有为相比。
其实,将四川学术放在晚清以来学风流变的系统论述中加以评估,更多地乃是事后的诠释。康有为发挥廖氏学说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后,名声蔚起,廖氏移书云:“后之人不治经则已,治经则无论从违,《伪经考》不能不一问途,与鄙人《今古学考》,永为治经之门径,欣忭何极!”又云:“天下之为是说,惟我二人,声气相求,不宜隔绝,以招谗间。其中位置,一听尊命”,惟希望“称引必及,使命必道,得失相闻,患难与共”。钱穆说:“《伪经考》既享大名,季平欲藉其称引,自显姓字,故为《古学考》先两引长素《伪经考》云云,我以此施,亦期彼以此报。盖长素骤得盛名,全由《伪经季》一书,宜季平健羡不能置。而长素则深讳不愿自白。然季平亦震于盛名,方期相为桴鼓,故书辞亦逊”④。则正看出廖平彼时社会声望远不如康。
同时,前引黄崇麟、吴虞等描述蜀学勃兴,几乎不约而同用了“比于江浙”、“比于齐鲁”的话,反见其内心对蜀学地位实不甚自信。这些脱口而出的用语,和前述廖平期望康有为“称引”一样,都是长期处在边缘者的心态⑤。另一方面,在讨论近代学术的著作中(四川学者作品除外),对蜀人注意较多的乃是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但书中有关廖平、吴虞等的记述,乃是第4版增补,此前数版,并未及之,也意味着蜀学最初并未进入其眼中,则蜀学在全国的影响力到底如何,亦甚难言矣⑥。
故晚清民初四川学术实际是处于已有所发展并潜在地开始对其他地区学术产生影响,而在人们心目中仍基本处于边缘的状态。有关此时蜀学勃兴的论述,有一半乃是事后的总结,未必真正反映了实况,也多少夹杂了想像。但这些论述也绝非虚构,自有若干事实为素地。实际上,此期的四川学术确实呈现一些特色,正是这些特色成为近代蜀学论的依据,而它们又必须放在整个近代学术转型和四川文化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加以解析。
二、近世学风转移与蜀学勃兴
钱穆曾说,学术潮流“皆出于时代之需要”。及至“时代变,需要衰,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15]。蒙文通则云:“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16]在近代蜀之学人中,廖平尤受关注,正是“时代变”的表现;且正因为他是时代浪尖上的人物,故提到近代蜀学,多突出之。但前已讲过,其时四川学界绝非只有廖平。研究近代学界尤其是川外学者对蜀学认知,自不能不突出那些有全国声望的学者,但此中所见也更多的是“全国”而非四川;研究四川学术,则必须同时兼顾那些不常被提到的学人。蒙先生提到的“学脉渊源”,也须做多角度的理解。既要关注学派系统,也要注意某地区文化风格的影响。一般学术史提到廖平,主要注意的还是今文学;但如果放眼尊经书院乃至四川学界全体,不但今文学不足以涵盖之,且近代蜀学自张之洞、王闿运二人所开辟的结论也须稍作辨正。
把近代蜀学自尊经书院算起,意味着清代四川在此前无所谓“学”。但仅凭一二人之力(且其在学术上亦无高深建树)而使一个地区学术蔚起,实不无夸张。更重要的是,尊经书院几乎同时涌现大批人才,意味着此前四川文化土壤中已经存在合适的种子,一旦春风吹过,立刻萌发壮大。这看起像是忽如其来,实际是由于研究者忽视了一些潜在根苗所致。
学界断言四川文化落后的一个重要根据是科考情况。但能否在科考中胜出,不仅取决于考生水平,还取决于录取标准。考官喜好往往决定了考生能否中试,这种喜好一旦为人接受,又成为风气所趋。对于居住在偏远地区的考生来说,常因不了解这些风气落第。清代四川恰是这样一个地区。道光年间一位任职江安的官员就说,该地二百年来“擢科甲者仅二人”。他“检阅戊子科落卷”,发现“笔意条鬯者颇多,然皆疏于法,又无熔铸才,此特不讲求之过也”[17]。江安考生“无举于乡”,不见得是水平不够,而是不了解科场风气所致。这里揭示的问题,恐怕不是江安一地特有的。李新就说:由于方言影响,“在科举考试的年代,不少四川举子,常因作诗押错韵而名落孙山”,并举出他幼年时的一位老师为例[18]。这也是因为文化风气与外地不同而吃亏的事例,仍可谓是“不讲求之过也”。
学额限制也是造成一般印象中清代四川文化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据张仲礼统计,1812年,四川府厅州县有官学152所,以数量论,位居全国第三;但学额仅1366人,位居全国第七,而位居第一的直隶较四川多出近1500人。这一状况在1886年的统计中有所改观:四川官学155所,居全国第二;学额增为1918人,居全国第五,但位居第一的直隶学额也增加了,仍较四川多出970人[19]。官学数多,未必意味着读书人整体数量大,但学额与官学数不成正比,四川显然吃亏不少。
清初到清代中叶,四川确是文献凋敝。张之洞在同治十年注意到:“楚、蜀藏书家、彝器家皆少。”[20]10105清末四川成立存古学堂,谢无量向社会各界募捐,仍说:“蜀地僻远,民间鲜藏书之家。”[21]2不过,仍有一些例外。赵熙曾说,乾、嘉之际,其曾祖“已多藏书”[22]1253,则已有学尚博雅之士;而乾隆时的李调元已开始从事朴学,治经宗郑玄。张循注意到:“四川汉学风气之起固不待张之洞的推动,但张氏督学之后,此风气方得普及。”[23]421是也(惟其时汉学是否已经达到“风气之起”的程度,仍可商榷)。
在汉学以外,前尊经书院时期的四川学界更多可观。雍正时期的彭端淑长于古文辞,对蜀地文风产生过影响。蜀人中讲宋学者亦多。清初有费密⑦。钱穆云:“晚明兵燹,蜀中所罹尤惨酷,宜其学者谈思所及,常有余痛,而激宕所至,亦与河北颜、李如合符节,若新繁费氏其著也。”[24]他特别从蜀地历史中寻找费氏学术精神所在,值得关注。嘉庆时期刘沅学杂三教,在儒学脉络中倾向宋学,而尤近陆王一线。其学通过“刘门教”在民间传播甚广,实系清代蜀学一潜流,值得更深入研究⑧。
按照主流汉学立场来看,前尊经书院时期的四川学术确可谓不入流。惟也正因如此,川人对学术风气的变化也就较易有体会。咸同时的李榕论学调停汉宋,谓:“汉学详训诂,宋学明义理。学问之道,二而一者也。”又云,汉学“主于切实”,其弊或在“穿凿附会,曲为臆说”;宋学“主于精深”,其弊或在“悠蔓奥衍,而矜为独得”。调和汉宋,正是得时代先机的议论⑨。是李榕虽不以学术知名,而学术感受力是相当敏锐的。
清末四川读书人给外人的一个印象即聪慧趋新。张之洞言:“蜀中人士聪敏解悟,向善好胜,不胶己见,易于鼓动,远胜他省。”[20]10056王闿运说:“蜀士驯秀虚心,异于湘上。”⑩吴庆坻也说:“蜀士聪俊,可与言开新知者,不乏其人,因艺导之,颇得通敏之士,它日或觊有出而表异者,山川之灵,庶几其不终阏乎。”又云:“蜀士秀杰,稍病浮夸,其间有通识能知时者,颇不乏人。……此邦人士,不患风气不开,而患志识不正。……蜀士它日有兴起者,当可与东南诸子颉颃,此亦山川之气,久而必昌,机固如此耳。”[25]377,379其观察较张之洞差了20余年,结论则非常相类。
不过,参与了维新事业的蜀人吴樵则说:“四川之不开化,非湖南之比。湘人固拒,川人恍惚。固拒者有物,恍惚无精。蜀民之变,恐在天下后矣。”[25]505-506与前述诸人看法相异,大约乃是爱之深恨之切,但他也明确指出川人不变非“固拒”也。揆诸实例,可知上述诸人的见解不错,廖平经学就正可说是张之洞判断的注解。
关键是,清代学术在咸、同以降确已在发生大变化,汉学正统衰落,各路英雄竞起,恰是一个求变求新的时代。蒙文通1925年写《议蜀学》,实际是议“廖学”,开篇便从清代经学“之穷”讲起:“清代经学之明,称轶前世。……迄乎近世,特识之士,始喟然慨清儒之无成,独古音之学,实能于散漫繁惑之中明其统理,斯为足尚,则清学之穷矣!”穷则变,故清季“浮丽之论张,儒者侈谈百家之言,于孔子之学稍疏,经术至是,虽欲不改弦而更张之,诚不可得”。廖平学术的勃兴,便与此变化息息相关:“井研廖先生崛起斯时,乃一屏碎末支离之学不屑究,发愤于《春秋》,遂得悟于礼制。《今古学考》成,而昔人说经异同之故纷纭而不决者,至是平分江河,若示指掌。……论者比之亭林顾氏之于古音,潜丘阎氏之于古文《尚书》,为三大发明。于是廖氏之学,自为一宗,立异前哲,岸然以独树而自雄也!盖三百年间之经学,其本在小学,其要在声韵,其详在名物,其道最适于《诗》、《书》,其源则导自顾氏者也。廖氏之学,其要在《礼》经,其精在《春秋》,不循昔贤之旧轨,其于顾氏,固各自张其帜以相抗也。”[26]177-178蒙氏特意把廖学与清学区分开,其划时代的意味昭昭;而廖平的崛起,也是应此时代的需要造出的英雄。
自王闿运后,今文经学在四川大行其道,廖平学说一时甚得势。庞石帚言清末民初川内学术风气云:“蜀人言经,必曰廖氏。游食之士,攀附光景,惟恐弗及,至有不读注疏,不知惠、戴、庄、刘为何人,而日言‘三科九旨’、‘五际四始’,附会牵引,无所不蔇。”[14]212-213姜亮夫也说,自廖平学术出,康有为大扇其风,“蜀士之轻偼者悉尊之”[27]286。郭沫若说,在乐山读小学堂期间,“帅平均老师讲的《今文尚书》讲义是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后来“在中学里面感觉兴趣的仍然是经学”[28]。帅平均和郭的中学经学老师黄经华均是廖平弟子,则郭氏感兴趣的主要还是廖平的学问。张秀熟则回忆自己1917年升入成都高师本科,由廖平讲授“群经大义”,张甚崇拜之,“立志将来作一个经学家。在笔记本上,仿朱熹称二程子为‘子程子’的例,写为‘子廖子’口授”[29]。均可想像廖平的号召力。
那些不以今文学自居的学者亦多染此风。吴之英主张会通今古,其《寄廖平》诗云:“礼制何必说古今,历代损益圣贤心。”[5]71根本不同意经学分古今的取向。稍后精于经学者有龚道耕,其论学亦与廖氏异。与龚交往甚多的庞石帚言,对于“蜀人言经,必曰廖氏”,“先生故深耻之,益闭门自精,于廖说不为苟同”[14]212-213。姜亮夫也说其“虽与廖君同郡国,且亦习今文,悯其恣睢不实,以为此哗世取宠,弋取富贵尔,故从无一语和之”[27]286-287。龚氏以“希郑(玄)”为号,亦会通今古一脉也。不过,正如庞、姜所提示的,会通今古亦需“习今文”。
在经今文学以外,宋学一直在四川不衰。曾学传、徐炯等俱以理学著名,龚道耕也学兼汉宋。稍晚一辈人中,专治理学者则唐迪风等,蒙文通亦一生对理学情有独钟。宣统二年(1910年)四川存古学堂招生,以理学、经学、史学、词章四门为正课,教经学者即为曾学传,张循推断曾氏所讲不出理学范围,则此四门功课中宋学就占了两门[23]391。如是,则清季四川理学风气之盛可想而知。讲宋学乃是四川学界的“传统”,今文经学更多受到外来学风的影响,惟从全国学术典范转移的趋向看,这两种学问均是近代学风趋新的产物,而蜀人于此均有独得,殆非偶然。在这方面,近代蜀学确与湘学近(按此是讲大趋势和为学风格,非特指王湘绮一路经学也)。罗志田教授曾论近世湖南学风:“在学术典范的‘话语权势’存在时,‘独立’不过是不入流的代名词;只有在道咸以后,经学之正统已衰落,‘独立’才可能成为正面价值。价值观一变,不利的条件就转化成有利的因素了。”[30]近代的蜀学与湘学均面临着类似环境,故学者多将其并提。
近代蜀学与湘学还有一个类似处,即是对新学的接受。在这方面,学界也长期存在误解。钱基博云:“蜀处奥壤,风气每后于东南。”西学流布后,“蜀中老宿,蹈常习故,指其政治、舆地、兵械、格致之学为异端,厉禁綦严,不啻鸩酒漏脯”。吴虞则“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也”[10]72,77。吴氏自己也说:“新学自壬寅、癸卯以来”,他与几位趋新士人“竭力提倡”,不到十二年“而风气大通,学校林立”[6]36-37。蜀地确乎“风气每后于东南”,但其人“易于鼓动”也不容忽视。川人在戊戌期间的作为有目共睹,除了杨锐、刘光第外,吴之英、宋育仁、骆成骧、赵熙均是新派,其于兵械、格致之学或确不通,而于西人政治学说绝不“厉禁”,廖平学术更是融入大量西学元素,固不逮吴虞等开风气也。
清季民初四川最流行的学问大抵是道咸以降兴起的学术新风气,这表明蜀学实是中国近代学术的一部分,且廖平能够获得全国性声誉,也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这一总体性的学术典范转移。
三、近代四川地方认同和学术自信心的提升
前面讨论了近代四川学术的兴起及其与全国范围内学术典范转移的关联,这多被视为蜀学勃兴之相。不过,“蜀学”在实际上是否自成一格是一回事,蜀人有未自觉意识到“蜀学”的存在并将其作为一种追求目标是另一回事。后者自然要以前者为基础,但仍是一独立问题,而这又是和近代四川地方认同的兴起分不开的。
这要再次回到清代四川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特征上。移民通常会在社会层面上经过一个由分到合、在心理层面上经过一个由保持强烈的原乡认同到转向新家乡的过程。不过,这涉及心态,相对模糊,持续甚久,亦无明确的阶段性标准,实难把握;同时,四川地域辽阔,对于不同地区乃至具体个人(包括叙述者和记录者)来说,答案也有很大差异。一般说来,大多数移民后裔都自认已成“四川人”,大约已是光绪时期甚至是清季几年的事情了。近代蜀学概念的流变,也是这一意识在学术文化上的体现。
对地方文献的整理是清代四川认同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和体现。李调元已开始整理乡梓文献,编有《蜀碑记》、《蜀碑记补》等著作[31]。嘉庆初,朱遐唐购得杨慎《全蜀艺文志》稿本,加以校对,付梓刊行,距此书成稿已达257年。此后,经安岳谭言蔼等人整理重刊。光绪三十一年,安岳邹兰生又将其整理印行。应邀为此书作序的俞廷举云:“李穆堂曰:凡能拾人遗文残稿,而代存之者,功德当与哺弃儿、埋枯骨同。夫以本地之文献,本地之人,尤当爱惜而表章之。”历史名人之书自可流传,“若迁客骚人、隐逸缁黄辈,名位未著人间,其所作零星碎锦,片羽只光,必附青云乃显者,不得是刻,不几湮没弗传乎?噫,亦幸矣!使升庵诸公闻之,固未有不鼓掌称快者。然蜀之贤士大夫多矣,百余年来,何以任其湮没,不闻续刻于前,而必俟我遐唐,始得重刻一新。噫,亦甚危矣!”[32]此书的整理刻印是与四川地方社会、文化重建的进程相吻合的。事实上,首次将此书整理出版的朱遐唐只是曾在蜀为官、寓居蜀地的江陵人,而参与此书后来整理重刻工作的便都是川人了,其中如谭言蔼还是移民后裔。这种“本地之人”表彰“本地之文献”的过程,折射出四川士人地方认同感的发展轨迹。
对乡邦文献的整理既是士人地方认同感的体现,也强化了这种认同。前引同治《仁寿县志》说四川在宋代文化彬彬而历经元、明、清未能复原的感慨就揭示了作者对地方文化发展状况的关注。嘉庆《双流县志》也流露出类似的不安:“双流当宋元明时,世家遗俗,相沿七八百载。”经“明季兵燹后,招集雁户,苟安苟得”,风俗沦丧[33]。历史的辉煌与晚近的黯淡相对比,造成四川读书人长期存在一种焦虑感。吴之英有写杨慎的《桂湖》诗,其序曰:“英尝谓吾蜀自汉室初兴,司马相如以文章冠天下,厥后异代间生,虽类聚无多,皆有清拔之才,震熿当世。(杨)慎之在明,亦天生独使者也。而由慎至今,未有作者,是可慨已!”[5]55宣统元年,谢无量也说:“蜀兴自人皇以来,蜀山巨灵尚矣,巴黔则有神农之祥焉,峨眉则有黄帝受经咨道之迹焉。凡大酋秘藏三坟之文,彪炳恢奇,露见乎岩壁,不可胜数。”直到“秦灭蜀置郡县,犹代以文章冠天下。降至元明之际,兵火盗贼相接,遗民熸焉”,遂至“典籍畔散,风雅响息”[21]1。
这种焦虑感和四川地方认同的强化结合在一起,流传甚广。聂荣臻曾云,由于交通不便,清政府很难控制“富饶”的四川,“同时,四川人民富有反抗精神,对清王朝的统治并不买账,不断掀起各种斗争。因此,清政府对四川人民是又气又恨,统治手段特别残酷”。他还举证小时听到的传说:“清朝的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可见对四川人厌恶之深。可是,四川人还是争了一口气,有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把他中状元的事情传为佳话,说什么‘骆’字拆开是‘马’字和‘各’字,‘角’和‘各’在我们四川是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34]
“石头开花马生角”显然是街谈巷议,不足为据。不过,这个传说一方面折射了地方认同感在川人中的普及,另一方面也流露了对四川文化不具备全国性地位的不满,代表一种流行的社会心态,是非常传神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说把川人不中状元与“清朝官员”的嫉恨联系起来,似乎问题主要是由于外来的歧视造成的,既有一种屈辱感,也已隐隐透露出川人文化自信心的提升。四川曾有民谣云:“光绪乙未年,势不比从前。”[35]即指骆成骧于光绪乙未科(1895年)中状元之事,扬眉吐气之情溢于言表,再次表明此事对四川地方社会心态的影响。
蜀学在全国的地位是清末民国四川学者持续关注的问题。直到傅增湘编《宋代蜀文辑存》还说,其“于乡邦文献尤三致意焉。后阅《宋史》,见吾蜀人名登列传者至一百五十余人,其人类以政治、学术有名于当代。设纂其遗文,汇为一编,扬蜀国之光华,即以彰一朝之文治,岂非不朽盛业乎?乃稽之簿录,《四库》所存两宋蜀人之集,不越三十家;且有本集久亡,而由《大典》辑出者,又居其半。然后知蜀都耆旧之文,历四朝七八百年,沦丧于兵尘,摧毁于蠹屑者,正不知纪极”,于是“怵然于网罗放失之责”[36]。动机和吴之英相似,都是对蜀学长期在国内处于边缘状态感到不满,但关注点显然又不同。吴氏承认清代四川文化处在衰落之中而思以振兴之,傅增湘则更多强调蜀中文献长期隐没不彰而欲以表彰之。二人关注非同一时段,宜乎所见不同,但从表述重点看,傅增湘的文化自信心已增强很多。
这和川人地方意识的勃兴有关。清末《四川》杂志发表过一篇《过去之四川》,其“意在溯文明之变迁,考先贤之旧事,明攻守之得失,叙治乱之由来。使读者参观过去陈迹,即知吾四川未始不可以有为,感怀现在之心生,希望将来之念起”。作者把四川历史追溯到人皇时期,谓人皇有弟八人,分封域内,巴蜀居其一:“其血统之尊,固足矜尚;其建国之古,亦无与伦比者。特异如是,维我蜀人。尚论至此,岂不足多乎!”[37]作者显然忘记了,即使原始蜀人的血统真可上溯至“人皇”,但“我蜀人”多为明清移民后裔,实与之无关。惟制造谱系历来是凝聚族群认同的手段,作者着意提拔蜀人地位,更有激励救国之心的含义在。
清末另一份杂志《鹃声》则是因为看到东南很多地方都办有白话报,而“我们四川一省,一种白话报都莫有”而感到“可耻可恨”。“鹃声”二字典出杜宇传说,“原来是望我们四川人,听了‘鹃声’二字,就想起来亡国的惨历史,触目惊心”。这也在反映出地方意识的觉悟。该文虽和前文着力强调历史的光荣不同,意向是一致的,都归结于四川对中国的责任。
作者进一步强调:四川地大人多,财力“雄富”,风土、气候、历史、社会、文学、美术,“无不与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以及扬子江下游三河系绝不相混,如别辟一新天地”,而“负有一独立国的资格”。但川人“程度”不高,“为各省同胞所不耻,不骂我们是川老鼠,就骂四川人有奴隶性质,为中国民族中之最劣种”(11)。这里有关四川的一些言说,实流传很久。王闿运光绪六年回湘探亲返蜀途中诗就有“乘车入鼠穴”句,又此前王氏仍在湘中时,二少年问“往俄往蜀孰利”,王“云蜀亦外国也”[38]。惟王氏不无揶揄之意,此处则成正面形象。作者一方面强调地理、历史的优势与独特性,另一方面强调现时人民“程度”的低下,喜忧交杂,表明此一时期四川地方意识的复杂性。
同一时期的《蜀报》也透露出同样思虑。创办者提出,川人离立宪国民的标准相去甚远:“吾蜀虽地居西偏,得天下风气之后,苟非丧心病狂,必无反对立宪之意思。第较诸大江南北沿海各行省,被发撄冠,上以强聒其君父,下以提倡其乡间者,固瞠乎若后矣。中国国会制成立,早暮虽不可知,使幸而得请,以吾蜀委随期间,碌碌无所表见,固可耻;不幸而不得请,当局者或以边省人民程度不齐为辞,则以吾蜀之不自振拔,而使天下不速蒙国会之利,甚且陷中国于意外之危亡,此则吾人之所大惧深忧”者(12)。
作者承认川省人民程度落后于其他地区,而唯恐蜀人“不自振拔”,便可能连累全国。这与《说鹃声》一文不尽相同。后者主要强调四川在自然资源和文化方面的优越,进而提出四川在全国地位的重要性;此文则对此未置一词,反而是从非常消极的方面论证四川的重要性。不过,两位作者都同意四川是影响到全国的。1903年,蜀人钟云舫赠岑春煊诗云:“天下常山首西蜀,蜀中治乱关全局。”(13)也是同样意谓。
四川自成地理单元,交通不便,社会与文化方面也自成风气,故一般缺乏全国性的影响力。不过,正如《说鹃声》提示的,一旦国内形势发生变化,边缘便可能一变而为优势。梁启超在《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文中说:“我蜀僻处西陲,距海岸最远,以交通之不便,故开化稍后于中原,而外力之侵入,受其影响者亦较缓。今日沿江沿海各要区,已亡之羊,不可追矣。惟全蜀一片干净土,其地力之丰、民数之繁、天险之固,皆非他省可逮。识者谓我族终有蜀,则中国虽亡犹可以图存,非过言也。”[39]这是特意讲给川人听的,但亦可与前引川人的言论相互发明,代表了其时的一股思潮(然其影响力主要也还是在四川人中)。
梁启超夸奖四川主要集中在地理、人口等“硬件”方面,至于学术则不甚许可:“四川夙产文士,学者希焉。晚明成都杨升庵慎以杂博闻,入清乃有新繁燕峰费密传其父经虞之学,而师孙夏峰,友万季野、李恕谷,著书大抨击宋儒,实思想界革命急先锋也。康熙中叶,则达县唐铸万甄著《潜书》,颇阐名理,洞时务。然两人皆流寓江淮,受他邦影响不小也。同光间王壬秋为蜀书院师,其弟子有井研廖季平,平治今文经学,晚乃穿凿怪诞,不可究诘。”(14)强调有成就的川人均“受他邦影响不小”,显然不怎么看得起。其他各家虽未明言,但所关注者每只廖平一人,且多视为王闿运一线传人,当然还是“受他邦影响”也。
不过,蒙文通在《议蜀学》一文里提到的经分文家则根本未及王闿运。30年代初,他更是明确提出:“前乎廖师者”,有陈寿祺父子、陈立等,“皆究洞于师法,而知礼制为要。然大本未立,故仍多参差出入。廖师推本清代经术,常称二陈著论,渐别古今。廖师之今文学固出自王湘绮之门,然实接近二陈一派之今文学,实综合群言耳建其枢极也”[40]。正所谓“知师固莫如弟子”也。按廖平不欲依傍王闿运,蜀人知之甚详。吴虞曾记廖平言:“王湘潭于经学乃半路出家,所为《春秋例表》,至于自己亦不能寻检。世或谓湘潭为讲今学,真冤枉也。”[6]91明是看不起王的学问。又记,廖“居蜀时,未敢自信其说”,出蜀后,交接俞樾等学界大老,“以所怀疑质之,皆莫能解,胆乃益大。于湘潭之学,不肯依傍”。故王闿运与人书,谓其子王代功、弟子杨度乃“依我以立名”,廖平则“思外我以立名”,而许其“能自立”。王死后,廖平祭文“亦有避水画火之语”[6]93-94。此段回忆甚生动。可知其先“未敢自信”,乃因久处“边地”所致,内心实早有独立之意,与外间学术界的交往也强化了廖平信心。如吴虞转述的是廖平原话,则还暗示着如果在外间不能印证自己的学问,廖平或也不会明确独立于湘潭之外。
吴虞又记胡安澜云:“季平长游湖北,历指《书目答问》之谬误。南皮爽然久之,曰:‘予老矣,岂能再与汝递受业帖子耶?’是后,南皮颇言高邮派之非(湘潭即高邮一派)。南方人士,知受季平之影响,谓廖说若行,南方经学,罕能立足,遂授意吴郁生,而参劾季平丈之事发生矣。(赵启霖为湘潭弟子,以廖学与湘潭参商,亦大不洽。)故南皮之亡,同学公祭,季平丈独痛哭,盖感南皮之相知也。”[6]91(15)王闿运为高邮一派,此说似是胡氏的“独家报道”,不过,他注意到廖平最与张之洞亲近是很重要的,而张亦深知廖者。惟张不以经学名,则廖所得仍是自悟。胡推测廖平被劾出于经学内部各派之争,尤与廖学不肯依傍王闿运有关,仍待考证,惟其云“廖说若行,南方经学,罕能立足”,则可知蜀中学人确把廖学视为独立一家。从廖平自己由“未敢自信”而“胆益大”,再到蜀人传言廖说一行则“南方经学”可危,蜀人对蜀学的信心不断增强。
廖平学术自成一派,也得到章太炎的认可。章氏最初在《訄书》中说廖平“传”王闿运学,后改为:“闿运弟子,有井研廖平,自名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左氏为六经总传,说虽不根,然犹愈于魏源辈绝无伦类者。”[13]17则已承认廖学已独成一家了。廖平逝世后,太炎再次强调:“初,君受学湘潭王翁,其后说渐异,王翁颇非之。清大学士南皮张之洞尤重君。及君以大统说《周礼》,之洞遗书,以为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而有为之徒见君前后异论,谓君受之洞贿,著书自驳,此岂足以污君者哉?君学有根柢,于古近经说无不窥,非若康氏之剽窃者;应物端和,未尝有倨容,又非若康氏自拟玄圣居之不疑者也。顾其智虑过锐,流于谲奇,以是与朴学异趣。”[13]101则廖学不但异于王,亦不同于康,确可谓“自名其学”也。
蜀人为学求自立,非独廖平为然。吴之英自述其祖父授其为文之法:“古昔有鸿文,高韵何清丽!已近咫剿袭,已远咫缪戾。不远亦不近,孤立求真谛。理质意自卓,气赢辞有系。我学非古法,我法非今制。格律会精神,得诸天地际”。所谓“孤立求真谛”、“非古法”、“非今制”,皆写出自求一格的胸怀。又说:“蜀都广乡学,石室仍新构。郡县悬高材,弟子聿来凑。大师据尊席,列坐承口授。我时与讲会,默默无往复。先生故设辞,诘屈引灵窦。颤而机初触,捷而意与遘。终乃搰搰而,精爽交驰骤。先生兀惊咨,为汝遐老耇。我为说我法,家世传以旧。”[5]6,8-9这一段叙述在尊经书院从王闿运学的情形,主题在强调其治经之法来自家传。故吴、廖学术不同,而均不甚认可其学出自王闿运,和一般的认知颇有距离。
廖平曾云,德阳刘子碓“心思精锐,好辟新说”,读《今古学考》后,“以为治经不讲今、古,是为野战”,但“讲今、古,又不免拾人牙慧”,故“不肯治经”,而“耑攻诗辞”[41]。此又一自立门户的例子。廖、吴同门有富顺陈崇哲亦修习经学,吴之英言其论学宗旨云:“习见郑、何列同异,不嫌贾、马更短长。各具真识求独到,出我入我自门墙。”[5]31最后一句可能是陈氏真意,也可能是吴之英“仁者见仁”,不过无论如何,都反映出蜀中学者不但在学术风格上确有其独到之处,在主观上亦以追求独立为治学目标,成为近代蜀学勃兴的重要心理渊源。
汪国垣对近代四川诗派颇为赞赏,而言蜀中诗派自有渊源:“张广雅督学蜀中,以雅正导其先路;王湘绮讲学尊经,以绮靡振其宗风。风声所树,沾溉靡涯。惟蜀中诗派,自有其渊源可寻,广雅、湘绮虽启迪之,蜀人未能尽弃其所学而学之也。”他引述陈衍论赵熙的话,认为四川诗人所作“甚肖蜀中山水”,而引申曰:“诗人每与地域山水相发。”[22]1356-1357胡先骕论赵熙词,亦云:“昔人尝称文章在得江山之助,征诸往事每每而信。”赵熙生于峨眉山下,“于此故倍能擅场”[42]。均强调蜀人诗词独成一格,自有脉络可寻。
论及文学,蜀人之气确要充足许多。吴之英有自杨慎以后蜀中无有“作者”的感慨,而乡人赵正和挽吴联亦说:“蜀士号能文,自扬、马而还,旷世逸才人几个?”[5]122二人看法似颇谦让,但“蜀士号能文”一句,也确有几分得意。赵熙更是认为,四川经学或不逮人,文学直可谓天下第一:“巴蜀以文章盛,谈者谓司马相如后,文学彬彬比齐鲁,此或经术然耳;若其文章,则楚骚外无伦北也。二千年夏声,至于今而寂,今之世又自奴于海外之言。惟荣也为僻乡,今求学于斯,而为举世所不为者,诗其一也。”[22]1222(16)
一方面是追求独立的治学取向,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强的文化自信,作为一个学派意义的蜀学概念的提出已是呼之欲出了。
四、近代蜀学的自觉
蜀学二字在清末已较流行,其时有两个团体都以此为名,一是杨锐等1898年在北京成立的蜀学会(并设蜀学堂),二是同一年宋育仁等在成都尊经书院设立的蜀学会(刊行《蜀学报》)。粟品孝已指出,前一蜀学会取名“蜀学”,仅仅因为发起者和参加者均为蜀人。后一蜀学会则明确提出“昌明蜀学”的口号,而其所谓蜀学“就是蜀地之学,具体是指在蜀地学习以儒家经学为核心、包括西学在内的学术文化”。不过,仍需稍做辨正。杨锐等所办蜀学会与其时闽学会、浙学会、湘学会等团体相类,蜀、闽、浙、湘等只是一个词头,关键部分是在“学会”二字,确与一般在学派意义上使用的“蜀学”、“湘学”等落在地域上不同。至于宋育仁等办蜀学会,情形似稍复杂。一方面,粟先生已引用过的《蜀学会章程》第一条云:“现在时事棘艰,叠奉上谕,各省振兴学校,以期储才备用。学使慨济时艰,尤以振兴蜀学为念。”则此处所谓“蜀学”者,主要指学校,仍非学派也。就此而言,它和北京蜀学会虽有偏重教育和议政的不同,本质上似无甚差别。惟另一方面,《蜀学报》主笔吴之英又说:“蜀故有学也,何至今日始会始报也?曰:蜀学微矣。学者失其所学,今将返吾故焉,故以蜀学名也。”(17)此蜀学实已涵盖整个文化学术(仍包括学校在内),而“返吾故焉”四字更直接透露出强烈的地域自觉,含有文化认同意味。
晚清人对蜀学一词的使用,值得注意的还有两个例子。一是光绪十四年冬初刊的《蜀学编》。此书原为尊经书院两位学生方守道、童煦章所辑课艺,原题《蜀贤事略》,经曾任四川学政的高赓恩与尊经书院山长伍肇龄增补而成。此书收集四川历史上“心术、学术不诡于正”的学人,辑录其事迹,参考的范本是《关学编》、《洛学编》等。这里的“蜀”标定的毋宁是四川这一地域范围,近乎宋育仁等人的用法。特别要提出的是,《蜀学编》的发起者是宁河高赓恩,意在训士,而编者多为蜀人,更多一重地方认同之感。伍肇龄在序中就说:“由是敦崇四教,以上溯邹鲁渊源,将张、魏所诣,尚可扩充,岂徒以扬、马文章夸冠天下哉!”[43]显然,在伍氏看来,川人为学“徒以扬、马文章夸冠天下”,而对此实不以为然,则此编是要通过对“蜀学”渊源的发掘,以振拔蜀地士风。
相对说来,另一条材料更倾向于“有特色的学派”这一意义。1886年,廖平在《今古学考》中说:“予创为今、古二派,以复西京之旧,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18)则廖平的计划是以自己学说为框架,联合蜀中学人,以成“蜀学”。换言之,真正的“蜀学”仍是“未来时”,惟大纲已具。此已是兼具地域与学派两重意义的概念。但有意思的是,廖平的同学岳森则在致廖的信中说,此书即使告成,“只为兄一人之业,于全蜀无与”(19)。则廖平心中的蜀学在岳森看来,仍只是廖学,不能算作真正的蜀学也。
进入20世纪,在学派意义上使用而更明确地具有地域认同意义的蜀学一词更广泛地使用起来,本文拟以谢无量、刘咸炘、蒙文通的三篇文章为例,加以分析。
谢无量《蜀学会叙》为其倡设的蜀学会(与前述两个蜀学会同名)所作,是一篇综论蜀学的文章,首揭“揵”、“通”、“礼”三义。揵者,“守其固有之学”也,实是一部蜀学简史。通者,“明其未有之学”也,主要指西学,即谢无量认为生当此世应掌握的新知,体现出蜀学的开放性。不过,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学人均面临的任务,故与“蜀”不“蜀”实无多大关系。第三部分叙“礼”,实为蜀学会的章程,其中解释此会得名:“蜀人公创论学之会,故名蜀学会。”又云:“蜀学会在佐蜀人兴起于学,修其所有者、以达其所未有者,无关于学则一切不论。”又云:“蜀学会以谿(“谿”,《崇文集》本作“一”)进全蜀智识学问为旨。”又云:“本会既厝意蜀字(“字”,《崇文集》本作“学”),有改造蜀士之责。及蜀中教育之事,有所弊害,皆当出其力而干涉之。”并有在成都设立大学,“使蜀人之向学者不必奔赴求学外省”的计划(20)。可知谢无量使用蜀学这一概念,亦取义甚广。不过,其讨论“固有之学”又主要集中在四川学术史方面,故本文主要讨论其第一部分。
谢无量提出:“蜀有学先于中国。国人数千年崇戴为教宗者,惟儒惟道,其实皆蜀人所创。”此外,还有“其学不自蜀出,得蜀人始大;及蜀人治之独胜者”,均可称为蜀学。简要说来,包括儒、道、释、文章四部。
蜀人对于儒学的贡献有二。首先,原始儒学乃禹所创:“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伏羲因河图画卦,禹受洛书,乃制洪范。洪范于人事详已,儒者所法,故禹纯然儒学之祖。易广大而不可测,深切著明,莫如洪范。箕子曰,天锡禹洪范九畴,……洪范于儒家众说,范围而不过,实自禹起。盛若仲尼,而曰:禹,吾无间然矣。王制至禹始备。儒者称先王,大抵自禹以下。”禹生石纽,蜀人也(禹的出生地有多种说法,石纽在四川,谢无量主此说)。其次,儒学“最古经典”亦“蜀人所传”:“儒家尊六艺曰经,经莫大于易。”古有“三易”。“《连山》,蜀人所作,已灭不见”,《归藏》、《周易》能“不坠于地”,亦“唯蜀人之功”。
道家亦“蜀人所创,其变有三宗,三宗亦自蜀始。”所谓“三宗”,一是“原始之道”:“《道藏》数千卷,首著《度人经》,以为峨嵋天真皇人授黄帝云。……故天真皇人,道家之祖。”同时属于此宗者有青城山宁封,继起有老子。据宋谢显道《混元本纪》,老子出自成都李氏,“今成都青羊宫是其遗迹。”二是“养生之道”,创自彭祖。三是“符咒之道”,创自张道陵,“道陵非蜀人,然得道在蜀,终于蜀”,亦蜀学也。重要的是,“司马谈论六家指要,独尊道家。中国诸学,惟道家先出”。故云“蜀有学先于中国”。
佛教本“异邦之学”,自汉传入中国,“其时蜀与西域比壤,至西域必道蜀,亦自蜀以达于中国”,蜀地自然得其先机:“刘蜀尝出《楞严》、《普曜》诸经;”隋费长房、僧琨、智炫、慧影等“并翻译经典,论述玄谛,蔚乎如林,”俱蜀人也,惟无创造,“不名宗祖”。至什邡马祖道一创临济宗,华严第五祖圭峰禅师,西充人,“讲道阐玄,贤首教宗,由是而大。于《华严》、《圆觉》诸经皆有疏说,圆澈通辨,他家不及。终唐之世,华严宗行于蜀,宋初蜀僧游江南,其传始东”。
文章本“惟蜀士独盛”,仅以创造论,其贡献有四大端:其一为“南音”,本是“离骚所出”,创自涂山氏。二是“赋”。“汉志录赋实首屈原,原所生即今巫山地。”三是“古文”,系由陈子昂首倡“复兴”者。四是词曲,创自李白。
中国学术思想本以儒、释、道为三大宗,文章则载道之器,而儒、道均由蜀人创始,文章、佛教亦有独到贡献,这样,蜀学真可谓“大哉”:“蜀学所由称,何独尧尧然!”不过,使谢无量感到不快的是,蜀学在学术史上并未得到应有的地位:“余览百家说、蜀史记,不知涕之无从也。夫蜀有循蜚、因提、钜灵、蜀山,在五帝前,治迹章矣,司马迁略而不载。黄帝之孙青阳玄嚣之裔,往往在蜀。神圣之都,学术先兴,如太阳生于东方,自然然也。蜀之于中国,其犹埃及之于欧洲乎?欧洲学术均出于埃及。中国无蜀则无学,蜀何尝籍学于中国?蜀学自秦灭国而衰,至宋世金元之祸,蜀民靡孑遗,古先传之学熸焉遂亡。世但知张献忠残蜀,而不知元人入中国,蜀被祸最惨,虞道园、袁清容、赵东山诸集言之綦详。于今又五百载,承学之士,欲何以明?虽然,仲尼犹云,文武之道,待人而兴。是在吾党勉之尔矣。”谢氏一方面为蜀学争地位,一方面也要振兴蜀人的学术自豪感和进取心,再一次表现出文化焦虑感和自信心交缠在一起的复杂心态,而其关怀也一望可知。
刘咸炘的《蜀学论》开篇即点出主题:“有是主人,蜷伏虫墐,口谈不对于魁士,足不出于一郡,兀然仰屋。有客来问,曰:吾尝历数师儒,旁求篇帙,衡较天下,蜀学尝黜录于《四库》,十不占一。”更以“晚近二百年来学士”为例,“殷赈大河南北,守关洛之朴实;长江东西,驾汉唐之博敏;黔荒晚通,亦绍许尹。……而蜀士闻者才三四人”,且各有疵病:彭端淑“文杂八比之陋习”,张问陶“诗附随园而效颦”,李调元“记丑而不博”,李惺“识隘而不纯”。虽“光绪以来,渐致彬彬”,又“遽遭丧乱,古道湮沦。岂山川阻蔽,化不通而气不伸乎?何其贫也”(21)!则有清蜀学不但比不上江南、河洛,甚且不如贵州。
对此,刘咸炘的回答是:“子徒见今之荒秽,而不闻昔之荟蔚也;徒羡彼之多而沸,而不识此之少而贵也。夫民生异俗,士习成风。扬州性轻则词丽,楚人音哀而骚工。徽歙多商,故文士多密查于考据;常州临水,故经师亦摇荡其情衷。”四川则“介南北之间,折文质之中,抗三方而屹屹,独完气于鸿蒙”。具体而言,其长有四:一为《周易》:“《易》之在蜀,如诗之有唐矣。”二为史学:“史氏家法,至唐而斁。隋前成书,仅存十数,蜀得其二”;有唐之后,更是“史学莫隆于蜀”。三为文学,诗文名家辈出,不绝如缕。四为小学,自扬雄《方言》以下,著作良多。至经学、诸子,蜀人稍差:“若夫经生考典,子部成家,斯则让于他国,不敢饰其所无。”但在理学家中,蜀人如魏了翁、张栻、黄泽、赵贞吉等皆有建树;杨慎说经亦“往往与惠、戴之传合符哉”。此外,“杂流之求”如纵横家、兵家、博物家等等,亦俱有可观,“又岂可以小道轻乎”?总之,“统观蜀学,大在文史”,其治学无门户之见,而有独立之风,“寡戈矛之攻击,无门户之眩眯,非封畛以阿私,诚惧素丝之染紫”。
刘咸炘着力表彰历史上的蜀学,针对的正是蜀中无学的意见,这和谢无量及傅增湘等的关怀是一致的,实际都有一种焦虑感。不过,与谢文比较起来,刘的描述相对客观。如同样论证《易》学在蜀,谢无量直称商瞿成都人,故《周易》之传,端赖蜀人;而刘咸炘就慎重得多:“商瞿北学,尚曰存疑。”又如谢无量把屈原划入蜀人,故云赋创自蜀,而刘咸炘则云:“诗有四系,独缺骚一耳。”他如谢无量以禹创兴儒家,更谓“中国无蜀则无学”,刘咸炘均不道。相反,刘氏坦率地承认,蜀人于说经、子部实不如人。这些差异和两人的学术态度有关,刘咸炘是学者,言必有据,谢无量发言要随便得多。不过,这也意味着刘氏对蜀学的自信更强。事实上,文中那个“蜷伏虫墐”的“主人”,正是作者自况(刘氏足迹终生不出四川一步),而文中所描述的这一“隐士”的形象,也象征了蜀学之衰微是外人不知,非真的不行也。
不过,刘咸炘仍承认蜀学于今已经“荒秽”,故和谢无量一样,主要着力于“昔之荟蔚”,而蒙文通的《议蜀学》一文所谓蜀学乃近代蜀学也,其意在表彰廖平学术。他首先将廖学放在整个清代经学典范转移的背景下界定其意义,肯定廖平指示了一个学术的新方向:“今古之学既明,则孙、黄、胡、曹之礼书为可废……然不有乾嘉诸儒之披荆榛,寻旧诂,以导乎先路,则虽有廖氏,无所致其功。惟廖氏之学既明,则后之学者可以出幽谷,迁乔木。”不过,此文的用意更是欲倡导后起的蜀中学人继承廖平的治学道路,以开创一个新蜀学局面:“廖氏既成《今古学考》,遂欲集多士之力,述八经著述,以成蜀学。夫伊洛当道丧学绝之后,犹能明洙泗之道,绍孟学之流,以诏天下,蜀人尚持其文章杂漫之学以与朔、洛并驱。自顾以迄于今,其道已蔽。吴越巨儒,复已悔其大失,则蜀中之士独不思阐其乡老之术以济道术之穷乎!”[26]178,179既云“欲”成蜀学,则实未成,不过由廖平开了一个头,尚待后学竟其事业。关键是,蜀士并未自觉地担当此责任,这正是蒙文通所焦虑的。
其时对蜀学抱有类似感受的人还不少。吴虞就说:“余常谓蜀学孤微,不仅受南方人士之排抑(正续两《经解》、正续《碑传集》,‘文苑’、‘儒林’,皆不收蜀人),即蜀中士夫,亦未尝有崇拜维持之事。且于一代不数见之人才,淡漠视之,倾陷及之,务使其沈埋困顿而后快!其所标榜者,皆虚伪不学之辈也。而后生之继起者,于前辈为学之本末,用心之深苦,毫无所见,亦复雷同訾謷,予智自雄,意气甚盛,浮薄浅陋,罪过尤甚。余书至此,不能不为蜀学前途悲也。”[6]92比较起来,吴氏对蜀学面临困境的估计比蒙文通更严重。
因此,近代四川学人一方面确已具有了蜀学自觉,这显然是近代四川地方认同的产物,不无自信的成分,但同时又夹杂着焦虑感和危机意识,情绪相当复杂。此后,这两种情绪也一直在四川学者的心中并存。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国内学术风气的转变,四川又一次被归入文化落后地区,连蜀人对此也颇感不满。一位成都大学学生就在1930年指出:“吾蜀僻处边陲,交通梗阻,文化落后,风气不先,教育衰颓,于今极斯。”[44]连并不怎么趋新的学生,也对长期局于四川一隅感到不满足,而思以出夔门以启耳目。萧印堂就说:“余居益部,隘于闻见,久乃有薄游南北之思。”[11]
另一方面,被认为保守的学者对外间的学术风气也甚是不满。庞俊在20年代表示:“自顷世途辀张,民生日蹙,病每变而愈危,药厉试而不验,或有谓巴菽甘遂可帝者,激而行之,异喙加厉,遂乃诡更风雅之体,崇饰鄙倍之辞,横舍小生,乐其汗漫,探喉而出,一日百篇。然而坑谷皆盈,势亦难久。淮南王有言: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沟植生条而不容舟,三月必死。何者?狂生而无其本者也。”[14]28530年代初,赵熙致友人书,亦对当世学风表示不满:“敝处文学舍仍是三家村模范,近来学童少能读《论》、《孟》者,则一切无从说起,稍举唐以来诗,又平仄茫然,世运所驱至此,早知其当然,有不料其果然也。”[22]286-287
对于外间的成名之士,蜀中学人亦多有看不起者。30年代,庞俊评论王国维弟子就说,王学“多本之乾嘉诸儒,高邮王氏,尤所服膺。至于讲堂口述,无取繁词,不复一一,非剿说也。而弟子不知,震而矜之,暖暖姝姝,以为莫非先生之孤诣独造,而伛偻以承之,则多见其固陋而已矣”[14]269。其文中点名者有吴其昌、刘盼遂等。曾在四川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程千帆回忆说:“四川这个地方,一方面外面的人根本不晓得四川的学者有多大的能耐,另一方面,四川的学者还很看不起外面这些人。他看不起自有他值得骄傲的地方。”[45]
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近代以来川中学人自信力的增强。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国内学术风气一新,四川反因其偏僻,相对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国学”成为强项。1928年,刘咸炘提出,今人“好利”,时风趋于“张”,宜矫之以宋学,而浙东史学实宋学之一脉相传。考浙东学派之源,不仅有“中原文献”、“王刘学派”,在此二者之间,“尝受吾蜀二李掌故之传”也。盖五代北方大乱,文士多聚吴、蜀二处,降至有宋,“掌故、文献,蜀人保存之力为多”,甚至可说“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至元兵入川,蜀学南迁于浙,遂成浙东史学,“蜀反如鄙人矣”。然“绍述浙东,正是中兴蜀学,非吾蜀学者之当务乎”?进一步,“吾华汉后文化实在长江二源出于蜀,特蜀山险难通而水湍不蓄,故士多南迁不返,而土著者深而固僻”。在“今西来之风侵削华化”的情况下,“东南人轻浮,随风而靡;西北人则朴鲁,不能兴。且西北文风自汉唐大盛,宋后已衰;东南宋后乃盛,今则盛极将衰”,是均不可赖。惟“吾蜀地介南北之间,民性得文质之中,虽经元明两灾,而文风已渐有兴象。又自东西大通以后,中国南北之大势将变为东西”,蜀地“后负须弥而前距海,山环原野,水如罗纹,亦殊燕豫晋秦之荒漠,后此或将为华化退据之地乎”[46]?
刘氏比较各地文风升降的历史与地理状况后,自信蜀学乃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基地,多少反映了一些四川史家的共识(22)。这一情形和廖平学术随着道咸时期学术典范转移而兴起的状况颇有相似之处,而表面上则恰好相反:道咸时期是蜀学承“新”而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蜀学则在一定程度上因“旧”而获得其地位。
不过,也正因四川学者不怎么与外界交往,再一次造成四川学术在国内的边缘化。庞俊论龚道耕曰:“大抵生平著述,多罔罗众家,刊改漏失,似善化皮鹿门而无其剽窃,似象山陈伯弢而无其庸琐。以僻处西陲,书未刊行,往往为他家所先。”[14]215此正程先生所“谓外面的人根本不晓得四川的学者有多大的能耐”也。
另一方面,虽然大家都提蜀学,而各家心中的所指并不大一致。蒙文通以廖平之学为蜀学,未必为全体蜀中学人同意,倒或可获得外部学者的认同。1943年,金毓黻论当时学人,首推康有为、章太炎,次推王国维、廖平。谓“平以文学之雄而为今文学之经师。其学凡四、五变,年愈老而语愈怪。吾无以名之,可名之曰蜀学。其传授不若王氏之盛,而能绵延不绝,以自张一军”。金氏并于“蜀学”二字下加注云:“廖氏弟子蒙文通曾撰《蜀学考》,以称述廖氏之学。”[44]5275,5278虽有些勉强,但能够列入前四名,已是相当推重了。谢无量与刘咸炘均认为近代蜀学无可观,刘氏且直言蜀人说经非特长,则对廖平恐亦不甚许可。如前所述,二人论蜀学多讲中古以上,所观察有相似的地方,但亦有参差。刘特别表彰的史学,谢便根本不提;谢尤其看重的道教,刘也几未着一字。
1940年代,王恩洋谈及四川文化的特点,又有不同:“四川文化因为别有乡土关系、地域关系,自有其特殊之点。四川的风俗人情,与一般平民特殊的宗教思想信仰,有些是很高级,有些是最低级。”王氏认为,四川文化中“最为发展”的有两方面:“一是文艺,一是宗教。文艺如司马相如、扬雄、三苏等之文,李白、陈子昂等之诗;宗教如在佛教方面、道教方面,四川也出了若干伟大的人物,对于文化都很有贡献,”特别是在“各乡市间”流传的“若干的宗教思想、信仰……或者还够不上为一种宗教思想,也应有一番整理。四川有许多道门,其中影响于人民颇深,其思想比孔孟之书还来得流行,而许多人都得其安慰”[48]。
可知何谓蜀学,正与论者自己的学术文化关怀息息相关。每个人关心的问题不同,甚至写文章时所特别关注的对象不同,笔下的蜀学便有可能不大一样(蒙文通在《议蜀学》中虽以蜀学二字特指廖平经学或廖平心目中所欲达到的经学,但实际也认可刘咸炘所说的史学为蜀人所长),此正所谓见仁见智,不但代表了不同学者对既往蜀学认知的差异,大约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们对蜀学未来走向的规划。
更重要的是,不论大家所说的蜀学有多大差别,关键在于,这一概念广泛使用,表明四川学人正在自觉构建一个带有地域性特点的学术系统。20年代末30年代初,金毓黼热衷于东北地方文献收集整理,曾提出东北学或辽学的概念,欲“以此求异于人,即所以求自立于斯世”[47]2447。近代蜀人揭出蜀学一名,亦可作如是观。这虽然看起来只是几个学者的工作,却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反映出四川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已完成了意识上的“本土化”过程,“四川人”这一新的身份认同被普遍接受,并且进一步希望在全国的视野中寻求地位。同时,正如前面指出的,近代蜀学论的提出,也是晚清以来四川学术大发展的产物。离开这一实在的背景,蜀学也就真成虚构之物了。
五、余论
本文把近代四川学人的蜀学论放在一个稍长时段的地方社会文化史脉络中考察,以突显地方认同在学术文化层面上的表现。但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学者对这一地域性学术的描述,又不仅是地方视野所能涵盖的。王恩洋曾说:“四川是中华民国的一员,我们应将四川文化方面所贡献于全国者如何,其特殊之点在哪里,加以研究,同时加以表彰。”[48]实际上,各类有关蜀学的论述看似都是在强调其“特殊之点”,但背后都有一个全国性背景,重点无一不落在“四川文化方面所贡献于全国者如何”。换言之,只有在全国性学术视野下,蜀学之特殊性才获得了其意义。不过,也正因如此,蜀学亦显得非常脆弱。由于四川地理条件的限制,其为学风气通常与国内主流有异,而论学者又每执主流风气为标准,蜀中学问或有时显得无足称道。关键在于,即使是川内学人,也不能忽视这一大背景,故其虽时时有自信,亦常常有焦虑。另一方面,一旦国内学术风气大变,四川学者也可能乘势而起,后来居上,廖平在清季声誉鹊起,便是一例。但这种影响也是多元的,新文化运动后,四川反以保留传统取胜,则近乎“礼失求诸野”了。
另一个要解释的问题是,尽管学者对蜀学的认知并不一样,但文学与《易》(以及与之关系较密切的宗教)乃是四川学术的长项,却基本上是公认的(另一与道教、《易》有关而学者不常提到的是医。四川医学也自有其传统。廖平晚年以《黄帝内经》遍说群经,留下了大量著作,离开医学,实无从理解其后“三变”。吴之英亦有大量医学著述,都值得重视)。近代四川《易》学似稍衰(但也未必,恐只是“沉沦下寮”而已),而文学艺术仍发达。金毓黻抗战时期入川,见到王缵绪致张群书,谓其“韵味极似东京,不知出何人手笔”。因而感慨道:“今世非无美才,特伏处岩穴不肯出耳。吾华文章之士多出于蜀,亦以蜀士早见于史乘,如司马相如、扬子云其杰出者也。遗风不替,绵绵可接。今之文士,亦当以蜀为雄。岂以山川奇秀使然耶?蜀士如谢无量,以诗以书雄于时;如郭沫若,其学亦杰出;如张大千,以画雄于一世。求之南北各省罕有其匹,讵非明证?”[44]6528
这里和汪国垣、胡先骕的看法一致,实际继承了自《礼记·王制》篇及《汉书·地理志》以来中国人讨论地域文化的一个基本思路。这一观点看似不无“地理决定论”的嫌疑,且听起来也有些“玄妙”,几乎很少得到现代社会科学的认可,但仍应值得认真对待。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大师布罗代尔便特别注重地理、生态一类“不变的历史”对政治这一看起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的深层影响,但布氏的或名作《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实未曾将地理对历史的具体影响讲清楚。就此而言,中国传统从“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的角度解析各地文化风习,恐怕仍是具有启示力的。
这也部分地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前面说过,四川在历史上经过了多次移民,故从某个方面看,今日的四川人与往日的四川人实际相差甚远,其文化亦确有改变。研究历史必须注意到这些变化。但另一方面,各个时代的四川文化面貌又分明呈现出一种不绝如缕的延续性,这也是不可否认的。这种延续性从何而来?至少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首先便是地理的因素。人及其文化都是特定自然环境的产物,同时,尽管四川历史上经过多次移民,但其主体大部分保留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在四川的自然环境和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的情形下,产生类似的文化特色是可能的。
其次,特定的区域历史感对地方文化形态的塑造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本文指出的,近代四川学者由于感到蜀学的衰落而对四川历史和文献加以发掘、研究。这种研究凸显的地方特色无疑既是地方感的一个表现,也进一步强化了地域认同。换言之,人们对历史上四川文化特色的认知,无可避免地参与了对此下四川文化面貌的塑造,成为区域文化延续性的一个重要条件。据云:吴之英“好诵司马相如、扬子云之文,曰:‘吾蜀人,当为蜀文尔。’”[10]78(23)即是地方认同造就学术取向的一个显例(24)。
进一步,这也涉及对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的认识。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注重地理环境对文化的深层影响,直到近代不绝。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还提出,中国现代学术的方向之一就是“分地发展”:中国幅员辽阔,兼有平原、海滨、山谷。“三者之民,各有其特性,自应发育三个体系以上之文明。我国将来政治上各省自治基础确立后,应各就其特性,于学术上择一二种为主干。例如某省人最宜于科学,某省人最宜于文学美术,皆特别注重,求为充量之发展,必如是然后能为本国文化、世界文化作充量之贡献。”[12]80梁氏此处所云是有意的“规划”,一般所指某地之学则是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但他强调地理环境造成民性不同乃至相异的学术文化体系的思路,显然上承《礼记》、《汉书》等而来。上文征引的不少学者的议论中,也倾向于从地理环境的因素解释蜀中文化的特点。
不过,近年来,有一批学者指出,这种区域文化研究的思路忽视了历史因素,带有“本质论”倾向。实际上,所谓某地之学或某地文化的概念本身即是在特定历史进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不是一个“透明”的术语(25)。诚然,过去那种把区域文化总结为几个印象式的“特征”,再将其归结为当地特定地理环境产物的做法确实遮蔽了不少历史面向,显得过于简单和懒惰。“建构论”的批评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力的。不过,后者似乎也过于小视了地理因素的影响力。实际上,地理因素是塑造特定区域文化的一种重要力量,绝不可忽视。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地理因素的认知本身也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这种认知和人们对当地历史的认识(所谓“乡邦文献”之学)一起,塑造着地方认同和区域文化自觉。因此,对于区域文化研究来说,把“建构论”和“地理论”结合起来,恐怕是更可行的方案。
(本文初稿承刘复生、徐亮工教授指正,粟品孝、韦兵、周鼎兄提供了部分资料,谨致谢忱。)
注释:
①详论见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宋代蜀学研究》,巴蜀书社,1997年,第1—6页;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页;粟品孝:《“蜀学”再释》,《蜀学》第3辑,巴蜀书社,2008年,第51—56页;胡昭曦:《蜀学与蜀学研究榷议》,《天府新论》2004年第3期。有关近代蜀学,见刘复生:《表宋风,兴蜀学——刘咸炘重修〈宋史〉简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刘咸炘〈蜀学论〉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
②最近持此看法的研究如Yu Li,"Social Change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nd the Decline of Sichuan's Classical Learning in the Early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June 1998,pp.26-55.
③李燿仙说,廖平平分今、古文,知今知古。梁说“仅限于今文一隅,不免偏低了”(《〈廖平选集〉(上册)内容评介》,《廖平选集》上册,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9页)。
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17—718页。廖平致康有为书亦转引自此。
⑤在一些自居正统的经学家看来,不但四川经学算不得突出,被认为蜀学出处的湘学也不怎么样。章太炎1932年在论述清代经学的地域分布时,仅说“四川、两湖亦有经学家”(见《清代学术之系统》,徐亮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第36页)。显然不甚认可。
⑥钱基博在《四版增订识语》中感谢“致书通殷勤,匡我不逮”者的名单中有王利器,增补廖、吴或王氏提醒乎?然未见原函,此亦猜测而已。
⑦另一位常被提到的是唐甄。实际上,唐氏几乎终身流寓东南,其人虽为蜀人,学不必蜀学也。
⑧关于刘沅,参考周鼎:《刘咸炘学术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第31-44页。
⑨李榕:《问汉学宋学异同得失》,《十三峰书屋全集》,巴蜀书社,1995年,第27页。李氏曾参曾国藩幕,而曾氏固讲究汉宋调和者也。
⑩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2卷,光绪五年二月廿九日(1879年3月21日),岳麓书社,1997年,第755页。但不久,他就改变了看法,屡次抱怨蜀士“失教”,见第834、846、887、1022、1039、1337页。
(11)本段和前段,见山河子弟:《说鹃声》,原刊《鹃声》第1期,收张枬、王忍之编:《辛亥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563、564页。
(12)叶治钧:《发刊词》,原刊《蜀报》第1期,收《辛亥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716页。
(13)钟家源:《清末诗人钟云舫诗谳始末》,《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5页。
(14)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第80页。唐甄实不应算入蜀学。
(15)廖平被参劾事见李伏伽、廖幼平:《经学大师廖平》,四川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等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页。
(16)按此书为赵熙主讲荣县文学社时教材。
(17)粟品孝:《“蜀学”再释》,第54、55页。本段引用蜀学会的文献,俱转自此文。
(18)廖平:《今古学考》,《廖平选集》上册,第89页。自注已删。
(19)岳森:《南学报廖季平第二书》,《癸甲襄校录》,光绪二十年成都尊经书局本。转引自李晓宇:《尊经·疑古·趋新:四川省城尊经书院及其学术嬗变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147页。
(20)本段和以下数段,均见谢无量:《蜀学会叙》,民国时期油印本(具体年月和出版地不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按谢氏另有《蜀学原始论》,系《蜀学会叙》的一部分,收中央文史馆编:《崇文集》,中华书局,1999年。姜莉对这两个本子做了校对。
(21)本段和以下数段,均见刘咸炘:《推十文集·蜀学论》,《推十书》第3册,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2100—2102页。刘氏自注已删。
(22)蒙文通亦提出“蜀学重史”和蜀学为浙东史学源头之一,详见《中国史学史》、《评〈学史散篇〉》,《经史抉原》,第317-322、411页。
(23)按钱氏未明此条论据的出处,估计是“口述史料”。不过,吴之英著有《八总督箴》一文,不管命题还是形式大约都借鉴了蜀人扬雄的《十二州箴》,可为旁证。
(24)另一个例子是前文提到的廖平“以庄周为儒术”。提出此说较早者为苏轼的《庄子祠堂记》:“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转引自周启成:《前言》,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卷前第5页。)无直接证据表明廖平此说袭自苏氏,不过可能性是存在的。
(25)在这方面值得参考的一篇论文是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7—4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