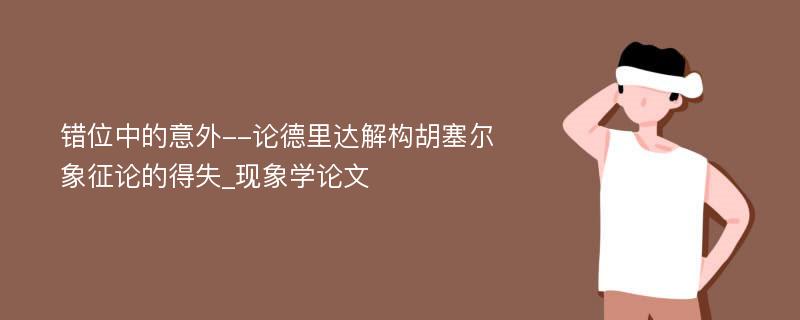
误置中的意外——论德里达解构胡塞尔符号理论之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失论文,符号论文,意外论文,理论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1)05-0031-07
胡塞尔的符号理论主要见于《逻辑研究》和《纯粹现象学通论》,这也是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解读胡塞尔符号理论所依据的主要文本。除此之外,德里达还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胡塞尔的《经验与判断》、《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以及《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等著作。本文的讨论主要限于上述文献。直接发生冲撞的文本是《声音与现象》和《逻辑研究》第二卷中的“第一研究”。《声音与现象》在结构上和行文速度上并没有与“第一研究”保持平行,德里达对“第一研究”中的“第一章”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特别是对其中的第1节和第8节,而对其他各章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这种不平行性导致德里达在胡塞尔符号理论的解读中发生了偏离和错位,这种状况极易给读者造成两种相互冲突的印象:或是成功的“批判改造”[1](P43),或是主观的“轻率任性”[2](P232)。笔者在此尝试了一种互文式的阅读方法,即在《声音与现象》和《逻辑研究》两个视域之间来回穿梭。这种阅读模式呈现出来的结果不是简单的是与否、对与错,它展现给我们的是德里达运用结构策略的得与失的交错性。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既能够目睹两个不同视域的并置、启发和融合,也能发现它们的差异、排斥和对抗。让作者走开,让不同的所指消失,让意义跨越视界,在交流、对话甚至对抗中自行展现自己的轨迹,这或许恰好暗合解构主义的符号学旨趣?
一、声音
声音是德里达使用的核心概念。在《声音与现象》的视域内,声音是传统形而上学自我保护的最重要的武器。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在世界的在场受到质疑并被摧毁之后,正是通过声音,意识的在场才被重新建立起来。在这其中,胡塞尔的现象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发掘了被形而上学历史所包含的声音的必然特权的种种根源并把这种特权推向极致”[3](P18)。这种指责大可值得推敲,姑且不论德里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评价。德里达的“声音”概念只要走进《逻辑研究》的视域,就会呈现出自身的被误置状态。德里达告诉我们,“胡塞尔很快就确定表达……的表达性与口头话语(Rede)有着一种不可还原的关系”,“胡塞尔保留了口头话语对表达的专门权利”。[3](P21)口头话语与其他类型符号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的声响,这也就是说,声音与表达具有一种必然的、排他性的关系。果真如此吗?胡塞尔“反驳”说,“我们所说的表述显然不是指……声音构成物”[4](P44),他还进一步对表述作了一般性的区分,指出表述的物理方面包括“感性符号、被发出的一组声音、纸张上文字符号以及其他等等”[4](P44)。很明显,对表达享有权利的不仅有声音,还有文字、感性符号等其他许多方面。诚然,胡塞尔的确说过,“言语声音只能被称作表达”[5](P302)。但他紧接着又指出,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言语声音本身,而是“因为属于它的意义在表达着”。胡塞尔晚年甚至将“口头方式”(muendlich)与缺乏“精确规定”相联系[6](P220),我们知道,精确的、单义的规定恰恰是胡塞尔符号理论的理想之所在。
在谈到“Bedeutung(意谓)”和“Sinn(含义)”的区别时,德里达断言:“Bedeutung被保留在口头表达和口头话语的理想的意义的内容之中,而Sinn则遍及整个意向相关项的范围直至它的非表达层次。”(注: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22页。引文根据德译本"Die Stimme und dasPhaenomen"(J.Hoerisch 译,Suhrkamp Verlag,1979年版,以下简称德译本)略有改动。)出于这个理由,他将"hedeuten"翻译为法文的"vouloir-dire"(想说)[3](P22)。胡塞尔的确区分过"Bedeutung"和"Sinn"的用法,但准确地讲,胡塞尔认为,"Sinn"泛指一切意向体验,而"Bedeutung"仍被局限于语言的、逻辑的、表达的范围之内[5](P302)。很明显,同样一个"Bedeutung",德里达强调的是它的口头表达性,而胡塞尔则明确指认它应局限在语言的范围之内。
为了进一步提高声音在胡塞尔现象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德里达在作了上述判断之后又指出,“意义只有借助于声音……才能够在自身中保持自身”[7](P85)。不论德里达怎样描述声音,他的意思始终是:声音一定属于口头话语(这也是德里达为什么将口头话语与"Bedeutung"绑在一起的缘故),即使它不发出声响。但胡塞尔精心构思的一个案例却将语词——即使是被想象的声音语词和被想象的印刷文字——逐出纯粹表达和意义的体系之外:“在孤独的话语中我们并不需要真实的语词,而只需要表象就够了……这里存在着的不是被想象的语词声音或者被想象的印刷文字……因为对于作为表述的表述功能来说,语词的存在与否无关紧要。”[4](P38)在胡塞尔看来,声音固然可以使意义“在自身中保持自身”,但印刷文字和表象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虽然这一案例后来遭到德里达的严厉批判(我们马上就会谈到这一点),但这丝毫无损于此处的证明。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德里达将自己关于声音的“前见”楔入胡塞尔现象学符号理论的结构中,这种误置不仅使胡塞尔符号理论发生畸变,也影响到他对胡塞尔著作的理解。难怪他“奇怪”于为什么胡塞尔“从来没有把书写的问题置于他的思考的中心,也没有在《几何学的起源》中分析过发音书写和非发音书写之间的区别”[3](P103)。他的“奇怪”不无道理:像胡塞尔这样一位严谨、细腻、全面的现象学分析天才,如果他把声音置于他的思考的中心,那么在他的体系中绝不会找不到对“声音”与“书写”、“发音书写”与“非发音书写”之间差异的现象学描述。
德里达对此也似有所悟。他小心翼翼地对“声音”作了限制性的描述(注: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18页。据德译本略有改动。):它不是世界中任何实体的声音,它是先验性肉体中发出的声音、气流,是一种把躯体(Koerper)改造为身体(Leib)、改造为一种精神性身体(geistige Leiblichkeit)的灵魂赋予(Beseelung)。从德里达所使用的词汇"Koerper、Leib、Beseelung"来看,他所理解的“声音”概念应该属于现象学的“立义”范畴。胡塞尔的“立义”是指意识活动“赋予一堆杂多的感觉材料(立义内容)以一个意义,从而把它们统摄为一个意识对象,……胡塞尔在这个意义上也把这种立义的过程称为‘赋予灵魂’(beseelen)或激活的过程”[8](P60)。如此一来,“声音”便成了意向活动的同义词。实际上,德里达后来也承认,“声音是意识”[3](P101)。如果德里达所说的“声音”就是意识、意识的意向活动,那么首先遭到解构的正是德里达自己精心炮制的声音的话语空间,因为胡塞尔从来都没有隐瞒或掩盖过意向活动在其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他甚至将意识行为所具有的活动功能问题看作是现象学“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8](P314)。
二、表达
胡塞尔在“第一研究”第8节中精心建构了一种现象学处境[4](PP37-39):在孤独的心灵生活中,表达可以以一种自言自语的形式,但这种自言自语并不是自己把自己设想为他者进行传诉(Kundgabe)和告知(Kundnahme),这里的表达绝非指号,它是一种纯粹的表达,因为我所意谓的正是我此刻所体验到的。
德里达对这一论点的解构非常成功[3](P61)。他从胡塞尔的“观念性”(Idealitaet)概念得到启发,发现了符号的原始结构在于它的可重复性(注:准确地说,德里达的“可重复性”思想也是受到胡塞尔影响的结果。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谈到观念的“重复”(Wiederholung)以及“重复链”(Wiederholungskette)。值得注意的是,《几何学的起源》虽发表在《逻辑研究》之后,但德里达却是先研究《几何学的起源》的。)。胡塞尔的“自言自语”究竟是一种纯粹的表达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符号、与一般交流意义上的符号完全一致的符号?孤独的个人在体验中发生的表象和经验统一性既不可被他人替代又不可自身逆转,它只是一个“只此一次”发生的事件,而“自言自语”却是可以无限重复的。因此,它的使用一定合乎符号的一般结构。如此一来,话语的实在性和代现性之间、外在性和内在性之间的区别就被彻底解构了,这种解构的效应还波及到真实的话语与想象的话语之间、代现和想象之间甚至是表达和指号之间的差异。德里达的解构是成功的,在此我们能体会到他的解构策略的巨大威力。
但是,德里达似乎过高地估计了这种成功的价值:“如果理想的或绝对‘本己的’主体性的孤独仍然需要指号以构成它与自我的固有关系的话,那么进行本质区分的第一章中所阐述的有关意义的全部理论就会被推翻。”(注: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52-53页。引文据德译本略有改动。)两种视域的错置在此鲜明地表现出来。对“第一研究”第8节的批判构成《声音与现象》的核心内容,但对“第一研究”而言,整个第8节在论述结构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即使在第一章中,第8节也不显赫。第一章的主旨是要论证表达的本质是含义,虽然在流俗的用法中,表达与指号、表情、手势、声音、文字、心理体验、对象等等交织在一起。第8节应是现象学还原方法之——“想象的自由变更方法”——的运用,胡塞尔试图通过这个精心构思的案例让我们明见地看到:即使在孤独的心灵生活中,表达也一如在交往中仍然以含义为本质。关于这一点,胡塞尔在该节一开始就已指出:“我们至今为止所考察的都是在交往功能中的表述……但是,即使在交流而不告知的心灵生活中……这个功能的变化也不会改变表述的本质。”[4](P37)我们可以这样设问:如果去掉第8节,会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论证的过程和结果?
胡塞尔在第8节中确实提到表达的含义与孤独个人的体验内容的理想的一致性问题,这一点被德里达归结为表达的纯粹性问题。如果仅仅从《声音与现象》的视界出发(注:国内有些学者单纯从德里达的视界出发,自然得出相同的结论:“声音现象学把有声的能指(事实语言)还原为独白,再还原为意识。”(尚杰:《德里达》,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我们可能会以为,胡塞尔是在企图建构表达的纯粹性、表达与体验在孤独的心灵生活中的完美统一性:“在‘孤独的心灵生活中’,如此这般的表达的纯粹统一性似乎终于对我建立起来。”[3](P52)但对胡塞尔的进一步研究清楚地表明,他并不关注主观体验、对象直观和含义充实这些与表达不具有本质关系的范畴:“表达与一个现时被给予的、充实着它的含义意向的对象性的关系并不是本质性的关系。”[4](P51)德里达的解构虽然是成功的,但并没有因此而“推翻”“第一章中所阐述的有关意义的全部理论”。
三、时间
胡塞尔在第8节的结尾处说,在自言自语时,语词不以指号的功能服务于我们,“因为这种指示在这里毫无意义。我们自己就在同一时刻里体验着这些行为”。德里达敏锐地意识到这句话的逻辑漏洞,在《声音与现象》接下来的一章(即第五章)中他运用胡塞尔的时间理论对“同一时刻”进行解构。他试图从胡塞尔的“孤独的心灵生活”的现象学个案出发,总结出胡塞尔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思想:听觉相对于视觉和触觉更能保持自身的纯粹性和理想性,即与自身在场更为接近。自我注视和自我触摸(das Sich-Selbst-beruehren)仍然会碰到作为外在性和异在性而在空间中自我陈列的我的身体,而“自白自听”(sich-sprechen-hoeren)似乎已被还原到身体的内在层面,在这里能指和所指绝对接近,自身完全透明。德里达将这种“自白自听”现象称为声音的“自身触发”(selbst-affeKtion)(注:德里达:《声音与现象》德译本第136页。"affektion"目前国内至少有三种译法:杜小真女士在《声音与现象》中译为“(自我)影响”;邓晓芒、张廷国先生在《经验与判断》中译为“情绪”;倪梁康先生在《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中定名为“触发”。第三种译名似更贴切。)。解构所谓的声音的“自身触发”性是解构在场形而上学的关键步骤,而“自身触发”正是一种时间化的运动,因此引入时间分析乃势所必然。
胡塞尔关于内时间意识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1)感知从当下瞬间的意向(Intention)开始;(2)但如果没有滞留(Retention)和前摄(Protention),感知无从显现;(3)因为纯粹当下的感知(印象)是某种“抽象的、能够就其自身来说是虚无的东西”[9](P42);(4)从任意一点出发,每一随后的点都是其先前点的滞留,在滞留中“隐藏着某种改动”[9](P64);(5)但是在滞留中又保持着“绝对的未改动因素。它是……指向直观意向的直观”。
德里达承认并借用了胡塞尔的观点(2)、(3)和(4)以反驳胡塞尔的观点(1)和(5)。他论证道,从现象学的严格性角度看,“滞留”不具有绝对的原初性和当下性,它与“再造”(Reproduktion)和“次级回忆”之间并无根本不同,但同时根据胡塞尔的观点(2),“滞留”又是当下显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这就足以得出结论:重复、印迹(trace)和延异(différance)不仅寓居于“当下”之中,而且构成了“当下”的纯粹现时性的可能性。[3](PP83-85)作为原始印象的当下在场的自我同一性遭到解构。
这里有两点需要提请注意:第一,德里达与胡塞尔争论的焦点在于,“滞留”的性质是属于作为时间、连续性、同一性的“现前”和“当下”,还是属于作为空间、非连续性、非同一性的“另一个”。从哲学史的角度讲,这至今仍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充满争议的问题。不过笔者认为,一种辩证的表达可能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即“滞留”是同一中的非同一,但是双方可能会各执一词,或偏重于“同一”或执著于“非同一”。第二,即使德里达在这点上完全正确,推翻了当下在场的自我同一性,也并不能解构“第一研究”的理论体系,它解构的只是声音“自身触发”的可能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表达与自身的纯粹同一性的可能性。如前文所述,这一点并不构成“第一研究”的核心论据。
尽管如此,德里达对“滞留”的非同质性的坚持竟出人意表地给我们展现了一种新的解构学的景观:由于延异的运动,直观的主体和被直观的对象的在场双双被无限地推迟。(注:德里达似乎忽略了胡塞尔的一个与自己只有一步之遥的观点:“任意点都是起点,任何给定点最终都是由许多无限的增加物的一个点所产生。”(《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第104页)当然,这一步是胡塞尔所不愿意迈出的。)
四、直观主体
让我们回到德里达的视界中来:“直观的不在场——即直观主体的不在场——不仅仅是被话语所容忍的,只要人们在它自身中考察它,它就是一般意义的结构所要求的。它完全是被要求的:主体的整体不在场和一个被表述对象的不在场——作家的死亡或(和)他能够描述的对象的消失——并不阻碍‘意谓’的行文。相反,这种可能性使得‘意谓’本身诞生,使人们听见它并使人们去读它。”(注: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117-118页。引文据德译本略有改动。)主体死了,被表述的对象逃离了在场,剩下的只是意义的衍生之链,“它把各种当下化互相连接起来,无始无终”[3](P132)。
德里达是怎样得出上述结论的?这些结论与胡塞尔有什么关系?德里达明确承认他的结论来源于胡塞尔,他与胡塞尔有着同样的前提。让我们再次进入胡塞尔的视界。胡塞尔运用严谨的现象学描述在符号学领域已取得两个极富启发性的成果。第一,将对象充实和含义充实排斥在表述的本质之外。他认为,“对于一个表述来说,与一个现时被给予的、充实着它的含义意向的对象性的关系并不是本质性的关系”[4](P51),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指出,充实着含义意向的行为(简称为含义充实)“对于表述来说”是“非本质的”[4](P40)。构成表述的本质是含义、含义意向甚至是直观空乏的含义意向。胡塞尔的这一研究成果突破了传统的符号理论和古典想象心理学的藩篱,在“对象缺失”(Gegenstandslosigkeit)和“含义缺失”(Bedeutunglosigkeit)之间建立了明确的区分,比较好地解决了像“圆的四方形”、“金山”之类的表达有含义却没有被表达或被想象的对象的难题。[4](P55)第二,主观表达被客观表达代替的无限延期性。客观的表达(比如理论表达)是最理想的,它的含义能够等值地、同一地在各主体之间或同一主体内部传递,“在这个同一的含义中,我们始终无法发现任何判断和判断者的痕迹”[4](P45)。主体的地位在此无足轻重,但主体在主观表述中却顽强地生存着,像人称代词“我”、指示代词“这里”、“那里”、“下面”、定冠词以及关于感知、信念、思考、希望等等方面的表述都强烈地暗示着主体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比如说,对人称代词“我”的理解离开对主体自身的直接直观便是不可思议的。即便如此,胡塞尔仍然没有放弃他的客观性表达的理想:“从理想上说,在同一地坚持其暂时具有的含义意向的情况下,每一个主观表达都可以通过客观表达来代替”,但同时他也承认,“这个理想离我们还无限地遥远”[4](P94)。
胡塞尔从“对象缺失”和“含义缺失”的划分出发,成功地驱逐了“对象”,但对是否要排除主体却显得犹豫不决。一方面,从纯粹的理想性出发,胡塞尔觉得应从主观表达中驱除主体,另一方面,“为了确定含义区别、明见地强调多义性……为了明察那些仅仅通过对含义分析而产生的认识”[4](P74),胡塞尔又认为必须回溯到相应的直观中去并加以应用。毫无疑问,保留了直观就是挽留了主体。
德里达正是在这一点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针锋相对地宣判了直观主体的不在场(死亡)。《声音与现象》的研究视域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两个这样宣判的依据。
其一,对主体直观的理解。当下的瞬间直观包含着延异运动,主体的理想直观、绝对的自身在场由于这一运动而被无限推迟(这一点前文已作过说明)。
其二,对主体的主体性的理解(以人称代词“我”为例)。当胡塞尔把人称代词“我”规定为一种在含义上不断更新、在指称上不断变化的符号时,他便陷入了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只好“回溯”到直观上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含义的有根基性:“在孤独的话语中,‘我’的含义本质上是在对本己人格的直接直观中完成的。”[4](P87)但是,根据胡塞尔在“对象缺失”和“含义缺失”之间所作出的区分,作为含义充实的对象性的“我”的缺失(Gegenstandslosigkeit)并不导致“我”的含义缺失(Bedeutunglosikeit),“我”的指称的每一次变化也不会引起“我”的含义的不断更新,否则,客观表述代替主观表述就是一种绝对的不可能性。胡塞尔的“回溯”已经与他自己的现象学符号理论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德里达深刻地反问道:“他难道没有违反他在对象缺失和意义缺失之间确立起来的差异吗?任何意义的话语和理想本性难道不排斥‘一种总是更新的意义’这种说法吗?”(注: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121页。引文据德译本略有改动。)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在话语中的地位,德里达还特意构造了一个“知觉陈述”的案例[2](P117):我从窗户向外看到某个人,就在这同一时刻我说“我凭窗看见这个人”。这个表述是理想的、统一的、主体在场的,但这句话要想在“被听见”时得到理解,恰恰要丧失“我”的知觉、直观和在场直至“我”本身。表达中被理解的是含义而非各种形式的直观和在场。
借助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符号理论的前提,德里达完成了对主体在场的解构,宣判了直观主体的死亡。(注:需要指出的是,德里达所否定的只是作为孤独个体的主体——作者的存在,他仍然保留了“主体”的概念,但这一概念指向的是一种关系和功能而非传统哲学的实体性主体。关于这一点,可参见:J.Derrida,Writing and Différance,transl.by:Alan Bass,the university ofChicago,1989,pp226-227.)
事情有时竟然是这样:收获在意料之外,《声音与现象》便是如此。德里达着力加以解构的“声音”对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而言竟是一个误置(注:国内学者钱捷先生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对此作了一定的思考,但遗憾的是,他得出了折衷主义的结论(参见钱捷的“‘Vouloir-dire’:创意还是误读?”,《哲学研究》,1998年第2期)。),但在我们怀疑这本书的价值之前,我们又发现它在符号的原始结构以及符号的时间运动方面给我们呈现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景观。对直观主体的解构更是意料之外的收获,是对胡塞尔意义理论的实质性突破,也是这本书的真正成就。含义从此摆脱直观主体和对象的纠缠;话语成为自由的嬉戏;文字穿梭于观念性、真理、直观和世界、经验、对象之间,它比直观更古老,它比真理更悠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