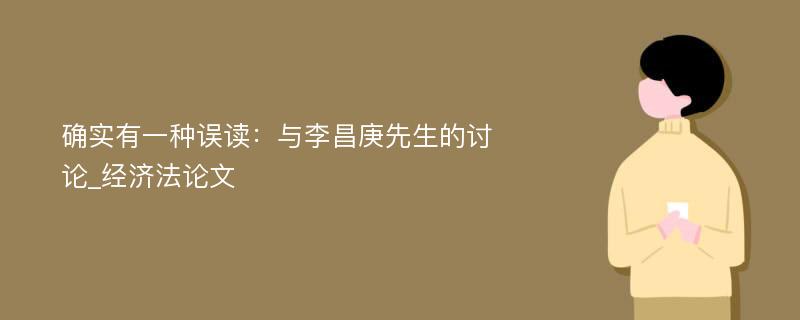
确实发生了误读——与李昌庚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读论文,发生了论文,确实论文,李昌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提示』陈云良在《转轨经济法学:西方范式与中国现实之抉择》(《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本刊2006年第10期全文转载)一文中,提出了“转轨经济法”的命题,认为“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轨时期,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法理论不能解读转轨中国的现实问题,西方范式不适应中国国情”。同时,刘光华在《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反垄断法——我们如何来破题?》(《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本刊2006年第12期全文转载)一文中也阐述了近似观点,提出“任何有效的法律制度都是‘内生’于自己的社会与法律机体而不是‘外植’自异己的社会环境”。其后,李昌庚在《转轨经济法:一个容易误读的概念——兼与陈云良先生等人商榷》(《求索》2007年第6期)一文中对“转轨经济法”这一命题的合理性进行反驳。这一话题争鸣并未停止。今年,双方又再次发文进行反驳论证,本刊摘取其中部分,以飨读者。
李文(指李昌庚《转轨经济法:一个容易误读的概念——兼与陈云良先生等人商榷》一文,下同)误读了“转轨经济法”提出的真正意图,并认为不宜使用“转轨经济法学”或类似观点是迁就中国国情的产物和中庸之道的体现。李文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担心又是多余的。我国目前的体制转轨是有目共睹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是现实的。“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政府的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仍然太多,在转轨时期,中国的经济关系与政府职能都呈现出过渡性的特点,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法的过渡性。”陈文(指陈云良《转轨经济法学:西方范式与中国现实之抉择》一文,下同)也认为:“自由市场还远远没有形成,还是政府管制‘襁褓’中的婴儿,发达市场呈现的各种缺陷还未成为现实的社会问题”,因此要“更进一步开放市场、培育市场”,“而政府体制改革可以说在加入WTO后才真正开始,转轨远未完成,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清晰、国家的调节权力和市场监管权力缺乏清楚的界定等公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显而易见,转轨经济法的内在逻辑处处折射出改变中国现实市场不完善的状况、构建科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约束政府在市场领域权力的改革进取的精神,但在李文看来,却是“过分迁就中国的国情”,硬是把“中庸之道”的帽子扣到“转轨经济法”的头上。提出“转轨经济法”并非是在经济法理论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横插一个阶段,而是为了消解中国经济法学的范式危机,明确转轨时期中国经济法的特殊使命——培育完善的市场、约束政府的权力、构建法治社会,使经济法乃至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更有用武之地。在目前我国法制建设不完善,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今天,而仍然“执着”于李文中所谓的经济法的“前瞻性作用”,不“穷则思变”,则恰恰是“故步自封”,是“过分迁就中国现实”的“中庸之道”。“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合理路径应当是‘计划经济法——转轨经济法——市场经济法’,但当下的经济法学过早地跳到市场经济法这一阶段,绕开了‘转轨经济法’这一段必经之路,从而走了一段弯路。”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出现了市场失灵的充分发达的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市场经济。但是,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之前,根本就没有市场,更谈不上自由竞争的市场,国家对社会经济各个领域进行统制。我们是逐步通过控制、压缩、约束政府的公权力来开放市场而建立市场经济的。中国目前与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经济基础根本不一样,西方是要消除市场充分发展后出现的市场障碍,而中国是要建立充分发达的市场。一个是规制已经成熟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构建与完善目前还没有的充分竞争是市场经济。这样,我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经济法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就出现了问题,成了空中楼阁。为了市场经济法更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就需要一定的变通,培育和建立经济法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所以,陈文提出了“转轨经济法”这个命题,使我国的市场经济法更好地、更充分地发挥作用,以期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消解经济法学在中国的范式危机。
李文认为:“对于后发性的市场不充分国家而言,经济法的价值导向性功能、前瞻性作用和事先的防范与控制作用比弥补市场失灵更为重要。”诚然,同其他部门法一样,经济法也具有价值导向和前瞻性作用,在构建我国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当然会顾及到经济法实施过程中的漏洞和不足,照顾到经济法的价值导向功能、前瞻性作用和预先防范与控制作用。但是,一味强调经济法的价值导向和前瞻性作用,只会使我们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反观中国经济法,它已经局限在西方的法学图景下,把西方的问题当成中国自己的问题,它的理论预设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得很充分了,而根本不是去有意地培育完善的市场。拿经济法的价值导向的作用来否认构建市场经济的紧迫性,从根本上忽视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建立市场经济。
李文认为,从法律功能的角度来看,理应由民商法而不是经济法来培育与发展市场经济。值得说明的是,“转轨经济法”这一命题的提出从来也没有说过培育市场可以没有民商法,从来也没有指出要放弃与其他部门法的合作。西方民商法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市场的温床孕育了民商法,而不是民商法培育和构建市场经济。而我国则是由完全没有自由市场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这样民商法没有其产生的基础。而中国经济法是民商法缺位下发展起来,其产生并非为弥补民商法不足,而是与民商法同生同荣同发展。在认识到民商法和经济法各自的作用和不足的同时,应该秉承民商法的个体本位、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构建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
李文认为经济法的授权功能并不否定其控权功能,认为“转轨经济法学”有混淆了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功能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嫌疑。这是值得反思的。首先,经济法本质上是授权法,但我国目前经济法的根本任务是控权。我们承认西方经济法是授权法,但中国经济法在目前更应该是控权法,我们不应该因为西方经济法本质的授权性质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也是当前中国经济法的本质。我们也不否认现有的经济法具有授权功能和控权功能,我们只是认为现有的经济法侧重于授权,而在我国市场发展很不充分的情况、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更紧要的任务是控权。市场经济法是在授权过程中对权力进行控制的,它对政府固有的权力无涉,而“转轨经济法”则更偏重于归还市场应有的权利、帮市场要回市场自己应有的权利,把政府手中本属于市场的权利削减出去,使政府减负,权力减少,并对原先政府已有的权力进行有效的规制。这便是“转轨经济法”所谓控权的实质所在。
我们并没有否定行政法在对政府权力进行规范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在规范政府权力的过程中,仅仅只有行政法是不够的。行政法更多关注政府权力行使的程序合法性,它对政府固有的权力无涉。国家行政管理与国家经济调节的内容和深度不一样,行政法难以顾及它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所蕴含的市场机制和财产内容,一般行政管理则涉及的经济领域程度比较浅,所以在社会经济领域限制规范政府的权力则应该主要靠经济法而不是行政法。经济法的功能定位是消除市场障碍,弥补市场失灵,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发展。而行政法的功能定位是通过对行政权进行控制、制约和规范政府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力,实现人们的社会广泛领域内特别是政治领域内的权利。我们不否认行政法的控权功能定位,也没有在控权问题上完全排除行政法的作用,我们只是认为“转轨经济法”的提出能够更有效的解决对社会经济领域对政府权力进行更有效控制这个问题。“转轨经济法”只是与行政法在不同的理念指导下,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入手解决社会经济领域政府权力过大这个问题。
摘自《时代法学》(长沙),2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