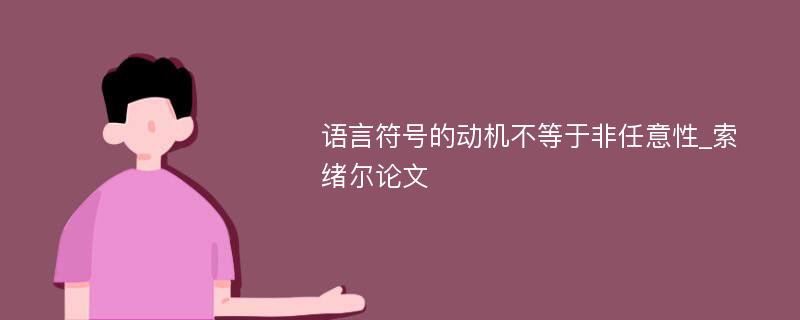
语言符号的理据性不等于非任意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等于论文,符号论文,语言论文,理据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索绪尔语言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而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被索绪尔称作语言学第一原则,“支配着全部语言学”[1∶68]。然而近年来,索绪尔任意性学说尤其在国内语言学界饱受质疑:很多人认为语言符号大多有理据,可论证,于是宣称任意性原则形同虚设,索绪尔夸大了任意性的作用。这些见解概括起来包括(1)语言符号大多是可论证(或有理据)的,因此任意性原则不成立(如[2])。(2)语言符号只在产生之初是任意性的,如许国璋先生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任意的,部落时期是约定俗成的,文明时期是立意的。如果说语言有任意性的话,那么也只是限于原始时期,在此以后就不是任意的了。”[3:32]换言之,只有在符号创制之处,与概念相对应的一刹那,任意性才是首要真理;一旦成为社会事实,任意性就无足轻重了[4]。(3)很多人承认任意性,但只限于单语素符号或根词(如[5])。(4)任意性指语言符号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如王德春先生说:“我们说语言符号与所表客体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应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索绪尔的任意说。”[6]
导致这些认识的原因,一方面是人们把理据性当成任意性的对立范畴,非此即彼,没有上升到语言哲学高度来审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本质,拘泥于字面表述,因此没有真正领悟索氏任意性学说。另一方面,人们对索氏学说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然而该书在内容和表述上都存在一定不足。索绪尔先后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1907、1908-1909、1910-1911)、但每次讲课内容都有所不同。由于他留下的讲课笔记很少,其同事Bally和Seehehaye未听过他讲课,只好根据学生听课笔记于1916年编辑出版这部著作。卡勒指出,书中存在误读,编者加进了自己的思想,尤其是关于任意性概念的讨论没有学生听课笔记翔实[7∶17],因此《教程》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准确反映索氏语言学思想。
关于任意性和理据性,国内外语言学界已有很多探讨和论述,如岑运强、李海荣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索氏任意性研究作了评介[8],但对二者本质差异的探讨仍显不足。我们发现对理据性的误读以及不准确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任意性的正确认识。本文根据《教程》和《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期讲稿1910-1911》(1993)(以下简称《第三期》),并参照某些学者的论述,主要针对“任意性=无理据性”或“理据性=非任意性”的观点,来解读任意性和理据性,旨在消除误解,还索氏语言符号任意性学说的原本面目。
二、任意性
人们普遍认可语言符号是二元结构体,但究竟是哪两个成分,说法不一。索绪尔之前的命名论把语言简单地视为命名过程:语言符号联结的是事物和名称。这种观点认为语言是词语的堆积,词语代表事物,语言符号与客观事物一一对应,即symbols=things。正如张绍杰所阐释,索绪尔认为语词在语言系统内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语言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9∶69],索绪尔在批判命名论的基础上阐述了任意性学说[1∶65-70]。他把语言符号定义为声音形象和概念的二元结合体,音响形象即能指,概念为所指。他强调,音响形象与声音是不同概念,它不是纯物质的东西,而是这个声音的心理印记,即声音作用于感官所留下的印象;音响形象是感知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称为“物质”。因此索绪尔将语言符号概括为双面心理实体[1∶66]。他把语言符号比作一张纸:正面是思想,反面是声音,正反两面无法拆开[1∶113]。能指和所指彼此相互区分,又相互依存。
索绪尔指出,所指是概念,而不是现实。该论断表明,语言并非直接指称现实,即不直接反映现实,因此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可能有必然联系。如法语“姐妹”的意义与其能指s-o-r这串音没有内在联系,也可用不同声音形式来表示,不同语言用不同声音形式表示同一概念也证实了这一点[1∶67-68]。申丹指出,索氏任意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的任意性:(1)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2)所指之间关系是任意的,即语言对概念的切分是任意的,不同语言对概念的切分也不尽相同;(3)某个能指和某个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10]。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任意性本质是无可争议的。该原则支配着全部语言学,它引起的后果是无数的。这些后果不是一眼就能看清的;人们只有在经过一些曲折后才能发现它们,并看清该原则之重要[1∶67-68]。该论断可阐释为:(1)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本质是不争的事实,并深信不疑。(2)任意性原则是索氏语言学及现代语言学的基石。任意性原则贯穿其整个语言学理论系统,包括言语和语言、组合和聚合、可变性和不变性、历时和共时、语言的价值、约定俗成性等概念。(3)索绪尔指出,该原则并非显而易见,人们需付出很大代价才能认识到它的重要。他不愧为大师,今天围绕任意性的讨论,尽在他预料之中;人们短时间内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人不会轻易真正领悟索氏任意性论断的价值和作用。卡勒认为该原则所引起的后果包括语言与言语、历时与共时等[7∶29-52]。
语言是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二者的关系是任意的,因此语言符号的价值不依赖其声音的物质属性,而是取决于它在系统中与其它符号的关系[1∶111-115]。符号与所指称的事物没有因果关系,其意义源自符号之间的差异。对符号的解释依赖符号系统,而不是客观世界。此外,任意性确保语言符号的稳定:因为语言是任意性符号系统,缺乏讨论的必要基础;没有理由认为soeur比sister更好[1∶73]。
索绪尔在谈到语言的价值时强调语言切分思想;离开语言,思想是模糊一片,呈浮游状;语言出现之前,不存在概念;语言起到连接思想和声音的纽带作用;某个概念附在某个声音上没有必要的理由,完全是任意的[1∶111-112]。因此,不同语言对概念的切分不尽相同,如汉语“看”的概念相当于英语的see、think等。符号无论是单语素的还是复合的,都是声音对概念切分的结果;声音和概念的结合本质上都是任意的,不存在自然的联系。如汉语的“机器人”是复合符号,而英语的robot则是单语素的。卡勒解释道,所指和能指结合可以采用任何形式;由于二者之间关系是任意的,那么就不存在固定的概念或能指,因此它们都是任意性的,是表示关系或差异的实体[7∶19-23]。
索绪尔论述了任意性与约定俗成性、拟声词和感叹词的关系,这表明他对任意性的阐述十分严谨。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是对立统一关系;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本质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个人可以随意选择能指,因为有社会和历史继承因素。能指与所指关系一旦确立,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稳定[1∶69-71;76-77]。社会中使用的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建立在集体行为基础上,即习俗[1∶68]。如玫瑰花用其它名称(能指)来称呼也会照样芳香,但是该名称一经使用,就不可改变。“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荀子《第二十二·正名》)同样说明了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因为有了约定俗成性,所指和能指才能“安定团结,相濡以沫”;同样,因为有了任意性,人们才能摆脱掉命名论思想和语言符号崇拜;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
索绪尔指出,拟声现象虽然可以证明能指的选择并非总是任意的,但拟声词不是语言系统中的有机成分,而且其数量在语言中只占很小部分,因此它不能撼动任意性原则;而且多数拟声词也同样具有任意性,只是它们接近某些声音或对某些声音习惯性模仿,况且各种语言拟声词的差异也证实了任意性的存在,如英语的bow-wow,法语的ouaoua,汉语的“汪汪”等。另外,这些词一旦被引入语言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就同其它词一样经历语音和形态的变化,从而失去原来特点,获得任意性特征[1∶69]。
感叹词被认为是对现实的自然表达。索绪尔认为大多数感叹词可以证明其所指和能指之间没有固定的联系。我们只需比较两种语言就可看出,这样的词语在各种语言中都不尽相同,如与英语ouch!对应的法语aie!(汉语中的“哎呀!”)。索绪尔指出,拟声词和感叹词在语言中居次要地位,而且其象征本源还有争议,因此它们不能动摇任意性原则[1∶69-70]。
三、语言符号的理据性
《教程》只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本质”和“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两节中为了说明任意性才提到理据性,但没给下定义。哈里斯[12]和卡勒[7]在索绪尔语言理论解读中也未特别解释过理据性;关于理据性讨论最多的还是在国内。《教程》关于任意性本质论述中有这样一句:“我的意思是说语言符号是无理据的(unmotivated),也就是任意的:它与所指之间没有自然联系”[1∶69]。此处unmotivated=arbitrary。哈里斯认为索绪尔混淆了任意性和系统性两个概念[12∶132-133]。然而harris《第三期》[11∶76-77]在相关表述中却未提到“理据”。从贯穿始终的任意性论述,我们认为后者更可靠。下面这句亦可证明“unmotivated”是强加给索绪尔的:“语言之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证明能指与所指结合的任意性。‘牛’这个所指的能指在国界的一边是b-o-f而另一边是o-k-s”[1∶68]。
《教程》[1∶133]将语言符号分为根本任意性的和相对有理据的两种,这种表述表明理据性是任意性的对立范畴。就此可推论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能证明语言中大部分符号是有理据的,任意性原则就不能成立。令人欣慰的是,《第三期》[11∶87]的相关表述是:完全无理据和相对有理据,这完全是从理据性角度划分语言符号。这点上,《第三期》更准确反映索氏思想。
从索绪尔关于任意性以及任意性与理据性关系的解释中,我们看出理据是语义形成的道理和语义构成的根据,涉及语言符号的可分析性和自我解释性,它并不涉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motivate的词根mot-本义是“move”;理据还可解释成“语言符号发生、发展的动因”[13]。语言符号都有或曾有理据,因为它们的发生与发展都有其动因,只不过有些理据已经变得模糊或消失了。符号所产生的动因可能是其声音、意义(联想、类比)或形态。《说文解字》可称为汉字理据大全。理据正是这种认识的反映。人们从不同角度认识世界,不同的认识自然反映在语言中。理据反映心理联想、文化差异以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认识的角度和程度不同,理据自然不同。如英语的dandelion(蒲公英)源自法语的dent de lion(即tooth of lion),缘起蒲公英叶子与狮子牙的相像。正如Hoven所述,语言符号具有可分析性,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现实世界具有可分析的关系[14]。
理据揭示语言的机制,具体表现在组合和聚合关系上。横向上,我们可看出语言符号意义产生的原因,如predict中pre-和-dict是共现关系,互相依赖,互为条件。同时,组合体的存在依赖联想关系,即纵向上组合成分处在联想关系之中,pre-和-dict与preview和edict等构成联想关系,又如“酒吧”召唤出“话吧”、“网吧”等。
四、任意性和理据性的区别与联系
索绪尔把任意性区分为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并从理据性角度加以说明,目的是要揭示语言符号任意性本质和语言机制。由于两种任意性都属任意性范畴,有理据并不等于非任意性。任意性和理据性都是语言符号的特征,前者表明音响形象和概念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而后者展示出语言符号的可分析性和可释性。同义词的存在也证明了这一点,如“西红柿”和“番茄”,tomato和love apple。但二者属不同层次范畴,具体区别如下:
(1)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基本属性,具有普遍性,因此任意性原则适用于一切语言。理据是语言符号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因此不同语言符号的理据不尽相同。理据不是绝对的;有些符号理据明显,有些可能变得模糊。因此语言符号可分为有理据和无理据两种。因为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本质特征,理据性不可能等于非任意性。“单语素符号是任意性的,而复合、派生词不是任意性的”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因为一种语言中的单语素符号可能相当于另种语言的复合符号,如fruit和“水果”,我们不能说前者是任意性的,而后者不是。
(2)任意性揭示能指和所指的非自然联系,因此具有客观性,不受人为因素制约。理据性则是主观性和民族性的,它反映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及认识能力、认识角度、构词心理、联想、知识水平、文化传统等。由于文化差异,不同语言符号的理据也不尽相同,如汉语“红茶”的命名是基于沏出的茶水颜色,而英语对应的black tea则表明茶未沏时的颜色。pineapple的理据表明,人们首先认识pine和apple。理据性表明,选择什么声音形象作为某个概念的能指是有道理和根据的。符号的语义结构是可解释的,又如英语的ninety是“9-10”,而法语quatre-vingt-dix(90)的构成是“4-20-10”。由于理据是主观性的概念,语言符号有或无理据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了解。因此我们不能说,无理据的符号是任意性的,而有理据的则是非任意性的。事实上,能指的选择都有其理由、根据或道理,也就是说语言符号大都具有可分析性和可释性。
(3)任意性是较宽泛的范畴,而理据性是具体的范畴。理据性涉及符号语义的形成、演变及词源等信息;它通过组合与聚合两种关系,展示和解释语言符号语义结构。讨论理据性只能在任意性原则下进行;偏离该原则,就不能合理解释诸多语言现象。如interloan和“馆际互借”,尽管理据不同,其能指和所指关系仍然是任意的。因此理据改变不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本质。
(4)任意性与理据性并非对立范畴。这可从语言与现实、思维的关系得到证实。现实在索氏符号概念中并没有一席之地,他强调,所指只是概念,并非所指涉的事物。语言符号联结的是声音形象和概念,而不是名称和事物[1∶66]。索绪尔对语言本质,尤其是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论述表明,语言并不直接反映现实,但却构建现实。是语言切分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依赖语言符号系统,现实与我们的经验彼此不是连贯的。不同语言表达同一概念的理据可能有所差异,即使在同一种语言内表达同一概念的语言符号理据也不尽相同。这正是任意性本质的体现。索绪尔强调,声音和思想的结合所产生的是形式,而不是物质;二者的结合完全是任意的。思维离开了语言就成为一片浑沌,语言联结声音和概念,语言切分概念[1∶111-112]。根据上述索绪尔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以及语言符号任意性本质的论述,我们可以推论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是语言使我们能够认识世界,是语言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因此,索氏任意性原则表明,不同语言对概念的切分不尽相同,换言之,语言影响思维,操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这是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说理据性就等同非任意性。
(5)正因为任意性原则始终在发挥作用,语言符号才具有其机制。因此“语言符号产生之初是任意性的,后来就不是了”这种说法很难成立。理据主要反映语言符号产生之初的状况。语言符号无论有无理据都是任意性的,受任意性原则约束。
(6)任意性和理据性作用不同:前者体现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即概念与声音形象之间的关系,而后者通过组合(共现)与聚合(联想)来体现语言符号的语义结构。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造成误读任意性原则的主观原因是人们对索绪尔任意性学说未能纵观整体,因此不能合理推断,以掌握其精髓;客观原因是《教程》中用理据性说明任意性的表述不够严谨。这就要求我们参照《第三期》,并合理推断,从整体框架上解读索绪尔。对照《第三期》我们发现,任意性和理据性作为语言符号特征,分属不同层次概念,因此把二者作为对立范畴并非索绪尔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