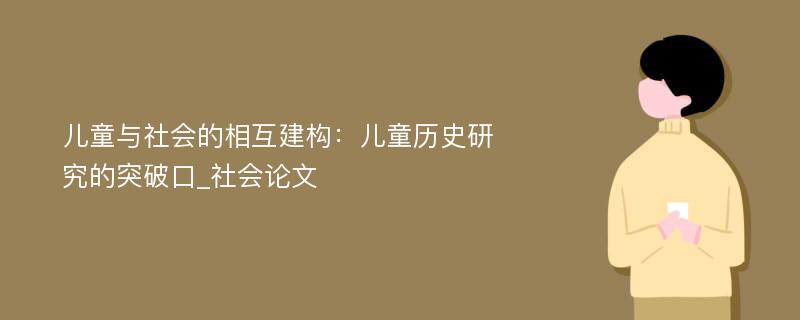
儿童与社会的相互建构:儿童史研究突破的一种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论文,史研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将历史学家比为“神话中的巨人”,因为他们“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肉气味”都能引起“巨人”的注意,妇女与儿童长期以来就似乎不属于历史学家中意的“食材”。不过,这一状况在最近几十年彻底改观。首先是“妇女”,近来几乎已成为历史研究的显赫对象;而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lipe Ariès,或译“阿利斯”“埃里亚斯”等)1960年出版的法文著作《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I'Ancien Regime),在两年后推出英译本,改题为《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被公认为“儿童史”研究的起点。著名儿童史家休·葛宁汉姆(Hugh Cunningham)指出:“所有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历史写作中都绕不过一些‘关系’,童年史家绕不过去的即是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因为他的研究使读者确信:“童年自有其历史。”② 从《儿童的世纪》诞生至今,有关儿童的历史研究著作已是汗牛充栋,其研究方法、取径和理论得到充分讨论,相关研究也在近年被引入中国。俞金尧教授对这一学科做了系统介绍,详尽介绍了儿童史领域的重要著作,勾勒出西方世界儿童史研究的编年脉络。台湾学者陈贞臻对儿童史的发展做了较为详尽的学术史回顾,在其中勾勒出两条研究路线,即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社会建构”取向和80年代在批评前一取向基础上兴起的“生活经验论”取向。③不过,近些年来,儿童史研究的速度明显放慢,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阶段。它是不是能实现一个新的研究突破?如果可能的话,将会对学科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 一、儿童史学科的发展及其瓶颈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历史学界将“儿童”对象化,从而催生各种与儿童相关研究的时代,也是对后来儿童史学科影响最重大的时代。这一时期崛起的史家,均以挑战阿利埃斯的观点为主要出发点。他们讨论的问题包括:中世纪是否“存在”对儿童的爱、是否具有“儿童”或“童年”的概念?近代是否发生了一场“情感革命”?亲子关系的变化究竟呈现出更多的“断裂性”还是“延续性”?阿利埃斯对家庭情感关系的“现代性”到底持什么态度?阿利埃斯的研究隶属家庭史还是儿童史?这两个领域的关系如何?等等。他们从方法、路径、问题各方面均挑战了阿利埃斯的观点,将这一研究推向深入。尽管他们对阿利埃斯不乏“误解”,④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经由阿利埃斯以及他的反对者之手,今天的史家已经将“史学边界拓展到儿童”⑤ 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到了今天,儿童史研究早已经与最初的“搏斗”式研究面貌大为不同,儿童史家在这一领域所展现出来的成熟的理论观点、多样的研究方法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已经远远超出了“阿利埃斯典范”。在主题上,研究者考察了儿童世界的大量疆域。其中既有宏大壮阔者如劳伦·斯通等人对情感结构与家庭类型变化的描绘,也有细致深入者如大卫·格利尔斯(David Grylls)对19世纪文学作品中父子关系的精密描述,⑥还有很多人将“童书”“玩具”等以儿童为中心的“制作物”纳入视野,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儿童史研究的空间。⑦在史料范围方面,研究者从传统的档案文献、教区人口登记扩大至日记、信件、玩具、游戏、服饰等从前不被注意的日常生活的遗留痕迹,也使得儿童的历史更加立体化。 比起主题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儿童史研究理论方面的变化。实际上,研究主题的改变也是和史家们理论视野的革新分不开的。儿童史成长的过程,尤其是到了70年代,恰好伴随着整个历史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历史学家开始将目光投向一个“主观”的领域中,那就是“儿童”概念的社会建构过程。根据埃里森·詹姆士(Allison James)的解释,对儿童“本性”的认知精练地体现了某一文化的“儿童”概念,而“儿童”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儿童“像什么”和“是什么”的观念表象,及成人“为了”(for)儿童的生活所作的一切思考。⑧这样,儿童和童年不再似乎只是等待历史学家去挖掘的静态的客观事实,而是处在主客观生活互动之中的流动体。历史学家需要讨论的是,哪些力量在塑造“儿童”的概念,又是怎样塑造的。 实际上,今天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依据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而有不同的“儿童”或“童年”概念。⑨在此意义上,作为今天的学者,我们也可以对阿利埃斯增加一种了解之同情。大多数人们认为,阿氏的观点是:中世纪“缺乏”儿童的概念;但不如说,阿利埃斯的著作展示的是中世纪的“儿童”概念,它和其批评者们心中那种更一元化的“儿童”形象是不同的。这样,《儿童的世纪》便不再只是一个质疑的对象,我们也需要重新评估其内容和观点。 从研究取径上看,在早期的儿童史研究中,“儿童”还仅仅是一个研究“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讲,如同早期的妇女史一样,那时的儿童史还属于“补赎的历史”阶段。⑩在今天,已经有新的史家在努力向新的境界提升。卡门·鲁克(Carmen Luke)说:“我并不将儿童当做客体,而是将童年作为话语研究。”这是典型的社会建构派的态度。这一派不是将儿童“当做关注焦点”,而是关注“儿童如何成为关注焦点”。(11)在后结构主义、福柯话语理论、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的冲击下,史家已经承认,童年不再是一个静等着“被发现”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分类”,它是文化的建构,被视为成人社会在医学、法律、教育、文学、艺术话语体系的作用下,为达到不同目的而做的积极表述。以往的研究表明,儿童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不成熟”的群体。但是,所谓的“不成熟”作为一种生理“事实”是一回事,成人对这种“不成熟”如何理解,赋予其什么样的意义,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涉及的不是生理的事实,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事实”。 对儿童概念建构过程的关注,无疑深化了儿童史的研究水平。但也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它逐渐走向了自己的瓶颈期。根据这个理论,儿童的概念主要是由阶级、性别、区域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建构”起来的,也随着它们的差异而不同。那么,儿童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儿童史将永远是成人历史的附属品。但是,近来的微观史学研究提醒我们:每个历史行动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了历史进程。(12)因此,儿童自身当然应该被当做行动主体,他们也参与了对他们自身乃是整个社会的建构进程。故而,我们应该进一步探索的是,对于成人加诸他们身上的种种“文化”,他们怎样看待,做何反映? 可是,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目前的儿童史研究的“无能为力”。就像人们通常在生活中经常把“妇女儿童”连用一样,在20世纪的史学史上,儿童史和妇女史的地位也具有极其相似之处。如前所述,他们一度都只是“补赎”的对象。但是今天,女性主义史学已经在历史研究中呼唤出一种“有意识的女权主义立场”,女性不再只是“被研究”的对象,重要的是,她作为一个行动主体的地位得到了历史学的认可。同样的道理,儿童史也应该不以成人的目光为焦点,而应以儿童的视角出发,通过儿童的眼睛观看,并借由他们界定的价值来解释他们所在的世界。但事实上,儿童与妇女还是有着相当大的不同:虽然都处于权力中心之外,但女性成人仍有可能以她们的价值来描述历史,儿童则永不可能。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婴幼儿的世界,问题就更为严重。既往的研究者所研究的儿童多少都是有“最小行为能力”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都是3岁以上的儿童。至于0-3岁的婴幼儿,尤其是那些尚未“看见”的胎儿,因其无行为能力,无所表现,则更少被史家关注到。(13) 因此,尽管有些史家自觉地希望把“儿童”视为一个行动者,力图站在他们自身的立场上看问题;然而,由于现存史料的性质,这种努力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说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历史学家只能依据史料说话,而现存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史料都出自成人之手,即使里面折射出一些儿童自身的信息,也很难从成人的眼光中区分出来。我认为,这就是儿童史学科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挑战,如果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定的突破,儿童将永远处于实际的失语状态,所谓儿童史也将难以继续存在下去。 二、突破瓶颈的可能:儿童与社会的相互建构 不过,在我看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个障碍虽然难以“克服”,却不是完全不能“绕过”的。 首先,以儿童为主体,并不是要把他们从社会中孤立出来。儿童并不是天然就具有某种面貌,他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持续不断但却是常常不动声色地通过各种微观机制对其身体和头脑加以规训的结果。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看法,在同一阶级或群体的不同成员中表现出来的“个别习性”,其实也是同一阶级或群体共享文化的产物:“个人风格……从来只是对一个时代或一个阶级固有风格的偏离。”(14)因此,在一个特定文化中,儿童对成人世界的反映在很大程度上和成人世界塑造他们的方式、对他们的要求有关;他们的看法不会离大人们的“期待”太远,这便意味着即使那些“不乖”的小孩,也要符合成人们对“不乖”小孩的定义。所以,要了解儿童这一“主体”,首先还是应该先弄清楚社会建构他们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即使儿童沉默不语,我们也能大致勾勒出他们的内在世界。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由于历史上儿童的生活环境所致,在通常情况下,学者们会倾向于将儿童史视为“家庭史”的一部分。准确地讲,无论是所谓“社会建构”取径还是“生活经验”取径,所说的“社会”都是“家庭内部”这个小社会,他们关注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种亲子关系。但是,这样一来,儿童就被封闭在一个有限空间内,儿童跟更广大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儿童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儿童与家庭外的成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一概难以知晓,因此我们也就难以准确地勾勒出社会建构儿童概念的具体路径。为了突破这个限制,就要求我们突破“家庭史”的眼光,从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立场上观察问题,注意到围绕着儿童产生的多重社会关系。 其次,这也需要我们特别地对“社会建构”的研究路径加以深入反思。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单向的,重视的是成人“建构”儿童的过程;然而,儿童并不真的像洛克所说的是“一张白纸”,他们在被成人世界建构的同时,也对成人世界施加了反作用力——而这一点正是过去的研究所忽视的。当然,我们说儿童在“反作用”于社会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儿童是在有意识地、自觉地这样做。有的时候,他们只是不知不觉地“改造”了成人社会,“参与”了由成人们把控的历史进程——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又建立在一个前提上:成人们认为“儿童”很重要,对儿童的“本性”采取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就曾指出,现代家庭是“被制造”出来的。在其中,有关儿童“本性”的新观念将儿童置于一个代表着未来的位置,但同时也把儿童身体和理性上的不成熟当做一个重要前提。当人们意识到儿童“本性”的观念时,便意味着成人开始了对儿童的关注。(15)但它也带给我们另一种启示:就在成人塑造儿童的同时,成人们岂不也在受到这种新观念的塑造吗?那么,儿童就看似以一种完全“被动”的方式,通过成人本人改造了“成人世界”。 通过上述两个步骤,我们可以把成人和儿童放在同一个世界中,而且这个世界不是单向的,儿童虽然仍然很难通过自己的嘴巴发声,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以成人们所预料不到的方式,成为改造历史的行动主体。 以近代早期欧洲儿童史为例。肖特所提出的近代早期有关儿童“本性”的新观念,已经获得了不少证明。不过,他的重点仍在借此讨论“亲子关系”。换言之,他仍把儿童放在一个家庭的范围内考虑。我想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有关儿童“本性”的“新观念”,也来自于那个时期爆发的“新知识”。福柯已经敏锐地观察到,16世纪以来的欧洲,发生了一场知识变革,并分别在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导致了“间断性”突变,“人随之并且第一次走入了西方知识领域”。(16)它赋予人们一种新的眼光,人开始以“观看”和“实验”的方式,重新思考“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该如何对待“自己”这一并非“神圣”造物这样的问题。而对儿童“本性”的思考,正是这一对“人”的思考的一部分。 因此,对那一时期“儿童史”的认识,就必须跟(广义的)启蒙运动联系起来。但以往研究儿童史的学者们过多地关注于“家庭”这一范围,多少忽视了近代早期欧洲历史上这个最为重大的事件对“儿童”的影响。当然,启蒙运动对于儿童的关注,不少学者都多多少少提到了。比如,法国学者托多罗夫所列举的启蒙运动在人权方面的成就之一就是:“儿童被作为个体看待。”(17)美国史学家彼得·盖伊的巨著《蒙运动》也偶尔会闪过一些孩童的面容,尤其是在讲教育的部分。(18)美国文化史家巴森则强调:“我们这个年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儿童的年代”。(19)不过,儿童在启蒙运动中到底居于什么样的地位,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却忽视了。 如同人们经常意识到的,“儿童”是启蒙思想家的目光所向,启蒙思想家们运用新的知识重塑了人们对“儿童”的认识。正是这一点,使得过去学者关注启蒙思想与儿童的关系时,都将这种关系界定在“教育”层面上,特别突出洛克和卢梭的“教育”理念对后世产生的极大影响。但也需要指出的是,洛克的目标在于理解“人”,并经由“人”而理解人所在的“世界”。在他的思路中,儿童的本性被看做人性的样本。他正是通过对儿童的观察和思考,才提出一套“人类知性论”的。这一点,托多罗夫也意识到了,他在讨论启蒙精神时说:“投射在儿童身上的目光正是人类意识的起源。”(20)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儿童位于启蒙运动的“核心地带”。 人对自己的了解不限于心理世界,身体甚至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认知出发点。这一时期,伴随着新的知识理念和技能实践,出现了一系列教人识“人”的文献,它们主要体现为各种医疗指导手册。手册的写作者多是在知识突变大潮中,开展解剖学实验、掌握外科手术新知识的医生,他们试图从人体的物质性结构来认识“人”,并将他们的“认识”教导给民众。这种知识的增进进一步改变了此前基督教传统观念中有关人的“本性”的认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儿童生产和养育实践的变化。通过这种变化,“生命历程”展示了不同年龄段生命的路径,而路径的深远程度则在生命的时间、空间和行动中体现出来,它是社会的“模型”。(21)布尔迪厄更提出,有共同社会经历的生物个体对精神结构的“归并”,可以称之为“习性”。他认为“归并很早就开始发生,甚至在会说话之前,在具有理性和控制思维之前就开始了”。因此,“婴儿期可能是个人将社会结构并入内心的关键时期”。换句话说,社会化的生物个体即是个体化的社会。(22)这意味着,“人”,从出生到死亡,没有一瞬不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而无论这一生命历程多短暂,都极富意义。 透过启蒙运动中关于“人”的新知识的扩展,我们看到,“不言不语”的婴幼儿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参与”到由生产和养育实践带来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模型重组的变化中。首先,启蒙思想家对“儿童”的关注固然出自成人自己的知识兴趣,但正如洛克的例子所表现的,成人对“儿童”的新认知又影响到有关“人”的整体观念。其次,彼得·盖伊已经提示过:启蒙运动不仅开启了一种新观念,也开启了人与世界的一种新关系。(23)儿童的生产和养育不仅是家庭的私事,它从来都是社会行为。一个人从其诞生的那一刻(甚至在此之前)开始,就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中。 另一方面,当社会的价值转向以儿童为中心的时候,对儿童的“爱”就带来整个社会资源与机会的重新配置。这里我们只简略地展示一下它对社会领域的影响。首先是职业结构的变化。启蒙运动之后,男性助产士(医生)借助于新知识的“霸权”,手持新的医疗“器械”,闯入并占有了传统女性专有的“知识领域”。他们跟女性接生婆的职业竞争,被视为代表“进步”的“医生”战胜囿于习俗和偏见的“无知”产婆的过程。正如启蒙思想家约翰·托兰(John Toland)的呼声:“我们从见‘光’开始,就身处巨大的骗局”——那“产婆以迷信的仪式将我们亲手带入此世”。参加这场“仪式”的“善女人”们,手中其实有“千般符咒”,婴儿的不幸或幸福都只在“她手中”,就看她怎么用。(24)这段话,不但针对产婆的“无知”,也指出偏僻黑暗的产房里发生的一切,谁也“看不清楚”,暗示了杀婴的社会现象。但是当男性医生介入生产,他们即需要“观看”。因此当婴儿的生产从偏于一隅光线幽暗、门厅紧闭的产房转移到有日光照入、亮亮堂堂、可以实践临床观察的产房乃至医院时,既可为新的医疗实践提供了条件,也让“生产”之事可被“看见”,杜绝“阴谋”。正如克里斯蒂娜·哈德门特(Christina Hardyment)所论断的那样:当医生们将产房从幽暗之处转移至明亮的地方,就在某种意义上抓住了“‘启蒙’的真谛”。(25) 儿童养育的工作同样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后果。由于人们强调母乳养育的重要性,使得此前一直在婴幼儿生活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乳母”,转为辅助性的“保姆”;而新的“保姆”不需要一定的生养经验,在年龄上趋于年轻化,在儿童生活中则日益边缘化。(26)由于“喂养”在塑造儿童的社会关系中成为关键一环,导致了一个新观念:“养”甚至比“生”还重要。这导致以“爱”为基础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私人收养关系,人们将无血缘的孩子收养后,通过“家庭化”的过程,使其成为新的家庭成员。随着这种个人化的“民间慈善”方式的推广,社会也介入其中。民间慈善机构兴起,最为著名的如英国的“伦敦资助院”等,承担起弃婴、孤儿的失怙救助与养育责任,对它们施行了更广阔范围内的“家庭化”工作。这在社会结构领域引发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职业化”的“保姆”——保育员也相伴而生。(27) 这些现象也引导我们重新审视儿童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成果,比如阿利埃斯与劳伦·斯通有关近代新型情感诞生的著名讨论。其中,阿利埃斯将新情感视为“私领域”的“专有产品”,特别强调这一因素使得家庭日益从社会中退出,成员在这一“私密、狭小”的空间内“抱团取暖”。斯通则将这种新型情感置放于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但他同样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公领域”与“私领域”的疆界越来越明显,“私领域”的功能逐渐缩小为提供情意的温床。(28)他们的看法确实予人无尽的启发,然而也须注意的是,家庭毕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单位,与广大的社会存在着多种形式的交流。对于儿童来说,家庭是生活的中心,社会关系是透过家庭这一途径进入到他们的世界里的。然而,上边谈到的现象表明,儿童被社会建构,反过来又重新组织社会的过程,并不限于家庭这一“私领域”,而现代社会中“公领域”与“私领域”的疆界并非那么界限分明。“私领域”中的变化实际上是“公领域”改变的结果。因此,劳伦·斯通发现的“核心家庭”的日益封闭化的现象,还应该予以重新认识。 可见,胎儿虽然沉默无言,婴幼儿也只会呱呱而哭、咯咯而笑,但它们也以自己的方式在改变着社会,重组了与之相关的人际关系,调整着更广阔的社会结构。毫无疑问,儿童在这里扮演的似乎仍是一个“被动的”和“消极的”角色,可是它和过去我们认知的“被动”不同:它呈现出自己对更为广阔的社会产生的影响,甚至可以说非常“积极”地在起作用。 上面的简略描述当然无法展示更加复杂的内容,但是已经基本可以告诉我们:在社会建构儿童的同时,儿童也在建构着成人社会。相对于“社会建构论”的研究方法,这里呈现的面相无疑要更加立体,也给了儿童一个更加积极的行动者的地位。为此,我试图把它命名为“儿童-社会相互建构”的研究取径。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对“社会建构论”的继承和超越:强调有关儿童的“概念”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历史的变动性等等。在这些方面,它不同意“生活经验论”对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脉络的轻视。当然,它也吸取了“生活经验论”的一些内容,比如关注作为实体的儿童和他们的真实生活。实际上,这两个理论并不一定是相互矛盾的:在一定程度上,“生活经验”也是概念建构的结果,而任何一种新的概念,也都必须建立在过去的(有可能是少数人的)生活经验基础上。 在儿童史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建构论”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但是也把这个学科带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儿童在这里只是成人处置的“对象”,对于外界完全无能为力,这使其仍然无法摆脱“被动”的失语地位,而儿童史也始终不脱“补赎历史”的性质。另一方面,对其表示异议的“生活经验论”,又不免矫枉过正,几乎完全否定社会对儿童的作用。为了让儿童史走出这个瓶颈阶段,本文在“社会建构论”基础上,提出了“儿童—社会相互建构”的研究取向,希望为儿童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 “儿童-社会相互建构”的理论由两部分组成:(一)突破传统儿童史中的家庭史研究取向,将儿童置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里加以认知;(二)从成人世界对待儿童的认识、态度、实践和制度等方面,探讨站在“被动”和“消极”地位的儿童怎样成为历史中的一个行动主体,参与到对社会的建构中。 当然,即使做了这些努力,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无论如何,儿童的世界仍是难以探知的,无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难以真正进入,就像儿童不能完全理解成人一样。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不能因为我们无法完全把握他们,就把他们丢弃在历史之外,耳闻他们的哭声和笑声而毫无心动。儿童史家奥雷尔·恩德(Aurel Ende)宣称:“我坚定地相信,若不能重建童年史,我们就不能够重建历史。”(29)这也是我的信念。我当然清楚知道,儿童史是“崭新而又困难重重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的证据‘在风中颤动’”。(可是,在历史学的哪一个领域中,证据不是“在风中颤动”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将致力于“此学术志业”,力图“理解人类的窘境”。(30) ①马克·布洛赫(Bloch Marc):《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②Hugh Cunningham,"Histories of Childhoo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3,No.4,Oct.,1998,p.1196. ③俞金尧:《儿童史研究四十年》,《中国学术》第3卷第4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儿童史研究及其方法》,《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陈贞臻:《西方儿童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阿利斯(Ariès)及其批评者》,《新史学》第15卷第1期,2004年。据陈贞臻的判断,“社会建构”取向大致分为两个不同的“建构”阶段,一是上世纪70年代,以阿利埃斯、劳伦·斯通、劳何·德莫斯等人为代表的研究,注重“童年概念”的追寻、成人对待儿童的态度以及亲子关系的演变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此后直至90年代,社会建构取向的史家将研究重点扩大至儿童与周遭社会关系上,以此探讨社会如何形塑了儿童的概念。社会建构取向认为童年概念并非生物性使然,而是一种文化产品,是不同时空之下的社会现象。陈贞臻的这一论断是准确的,也是儿童史研究领域的共识。“生活经验论”的代表是琳达·波洛克(Linda A.Pollock)。她主要批评70年代兴起的儿童史研究如阿利埃斯、斯通等人的研究都陷入了“现代性”范式而不自知。虽然她并没有否认累世以来亲子关系的变化,但她并不认同“情感革命”这种“断裂式”的论断。她指出,古代到中世纪的儿童世界并不像前期史家断定的那样,充满了黑暗暴力和成人的漠不关心,对他们的处罚也并不是整体状况,而只是亲子关系诸面相之一。父母疼爱小孩自古有之,也一样期待孩子的到来,并关心他们的教育。同时,波洛克坚持认为,阶级、受教育程度、文化、宗教、道德价值等因素对亲子关系并不具影响力(Linda A.Pollock,Forgotten Children:Parent-Child Relations from 1500-19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波洛克的批评自有其道理,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她过于关注累世普遍共同的“人性”,也就使得儿童史不可能具有更多的讨论空间,从而直接制约了儿童史的研究。 ④有关这些“误解”如何催生儿童史学科的“建立”,以及投入这场“思想搏斗”的史家及其作品,见辛旭:《由“误解”发现“童年”:“阿利埃斯典范”与儿童史学科的兴起》,《四川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⑤彼得·伯克(Peter Burke):《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0页。 ⑥David Grylls,Guardians and angels:parents and children in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London & Boston,Faber and Faber,1978. ⑦部分儿童史家专注于儿童的物质文化,研究与儿童相关的历史遗存,尤其注重对儿童图像和图像中的儿童的研究,成果卓著,如伦敦贝特内尔·格林儿童博物馆馆员们的儿童图像研究,例如Mary Frances Durantini,The Child in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Painting,Ann Arbor,UMI Research Press,1983. ⑧Allison James,Childhood Identities:Self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Child,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3,p.72. ⑨Anja Muller,ed.,Fashioning Childhoo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Age and Identity,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6. ⑩在妇女史研究中,曾有一个阶段(主要是20世纪60-70年代),可以被称作“补赎的历史”,其目标是补充男性历史记录中女性的缺失,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只是填补历史画卷空白的作用。 (11)Carmen Luke,Pedagogy,Printing,and Protestantism:the Discourse on Childhood,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p.5. (12)刘永华:《费雷、夏蒂埃、雷维尔:“超越年鉴派”(代译序)》,收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xxii页。 (13)实际上,有一些史家非常细致的研究了有关分娩的历史,如艾武瑞·鲁登的《死于分娩》(Irvine Loudon,Death in Childbirth: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Maternal Care and Maternal Mortality,1800-1950,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即是其中佼佼者。不过,这本书的主旨在于讨论历史上人们如何建构“母性”,如何实践“母爱”的,也讨论到产妇的死亡状况,胎儿只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雅克·盖利斯的《分娩史》(Jacques Gelis,History of Childbirth:Fertili,Pregnancy and Birth in Early Modern Europe,Oxford,Polity Press,1991.)详细阐释了近代早期欧洲有关“丰产”“怀孕”和“分娩”的观念与实践。不过该书关注的同样只是“成人”,并非胎儿。其他如阿德里安·威尔森的《制作男性助产士:英格兰分娩史1660-1770》(Adrian Wilson,The Making of Man-Midwifery:Childbirth in England 1660-1770,London:University College Press,1995.)关注了男性助产士与传统产婆之间的知识与权力之争,与本文关注的一些问题非常密切。迈克尔·多得等主编的《产科学史》(Michael J.O'Dowd and Elliot E.Philipp,The History of Obstertrics and Gynaecology,New York and London:The Parthenon Publishing Group,1994.)亦关注到知识带来的权力更替与社会重组。克莱尔·汉森(Clare Hanson)的《怀孕文化史:怀孕、医学和文化(1750-2000)》(章梅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将怀孕这一私事置放于现代国家的“管理”机制中,展现了“国家”应用“怀孕知识”将“人”深层“管制”的过程。不过,这些具有代表意义的与“胎儿相关”的著作,并没有将“胎儿”置于视野的中心。 (14)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15)Randolph Trnmbach,"review,The Rise of the Egalitarian Family; Edward Shorter,The Making of the Modem Family," in 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Vol.4,No.2,1976,p.212. (16)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1-12页。 (17)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启蒙的精神》,马利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18)彼得·盖伊(Peter Gay):《启蒙运动》下册,梁永安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第582-633页。 (19)雅各布·巴森(Jacques Barzun):《从黎明到衰颓: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生活》,郑明萱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1年,第989页。 (20)茨维坦·托多罗夫:《启蒙的精神》,第53页。 (21)Glen H.Elder,JR.ed.,Children in Time and Place:Developmental and Historical Insigh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22)皮埃尔·布尔迪厄、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4页。引文出自夏蒂埃对布迪厄思想的阐释,但得到了布迪厄的赞同。 (23)彼得·盖伊(Peter Gay):《启蒙运动》下册,梁永安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 (24)Roy Porter:Enlightenment:Brita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Penguin Books,2000,p.117. (25)Christina Hardyment,Dream Babies:Child Care from Locke to Spok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98. (26)George Armstrong:An Account of the diseases,most incident to children,from the birth till the age of puberty,London,1783,p.17. (27)Ruth McClure,Coram's children:The London founding hospita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28)进一步的讨论详见辛旭:《从“卧室”走出的“个人主义”:劳伦·斯通家庭史研究的启示》,《读书》2014年第5期。 (29)Aurel Ende,"Children in history:a personal review of the past decade's published research," 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Vol.11,No.3,1983,p.65. (30)Patrick Dunn,"Modernization and the family; review Edward Shorter,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 in Lloyd de-Mause ed.,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Vol.4,No.2,1976,p.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