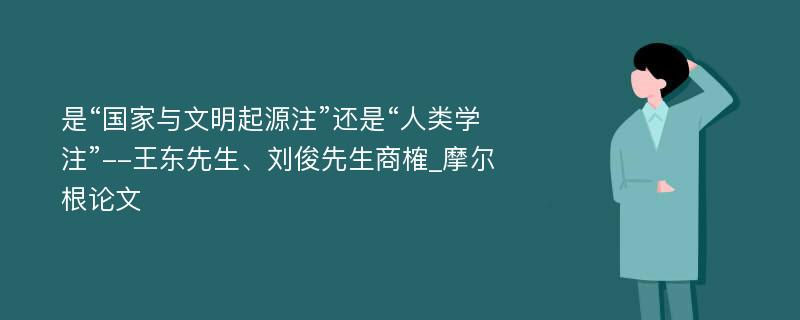
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记论文,人类学论文,起源论文,国家论文,刘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拜读王东、刘军先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注:见王东、刘军:《“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以下简称“王、刘文”)一文,颇有启发。但对于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这一称谓来取代“人类学笔记”的做法,笔者认为这不但有悖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而且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贡献也难以做出正确的评价,同时王、刘文在论述更名的依据时证据不充分、不准确。因此,笔者不敢苟同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这一称谓来取代“人类学笔记”是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的说法。现就这一问题同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以求教于王、刘两位先生及学界同仁。
一、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
探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个核心问题,王、刘文的解答是:“我们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归为‘国家与文明起源’,旨在表明他晚年的理论探索是其一生理论追求的必然延伸,其关注的理论焦点是探求社会历史的‘原生形态’问题。”按王、刘文所述,所谓社会历史的“原生形态”即人类社会的最初形式。难道马克思一生的理论追求,到最后必然延伸到“原生形态”的问题。此论断实属大谬也!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对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的误读,也是对马克思一生理论追求的误读。
革命挚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悼词对其一生做了极为精当的评断,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340、857、341-342、342、774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5、251页。)在标志唯物史观基本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恩格斯郑重宣告:“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5、251页。)这些论述,深刻地表明马克思理论的指向是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紧密相联。实际上,马克思一开始就将其理论意蕴不仅仅看作为一般的理论思维的学说,而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锻造锐利的武器。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集革命家思想家于一身,但在他一生中,革命始终是他一贯倾斜的重心。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不过是作为革命家马克思的观念的写照而已。不论是理论上的著述,还是亲身的革命斗争实践,马克思总是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5、450-451、451页。)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打碎锁链获得解放,马克思始终怀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求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马克思晚年在这方面的探索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最富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内容,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因而,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源于革命实践而非理论研究的需要,决不是王、刘文所说的“其关注的理论焦点是探求社会历史的‘原生形态’问题”。
马克思原来设想,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不能克服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要来临,并取得胜利。然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却趋于低潮。更为糟糕的是,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意识衰退,英国最为典型,“……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了卖身投靠的工联首领和职业鼓动家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139、346、345页。)所以,在可以预见的短时期内很难看到无产阶级革命重新高涨的情景。新的社会革命的突破口在那里成了马克思晚年探索的重要问题。
同时,现实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也引起了马克思的深思。特别是1872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虽历时多年,涉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但却没有造成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崩溃。马克思最初认为,危机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崩溃。他在1875年6月18日致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写道:“真正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我一直认为这种时间不是不变的,而是逐渐缩短的;但特别可喜的是,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139、346、345页。)但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这次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已超出《资本论》第1卷对经济危机所作的概括。这使他感到有些困惑,所以他认为“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139、346、345页。)他决心推迟《资本论》第2卷的出版,以便等它完全成熟,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他在1879年4月10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139、346、345页。)
与西方革命陷入低潮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东方各国却暗流涌动。面对资本主义推行的世界一体化,强迫其它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饱受苦难的东方各民族,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斗志,为保存本民族及其文化价值,而努力探索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印度、俄国和中国等国家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动,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并且日益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紧密地结合,显示出深厚的革命潜力。
再加上,自从《资本论》第1卷问世后,俄国的一些革命家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俄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来纠缠马克思,或是用马克思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来否定俄国农村公社,或是用俄国农村公社来否定马克思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因此,如何解决俄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就成了马克思晚年不容回避的问题。1877年11月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写道:“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340、857、341-342、342、774页。)尽管马克思在1877年得出了这个“准确”的结论,但它毕竟还只是一种理论的假设,人们也没有因此而停止对马克思理论的“揣测”。1881年2月16日,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革命者中极受欢迎,同时也引起了热烈的争论,特别是土地和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她请求马克思拨冗谈谈对俄国历史发展,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予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340、857、341-342、342、774页。)查苏利奇在信中表示,期待马克思写出一篇较长的文章,或者一本小册子,实在不可能则写一封信,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给予回答。
在强烈的现实要求下,迥异于西方的东方国家能否取代西方国家成为革命理论的践履地和新的突破点,自然进入了马克思晚年的研究视域。思想的闪电必须射入人民的园地。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决不可能仅仅是“探求社会历史的‘原生形态’问题”,而是立足时代风云,去超越过去,寻求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它决不是黑格尔所讲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是黄昏时姗姗来迟,而是昂头高歌的高庐雄鸡,不停地呼唤着黎明的来临。
二、“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不能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
王、刘文认为应将“人类学笔记”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此,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理由。在笔者看来这四点理由欠仔细推敲、认真辨明,难以令人信服,不足为据。
王、刘文的第一理由认为:“这样做符合马克思所选择的五本笔记对象的标题,是对其内容的准确概括。”在王东、刘军先生看来,马克思所选的这五本书的标题就是反映国家与文明起源这一内容的。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王、刘文举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副标题作为佐证。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确实有个副标题,即“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但这个副标题不是像王、刘文所认为的那样“它很好地反映了该书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主题内容。”稍微有阅读能力的人,只要打开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一看就再清楚不过。作为文化人类学家的摩尔根从文化角度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前两个时代又分别划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各有其文化标志。应该说论证人类社会或文化的不断进化过程才是《古代社会》一书的主题,而绝非王、刘文构想出来的所谓“关于国家与文明起源的主题”。至于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的摘要,马克思所关注的重点再明确不过。马克思摘录的侧重点在于探讨东方国家的土地制度、村社结构和社会生活等一系列的社会发展问题,重点考察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问题。马克思还着重批判柯瓦列夫斯基、梅恩、菲尔等人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社会的封建制度不能作简单的类比,它们各有其自身的特点,按照西方封建制度的模式来推论东方是不正确的。
王、刘文的第二个理由认为把马克思晚年笔记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符合马克思在五本笔记中所作的评注,因为“马克思对五本书中关于财产关系演变和私有制产生的内容进行了大量摘录和批注。”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马克思大量摘录和批注的内容做出辨析,是否如王、刘文所说是“关于财产关系演变和私有制产生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大量摘录的究竟是哪一个方面的内容呢?王、刘文又举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来加以说明。可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是用60%的篇幅,以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作为典型,叙述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而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其最大部分也在于此。但“在氏族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政治社会或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471、283-284、269、781、242-243、331、466、512、211页。)马克思在摘录这句话时是划了着重线的。我们知道,氏族是一种社会组织,而国家是一种政治组织,前者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后者是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更何况易洛魁人由于还未进入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就被欧洲人征服,所以这个只作为全盛时期的典型的氏族社会,并没有展示出它自身是如何瓦解的。既然如此,马克思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力气来摘录其内容,表明马克思的兴奋点绝不是要在此阐述所谓“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马克思在此着重是揭示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一般说来,氏族的发展会产生部落。摩尔根就是在考察了氏族之后考察胞族、部落和联盟的。而马克思则看到了氏族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以氏族原则加征服这样的方式,不会使氏族逐渐形成为等级吗?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禁止在不同氏族之间通婚的禁令,与禁止在同一氏族内通婚的古老规则完全相反”,通常来说,“血缘纽带不容产生任何形式完备的贵族”,而“一旦在氏族的血缘亲属之间产生等级之分,这就同氏族原则发生冲突,而氏族就会僵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即等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471、283-284、269、781、242-243、331、466、512、211页。)即在氏族的基础上产生出与氏族相对的等级是氏族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这样,马克思在考察史前社会的发展时,揭示出了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其次,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批注写得最长的又是哪一个方面的内容呢?王东、刘军先生也知道,马克思的批注最长的大约300字。但这最长的批注却不是论述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而是批评柯瓦列夫斯基将东方古老国家的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瓦解看成是与西欧封建化同样过程的错误看法。马克思写道:“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471、283-284、269、781、242-243、331、466、512、211页。)在马克思看来,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对所谓东方社会封建化过程的描述,“都写得非常笨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471、283-284、269、781、242-243、331、466、512、211页。)因为“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迷惑了柯瓦利夫斯基的视线。马克思在摘录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时,也同样对菲尔的“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批判。菲尔在论述东方乡村公社中的家庭和公社的关系时,把东方的公社和社会的关系看作是封建主义,马克思对此批评道:“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作封建的结构”。(注:《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
王、刘文提出更名的第三个理由是通过“对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的比较阅读中可以找到理由”。为了说明论证这一理由,王、刘文把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最晚的拉伯克笔记的写作时间认定是1881年6月完成,而“《历史学笔记》则大致写于1881年底至1882年初,二者在写作时间上前后相连。”但不知道王、刘文确定马克思的拉伯克笔记完成于1881年6月有何权威性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在关于《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的注释中指出:“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摘要,是马克思在1882年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471、283-284、269、781、242-243、331、466、512、211页。)笔者又查询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此书明确指出:“1882年10月-11月,马克思研究原始文化史,阅读约·拉伯克的著作《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并作了摘录”。(注:《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47、440页。)而且在“年表”一书中,写明马克思在1881年8-9月阅读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并作了许多评注性的摘录。(注:《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47、440页。)因此,可以认定所谓“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二者在写作时间上前后相连”的判断是不成立。在谈到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情况时,王、刘文又出现了类似的错误。王、刘文指出:“在马克思晚年的计划中,曾明确提出要完成‘《资本论》续篇’,并先后提出了‘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的方案。”要知道马克思明确提出“六册计划”是在1858年2月22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提出的。马克思在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1页。)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中,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的注释中很明确地写道:“1857年8月,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整理他搜集的材料,并着手写作经济学巨著。1857年8-9月,马克思草拟了这一著作的提纲的初搞。在以后的几个月中,马克思更加详细地拟定了自己的计划,并在1858年4月决定把整个著作分成六册来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99、7页。)1858年怎么能算是马克思的晚年时期?笔者实在不知将1858年归属于马克思晚年的依据又是来自何处?由此可见,王、刘文的错误就在于为了论证马克思晚年笔记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总是犯了牵强附会的毛病,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硬是扯到了一起。
王、刘文提出更名的第四个理由是“此举与恩格斯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解读相符”。为了证明这一理由,王、刘文列举了看起来很是让人信服的证据:“作为马克思的亲密好友和理论合作者,恩格斯应该最清楚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走向。”事实上,马克思晚年所从事的研究,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恩格斯也不大清楚。对此,恩格斯在处理马克思遗稿时,与友人的通信中多次提到。恩格斯在1883年4月2日致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写道:马克思晚年“总是瞒着我们不讲他的工作情况。他明白:我们要是知道他写好了什么东西,就一定会同他纠缠不休,直到他同意发表为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7、112-113、127、132、133页。)在1883年8月30日,致奥·倍倍尔的信中又一次谈到马克思晚年研究工作的情况,写道:“你问,怎么会连我也不知道该书(指《资本论》-引者注)完成的程度?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7、112-113、127、132、133页。)马克思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只要他的理论尚处在仍需探索的阶段,他是不会轻易地把它写成正式作品的,更不会轻易地拿出去发表。在他看来,“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99、7页。)正因为如此,使得包括恩格斯在内的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晚年的工作情况不完全了解,往往误以为他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资本论》第2、3卷的写作上。所以说,“恩格斯应该最清楚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走向”的说法,又是王东、刘军先生自己构想出来的,事实绝非如此。应该说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之前,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走向是不甚清楚的。即使在整理遗稿初期,由于恩格斯当时所关心的是如何应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请求尽快将《资本论》的第2卷和第3卷整理出版,因而也就忽视了对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其他文字的整理和出版工作。重要的转折是发生在1884年初。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的过程中发现了马克思晚年在1880-1881年所作的关于摩尔根的笔记,这使他异常兴奋。1884年2月16日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件中写道:“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来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杂文栏或《新时代》写点东西,但是,目前不可能去考虑这一点。……五个星期以前我就订购了这本书(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引者注),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7、112-113、127、132、133页。)1884年3月7日恩格斯得到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后,非常高兴地写信给弗·阿·左尔格,请他“读一读摩尔根(路易斯·亨·)的《古代社会》,是1877年在美国出版的。他巧妙地展示出原始社会和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的情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7、112-113、127、132、133页。)但是,由于时间关系,直到这时恩格斯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对“摩尔根的书”作“一番加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7、112-113、127、132、133页。)他在1884年3月31日向劳·拉法格抱怨说,由于受到种种干扰和纠缠,“不但是我的时间,而且连我的房间和书桌都不是我自己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7、112-113、127、132、133页。)后来,通过对马克思关于摩尔根笔记的仔细研究,恩格斯才下定决心,改变了自己原先如有时间仅仅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进行概括的写作想法,而是广泛地运用马克思的批语以及摩尔根这本书中的某些结论和材料,来写一部专门的著作,以便“执行遗言”。这怎么能说“在马克思的带动下,恩格斯晚年一直重视对原始社会及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呢?
三、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
对于马克思晚年的这些笔记(所指范围与王、刘文相同)的称谓,现在大致有四种,即王、刘文原先所列举的三种之外又加上“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一种。
在笔者看来,王、刘文所提出的为笔记更名的四个理由不仅不充分,而且在论证过程中不够缜密,存在着不少漏洞。因此,不足以成为依据,故不能将这些笔记的称谓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能否用“古代史笔记”或“东方社会笔记”这一称谓,笔者认为也不太妥当。因为从马克思这些笔记所摘录的内容来看,即非局限于古代史,也非局限于东方社会。也就是说,这些笔记时间跨度空前广阔,上自原始社会形态下至近代殖民地现状的原因。从地域来说,涉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希腊、罗马的古老社会形态的问题。因此,用“古代史笔记”或“东方社会笔记”来称谓也显得不太准确。
至于用“马克思晚年笔记”来称谓,则又显得过于粗糙、笼统。因为马克思晚年笔记除了这五本之外还有许多,这五本笔记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四种称谓,究竟哪一种更贴近马克思晚年这些笔记的内容呢?笔者经过认真地相互比较,认为还是将这些笔记的称谓定名为“人类学笔记”更为贴切。那么,用“人类学笔记”的称谓,是否如王、刘文所说的会造成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误读。王、刘文还为此提出两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在笔者看来,造成对马克思晚年笔记误读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来自于王、刘文自身。
首先,笔者认为王、刘文没有厘清“人类学”这门学科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大致分类。人类学,顾名思义是关于人类的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前者着重于人体解剖科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后者着重于人类习得的种种行为,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以及各民族地区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从马克思所摘录的有关人类学笔记的内容来看,应归属于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在研究内容上,又被分为广义文化人类学和狭义文化人类学。其广义的研究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其狭义的研究,即指民族学。民族学是在民族志基础上对各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这样的研究,又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尽管“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有相通之处。但在我国,“民族学”往往只指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人类学才是指包括主体民族在内的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所以,笔者认为不能像西方那样将“人类学笔记”与“民族学笔记”通用,而只能用“人类学笔记”的称谓。因为,马克思的笔记所摘录的著作正是广义的人类学著作。
其次,王、刘文认为若将马克思晚年的这些笔记称之为“人类学笔记”将会“忽略了马克思理论革命性特征的关注”。笔者的看法与此恰恰相反。马克思晚年所从事的人类学著作的摘录与研究确实并非是受“不可饶恕的学究气”驱使,而躲进书斋进行纯粹的学术性的人类学理论的探讨,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革命实践方面提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笔者已在“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中予以详尽的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用“人类学笔记”这一称谓不仅能够较为真实地表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而且能够客观地评价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贡献。对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和贡献,我们既不要拔高,也不要贬低,而是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看待。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
马克思晚年在著名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严厉批驳了米海洛夫斯基对他思想的曲解。马克思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340、857、341-342、342、774页。)“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340、857、341-342、342、774页。)马克思在信中认为,每个民族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各不相同,不作具体分析,把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当作万能钥匙,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在1881年3月8日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更是明确指出:《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340、857、341-342、342、774页。)
19世纪80年代,农村公社在广大非欧世界还普遍存在着,但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侵蚀,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面临存亡危机之秋。农村公社关联着世界亿万农民,落后国家农民问题也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问题,而民族殖民地问题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对马克思来说,农村公社的命运将影响整个世界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出于这种意识,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特别关注农村公社问题。而就农村公社而言,公社土地所有制是它的支撑点,农村公社的命运取决于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命运。因此,马克思对公社命运的关注都倾注在对农村土地所有制的研究中,这集中体现在对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的摘记和评注上。柯瓦列夫斯基以印度为例对公社发展的一般进程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揭示出公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1)最初是实行土地共同所有制和集体耕种的氏族公社;(2)氏族公社依照氏族分支的数目而分为或多或少的家庭公社……(3)由继承权即由亲属等级的远近来确定份地因而份地不均等的制度。……原先的不均等日益加剧;(4)这种不均等的基础已不再是距同一氏族首领的亲属等级的远近,而是由耕种本身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的占有。这就遭到了反对,因而产生了:(5)公社土地或长或短定期的重分制度,如此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471、283-284、269、781、242-243、331、466、512、211页。)对此马克思赞同他的看法。但马克思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把亚、非、美洲各古老民族的社会历史的演变同西欧作机械类比的做法。他在作摘要时常常把这些类比删除或予以修改,并且对印度在德里苏丹统治时期和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土地关系的改变的性质作了大段的评注。马克思不同意柯瓦列夫斯基把印度在上述时期中发生的土地关系上的变化看作“封建化”。这表明马克思坚决反对把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作为唯一的尺度去衡量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反对把人类社会历史简单地机械地挤压到欧洲模式中去。
马克思通过文化人类学著作的认真研究,还发现在人类的形成过程中,由于各民族生存环境的独特性以及由于生产力和分工的落后,交往不发达而产生的闭塞性,使得各民族有着自身所应有的特点,表现出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存在的状况。马克思在阅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时,特别注意摘录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发展状况方面的资料。写道:“有一些在地理上与外界隔绝,以致独自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另外一些则由于外来的影响而混杂不纯。例如非洲过去和现在都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种文化交织混杂状态;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则曾经处于完完全全的蒙昧状态。美洲印第安人族系,和其他一切现存的族系不同,他们提供了三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期的人类状态。”这是马克思改造过的,并特别冠之以“不同的部落和族系的发展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471、283-284、269、781、242-243、331、466、512、211页。)的标题,它体现了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问题有了明晰的认识。
马克思在阅读摩尔根《古代社会》时,在注意各原始氏族组织形式相似性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各自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例如,在论及北美印第安人中的迈阿密人的母系氏族组织瓦解较早的原因时,他写到:“他们已经放弃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而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的氏族组织也在迅速消失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471、283-284、269、781、242-243、331、466、512、211页。)在论及古希腊人氏族组织的解体过程时,他写到:“在英雄时代,希腊部落都居住在有城墙围绕的城市中。人口的数量由于经营田野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而增长起来;需要设立新的公职,其职能要作某种程度的划分。新的市政制度发展了起来;为了占有最合适的领土而不断发生军事冲突的时期(到来了)。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贵族分子在社会中日益得势,这是从提修斯时代到梭伦和克利斯提尼时代的雅典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471、283-284、269、781、242-243、331、466、512、211页。)诸如此类的论述很多,都表明马克思主要不是从形态的类似上探寻共同规律,而是着眼于揭示各原始民族氏族组织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在《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所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注意记下:“在(原始)美洲,由于除骆马和羊驼以外缺乏可供驯养的动物而很少有畜牧业,而且畜牧业也只是存在于中美……,这种情况就使美洲这部分地区成为美洲文化的中心。因此,许多红种人不得不依旧从事渔猎;野生的某些食用(粮食)植物,特别是玉蜀黍,使他们有可能还在由游动的生活方式过渡到定居生活方式以前,就获得植物类的食物。这种情况,反映在他们的财产关系的发展中,阻碍着财产关系的个体化并使动产和不动产的或多或少受着限制的公有的古老形式保持了数千年之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471、283-284、269、781、242-243、331、466、512、211页。)这确实是特定的生活方式决定着特定的发展道路的一个生动例证。
经过深入的研究,马克思进而认为,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环境,因此就必须寻求适合自己个性的发展道路。即使在东方,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走不同的道路。1881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认为,俄国“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5、450-451、451页。)正是基于上述的考察,马克思进一步得出结论:“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5、450-451、451页。)此后,马克思在他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又指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5、251页。)这就是说,如果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俄国可以不经过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可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以逾越,这是马克思晚年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革命道路的设想,标志着马克思对社会革命道路问题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实际上,马克思是用社会革命的链条把东西方联结起来,从而架起一座从西方社会到东方社会、从东方社会到西方社会互相沟通的理论桥梁。(注:蔡金发《论东方社会革命与发展道路》,载《东南学术》2003年第6期,第73页。)马克思提出以俄国革命为“信号”,东西方“互相补充”的革命策略。这是一种特殊的共同胜利的思想,它包含着历史发展的递进与跨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巧妙结合与辨证统一。总之,马克思晚年通过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既应答了来自革命实践方面的挑战;又完善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注:详见拙文《历史之谜的文化求解——晚年马克思思想论析》,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9期,第2-6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高度评价马克思晚年的科学探索和理论贡献。因此,对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称谓,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将其称之为“人类学笔记”。
标签:摩尔根论文; 古代社会论文; 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人类学论文; 氏族社会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