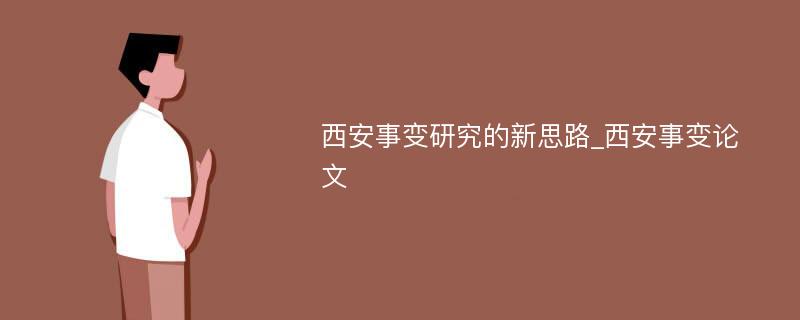
西安事变研究的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3-0149-08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的事变。西安事变震惊海内外,并“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结束了长期的互相厮杀,并化干戈为玉帛,再度携手合作,联袂投入到了抵抗外侮的时代洪流中,从而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坚实基础”①。西安事变的真相经过70年来学人的研究已经明晰,但对一些当事人的评价则相差甚远。比如对张学良的评价就很不一样,中共的周恩来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挽救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他说:“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②。国民党的秦孝仪则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功罪,至今尚未完全论定”③。还有人认为,“西安事变使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侵略提早进行”,“张学良的罪过实在是太大了”④。本文拟就西安事变和评价张学良等当事人,在综述各方研究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目的在于求教,并无强人就已的意图。
一、关于西安事变的评价问题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由多种因素的作用,逼迫出来的。
首先是日本侵略加剧了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起初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须安内”政策,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1931年9月28日,北平各界240多个团体共20万人举行市民大会,张学良对于北平市民大会提案提到应积极对日宣战时表示:“积极对日宣战,乃国家大事,当转达中央,想蒋主席亦必以国民之意见办理”。又说:“事前为防止日人挑衅,故令其取不抵抗主义,此可证我方之酷爱和平也。现在军队已至相当地点,诸事均听命中央”。尽管张学良自有苦衷,但他表示:“个人无论地位生命,皆可牺牲,但决不做卖国之事”⑤。可见,“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属于不得已而为,但也表明无论如何他不会卖国。随着日寇的进逼,张学良感到“学良守土无方,罪行山积”,对不起国人,表示要“与中央筹计妥善应付办法。许身为国,宁计其他,一息尚存,誓与周旋,大敌当前,愿与共勉”⑥。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虽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但人不在东北,而是“驻在北平主持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首领,执行不抵抗主义很快丢掉了东北,他难辞其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当国人对此政策责骂和谴责时,则把不抵抗的罪责全部推给张学良,并乘机贯彻排除异己来削弱东北军的政策。结果张学良代人受过,三降其职直至被解除兵权,心里自然不满。1931年11月16日张学良被免去中华民国陆海军空军副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11月20日,张又被免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改任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1933年3月12日张又被免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从此张学良则下野释兵权降为“平民”。东北军在日寇的军事进逼以及政治诱降下由近40万人下降为25万人。张学良被国民指斥他为卖国主义者。他虽强调“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不统一不能抗日,并解释“我姓张的诸事均是愿意自己干,如有卖国行为,你们将我杀死,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⑦。虽然他对东北失守作了解释,但无法冰释东北军将士的怨言和由此带来的悲伤。
其次,是东北军不愿追随张学良剿共,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被日军炸死,他又由于执行剿共和不抵抗主义带来的地位和名声的流失,其苦闷心情有口难言。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下野,4月11日离开上海出国考察。1934年1月回国后继续追随蒋介石“剿共”,1935年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这个时期蒋介石对张学良极为信任,张对蒋也顶礼膜拜,听从指挥。正如蒋所言:“余对张(学良),尝念其17年(1928年)自动归附中央,完成统一之功,因此始终认其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当蒋介石将西北国防重地全权给张时说:“望尔能安心作事,负责尽职,以为雪耻救国之张本”⑧!后来,张学良的思想发生变化,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不能简单的以道德如何作为判断。过去人们一般都将张学良思想的变化说成是由于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父亲张作霖,与日本有家仇,以及对蒋介石要他专门“剿共”、不抗日不满;也有人解释为张学良受到共产党的拉拢、煽动思想发生了动摇。“九·一八”事变,使由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从民国时起经营的奉系军阀,以及东北军的损失和分裂,张学良自有他的仇日情结。尽管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追随蒋介石执行“攘外必须安内”政策,但他毕竟与投降派不同,他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对日寇侵略造成的家仇国难,耿耿于怀。此外,东北军分裂,大部追随张学良在鄂、豫、皖“剿共”的东北将士,既失去了家园,又由于“中国人打中国人”损兵折将而对张学良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如果继续剿共不抗日,必然众叛亲离,因此,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思想产生既是时局变化的结果,也是东北三省丢失后,东北军将士要求联共抗日思想的体现。正是在军事上受挫和心理上陷于苦恼的张学良,由于受到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所影响,才有西安事变的发生。
再次,蒋介石对张学良的逼迫,使张不能容忍。东北军将士一致要求张学良停止内战,抗日复士。张学良在极端的苦闷之中,不得不考虑与中共商谈停战⑨。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一直追随和服从蒋介石,但由于东北军将士要求抗日,停止内战,以及不愿跟随蒋介石“剿共”毁灭自己。张学良虽没有放弃“剿共”的主张,但不能不听从东北军将士的劝告,产生联共、联蒋抗日的思想。由此张学良与蒋介石发生政见分歧。蒋主张“安内攘外”,张主张“攘外安内”。张屡劝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毫无结果。直至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前,张还和蒋争辩。张慷慨激昂地说:“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蒋又是勃然大怒,厉声训斥道:“你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年轻无知!”张学良怒目反驳蒋介石,“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你再一意孤行,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袁世凯第二!”蒋拍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这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蒋介石对张的苦谏无动于衷,骂他“竟敢犯上作乱”⑩。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他当时出路的唯一选择。如果他继续执行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原东北军的将士已说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而是要求全体中国人先打日本侵略者,执意剿共必然众叛亲离,变成孤家寡人。如果不执行“剿共”计划,蒋介石又认定他受共产党迷惑,“犯上作乱”必受惩处。所以,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然而,张学良扣留蒋介石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要他改变剿共不抗日或消极抗日的政策。只要蒋答应抗日,仍拥蒋作领袖。所以,“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对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向前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所做的最大贡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毛泽东说“成了时间转换的枢纽”。张学良说“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由此中国由内战转化为和平,国共两党由分裂转化为合作,并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1)。
对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和结果本已十分清晰,然而70年来围绕西安事变对张学良的评价则成为海峡两岸国共两党和文人学者争论不休和分歧最明显的一个问题。
据台湾李敖著《蒋介石与张学良》文中所披露,“国民党一谈丢掉大陆的原因,就赖别人,从张学良到马歇尔,等等等等,无一不赖。以赖张学良为例,国民党钦定的历史与宣传,标准本说法是中共‘流窜’到陕北后,本来已经完蛋了,因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局处陕北一隅的中共党徒将全被消灭”(12)。“西安事变使中共死灰复燃,最后坐大占领了大陆,国民党才来了台湾。所以,一切祸源都是张学良惹起来的,一切都怪张学良”(13)。张学良在1955年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也说:“西安之事,言到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讨商。事变以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14)。这与大陆中国共产党和学人对张学良的评价相去甚远。
近年来,台湾学者依据蒋介石的档案,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及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宋子文专档”、“张学良及张赵一荻文件”进行研究得出的一些看法,对于研究西安事变,以及评价张学良与蒋介石给予很大启发。比如,邵铭煌先生在《暂别南京:西安事变后蒋中正先生之进退出处》大作中,虽然对西安事变“蒋先生遭部属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为名挟制12天,酿成一场政治风暴,身心备受前所未有之煎熬。事变虽然和平落实,剿共工作却功亏一篑”,表示惋惜。然而,他说到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回南京,因行为触法,接受司法审判,判处10年有期徒刑,经蒋呈请特赦,后交由军事委员会管束。邵先生还说,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被送至溪口,安置在武岭山一处小筑,开始此后的幽居岁月。邵先生说张学良当时“过得相当惬意,不似外界传言之凄惨”。邵先生文中还引蒋氏日记,蒋称“张恐以残杀为能、以叛乱为荣之恶风,非彻底消弭,不能复兴民族”。并以所谓宽宥杨虎城“仍回西安,不追其既往”,表示对杨虎城的宽大(15)。真相果真如此简单吗?半个多世纪,蒋介石为了管住张学良,从浙江溪口关到安徽黄山,从安徽黄山关到江西萍乡,从江西萍乡关到湖南郴州、沅陵,从湖南郴州、沅陵关到贵州修文,从贵州修文关到台湾新竹、北投。在国民党逃到台湾来以前,谁也见不到张学良(16)。此中的情况只有张学良才知道,而且杨虎城在蒋逃到台湾之前也被特务杀害了。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都希望张学良将真相讲出来,但非常遗憾,张没有能做到,所以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诚如吕芳上先生到美国查阅“宋子文专档”及“张学良及张赵一荻文件”后所说:“至于张学良档案。个人说句真心话,是有些失望”。“大家所关注之西安事变,其实在张档内并无太多资料可资说明”。吕先生还说“西安事变之后续发展,不管在张学良档案及宋子文档案均可以看到,宋子文与蒋夫人对张学良非常照顾”。“这也牵涉到一个问题,张学良后来遭管束半个世纪,是否令宋子文及宋美龄心中有所挣扎?从张档中有几封宋子文写给张的信,表示他不止一次要求并希望蒋先生还给张自由,但最后都无结果。我们大约也可推测到宋子文在西安事变前后,在口头或许允诺张在事变后的自由,但未料到要管束那么久,心中对张多少有些歉咎的感觉”。吕先生又指出:“端纳于1947年过世时,蒋夫人写了一封很长的英文信给张学良,叙说端纳过世之情景。……不过即使是从两个档案来看,仍未透露太多相关西安事变的讯息”(17)。吕先生的分析较为合乎情理,正因为如此,张学良到台湾后,国内外传媒记者访问他,问到西安事变时,他总是怕给别人“带来麻烦”,“缄默50余年”(18)。并强调:“此事我不愿说太多,外边发表的也多,大家也差不多都知道这些事情。我不是不愿用语言伤害到他人。这件事留给历史去评论吧。它爱怎么评就怎么评,事情清清楚楚摆在那里”(19)。在西安事变50多年后,张学良开口说话,说:“蒋总统对我很好,他保护我”。为了证明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不错,还说他在蒋介石故去时,写了“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作私人的吊唁。还说:“蒋介石故去时,还没入殓,宋美龄叫秘书带他去与蒋的遗体告别”。张学良说:“对于这个情形,外头人很少知道,只有蒋夫人,还有蒋经国知道”。由此看来,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很可能如张学良所说两人的关系好象自己的骨肉一样,可是政见之争却好象仇敌一样(20)。
张学良是个悲剧人物,他干了对国家民族有益的西安事变,但一直未得另一部分人理解。他被蒋软禁了半个多世纪,本来对蒋介石要追讨一个是非对错,但张到台湾后,为了讨好蒋,在自述中吹捧蒋对他“爱护周至,宽严并济,公私两全”,使他心悦诚服。张虽说他与蒋介石之间只有“政见之争”,私人关系还不错。政争也有一个是非对错,但有的人就不认为蒋介石是错,好似张学良失掉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自由,是他应得的回报。暂不管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恩与仇,但诚如郭冠英先生的文章《张学良——主恩天高厚》所言,张自己对自己的行动应有个估评,但到了晚年还不将事实的真相告知世人,这本身就是错。张学良常说:“上帝那有本帐”,但他不愿讲出来伤人,其实他很想讲,常欲罢不能。可见,张学良也是个两面人物,诚如唐德刚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是Nothing。张学良有爱国心,但做事不认真,‘春性大发’常误正事。做英雄不够,但他冲冠一怒,却改变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的历史”(21)。所以,我们对西安事变要有一个正确的或合理的说法,对张学良也要分析,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有关人物的评价问题
西安事变发生后,对蒋采取什么态度,国共两党之间都有两种声音。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当日,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日将蒋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22)。中共中央接电后,张闻天(即洛甫)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初步商议,决定应张学良之邀,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次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张闻天针对会上“审蒋”、“除蒋”,以及“以西安事变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他说:“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这次会议未能作出明确一致的方针。12月19日,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张闻天在发言时说:“我们上次开会至现在开会已有6天。在6天中,这事变的现象与本质都[显得]更充分,所以,我们今天的方针,比前次是更进步的”。接着张闻天又分析事变发展的前途指出:“这次事变的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张闻天强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并批评了“审蒋”的口号,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对于蒋的处置,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指出中共的方针是“进行和平调解”,同时在军事上“以防御战斗反对内战”。最后张闻天发言指出:对于“苏联的舆论(23)[是]应该解释的”。他坚决反对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立场。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一是对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这是中共中央公开明确表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文件。另一个文件是由张闻天起草对中共党内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具体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任务,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共产国际书记处来电,指出,共产国际同意中共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冲突(24)。可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是中共中央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及时做出的决定,并说服共产国际改变态度,为周恩来等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然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是单方面能解决的。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蒋介石的亲属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的态度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以及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从上海到南京到洛阳到西安的频繁活动,并对何应钦主张“讨伐”西安加以制止,并通过张治中争取冯玉祥一起同情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主张的支持,西安事变便不可能和平解决(25)。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它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但也不尽如一些人所说,蒋夫人“以其人格、智慧、坚毅,特别是以其道德勇气,感动了张学良,并得到张氏的信任和尊敬,是解决这一事件的决定性因素”(26)。宋美龄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应该肯定,但也不是她一个人可以主宰得了当时的形势。
其实,现在国内外的学者都明白,如果不是周恩来利用他的智慧和各种手段在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同宋美龄、宋子文和端纳的多方周旋,并亲自会见了蒋介石,并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反复征询各方得到各方的承诺和协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绝对不可能那么迅速。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所起的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即将他草拟好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报稿,交给刘鼎急速发出(27)。随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邀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共同处理扣蒋的善后事宜。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告“文寅电悉”,“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28)。周恩来临危受命,率中共代表团于12月17日晚上到达西安,并在张学良公馆与其谈话到深夜。张学良认为,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意见。随后周恩来就同南京派来的端纳以及随后而来的宋美龄、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事件的有关事宜,最终与蒋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协议。12月25日放蒋回南京,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29)。可是,12月26日,蒋介石一行乘飞机回到南京,即授命陈布雷起草《对张杨之训词》,将事变的和平解决归功于主事者受蒋“精神之感召”,只字不提和平解决事变各方的努力。1937年元旦,蒋介石在溪口请陈布雷为他作《西安半月记》隐瞒事实真相(30)。1937年6月南京正中书局出版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西安半月记》只字不提周恩来,《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提到见过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李云汉先生在有关文章中说过,这个“有力分子”,实则周恩来其人(31)。这两本书很明显都带有为蒋介石辩解的情感因素,宋美龄在回忆中,说西安事变是“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决不能把它当作“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的平息所可比拟,因为它“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她表示要把其中的事实“准确明了”地表现出来,但又说要做到这点固非易事,只有“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然而宋美龄并没有能排除个人情感,所以她在回忆录中所陈述的“西安事变”的经过,对和平解决的事实与真实情况仍然相去甚远(32)。所以,正如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所言: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和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对事实的真相,自然都有所删除(33)。
至于周恩来等人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所起到的关键的作用,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郝建生编著的《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黄修荣著《国共关系70年纪实》等书都有详尽记述,这里不再重复。
应该说,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70年,事变的前因后果大致说来是清楚的,但对西安事变和相关人物的评价则不尽人意。为了反映真实的历史,给予真实的解读和评析,参与其事的各方都应做真实的回忆,但由于参与其事的各方没有将准确无误的事实告知世人,这就为学人评论这段历史和人物增添了许多麻烦。然而,70年来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虽观点不一,结论不同,但评判西安事变是历史问题、学术问题,较为客观地评析和解读西安事变也存在某些共识,我们应该做到尽可能客观,说得合理些。
三、西安事变研究的新思考
首先,西安事变对中国所起的作用,过去由于国共两党的对峙、对抗,从各自党派的立场出发,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同的。这在当时也是可以理解的。究竟是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和民族利益,还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党派的利益呢?应该是后者,不是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日益尖锐,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发动侵略中国战争,妄图灭亡中国的情势下,阻止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不仅是救国的需要,也是民族振兴和生存的需要。所以,在当时,争取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这不仅是符合国家、民族利益,也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的要求。在当时为了抗日争取蒋介石停止剿共,所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而中共在西安事变后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也是正确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采取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主张,毫无疑问也是正确的。也正因为这样,才有后来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才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多种因素造成,但这个解决办法是理性的、正确的,因为它对中国的政局发展和抗日战争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对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要作积极的正面的评价,如果否定西安事变对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其次,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都以悲剧告终。有人指责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助日本侵略中国是造成日本发动卢沟桥“七七事变”全面侵略中国的原因,实在是倒果为因。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不仅结束了10年内战,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而且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有功于国家、民族历史的事件,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说明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是一位有骨气的中国军人,但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被蒋介石监管了半个多世纪,杨虎城也被杀害,献出了生命,这是一桩不仁不义的冤案。如果70年后的今天对此还不能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共识,给予张、杨一个公正的结论,这是历史学界的一大缺失,也是历史学者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再次,张学良本是国民党员,他发动“兵谏”,拘禁本党的领袖蒋介石,这原是国民党内部的事情,但因为中共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因此带来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所以中共虽然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无关,但因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因此西安事变对中共也有影响。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虽有人主张“审判蒋介石”,“除掉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对抗,但中共中央及时做出不审判蒋介石、不杀蒋介石,只要蒋答应不再剿共,决心抗日,就拥蒋作为全国抗日的统帅。这个决定对中共来说,既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也争取到社会的同情,为国共合作抗日创造了条件。国共两党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政党,而且前后都曾是中国的执政党,对中国社会都发生过影响。虽然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国共两党仍有共同合作的政治基础,有实现中国统一和复兴中华的共同使命。因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需要反思,都需要总结经验教训,这是目前国共两党在追忆和纪念西安事变时我们应该记取和反思的重要问题。
注释:
①付建成、李云峰撰:《西安事变》,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52页。
②参见郝建生编著:《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③④参见台北:《近代中国》杂志,2004年,第158~159期合刊,第221、223页。
⑤⑦《张学良对北平市民大会提案的解答》,天津:《大公报》,1931年9月29日。
⑥《张学良复上海抗日救国会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第171页。
⑧原载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翻译组:《蒋介石秘录》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4页。
⑨关于张学良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听从东北义勇军将领杜重远等人的劝告,采纳“联共、联杨(虎城)、联盛(世才),实现大西北大联合,抗日报国的建议。可参见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全传》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41~442页。
⑩原载居亦侨著、江元舟整理《跟随蒋介石十二年》,参见齐甫编:《名人眼中的蒋介石》,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3~124页。
(11)参阅周毅、张友坤、张忠发主编:《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第33~34页。
(12)据李敖注,这是于衡在《张学良访问记》(1981年9月18日《联合报》)中说的话。参见李敖著《蒋介石研究》5集,北京:华文出版社,1988,第47页。
(13)(16)参见李敖:《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一——别赖张学良了!》,《蒋介石研究》5集,第47、93页。本书收录有李敖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就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以及台湾国民党人对张学良的评论提供了不少事实和信息。
(14)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1964年7月,台北《希望》杂志创刊号登载时标题为张学良著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共9段27款。台北《民族晚报》迅即分段转载,但第二天就奉令停载,《希望》月刊也被勒令停刊,并把已发行的创刊号“悉数”收回,据传是因为张学良提出了抗议,但其内情至今不明。后来,台湾发行的《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也发表了摘选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份量比《希望》月刊少一些,但主要内容大致相同。据司马桑敦考证,此篇文字是张学良写于1946年11月之后,但实际应在1956年年底之前。张魁堂《张学良在台湾》一书对此文真伪作了详细的剖析。另据郭冠英在《张学良在台湾》一书,考证本文是1955年张学良给蒋中正的复信。引文原载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381~391页,参见《张学良文集》下卷,附录(一)“张学良回忆录”,第545页。
(15)邵铭煌:《暂别南京:西安事变后蒋中正先生之进退出处》,台北:《近代中国》杂志,2005年,第160期。
(17)吕琳、任育德:《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学术座谈会记录》,台北:《近代中国》杂志,2004年,第158~159期。
(18)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年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3页。
(19)《张学良接受美国之音访谈纪要》(1991年5月),《张学良文集》下卷,第521页。
(20)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96~97页。
(21)参见郭冠英:《张学良——主恩天高厚》,台北:《近代中国》,2002年,第149期。
(22)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第441页。
(23)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发表社论称西安事变是在“敌人指使下”阻碍中国的统一,接着《消息报》12月15日社论指责了张学良是“假借反日”,实际上“有利于日本”。12月17日《真理报》又发表国际评价,进一步提出事变“纯为日本在中国之新阴谋”。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
(24)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年谱》,第158~163页。
(25)参见李云峰:《西安事迹史实》第257页;《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48~150页;熊宗仁著:《何应钦传》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2~377页;林家有、李吉奎著:《宋美龄传》,第137~145页。
(26)秦孝仪:《中国跨世纪历史的伟大心灵捕手——蒋夫人》,台北:《近代中国》杂志,2000年,第134期。
(27)《金凤玉露——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5部),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25页。
(28)《金凤玉露——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5部),第426~427页;又见《张学良年谱》,北京:文献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132页。
(29)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24~334页;郝建生编著:《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第166~248页。
(30)罗炯光、向全英编著:《蒋介石首席秘书陈布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2~77页。
(31)李云汉:《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又见李敖:《蒋介石研究》5集,第80页。
(32)王亚权编:《蒋夫人言论集》上集,台北:上海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第53~89页。
(33)厄尔·艾伯特·泽勒著,徐慰曾等译:《端纳传》,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324页。
标签:西安事变论文; 杨虎城论文; 张学良论文; 宋子文论文; 我的东北军论文; 国共内战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西安南京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宋美龄论文; 张闻天论文; 东北军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