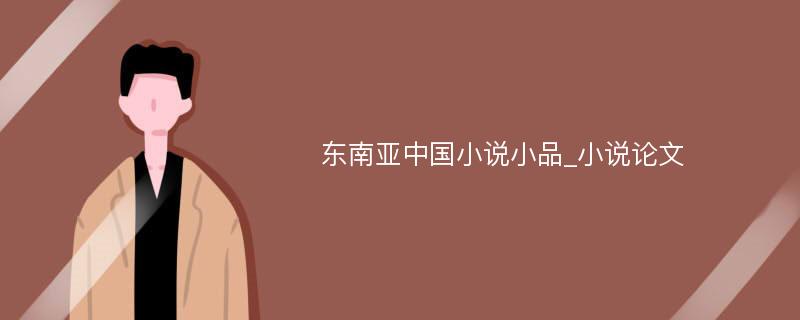
东南亚华文小说素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素描论文,小说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人向东南亚发展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王莽新朝。至晚明和前清雍乾两朝,随着中国小说的成熟定型,描写华人沟通东南亚生活的作品,已具鳞鳞爪爪。如明末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中有《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叙苏州文若虚家业破败后到东南海外经商,在吉零国卖橘得千金,后在荒岛拾得鼍龙壳卖与波期胡,逐成闽中富商,重立家园。又如明末清初陈忱《水浒后传》,记梁山好汉李俊、阮小七等在登云山饮马川重新聚义,杀童贯、高俅、蔡京,奋起抵御金兵,后渡海至暹罗建立王业。这些作品中有交通海外的经验,有“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理想,当是古代华人移民的传奇和英雄传说。
晚清,尤其是梁启超倡导“小说革命”之后的晚清,小说的重要性受到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怀,“新小说”与“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相提并论。小说结束了在史部和子部之间流放的状态,从“述杂事”、“录异闻”、“辑琐语”的残丛小道跃升为“想象”的文学,并以高度的精神自觉参与了“改良社会,开启民智”的过程,加之外风习染和新闻、印刷事业的日渐兴盛,小说创作繁荣高涨。据阿英《晚清文学史》统计,当时成册的小说达千部以上,其中描写海外华人生活的作品如佚名的《苦社会》,“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且“有字皆泪,有泪皆血”,可视为近代海外华文文学代表之作。辛亥革命期间,大批革命党人在香港及南洋各地创办各种报纸杂志,除宣传革命言论之外,多增辟小说剧本等文艺专栏,开东南亚华文小说创作之源。晚清的小说高潮,不仅为“五四”白话文新文学运动铺垫了道路,也为东南亚海外华文文学的萌发筑起了畦垄。
“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也直接启动了东南亚华文新文学的发生。从本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东南亚华文文学都笼罩在以“五四”新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精神之下。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在论述中国文学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影响时曾经说到:“马华新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受到中国新文学的深刻影响。不但马华新文学的诞生,是渊源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其后的发皇滋长,也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一九二五年以后的文学团体的繁兴,一九二八年以后的新兴文学运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间的大众语运动,一九三七年以后的抗战文艺运动,以及由此生出来的救亡戏剧运动,通俗文学运动,文艺通讯运动等等,就都是各该时期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潮振荡辐射的余波。在作者作品方面,中国作家的创作风格,文学技巧等等,也常常成为马华作者吸取滋养的对象。如鲁迅的小说、杂文;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等人的诗,就都有许多人在摹仿学习;而本地作者之间在这方面倒很少有其继承的关系。”[①]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新马华文文学,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都是如此。比如,菲律宾文艺评论家王礼溥就曾指出,菲华文艺作品,在酝酿时期(指1928—1950年),深受鲁迅、巴金、艾青、徐志摩、朱自清、许地山、冯承植、卞之琳、臧克家的影响。[②]
本世纪前50年,中国文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大致有以下一些特点:
(1)在“五四”新文学所承担的思想革命、科学民主、人道主义启蒙、个性解放、人格自觉、教育民众、唤起民众、反帝反殖、救亡图存以及写出全民族的普遍深潜的黑暗“以揭出痛苦,引起疗治”等多种任务中,东南亚华文文学偏重于接受最后一项任务。
(2)因而在题材上,未脱描写“工厂之男女,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商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以及一切“家庭惨景,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等社会生活范围,强调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来“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
(3)在创作观念和方法上,于“五四”新文学标举的“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中,侧重“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在表现“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中,不取或次取以美为主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强调“以真为主,美在其中”的“为人生的艺术”一派,即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一派。
(4)无论是在近代,或是在“五四”与“五四”之后,社会革新与救亡图存是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因而在小说的功能上,往往将小说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和宣传功能置于首位,而小说的艺术功能和审美功能相对受到轻视。东南亚广大地区的社会情境与中国相似,加之海外华人在社会、文化、政治、思想上与中国的紧密血缘关系,小说的创作在时间上常步中国小说之后,在作用和力量上,未出梁启超所说的“熏”、“浸”、“刺”、“提”格局;并且,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几乎是以报章为载体,因而这一时期的东南亚华文小说,一方面汲取了“五四”新文学精神,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同时又在某些方面传留了近代小说遗风。
(5)从作家队伍组成来看,无论是旧文学,不是新文学,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基本骨干都是因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原因流落到东南亚地区的中国知识分子。古代,如宋遗民、明遗民;近代如太平天国、戊戍维新、辛亥革命的活动家和革命志士以及部分清遗民;“五四”之后,中国国共两党长期的政治斗争,中经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许多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如郭沫若、郁达夫、巴人等,都直接参与了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活动,创办刊物,扶植当地作者,促进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繁荣。
我曾在《〈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碎读》一文指出:“新华小说,以现实主义为正宗,苗秀、姚紫时代,曾将这一派小说的水平推上高峰。大体来说,新华小说在内容上,集中于批判社会现实和写小人物生活命运两个方面,很明显,这种创作局面是受上代社会风潮和文学风潮的影响,尤其是受俄国批判现实主义、苏联革命现实主义和中国左翼作家的现实主义影响,并将这一影响维持至今”[③]。我想这种情况,不仅在新华小说中如此,在整个东南亚华文小说中亦然。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变化,始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末,小说创作出现了新的因素。这十多年间,中国社会疾风暴雨式的政治斗争已基本结束,海峡两岸已呈对峙;国际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已成明局;东南亚各国民族、民主、独立运动此起彼落。由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联系至为密切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开始与大陆的中国文学隔绝而受到台港现代主义文学风气的影响。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特点可作“三足鼎立”来加以形容。一方面,传统的现实主义仍积极发挥摹仿现实、批判现实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大批的知识分子纷纷从东南亚各地回到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遂使当地的文学迅速成长起来,自觉地承担起本地文学发展的任务。如果说,50年代中期之前,东南亚华文小说未脱中国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是中国小说在外土的移植,那么,50年代中后期之后,东南亚华文小说的“本土传统”逐渐形成主流,而“本土传统”一经形成,东南亚华文小说就有可能产生新的遗传基因,从而与过去那种“中国小说的外土移植”的“环境变异”状况区别开来。当然,这种变异明显地分为两流,一流表现为对本土社会与人生的关怀,注重的是小说的社会生活容量,方法上仍取现实主义一派,强调小说“写什么”,“为什么写”;一流则在关怀现实的精神之下,注重的是小说的艺术形式的革新,作品中出现了新的文体观念、新的叙述意识和叙述语言,方法上取现代主义一派,强调小说的“怎么写”,“怎么叙述”。从整个东南亚小说创作的情况来看,新、马、菲的小说出现的“现代主义”较多一些,而泰国、印尼等地则更为“现实主义”一些。
70年代之后,东南亚除局部地区(如越南、老挝、柬埔寨)陷于战乱之外,普遍地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迅速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结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逐渐从国家管理的指定性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在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超越了自然状态而形成科学的智慧管理的人类生存环境。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总体格局中,形成了整个人类共同和平发展以建设新的“地球村”的世界主义和全球观念。这些都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然而,与科学技术高歌猛进、商品经济主宰社会生活相悖的是,人文科学与精神文化受到严重的挑战。消费意识同时渗入自然与人类意识两大领域,对传统的道德观念、精神价值、生命意义和本文深度进行消解。在这种情势下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一方面顺应现代化的过程,出现了新的繁荣(尤其是在80年代),另一方面,现代化过程对传统的破坏,又使其出现新的困扰,在小说创作中表现为以下特征:
(1)多元化。多元化的积极表现是广泛吸收吐纳各种观点、各种流派、各种方法彼此之间互相溶合,积极“对话”,取消对立。小说创作队伍也迅速扩大,作家成份不象过去那样多限于知识分子,题材范围也不断拓宽,这无疑给创作带来了更大自由。多元化的消极作用是,既然每一元都是真理,因而也就没有了真理。作品在内容上便消除了现象与本质、深层与表层、真实与非真实的界限,以本文代替真理,以表述代替思想,从而取消了深度。
(2)通俗化,或称大众化。这是商品经济和商品社会的结果。市场经济培植了商品社会,也养育了消费的大众。没有永恒的商品,因而也没有关心永恒的大众。大众的消费以“现实”和“有效”为尺度,作为消费品的文学和艺术也就不再关心信仰、人生价值、人类命运等不能立见成效的非现实的精神问题。不要说大量的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满足人们的消费快感,即使是严肃文学也带有浓厚的通俗文学性质。而真正对“纯文学”保持忠诚的,只是极少数。
(3)保守化。我很难用准确的词汇来指称这种现象。我把“保守”二字拆解为“保护”和“守成”。就是说,“保守”,不能抱残守阙,食古不化,而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保护和文化守成。一方面,华文文学向居处地的文学传统认同,要求成为居处地本土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又努力向作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传统寻根,并且在艺术形式上向传统回归。70—80年代,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诗歌、散文、小说中普遍的“怀乡”主题,从家国之思——文化乡愁——精神还乡(寻找灵魂家园),都是这种文化“保守”的反映。这种文化现象不仅与盛行于东南亚的新儒家哲学思潮有关,更深一层的意义是,近两百年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和反现代思潮水火不容而又并行不悖,“保守”的文化态度,不仅是反抗现代化消极影响的武器,也是东南亚华人企图透过传统寻找新理想、新历史意识以获得新生存环境的武器,使他们能够在“不属于自己但亲切的土地上”落叶生根,并在落叶生根之后,获得更大的发展。
总的来说,华文小说创作在东南亚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40年代中后期至50年代中后期,第二个高峰期是70年代中期之后至今,两峰之间,呈鞍型发展。前一高峰期中,现实主义是唯一的一流;后一时期,现实主义仍为主流,却与其它流派兼容并蓄,争芳夺艳。不过值得清醒的是,后一高峰期中的作品虽然在文字、语言、结构、叙述等技巧上比前一高峰期中的作品有了很大进步,风格也比过去更有个性,但在主题的深度和精神品味上却并不比以前更有份量。多元化的自由导致无中心化和主观化,使许多作家失去对信仰和人生价值的尊重,失去对社会现实的关怀;通俗化和大众化在民主的气氛中,也容易使人们忽略崇高而敬奉平庸,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对文学的这些冲击,是不能漠视的事情。
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界经常讨论的一个题目是华文文学的危机问题。许多人将华文文学的危机归因于华文和华文教育的式微,而我认为,这只是外因,不是内因,根本的原因是来自作家本身。如果作家们不能对整个世界文学的潮流保持高度的敏感,不能象现实主义经典作家那样抱有改造社会的巨大热情,不能象现代主义精英作家那样对现代社会始终保持反抗和批判的勇气,而是认同现实,认同流俗,认同功利,认同平庸,首先就是精神的失败,就不可能生产出象样的作品。文学是一种信仰,需要作家有永不昏暗的批判眼光,需要作家坚持文学和自身人格的高贵与尊严,需要作家甘于清苦、甘于寂寞、甘于宁静。所谓“无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业”、“世情浮躁,只一个静字定得”,作家如果不能在纷扰的商业现代社会保持宁静和高贵,就不能在作品中表现人类战胜丑恶并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
与此同时,广泛讨论的另一个题目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如何走向世界”。这个命题是很好的命题,反映出东南亚华文文学要求不断成熟、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积极和自觉。不过,我认为,在“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上,关键不是如何“走向世界”,而是“如何”走向世界。照我的理解,一个语种的文学要走向世界,不仅在于这种文学向世界文学吸收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在精神上和艺术上向世界文学贡献了什么。华文文学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一样,已经受到世界的关注,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我认为,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华文文学对世界的贡献还只是体现在文化倾向和社会价值的意义上,而不是体现在文学和艺术的意义上。这一点,我们可以用魁北克文学即加拿大法语文学来作个比较。本世纪60年代之前,魁北克还处于一个被称之为“黑沉沉”的时代,笼罩在一种极为保守甚至倒退的政治社会体制下。按魁北克著名批评家吉勒·马科特的说法,那时的魁北克文学“没有任何令人惊奇的东西”,小说家“给人的感觉是从不为形式创新而动情”,不论他们写得如何文通字顺,智巧生辉,也不论他们是否卷入动词的狂热中,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恪守一般认可的写作技艺,不敢越雷池一步……除了极个别外,他们似乎对自己作品形式从不潜心锤炼。他们被一种原始表达需要所占据。”[④]60年代之后,随着魁北克坚定地迈入了现代化时代,魁北克文学以“静悄悄的革命”,摆脱了法国文学的传统,确立了自身的精神境界和新的价值体系,并以富于民族个性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表达方式,对“魁北克民族”特定的生存环境提出了“本质性的诘问”,表现出魁北克作为集体的命运。这样,魁北克文学不仅拥有了如布丽埃·鲁瓦、阿兰·格兰布瓦、安娜·埃恩等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而且从此结束了作为“加拿大法语文学”的边缘境遇和眩晕状态,成为一种新的民族文学进入了世界现代文学行列。我想,东南亚华文文学一定能在与魁北克文学极其相似的发展过程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和经验。同时我也感到,尽管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要缩短这一段距离,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尤其需要有一批以文学为生命的艺术天才的带动,但它毕竟有了近80年的经验并已生长成林,在这片茂密的热带雨林中一定会生长出一种新的生活价值观念和文学价值观念,推动东南亚华文文学冲破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为世界文学提供富于个性的艺术。
注释:
①(新加坡)方修:《马华新文学简说》,载《新马文学史论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1986年4月香港第1版,第19页。
②(菲律宾)王礼溥;《菲华文艺六十年》,载《华文文学》1991年2期(总第17期),第76页。
③《〈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碎读》,载《华夏》1992年6期(总45期),第35页。
④(魁北克)吉·马科特:《加拿大法语小说中的眩晕体验》,载《世界文学》1992年5期(总224期)第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