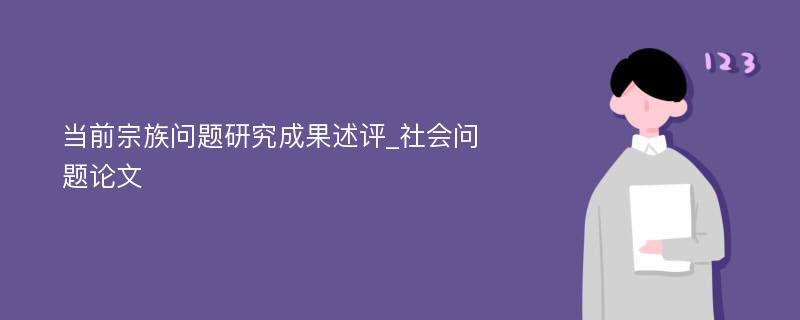
对当前宗族问题部分研究成果的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族论文,研究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力量陡然增长了。在一些地方,修家谱、建宗祠、搞祭礼等活动异常兴旺。农村宗族活动的泛起,牵涉到农村经济水平、农村宗族聚居“自然村”结构、农村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同时,由于政治控制能力削弱,有的地方出现了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社会秩序的情况,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问题。
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由于某种固有观念和观察视野差别的存在,不仅他们依据现状而来的对宗族活动和宗族问题的原因、特点分析不同,而且他们据此提出的针对策略也有不同,有些甚至截然相左。笔者考察了部分研究者的资料、文字,在比较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科学、客观、全面地描述当前中国宗族活动与宗族问题及其研究现状。
本文选用的资料、文字,大致来源于三个研究者(研究组):(一)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钱杭教授;(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华中师大课题组”);(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1994-1995)”《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研究组(以下简称“发展报告”、“人大研究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大体上代表了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较高水平。
一、当前宗族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及评述
宗族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根源的文化现象,在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中,它从未间断过。1949年以后,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由于社会主义政权的有力整合,宗族受到严格抑制和打击,但并没有绝迹。80年代以后,在对农村的社会控制相对松弛的情况下,宗族现象普遍复萌,并有蔓延之势。
宗族现象的存在毋庸置疑;宗族在农村的复萌也不是偶然。
钱杭1993年在《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学术季刊》1993年第4期)一文中列举了对宗族现象的三种解释:第一,社会体制目前还不可能担负起农村的所有功能,宗族作为一种功能团体就“有机可乘”;第二,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以后,农村的基层组织趋于涣散,集体已经不再构成依靠的力量,农民为寻求心理上的依靠,就转向宗族组织;第三,由于基层秩序的松散,违背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现象就处于无人管理的放任状态,于是宗族势力就利用这一机会发展起来。正如钱杭在列举之后所分析的,这三种解释,除第二种部分地描述了真实的图景之外,第一种、第三种解释均“似是而非”。事实上,钱杭在分析之中指出:“……中国农民,对宗族有一种‘本体性’的需求——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钱杭这段富有见地的分析具有人类文化学的意义。可惜他没有再进一步对“本体性”需求作科学概括、总结。他只是接着写到:“……宗族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还会取得相当大的发展,就因为它关注的主题,正是这个时代所失落的关于人类的本体意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原注:《丑氏嗣裔录》封面题语)’。”
钱杭在稍早的另一篇文章《亲族聚居现象与我国目前农村的宗族活动》(《学术季刊》1991年第3期)中论述了他本人关于宗族现象复萌的原因(条件):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结构——亲族聚居弱(无)控制发展。钱杭认为:“自然村落中的亲族聚居现象,是中国农村许多地区居处形式的突出特征,为农村宗族活动的发生提供了土壤。”钱杭分析研究了历史上和近现代农村的村落面貌,他把现代农村较普遍的亲族聚居形式分成三种类型:(1)由拟制血缘产生的单姓亲族聚居村落;(2)由联姻关系产生的双姓或多姓村落;(3)由地缘关系形成的双姓或多姓村落。他进而指出:每一种类型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一种宗族组织形态。钱杭在具体论述此三类宗族聚居现象与宗族活动的因果关系时写到:“在突出父权和夫权的原则下对亲族中的血缘亲属关系进行有意识的‘重组’,即形成宗亲范畴,是亲族聚居向宗族形态转化的关键。”但是,钱杭在该文第三部分指出:历史上的那种由封建国家保证的重组过程(即国家和伦理道德对父权和夫权的支持)自然已不可能再现,而当前农村中宗族活动的重组过程大体上是(在自然村结构普遍存在、亲族聚居现象继续发展的土壤里)又“以农村基础政权的削弱为条件”发生的。钱杭的这个观点是上述1993年文章观点的原型和基础。从其他一些研究者的文献来看,这种解释也是站得住脚的。钱杭还分析了传统资源——宗族现象不可能几十年间根本摧毁的事实。无疑,这是当前农村宗族活动发生所需的“物化的和智化的”条件之一。
如果说钱杭对宗族活动和宗族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为人们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明晰而深刻的解释的话,那么在此后的研究者中华中师大课题组则提供了较为客观、全面的原因分析。这些原因分析既承继前人也突破了陈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基于深刻广泛的社会调查。这一课题组的成果《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1995,武汉出版社)反映了这些内容。
华中师大研究者将宗族活动和宗族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以下四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第一,宗族聚居——宗族复萌的自然基础;第二,社会互助——宗族复萌的内在根据;第三,宗族意识——宗族复萌的催化剂;第四,农村基层体制的缺陷——宗族扩张的制度背景。可以看出,研究者不仅从客观方面——亲族聚居、体制缺陷,还以主观方面:社会互助——经济需求和宗族意识——社会心理层次进行了分析,(这其实是对钱杭“农民本体性需求”的某种明晰化和类别化),从而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实证研究结论。研究者在分析宗族现象“社会互助”原因时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族人互恤互助是宗族长期得以存在的社会合理性。”“人民公社体制把社会互助功能从民间私人组织中转移到公共集体组织,宗族存在的社会合理性被抛掉。”“在土地承包到户,集体经济解体的情况下,农民只能求助于社区私人团体,而宗族则以其血缘的亲近性而成为农民最好的选择。”研究者还援引两个重要的统计资料“经营中遇到困难时找谁”和“经营中得到帮助的大小来源”予以证明。(这两份资料表明:无论是在经营遇到困难时还是得到帮助时,向“血缘关系”的求助比例和“血缘关系”的施助比例均是最高的。)研究者在分析“宗族意识——宗族复萌的催化剂”时,将宗族意识作为一种传统的“观念文化”,并认为它“长期以来已深深积淀在人们心理之中,不像有形的宗族文化如宗族礼仪、族谱等那样容易消失”,它经过“长期潜伏”在人民公社解体、家庭地位突出、社会控制相对削弱的时候又“表面化”,“并通过旧有的宗族资源,如宗祠、族谱、旧宗族的骨干人员等,得到扩展,……。”(本段引用文字见《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第360至364页。统计资料也可参阅《中国农村家庭的变迁》,第91、89页,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
二、当前农村宗族现象的特点、表现分析及评述
基于人们总抱以不同态度的原因,研究者对某一问题的现状描述会有所不同。态度不可能总是客观的、不带主见的;而对现状的观察角度、描述方法、叙述话语的不同选择本身就是人类哲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不能超越的困境,所以“一个问题”不可能被完全真实完整地记录、描述出来,世界“不可能是一幅巨大的图画般的世界”(普特南·罗蒂,转引自《倘若我们有足够的世界与时间?》,《复旦学报》1997年第2期第95页)。对宗族问题特点、表现的分析、描述也是如此。
钱杭在《亲族聚居现象与我国目前农村的宗族活动》中分析宗族问题时,把他提供的宗族活动发生原因:以农村基础政权的削弱为条件、旧传统资源的作用列为宗族活动发生的特点。此外,在描述当代农村宗族问题现状时,他认为:“从整体上说还是低水平的。一方面,这些宗族组织一般很难有公开和严密的组织形式与机构;另一方面,宗族成员与宗族组织的关系也还比较松散,并带有一定的临时性质。”尽管如此,他同时也指出:“……其行为亦更具有随意性和破坏性”,宗族活动当前的表现特征为:相对松散的组织、缺乏远见、情绪化、盲目的破坏性”。
华中师大课题组的研究者根据其掌握的材料将当前宗族活动抽象为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宗族活动的理性化和非理性化倾向并存;其二,非实体化和准实体化并存。在分析理性化和非理性化倾向并存的特征时,研究者分别援引江西中部地区出现的有很强自我约束机制、观念的宗族和一些地方发生宗族械斗的事例进行了说明;在分析非实体化和准实体化并存的特征时,研究者指出了当前宗族活动的特点是松散性(无固定组织或无严密的组织),这与钱杭的分析是相似的。由于华中师大课题组的研究者站在维护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的立场上进行调查研究,所以他们从宗族的消级政治后果列举了宗族活动的三个主要表现:1、排斥公共权力,增加整合难度;2、侵蚀公共权力,使其变质;3、宗族势力恶性膨胀,破坏社会秩序。总体上说,无论是排斥公共权力还是侵蚀公共权力,都跟钱杭认识到的“以削弱基础政权为条件”的后果一致,都将“促使公共权力变质为族权、私人权力”,“长此下去,甚至可能导致政治体系在(农村)社区基础的瓦解。”(本段引用文字见《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第364至368页)
正是因为上述分析带有普遍性意义,并且这种普遍性具有强大危害性的缘故,人大研究者在“发展报告”中才措词异样尖锐地指出:“在一些地方,宗族势力已成为重要的地方势力……宗族活动恢复异常迅速……宗族势力的作用越来越大……乡村宗族势力的蔓延有可能发展为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研究者在列举宗族势力的特征、表现及严重影响时这样写到:“它常常以宗法作为处理各种关系的准则,甚至以宗法替代党纪国法,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其主要表现(及后果)一是破坏计划生育政策,二是挑起宗族之间的争斗,三是阻碍公务执行。”(本段引用文字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1994-1995)》第331、332页)
笔者认为,上述对宗族活动和宗族问题特点、表现的分析,在持消极评价的方面,三种研究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均从现实描述出发,指出了宗族势力的落后性、破坏性、不合理性。三者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并可以认为,华中师大研究者的分析因占有资料详尽较为全面、可信,人大研究者则由于宏观研究的局限和缺乏材料实证稍嫌偏颇。但是,这两个研究者都没有把他们的分析再深入追究下去。而钱杭显然作了更深入的追索,他在《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结论”中曾设想:“宗族……可以……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契合”,也就是说,农民对“本体性的需求”并由此导致宗族复萌现象具有合理性、合现实性的一方面,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思考,笔者将在后文中再作必要的说明。
三、宗族问题应对策略的比较分析
由上述研究者对宗族现象产生原因、特点和表现分析的不同可以得知:他们针对宗族活动与宗族问题主张采取的策略必定也不同。
人大研究者由于稍嫌偏颇的分析导致他们应对的态度和策略均有些急躁。如“发展报告”认为,一方面,如果政府和社会各界不予以高度重视,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就会严重干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发展报告”写到:“有效地解决乡村宗族势力问题,涉及许多方面,不宜粗暴干涉,但也决不能掉以轻心。”这近乎于在说:宗族问题是一个“烫手的山芋”,问题很严重,但却十分棘手。随后,研究者提出三条对策。概括地说:(对宗族问题)一要高度重视、重点来抓;二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维护基层组织的合法权威;三要采取积极引导、法制制裁的两手处理办法。这些对策比较宏观、抽象,具有一定政策导向作用。(本段引用文字见“发展报告”第331、332页)
华中师大研究者在《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中没有开辟章节专门论述解决宗族问题的政策、办法。但这不等于说他们没有提供。第一种可能,可以把该书第三编“促进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思路和对策”所涵盖的前十一个章节作为宗族问题全面而细致、深入又具操作性的应对策略。因为正如人大研究者指出的“宗族涉及许多方面”,所以解决起来不能“牙痛医牙”,必须有全方位、多角度的系统的思路和对策。通读华中师大研究者的著述,他们确实高度负责、力所能及地提供了解决包括宗族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如:完善农村政策、健全管理体制、促进经济进步、创造文化环境提高农民素质、重视社会发展、贯彻民族宗族政策、加强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实施依法治农、依法治村、实现村民自治等。第二种可能,根据研究者对宗族问题产生原因特别是特点、表现的分析,可以在该书中找到相应对策。如针对宗族势力排斥、侵蚀公共权力的倾向,他们提供了加强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的对策;针对宗族势力破坏社会秩序的特点,他们提供了依法治农、依法治村,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等对策;针对农民“社会互助”的需求,他们提供了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对策;针对宗族观念文化的影响,研究者们十分有见地地指出,应当建设以村户为载体形成现代村落文化;等等。总的来说,华中师大研究者们提出的思路和对策,不仅具有政策导向功能、细致、全面,而且具有相当的实践可操作性。
四、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置于现代化视野的思考
“现代化”这一概念,它既标榜同传统背离,其实也在同现实背离,它还同将来相背离。因为一则它是人们自己设置的宏伟目标,二则它的过程中的每一重大步骤,都是对过去人们设定目标的否认。尽管如此,现代化的魅力太过巨大,以致于诱惑着人类在现代化潮流中晕头转向,惘然迷失了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根?”
——或者,由现代化潮流中“最愚昧、最无知”的农民的这种“本体性”追问,正牢牢牵住了现代化人类最敏感而痛苦的神经,它才这样震聋发聩。
农民由“本体性”追问而引发的“宗族问题”同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现代化潮流是相悖的吗?
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人们对于宗族问题的历史命运持几乎一致的观点:宗族作为一种特殊的血缘集团,因其结构与功能的狭隘性,与社会的现代化目标很难相容。不仅倍受落后、封建困扰的中国人这样认为,远比中国人现代化的西方人也这样认为。中国人总是习惯上对农民选择宗族为自治性组织形式持批评态度。因为,“生产水平前所未有地增长了;资源总量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自然屏障前所未有地突破了;社会调控前所未有地强化了;文化因子前所未有地更新了;生育制度前所未有地变化了”(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宗族现在的存在理由已经没有了;因为,“传统的宗族组织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内控力的血缘群团,无论是它的价值标准,还是它的组织形式,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不相符合”(钱杭:《关于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93年第4期)。概而言之,宗族既没有存在理由也失去存在价值,它应该被历史淘汰;假如存在,即是不合理的、落后的。西方人的态度或者还干脆些。美国研究农村问题的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在《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中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没有丝毫宗族痕迹的前景图:“农民们被卷入世界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国家的政治轨道之中,正在丧失其半自主的地位。……农夫的桃花源被卡车与飞机碾得粉碎,他们的视野开阔了,教育则使他们陷于更痛苦的失望之中。由于大众传播,他们的文化也接近了全民的文化。……城市已扩展到乡村,而乡民也进入城市。在货币经济中受到付薪劳动的诱惑,不发达国家中农村的高出生率,以及农场的合并与机械化,所有这些合在一起,使农民离开不能再养育他们的土地而涌入城市。……”这里描述的发达社会中,不仅没有宗族的影子,“甚至连农村和农民本身也将在现代化的潮流中面临逐渐消亡的命运”。(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二是现在的宗族不同于传统的宗族。尽管我们目前无法在中国大陆找到不同于墨菲描述的现状,(这不是因为没有发现,而是因为目前的经济状况和技术水平还没有使其产生),但可以找到中华文化圈中广义中国人的例证。钱杭在《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中指出:在海外汉人社会(经济发达社会)中,宗族仍然成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据1982年统计,(1)新加坡253万居民中,华人占76.8%,总数达192万,其余为马来或印度裔居民。但只有华裔居民才在本族之内,另行再分出宗族组织;(2)新加破汉人现有224个姓氏,其中的96个姓氏,拥有经正式登记成为合法社团的宗族组织共173个,占汉人姓氏总数的42%;(3)新加坡汉人中,只有5%人口所属的姓氏没有宗族组织,而另外95%的汉人均属于某一宗教。如钱杭的分析,新加坡汉人对宗族组织如此地热衷,显然不是用社会资源总量的高低与否和社会调控形式的有效与否能解释清楚的。尽管中国人与西方人过去产生宗族的原因可能是类似或相同的,但在过去的原因消除以后,中国人并不象西方人那样,一下子消解结果。唯有的解释可能是这样的:中国人的文化、文明与西方人的文化、文明不一样;“中国人的民族性中对宗族有‘本体性’的需求。这种需求可以转移或被压抑,但不能被替代或取消。”(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
现在的宗族不同于传统的宗族,这是人们都能意识到的、但大多数人没有深究的问题。过去的、传统的属于历史,不属于现在。但现在的呢?钱杭在《关于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研究的几个问题》第一节中指出,当代中国农村出现了一种与“传统的”宗族很不相同的宗族类型。“这类宗族虽然……与历史上的宗族形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这主要是出于提出今日宗族存在的历史依据(借口),和使宗族传统中的某些积极性的因素在适应今日社会生活条件的前提下得以保存,……。”他进而注意到:在一些典型的地区,在宗族组织主持的活动中,宗族色彩与有意识地加进的法律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因素部分地调和,因而显示出协调村民关系的功能特征,而很少导致常见的恶性宗族冲突。他在第二节又指出,应该从宗族的结构特征而不仅仅是功能特征入手来确定宗族的性质。“严格来说,一些宗族……只是对传统宗族引为的‘模仿’……这些所谓的宗族,实质上并不是一个依靠严格的系谱性(传统宗族结构特征)因素联结起来的组织,而仅仅是一个松散的功能性的团伙,……它明明是一个临时拼凑的功能团体。”而之所以导致研究者偏向功能主义,仅仅在于“因为参加者必须属于同一姓氏……(这使得他们的宗族)看起来却仍然像一个具有深厚根基的‘宗族’。”这样看来:现在的宗族之所以存在于“现在”,不是因为它与传统的相同,而是因为它恰恰与传统不同。(钱杭在文中例举了江西中部一个典型的宗族实例)既如此,倒是我们自己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应当改变我们面对现在的宗族却持有的对传统的宗族的态度,而认真思考一下中国农民宗族问题的“本体性”根源和现代性意义呢?
现代化的本质是现在的,虽然它叙述将来。站在现代化的立场,华中师大研究者在《中国农村的政治稳定与发展》中提出的思路和对策与其说是解决宗族问题和农村问题的一揽子方案,不如说是人们依据自己设定的现代化的设想而回过头来对现在的某种矫正。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最终可能与现在背离、与将来背离,甚至达不到他们企及的目标。
钱杭对宗族问题在现代化潮流中的本体性分析是富有深意的。我们可能没有感觉到:中国的宗族正在经历着自己的现代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