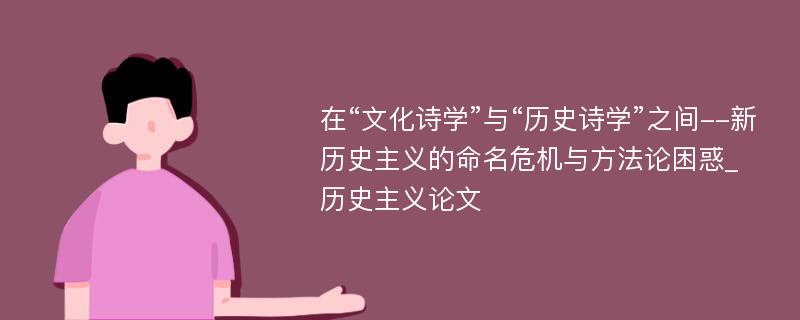
在“文化诗学”与“历史诗学”之间——新历史主义的命名危机与方法论困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方法论论文,历史主义论文,困惑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1)05-0063-03
近年来,“文化诗学”的呼声在国内文艺理论批评中日益高涨。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门类和方法体系已经呼之欲出。这显示出文学批评在文化系统中重新确立自身理论位置和逐步走向整合深化的新趋势。
在国外,“文化诗学”是与“新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与“新历史主义”联袂而行的,是一个跨学科、超国界的松散的学术群体,其中有一大批引人注目的批评家:包括美国的格林布拉特、蒙特洛斯、伽勒赫、奥格尔,英国的多利摩尔、辛费尔德,德国的魏曼,加拿大的帕克等文学批评家,还有美国的海登·怀特等历史学家。他们以恢宏的理论视野和新颖的批评方法,向陈旧僵化的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和处于强弩之末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批评发起了挑战,被认为代表着近年来世界文学批评的主要趋势。这个群体先后拥有“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以及“历史诗学”等几面底色相近的标签,并已走过了近20年的批评历程,其成败得失理应成为我们今天在国内建立“文化诗学”的宝贵借镜。然而,种种迹象显示,我们对这个流派的清理批判工作尚未完成,不遑借鉴。
一、称谓之内涵:殊名异义
格林布拉特首先用“新历史主义”作为自己代表的批评流派的旗号,但对其界定相当笼统。他在1982年将“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践定位为“向那种在文学前景和政治背景之间做截然划分的假设挑战,或者说得宽泛点,向在艺术生产和其它社会生产之间做截然划分的假设挑战”(注:Stephen Greenblatt,"Introduction:The Forms of Power",Genre 7,(1982):3-6.)。这个定义的确太“宽泛”,就是所谓“旧”历史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未尝不适合这一定义。
格氏对“文化诗学”的定义却相当详细而具体。在《文艺复兴自我塑型》中,格氏认为“文化诗学”的“中心考虑是防止自己永远在封闭的话语之间往来,或者防止自己断然阻绝艺术作品、作家与读者生活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我仍然关心着作为一种人类特殊活动的艺术再现问题的复杂性”。作为文学批评家,其阐释的任务是,“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注:《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第80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988年,在《莎士比亚的商讨》一书中,格氏将“文化诗学”界定为“对集体生产的不同文化实践之研究和对各种文化实践之间关系之探究”。具体而言,就是“追问集体信念和经验如何形成,如何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它种媒介,如何凝聚于可操作的审美形式以供人消费。我们可以考察被视为艺术形式的文化实践与其它相近的表达形式之间的边界是如何标示出来的。我们可以设法确定这些被特别划分出来的领域是如何被权力赋予,进而或提供乐趣、或激发兴趣、或产生焦虑的”(注:Stephen Greenblatt,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p.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这就要求“文化诗学”实践者能够辨别不同的文化实践;能够检视不同文化实践的形成;也意味着他们认为文化实践的形成是一种集体努力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单个人的工作;也要求他们探索一种文化实践与它种文化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工作事实上是格氏等人始终致力为之的。
蒙特洛斯针对格氏对“文化诗学”的上述界定指出:“文化诗学倾向于强调结构关系,而以牺牲连续性进程为代价;实际上,它以共时的文本间性轴线为取向,将文本视为文化系统的文本;而不是以历时性为取向,将文本视为自足的文学史的文本”(注:Stephen Greenblatt and Gile Gunn ed.Redrawing the Boundaries,p.401,New York,1992.)。看得出来,通过对“文化诗学”的提倡,格氏的兴趣主要在于:将文学放在一个“共时的”文化系统中进行研究。至于这个共时文化系统是如何历时发展变化的,这一问题似乎并不是“文化诗学”的关注焦点。
“亲历史主义”这一术语显示出修正和更新“旧历史主义”的意愿,换言之,就是要向传统的历史修撰进行挑战。格氏对它的界定始终很宽泛,相比之下,蒙特洛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ies)的定义,整饬而简明,因此广为认可和征引。按照蒙特洛斯的解释,“文本的历史性”是指,所有的书写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而且包括人们处身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历史具体性,镶嵌着社会的物质的内容;因此,所有的阅读也都具有历史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成分。“历史的文本性”则指,一方面,只有通过保存下来的文本,我们才能真正地、完整地了解一个社会的过去和它的物质性存在;另一方面,这些文本在转变成“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的时候,它们本身将再次充当文本阐释的媒介(注:H.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pp.19-20,Routledge,1989.)。那么,这个界定在理论上的新意何在呢?就“文本的历史性”而言,“旧”历史主义对它的强调尤力;就“历史的文本性”的强调而言,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走得更远,甚至于认为“文外无物”。其实,这个命题的理论新意正在于这两个方面的杂糅整合上,因而也缘此达到了对旧历史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双重扬弃。这种理论立场的选择注定要受到旧历史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两面夹击:前者以为它不够历史主义,后者则以为它不够后结构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有理论家指出,新历史主义恰恰吸收了历史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各自视为糟粕的东西。
事实上,“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历史的阅读和考察,在对它的各种批评面前显得非常脆弱。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已经走过了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批判的历史哲学”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到70年代,它开始有了新的取向,进入到一个以利科和怀特为代表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阶段(注:严建强、王渊明:《西方历史哲学》,第248-26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应该说,“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哲学主要是“叙述主义”的,但是,诚如格林布拉特所说,“总的说来,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一般又都不愿意加入这个或那个居主导地位的批评营垒”(注: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它不愿加入已有批评营垒,又要冠以“新”“历史主义”;擅“历史主义”之名而又不能行历史主义之实,这势必受到传统历史主义的严厉批评。怀特指出,“新历史主义之所以转向历史,不是为了寻找他们所研究的那种文学的材料,而是为了获得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所提供的那种知识。不管怎么说,到现在为止,新历史主义已经发现的是,根本就不存在历史研究中的特定方法”(注: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它不求历史“材料”,专求“方法”又不可得。那么,新历史主义者“既冒犯专业的历史学家和研究者”,又冒犯“在自己专业内进行研究的研究者”,是否值得呢?
批评者的矛头多指向它对历史的共时处理方法,自然也就涉及到“新历史主义”这个标签的名不副实。如何摆脱四面八方的理论围攻呢?他们选择从历史撤退而进入更加名正言顺、更少争议、也更为学术化的“文化”领域。
二、异名之究里:方法困境
从总体上看,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这些批评家都希望自己能以一种无定性的整体观照来看待历史文化,因而标榜其批评“没有任何政治动机”,以避免将历史文化“单声道化”。但是,进入历史的结果却是:必须立刻选择某种政治立场,否则,你就被所有的历史主义者视为忤逆。于是,从“新历史主义”的旗帜下撤退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退向哪里呢?“文化诗学”是一面现成的旗帜。批评家斯垂尔(Strier)指出,“在文化诗学和新历史主义之间,格林布拉特更喜欢前者,原因之一是前者不仅更机智、更暧昧、更具描述性,而且也更少争议”。布兰尼甘(Brannigan)则指出,“不管是称作新历史主义还是文化诗学,他们的批评实践保持未变,但是名称的更换使得他们的批评实践少受非议”(注:John Brannigan,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p.91,Macmillan Press Ltd.1998.)。
名称的改变是否涉及批评实践的变化呢?这个问题上理论家存在分歧。上述二位理论家持“不变论”,批评家雷恩(Ryan)等人反之,认为“作为一个口号,文化诗学以对文化文本性的关注代替了对文本历史性的强调……这个术语也让人想起结构主义者的一番努力:将对象作为一个共时的空间化的关系系统来把握,抑制历史进程中所牵涉到的历时性因素”(注:Kieman Ryan,ed.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AReader,XIV,London:Amord,1996.)。笔者赞同后者。名者实之宾也。从“新历史主义”变为“文化诗学”意味着转向一种对于文化的更加形式主义化的研究和新批评方法向文化领域的渗透。
这得从“新历史主义”面临的困境方面去解释。“新历史主义”这个称谓始终遭受着来自三个方面的猛烈批评:传统历史主义认为它不够历史主义,方法上也未将“历时性”放在优先地位;后结构主义则认为它太历史化,与“文外无物”的观点不协调;在美国拥有悠久传统的“新批评”则认为它所进行的批评迷恋历史碎片而根本不是“诗学的”批评。在这三重批评织成的张力网络中,张扬“文化诗学”可以一石三鸟:以对文化的关注代替对历史的强调,摆脱职业历史学家和传统历史主义者的攻击;以将文化主要限定在“文本、话语和语言”之中而争取后结构主义者的支持;以对“诗学”的提倡而讨得传统新批评的同情。这样,它就在自己的批评中,把新批评对文本的细读转向对文化的细读,从而与新批评的传统接续上了。因而也就一改以前四面出击的挑战姿态,而向同时共存的其它理论露出了笑容;进而“名正言顺”地投入共时性方法的怀抱。
当然,它的方法论与它所接受的理论影响是分不开的。它之所以更偏向共时态文化,主要是受到英美各种文化学派的影响。格氏明确表示,他企图实践一种更为文化的或人类学的批评,这种批评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阐释者的身份,同时,有目的地把文学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注:《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第80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有批评家指出,“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乃是一种采用人类学‘厚描’(Thick description)的历史学和一种旨在探询其自身可能意义的文学理论的混合产物,其中融会了泛文化研究中的多种相互趋同又彼此冲突的潮流”(注: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0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而且,在有关文化的观点上,格林布拉特等人也与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密切关联,其中属于后者的部分批评家被也被视为“新历史主义”者。有人指出,“与新历史主义一样,文化唯物主义将权力关系优先置于文本阐释的最重要的语境地位上,但是新历史主义者处理的是过去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文化唯物主义则探讨当前权力关系构成中的文学文本”(注:John Brannigan,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p.9.)。就拿文化解释学者格尔兹(Geertz)的影响来说,他提倡“厚描”,主张人类学的描述不能停留于“制度性素材的堆砌”,而应该使理解超脱于“生硬的事实”之上,追求对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观察者自身的观念世界以及观察者“告知”对象即读者的观念世界的沟通,这犹如在一系列层叠的符号世界里跨时空漫游,其所要阐明的是意义的人生与社会里的重要角色。这种“厚描”“是阐释性的;它所阐释的对象是社会话语流;这种阐释在于努力从一去不返的场合抢救对这种话语的‘言说’,把它固定在阅读形式中”(注: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这样一种方法似乎并不排斥历时性,但是,当把自己封闭在符号层面的“社会话事流”时,其方法就不可避免地是共时性的。格林布拉特从新历史主义走向“文化诗学”,在方法论上受文化解释学的影响恐怕是原因之一。
三、名称之实义:范导实践
综上所述,格林布拉特始终倾向于以“文化诗学”自称,而且这个标签更加名副其实;然而批评家使用最广的称谓是“新历史主义”,而这个标签已沿用日久,渐成定例。目前,国际学术界以“新历史主义”冠名并以之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已有数十部,尚不多见以“文化诗学”为名的专著。在历史上,有些文学批评流派的称谓是自出的;有些则是其论敌贬义地贴上去的。如此,则“新历史主义”之称大约已难摘去,而格氏的一番更名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只是适得其反地暴露出其方法论上的困境: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高度紧张。
当然,名称除了定义和描述功能外,还有尤为重要的评价、期许和范导作用。因此,人们关于这个流派的名称之争,不只是在竞争对其既往历史描述上的合法性,也是试图对其未来发展做出预期和范导。虽然名称之争至今尚未结束,但批评家已经讨论“新历史主义之后”的问题了。
早在80年代,怀特就认为,新历史主义提出“文化诗学”观点后,进而提出一种“历史诗学”观点。因为它对待历史所选择的边缘立场和边缘素材,“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注: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怀特以历史学家身份,以“历史诗学”的概括,希望新历史主义转向并深入历史领域。怀特在1973发表的专著《元历史》中就大力倡导“历史诗学”并以之为该书导论部分的副题(Introduction:The Poetics of History)。细究起来,巴赫金在30年代已提出并进行了大量自称为“历史诗学”的实践,只是其长文要到70年代中期才得以面世。(注: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小说理论》,第27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90年代末,布兰尼甘不无疑虑地揣测,“新历史主义之后”可能是“文化诗学”。他说,“描述批评实践的标签上的变化可能对这种实践的履行无甚意义,但它确实能给实践者和评论者一个机会,来重新检视该批评的特点、功能和内涵。在此意义上,评论家以新的视野来审视新历史主义,不是将它作为一种文学历史化和历史文本化的实践,而是将它作为这样一种实践:将文化阐释为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将任何现实和历史的观念都看成这个符号系统的结果并完全由表述所决定。”(注:John Brannigan,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p.93.)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今天借鉴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时,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并引以为戒。
首先,这个流派在理论资源上的杂然纷呈与相对匮乏并存。就前者言,它先后受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女权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解释学等诸多理论的影响,这使其无法对自身归宗入派,造成其归类危机。这显示出它对其它理论的吸收整合工作尚未完成,其理论的独立品格尚未完全定型,尚没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话语与其它理论抗衡,这又是它理论贫弱的一面。这种“丰富的匮乏”要求我们对它的借鉴必须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
其次,其命名危机事实上是其方法论困境的一部分。它由涌入历史到从中撤退,显示出其在历时性与共时性方法之间进行抉择时的二难处境。20世纪自索绪尔共时语言学一出,共时性方法逐渐取得了压倒优势。“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初出之时,曾有人惊呼,“文学研究背弃语言取向的理论而转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阶级和性属、社会语境和物质基础”(注:Stephen Greenblatt and Giles Gunn ed.Redrawing the Boundaries,p.395,New York,1992.),但这种转向仍未动摇共时性的优先地位。格氏向“文化诗学”的转移,是该派进一步摆向共时性的表征。其“文化诗学”主要是将文化视为一个静态的共时结构系统而从中抽绎出一种“诗学”,这种诗学是值得商榷的,这是泛文化主义的诗学,有重新退向结构主义的危险。
再次,我们相信,结构与历史、共时性与历时性并不是天然不相容的。有人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结构分析的方法与历史发生的方法同时并用。”(注:施密特:《历史和结构》,第3页,重庆出版社,1993。)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也在一直追求着这种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