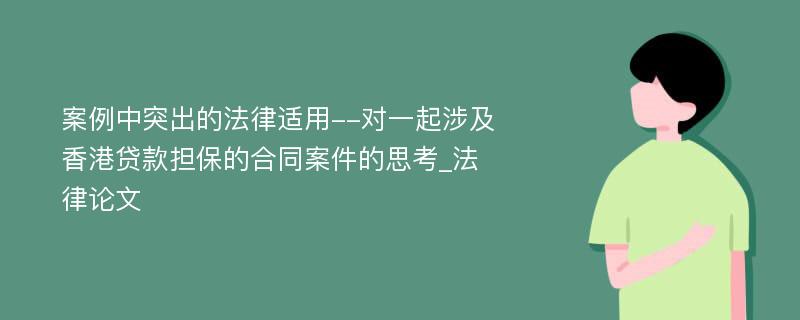
个案中凸现的法律适用问题——由一起涉港借款担保合同案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案论文,个案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2.295;D9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95(2007)03-0024-03]
一、基本案情
原告:香港J银行,被告:香港F国际有限公司、内地Y进出口公司、香港居民H。案由为涉港借款担保合同。J银行与F公司于1995年5月25日和1995年6月22日分别签订银行信贷合同各一份。借款由Y公司、H提供保证担保。在担保合同中,当事人选择了香港法为合同的准据法。合同签订后,J银行按照合同约定,为F公司开出多份不可撤销信用证,代付了信用证项下的全部货款和其他应付款项,依约将分期贷款划至F公司帐户。借款期限届满时,F公司未能履行还本付息义务,保证人也未承担保证责任。
二、法院判决
法院对实体问题的判决是,F公司要偿还本息,Y公司和H必须承担保证责任(本文不讨论此问题)。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法院认为:
(一)借款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为香港法人,合同签订地和履行地均在香港,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是香港。借款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45条第2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本案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应适用香港法。
(二)银行与H的保证担保关系因当事人选择了香港法律,本应适用香港法律,但当事人没有向法院提交香港有关保证的法律文本,法院无法查明香港法律中对于保证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193条的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外汇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提供对外担保,只能由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办理,并须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Y公司为F公司向J银行借款提供保证,违反了上述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意见》第194条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J银行与Y公司在保证合同中选择香港法律做为准据法,规避了我国的强制性法律规范,依法不能产生适用香港法律的效力。故J银行与Y公司的担保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体法。
三、法理评析
(一)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问题
按照我国内地冲突规范的援引,合同纠纷首先适用“意思自治原则”,其次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① 本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香港法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对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从上述判决中可以看出,法院进行了“量”的分析,即“借款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为香港法人,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均在香港”,由此得出“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是香港”的结论。法官只是指出了本案连接因素在数量上最集中的地方是香港,并因此把香港确定为最密切联系地。这种只靠“量”的分析就直接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做法,不是很全面。最好能就“质”的方面进行分析,即指出香港在该法律关系中能使合同有效,从而保护原告的正当期待的利益。
(二)香港法的查明问题
在本案银行与H的保证关系中,当事人选择了香港法,根据我国内地法律规定的“意思自治原则”,应适用香港法。法院以当事人没有提交香港有关保证的法律文本为由,没有适用香港法,转而适用了我国内地法律。这里涉及到域外法的查明问题。在本案中,对香港法的查明存在以下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准据法是香港法时,应由谁负责查明该法的内容,是法院,还是当事人?关于此问题,我国内地的法律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法官可以依职权查明香港法,也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香港法。这样认为的理由是,单纯由其中的任何一个来负责,都会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只能由法官查明,那么法官因为不可能像了解我国内地法律那样了解香港法,所以就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查,影响了案件的及时审理,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第二,如果查明香港法只是当事人的义务,那么在减轻法官负担的同时却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在法律资源的掌握上不如法官,同时可能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在某些情况下法官可以轻而易举查明的,而当事人想查明却很困难。那么,法院在什么情形下应当依职权查明,在什么情形下要求当事人提供香港法呢?笔者认为,如果香港法属于司法认知的范畴② 或者法官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资料能够查明香港法,法官就应该主动去查明。如果当事人事先选择了法律,说明其了解该法律的有关内容,就应由当事人提供。
2.如果法官已经知道了香港法中的有关规定,是否仍必须要求当事人提供?本案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选择了香港法做为准据法,本应由当事人举证,而本案当事人未提供香港有关保证的法律文本,所以法院认为本案应适用的准据法无法查明。笔者认为,鉴于审理本案的法官在此之前实际上已经知道了有关的香港法,③ 因此法官可以直接适用有关的香港法而不一定非要当事人提供。这样可以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节省审理案件的时间以及节约诉讼成本。
3.当事人未提供香港法,是否就可以认定香港法无法查明,转而适用我国内地的法律?这里涉及对司法解释的理解。《意见》第193条规定:“对于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可通过下列途径查明:(1)由当事人提供;(2)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3)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提供;(4)由该国驻我国使领馆提供;(5)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从字面上可以看出这五种途径是并列关系而不是递进关系,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不提供、提供不出、提供不充分时一定要用尽其它的方法。如果要穷尽上述五种途径,将会造成审理时间的延长和诉讼资源的浪费。但也不能认为只要当事人不提供,就可以认定域外法无法查明。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在上述案件中,如果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提供香港法的,法官就可以认定该法无法查明。如果当事人确因困难无法提供香港法的,法官不能就此认定香港法无法查明,应该发挥积极作用,采用其它途径查明。
(三)法律规避问题
在Y公司与J银行的保证合同中,当事人选择了香港法,但法院认为这种选择规避了我国内地的强制性法律规范而不予适用。笔者认为,法院的做法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如前所述,判决书在认定法律规避之前引用了《外汇管理条例》的规定,但未说明它与“法律规避”之间的逻辑关系。这在文字表述上是存在问题的。对法院的本意,可以做以下的理解:因为《外汇管理条例》对对外担保有强制性的规定,而香港法对此没有限制,于是当事人故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香港法作为合同准据法,以避开对自己不利的中国内地法律。所以当事人的行为属于法律规避。如果作此理解,法院就应通过证据证明当事人的主观故意,同时说明本应适用的法律是中国内地的法律。因为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之一是主观上为故意,另外一个构成要件是避开了本应适用的法律,而我们从判决书中看不到对这两个问题的阐述。
2.实际上法院根本不可能说清楚本合同本应适用的法律是哪一个法域的法律。根据我国内地法律的规定,除了三种合同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必须适用我国内地的法律外,④ 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这时当事人完全可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自由地选择法律。其选择的法律就是合同的准据法。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是指,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利用某一冲突规范,故意制造某种连结点,以避开本应适用的法律,从而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一种逃法或脱法行为。[1] 上述保证合同本应适用的法律是什么呢?应该说,在当事人选择本保证合同的准据法之前,是不存在该保证合同本应适用的法律的。只有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才是应适用的法律。另外,法院也无法证明当事人有规避中国内地法律的主观故意,不能把当事人未办理审批登记手续认定为故意制造或改变连结点。因此,本案根本不存在法律规避的问题。
(四)直接适用的法的问题
从本案的判决中可以看出,法院首先考虑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最终没有适用当事人通过合同法律选择条款所选择的香港法律。法院最终决定适用中国内地的法律的依据是,当事人选择香港法律是基于规避内地的有关强制性规定,因此,这种选择是无效的。上文已谈及,在本案中,以法律规避制度为根据来拒绝香港法的适用是不恰当的。笔者认为,可以从“直接适用的法”的角度来做出判决。
关于“直接适用的法”,学者们下的定义不尽相同。最早提出这一术语的法国国际私法学者弗郎塞斯卡基斯认为,在处理国际性案件时,有关国家所制定的某项法律规则对该国家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从而必须强行适用于这种案件,而不管一般冲突规范所指引的为何国法律,这种法律规则被称之为“直接适用的法”。[2] 肖永平认为,“直接适用的法”的理论前提是,在每一法律体系中都存在着一些实体规范,由于其特殊性质、目标或政策,可以不考虑正常的冲突规范的要求而予以直接适用。[3] 所谓“直接适用的法”,在一部分学者的视野中是指那些不必经过冲突规范的指引而可“直接”适用的法律,而另一部分学者并不完全否定它们与冲突法制度的关系,但它们的适用界限或空间是由它们自己决定的(即不是通过冲突决定的),所以又称“自我限界的法”或“空间上有条件的法”。对于这类法律,目前普遍认为乃“起源于现代国家的干预直接深入到了传统上本属民法范畴的事项”,“主要是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的重大利益或基本制度的法律”。[4]
笔者是这样理解“直接适用的法”的:“直接适用的法”适用的基础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其适用的特点是绕开冲突规范的援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它的表现形式有两种,即它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种是“自我定位的空间适用规范”,另一种是“实体法规范”。“自我定位的空间适用规范”确定某涉外民商事关系属于“直接适用的法”的调整范围,“实体法规范”确定该涉外民商事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外汇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境内机构、个人、驻华机构、来华人员的外汇收支或者经营活动,适用本条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外汇管理制度是我国内地的基本经济管理制度,是保证外汇收支平衡的基本政策,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体现,如果不在批准或登记环节进行控制,就会影响国家对可能产生的外债的事先调整和总量控制。这一条就属于“自我定位的空间适用规范”。它确定了《外汇管理条例》的适用范围,决定了其中的实体法规范对相关的涉外案件的强制适用。《外汇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提供对外担保,只能由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办理,并须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这一条就属于“实体法规范”。它规定了对外担保合同中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
本案当事人对准据法的选择,依法不能产生适用香港法的效力,实质上是因为我国内地强制性法律规范对这类合同具有直接适用性。本案受理法院完全可以肯定有关对外担保必须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规定对涉港担保合同有直接适用的效力,不再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适用香港法,进而判决担保合同无效。
注释:
①我国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国家的法律。”
②司法认知,是指法院认为某些事实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或常识,无需当事人证明。
③根据笔者查阅到的判决书,审理本案的法官在此之前已经审理过同案的案件。当事人提供过香港有关保证的规定。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6条第2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标签:法律论文; 法官论文; 担保合同论文; 外汇管理条例论文; 法律适用论文; 法制论文; 法律规避论文; 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