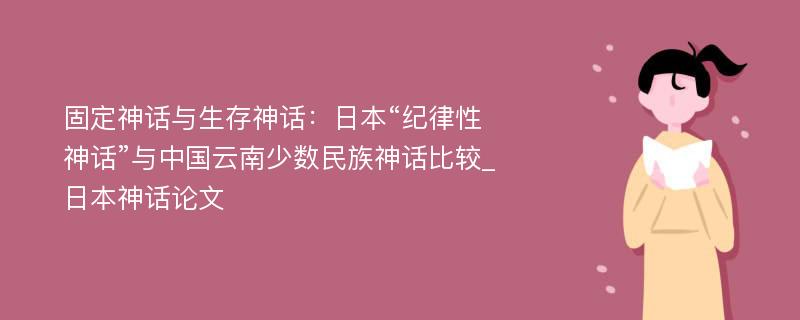
被固定了的神话与存活着的神话——日本“记纪神话”与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话论文,云南论文,日本论文,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13(2000)01-0074-06
一
日本在8世纪就出现了《古事记》、《日本书纪》这样用文字将神话系统、完整地写定下来的古籍,在东亚各国中是不多见的。这充分表明了在“记纪神话”写定之时,日本神话的丰富、多样性,以及神话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日本古代神话成书以后,当有一段文献神话与活形态神话的并存期。应当说,在“记纪神话”成书前后,人们不难看到日本古代神话的原始形态——即存活于某种特定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活形态神话,也不难理解神话所述的一切。但是,随着历史的流逝、时光的推移,曾经存活于日本民间的许多活形态神话渐进消失,加之“记纪神话”是用中国汉字记录写定的,其中许多神名、神物、神话中的地名等都只能用汉字记音,而不能准确地表述其原义,因此,后人就难以对其作出准确理解,有些可能成了一堆“哑谜”。至于“记纪神话”是怎样形成的,其原始形态如何,若研究视野有局限,就更加难以探讨了。
自本世纪以来,尤其是50年代以后,以日本学者为主力的世界许多神话家,已对日本“记纪神话”作了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10多年来,日本神话的研究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术视野、理论层次、研究方法都上了一个新台阶。(注:松村一男:《日本近十年神话研究》,《思想战线》1997年1期。)笔者对“记纪神话”的内容尚未进行过深入研究,不敢冒昧奢谈。这里,对“记纪神话”写定之前的存在形态及特征进行初步的探讨。因为云南与日本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古文化要素;云南与日本共同存在着许多独特的神话母题;云南各少数民族至今仍存活着吟唱出来的神话,与“记纪神话”有某些相似之处;云南不仅有活形态神话、口头神话及文献神话,而且在藏、彝、白、纳西、傣等民族中,仍保留着活形态神话与文献神话并存的格局;云南至今还可视为一部活的文化史,是世界罕见的民俗文化宝库。因此,可否从原始文学、文化生态学的角度,通过比较,寻觅“记纪神话”写定之前日本古代神话的原始面貌?这显然具有假说的性质,希望得到相关学者的指教,以便笔者对此作更深入的思考。
二
写定于8世纪的“记纪神话”,尤其是《古事记》神代卷,是在大化大革新之后古代皇制已经确立、日本统一国家业已形成的背景下,为了确立天皇“万世一系”、天皇即国家、天皇是“现人神”等思想观念而将日本古代氏族神话(主要是天皇系氏族神话)上升为民族神话、国家神话的。虽然如此,“记纪神话”显然是在当时民间流传或已被写入《帝纪》、《旧辞》中的神话之基础上,加以选择、编纂而成的。应当说,它仍然保留了日本古代神话的基本面貌。
为了寻找到云南少数民族活形态神话与日本“记纪神话”进行比较的时间轴,增强其可比性,我们不妨从南诏文化谈起。在云南,以洱海区域为中心,曾于8世纪初出现了地域辽阔,足以与唐王朝和吐蕃王朝对峙的南诏。南诏中心区的大理洱海地区,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就已开始了水稻种植,这跟日本的水稻种植史接近。顺便说一句,与属于氐羌系的白、彝、哈尼等民族一样,日本大和民族也是由旱作文化转为作(水稻)文化的。这个以彝族先民(乌蛮)为主体的奴隶制国家虽然崇尚武功,曾在天宝战争中大败唐军,但却深受汉儒文化的影响。南诏曾先后派遣几千人到成都“习孔子之诗书”,以至出现了“人知礼乐,本唐风化”的局面。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南诏文化是“仿唐文化”。现今仍保存完好的大理三塔寺、剑川石宝山石窟等足以说明南诏文化的发展水平。《蛮书》记南诏阳苴咩城说,城内有一“方池,周回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太和城“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南诏野史》说:“圣僧李贤者,建立三塔高三十丈,佛一万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千五百五十斤,自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始完”。成画于南诏中兴二年(公元899年)的《南诏中兴国史画》,是一件有关南诏历史的重要文物,画末的题记说:“谨按巍山起因,铁柱西洱河等记,并国史上所载图书,圣教初入邦国之原,谨画图样,并载所闻,具列如左,臣秦宗等谨奏,中兴二年三月十四日。”此画现藏日本京都有邻馆,纸本彩画神像、人物94个以及马、象、犬、蛇、鱼、螺、鸟等多种动物,均极生动。特别是所描绘并有文字记述的巍山失柱等事,都涉及南诏重大史实。这似乎与日本在“记纪神话”写定前后全方位地持续地吸收汉文化、建立律令国家的情形颇为相似。当时,南诏的宗教是以本土的原始宗教居主导地位,同时,又传入了佛教和道教。这与日本“奈良时代”以神道教为主、佛教逐步开始盛行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但是,南诏文化与日本同一时期的文化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一,至大和政权形成并统一了日本之后,日本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走上了自己独特发展的道路。而作为地方政权的南诏国,自8世纪初产生,至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之后,便消解了。其二,由自然宗教演变而成的神道教,是在大化大革新之后才逐步上升为日本的国家宗教,并一直延续至今。南诏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原始的巫鬼教(原始宗教)却始终没有上升到国家宗教的层次。虽然南诏第5代王阁罗凤于公元748年即位之后,曾试图
创立南诏国的统一宗教,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南诏多种宗教形式的并存,一直贯彻于南诏的始终。这样,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记载南诏的文献中,就没有类似《古事记》、《日本书纪》这样的著述。南诏德化碑主要是颂扬阁罗凤的文治武功,开头却有关于神话的内容。《南诏德化碑》开篇云:“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辩位,莫大于君臣。”“王姓蒙,字阁逻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应灵杰秀,含章挺生,日角标奇,龙文表贵。始王之在储府,道隆三善,位即重离。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用现代白话来说,以上一段话的意思是:天地初分之时,阴阳运行而生万物,山河既已排列,人类就树立元首而定八方,所以知道悬于太空而著名的星象,最大的莫过于日月;人间辩别地位的崇高,最大的莫过于序列君臣的名分。”“王姓蒙,字阁罗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义同三司(皮罗阁)的长子,是应运而生具有内美的杰出优秀人物,额骨有隆起的奇异标志,身上有龙纹显示大贵的仪容。当初他还是王储的时候,就深懂事君事父事长之道,镇守在重要的边防地方。他不读不是圣人的书,曾经学得养育人民的方法。”由于南诏的统治者深受汉儒文化的影响,在其潜意识中,一直对唐王朝称臣,因此,《南诏德文化碑》中的神话内容并未突出王者是神的后裔,《南诏德文化碑》中也未纳入更多的神话内容。这显然与《古事记》、《日本纪》有着明显的差异。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据《蛮书》载:“乌蛮”的宗教是“一切信使鬼巫”。当时有多少个部落,就有多少个集政教于一身的大鬼主。“乌蛮”属氐羌原始族群,其巫鬼教的特征是“以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雷霆、雪、雹、山川、陵谷、土石、草木、禽兽乃至一切万物等幽灵巫鬼,祈福禳灾为事。”(注:彭英全主编:《西藏宗教概说》。其另一个特征是祖先崇拜极盛。此种情况与日本学者石田一良在《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中所述日本古代的鬼神信仰颇为相似。(注: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所至,在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中,南诏时代盛极一时的巫鬼教一直得以延续至今。于是,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断: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中至今仍存活着的各种古文化事象,可以作为考察“记纪神话”写定前文化状况的参照。换言之,云南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保留着的古文化事象,其历史化“记纪神话”写定的“奈良时代”也许还要古老。
三
直到本世纪50年代,在云南20余个少数民族中,约有近半数还处于氏族社会发展阶段或仍保留着氏族社会的许多残余。这样,就为我们探寻神话发展的轨迹提供了活生生的样品。
就其存在形态而言,神话大致可分为:一、活形态神话;二、口头神话(即只是讲一讲的故事);三、已被用文字固定下来的文献神话。在云南,这三种形态的祖籍都有。就神话的发展演化历程而言,初始阶段的神话无疑是活形态神话。当某些活形态神话与宗教信仰渐进分离,就变成了只是讲一讲的故事,即口头神话,当文字产生以后,有的民族就把自己的神话用文字固定下来,于是便形成了文献神话。但就某个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民族而言,就不一定明显地表现为上述发展演化系列。例如,在日本,早在8世纪神话就被系统完整地写定。在此之后,日本的活形态神话肯定在民间继续存活。又如,在云南彝、纳西、傣、藏等民族中,至少在明代以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唐代以前)就已出现了用彝文、东巴文、傣文、藏文写定的系统完整神话——经书。但是,直到现在,在这些民族中,仍保留着活形态神话及口头神话。
如前所述,神话的初始形态,是存活于某种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之中,与民间信仰,宗教祭仪、节日庆典、民俗活动、文化心态密切相关的活形态神话。就云南少数民族的活形态神话来看,又可分为以下几种层次:(一)、属氐羌系,以旱作文化为背景,尚处于氏族社会发展阶段的独龙、怒、傈僳等民族的活形态神话。其特点是:以上各民族的活形态神话,还处于由氏族神话向民族神话转化这一发展期。一方面,讲述氏族起源的神话(在傈僳族、怒族那里又多为图腾神话)广泛流传;另一方面,为该族群体所认同的讲述人类起源、天地创造、文化创制等神话已形成并纳入了该民族的长篇创世史诗之中。居住于怒江峡谷的上述三个民族,纵然自古以来相互交往频繁,但各自的神话皆自成体系,都有其特点。由于其封闭的地域环境,他们的神话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几乎未受汉儒文化的影响。在那里,直至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万物有灵观念盛行,神话观念仍在支配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对神话所说的一切深信不疑,仍存在着神话不断产生的土壤。(二)、属百濮系的佤,属氐羌系的景颇、拉祜、基诺、德昂、阿昌等民族,在本世纪50年代初以前,虽然仍处于氏族社会发展阶段,亦全然未受汉儒文化影响,但由于所处的地域环境条件较好,社会、文化发展层次略比怒江峡谷诸族高一些,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受傣族文化的影响,所以其活形态神话虽然也各具特色,但其神话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比较明显。其中,以德昂族最为典型。在以上民族中,活形态神话的特征仍然非常典型。例如,佤族的猎头习俗就与佤族神话密切密不可分。(注:参阅李子贤《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三)、藏、傣、壮、白、彝、纳西、哈尼等民族,其社会文化发展层次较高,过去,有的处于封建领主制社会,有的则早已进入封建地主社会,其中大多属于稻作民族,有的受汉儒文化影响较深(如白、壮、纳西等民族),有的则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如藏、傣等民族)。这些民族的活形态神话,就其内容而言,因素就比较复杂,如藏族神话中较古老的本土神话(如岩妖与弥猴生人)则已蜕变为口头神话;藏传佛教中的神话则保留着活形态特征。又如傣族神话中的谷神奶奶,寨神、勐神,大多已逐渐与宗教祭仪脱离,人们对上述神祗的信仰已逐渐淡化。南传上座部佛教中的神祗不仅一直受到供奉,其神迹也一直被视为神圣性的叙述而成了活形态神话。上述各民族中的纳西、彝、傣、藏等民族,并存着活形态神话、口头神话、文献神话
,而且文献神话又成为了宗教经典的组成部分。因此,上述各民族文献的神话中的相当数量的神话,又具有活形态神话的特征。这一点,当与日本“记纪神话”成书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情况大体相似。
由以上简要论述中,可看出属于第一、第二层次的活形态神话,无疑可看作是“记纪神话”成书前的神话发展阶段。第三层次的活形态神话则与日本“记纪神话”成书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情形相当。
概括起来说,云南少数民族的活形态神话,大致有下特征:1、最古老的活形态神话,当是氏族起源神话。只是到了后来,氏族神话才发展为民族神话。2、最古老的活形态神话,其内容主要是讲述人类(氏族)的由来。较完备的天上创始神话,是后来才产生的。例如独龙族《创世纪》开篇第一章就讲的是人类的起源,之后才讲到地分离(即天地调整神话)。笔者1962年在独龙江畔进行田野调查时,就未发现独龙族有完备的天地创造神话,而仅仅有所谓本来就有天和地,只不过二者连接在一起,后来天地才分开这样的内容。在台湾高山族中,亦未发现完备的天地创始神话,而只有天地调整神话。日本“记纪神话”中的天地创造神话,严格说来,也仅属天地调整神话。由此也可以证明“记纪神话”当为较古老的神话。3、最古老的活形态神话,当为可以吟唱的韵文体。这一点,不仅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可以找到活的样品,而且据笔者60年代初对彝、纳西、藏、怒、独龙、傈僳等民族的调查,凡与民间信仰、宗教祭义融为一体的活形态神话,都是以吟唱方式来表达的,而且在吟唱神话时有很多规定和禁忌,对演唱场合亦有严格的规定性。笔者以为,这与氏族群体便于表达、便于接受、便于记忆、便于规范、便于传承自己的“圣经”密切相关。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吟唱神话都必须有某种调式(调子),例如,楚雄州大姚、姚安一带的彝族,吟唱自己的创世神话就必用“梅葛”调;红河州弥勒县彝族吟唱自己的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时,还以男女对唱的方式进行。据笔者的调查,讲述的神话(散文体)大多属于已与民间信仰及宗教祭仪分离了的口头神话(即只是讲一讲的故事)。4、云南各民族的活形态神话,在人们的心目中,都具有神圣性、权威性、规范性的特质。人们不仅对神话所述的一切深信不疑,而且认为“本来就是那样”、“应该那样”、“不许那样”,神话中所讲述的某神的神迹,就成了对某神必须顶礼膜拜的根据。在各种宗教祭仪中,“必须这样,”“不能那样”,“要这么做”,“不能那样做”等等之根据,也来自于神话。纳西族为何至今仍保留着祭天习俗,祭天仪式的场地、神器、主祭人、祭品、程序等的规定,均来自于神话。历史上佤族为何供奉木鼓,木鼓为何必须以人头加以祭祀,也都来自于神话。所以,活形态神话之所以能够存活,是与人们的信仰、崇拜对象密切相关的。离开了神圣性、权威性、规范性的神话,就已不再属活形态神话。5、活形态神话的传承,不仅与民间信仰、宗教、祭仪、节日庆典、民俗活* 动、文化心态密切相关,而且必须要有把这一切与神话加以联系和整合的祭司这一关键性的“精神领袖”来实现。祭司被视为人与神的联络者,人们的祈求需由祭司去向神禀告,神的旨意和恩赐也需通过祭司来传达。于是,在历史上,云南各少数民族中的祭司,几乎成了“半人半神”。在人们看来,祭司本身就具有神力,人们必须有神的庇护,因此,也就须臾不能离开祭司。用元江县大羊街乡一位80多岁的哈尼族大摩批(祭司)的话来说,“没有摩批,这里的人就不会过日子。连人死了都送不走。”由此可以推想,日本古代天皇制中最初的天皇,可能既是部落首领,又是宗教祭司,地位极高,故被视为“现人神”。据笔都30多年来的调查,云南少数民族中的祭司,都是各民族神话的保存者、传承者。在什么场合吟诵什么样的神话(祭词),何种仪式的神话依据是什么,他们都了如指掌、烂熟于心。我们甚至可以说,神话赖以存活的某种文化生态系统存在与否,最简单的观察方式就是祭司在该群体中是否还有特殊的地位,是否还在频繁地被人们请去主持各种宗教祭仪。典型的例子是,四川凉山州美姑县,这里仅有15万左右的彝族,但祭司(毕摩)至今仍多达近8千人。在那里,神话赖以存活的文化生态系统至今一直得以存留。反之,丽江地区的祭司(东巴)则出现日益减少的现象,神话赖以存活的文化生态系统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6、活形态神话大多处于一种缓慢变动的状态。有的神“死”了,有的神“诞生”了,有的神地位上升了,有的神地位下降了;有的神一直受到崇拜,有的神则不再是被崇拜的对象……这样一来,凡是“死”了、地位下降了的神,其神迹或者成了只是“讲一讲的故事”,或者慢慢被人遗忘而最终式微或消失。而文献神话一经写定,就被固定下来,不再发生变异,只不过后人对它难以理解而已。
四
从内容看,“记纪神话”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首先是它的完整系统性,是一部创世史诗式的作品。与东亚其它国家或民族的神话比较,它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突出了创生意识,神话情节的铺衍都由不断地创生为主轴,此外,宗教化与历史化的统一也十分突出。它不象中国的华夏——中原神话自春秋以后就被历史化,从而导致了中国汉文献神话的不完整性。再一点就是,“记纪神话”虽早已被写定,却仍有活形态神话的某些特征。一般而言,大凡被写定的神话,大多逐步“僵死”,然而,“记纪神话”不仅在天皇系而且在民间却一直具有某种程度的神圣性特征。
若将“记纪神话”与云南少数民族神话进行比较,我们又发现至少有以下共同的特点。其一,人是神的后裔。在云南的大多数少数民族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都可追溯到神那里。纳西族的《木氏宦谱》讲木氏土司的祖先是神。哈尼族、彝族的父子连名制,人们可背诵出五、六十代甚至上百代,但开头的一、二十代大多为神。例如哈尼族父子连名制至塔婆之后才为各个氏族的直系祖先。又如,曾任云南省省主席的龙云(纳甲乌萨)先生的父子连名谱牒,开始第一代始祖就是洪水神话中的幸存者居木阿普(居木吾吾),至34代阿宁蒲伙之前,均为神话、神说中的人物,他们均被视为所有彝人之共同祖先。蒲伙牟阿乌(35代)之后分六祖,至龙云已为176代。(注:王昌富:《凉山彝族礼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其二,世界父母是从天而降的。类似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二男女神从天上垂直下降创生万物的神话,在云南有傣族的“布桑该与亚桑该”。哈尼族有洪水后天降二神自地上重新繁衍人类的神话。其三,与其二相关的是,特殊的天的观念,即万物的始源来自于天。在云南、四川大小凉山彝族中,有如下谚语:“天上不下来,地上不会有”,“天不落,地不生”。在云南少数民族的观念中,甚至将天等于山。诸如,景颇族、独龙族就认为太阳住在山上;滇南哈尼族的梯田水稻种植,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认为,天和地之间有一条秘密的水通道,地上的水就是从这条通道源源不绝地从天(山)上流下来的。凡此种种,与“记纪神话”中反映出来的天的观念有相似之点。其四,在云南绝大多数民族中,都流传着太阳神话,至今在景颇、基诺、哈尼族等民族中,仍残留着太阳崇拜。(注:李子贤:《女性太阳说刍议》、《日中文化研究》第三号。)在有关太阳的神话中,大多有英雄神与太阳争斗的故事。最典型的是英雄射太阳。在“记纪神话”中,也有类似的情节:《古事记》中的速须佐之男命大闹天国导致天照大神的藏匿。(注:李子贤:《太阳的隐匿与复出——日中太阳神话比较研究的一个视点》,《思想战线》,1994年6期。)其五,兄妹开亲神话。众所周知,云南各少数民族都流传着或与洪水相关、或与水无关的兄妹婚神话。在“记纪神话”中,创生国土的天降男女二神既是兄妹,又是夫妻。值得研究的是太阳女神天照与其弟速须佐之男命却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对立关系,乃至于姐弟之情破裂。如果说,在“记纪神话”中,天照天神登场与伊邪那美命的消失意味着以再生和纯洁取代死亡和污秽
的话,那末,太阳女神和其弟的对立,是否与“记纪神话”写定时母系制的残留相关,是否意味着天皇系血统的“纯洁性”?对此,笔者拟另文作更深入地研究。其六,谷物起源神话。笔者曾将云南的谷物起源神话归结为9种类型(注:参阅李子贤《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在“记纪神话”中,则主要是“死体化生型”。以上各相似之点,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与“记纪神话”的主干部分。这里有必要指出,世界上没有两个民族的神话绝对相同的实例,因此,不同民族神话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
本文的主旨是想就“记纪神话”与云南少数民族的神话的存在形态进行比较。如前所述,“记纪神话”虽属文献神话,但它却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献神话,自它写定之日起直至以后,仍是有许多活形态的特征。这是我们将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与之相比较的一个重要前提。这里,主要想谈以下几点:
1、神话是某种祭礼活动的依据和注脚。在日本,直至今日,天皇每天要亲自插秧、割谷,举行“尝新祭”;新天皇登基时必在举行“大尝祭”之后,天皇才被视为真正的天皇。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天皇被视为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的直系子孙;其二,据《日本书纪》载,天照大神是第一个插秧的人,因此,天照大神=稻魂。日本天皇现在仍然是稻魂的继承者。(注:欠端实:《日本神话中的“太阳再生神话”和“谷灵降生再生神话”》1998年11月4日在云南大学讲演。)这与云南少数民族各种祭祀活动,诸如祭“天”,祭祖等仪式完全按照神话来规范或影响人们的心理是非常一致的。
2、在各种大型宗教祭祀活动中,主持者大多为祭司。在祭祀活动中,吟诵祭词或吟诵《创世纪》的,大多必为祭司,这在云南和日本都一样。据有关资料(如《古事记》序)介绍,在日本古代,吟诵祭词(其间包括神话)的是“稗田阿礼”是天皇的近侍,《古事记》中猿女群的后代。稗田阿礼是否为主持祭祀的人,目前笔者尚不清楚。但即便“稗田阿礼”不是主祭人之一,也必定是参与祭祀并专门吟诵祭词的重要成员。此种情况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也有。如哈尼族的“昂玛突”(祭寨神、树神),参与主祭的,就不仅仅是祭司(摩批),而且有被众人推举出来的“龙头”(咪谷)。“龙头”不是巫,但必须是德高望重、一生清白、家庭全福、并谙熟全套祭仪的人。
3、在各种祭祀活动中,如果有必须吟诵神话的程序,那末,其神话内容必定是韵文体的形式并以某种调式吟唱出来。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上古神话当它与宗教祭祀、民俗活动融为一体并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时,由于其神圣性、规范性,故绝不允许念错或中间出现停顿,而必须琅琅上口,一气呵成。为了便于记忆,押韵、节奏是必不可少的。笔者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凡被视为讲述其民族来源、民族发展的“根谱”的创世神话,只能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演唱,其样式均为韵文。讲述出来的神话故事当然也广为流传,但它多与宗教祭仪无关。而且,这些神话所讲到的神,大多也不再是人们信仰中的神。由此可见,上古神话主要是韵文体,是吟唱出来的,是祭司经过长期磨练强记在脑海里面的。日本古代神话的情形,也大概应当如此吧。
4、神话的发展历程,当由氏族神话逐步发展为民族神话。在有的民族那里,如日本民族,再由民族神话上升为国家神话。在云南,我们还可以找到由氏族神话向民族神话过渡的活生生的实例。直到本世纪60年代,在独龙族中,还广泛流传着许多氏族起源的神话。大约自本世纪上半叶,独龙族的民族神话开始形成。这就是笔者于1962年在独龙江畔搜集到的《创世纪》这部长达700多行、吟诵出来的创世史诗。它包括了人类起源、人与鬼的斗争、洪水滔天、天地分离,聚媳妇的由来、“卡雀哇”(年节)等神话内容。(注:李子贤:《神话的民族特色与文化生态——独龙族神话探幽》。《中国民间文化》,学林出版社,1993年3期。)在傈僳族那里,也存在着类似的文化现象,即氏族神话与民族神话并存,并逐步趋同于以民族神话为主的格局。《日本书纪》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某些氏族神话有所展示,“一书曰”,“一书曰”多少能说明这一点。君岛久子教授在《仙女的后裔——创世神话的始祖传说形态》中指出,见于《帝王编年纪》中养老七年条所记载的《余吴湖的仙女》,就是近江国的始祖神话。但“由于其与天孙降临的皇统相抵触,因此,在作为正史的《古事记》、《日本书记》中没有记载。”(注:载:中国西南民族学研究会、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合编,1990年,大阪《中国西南诸民族文化的研究》。类似的氏族神话,在日本古代肯定不在少数,如《常陆国风士记》中有关鹿岛神宫的“献国”神话;《播磨风土记》中创造该国的大国主命神话;《出云国风土记》中有关此地大国主命传说等,只不过是在当氏族神话上升为民族、国家神话的过程中,这些氏族神话大多被在“记纪神话”中扬弃了。
5、大凡存活着的神话,都必须依存于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直到本世纪80年代初,即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云南少数民族大多保留着神话赖以存活的文化生态系统。在日本,“记纪神话”被写定前后,神话赖以存活的文化生态系统亦当存在。今日日本各地的神社和相关的祭祀活动,亦表明这种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仍有残留。
五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云南与日本曾经有着相似的自然生态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因此,我们可以借助于云南少数民族的活形态神话还原日本“记纪神话”写定前后的原始面貌和存在形态。本文所论日本与云南神话内容和形态的共同特点,已大体勾勒出了日本古代神话的面貌。我们纵然不能说日本古代神话就是那样,但我们可以说日本的古代神话可能就是那样。这就是“记纪神话”是从氏族神话逐步发展而来的;在“记纪神话”写定时,神话大多已被纳入各种祭词、氏族谱系而在各种祭祀活动中被吟诵;各氏族的祖先都被追溯到了显赫的神祗那里并受到崇拜;由于不同的氏族和不同的地域所至,同一类型的神话有多种说法。神话的存活从属于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
“记纪神话”是早已写定而被固定了下来的文献神话,日本的社会历史经历了许多次转型,但其为何至今仍具有活形态神话的某些特征?“记纪神话”中的不少神,虽然业已消歇,乃至“僵死”,为何有的神(如太阳神、稻魂神等)又一直得以存活并仍受到顶礼膜拜呢?这在东亚乃至全球都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对此,笔者怀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对上述问题做出一个较为合理、有说服力的解释。
【收稿日期】1999-09-23
标签:日本神话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文化论文; 云南发展论文; 氏族社会论文; 艺术论文; 日本书纪论文; 古事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