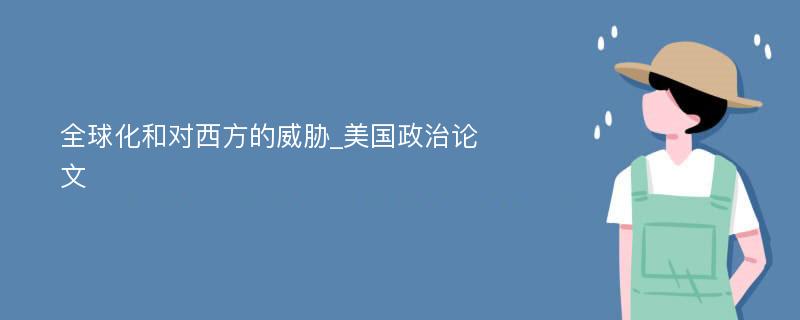
全球化与对西方的威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场治理能力危机已经席卷世界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同时陷入政治僵局,这绝非偶然;全球化正在不断拉大选民对政府的要求与政府所能够提供的需求满足之间的差距。善治要求的持续增加与善治供给的不断萎缩之间的不匹配,正是今天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
工业化民主国家的选民指望政府对因货物、服务和资金空前规模的全球流动而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做出反应。他们还期望政府应对移民激增、全球变暖以及全球化世界的其他连锁反应。但西方各国政府并不能胜任这一使命。通过“他者的崛起”,全球化正在使得任由西方各国政府支配的政策杠杆变得不太有效,同时也抑制了西方对世界事务的传统影响力。民主国家政府无力满足广泛公众的需求,这反过来只会增加公众的不满,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代议制机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西方世界内部的这场治理能力危机是在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时刻到来的。由于财富和权力扩散到新的地区,国际体系正处于巨变之中。全球化的运作本应有利于自由社会,因为这种社会或许最适合于利用全球市场这种快速和流动的性质。但恰恰相反,北美、欧洲和东亚发达民主国家的芸芸大众却一直遭受重创——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体既是成熟的又是向世界开放的。
相比之下,巴西、印度、土耳其以及其他正在崛起中的民主国家却在从经济活力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世界的转变中获得好处。而中国在限制债务的同时也证明它尤其擅长获取全球化的各种好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已掌控了被竞争对手所抛弃的政策工具。至少眼下,社会主义享有独特的优势。因此,今天利害攸关的不仅是西方物质上的首要地位,而且更是其现代性版本的魅力。除非民主国家能够恢复政治的和经济的偿付能力,否则21世纪的政治以及地缘政治极可能需要公开竞标了。
被车灯吓呆的鹿
全球化已经扩大了财富的总量,并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繁荣。投资、贸易和通讯网络的扩散已加深了相互依存度及其潜在的安抚效应,并且帮助撞开了非民主国家的大门,推动了民众起义。不过,全球化及其所依赖的数字经济同时也成为西方面对治理能力危机的主要根源。产业空洞化和外包、全球贸易和财政的失衡、过剩的资本、信贷和资产的泡沫——全球化的这些后果正在强化几代人所未曾经历过的艰辛和不安全。虽然源于2008年的这场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不幸尤为严重,但根本性的问题则始于更早。在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全球化慷慨地回报赢家,同时将许多输家抛在后面,世界主要民主国家中产阶级的工资已停滞不前,而经济上的不平等则一直在急剧地加剧。
这些趋势不是商业周期的临时性副产品,也不是因为对“金融业”监管不足、昂贵战争中的减税行为或者其他的错误政策,正如经济分析家丹尼尔·阿尔伯特(Daniel Alpert)、罗伯特·霍克特(Robert Hockett)和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最近在《前进之路》(The Way Forward)的研究报告中坚持认为的,工资的停滞不前和不平等的日益严重,是数十亿低薪工人融入全球经济以及因信息技术用于制造业而使生产率提高的一个结果。这些发展已经使得全球产能远远超过需求,从而让西方工业化国家高工资经济体的工人损失惨重,由此在西方选民中造成的混乱和不满更因全球化对跨国威胁,诸如国际犯罪活动、恐怖主义、不受欢迎的移民和环境退化的强化而被放大,促成这种令人不快的混合的则是信息革命;互联网和大量的大众传媒不只是在培育慎重的辩论,看来也正在助长意识形态的两极化。
面对着经济胁迫、社会混乱和政治分歧,选民指望他们选出来的代表能提供帮助,但正如全球化迫切需要治理的迅速反应一样,它也使得迅速治理的供应是极为有限的。出于三大原因,西方工业化国家政府都进入了一个明显无效的时期。
首先,全球化已经使自由民主国家所采用的许多传统政策工具变得十分迟钝。华盛顿定期求助于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的绩效。不过,在全球竞争和空前规模的债务中,刺激开支的举措或者美联储的利率调整几乎影响不了美国经济。商业和金融资本流动的范围和速度意味着其他地方的决策和发展——北京在人民币价值上的不妥协,欧洲对自身金融危机反应缓慢,投资者和评级机构的行动以及现代公司最新款车型质量的提高——在重要性上超过了华盛顿所做出的各项决定。欧洲民主国家长期依靠货币政策来适应国家经济绩效的起伏波动。但当它们加入欧元区后,它们就放弃了这种选项。日本在过去20年里已经尝试了一个接一个的经济刺激战略,但却没有什么结果。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各民主国家对结果的控制已大不如以前了。
其次,西方国家选民要求政府去解决的许多问题需要某种难以达到的国际合作水平。权力从西方向其他地区的扩散意味着今天有发言权的新人太多了;有效行动不再主要依赖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间的合作了。相反,它依赖于范围更大的和更加多样的国家群体间的合作。美国如今指望二十国集团来重新平衡国际经济。但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并欣然接受不同经济治理做法的国家中,共识是难以达成的。诸如遏制全球变暖或者有效孤立伊朗等挑战,也同样有赖于遥不可及的集体努力。
最后,虽然当选民感到满足并就不断提升的期望达成共识时,各民主国家是可以实现反应灵活和迅速的,不过当公民情绪低落和分裂时,它们则是动作笨拙和反应缓慢的。比起分担牺牲来,在治理上依赖民众参与、机构制衡和利益集团间竞争的各个政体看起来更善于分享好处,但牺牲恰恰是恢复经济偿付能力所必不可少的,这就使得西方国家政府面对着推行可能削弱自身选举诉求政策的不利前景。
一个问题三种味道
在美国,党派对抗正在使得政治制度陷入瘫痪,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状况不佳。自2008年以来,许多美国人失去了他们的房子、工作和养老金,而且这些挫折都是在10年来中产阶级工资停滞不前之后接踵而至的。在过去10年里,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已下降了10%以上。其间,收入的不平等一直稳步上升,使得美国成为工业化世界里最不平等的国家。美国工人资产不断下降的首要根源是全球性竞争;工作一直在流往海外。此外,数字经济中许多最具竞争力的公司并没有多少政治影响力。脸谱网的市值估计为700亿美元左右,而且它雇佣了大约2000名员工;相比之下,通用汽车的市值仅为350亿美元,却在美国有7.7万名雇员,在全球有着20.8万名雇员。美国尖端公司的财富并没有往下扩散至中产阶级手中。
这些严酷的经济现实正在帮助意识形态和党派分歧复燃,而这些分歧此前因美国经济财富的不断增加而在很长时间里已悄无声息了。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广泛共享的繁荣将民主党和共和党拖向政治中心。但现如今,美国国会在很大程度上既缺乏稳健派又缺乏两党合作:民主党围绕着更多的经济刺激、失业救济以及对富人征税而展开竞选活动,共和党则极力呼吁大力削减政府的规模和费用。党派选区的重新划分,煽动性的媒体环境,被特殊利益所把持的破碎的竞选财务制度加快了中心的空洞化。
由此造成的两极化正在让美国陷入困境。奥巴马总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何他在就职时许诺成为一位“后党派”总统的缘由。但奥巴马为振兴经济和恢复两党合作所做最大努力的失败,已暴露出美国经济和政治功能的系统性失调。奥巴马的7870亿美元刺激方案是在未获众院一位共和党议员支持的情况下通过的,该方案是无力振兴饱受债务、中产阶级就业不足以及受全球经济放缓困扰的美国经济的。自共和党2010年获得了众院控制权以来,党派对抗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阻挡了前进步伐。促进经济增长的法案要么未获通过,要么被明显打折以致没有什么效果。移民改革和遏制全球变暖的立法甚至未被摆上桌面。
无效的治理,再加上日复一日的党派斗争,已经将公众对国会的支持率推至历史低点。正在蔓延的挫折感已催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自越南战争以来第一场持续的公众抗议活动。随着地位脆弱的政治家迎合该党的狭隘利益,而且政治制度失去了起航时的一丝微风,选民的不满只会加剧各项治理挑战。
与此同时,欧洲的治理危机则以政治重新国有化为表现形式。公众反感欧洲的一体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双重混乱。因此,欧盟各成员国正在忙着追回各种主权,从而威胁到二战后启动的欧洲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大业。正如美国的情况一样,经济状况是该问题的根源。过去20年,欧洲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在下降,而不平等程度则一直在不断上升。西班牙的失业率徘徊在20%以上,甚至在德国这一欧盟首要经济体,也能看到中产阶级的规模在2000-2008年期间收缩了13%。那些逃过此劫的人发现自己脚底下是一个正在磨损的安全网;面对全球竞争,欧洲安逸的福利制度已变得无法持续了,正在遭受大幅度的缩减。欧元区债务危机导致的这种紧缩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希腊人对欧盟强行紧缩开支的愤怒程度并不亚于德国人对不得不解救欧洲经济落伍者的愤怒程度。
欧洲正在老化的人口已经使得移民变成为一种经济需求,不过由于在使穆斯林移民融入社会主流上缺乏进展,加剧了欧盟在接纳更多外来人口的不适感。极右党派一直是这种焦虑的受益者,而且它们锋芒毕露的民族主义所对准的不仅仅是移民,而且还有欧盟本身。世代交替正在对公众对欧洲一体化的热情造成损害。对二战有着深刻记忆的欧洲人将欧盟视为欧洲摆脱其血腥过去的逃生路径,但较为年轻的欧洲人则没有任何所要逃避的过去。鉴于他们的前辈将欧洲统一大业视为一种信念,因此目前各国的领导人和选民往往以一种冷漠的——而且往往是消极的——成本效益评价来对待欧盟。
欧盟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获得繁荣发展所迫切需要的集体治理,令人不安地取决于对欧洲大业抱有明显敌意的街头政治。欧洲各机构可能卑微得像其政治一样,这种情况事实上将欧盟降格为仅仅是一个贸易集团。否则,国家政治可能再次被灌输一种欧洲的召唤,这将向一个越来越空洞的联盟注入新的合法性。后一种结果虽然较为可取,但它将需要领导和决心,可是至少眼下任何人都找不到它们。
至于日本,自从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2006年辞去首相以来在政治上一直随波逐流。此后,在战后大多数时间里主宰着日本政治的自民党出现了严重失误,在2009年将权力拱手让给了日本民主党。两党制的巩固虽然具有改善治理的可能性,但却导致了僵局以及公众信心的不断下降。在过去5年里,日本已更换了6位首相。刚刚过去的夏天,民主党的公众支持率仅为18%。民主党和自民党内部分裂的程度并不亚于两党相争的程度,即使在紧迫的问题上,决策过程也已经陷于停顿;国会通过向地震、海啸和核灾难受害者提供救济的立法,就花了100多天的时间。
这种麻烦开始于1991年日本资产泡沫的破裂,泡沫破裂暴露了该国经济中的更深层问题,并导致了陷入经济衰退的“失去的十年”的一大挫折。随着工作和投资流向中国和“亚洲诸虎”,日本的制造商就遭了殃。该国传统的社会契约,各公司提供的终身雇佣制度和宽裕的养老金,已不再是可持续的了。过去20年已造成了中产阶级收入的长期下滑和不平等的不断加剧,而贫困率则从20世纪80年代时的约7%大幅度升至2009年的16%。1989年,日本的人均GDP位居世界第四,而2010年的排名已经暴跌至第24位。
正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小泉发起了雄心勃勃的、旨在实现经济自由化并打压官僚和利益集团权力的努力。虽然他的魅力和国会的充分支持有利于获得重大进展,但他领导的自民党以及民主党的继任者太软弱,无法将这一进程继续推进。日本由此陷入一个无人区域,面临着一个尚未放开或者在战略上尚未足以展开有效竞争的全球化经济里所带来的种种混乱。
良药苦口
西方的治理危机与崛起大国新形成的政治实力相随而行,这不是偶然的;经济和政治的活力正在从国际体系的核心传向外围。而且在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随着融入一个全球化世界而遭受控制权损失之时,非西方的国家则正在刻意通过集中决策和国家监管来维持它们对各自社会的更严密控制。随着发展中国家设计各自崛起的路线图,如果各主要民主国家继续失去它们的影响力,那么全球力量的过渡将会明显变得更不稳定。反过来,如果西方民主国家重拾并提供有针对性的领导力,那么国际强弱排序的重新调整可能会变得更加有序。
所需要的只不过就是在21世纪找到令人信服的办法来解决民主、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之间的紧张状况。这项新的政治议程的目标应该是重申大众对政治经济的控制权,将国家的行动引向对全球市场的各种经济现实和大众社会公平分配利益和牺牲的要求做出有效反应。
西方国家应该推行三大策略来迎接这一挑战,从而更好地为一个全球化世界配备民主制度。第一,面对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市场的强大力量时,西方民主国家除了以空前规模参与战略经济规划之外别无选择。为恢复经济竞争力,就需要国家去主导就业、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等方面的投资。第二,高举平民主义的进步大旗,各国领导者应该设法把选民的不满引向改革主义者的目标。通过推行有利于大众而非本党或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政治家不仅能够重新确立信誉度,而且能够重振各种民主制度以及公民和奉献价值。第三,西方政府必须引领选民摆脱内转这一诱惑。正如历史所表明的,艰难时期可能会激起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但全球化却停滞不前了,而退却不是一种选项。
这些战略没有一个是容易推行的,而且欣然接受这些战略还需要相应的非凡的领导能力和政治勇气。不过,在确定和实现这一议程前,对民主的这种忧患将会继续存在。
选自美国《外交》杂志2012年1/2月号
原文标题:Globalization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