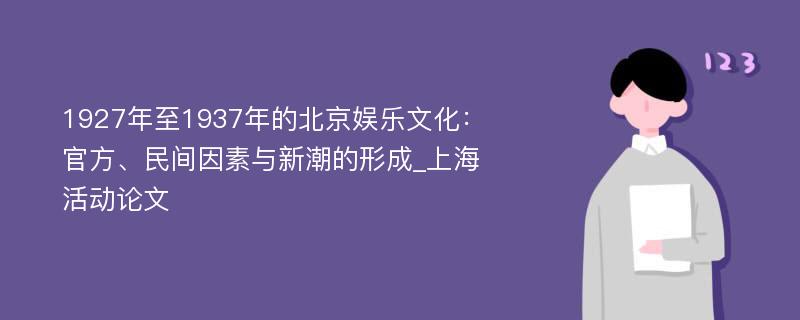
1927—1937年的北京娱乐文化——官方、民间因素与新时尚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娱乐论文,新时尚论文,民间论文,因素论文,官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7—1937年的北京(自1928年6月起,被南京国民政府改称为北平)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市民的娱乐文化丰富多彩,娱乐的物质载体——各种类型的娱乐场所遍布内外二城。戏园、茶馆、妓院、杂技场作为传统的娱乐场所继续占据重要地位,但电影院、公园、舞厅、游乐场等新型娱乐场所也在向市民提供新式娱乐生活。
北平市政当局对于市民的娱乐活动采取鼓励态度,并参与管理,力图引导其发展方向。而民间力量也积极介入,推陈出新,这就推动了北平娱乐文化的更新和发展。
到目前为止,涉及到民国北平娱乐文化的书籍文章不少,但有代表性的专论并不多。崔普权的《老北京的玩乐》一书,有助于人们了解北平百姓娱乐活动的一些基本情况;刘宁波的《北京娱乐游戏民俗的演进与成因》、林一白的《北京的花会与幡会见闻》等文章对北平的娱乐文化有专项介绍。但1927—1937年间官方、民间因素是怎样参与到北平娱乐文化中的?这些参与活动同新的娱乐时尚形成的关系如何?学术界到目前为止还少有研究。本文以民国原始档案和报刊杂志为主要研究材料,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缺失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 娱乐活动中的官方角色:新式公共管理和风化审查
对于娱乐文化业,北平市政当局的施政重心在于公共娱乐场所的管理和娱乐内容的风化检查,具体负责部门是市政府下设的社会局、警察局、卫生局。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被当时很多人认作是新时代的开始,北平市因应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制订了一些富有新意、带有科学性的法令条文,对市民的娱乐活动有一定正面影响。从这个角度讲,市政当局的管理思路和管理内容已有别于过去,故称其为“新”。
市政管理条例明言:娱乐场所“应有卫生、消防及安全等项设备”(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932。)。北平的娱乐场所,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式的,都得配备消防器材,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卫生方面的规定更具体,查证今天北京档案馆的档案,在民国北平市政府第142号令上有这样的记述:“查本市公共娱乐营业场所,关于通气采光设备,大都不合标准,尤以厕所建筑简陋,公用面巾及所售饮食物极为不洁,均足影响市民健康,本局曾经分别调查,填有记录详表。”(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由此可见市政当局已把民众健康放在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依此制定相关的卫生条例。对于与顾客的健康有密切关系的饮食卫生更有严格要求,“一切饮食用具每次使用后须以沸水冲洗或经其他有效方法消毒后方准再用;不沸之水及不洁食物不准供给顾客”(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卫生条例中甚至规定了各娱乐场所应提供给顾客的空间,每人“至少须在三五立方公尺(约合英制一百二十四立方尺)以上”(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此外,还规定了室内的温度、采光,“必须有适宜之调温设备;于适当处所必须悬挂温度计至少一个以上并须随时作温度之检查;必须有人工换气装置或将门窗按时开启以便放入新鲜空气,倘已有之门窗流通空气不足时须增加及改良之”(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最主要的是“新鲜空气之换入量及室内空气之温度、湿度、速度必须调制适宜以使顾客不感气闷、过热、过冷为标准”(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
为了保障民众在公共娱乐场所中的人身安全,还严禁患有肺结核、花柳病、疥癣和其他传染病的人在公共娱乐场所充当伺役。
在《北平市警察局管理舞厅规则》中,舞厅中受限制的人更多。“舞厅应限制泥醉者、有传染病者、未成年人,以及携带危险物而有妨害秩序之虞者进入厅内。”(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932。)舞厅的营业时间受到控制,夏季不能超过晚十二点,冬季不能超过晚十一点,只有“星期六星期日得延长至翌日二时”(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932。)。舞厅的经营也有规定,如舞厅内所卖的饮料、食品的价格不能高于市价;舞票的价格也不能任意变更;“舞厅雇佣之乐队及舞女不得演奏妨害善良风俗之音乐及舞蹈”,“舞厅雇佣之舞女不得奇装异服或有其他违害善良风俗之行为”(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932。)。对于屡犯规定、利用舞女以色相招引顾客的舞厅,市府即予以停业惩罚。由于多数舞厅对管理规则置若罔闻,有一段时间北平所有的舞厅都被勒令停办。以上这些规定和举措说明,这一时期的北平市政府,确实是想把娱乐活动导向健康和文明。
但从效果上看,却并不理想。仍举舞场为例,“一般摩登青年男女,正在嗜之若狂,哪能因为被官家封了舞场,就不跳舞,所以一般外商为迎合他们的心理起见,变本加厉,在外国人势力范围内,设立了很多的舞场,把这些失业的舞女,完全收罗了去,大大的干起来”(注:《大公报》,1933年2月3日。)。像北京饭店、华盛顿饭店、德国饭店、利通饭店、长安饭店、北平饭店等,均设有舞场。市警察局和社会局对这些舞场确实下过停办的命令,但洋人不听,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中国人开办的舞场,也有不少转入地下继续营业,舞女们的活动更隐秘,令警察局和社会局很头疼。
电影院则是使用女招待,“听说有个电影院女招待是多极了。这个影院不用说,人家也知道他们不是靠影片吸引观众,而是专靠女招待们来号召顾客的。这戏院的经理限制女招待的条件很严,如果每日每人售茶不满一元,那三天内就得开步走了。然而她们的工钱,每月不过六元。如果她们售茶不多的话,她们只得自己辞退了”(注:《大公报》,1933年4月30日。)。有些女招待为多卖茶,就免不了与一些轻薄的顾客打情骂俏了。
表一:30年代中期北平一些影院经营及纳税情况表(注:根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J1-3-91、J2-7-337、J2-7-338、J2-7-339中的相关数据制表。)
名称 地址 开办时间 座位数 放映场次 票价 捐税 经营状况
中央电 北新华街
1927年850个
2或3场 1—6角市政捐、弹压勉强维持,盈
影院25号
2月 捐、慈善捐、利甚微
广告捐、房捐
及附加税等
光陆电 崇文门内
1930年900个
3场 2角7分市政捐、弹压尚能维持,稍
影院大街1999月
到9角 捐、戏捐、慈有盈利。但
号 善捐、广告 1935年亏损
捐、公益捐、5000元
印花税。
大观楼 前门箭楼
1935年室内2场 1角、1市政捐、弹压亏损
电影院 5月
240个
角8分 捐、慈善捐
露天
350个
飞仙电 东城灯市
1936年800个
2场,周六
1—4角市政捐、弹压亏损
影院口12号 1月
和周日3场 捐、慈善捐、
舞场、影院等娱乐场所的色情因素屡禁不绝,主要原因在于经营者的牟利意图和政府的高捐税政策发生了冲突,老板们于是不惜冒风险,借用美色多招引顾客,以图保本或盈利。
市府对各娱乐场所征收高捐税的情况,我们可举影院为例来说明。在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中,有关电影院的材料比较多,内容也比较详细。
把各影院的平均票价、放映场次和座位数(因观众时多时少,取其平均座位利用率)放到一块计算,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全年不间断,每天都放映,中央电影院一年收入约为114700元(精确到百位数),光陆电影院为291600元,大观楼电影院为29700元,飞仙电影院为69120元。上述数字还只是我们今天粗略统计出来的字面上的数字,并不代表影院当时的实际收入,因为有各种影响其收入的因素我们并未考虑在内。战争、政局变动、灾异、经济不景气,片源不济等都会造成影院一时的关闭停映。这样看来,各电影院一年的收入其实并不多,但要支付政府名目繁多的捐税,再加上各种设备的购置与维修,工作人员的工资发放,其他额外开支,这就使得一些电影院面临盈利微薄甚至亏损的状况。
这一现象在舞场、戏园等娱乐场所也较为普遍,而且相比较而言,电影业的利润还要大一些。舞场、戏园靠正常营业难以盈利,就采取各种办法招徕顾客,包括舞女、淫戏等色情手段。在北平市政府看来,娱乐场所就存在着令其头疼的风化问题。
北平市政府对娱乐场所的风化问题有一整套审查制度,因一些审查内容,如舞女系民国时代才出现的新现象,而审查手段如动用社会局、警察局也有别于过去,故称之为新式审查。
按照市政府的规定,传统或新式的娱乐节目,都要经过社会局审查备案。审查通过,无伤“善良风俗”,取得许可后,才可以公开表演或放映。如有涉猥亵的,则将此剧禁演,饬令改正才能再行公演。
社会局还经常派人去娱乐场所进行检查,一般来讲,天桥一带的娱乐场所中的问题较多。一个社会局的科员在报告中写到:“为呈报事。奉派检查天桥各戏棚及一切娱乐场所等因。遵即前往调查,计吉祥、凤记、丹桂、荣和、魁华、华安、三友轩等分别检查,除吉祥、凤记、丹桂、荣和、魁华所演均系徽秦旧剧,大致尚无不合外,其华安、三友二家均演评戏。计华安所演为黄爱玉,三友所演为高成借嫂。华安茶园角色表演尚无大差之处。惟三友轩系男女合演,猥亵不堪。女角计大香蕉、大面包二人,均系三十余岁妇人,装束妖冶,作态狎亵而词句多粗鄙不堪入耳,致使一般下级顾客狂呼怪叫,其势若狂,且零碎打钱。而该女角等每有向顾客随便打诨,殊属有碍观瞻。查该轩利用猥亵唱作招引顾客为日已久,而兼卖女座似更属非宜,若不严予取缔,将来影响社会风化实有不堪设想之处。”(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261。)
一般来说,剧本及演出内容是重点审查对象,但有时演员的服装也在检查之列。“奉派检查白玉霜所演《拿苍蝇》是否有伤风化等因,遵即前往。查该伶所演之《拿苍蝇》前半部,系秦腔班所常演之孟姜女哭长城本事,尚无不合之处。后半部剧情,系三个女性苍蝇精,迷惑两男性青年,由白伶及两女伶分饰苍蝇精,着白色卫生衣裤,长筒丝袜、红色兜肚,裤长不及膝,紧裹其身,外披翼形氅衣,由苍蝇成精起至被天兵捉拿止,除生子一幕着衣裙外,其余各场,均着上述衣饰。且全场电灯熄灭,用五色电光,照耀台上,该伶等且歌且舞,宛如裸体,剧情及唱词,亦均极猥亵,实有审查章程第五条乙项第二款情事”(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102。)。
接到社会局通告,警察局遂对白玉霜戏班进行了处罚。“查女伶白玉霜,演唱《拿苍蝇》一剧。经查前半部,尚无不合。后半部各场其剧情、唱词以及服饰、做工均猥亵,亟应停止公演,以维风化。……其女伶白玉霜,嗣后无论在何戏园,均不得演唱此剧”(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102。)。
当然,因国民党力行党治,北平市政府对娱乐活动的审查还包括政治审查,《北平市戏曲审查委员会章程》规定:取缔那些违反“党义”的演出剧目。从档案材料上看,带政治色彩的演出并不多,多数剧目是感情戏、家庭戏、历史戏、神怪戏。
从娱乐场所风化审查、纠改的效果上看,有时并不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警察与老板相勾结,为不法经营充当保护伞。如西单新商场后门内,路南静轩茶社的“坤书杂耍”,其主持人姚佩然,是一个地痞流氓。他从天桥约来的“鼓姬”,即边敲鼓边说唱的女艺人金玉玲、赵金环是兼操色情业的人。她们“每日除登台奏曲外,即在该社门前招摇,施其狐媚手段,无识者流,一经入内,伊等即百般勒索。昨日有某校教员高某(辽宁人,年二十许),在该场因点曲发生龃龉,某便衣大加威吓,高即质问理由,并坚欲随行受罚。幸经在场顾客竭力排解,一场风波始平,某便衣亦潜迹遁去”(注:《北平老百姓日报》,1933年8月31日。)。
旅美学者王笛在《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一文中指出:“中国警察介入市民社会代表着国家企图建立一种新文化的努力。”笔者对此观点表示同意。只是警察等政权力量自身的文化素质有不少问题,再加上他们对文化活动的特质缺乏了解,这种努力往往效果不彰。况且旧有的社会文化形态、次序很难通过行政命令、公文条例被摧毁,建立一种新文化往往障碍重重。1927—1937年间的北平市政当局,也只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作些文化改良的工作,尽力规范娱乐文化等市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官方导向性明显,而官本位社会中人们对威权力量又习惯性慑服,再加上这些导向不乏进步性、科学性,因此北平市政当局的这些努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有别于旧式娱乐的新时尚的形成。
二 民间力量的参与:娱乐文化转型的推动
娱乐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民众休闲文化,由于远离党派、阶级、主义等各种社会严肃主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随机性和可塑性,就比较容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自我变迁。当然,一定的动力是必不可少的。
1927—1937年的北平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娱乐文化的发展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对于它的未来走向,北平各阶层人士都给予了积极关注,并努力参与,施加自己的影响。
北平当时是新旧文化并重之地,市民的阶层结构也比较复杂。既有满清贵胄遗老,也有北洋政府退休的官吏、各地来京的达官贵人,这些官僚阶层人士偏好传统娱乐活动,是维系旧式娱乐文化的主力。但北平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区,新派知识分子的力量也比较强大,这些人往往成为推动新式娱乐事业产生和发展的中坚力量,又有一心扩大娱乐文化市场、想利用百姓的喜新厌旧和猎奇好玩心理赚钱、投资新式娱乐业的民间资本家的支持。斯时的北平娱乐文化,在保持多元色彩的同时,在朝着求新求时尚的方向发展。
新派知识分子对娱乐文化转型的推动。首先是对旧式娱乐文化的改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戏剧的改良。他们对京剧的因循守旧很是不满,认为旧戏一是太迷信,好演神仙鬼怪的故事,与科学多不相合,给无知识的观众造成不良影响;二是官戏太多,动不动就演状元及第,会激发观众的做官当老爷心理;三是演全本戏太少,仅能取悦个别票友,而一般顾客则多茫然,难感兴趣;四是剧词质量不一,有的太雅,有的太俗。
随着梅兰芳等人对京剧的成功改良,新派人物的论调也有所改变。胡适、周作人曾主张把京剧根本废除,或是把唱功废掉,但看过梅兰芳的表演后,又主张保存京剧了。钱玄同曾骂京剧脸谱为“粪谱”,但这“粪谱”在二十年代中期却赫然印在戏剧刊物的封面上。
也有一些人坚持认为,京剧在整体上并没有大的改变。“改而能良,如果不是丧心病狂,绝不能提出任何理由来反对,然而现在所谓国剧改良,我却以为绝不是推进国剧运动之正当途径”(注:《老百姓报》,1935年1月19日。)。指出所谓的改良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没有完整的计划。一些戏班班主看到改良新剧有市场,就委托一些戏曲专家改写剧本,这些专家“把语句通顺一下,有断章取义的把场子略事增删,不但并未提高原剧之价值,而且使人感觉到所修改之处,与全剧有了显然的不调合,而班主们便大言不惭的在剧名上大标其改良×××以诱惑观众”(注:《老百姓报》,1935年1月19日。)。
京剧的改良,有的戏班成功,有的不成功。原因何在呢?从根本上说,改良京剧,是为了使这种传统娱乐文化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这就需要改良者既熟悉旧京剧,又了解新文化,当时这样的人却不多。对旧剧最熟悉的当数梨园人士,但除梅兰芳等少数人外,多数梨园人士却“不可与谈新戏”。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文人,其文化背景又多建构在社会的上层,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编出的新剧自然难以扎根在民众的土壤中。一些新剧“有的是鸳鸯蝴蝶派的风流剧本,有的是新奇的布景来引人入胜,它不但是麻醉了一般青年学子们的敏活底心腔,而且对于现在社会上的人群,也无多大的裨益”(注:《北平老百姓日报》,1934年1月24日。)。
但无论怎样,在新派人士和梨园界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旧京剧已经开始了现代转型,能部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潮流了。
在不断探索、努力改良京剧的同时,新派知识分子还积极提倡新式娱乐文化,如话剧。
北京和上海都是中国话剧的发源地,但北京普通百姓觉得话剧比较粗陋,不如京剧细腻,对话剧不太感兴趣。喜欢看话剧是一些知识分子及大、中学校的学生。大家就共同努力,在社会上宣传、推广话剧。早在1922年,戏剧家陈大悲等人就在北京创办了人艺戏剧学校,专门教授话剧,此时更不遗余力地推动话剧的研究、普及与发展。林徽音“精研舞台布景及导演诸法”,对中国话剧做了细致解说,澄清了一些人“话剧粗陋”的错误认识。她介绍说:“现代话剧可分三派,一是构成派(Constructivism),布景略具物体的轮廓;二是表现派(Expressionism),布景简单,但观众目之所及,却能会意于不言中。演员表演注重象征,比如演一个人悲痛,可以做类似的动作,而不必大哭掉泪;三是写实派(Realism),布景逼真,演员众多,演出跟真的一样。由于京剧表演手法,与话剧表现派有相似之处,因此京剧观众渐渐明白,话剧和京剧并非不能沟通。一些人遂由最初的反感话剧,而变得慢慢接受它了。话剧也终于在1928年,经过新派人士的不断改进和努力,成为北平市民们认可的戏剧品种了。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也是话剧的正式命名年(注:1928年,戏剧大师洪深、欧阳予倩、田汉聚在一起,讨论“新戏”、“文明戏”的正式命名问题。洪深提出用“话剧”一词,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从此这一称谓就确定下来,一直沿用至今。不久洪深专门写了《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一文,又解释了话剧的含义,“话剧,是用那成片段的、剧中人的谈话,所组成的戏剧”。)。
新派知识分子还积极提升娱乐文化的意义,把它与社会时势、国家民族联系起来。“九一八”以后,有人提倡在新的形式下戏剧应该“国防化”,戏剧界人士应该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不能再吟风弄月,伤春惜秋了。“国防文艺”、‘民族文艺’的口号也相继提了出来,娱乐文化开始与国家大事接轨了。
民间资本对娱乐文化转型的影响。1927—1937年的北平,文化娱乐新旧并呈。民间资本家看好新式娱乐文化市场,认为有较大的商业利益,就纷纷投资建设电影院、舞厅、台球厅、公园、游乐场。比如北平的两个大型游乐场城南游艺园、新世界都是由私人投资兴建的。这些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平娱乐文化的转型和发展。
电影刚传入北京时,是依托于茶馆、戏园的。“电光影戏京中称为电影,初自泰西流入中国南方各埠,继自上海、天津等处流行入京,惟常设专演之处亦无多”(注:中华图书馆编辑部《北京指南》,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1919年版,第10页。)。一些戏园、茶楼在演戏之余会加演电影。1927年以后,电影已与戏园、茶楼分离,在都市娱乐空间中有了独立位置,扮演的娱乐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这与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影院有很大关系。“十年以前,北京之电影院,寥寥无几。就余所知,仅东城之平安与城外之大观楼而已。盖斯时京人于电影,听之不能成瘾,更何论乎鉴别。平安皆外侨与豪阔贵眷,大观楼皆学生与店贾。北京之与电影,极幼稚矣。与上海较,相去何止十倍。嗣后有北大教授吴某,出而组织真光社,就东安市场丹桂茶园之址,于选片颇具心思,拟与平安相抗,而抑大观楼之势,果也收效不恶。更由粤商罗明佑君,纠集股份,而创真光剧院于东华门外,遍征文人,研究设备。对于院内布设,一洗从前戏院恶习,大受社会欢迎。……电影生涯,遂为人注目”(注:涤秋《谈北京之电影院》,《北京画报》1937年第2卷第3期。)。
北平的舞场当时并无官家经营,对其投资的多是民间资本家或外商。舞场不如影院受欢迎,一是跳舞与中国传统价值观有出入,二是跳舞需要去学,需要技术。去舞场的多是学生、职员、秘书、洋人。显宦、财阀、商贾倒不轻易涉足舞场。
跳舞是比电影更西化的娱乐文化,它从形式上突破了北平人习惯的男女社交界限,市民们围绕跳舞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反对的人说:“跳舞场中的人才,多半是小姐、少爷,或是少奶奶们。家里过的安闲日子,整天没有事情做,怎么不想找这些地方去开开心呢?说到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要多认识几个异性朋友,而在众目炯炯之下,显一显他们的技能。”(注:《大公报》,1927年7月13日。)跳舞没什么价值,“寓娱乐于跳舞”是“满足肉欲”。赞同跳舞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潮流,对于跳舞有伤风化的议论,他们指出“这是很可笑的理由,假使没有跳舞,那么‘风化’就无伤了吗?譬如有姨太太的人们,那个不是监视极严,但结果多半闹出许多笑话来,这也是跳舞之过吗?”(注:《大公报》,1927年7月22日。)赞成者还将跳舞与男女平等划上了等号。“在现今女权极幼稚的时候,应当设法提倡才是,提倡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先使男女平等,所以我以为跳舞实为男女间平等的游戏,高尚的娱乐,由此渐渐推广,一切事情男女必能合作,由此女权必可迅速的发展。反对跳舞,本无关系,但轻视女界,压制女权,其罪可不小啊!”(注:《大公报》,1927年7月22日。)古老的北平有不少人对跳舞肯定,说明在对待娱乐文化的问题上,市民的思想观念确实有所进步。
公园在北平的娱乐文化中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从皇家园林发展而来的,体现了平民文化势力的上升。北平第一座严格意义上的公园是中山公园,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私人资本有关,是用民间集资募款的形式建成的。时人认为,公园能使一般市民“都能够在当中,从精神的受其洗涤……社会的教养,都概行提高。加之,更有了都市生产上能率的增进,都市全体,因能够有疲劳与困惫的灭亡上效果。凡是文化的远大之理想,也是它应有的职能和功效了”(注:《大公报》,1929年2月1日。)。逛公园作为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其娱乐主体最齐全,娱乐人群的范围最广,包含了城市几乎各个阶层的人士,但也各有侧重。以北海公园为例,“北海的所在地,因为临近北大与国立图书馆,所以在清晨,时有大学教授等等名流雅士,手提文明杖,漫步在荷叶青青、藕花艳艳的海岸”(注:《大公报》,1933年7月25日。)。一些平民百姓也会游乐其中,这主要是因为公园门票比较低廉。中山公园的门票开始为10个铜钱,折合银元0.074元;到1927年才改为20个铜钱,折合银元反为0.053元,是一般市民花得起的。
参与新式娱乐活动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平民化,说明它已经变成普通市民阶层的娱乐。娱乐人群的扩大,导致各娱乐场所都扩大规模,力争客源。商业演出所面临的市场压力和竞争也就更大。投资人顺应时势,纷纷改良旧的经营模式,采取了一些新的经营方式,比如先期售票、分门进出等等。
民国初年至20年代,北平各娱乐场所多是不卖票的,门口也没有什么人把守,观众可以随意出入,各种小贩、茶役也是自由往来。在演出开始一段后,才开始收钱。茶役“你给多少钱,也向你哓哓勒索,语音无味,态度可憎,直闹得你加钱满足其欲望而后已”(注:《北平老百姓日报》,1933年10月4日。)。等到老板们借鉴了上海等业界同行的管理经验,才有了先期售票的方法,采取对号入座的管理方式。先期售票在电影院更是形成了制度。
以前,娱乐场所进场与出场是同一道门,这样一来就显得异常拥挤。一些影院采取了分门进出的方法,即散场后,出场观众走两旁的太平门,而入场观众走正门,这样就秩序井然,避免了拥挤现象,提高了文明程度。
总的说来,虽然北平的市民文化比较传统,“北平的生活,可说完全是代表着东方色彩的平和生活。那里,生活的环境,是十分的伟大而又舒缓。不若上海以及其他大都市的生活那么样的急促,压迫着人们一步不能放松地只能向前,再也喘不过气来。又不若内地各埠那么的鄙塞简陋,使人感受着各种的不满足”(注:倪锡英《北平》,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51页。)。但由于民间人士对新式娱乐业的持续投资和经营,新的娱乐文化一直平缓但稳定地发展,终于在1927—1937年间与旧式娱乐分庭抗礼,并日益深入人心。
民间资本投放的趋新性,使得北平的娱乐文化能够不断吸收新元素来发展自己,并与外地文化保持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流。公园的开放、话剧的发展、剧场的建设等等都受到了上海等城市娱乐文化的有益影响。有时候,上海文化更直接被引入北平,“麒麟童的上海机关戏,在北平开演了。10年前,北京戏在上海被人尊重,现在,上海戏在北京来却也大作广告。上海把北京给征服了”(注:《北平老百姓日报》,1934年6月24日。)。民间资本家从外地吸取经验,对北平的娱乐文化进行建设,促进了北平娱乐文化的转型,而转型又带动了这一时期北平娱乐新时尚的形成。
三 结语:娱乐新时尚的形成——从主体、本体到观念
在传统社会,娱乐是有性别的。意思是说,娱乐的主体——即娱乐人群必须鲜明地分为男人和女人,男女的娱乐活动不应该相同。封建礼法之下,社会舆论反对把两者混淆,而是主张双方各守本位。实际上,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教,在实践中则很难百分百地严格区分、执行。
进入民国以后,女性在娱乐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女子娱乐生活的实质内容都随着时代的进步、妇女自身的不断解放而发生很大改变。男女社交已经公开,男女平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特别是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女性,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为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而抗争。
妇女对娱乐活动的积极参与,是北平娱乐新时尚之一。虽然较之上海妇女晚了几年,但北平妇女急起直追,也要在娱乐文化生活中,和男子分得一样的权利。如在剧场中设置女座,这在当时还是颇引人注目的,时人做诗曰:“正坐洋椅不能盘,粉纸印来大戏单。楼上粉黛人似玉,满园不向戏台看。”(注: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46页。)很多女子还抛头露面,从事娱乐他人的职业。女性在娱乐业中的从业人数、收入、影响力等方面已经可以和男性平分秋色了。比如舞女的收入。舞女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舞票,通常情况下,一枚大洋可购三枚舞票,舞客以现金向舞场购票;陪客的舞女则从舞客那里得到舞票作为酬金,然后拿着舞票去舞场老板那里换现金,一般是六枚舞票换得一个大洋。“盖舞场须扣去其半也,故每夜得票三十张者,可得五元进款,六十张者,可得十元。视舞场营业程度而定,亦视舞女之号召力如何。姿容秀丽之舞女,为一般舞客所欢迎者,彻宵达旦,无时或辍,每夜收入,恒自二十元至三十元不等,此外月薪尚不计也。以舞女一夕之收入,是乡农半载年勤之所不及,小学教员一月中所不能得者。“(注:《大公报》,1933年2月3日。)各娱乐场所也都聘来女艺人充门面,吸引顾客,如城南游艺园,专门设有坤伶场,邀请一些女艺人来此演出。
分析北平女性在娱乐业中影响日增的原因,首先是她们自身才艺的提高。以前女演员艺术功底不深,人们看她们演戏,只是为了消遣,“自不能见重于世人也”。很多女艺人仅以“色”取悦于观众,唱腔则不堪入耳,被称为“鬼音”。但自雪艳琴开始,越来越多的女艺人在才艺上为人倾倒。雪艳琴嗓音甜润圆亮,一如梅兰芳、尚小云,各剧院抛开以往的成见,竞相聘其为台柱,观众也爱看女子唱戏了。其次,男女艺人性别偏见渐除。民国初年,无论是京剧还是话剧,男女还不能合演。男演员不屑于和女演员合演,老师也不屑于收女弟子。到了1928年,男女合演之风兴起,各剧院也都提倡男女合演来吸引观众。一些女演员也红极一时,影响力大增。
除娱乐主体的变化外,北平娱乐文化的本体——娱乐活动的内容自身,也在与时俱进、吐故纳新。实际上,与时俱进是娱乐文化自身的一种本质属性。
娱乐活动内容的趋新和商业化,是北平娱乐新时尚之二。1927—1937年间的北平,新式娱乐文化渐渐从旧模式中摆脱出来,形成自己的范式。电影院使电影的演出场所专门化,不再同传统娱乐共享空间;话剧在打开市场后,渐渐朝专业化发展,不再是不伦不类的组合。因前面已有阐述,在此对这二者及公园、舞厅等新式娱乐不再累叙,只对流行歌曲这种颇具现代娱乐色彩的娱乐文化做一介绍。在当时的北平,流行歌曲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影院放映的影片中的主题歌和插曲,如《西厢记》中周璇唱的《拷红》、《月圆花好》;《木兰从军》中陈云裳唱的《月亮在哪里》;《续三笑》中李丽华唱的《深闺吟》、《闭门羹》;顾兰君在《刁刘氏》中唱的《临刑曲》;路明在《弹性女儿》中唱的《双双燕》和《红粉飘零》中的《四季情歌》等等。这些歌曲都是影片中主要演员本人演唱的,由唱片公司灌成唱盘,发行于市。……另一类是由当时的专业歌唱演员录制的唱盘,以姚莉、姚敏为最有名,而且姚敏又擅写词曲,当时的流行歌曲中,大约每三首就有他们二人写的一首”(注:《北京文史资料》第59辑,第132页。)。
由于流行歌曲有较大的市场价值,民间投资者纷纷经营这种娱乐项目,一些舞女也改行唱歌了。一开始,歌女还知道自爱,歌曲也不太低级和色情。但很快,一些歌女就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唱起淫词浪曲了。
娱乐文化内容的趋新,部分是由当时娱乐活动自身的商业化性质造成的,利之所在,商家逐之,原不奇怪。而传统娱乐如京剧,因不如新娱乐项目吸引人,就一度面临困境。“就事实来看,现在各戏班里,除了四大名旦同高马杨等能够常悬‘座满’之牌外,此外恐怕没有一个班莫不是叫苦连天。即以言菊朋而论,其演剧之肯卖力,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连演《洪洋洞》、《长坂坡》两出大戏,上座也不过四五成而已,其不景气为何如,从可知矣”(注:《北平老百姓日报》,1934年4月22日。)。
为迎合娱乐商业化的潮流,改变利润微薄的现状,一些娱乐场主就对娱乐活动进行商业包装演出。如在北京上演的广东戏,“裸腿高跟鞋旗袍的大乔,在北平登台了。十年前,京戏最重规矩,由脸谱到脚上的靴鞋都有一定的法则。现在,摩登古人登台了”(注:《北平老百姓日报》,1934年6月24日。)。
当时娱乐本体的趋新,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北平市民娱乐观念出现了新变化。虽仍有争论,但总体上日益开明。
为娱乐文化“正名”,是北平娱乐新时尚之三。当时,北平市民已开始正视人自身的娱乐休闲需要,认为娱乐对人有正面意义,并主张提高对娱乐文化的正确认识。“普通的社会,每多茶肆酒店,烟馆赌场,多数的平民,没有不藉此以解闷。何以故?因为现在的平民,智识既薄,也无正当的消遣,其以为消遣者,不是集人作赌,便在酒馆狂饮;不是荡马路,逛游戏场,便入花丛间解闷。至若远足、音乐、打球等等,在他们固视为常事,也不屑的藉为消遣。因此当消遣者不以为消遣,不当消遣者以为消遣,也何怪趋入歧途呢?。”(注:杨流云《日常所忽略的几件事》,《生活周刊》1927年1月,第136页。)
也有少数人否定娱乐文化,认为:“不论什么消遣方法只要是消遣,都是无益的;而且非惟无益,实在有害。人类的一切罪恶,莫不从消遣中产生出来。”(注:《大公报》,1933年6月12日。)
这种论调受到了大家的抨击。“人们所以变坏的主因,绝对不能归咎于人类的有消遣,这正是十足表现出来人们不知道怎样应用业余消遣所致。真正了解、会应用的人,不但不致于堕落,而且可以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无形中反倒防备着堕落呢!一方面远离了坏习惯的侵袭与潜化,他方面更于自己的身体上、精神上、人格上都逐日无限的能向上发展着”(注:《大公报》,1933年6月12日。)。
由于北平社会存在阶层分化,在一些市民的观念中,娱乐文化也具有“阶级性”。“多少人呢,多半是为吃饭问题出来奔走,或有问题已经解决了,而图谋他以后的需要,因此就把这世界渲染的说不出的一种繁华,同时也就把所有的人们判断出若干的阶级,和什么‘上’、‘下’的名词。资产阶级的人是最先把这问题解决了,但解决以后,还有许多的需要,什么身体的享受必要安适,精神的感受必要快活。所以都市里的楼房、山村里的别墅、庄严的戏院、华贵的舞场,这多是他们这类人调剂精神、舒畅身体、寻找娱乐的所在。但是这类人不过占社会里最高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呢?是以身体和精神换来些劳动的钱,在这休息的空闲,也须有些娱乐,以安慰他那疲劳。但享受的程度,是要随着身份。所以由这点起,就分析出若干的阶级来,一般的人们,也就按着他的身份,去享这相当的娱乐”(注:《大公报》,1933年3月22日。)。
应该说,市民对娱乐文化作用的评价,对其特性的一些概括,都是在为北平娱乐文化“正名”。从1927—1937年北平娱乐文化的实际情况看,市民所“正”的“名”,是契合实情的。
不同的阶层确实拥有不同的精神生活,北平底层的民众“虽然穷得可怜,可是有了三四毛钱就可以看电影了”。在他们眼中,上层社会的生活也有让人不如意的地方。“可怜那些最大的大人物,……一切公众娱乐的地方都是少去的,甚或有时走几步路都要戒严,想要跑到农村或郊外去领略大自然之美更要兴师动众了,那是何等的不自由呦!”(注:《大公报》,1927年8月22日。)
总的说来,北平市民对娱乐文化的态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有一定规律可寻。人们娱乐观念的开放,说明社会在向前迈进,也说明北平文化在努力寻求现代转型。因为,面对新文化的冲击,民众往往在娱乐层面上先进行尝试,看看能否调适、接受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这提示人们,文化的发展、演变必须与它的主体人群相适应。1927—1937年北平娱乐文化的变迁史已经证明:一种娱乐文化形式的改变如果超出了普通观众的承受力,其生命力是会受到影响的。如当时北平的戏曲,“蹦蹦戏是不雅的、不美的,但是却能够受平民的欢迎。抢匪临上杀场,还得要唱两句白玉霜的句子,这是最接近民间的戏,文人所看不起的。京班渐渐由民间的戏变成文人的戏了。许多无聊的文人替梅兰芳、程砚秋编戏,愈编的好,愈和民间离得远了”(注:《北平老百姓日报》,1934年2月25日。)。而昆曲,“除了三十以上,或专攻文学的人以外,是少人看的”(注:《北平老百姓日报》,1934年2月25日。)。
标签:上海活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