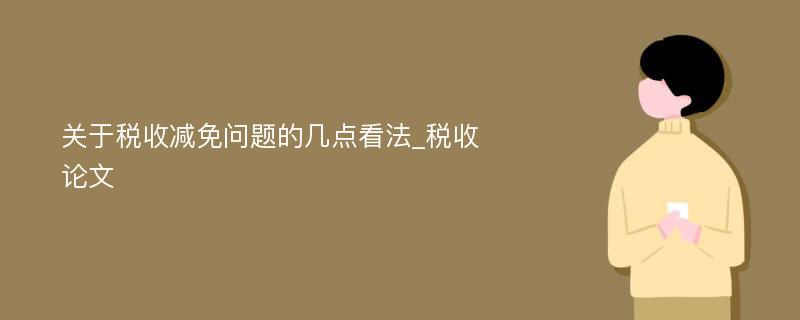
对税收赦免问题的几点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税收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税收赦免的一般分析
(一)税收赦免的基本内涵
根据美国国会联合赋税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1998)的分类,税收赦免项目按政府承诺的优惠条件的宽严程度可以有多种形式。条件最严的赦免形式是,要求偷逃税者缴纳所有的税款、利息和罚款,只对其免除刑事处罚;条件更宽些的赦免形式是,要求偷逃税者缴纳所有的税款和利息,但免除全部的民事和刑事处罚;条件再放宽的赦免形式是,要求偷逃税者缴纳过去偷逃的全部或部分税款,但在免除全部民事和刑事处罚的同时,还免除这些税款应计的全部或部分的利息;条件最宽的赦免形式是,免除纳税人过去偷逃的所有税款和应计利息以及本应给予的民事和刑事处罚,显然这是一种全方位的税收赦免。
从国际实践来看,除了在特殊情况下(如为了将非法逃到境外的资本引回国内)可能实施上述条件最宽的赦免形式外,一般情况下税收赦免并不是对纳税人过去的偷逃税既往不咎,而是指政府对于主动补缴以前的未纳税款的偷逃税者(个人或企业)免除通常情况下需要给予的刑事起诉和全部或部分的罚款。通常所说的税收赦免是一种一次性的、偶然性的赦免机会,即只给予纳税人一次赦免机会,以后一般不再给予同样的机会。(注:不过,在实践中,尽管许多政府在实施税收赦免时通常都会声明“仅此一次”,但过若干年后一些政府(如美国许多州政府)可能又因财政赤字压力或配合税收改革等原因而再次实行税收赦免。)
(二)税收赦免的基本特征
根据世界银行集团(The World Bank Group,2002)的不完全统计,已实施过税收赦免的国家起码有30多个,其中既有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和新西兰等OECD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和转轨型国家(如俄罗斯)。从政策设计上看,税收赦免的主要特征是:(1)在实施期限上,通常为2~3个月,即只有在规定的这段时期内主动坦白并补报补缴的纳税人才可享受减免处罚等优惠待遇;(2)在税种范围上,既可以针对所有税种,也可仅针对某些或某个特定税种;(3)在参与主体上,可以只允许未申报或未登记者参与,也可以允许一般的逃税者参加,但通常不允许那些正受到税务机关审计或犯罪调查、与税务机关还存在未结诉讼、或已被宣判犯有税收方面的罪行的纳税人参与;(4)在参与客体上,可免除罚款的未纳税款包括还未被税务机关所知的未报、少报以及还未注册登记的纳税人的税款,而税务机关已核定好数额并向纳税人发出纳税通知的已知税款即所谓的“应收账款”(accounts receivable)(包括欠税)不一定允许参与;(5)在应纳款项上,一般情况下除了偷逃的税款本金需如数缴纳外,通常还要加收利息,但可以免除全部或部分的罚款,这些应纳款项有时也允许分期支付;(6)在税收执法上,许多赦免项目规定,赦免期过后将加强税务审计,提高对偷逃税的处罚标准,并增加执法经费投入。
(三)税收赦免的效应分析
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政策设计的税收赦免项目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注:关于税收赦免效应的具体分析,参见邓力平、李林木《国外税收赦免的理论与实践》(上、下),《涉外税务》2003年第2期、第3期。)
首先,从税收赦免的短期效应看。一次税收赦免的短期效果可从以下两个指标来判断:一是政府从赦免项目上取得的收入数量,即判断赦免项目的效率水平;二是赦免参与者与诚实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比较,即判断赦免项目的公平程度。Parle和Hirlinger(1986)、Mikesell(1986)以及Alm和Beck(1991)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影响赦免收入大小的因素主要是宣传力度是否强大、是否允许“应收账款”参与、减免滞纳税款的利息、提高赦免期过后的偷逃税处罚标准和加强赦免期过后的执法力度。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允许“应收账款”参与赦免,甚至减免滞纳税款的利息,则使赦免项目的参与者比那些已经依法诚实纳税的人获得了更大的好处,从而损害了税收的公平负担原则。这是因为,政府在对主动坦白补缴税款的偷逃税者免除刑事和民事处罚的基础上,如果还对滞纳的税款降低利息。(使这种利率水平低于市场利率)甚至免除利息,就相当于政府对偷逃税者提供了一笔优惠利率甚至免息的贷款,而对已经诚实纳税的人则没有。另外,是否允许“应收账款”参与也是一个关系税负公平的问题。由于这部分滞纳税款(其中常包含相当部分的利息和罚款)是税务机关已经知道的,并不是纳税人在赦免期主动暴露的,如果允许这部分税款也参与赦免,虽然可加快其收回的速度,但减少了政府的收入(因为其中核定的罚款甚至利息被免除了),并且对于非赦免情况下的同类纳税人来说显然有失公平。
其次,从税收赦免的长期效应看。Leonard和Zeckhauser(1986)、Alm和Beck(1990,1993)以及Alm、Mckee和Beck(1990)等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当税收赦免的实施与赦免期过后执法力度的加强“双管齐下”时,即使纳税人因期待着将来的再次赦免而不愿自觉遵从,但由于所期待的再次赦免伴随的是更严厉的执法环境,使得税收不遵从的预期成本将更大,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纳税人在权衡偷逃税的成本和收益后就会更偏好于税收遵从,结果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赦免对其后的税收遵从和税收收入就会有积极的正面影响,或者至少不会对纳税人的长期税收遵从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地,若纳税人认为赦免期过后的逃税处罚标准和审计概率不大可能提高,则赦免项目不仅很难吸引偷逃税者前来参与,还可能降低以后的税收遵从水平。
二、制约税收赦免成效的条件: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一)税收赦免成效的制约条件: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分析
由于一次性税收赦免的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可能并存,因而理想的税收赦免项目的目标就是要使它的积极效应最大化(即吸引尽量多的偷逃税者前来如实坦白)和消极效应最小化(即抑制其对社会公平和税收遵从的可能损害)。为此,政府必须优化赦免的机制设计,兼顾效率和公平,使纳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政府利益和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根据信息经济学关于机制设计的基本原理,要使税收赦免政策成为最优的机制,作为委托人(即不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的政府必须考虑来自作为代理人(即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的纳税人的两个约束:一是参与约束,也就是要使偷逃税者从参与赦免中得到的预期效用不能小于不参与赦免时能得到的保留效用(即机会成本)。参与约束要求税收赦免政策所针对的纳税人愿意参与,而不采取规避行为。二是激励相容约束,即在政府对纳税人的税源信息不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必须使参与赦免的纳税人有积极性去揭示自己的真实信息,使纳税人诜柽政府所希望的行动(即如实申报)能够得到的预期效用不小于他们选择其他行动(即少报)所得到的预期效用,这就要求政府对纳税人的支付(激励补偿)应当使纳税人发现如实申报是自己的最优选择。由于并非所有的纳税人都偷逃税,因此一项优化的税收赦免政策必须能够有效甄别纳税人的不同类型,使偷逃税者不仅愿意主动坦白,而且愿意如实坦白。也就是说,在这种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下,如实报告不仅符合政府的最大利益也符合纳税人自己的最大利益,只有这样,理性纳税人才会参与赦免且如实申报。从实证研究上看,已有一些学者运用预期效用模型对此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成果表明,理性的纳税人在面临税收赦免机会时的行为决策(即决定参与还是不参与、如实报还是少报),实际上就是他们在不确定性或风险条件下如何实现预期效用最大化的问题。
由于在通常情况下纳税人偷逃税被税务机关查获,除了需要补缴所偷逃税款,还需缴纳利息(滞纳金)和罚款,达到刑事犯罪标准者还要被起诉,因而,偷逃税者在面对赦免机会时是否选择参与赦免并如实申报,其预期效用的衡量就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被减免所偷逃的税款、利息、处罚以及对赦免期过后被查获的概率和处罚率的风险预期。显然,在免除刑事起诉的基础上,如果对税款本金、利息和罚款的减免比率越大,那么对偷逃税者参与赦免的激励就越大。但政府让利过多,则会让诚实纳税人感到不公平,产生消极的政治影响,并使今后的税收遵从水平降低,从而会损害政府的长远利益。基于这种考虑,税收赦免项目通常只宜对参与者免除所有处罚,而不宜免除利息,更不能减免偷逃的税款本金。在利息和处罚的减免程度既定情况下,只有当偷逃税者确信,过了赦免期偷逃税被查获的概率肯定比以前大得多,并且一旦被查获肯定受到严惩,任何人都不例外,税收赦免只是政府在从严执法前给予的“坦白从宽”机会,他们才会在赦免期向税务当局承认过去的偷逃税行为。为此,政府不仅应当预先规定,赦免期过后将加大打击偷逃税的力度,提高处罚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赦免期过后的执法中能切实做到大大提高偷逃税查获率并依法严惩。只有当税收赦免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满足这种动态一致性要求时,其实施的最终结果才能使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博弈达到最优均衡状态。
纳税人偷逃税被查获的概率大小以及查获后能否受到依法严惩,实际上反映了一国的税收征管水平(特别是对纳税人税源信息的获取水平)和廉洁法治水平所构成的税收征管环境。税收征管水平特别是对税源的监控水平越高,意味着政府对税源信息的掌握就越充分,纳税人偷逃税被查获的概率越大,他们从事税收不遵从行为的成本就越高,因而,其偷逃税的可能性就越低。而政府廉洁法治水平越高,意味着偷逃税一旦被查获后越会受到依法处罚,纳税人越难以通过金钱、权力、人情等法外手段获得宽大处理。反之,如果偷逃税者预期在赦免期内不诚实申报,以后被查获的概率不大,或者即使被查获了也有办法以较小的成本减轻甚至免除处罚。那么,不管政府给赦免参与者承诺的激励条件多么优惠和事后对偷逃税者的处罚多么严厉,理性的偷逃税者是不愿来参与的,即使参与了也不会如实申报,因为这种承诺并不具有很强的可置信度,逃税的预期收益远大于预期损失。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哪怕赦免政策设计得再好,其实施的结果也将大打折扣,甚至事与愿违。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税收赦免能否取得成功,不仅取决于机制的自身设计,即能否兼顾激励和约束、效率和公平,也取决于外在的支撑环境,即税收赦免政策所规定的约束承诺能否在实际运作中得到切实履行,内外因不可缺一。(注:在西方学者对税收赦免的研究文献中,几乎看不到他们对最优税收赦免所需要的社会环境的探讨,原因可能是在比较健全的法治环境下,法律政策的规定与实施一般能够做到一致,因而也就没有多大必要去探讨政策的支撑环境问题。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政策的支撑环境显然是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二)经验证据:案例分析
国际上税收赦免的成败案例似乎验证了上述结论。从赦免的结果看,有不少项目取得了成功,如新西兰1988年的税收赦免和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纽约、马萨诸塞、伊利诺斯、康涅狄格等一些州的税收赦免,但是也有不成功甚至是以失败告终的,如法国1982年和1986年、阿根廷1987年、爱尔兰1993年以及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3次税收赦免。以下分别以新西兰和俄罗斯的税收赦免实践为例加以说明。
1.较成功的税收赦免分析:以新西兰1988年赦免为例。新西兰1988年的税收赦免是国际上公认的一次较成功的实践。这次税收赦免共有16083个纳税人提交了24685份赦免申报表,政府不仅获得了2660万美元的税收收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申报资料为税务机关以后的征管提供了重要的详细信息。首先,从政策设计上看,本次赦免充分兼顾了效率和公平。赦免政策规定,对完全如实坦白的参与者免除处罚,不公布其姓名,但滞纳金(late payment penalty)照收——因为政府认为,若不征收滞纳金,赦免参与者的实际税负就比那些已经按时诚实纳税的人低,从而使公众削弱对税收制度的信心;赦免政策还规定,赦免期过后的处罚标准将大大提高,而实际上早在1986年对逃税的处罚标准就已经提得很高了,比如对填写错误的所得税申报表的最高罚款从相当于2000美元提高到了15000美元。其次,从征管环境看,新西兰的税收征管水平和政府廉洁法治程度在世界上是较好的。新西兰1988年~1992年间平均腐败感知指数为9.3,(注:国际上比较各国腐败程度的一个常用标准是“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该指数取值为0(高度腐败)到10(高度廉洁),因而指数越高说明政府越廉洁高效,依法办事,该指数在5以下的国家通常被认为是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参见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3,"CorruptionPerce ptions Index",http://www.transparency.org/cpi/index.html。)纳税人违反税法系数低于10%。(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违反税法的系数将各国税收征管的有效程度划分为四类:第一类国家该系数低于10%,第二类国家在10%~20%之间,第三类国家在20%~40%之间,第四类国家高于40%,因而该系数越低表明征管水平越高。)正是这种良好的征管环境和优化的制度设计的结合使本次赦免取得了良好效果。
2.不成功的税收赦免分析:以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赦免为例。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联邦政府面对严重的逃税欠税和巨额的预算赤字(1992年的赤字额相当于GDP的18.9%),先后于1993年、1996年和1997年实施了3次税收赦免。1993年的总统赦免令规定,对于在赦免期内主动补缴未纳税款的纳税人免除任何处罚,在赦免期过后被查获的逃税者将按未纳税额的3倍予以处罚。1996年的赦免则规定,允许分季缴纳欠税,并对纳税人主动坦白的逃欠税降低利息处罚,并声明在赦免期后将提高税务审计频率。1997年的赦免除了规定免于处罚外还对新近批准的延迟缴纳的税款的利息降低50%。但是这些税收赦免政策实施的结果却使欠税问题更为严重:1998年末欠税总额(包括税务机关批准同意的延迟纳税)占GDP的比重高达16%,当年欠税额几乎等于已征收的税款额,尽管从1995年到1998年税收收入提高了1.49倍,但同期欠税却增加了5.85倍。在实施赦免前的1992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9.60%,赦免后的1998年和1999年该比重则分别降为20.27%和27.39%。这3次税收赦免之所以没有达到政府的预期目的,不仅由于其政策设计上的不足,更重要的原因是俄罗斯税收征管水平和政府廉洁法治程度比较低——缺乏比较完备的税源信息监控体系,社会腐败严重,(注:根据“透明国际”组织的评估,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感知指数均在3以下。)依法治税的水平低。尽管赦免令中声称事后将加大审计概率,提高对偷逃税的处罚标准,但在现实情况下纳税人几乎都清楚这种威胁的可置信度不高,特别是那些同政界关系密切的逃欠税者基本上不把它当一回事,结果逃欠税问题仍然积重难返。
三、税收赦免在我国的运用前景
在我国实施一次性全面税收赦免是否可行?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借鉴已有的国际经验,设计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优化政策方案并不太难,难的是我国的税收征管环境能否为其提供足够的支撑条件。首先,从税收征管水平看。通过20多年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的税制和征管改革,我国税收管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征管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建立一个严密的税源监控体系所必需的纳税识别码制度、财产实名申报制度、第三方信息报告制度(third-party information reporting)等在西方国家已广泛实行的监管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实施。另一方面,这些监管制度要落到实处必须依靠强大的信息技术的支持,而我国受到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的制约,尽管近年建立了CTAIS和“金税工程”,但税收征管信息化水平特别是信息共享水平仍较低,(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02年~2006年中国税收征收管理战略规划纲要》,2004年全国约80%的地区实现与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信息联网;2006年争取实现全国税务系统的征管信息系统与税务总局联网运行,约80%的地区实现与银行系统的联网。税务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联网还未纳入规划。)税务机关要想通过先进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充分获取纳税人实际发生的交易往来、收支状况等税源信息还较困难,目前的审计稽查主要还是靠纳税人自我申报和群众举报等传统办法,因而对纳税人的边际审计成本很高。其次,从社会法治水平看。只有当政府的廉洁法治水平可以使纳税人确信,偷逃税一旦被查获肯定受到从重处罚,不可能通过金钱、权力、人情等手段得到宽大处理时,赦免政策所制定的处罚威胁才是可置信的。而我国目前还存在较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人情关系又比较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完全的依法办事还比较困难。因此,在我国当前征管技术水平和依法治税水平都比较低的情况下,一次性的税收赦免是难以取得理想成效的。
那么,在我国目前不能实行一次性的全面税收赦免而税务机关因受到自身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制约无法对所有纳税人实施全面审计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政策可以激励那些还没有被税务机关稽查到的、有过偷逃税行为的纳税人前来主动补缴偷逃的税款而又不会使诚实纳税者感到不公平?国际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所采用的另外一种特殊赦免形式——“常设性税收赦免”(standing tax amnesty)值得我国借鉴。
为了鼓励偷逃税者在未被税务机关发现的情况下主动来补报补缴所偷逃的税款,一些国家或地区在法律上规定对自动补报补缴的纳税人减轻或免除处罚。如,美国联邦国税局的“未申报者项目”(nonfiler program)规定,对于从未填写纳税申报表但主动补报的纳税人,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没有申报是由于合理的原因引起的(如家庭成员死亡、自然灾害导致涉税记录毁失),则可以免除未申报处罚。印度所得税法规定,对于自我坦白的、还未被税务机关稽查的逃税者,给予“一生一次”的免予处罚的机会。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48条也规定,对违反税法者在被检举或调查前自动向税捐稽征机关补缴所漏税捐的予以减免处罚。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荷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都实行了这种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被冠以“赦免”的称呼,并且实际上政府往往避免使用“赦免”之类的措词,(注:比如,美国联邦国税局一直声明其“未申报者项目”不是税收赦免。)但是,由于这种政策同通常所说的税收赦免(即一次性赦免)一样都是对税收不遵从者的主动坦白给予减免处罚的,因而不少学者倾向于把这种政策称为“常设性税收赦免”或“永久性税收赦免”(permanent tax amnesty)。
“常设性税收赦免”同一次性税收赦免相比,两者都具有吸引税收不遵从者前来坦白、减少税务机关的稽征成本、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共同特点,但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明显差别。(1)从目的结果看。前者试图通过“细水长流”式的固定制度以吸引税收不遵从者逐个来坦白,长期增加政府的收入;后者试图通过一次“暴风骤雨”式的偶然政策使最大多数的税收不遵从者“改过自新”,并使政府在短期内获得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尽管实际结果并一定能达到这些目的。(2)从政策设计看。虽然两者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但前者的政策设计相对简单些;后者则相当复杂,对于赦免应适用于哪些税种、哪些纳税人、哪些未纳税款、给予哪些优惠条件并选择在什么时段实施等具体问题都需要预先做出严密规划。(3)从实施管理看。前者在实施时间上灵活机动,政府不需要特别加以宣传,也不需要增加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经费投入;后者则只限于一定时期内,要促进其成功,政府需要在公布赦免方案后加以大规模宣传,需要抽调大量人力从事赦免项目管理(特别是从事赦免申报表的审核处理),需要增加赦免期过后的稽查人员和经费投入。显然,相比之下,一次性税收赦免具有高风险、高成本、高收益的特点,而“常设性税收赦免”具有低风险、低成本、低收益的特点。在一次性的税收赦免受到支撑环境的制约可能难以取得理想成效的情况下,“常设性税收赦免”不失为一种次优的选择。
对于那些在未受到税务稽查情况下愿意主动坦白的偷逃税者,我国目前的涉税法律并不允许免除或减轻罚款,更不用说对其中达到犯罪标准者免于刑罚。而在实际税收执法中,在人情关系等法外因素的影响下,对查获的偷逃税案件从宽处理甚至以罚代刑现象又相当普遍,使得税法的规定与执行并不严格一致,损害了税收制度的公平。因而,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实行一次性全面税收赦免的时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为了激励那些还没有被税务机关稽查到的、有过偷逃税行为的纳税人前来主动补缴税款,我国也可以借鉴和设立“常设性税收赦免”制度。通过修订税收征管法或由全国人大予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允许那些还没有被税务机关发现的但主动前来如实坦白的偷逃税者在补缴税款和滞纳金的前提下,给予免除处罚;同时,对于事前不主动坦白而被查获的偷逃税者则依法予以处罚。这种“常设性税收赦免”制度将有利于节省稽征成本,避免我国税收执法处罚幅度长期受人情关系左右的现象,从而有效地维护税收公平负担原则。实施“常设性税收赦免”制度,对于愿意主动坦白的偷逃税者,即使政府免除其全部罚款和刑罚,只要如数征收税款本金和滞纳金,由于滞纳金的利率大大高于市场贷款利率,(注:我国新征管法规定对滞纳的税款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相当于年利率18.25%,是一年期市场贷款利率(2003年)的3倍以上。)他们就不会比已经按时诚实纳税者得到更大的好处,尽管其负担比起那些不主动坦白而被查获的偷逃税者要轻得多。通过对有偷逃税行为的纳税人在制度安排上的区别对待,将可以有效引导他们选择政府期望的类型,使纳税人之间从低效的混同均衡转变为高效的分离均衡,从而实现征税的帕累托改进,有利于维护税制的公平,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