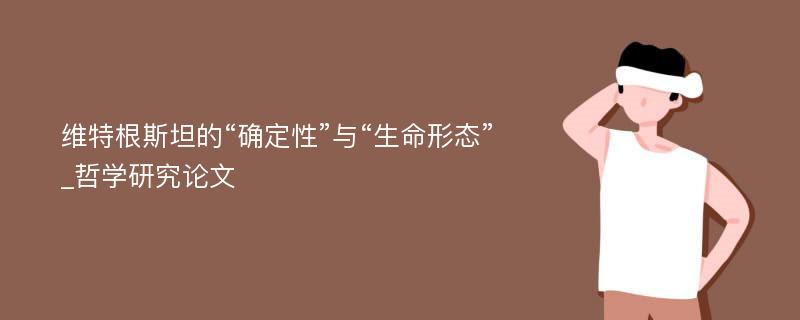
维特根斯坦的“确定性”与“生活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确定性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确定性”与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等概念一样,是与知识有关的一种重要性质,因而是认识论必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半时间中集中研究了这一问题。他写下的有关这方面的思考笔记,死后以《确定性》为名出版。在这本书中,维特根斯坦的思考所直接针对的对象,是摩尔在反驳怀疑论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论证。摩尔这方面的思想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a.他列举一些所谓“常识”(Common snse)性的命题,如:我有两只手;我是一个人;地球在许多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等等,宣称“我确定地在此时知道(know)这些命题”。例如我可以通过先后举起我的左手和右手来表明这一点,而这是无可怀疑的。他认为,如果有谁要否认他知道一命题,只承认他“相信”(believe)这一命题,那是“十分荒唐的”。(G.E.Moore:Proof of an External world,pp145-146.In Moore;philosophical Papers,Allen and Unwin 1963)
b.在摩尔看来,一个证明要是能够满足如下三个条件,那就是一个完备而严格的证明。第一,证明的前提必须不同于有待证明的结论;第二,证明的前提必须是我所知道是如此的某种东西(was something which I know to be the case),而非只是我所相信但不确定的东西;或只是虽然事实上是真的,但我并不知道是如此的东西。第三,证明的结论是确实由前提所得出的。(同上书,第146页)
c.按照上述证明的标准,摩尔得出的结论是,他所作出的关于常识命题的证明是完备而严格的,“不可能再给出任何关于无论其它什么东西的更好或更严格的证明了。”(同上书,第146页)并且,由于证明了手、我、地球等这类客体的存在,他也从而证明了另一类与常识命题不同的哲学命题,即外部世界的存在。
二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摩尔的上述证明存在着一些错误。这些错误集中表现在对知识与“常识”命题的理解上。首先,摩尔对“知道”(know)的性质的理解是错误的,因而他误用了“我知道”一语。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摩尔对这类常识命题及其“确定性”性质,以及它们在语言游戏中的功能,有着本质上的理解错误。下面让我们加以具体说明。
1.知识的性质与“我知道”(I konw)
A.维特根斯坦认为,从“我知道某某东西如此”,推不出“某某东西是如此”,因为仅仅给出“我知道”这样一个主观性的保证(assurance)是不够的,这只是保证我不会犯错误。维特根斯坦指出,当人们说“我知道”时,往往忽略了这实际上指的是“我想我知道”(I thought I know)。显然,“我想”只是一种主观的东西。这种状态总是存在犯错误的可能。但我们需要的是客观地确认我对于这某某东西并没有发生错误。(L.Wittgenstein:On Certainty,Oxford,1969.§12—14。以下该书简称为“OC”)因此,当摩尔反驳怀疑主义者的不可能真正认识事物的说法时,“他不能用向他们保证他知道这个或那个[事物]来进行,因为人们无须相信他。”(OC,§520)即使这样的保证是来自一个可信赖的人,也同样是无济于事。因为即使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向我们保证他知道事情是如此这般的,也并不足以使我们相信他的确知道。只有他自己才相信他知道。维特根斯坦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摩尔保证他知道的说法并不使我们感兴趣的原因。
另外,与上述说法有所不同的是,在《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中,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关于“我知道”的通常用法与哲学家的用法之不同。他写道:“在可以怀疑之处,我们说‘我知道……’;反之,哲学家说我们知道某件事,是严格地在没有怀疑之处。因此在这里,‘我知道’这一用语作为一个命题的引入,是多余的。”他举例说,“‘我知道……’通常意味着‘我断定……’。没有人说他断定他有两只手。”(L.Wittgenstein:Last Writing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Oxford,1982.§18,§243)这是从通常的“我知道”的用法上反驳摩尔的证明。
B.知识与相信不同,前者是需要提供证据的。因为由“我知道”直接引发出“你是如何认识的?”维特根斯坦写道,“‘我知道’通常意味着:对于我的命题,我有正确的根据。”(OC,§18)也就是说,“我知”与证明该命题的真实性相联系(OC,§243);我能够向别人指出我是如何知道该命题的,而别人也可能据此来接受或否认它。因此,假如其他人也熟悉这种“语言游戏”(即熟悉该语词或句子的使用),他就会承认我知道这个命题。这与“我相信”某一命题不同。一方面,作为“相信”,我可以不给出根据,而仅仅作为个人的信念。这类信念仅具有主观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假如我给出的一些根据并不比我所做出的断定更肯定,那么我不能说我知道我所相信的。由知识需要“根据”这一特征,维特根斯坦否定了摩尔那些常识命题能够作为“我知”的命题,因为它们不但不需要寻求根据,反倒是为其它命题提供根据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些根本性的命题,维特根斯坦称它们为“河床”、“底基”等等。换言之,它们就是“生活形式”本身,不属于认识论的范围。指明这类命题的这一根本性质,是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的主旨。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详加论述。
C.知识总是具有可怀疑性,因而与确定性相关。维特根斯坦认为,知识的一个特点在于它们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从而是可以怀疑的。一个认识某物的人,具有怀疑的能力。怀疑意味着思想。不可能被怀疑的东西,同样也不可能具有确定性。而没有确定性也就谈不上是知识。知识表现为一些普遍的经验命题,它们具有客观的确定性。这类确定性来源于它们的根据。所以,维特根斯坦写道:“我知=我确定地熟悉它。”(OC,§272)
维特根斯坦认为,诸如:“我知道我身上痛”,“我知道我牙痛”,它们或是无意义的,或只是意味着“我身上痛”,“我牙痛”。因为,“说其他人怀疑我是否痛是有意思的;但不能这样说我自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21页)也就是说,某人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的疼痛是没有意思的。既然不可怀疑,也就不属于知识的范畴,因而也就不能使用“我知”这一用语。因为,我是否知道某事依赖于是否有证据支持我。所以,知识的可怀疑性与确定性是与它们的根据性相联系的。
2.怀疑与确定性
既然怀疑构成知识的一个特征,而确定性则成为与知识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因此这两个概念就成为知识论研究的必要问题。前面提到,摩尔将“这是我的手”之类的常识命题看作是不可怀疑的、具有确定性的知识,认为它们具有同数学命题一样的认识论地位。他并且相信,通过这些命题他已成功地驳倒了怀疑论,证明了外部世界的存在。在上一部分里,我们已经看到,维特根斯坦论述了摩尔在知识性质上的错误。这里我们将进一步分析维特根斯坦对“怀疑”以及“确定性”的性质的思考,以及他在这些问题上所认为的摩尔的错误。
A.“怀疑”的性质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怀疑要成为有意义的,必须满足一些条件。他所提到的条件有如下这些:
其一,怀疑必须有根据。
维特根斯坦举例说,假如有人要怀疑诸如“我有大脑”,“这座山已经在此地存在很久了”之类的命题,那么我们说他没有怀疑的根据。因为任何东西都支持这些说法,没有任何东西反对它们。“因此,合理的怀疑必须有根据?我们可以说:‘有理性的人相信这一点。’”(OC,§323)
其二,怀疑仅在语言游戏中有效。
这里,“语言游戏”主要指的是语词的使用。例如,假如我要怀疑这是否是我的手,这时我已经不可避免地关联到这一语词的意义。但只要懂得这一语词的意义,这是否我的手也就不成其为问题,它正是我所知道的东西。由此也可说明确定性的一个性质。“确定性存在于语言游戏的性质里。”(OC,§457)
其三,怀疑只能在正常的状况下进行。
在正常的情况下,我有两只手是确定的,就像任何我能提出证据的东西一样。但是假如有人说他怀疑他的手的存在,反复地从各个角度看它们,要去确认这不是镜子中的幻像,那么这不能说是怀疑。
其四,“怀疑”以确定性为前提。
“怀疑本身是建立在不疑的基础上。”(OC,§519)维特根斯坦举例说,假如你在遵从一个指令“递本书给我”,那你必须检查是否在你面前的真是一本书。此时你至少知道“书”指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那你可以查查字典,但你必须知道其它词意指的是什么。某个词意指如此这般,在如此这般的方式下使用这一事实,就像前面所说的对象是一本书一样,是一个经验事实。
“因此,为使你能够遵从一个指令,必须有一些你并不怀疑的经验事实。”“怀疑的游戏本身以确定性为前提。”(OC,§115)
其五,怀疑一切并不是怀疑。
维特根斯坦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有个学生不接受老师的任何解释。他不断地以怀疑来打断老师,例如关于事物的存在、词的含义等等。老师只得对他说,不要再打断我,照我所说的去做。你的怀疑一点意思也没有。维特根斯坦指出,“假如你要怀疑一切,你将怀疑不了任何东西。”(OC,§115)孩子们首先通过信任大人来学习。“怀疑来自相信之后。”(OC,§160)
B.确定性
在这一问题上,维特根斯坦主要表达了如下三个观点。一是将“确定性”概念区分为“主观的”与“客观的”两种;二是认为“确定性”与知识分属不同范畴;三是将“本源的确定性”视为“生活形式”,也就是说,将摩尔的常识命题、人们的实践活动,看作是思想与语言游戏的基础。这一观点可说是维特根斯坦后期“生活形式”哲学的进一步发挥。
其一,主观与客观的确定性。
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们用‘确定’一词表示一种完全的确信,没有怀疑,并由此试图使别人也相信。这是主观的确定性。但在什么时候某个事物是客观地确定的?当错误是不可能时。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可能’?是否错误必须被逻辑地排除?”(OC,§194)这时,维特根斯坦的“主观的确定性”是指某人自己对某个命题、某个事情的相信,这可从他的“试图使别人也相信”这一说法中看出来。因此,这里的“主观”,指的是仅限于“个体”方面的相信,因而纯粹是一种主观的状态。我可以完全确信我的某个想法是正确的,但不难明白,这有时只是一厢情愿,它们是会出错的。
客观的确定性则相反,它是不会有错的。但问题正在于,有如维特根斯坦问及的,这是什么样的“不可能”?是逻辑的呢,还是经验事实的?维特根斯坦曾试图把它解释为事实方面的。他写道:“是否任何情景都支持而不反对某一假设,它就是客观确定的?人们能够这么说。”这种意义上的客观确定性是一种很强的确定性,我们可以把它等值于“真”。因为假如任何情景都支持而不反对某一假设,这个假设就是一个真的判断。不过,维特根斯坦继续问道,“但是否它必然符合于事实的世界?它向我们最好地展示了‘符合’的意思。我们难以想象它是错误的,但也难以运用它。”(OC,§203)但维特根斯坦似乎对上述这段话没有把握,因而在笔记中划掉了它。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在思路上与康德将客观性等同于普遍有效性有点接近。康德认为,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性是两个可以互相换用的概念。因为,当一个判断符合一个对象时,关于这同一对象的一切判断也一定彼此互相符合;反之,如果我们找出理由把一个判断当做必然的、普遍有效的,那么我们也必须把它当做客观的,因为没有理由要求别人的判断一定符合我的判断,除非别人的判断同我的判断所涉及的对象是同一的,它们都同这个对象符合一致,因而它们彼此也一定符合一致。(参见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3—64页)不过不同的是,康德的“普遍有效性”是与人们的判断有关,而维特根斯坦的“任何情况”则关涉的是事实的世界。
其二,知识与确定性分属不同的范畴。
首先,知识与主观的确定性不同,这是维特根斯坦明确表示的。“不存在任何关于我知道某一事物的主观确信性(sureness)。确定性是主观的,不过不是知识。”(OC,§245)他举例说,因此,当我说“我知道我有两只手”时,“它不应当只产生主观的确定性,因而我必须能够使自己相信我是正确的。”(OC,§245)但我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我看了我的两只手后,并不比看之前有更多的确定性。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应当注意的,一是维特根斯坦区分开知识与主观确定性的不同。“我知道”(I know)既然是“知”,就不会是一种主观确定的东西,它必须能够提供真实的证明。二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说在我看了我的两只手后,并不比看之前有更多的确定性,这是由于他把这类摩尔的常识命题与知识区别开来。这类常识命题不属于通常哲学上所说的经验命题或真值命题(这里我用“真值命题”一语,仅限于借用它的有真、假之两种可能之义)。维特根斯坦将这类命题界定为知识的基础。它们与经验命题的关系,就像河床与河水的关系一样。这类常识命题具有另一种确定性,我们马上会谈及这一点。
其次,客观确定的是一些普遍的经验命题。维特根斯坦举例说,假如某人的手臂被砍断了,它就不会再长出来;某人的头被砍掉了,他就死了,再不会活过来。这类普遍的经验命题之所以具有客观的确定性,关键在于它们能够被提供出关于这种确定性的根据。“对于我的确信,我有令人信服的根据。这些根据使这种确信成为客观的。”(OC,§270)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知识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根据性。维特根斯坦指出存在着无数的具有这种客观确定性的命题。
再次,最后一类确定性是超出于确证或不确证的范围之外,即具有这种确定性的命题本身既不真也不假,它们就是上面提到的摩尔的“常识命题”。维特根斯坦之所以说它们超越真假与确证的范围,原因在于它们构成经验命题的基础。维特根斯坦这方面的思想完整说来是这样的:
a.他把经验知识看成是一个完整命题的系统。在这一系统里,前提与结论是相互支持的。我们把此系统中的命题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有待确证的经验命题,二是作为确证的基础的“常识命题”。上面提到,维特根斯坦把它们比作河床与河水的关系。这里值得特别提及的是,维特根斯坦又把“常识命题”本身看作是一个系统,认为某一假设的所有的验证,所有的证实与否证,都已经在这一系统里进行。对于我们的所有论证来说,这一系统不是某个或多或少任意的、或可怀疑的出发点,而是属于我们称之为论证的本质。
b.之所以说它们属于“论证的本质”,理由在于维特根斯坦将它们看作是某种“世界图画”(OC,§95)。它们是我们从小通过学习而承继下来的知识文化背景。我们根据它们来区分出经验命题的真与假。因此它们虽然在形式上是经验命题,但在我们的经验命题系统中,却具有“特殊的逻辑作用”(OC,§136)。这种作用就像“游戏的规则作用一样”(OC,§95),即起一种“描述的规范”的作用,使我们以从小学得的知识作为规范来从事研究。因为不论我们检验什么事物,我们已经预先以某些不受检验的事情为前提。这类规范来自于我们通过实践行为所掌握的“事物的稳定性”。例如,通过书写的练习,我们掌握了写信的一些基本格式。因此这些“常识命题”,作为“先决命题”,作为认识的基本框架,是免受怀疑的。它们就像是一些铰链一样,有待确证的命题是围绕它们旋转的。它们稳固地存在着,构成所有思想与判断活动的基础。这类“常识命题”与有待确证的命题的关系,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就像是“河床”与“河水”的关系一样。虽然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关系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哪些经验命题作为“河床”,哪些作为“河水”,这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改变。不过,不论何时,总是存在着“河床”,作为判定经验事实的真假的根据,这是毫无疑义的。这里,维特根斯坦的所为实际上是关涉到哲学上的一个传统努力,即为认识寻找一个最终的根据。虽然维特根斯坦反对形而上学,把哲学的作用界定为“治疗”、“描述”的作用,但他后期哲学的核心,实际上却在于给出一个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世界图画”,尽管他所用以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与方法和传统哲学大为不同。
c.这种世界图画从根本上说是我们的实践、行为、生活形式。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我们对经验命题、信念提供根据、论证、确认的有效性过程,最终会遇到它们的界限,结束于某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并不是某些直接显现为真的命题,而是我们处于语言游戏底基的“行为”(OC,§204),是我们的“实际经验”,就像如果我们把手放进火里,它就会被烧伤一样。“这就是确定性”。维特根斯坦认为,“确定性”一词的意义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也就是说在“火”与“烧伤”这一事件之间的联系中,表现出事件发生的齐一性。这里的“齐一性”与前面的“恒常性”,表现了确定性在事件方面的客观特征。所以,从这两个特征的说明上看,维特根斯坦似乎在把“确定性”区分为主观与客观两类之后,又把客观的确定性确认为事件间联系的一种属性。不过令人不解的是,他又有这样的说法,即“完全的确定性仅与人们的态度有关”,而不是人们在某些方面以完全的确定性认识着真理。在《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并把这种确定性明确地等同于“生活形式”。他写道:“现在我想把这种确定性不是看作某种类似于轻率、表面的东西,而是看作生活形式。”(OC,§358)
三
“生活形式”这一概念,在不少研究者看来,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并且也是一个最难以理解的概念。(G.D.Conway:Wittgenstein on Foundation.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1989,p.31)虽然这个词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生前正式出版的唯一著作《哲学研究》里仅仅出现五次。这里,我们不妨把它们摘录如下:
a.“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哲学研究》,第15页)
b.“这里‘语言游戏’一词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同上书,第19页)
c.“‘所以你说人类协定决定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真是假的是人类所说的内容;他们在使用语言时的一致。这不是意见方面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上的一致。”(同上书,第120页)
d.“只有会讲话的人才能够希望吗?只有掌握了一种语言的用法的人,也就是说,希望这种现象是复杂的生活形式的样式。”(同上书,第241页)
e.“必须接受的,被给予的,是——我们可以这么说——生活形式。”(同上书,第315页)
由于维特根斯坦本人没有对“生活形式”这一概念给出任何定义,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对此就有多种的解释。J.Hunter曾把它们归结为如下四类:
a.把“生活形式”视为与“语言游戏”相同一,也就是把语言看作是作为复数的生活形式之一,看作是某种在我们的生活中成型了的、规范化了的东西。
b.认为“生活形式”指的是在不同情况下行为具有的共性,如某些面部表情和姿势,做诸如数苹果、帮助别人之类的事情,或谈论某些事情。这属于心理方面的解释。
c.认为说某种东西是“生活形式”,等于说它是某种生活的方式、类型、时尚等;是某种与阶级结构、价值、宗教、工业与商业类型等表现作为群体的人们的特征有关的重要东西。这属于文化方面的解释。
d.从生物性方面作出解释,把“生活形式”看作属于生命存在体的典型的东西,如生命有机体的生长,对环境所作出的反应等。(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5,No.4,October 1968,pp233-243)
应当说,Hunter的上述概括只是大致的,因为就笔者见到的资料而言,就有一些研究者把“生活形式”理解为自然历史的一部分,理解为人类的共同行为,如N.Malcom,N.Garver等。(N.Malcom:Nothing is Hidden.Cornell Univ.Press,1986,p.237.及N.Garver:The Complicated Form of Life.Open court,1994,p.258)本文认为这种理解一般来说是恰当的,不过并不完整。完整说来,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应当说包含这么四个方面:
一是人类继承下来的共同文化背景。这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图画”。在上一部分的末属,我们提到,维特根斯坦把摩尔的“常识命题”视为属于“论证的本质”,因为它们是我们用以区分有待确证的经验命题之真假的“世界图画”。而“生活形式”所起的作用之一,也正是这样。它作为本源的确定性,在知识的系统中,起着“河床”的作用。而这种“世界图画”,维特根斯坦把它界定为我们从小通过学习而继承下来的知识文化背景。
二是作为“自然历史”的一部分。维特根斯坦写道,“命令、询问、叙述、聊天同吃喝、行走、玩耍一样,是我们自然历史的一部分。”(《哲学研究》,第21页)此外,当他在讨论意识、内省等问题时,他指出,“我们现在所提供的其实是对人类自然史的评论。”(同上书,第170页)这样,从意识到行为,这些生活形式的不同内容,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都是自然史的一部分,这与他把“世界图画”看作是人类继承下来的文化知识背景是相一致的。
三是人类的共同行为。维特根斯坦说,即使狮子能说话,我们也无法理解它。这实际上说的是,要理解一种语言,只有通过语言使用者的遵守规则的共同行为。而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这意味着生活形式的含义之一是人们的共同行为。
四是作为“习俗(习惯、制度)”(德文原文为Gepflogenheiten〔Gebrauche,Institution〕)。(同上书,第109页)维特根斯坦写道,“遵从一条规则,做一个报告,下一条命令,下一盘棋,都是习俗(习惯、制度)。”按照他的“讲语言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的说法,这里他所举的例子都属于生活形式的内容。维特根斯坦甚至讲到连主观的意图也是受习俗所制约的。“一种意图深植于其处境中、即人类的习俗和惯例中。”(同上书,第147页)因为假如象棋游戏的技巧不存在,人们也就不可能有下棋的意图。他把“生活形式”看作是“被给予的”,实际上指的就是习俗与习惯。
本文认为,至少应从上述四个方面来把握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才是恰当的、完整的。反之,孤立地从某一个方面,如语言、自然史等,来理解这一概念,则是片面的。
四
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既是等同于习俗、继承下来的文化知识背景等,那么他的这一概念以及“确定性”概念,就具有一种保守的品格。他认为我们用以判定经验命题真假的基础,是这些所谓“常识命题”,是由习俗、制度、共同行为以及继承下来的文化知识背景等构成的“生活形式”。这样一来,现成的生活形式就成为既定的前提,成为认定事物真假的出发点,成为思考问题所依据的“河床”。但这样一来,哲学就失去它的批判的品格,成为现成事物的辩护士。而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它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恰恰就在于它对现存事物的思考与批判。这种批判形成一种理性的“法庭”,努力确保为社会提供进步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
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不由使人联想到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先于科学世界的、我们具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这一“具体的生活世界是科学地真的世界的基础”(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Northenwesten University Press,1970.p.131),即科学的经验世界的意义基础。他这一概念的提出,乃因痛感实主义思潮所引起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即人类生存意义的危机,而要以这一概念来确认生存世界的本源性,以及作为这一世界的意义的赋予者的人的主体性。这样,虽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角度不同(价值论与知识论),但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两人在这方面却有共同点,即都以日常的、具体的生活世界作为科学经验世界的基础。这似乎是世界的俗世化(与宗教的神圣化,哲学的形上化相比照而言)的一种结果。哲学在日常生活的形式与世界中确认自己的本源,并从而引申到科学与社会的基础。
就“确定性”概念本身而言,维特根斯坦这方面的分析提供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的框架。他从知识的性质入手,从怀疑与确定性的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确定性”概念的特征,并对它从类别上加以分析,这些都是开创性的。不过,他把“常识命题”作为确定的“先决命题”,作为认识的基本框架以及判定经验命题的真假的根据,这一作法似乎难以成立。像“我有两只手”、“我是一个人”这样的命题,虽然很稳固,但它们能在判定经验命题的真假上起什么样的作用,是很可怀疑的。因而,把它们作为“本源的确定性”,也就没有什么意义。我想,我们在知识论上需要的,毋宁是客观的确定性与逻辑的确定性。前者属于在经验领域得到确证的命题,后者则是在逻辑上得到确证的。尽管深究下去,一个命题是否能够得到最终的确证仍是问题。因为人们总是不难找到理由来对一个命题的确定性提出进一步怀疑的。不过,这方面的探讨已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