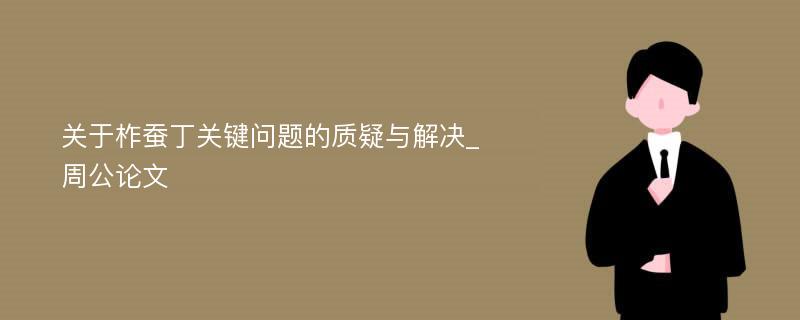
关于柞伯鼎关键问题质疑解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键论文,柞伯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柞伯鼎铭存在的关键问题、重大争论考察揭要
先释柞伯鼎铭文如下:
佳(维)四月既死霸,虢中(仲)令柞白(伯)曰:“在乃圣祖周公,繇又(有)共于周邦。用昏无及,广伐南国。今女(汝)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既围城,令蔡侯告遂虢中遣氏曰:“既围昏。”虢中(仲)至,辛酉博戎。柞伯执讯二夫,获馘十人。其弗敢昧朕皇祖,用作朕剌(烈)祖幽叔宝尊鼎。其用追享孝,用祈眉寿万人(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一)《文物》2006年第5期刊载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东证》,对中国国家博物馆2005年征集入藏的柞伯鼎铭文有关史实、年代、地理、民族等问题详予考证,提出一些新见,为鼎铭研究铺垫前进道路。但还存在一些关键问题,需要进一步商讨解决,使其重要价值更能彰显,并对西周金文与古文字学以及地理、历史研究都能起更多作用。最近我正在撰写《西周金文战争与民族历史地理研究》,作为《两周金文大系续编》中几个要项的综合研究,以免在正卷中产生多次纠葛,先予梳理疏通。此鼎伐南国、伐昏两次战争,既为拙稿增补新篇,也为已提出若干论点互证、匡补。多年用心,不少能予解难决疑,至为难得,实有“冯妇攘臂下车”,一举擒获的振奋心情。但是一如战争,哪里能想象这么简单?何况包括两个战争,牵涉不同时间、地域及主持者,问题复杂、纠葛,不同一般战争。朱文广征博引,资料甚丰,实是费力之作。按我一贯主张应运用全局、发展、辩证综合三个观点,进行科学“三真”、“三查”,除复按朱文所有资料证据之外,尽我所能查检有关资料、证据,已超过朱文范围,现还不能说全备,但确已发现诸多重大史实真相有异于朱文,而皆为铭文根本与要害问题。铭文牵涉伐南国与伐昏两次不同战争的时间、地域、主持人等历史与地理,尤其是地域演变极为纠葛,而都无可调和、折中解决。争论症结就在于铭文文字、文句的考定解释之异同,这是立论的根本基础,即使有很大困难,也无法回避。先后近两年,主要就是在试图清除这些拦挡去路的钉子,牵扯实在太多,而紊如乱丝难理,“并非好辩,实不得已”,决非求胜于任何人。很多烦琐考证,连我撰写此文过程中,也深感头痛眼昏,何况读者。先讨论解决铭文中最为关键与争论中要害问题,仍较纠绕,为便于读者易看明白,有必要简括讨论关键问题、指导思想、解决方法与途经。至于纠缠最多的古文字、字句解释争论,从来并未完全查明的昏被称为“戎”的族属、源流,和必须最后综合总结论定的绝对王年断代,皆留在下篇讨论。
(二)鼎铭最重要价值,首先就在两次战争,开首就记“虢仲令柞伯曰:……用昏无及,广伐南国”,紧接着令柞伯率蔡侯“围昏邑”攻昏。两者有何关系?究竟是谁“广伐南国”?为何要伐昏?朱文作为重点论证,定为周公广伐南国,详解战争时间与南国地域,而和伐昏时间、地域完全隔绝、分开。但是按我研究,伐南国不是周公,而实是昏,与伐昏时间先后紧接,地域也很有关系,不是相隔数王、地域又无关之战争。如此,铭文全貌和结论就全不一样,而所牵涉战争历史、地理、民族,也都大有不同。铭文提出很多新的内容,尤以伐南国战争的时、地、人(即主持者)真相不明,引出问题最大。次为伐昏的时、地、人(即主持人),虢仲“令柞伯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既围城,(柞伯)令蔡侯告遂虢仲”,等虢仲最后至,才发动进攻。虢仲必右至昏邑,即从左右合围昏邑,右围为主,否则决不能面命规定“左至”,不能只有左围,而无右围,也围不住,更非作战所能允许。战争主持者与决定攻战者都是虢仲,他必带有一定士兵,包括护身卫兵,而绝不可能单人前往。但鼎铭只记“柞伯执讯二夫,获馘十人”,战果之少实为金文仅见。这是因鼎铭为柞伯所作,只记自己战功,连蔡侯战功也皆未交代,所以虢仲也只字不说。伐昏战果决不能只此。为何伐昏,开头就已交代明白,这些都是柞伯鼎铭症结问题与要害所在。笔者拟先将铭文中两次战争直接相关的人、地、时、事,及其密切关涉文字、文句之争论、解释,进行论证确定落实,未必皆是,谨求各方匡谬,明辨是非,以为改正基础。
(三)铭文文字大都前见,但是也有个别新见,即朱文隶定为“徵”者,金文早就出现数组相似之字,隶定、考证各有异说。最多一组就是被释为“徵”之字,亦即朱文所本;也有下多从“贝”,用为货贝之名,旧多释为“遄”;还有其他不同解释之字,旧皆不能确认,就是因字形结构、音、义、用法,诸皆不明,纠纷至今。鼎铭此字,字形结构、字义、用法皆和以前明显不同,不是一字,故为新出。和以前数组结构用法不同各字之形、义、用法异同比较,得以深入各层查明。古文字形、音、义既是统一的,必须一同研究解决,有一不能落实,就都不能过关。过去释为“徵”字,外形近似,结构不同,用法有别,本文一一考明,都不是“徵”字,必须分为数组。现只论证鼎铭此字,它就是一直使用假借,本字失传的“遂”,义为预期意愿初成,实为秦统一文字时罢其与秦文不合者,不仅战国各国,以前“遂”字也皆废除不行。至今皆未能分辨,就在于形、音、义皆有众多纠缠,没有用法比较,无法证明本字形与义为何?本文从形、音、义全面研究,查明“遂”字形、音、义源流演变,与其长期假借用法过程,特别是字形结构所表原意,表示初成、遂愿,进而比较与其他组异同、混淆、不明所在。由于鼎铭此字结构、用法明确,从而解决长期疑难,非常关键,应是此鼎铭文对古文字研究一大贡献。至于与其他数组争论,需专论阐明。此文只讨论“遂”字形、义源流,与用法关系,在此指要,以免正文纠缠不休。
(四)铭文也有少数文字,自《说文》就已源流失明。这里只提出旧皆不明与误解的“共”字形、音、义及用法渊源关系。铭文“圣祖周公,繇有共于周邦”,朱文隶定为“共”,通假为“功”,解为有功于周邦。但此字字形结构,实是从双手奉祭器,是“祭供”的“供”字初文,由祭供义引申为“恭”。两周金文约30处,最早皆用为“供”,后由祭供义引申扩展为“恭”,后加心旁专造“恭”字,与加人旁为“供”,皆为后造专字,以为区别。“共”就是“供、恭”两字的初文,西周金文原只有此二用法,后仍为汉碑沿用,与从工声的“功”非同一声,不能相假。“周公有共于周邦”,实因祭祀、供献宗庙,获得祖先保佑周邦。而“功”来源于人事战争、政治等,为人为关系,而与祭祀宗庙得上天祖宗保佑、获福祚,来源于人与神根本不同。殷周皆尊宗庙神鬼高于人事之上,形成宗法制度,成为政治统治基础,而与后代观念根本不同,往往不被理解、认识。在此可通用的贡献,而今一般不知词汇来源与古汉语用法区别。现代汉语“贡献”意同有功之“功”,实系来源于欧语词汇的外来语,而为汉化的词汇,而古汉语贡献一词为下进献上财物,绝无功意,两者意思、用法根本不同。共与其后起字供,用于供献神鬼,后代引申用于人事,同于下献上,用为敬语,但是从无功劳、功绩之意。所以铭文有共于周不能是有无功绩之意。此字另一重要价值是,西周金文有一字,上从凡声,下从手奉祭器,而与“勤”连用,旧释“劳”或“奉”,是非不明,而称“劳勤”或“奉勤大命”。朱文疑与此字同为“共”,但它明从“凡”声。我确定是“奉”非“劳”,也不是“共”字。两者皆用于祭祀,“供奉”连文,皆表供奉或贡献宗庙,获得神鬼保佑,从而具有今“贡献”之意,皆源于神鬼,非出于人事之“功”。另专论刊发。
(五)铭文也有词汇,初见此鼎,即前后皆未见过的“无及”。旧所不知,以致朱文误释为周公不可及。“无及”即无忌,即昏肆无忌惮。而广伐南国,“广”同“横蛮”、“凶横”之“横”,不是广泛意。“广伐”与“无及”都是贬义词,说的都是昏,不是、也不可能说周公。这是虢仲交代所以伐昏的原因。朱文都解为周公敏暋无人能及,敏暋为褒义词,而昏为贬义词,义正相反,不能通假。“昏”与“民”字形极近,从昏与从民声的字书写印刻,又最容易发生互混不清,造成古文字学与训诂学上重大纠缠近两千年。《说文段注》一再强调;“昏声之字皆不从民,有从民者讹也”,“昏字从氐省为会意,决非从民声为形声字也,盖隶书淆乱,乃有从民作昬者”。《说文》“昏,日冥也,从日,氐声。氐者,下也”。铭文正是上氐、下日,氐不是从“氏”,更不是从“民”,昏原意表日下落至地前,就是黄昏。后起孳乳、引申都是表不好之事,即贬义词,如“昏迷、昏沉、昏庸、昏乱、昏愚、昏暗、昏瞆”等,其所从之字如“惛、殙、睧”等也皆如此。而从“民”之字多是与其相反之褒义词,如朱文所举之“暋”。昏国绝非自称,乃是被周称为“昏”,也是证明。“用昏无及”是说昏国肆无忌惮,无国可及。“无及”、“广伐”都是贬义词,决不能表周公暋敏无人可及,广伐南国。我在历次古文字研究会上坚决主张慎用通假,从严毋滥,否则为自己开方便之门,而为研究大戒。究竟是谁广伐南国?是周公还是昏?为什么要伐昏?直接关乎战争的关系、原因。所得的结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关键就在于古文字渊源纠葛,与词汇褒贬、句法用意不明,解释差异,导致铭文面貌完全改观,一时很难看清楚。
以上三项皆不限于铭文本身,更多是牵涉铭文以外史事,必须合一研究,统一解决。后者价值更大,但是正文论证,只限本身问题,以外都必须全面专论刊发,所以先将关键论点、结论简述于此。
(六)年代问题既是柞伯鼎的根本,也是史实讨论重要基础。朱文分析此鼎文字、纹饰、形制,认为“时代宜定在西周晚期,如考虑铭文文字特征,当以厉宣时代为妥”。纹饰、形制都通行较长时间,只能断相对年代,不能定绝对年代。按通行分法西周晚期包括厉、宣、幽三王世,中期为穆、恭、懿、孝、夷五王世。据我考订,此鼎应属中期夷王世。昏广伐南国,对周说来,不是一件小事,不能不征伐,以宣周威德。但是王不亲见、亲令,全由虢仲主持代行,令柞伯率蔡侯围昏,而战绩甚微,凡此皆为金文仅见。这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夷王,王衍于厥身,诸侯莫不奔走,以祈王身”,与《礼记·郊特牲》“天子之失礼,自夷王以下”,所记完全相合,此铭文记事以夷王最适。而在铭文字句与词汇用法,夷王世也有证据,如“共”字写法,与两“其”字用为虚词。此鼎记伐昏,王不亲见、亲令,连“王若曰”代行王命的简单仪式都没有举行,这在西周金文中非常特殊,不仅与厉王暴厉,所作诸器铭骄横不可一世,悬若天渊,即与宣王令伐淮夷等战,气势、口吻、魄力也无法相比,全可排除。所以绝对年代断为夷王,先解最大争论,下分专论详举重要证据。
二、“广伐南国”究竟是谁?和伐昏是何关系?和周公究有何牵涉?
(一)朱文题目已综括为《柞伯鼎与周公东征》,“广伐南国”已确定就是周公,牵涉周初开国历史与许多战争方位。这是一个关系很大、也是铭文一个根本的问题。按我反复研究,全铭中心就是记虢中(仲)令柞伯率蔡侯围伐昏及其胜利结果,与已过了十代的周公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要伐昏,不能没有原因。据我研究西周战争,征伐起因可以分为数类,其中最主要、最多的一类,就是不服周统治,反周,或不断叛乱,进行反抗,周称为“反”、“大反”、“反夷”。除个别在北方外,最初皆为东夷,成为灭殷后周之大敌,周多次遣将派兵。中期及以后始出现南国的战争。“广伐南国”就是虢仲向柞伯交代伐昏国原因,“广伐南国”者根本不是周公,而就是昏。铭文本身已有交代,“用昏无及”,“用”就是“因”,昏就是下文所伐的昏邑。这是一个小国,铭文虽未称为昏国,而国与都同名。我很早就提出《城、国同源论》,最初一国就是以一城为都,向外扩展,春秋以城名国,城、国同名,还很多见。鼎铭称“昏邑”即是以城为都,表国,正可互证。但是朱文用通假将“昏”字读为“愍”,“努力、尽力之意”,大意是说,周公致力于周邦,而其勤勉无人可及,是指周公。周公下距厉、宣时代已经十世,据拙文《西周战争与民族历史地理考古研究》,西周初期战争,包括全部有关周公金文,根本没有征伐南国,只有东国。铭文如何能上溯十世之周公,系联为一,而把“广伐南国”作为周公领导的战争?不仅没有任何证据,且只有否定的反证,南国与南夷对别,指的是周的国土,而不是夷族之地,实在无法解释为周公“广伐南国”。
(二)“用昏无及”根本不是朱文所说周公无人可及之功,而是说昏敢“广伐南国”之罪。至于虢仲令柞伯伐昏,上溯周公,则是因柞伯是周公之后,所以让他率蔡侯伐昏国,在当时就是一项重要而光荣的任务。首先,因是周公之后之故,因昏“广伐南国”,必须伐昏且一定要成功,无负厚望与祖周公先德。朱文解为周公,战争对象逆转变为相反,由昏反周之反面战争,变为周正面的征伐,真相就全改换,性质完全不同。
(三)昏“广伐南国”对周不是件小事,必须命将征伐重惩,一般都要有正式王命或代宣典礼,兵马人数也不能过少,以保证胜利,宣示周之威德永扬。所以一开始都大张旗鼓,宣扬声势,为战争胜利鼓动,制造将士战斗气氛,加强必胜信心。战争最后目的都是为政治与统治需要,不成就是表统治失败。但是此铭伐昏,与西周战争很不相同,战前几没有做多少工作。1.周天子连招见柞伯、亲自面令或代宣王命的仪式都不能举行,皆由虢仲下令执行,只能是有病在身的夷王。2.虢仲令柞伯率蔡侯伐昏邑,而由柞、蔡二国左至于昏邑,并未说周出兵,似乎就是依靠柞蔡二国出兵,主帅就是柞伯,蔡侯佐之为副,周仅由虢仲作为周王室的代表,居于最上主持吩咐而已,这也是前所未见之事。3.铭文记柞伯战功,仅割十首,俘二人,人数之少,也为金文仅见,因系柞国纪功鼎铭,不记王师、周帅、战功等等。但是由铭文已有记事,可以由表及里,查明真相。查究为何原因、经过等,多在鼎铭之外,牵涉多而又很复杂,留下专论。
(四)由宗庙祭祀产生宗族、宗法礼制,是中国特有的早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决定性标志,经历夏商周三代成为上层血缘纽带政治依靠与下层社会家族、宗族长期联合的基础。周初封建诸侯,统治天下,分封同姓,以藩屏周,而皆按宗族血缘亲疏,分别爵位高低、地方大小、远近等级。这是周公所定周礼制度基础,用为统治新得的东国、南国政权的依靠。虢仲令柞伯时提出周公有共于周邦,盖因柞为周公之后,很被周重视。1993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242出土柞伯簋①,铭文称柞伯因参加王大射礼,十射皆中,获赤金十反(版),“用作周公宝尊彝”。我在《柞伯簋学宫制度与小子、小臣来源、身份新考》一文中,考明“王曰小子、小臣”,小子原称王族子弟,小臣则称王宫侍奉近臣,大抵选自近亲,依靠血缘亲近,为周王室服务。而设学宫辟雍,教育贵族子弟、近臣,作为主要对象。柞伯为周公子孙,属于小子,故与小臣等一同在周都学宫学礼、学射。而静簋“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暨服暨小臣暨夷仆,学射”,主要就是小子、小臣,包括侍卫官吏。以上究明了西周学宫教育制度、生员来源,与小子、小臣身份的渊源关系。柞伯称伯,已为柞国之君,而仍被招来学宫学礼、学射,说明周初对王族子弟教育培训何等重视。射、御皆为战争必需,依靠王族、近臣学习应用,以捍卫、巩固周朝政权统治。柞伯簋出于应墓,也因应与周血缘亲密的关系。而入春秋皆不见,王龙正等《柞伯簋铭文考释》,引《左传》成十二年,晋、楚盟于宋曰:“有渝此盟……无克胙国”,认为此时柞国尚存。但此胙明为动词“福胙”,不能误解为国名。晚清传世邾友父鬲,铭文“邾友父媵其子胙枣(曹)宝鬲”,杨树达解为曹姓邾国君友父嫁女于胙国所作媵器②。杜预《春秋时族谱》邾“夷父颜有功于周,其子友别封为附庸,居郳,曾孙郳犁来始见春秋,附从齐桓以尊周室”。按《春秋》庄五年经“郳犁来来朝”,友父为其尊祖,即此鬲友父,必在西周晚期。据《大系》图288,此鬲形制为无耳,宽平沿,带扉棱,三牛足,兽面饰,与三门峡虢墓出虢文公、虢季氏、虢季三鬲相同,确定为西周末期。在春秋之前,与柞国通婚,柞国东迁后不见,否则更近东周都王城与成周,必为周倚用,协佐周室,一如西周,至少不能毫无交往,春秋没有柞国,更为确证。
(五)蔡在淮水上,侯爵比柞伯大,但不令蔡侯为主帅。蔡始封蔡叔度与管叔挟武丁作乱,周公杀管叔,放蔡叔,其子胡周公用之,后复封蔡,故蔡后与周关系不能与周公之后柞伯相比。周初分封最南可至汉江、淮河北,所谓“巴、朴、楚、邓,吾南土也”,但皆为异姓,而接受周封爵,成为周属国。昭王两次征楚,即为其不贡。玉戈铭有戍汉,为周南国极限。“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即汉北所封姬姓国不断为楚吞灭,包括淮河以南国,地远国小,周无力保护,无法自存,被淮夷发展占据,更南近汉江北,则被楚灭。驹父盨记宣王时于蔡驻南诸侯师以防淮夷小大邦,昏即属于淮夷,所以广伐周南国就是在蔡防线南的淮河中游一带。昏当更近蔡,而柞在北稍远,但与周血缘最亲就是柞,其次就是蔡,所以虢仲利用柞、蔡以为开路先锋。此时淮河中游姬姓诸国几多不存,更无大国,所以虢仲令柞伯率蔡侯,尽管只作左翼,左至于昏邑,主力与总帅还是虢仲,最后右至昏开始总攻决战,并非专依靠柞、蔡两国。只是柞伯战绩极微,说明此时国小、兵少,虽未记蔡侯与虢仲战绩,总的说来此次西周王室战争收获甚小,所伤昏邑仅为皮毛,未触根本。不管怎样说,一个小邑昏国,周还不能独立征伐,这可能因夷王患病而受影响,但关键还在于人、财、物力缺乏,经济与物质基础的退化、衰弱,导致西周最后衰亡,这是根本问题所在。但仅儒家礼经记载,周衰始于夷王,而语焉不详,司马迁及其后史书皆只字未说,更不知情况,现由柞伯鼎铭反映当时真况,正确无讹。这是西周统治由兴转衰的重要证据。此证据唯一为鼎铭提供,而非考古所能发掘出来,所以价值极大,无可取代。此仅揭要,另详专文。
三、“广伐南国”不是周公,而是昏国,主持伐昏决战的是虢仲,而非柞伯
柞伯鼎记前后二次战争,实因两者有因果关系。“广伐南国”就是虢仲命柞伯伐昏时说明为何伐昏的原因;提出周公,是因柞伯是周公之后,故委此重任。这与已过十世的周公东征毫无任何瓜葛,该铭文本身就有决定性证据,无需外求,辨正如下;
(一)“用昏无及”。“昏”即是下文之昏,同指昏国。朱文说,昏“当读为暋”,解为周公“勤勉无人可及”,利用辗转通假,结果就把原来非常明确清楚的关系,完全弄反了。此句是说昏之罪,紧接“广伐南国”,就是指昏,非常明确。“用”在金文常有“以”或“因”意,而“以、因”之意又常互通。《经籍纂诂》“用”字下,其意繁多,但是第一条就是“以也”。《一切经音义》卷七引《仓颉》,而“以”常训“因”。此句“用”就是“因”。多友鼎(《集成》2835)“用严允放兴,广伐京师”,“用”与此句用法、用意完全相同,彻底解决两者都是表因果句之“因”,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曲解。“无及”就是说昏国肆无忌惮。而“广伐南国”,根本不是讲周公,而是指昏国,所以要派柞伯率蔡侯伐昏。两个“昏”字完全一样,都是同一个昏国。朱文分为不同两字,而用通假解第一个昏为暋字,变为另一个人,另一件事,铭文解释就全不同,导致面貌皆变,不能不予辨明。
(二)“广伐南国”。“广伐”屡见西周金文,除上引多友鼎外,他如师密簋“南夷肤虎……广伐东国”,禹鼎(《集成》2834)“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不期簋(《集成》)“严允广伐西俞”。1979年,我在《多友鼎铭年代与战争历史地理考释》③已经指出“广伐”之“广”与“横”皆从“黄”声,同“横行天下”之“横”,而不是广阔之“广”,横逆、横蛮、凶横等都是贬义词。朱文说“广伐当言征战区域广阔”,这是按后世汉语之“广”解释西周金文,是造成把“广伐南国”者当做周公的失误根源所在。多友鼎“严允放兴”与下文“广伐”并举,朱文解“放”为“方”,其实这个“放”义同于“横”,可以互证广伐之“广”同“放”,不能用通假解释为“方”而失原意。我已确考西周金文所有“广伐”全皆限用于反周、伐周的敌方,绝对不用于自方。不期簋“广伐”限用于严允,下文称“女以我车宕伐允于高陵”,立即改为“宕伐”。郭沫若《大系考释》解“广伐犹博伐”,“下复言宕伐亦同义”。王国维亦用宕伐为解。“广伐”实在只用为贬义词,不能用于周公,褒义只能称“宕伐”,而为王、郭二大师所不知。词义有褒贬,就有正反区别。铭文用“广伐”明确为贬义,确证昏国所伐。贬褒词义正反不同,错解就结果全相反了。
(三)“无及”也必然是贬义,但不见周以后任何记载,当是西周口头成语。西周金文有“无极”,后尚用于汉代瓦当“与天无极”,用为褒义,表没有穷极意,与此词不同。此词并无穷极义,不能解为“无人可及”,其义近于“无忌”,而表贬义,表昏“肆无忌惮”。“忌”(gie)与“及”(giep),上古音分属之与缉韵,声纽皆同,仅为去、入声之分,即有无收尾声之异,正是同音互假。真正的通假,我主张限于同音。至汉传抄经籍,今古文仍皆使用同声之字,故可定为原则,其他通假必须从严。
(四)《上海博物馆馆刊》第十期刊布2000年入藏的西周后期鼎铭有:
“用南夷口敢作非良,广伐南国,王令应侯见工曰:征伐□□□□□伐南夷。□□多孚,余用作朕烈考武侯尊鼎”(下略)。
南国明确与南夷对别,指周国土,南夷则为敌族,“广伐南国”皆表敌族,用“广伐”贬词,而周自称则用“征伐”,对比明显。“敢作非良”与此鼎“无及”,皆为斥责之词。开首“用”为“因为”义,与此鼎铭“用昏无及”用法全同,彼此互证,成为多重证据。“广伐南国”绝对不是周公,唯一就是昏国,可以定论。
(五)虢仲令柞伯“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主帅似是柞伯,而以蔡侯佐之为副。朱文以为虢仲,颇具识见。由于鼎铭并未说虢仲就是主帅,无其他铭文实据可凭,不能仅依表象推断,应拿出战争事实诸证。朱文仅凭“铭文言及虢仲柞伯蔡侯三人”,说“虢仲作为主帅也应以所辖(虢国)师旅与柞蔡的兵力协同投入战斗”。但是铭文只字未说虢仲任何战斗情况与实物的战绩、胜利收获,还是难以取信于人。更为主要的是,虢仲开头就讲周公,实是周执政者代王行令,用王室身份甚明。朱文以此推断虢仲封于荥阳东虢,与柞、蔡相近容易会师作为理由。虢仲实在不是、也不能以平等的虢国发号施令令柞伯,这不合理,不能成立。我也肯定主帅确为虢仲,根据铭文已记事实,至少证据有三:一是虢仲令柞伯,只令他率蔡侯“左至于昏邑”,首先柞伯不是全面攻昏主帅,从下令他任务时就已有明确地表示;二是先有“左至昏邑”,必有右至,就是后至昏邑的虢仲,明确皆为虢仲作战部署的具体措施。类似之例可为互证者,还有1986年安康出土史密簋,记“伐南夷肤虎”,有“师俗帅齐师、遂人,左周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嫠伯、棘□,周伐长必”。周伐就是围伐,师俗从左,史密从右,合围长必④。证明同于鼎铭“左至”,虢仲后至,就是右至,而等他最后至才下令总攻,所以就是主帅无疑;三是虢仲既是战争决定者,也是前后主持者,柞伯完全听命于他,谁是主帅?无需废词。
(六)最后还有两项要事,朱文未说,不能不阐明:一是铭文只记“柞伯执讯二夫,获馘十人”,战果之微实为金文战争仅见者。但又不记虢仲博戎情况,鼎为柞伯纪功,限记柞伯。史密簋也只记史密战果,不记师俗,尽管师俗也是第一主帅,战果不应比史密少,而皆同为体裁和字数所限,可为二重互证。二是这次伐昏之战是周王室征伐昏,柞伯与蔡侯只是周分派任务,不仅主帅为虢仲,主力也是王师而由虢仲最后率领右至昏,与左至柞伯蔡侯合围。而柞伯仅获十首二人,充分说明其不是主力,仅为配合而已。主力必为虢仲率领后至周师,但不是虢国之兵,绝不可能单人匹马,而独赴战场博戎,只是带人马多少而已,至少必带一队卫兵,也不能一无所获。但是总的战争安排、主持与具体指挥决战,前后事实明确,铭文无只字交代,而又无其他记载、物证,只能就铭文已记事实反复论证明确,否则就将永成不解疑案。
四、“南国”为西周南畿国土,而与“南夷”对别,不是夷土地
(一)鼎铭“广伐南国”,朱文定为周公,将南国定为周土外诸国,并特设“西周南国之地理范围”一节,论证此一观点,最后结论为“淮水流域皆属南国……所以西周金文将南国与南淮夷相联系”,并引用禹鼎与《诗·大雅》“南国”等,以为证明。首先就是混合南国、南夷为一,不分周土与夷土有敌我之别,导致诸多误解。西周早期淮河流域主要为淮夷,仅北部为周南国,并不存在问题。周公并无南征,更不能将周士“南国”以称异族,后者皆只称为夷,不能称为国,南国表周国土。朱文引禹鼎“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国与夷对别,东国、南国指周国内领土,南夷、东夷则是称以外不服周的异族,本身已是朱文反证。上文已证“用昏无及”是说昏肆无忌惮,而敢伐南国。“广伐”又是贬义词。首先要分清是在周国土内管辖邦国,还是在管辖以外异族之地?淮河流域直至春秋、战国,下游还多属淮夷或南夷之地,叛服无常。由于周日益向东南扩展,驱赶、降服东夷、南夷,占领、统治其地,人民不断融合,成为汉族最早一个来源,亦即最早的中原文明与汉族形成的总过程。
(二)南国是一个地理名称,但包含有政治因素在内。一因政治立场不同,限定所指地区概念与范围、内涵就会完全相反;二因时代不同,也有范围发展、变迁与概念背景差异。南国是周国土,而与周敌族南夷有别,西周金文、文献都有大量证据,朱文也皆举以证南国地理范围。文献多于金文数倍,朱文所举仅为少数。最早为《诗·大雅·嵩高》,“南国是式”,同一篇既称“南国”,又屡称“南邦”、“南土”,确证西周南国就是周土,无法误解为境外何国之地。《常武》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惠此南国”,下文皆记平定不庭的徐方,“……戒我师旅,率彼淮浦……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再次互证南国是周南土,而与南夷之徐方敌我有别。朱文引《诗·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此诗与《大雅·江汉》皆记宣王征服淮夷,文句多同,互接。《江汉》开首“江汉浮浮,武夫滔滔”,下一再称“淮夷来求……淮夷来铺”。昭王渡汉征楚未成,至宣王伐淮夷,“江汉之浒,王召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而“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庻定,时靡有争”,成为“南国之纪”。南国就是王国一部分,而被诗人宣扬夸大为“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但周南国确至江汉之浒,所以《四月》诗称“南国之纪”,下紧接“尽瘁以仕,宁莫我有”,说明“南国之纪”设官管理新降服归顺诸南淮夷,而作诗者正仕于此南国,地广事多,需尽瘁才能完成。袁盘、兮甲盘,都记淮夷要交实物赋税,不交即不服,故派将征伐。十八年驹父盨记征收淮夷小大邦服物,皆为宣王。以前淮河流域并非皆属周南国,部分属淮夷或南夷,还常“广伐南国”,多至四见。此鼎为夷王世,余为厉王世或宣王前。而过去对南国、南夷多未查明,混淆不分,产生重大误解。
但西周南国不断发展,将东夷、淮夷驱赶,地区范围皆有变迁。夷地变服属周土,而皆叛服无常,极为纠葛。这也是南国、南夷误混不清的根源所在,必需溯流穷源,讲清其来龙去脉。更为关键的是,朱文将“广伐南国”定为周公,专设“关于周公南征”,予以论定,并说“周公这一事迹是西周金文中首次见到的,对于西周史研究具有极重要价值”。但是周初金文与文献只有东征,“但周公是否曾南征”,朱文说“在西周文字中虽有涉及,但讲的并不明确,在周文献中似只有《荀子·王制》讲到‘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来迟也’”。按此明为荀子假设之词,根本不是周史,荀子也并非说历史,不能作为证明。周公有无南征,不仅关系周重大史实,也是此鼎铭一个根本问题,能否如朱文所说“金文首见,具有极重要价值”,按我考查,实都没有,或不可能存在。这就必须认真查明,彻底清除两大纠葛。
周以小邦灭大国殷,收为周土。一是殷本土,二是殷东方地区,包括臣服、半臣服、名义臣服,或反复无常,并未臣服,如人方等。周得于殷,比之周本土至少要大数倍。武王伐殷,仅克纣于殷都,其他皆未解决。首先就是殷本土,再则为殷东方之地。《逸周书·作洛解》:“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毛父宇于东”,分别称殷与东对别。同篇又称“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也将三叔之殷与殷东对别,而更将殷东地域、国、族进一步明确。传出洛阳唐寺门的保尊、卣记“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被定为武王与分封五侯,我考证“及”本义象追捕抓人,甲骨文与西周前期金文皆用为动词本义⑤,如果解为连词,首先就是甲骨文及金文前期语法不能允许,而又不说“令”保去做什么,岂能猜谜?更是违反常识。五侯即“太公封于齐兼五侯地”,《汉书·地理志》:“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正是五国,即保尊“殷东国五侯”,如合契符。武王克殷后即有病,两年即死,无再征伐之事。《周本纪》称“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而告周公……顾瞻有河……洛伊,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就是为此忧虑不寐,而要定都黄河中下游、伊洛河上洛邑,就是为解决殷与其东诸地。周一开国及以后数代,都用全力解决对东国统治。周公只有东征,因巴(蜀)、濮,早就参加武王之八国伐纣,楚也早附于周,不存在任何战争需要,周公南征就只能是“莫须有”。何尊“惟王初迁,宅于成周”,数千年不明的是否迁都,铭文争论关键的“迁”字,已由大盂鼎“亟囗迁自厥土”佐证,两“迁”字写法用法全同,铁定迁宅于成周,就是为统治以东之东国。何尊确记成王说“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周公营洛邑,成王初迁成周,就是按武王廷告,为解决再灭殷后周王朝能否持续存在,殷与殷东(合称东国)能否永远作为周东方国土。而其中又有人方(即夷方),就是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者,既不服殷,也不服周,正是所谓“殷鉴不远”,所以成为西周前期最主要征伐地区,对象就是东夷。直到穆王世的班簋“伐东国厌(奄或偃。或释骨,但无此族、国,似非是)戎”,“三年静东国”。东国是周国土,厌戎则属东夷,还是最大重点战争的对象。东国的东夷,一是被战争征服,归顺受周封爵,为东国属国,春秋还有不少存在。二是拒绝臣周,反抗到底,或先服后反,称为“反夷”,只能用战争,向东驱赶,迫使其不断退到海滨、海岛。如“营丘边莱,莱人夷也……而与(齐)太公争国”,后被齐不断驱逐、分化,部分臣服,部分不服者最后迁于海滨,最后皆为齐灭。后代分别置东莱郡、莱州、蓬莱等郡、州、县,都是因莱族迁居于此得名。小臣逨簋记“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伐海眉……承王令赐师率征自五隅贝”,正是成王灭殷后征东夷,远至海眉,即海岸。五隅就是海角,亦即《尚书·尧典》的“宅隅夷”,《禹贡》青州“隅夷既略”,为隅夷最早所居诸地区之一。1973-1975年,山东省长岛县王沟村西周至战国墓葬出土一些铜器,一舟底有一甗形徽识,确证为东夷族徽之类,无疑为周或齐多次征伐,被迫由海隅迁入海岛者。三是大量被迫南迁到淮河流域与其河口三角洲上,与淮夷杂居,一同被称为淮夷、南淮夷、南夷。西周后期,金文所记战争不见东征与东夷,就是由于东夷南迁淮上,不断加入淮夷、南夷后,被周总称为淮夷。日久族多人众,人口成倍增加,而皆在周南国之外,沃土已为周分封占领,淮夷族多、地狭,生活土地有限,必须向外大量扩展,与周争夺土地财物,成为西周后期成周大患,所以战争只有南夷、淮夷,没有东夷。按下文考证,昏就是迁居淮上成为淮夷,为何要广伐南国?正是同于上述情况。所以详细阐明其源流演变,才能获解。
周初称为“殷东国”,确证自殷,东夷即殷人方,既不服殷,也不服周。周用封建诸侯,分别统治,最大设齐、鲁为东国两大柱梁,齐有莱夷与蒲姑,鲁有奄与淮夷、徐戎,皆被驱逐。还有一些归顺,接受周封,成为周东国属国,最著名的就是“任、宿、须勾、颛臾,封姓也”之四国,“实司太昊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我已考明,宿最早服殷,“司有济之祀”,实为周封。苏钟记宣王巡狩东国,发现宿不服,而伐宿,最为确证。东夷不少反抗,周称为“反夷”或“东反夷”,就是先服后反。周初殷本土外的东方之地皆称东国,东至海,东南至淮,为周统治国土,臣服者封爵,不服或反周则征伐驱逐。总之,东国就是周土,人民原多为东夷,臣服于周后,与周人共处,为周臣民,经周不断融合成为最早汉族的一个源头。但中有反复无常者或“反夷”,成为周前期最大征伐驱逐对象,其多南迁淮河流域变为南夷,而与南国对别。此种情况周初还都未出现,故没有南征,不仅周公。旧皆不考东国、东夷源流,不得不予详证。
(三)最早出现南国与南征是在昭王末期,《竹书纪年》记有昭王十六年与十九年二次,金文明确记“省南国”已知有三篇:一是中方鼎,“维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王居”;二是同人同时所作中甗,“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居,在曾”;三是静方鼎,“王在宗周,令师中洎静省南国,设居”,师中即中。皆为同时王令,应即昭王十六年伐楚。南国都是指周国土内南部地方,省即巡视,贯行即开路,设居即建王行宫,都只能限于国土,不能在夷地内。1902年岐山出土玉戈,“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出殷南,命厉侯辟,用蛛走百人”,也是巡视国土,但非进行战争。太保如为召公则为康世,如为另一后继承者,就是昭世。所省南国也只能为周国土,不能为夷地甚明。昭王为何要伐楚?并非因楚伐周,主要是楚不贡,就是不臣于周。《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管仲对楚使问为何罪,第一条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证明楚贡于周,直至春秋不变。周原甲骨有四片有楚,其中“今秋楚子来告……”,“其微、楚升燎,师氏受燎”,证明楚参加周会盟祭天,并献了礼。《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仅、王孙牟、燮父、禽父共事康王”,更予确证。至于管仲第二条问罪为“昭王南征而不复”,楚使对曰“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拒不认罪。杜注“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西周南国之境至于汉水,楚越汉而北始于楚武王,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不仅周公没有南征,昭王十六年以前南征,全皆乌有,“广伐南国”为周南土,定为周公更属无稽。
(四)虢仲令柞伯伐昏,就是因昏“广伐南国”。南国是在周境内周之诸国,不是境外任何夷族之地。南国与南夷所指地域完全相反,这是首先必须查明分清的,否则敌我不分。西周南国与东国从何处划分?原则上成周以东为东国,宗周、成周王畿南部为周南国。《左传》隐公五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唐兰先生已指出陕是郏鄏之误。周灭殷以后,东国就是经营征伐的重要对象,所以由周公主持,这是非常可信的。宗周钟记厉王巡狩,“王谲省文武,觐疆土”,即视察文武开创的疆土,后世巡边之始,从而发现“南国服子敢陷处我土,王敦伐其至”,证明南国指王畿南部。“巴、濮、楚、邓”,都在成周之南,厉王就是巡宗周与成周南国而至成周,途中发现服子陷处周土,确证南国为周之地,而称“南国”,与下文称“南夷、东夷”相对区别。晋侯苏钟开首就记“王亲谲省东国、南国”,谲省即巡狩,“王步自宗周”,先巡南国,格于成周后,“王馈往东”,再巡东国。南国为宗周至成周王畿南部之地,东国则为自成周以东周地,至为明确⑥。其中有臣服而受周封的夷族之国,如夙夷,巡狩发现不服,故予征伐,可为互证。这里只是举例,不再详说。总之,最早就是以宗周、成周王畿南部,与成周往东的周土,分称南国、东国,与夷相区别。师袁簋“淮夷……弗速(迹)我东国”,明称为“我”,就是周土铁证。至于明公簋“遣三族伐东国”,上文特证周初东国承殷,此簋“伐东国”就是指东国内东夷,来自人方。东国、南国皆作为周国土,虽中可有叛服无常夷族,但仅为国土内部之事,不能改变其为国土性质,或否定与夷对别。所以“广伐南国”只能为昏国伐周之地,绝对不能是周公征伐周之国土,更不能用贬词“广伐”。这是鼎铭根本问题,一反一正就有天渊之别,所以反复辨明。只是南国随军事、政治与时代发展而有不同,本文限谈铭文中的城、国地理问题。朱文引“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南国、东国明为周之国土,而南淮夷、东夷则在其外,不属于周之夷族,朱文已经自提确证,点出就明。
(五)至于经籍记载,朱文举《诗·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是纪”,用以证明南国地理范围,仍混周土与夷地为一。上文已略引《诗》“南国”,不全,现为彻底解疑释惑,必须将先秦记载所能查明者全引,以确考南国皆为周南土,而非属南夷之地。首先,与西周晚期金文同时的《诗》大小雅更清楚。最为明确就是《大雅·嵩高》所记最多,全引于下:
“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我图尔居,莫如南土。……往近(矣)王舅,南土是保。”
“南国”下文又三次换称为“南土”,两称“南邦”,就是周土、周邦铁证,毛传早解“谢,周之南国也”,所以封申伯于此。
二是《常武》互为二重证据:
“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下文多次称“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徐方来廷,徐方不回,王曰还归”,即迫使徐方臣于周后,凯旋而还。周初“淮夷、徐戎并兴”。原居曲阜郊地故来与鲁争地,一如莱夷与齐争地,战败被驱徙徐地,在淮河北自立为一国,与淮夷地域相接,文化、人民不尽同,故被周称为徐戎。至周穆王时徐复兴称王,再与周争天下。徐在淮河之北,介于东夷与淮夷之间。徐国文化高于淮夷,但徐偃王后为周征服,徐受周封爵称为徐子,多见《左传》。徐为东夷最早用汉字者,造作大量金文,与较早接受周、鲁文化影响不无关系。郑玄于“惠此南国”下笺“以惠淮浦之旁国”,亦即周之属国、属地,否则就不能称惠,“惠”字成为周土决定证据。
西周后金文无南国,以后文献仅见《国语·周语》(上)记西周事,“宣王既丧南国之师”,韦昭注:“败于姜戎时所亡也,南国江汉之间”,《史记》将《国语》全写入《周本纪》,《集解》引唐固曰:“南国,南阳也。”申、谢皆在南阳,分别见《汉书地理志》与《续志》,正即周之南土。此外《礼记·乐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此为战国所记大武乐舞表演西周历史剧,三成、四成都是表灭商以后,向南奠定周之南国疆土,包括南土之“巴濮楚邓”,都受周封爵。所以说“南国是疆”,也是战国儒家最晚仍将南国作为周疆土的确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就是周初“南国是疆”时,南至汉水为界,分封姬姓诸国,但都不是使用战争。东国、南国主要为西周所称,周东迁后,皆有多种分化,基本不属周王朝直接统治,所以其名就不再用了。春秋齐、鲁为东方两个最大国,不断兼并周围地区诸多东夷族国家,不断融入华夏族,最后共同形成汉族而为其最早的一个源头。文明求源首先就是要求中国形成的地域与民族之源,地域包括夏之黄河中游武王所称之“中国”,与向南包括淮河流域,形成的中原地区最早文明,由夷夏并立的华夏族与东夷、淮夷共同创造。齐鲁主要向南扩展,包括淮、泗下游诸国、族。《鲁颂·闭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傅斯年最早提出《大东、小东说》,如同西方之称远东、近东。但他限于当时所知,未能利用大量地下出土的殷周甲骨金文资料。殷周甲骨金文中征人方,特别是与西周相始终的多篇金文,涉及征伐东夷、南夷、淮夷、南淮夷,向东与东南多次的发展,而使东方众多夷族迁移,发生地域变迁与地理概念的变化,拙文皆予详证。简括地说,小东就是周灭殷后的殷东国基础,最早分封齐、鲁两大柱梁作为中心,与归顺周的国、族,而形成周初期东国;大东则是后期向东与向南扩大。而《鲁颂·闭宫》明记鲁征服徐方、淮夷,称为“南夷”,《大雅·江汉》,《常武》分别歌颂宣王有“淮夷来铺”,与“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而征服徐方。宣王已荒大东,扩展到淮河下游,而与兮甲盘、驹父盨等铭互证。淮夷小、大邦向周交赋,而服于周,只是叛服无常。包括鲁僖公征服徐方、淮夷,必皆此前又叛,此后也不属鲁,仅为一时而已⑦。但至战国“淮泗之夷散为民户”,早在秦统一前已融为汉族,共同创造最早中原文明,成为汉族的最早一个源头。秦统一以后,江汉流域之楚与江浙流域之吴越融为汉族,故皆远在其后。
以上将西周金文与有关东国、南国记载全予查明落实,就是为确证东国、南国都为周之国土,非夷族之地。过去对南国、南夷的历史与地理发展变迁过程,缺乏由表及里的研究,仅看表面相似。所以就是要溯流穷源,彻底查明真相,斩除有关纠葛。从夷夏并立开始,直至西周,不断扩展东国、南国土地,驱占东夷、淮夷之地,南包淮河流域,形成中原地区(晋文公对楚子问“晋楚构兵遇于中原”,即指黄、淮河中游)文明,东夷、淮夷不断融合为汉族,成为中国文明最早、也是最大形成、扩展中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五、昏在何地?究为何族?原地何在?迁徙原因?
(一)鼎铭中昏的地望:昏与柞、蔡相近,皆在淮河流域内外
昏未留任何记载与考古遗物,唯一就是与柞、蔡相近,据以考订昏的相对方位、源流。
1.《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凡、蒋、邢、毛、柞、祭,周公之胤也”,柞杜注:“燕县西南有柞亭”。《后汉书·郡国志》:“东郡有柞城,古柞国”。《水经·济水注》:濮水“又东经柞亭东注,故柞国也”,扬守敬《水经(济水)注疏》引杜注:“在今延津县庞固社”。乾隆《一统志》:“柞城故城在延津县北三十五里,周为柞国”。《中国历史地图集》州县定位,基本就是依据清《一统志》所记古城方里,将柞标于延津北。最近看到《中国文物报》2007年12月7日刊登《河南延津沙门城址考古收获》,在延津西北榆林乡沙门村东北15公里,发现古代黄河南岸重要渡口,城墙为战国时代,前身或即是柞国,至少与柞相近。这使我追忆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历次会议,数次提出应尽可能利用考古定位,如缺才用方志古城。当时受限,今后已有条件利用文献、考古、历史地理微宏观考察三结合定位予以重编,以提高科学研究与应用价值。柞国当黄河之南渡口,因黄河摆动有所变动。今胙城县乃金元河道迁徙,州、县治皆改迁,明依记载于其附近所建,非古柞国城。今后按清地志所提勘查柞国故址,可能找到。总之柞国方位基本明确,即在延津北,古黄河南,最早津渡口,南接淮河流域支流。
2.蔡正在淮河流域中游汝水之上,今上蔡前身,一直在此未变。蔡故城仍在上蔡城外,最为明确。昏广伐南国,其必在成周王畿南国之南,亦即在淮河流域中游蔡国以南。上蔡及其北基本为周南国之地,故昏被彻底排除在蔡之北。
3.《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扜、晋、应、韩,武之穆也”。应国墓地已在平顶山市发现,应公、应监、应侯皆见于西周金文,为周依用。柞伯簋即出于应墓,柞、应与周关系皆在蔡之上。西周蔡国与周交往第一次见于此鼎。上海博物馆藏蔡侯作姬单媵匜,被定为西周晚期,但是器形介于东西周之间,字体尚待细考。除此外,蔡器时代皆为春秋,说明蔡在西周不显,地位也不重要。蔡为周依用,始见此鼎。而不用既近成周,又早就屡为周用之应,说明蔡近于昏,由柞伯率领,以为其副。昏必去应远而方位不合。以前伯雍父等驻于淮河北的胡、叶以防淮夷,甚近应国。宣王十八年,南诸侯帅师驻蔡,当与此次伐昏蔡起作用有关,改驻蔡以管制淮夷。引证于下,对广伐南国的昏的方位至少可供参考。
4.驹父盨记“南仲邦父命驹父簋(即)南诸侯率(帅)高父,见南淮夷,厥取厥服……还至于蔡”,就是为镇抚淮夷,收取服贡。“至于淮夷小大邦,无敢不□,具逆王命”。昏必与蔡近,昏伐南国为淮河流域周土,即成周之南畿。昏就是周南国之外的淮夷,在成周南畿之外、淮河上中游之南,唯一见于此鼎铭,春秋不见,亡于东迁时。现只知至此。
(二)昏原为东夷,后被周征伐,不断南迁淮上,与淮夷共处,成为淮夷
西周前期金文战争皆为征伐东国之东夷,后期基本为淮夷战争取代。东夷何以不见?唯一就是因被周不断东伐,南迁淮上,合于淮夷,地瘠且狭,而国、族日多,人满为患,从而不断与周争夺土地、财物。杜预《春秋释例》卷七[夷地]:“僖十三年,淮夷,东夷”,下注“东夷居淮水者,缺”,就是南迁淮上。按此为《左传》僖十三年“夏,会于咸,淮夷病杞故”。杜预最早指出此淮夷原是东夷南迁,后居淮水,所说甚是,而未说所据。考《左传》记当时东夷凡八见,淮夷四见,明分为二。淮夷以居于淮河流域得名。东夷原在其北的黄河下游,即周最东部的山东半岛中心地区,东尽海滨,东南达于淮河入海口,以北为东夷长期所住。以南淮河流域,周称为淮夷、南淮夷、南夷,但是民族分布、迁徙疆域并不固定,随军事政治发展以及时间变化而不同,只能大致而言如此。
(三)淮夷与东夷的演变关系,至春秋时期发展的过程
《诗经·小雅·大东》“小东、大东”,《鲁颂·闭宫》“遂荒大东”,东国后发展为小、大东国。春秋鲁僖公时,大东已扩展“至于海邦,淮夷来同”,成为海邦的淮夷。而自人方与殷对抗并立,周东国承殷,除一部分受周封爵归顺外,大部分被称为东夷,就是拒绝接受周统治,被周多次征伐,不断驱逐,被迫迁徙,最东至海,南则到淮上,与淮夷合一。杜预称“淮夷,东夷居淮水者”就是指此。《左传》哀十九年“楚沈诸梁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杜注:“从越之夷三种,东夷也”。春秋后期,东夷更越淮河南,至江浙海口三角洲吴越之境。《左传》八记东夷,与鲁、齐关系各一次,皆在前期,后期六次,证明曾为楚征服。文五年,“楚公子朱自东夷即陈”,必已属楚。襄元年,“晋降彭城,而归于宋,楚失东夷”。昭四年,楚子(灵王)第一次会盟黄河以南及淮河内外诸侯于申,随即伐吴,淮夷皆列最后,也是第一次附楚。胡渭《禹贡锥指》卷六谓“此皆淮南之夷在扬州之域者”,即已接吴境。次年再会伐吴为其继续,但以东夷列最后,取代淮夷,也是东夷最晚出现的唯一记载,证明二者原来是一。东夷不断南迁于淮河南北,直至长江。杜预注“淮夷,东夷居淮水者”,就是他长期研究《春秋左传》所得结果。过程比较复杂,一言难尽,只能出如此结论。
(四)昏就是东夷,南徙居淮水上,记载与金文互证
《春秋》僖十三年《经》:“公会齐侯(及诸侯)……于碱”,《传》:“夏会于碱,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旧皆依杜注“碱,卫地,东郡濮阳东南有碱城”。按文十一年《经》“(鲁)叔孙得臣败狄于碱”,实为鲁地,今纠其误。与会于此以救杞最合,西周后期杞已迁于东国,此地近杞故。次年春“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杜注“缘陵,杞邑,避淮夷迁都”。或据《管子·大匡》、《霸形》以缘陵为齐地,但与杞都相距不能过远,春秋皆在东国。而远处淮上的淮夷为何要病东国之杞?旧所未解,唯一就是因它原为东夷被迫南迁居淮,地为杞有,即杜注所据。武王灭商,封夏之后于杞,原在淮河流域,今之杞县前身。而史密簋已记杞在东国,《左传》襄十九年也记“杞,夏之余,而即东夷”。昏广伐南国,而与蔡、柞相近,必为南国附近之淮夷,或称南淮夷、南夷,但从不见任何记载,迁居昏邑必晚,国小只有一城。周封诸姬已至汉北,“楚尽有之”,即为楚灭,但昏未为楚并,就是因不在汉北,而在淮河上中游间,处于成周南畿外隙地之故,因地近,当为周并,而比较合乎情理。
(五)昏为何“广伐南国”?原因与目的
昏国小,人、地少而贫,“广伐南国”首先就是为生存需要,夺地,争人、畜、财产。另一原因就是原为东夷而迁居淮上,实被周驱逐至此,正与上述杜预所举相合,怀恨在心,不甘处此,企图报复,故反周。相似之例可以互证的,还有皆为西周晚期两件金文。其一吾鼎:
“王在成周,南淮夷遱及内,伐溟昴、参泉、裕敏、阴阳洛,王令吾追联于上洛析谷,至于伊班”。
北宋摹本未尽传真,“遱及”,《大系》释为“迁殳”。“遱”明从辵从娄,即《说文》“遱,连遱也”,《集韵》“遱,连遱不绝貌”。即连续行走不断迁徙于内,即周畿内,最后溯淮而上,至伊洛河上游析谷,直攻成周,所以“王令吾追联于上洛”。“追”后一字《大系》释“御”,张亚初《引得》依裘锡圭释“拦”,实皆未识。我考明实“从辵,从丝”,《说文》无,最早收于顾野王《玉篇》,而为日僧空海抄要为《篆隶万象名义》,卷三十三有此字“补幸反”。字僻,北宋字书始收之,《集韵》有此字,“必幸切,行急也”,《类篇》同。(《集韵》另有“从并、从辵之字,“一曰行急”,《类篇》“又必幸切”,认为同字,《字汇补》同,但并不是同字,见空海书“遱”前第二字“彼争反,走散”,可以为联绵字。)“广伐南国”,除扩展领土外,就是为报复被周赶出,南夷反周有些就是与此密切有关。
其二史密簋:
“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合南夷肤虎会杞夷、舟夷、雚(酄),不(丕)伒(近/进),广伐东国,齐师、族土、述(遂)人,乃执图(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左周伐长必;史密又(右)率族人、斄伯、棘囗,周伐长必,获百人……”
对象为肤虎,就是因其广伐东国,所以周师东征。有些论证将肤虎分为二,连征伐对象都混淆不清,明确是一岂能有二?但是何以又称它为南夷?已刊专文18篇都是谜。为何南夷要广伐东国,所会并不止一国,多至数国。周为何明令东征,却称为南夷?诸文对此都不能回答。已提出各说,多为误解附会。关键就在于不能理解肤虎为原在东国之夷族,而被周征伐南徙,成为南夷。所以广伐东国,除了报复外,就是为返取故地长必。它所会合的杞夷、舟夷,皆在东国。杞尤为明确,而称为夷,就是被其会合,结成为一伙,一同参加的证明。“广伐东国”的齐师、族土、遂人,明称为“东国”,皆为周土属国,而与南夷区别开来,可为确证。师俗、史密率齐师、莱伯等左右包围肤虎的长必,也正在东国,证明它最后确返居故地,也就是它广伐东国的原因、目的所在。但是又被称为南夷,证明它是被周人征伐所驱,逐步南迁。所伐齐师、族土、遂人,当因它的故地多被他们瓜分、占据,故予以报复。唯有如此解释才能完全通读,从而可与此鼎铭“广伐南国”互证。鼎铭“博戎”仅“执讯二夫、获馘十人”,证明昏是小国,已属西周晚期。此时东夷被周多次征伐,大量南迁淮河流域,国多人满,而沃土、要邑早被周分封诸国的王族、亲族占据。昏作为城、国之名,找不到任何有关记载,必因后迁于此,不是它的故土,杂居诸国之中,地狭人众,一是为生存与扩展土地需要,二是对西周报复,这是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与史密簋中肤虎被称为南夷,而广伐东国,返居故地,基本一样。昏的故地当在东国,与史密簋“南夷肤虎”“广伐东国”最为相似。
注释:
①王龙正等:《柞伯簋铭文考释》,《文物》1998年第9期。
②杨树达:《邾有父鬲跋》,《积微居金文说》卷七,187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③《考古与文物》专刊《古文字论集》(一)。
④铭文器形照片最早刊《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已发表讨论18篇,收入《近出西周金文集释》,关键问题多未解决,我另详考,不同众说,待发。
⑤黄盛璋:《保卣铭的时代与史实》,《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保卣铭的年代、地理与历史问题》,《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213页,齐鲁书社,1982年。
⑥黄盛璋:《晋侯苏钟在巡狩制度、西周历法、王年与历史地理研究上指迷与发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0年。
⑦唐兰:《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文物》1976年第6期,定域林在泾河上,“堂师地未详”。我最早告吴镇烽此字就是“堂”,他写于《简报》,非袭唐文。但现一般并不认为是“堂”,字既不识,地更不明。《说文》“堂从土,尚声,文堂从尚,京省声”,邑部有籀文加邑,又说为“古文堂字”。铭文此字上从同“京、亭”上部建筑形,用为形旁,下从“止”表基址,与从“土”意同。楚简“堂”下从“立”,见郭店《老子》及上博楚简,多假为“当”或“棠”等。总之,此字就是“堂”。《风俗通》“堂,楚邑,大夫伍尚为之,其后氏焉”。《左传》皆作“棠”,楚堂君伍尚所封即堂溪,后以封夫概,在西平西百里,驻此就是为防御淮夷。域林为许地。“博戎胡”,胡决非北方之胡人,也不可能南下深入至此,而是在郾城西。所有战争地名皆在淮河流域,淮戎就是淮夷,所以昏亦称戎。
⑧详见拙文:《录伯东铜器群与战争地理研究》,《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据《中国文物报》2007年11月16日2版《河南叶县古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古城在叶县西南25公里保安镇前古城村及其西北地,初步定为东周,即春秋之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