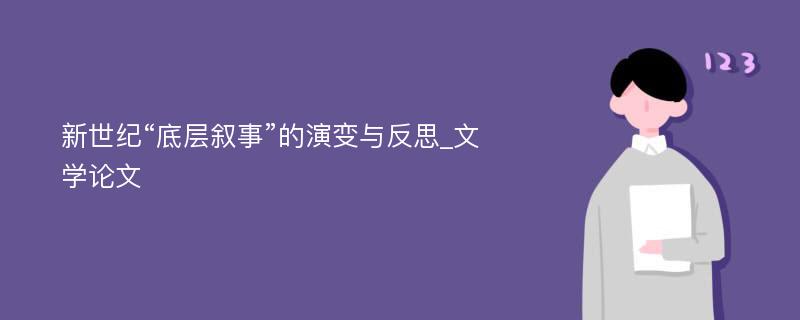
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流变与省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底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10-0117-07
一
检审新世纪十年的文学实绩,“底层叙事”无疑是其中最为醒目和最具文学史可能的文学现象。特别是2004年以来,由于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与大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的高度契合,“底层叙事”迅速受到评论界的注意和读者的欢迎,一大批着力开掘底层生活的作家竞相涌现——陈应松、罗伟章、刘庆邦、尤凤伟、王祥夫等,甚至一些成名已久且在文坛仍颇为活跃的作家铁凝、贾平凹、迟子建等也将笔触伸向底层,一时间底层写作蔚为大观,几乎成为十年来当代中国小说的叙事主潮。陈应松曾不无自矜地说:“以读者投票的《小说月报》百花奖我排名第四;三四五名恰好是几个‘底层叙事’的作家刘庆邦、我、罗伟章。”① 其时,各著名的文学评论刊物,如《天涯》、《小说评论》、《文艺争鸣》等也相继展开了关于“底层叙事”的热烈讨论,“底层叙事”几有一振文坛之势。
在2004年的“底层叙事”文学景观中,曹征路的《那儿》、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等代表性作品,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努力再现,用来自“泥土和苍生”② 的现实主义力量,给以在纯文学的名义下远离生活、矫揉造作的写作以沉重一击。《那儿》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公共资源被权力者蚕食,而底层工人非但不能享有分配公平,相反自身的权益却一再受到损害和盘剥,从而陷入到艰难生存困境的社会现状进行了大胆真实的呈现,将文学直接楔入到转型时期社会病态的核心症结处,显示出非凡的勇气与胆识。而《马嘶岭血案》则把故事发生地放在了神农架山区,在封闭、原始的自然环境中,社会底层遭受的歧视与压制不仅没有弱化和消弭,反而变本加厉。挑夫九财叔不断受到来自城市的勘探队的轻贱、怀疑和驱逐,从而失去工作机会,陷入生活的绝境。九财叔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有钱,而我们啥都没有”?“咱受的苦比他们多,都是一样的人,不该这样啊”。最终,走投无路的九财叔用手中的斧子将勘探队的七个城市人全部杀死,演绎了一个贫富不均导致底层小人物绝望反抗的骇人故事。面对社会的裂隙与不公,面对底层民众漂泊沉浮的命运,作家没有漠视与回避,而正是通过作品呼唤着公平与正义、道德与良知、尊严与价值,实践着文学的社会关怀品性,并因此赢得了读者。
然而正如被视作底层写作渊薮的“左翼”文学一样,人们在肯定它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立场的同时,其艺术性、文学性的不足也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为人诟病。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苦难的过分渲染与堆积,进而衍化为“残酷叙述”、“仇恨叙述”乃至“非人间叙事”,给读者带来无以言对的审“苦”疲劳。二是底层写作中人物性格的简单化、故事结构的模式化倾向过于明显。这样的缺陷成为底层写作的瓶颈,它与作家对底层的认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这些作品中,底层被视作整个社会大圆的一个扇面,表现方式是平面照相式的,或者复现式的,没有立体的剖析,更缺乏纵深的开掘。它的叙事所涉及的对象,主要包括贫困农民、进城民工、城市下岗职工和城市贫民等城市失业人群及边缘群体。这种将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作为底层写作着力描写对象的趋向,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有意指认,体现着作家对民生的关注,对现实的干预,对社会转型期因巨大的经济变动带来的底层民众生存焦虑的暴露。这样的声音虽然是有价值的,但并不能让人满足,特别是给人以美的启迪,因为它们大多是对底层的外部(物质层面)的观照,而对底层的内部透视显然不够,特别是对广大底层民众丰富的精神层面的体察与把捉更是薄弱。在这样的情势中,“底层叙事”的突围,特别是拓展新的审美视角、提升自身的艺术品格,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二
正如作家刘继明所言:“也许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理解的底层,只不过各自选取的认识路径不同而已,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真实的‘底层’向我们现形。”③ 可见,任何试图给底层所指称的人群以严格范畴的圈定都是徒劳的,“底”本身就是与“上”、“中”相对而言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叫作底层,而什么样的人又不属于底层,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在一个相对自足的范围里,只要还有上层,那么其他的都可以将之称作底层。虽然这是一种极端化的说法,却说明了底层的不确定性、动态性与丰富性。更何况,底层本来就不应该是单一的、平面的、凝固的,而是一个丰富的、立体的、变动的存在。只有基于这样的认识,作家笔下的底层人物才可能饱满立体,所展示的底层世界才可能真实可信,底层写作才有可能继续前行。作家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摆脱困境,他们做出了相当可观的努力。于是,底层生活中的“分层”、“流动”和“变异”等事象受到作家们的重视,成为其书写视域拓展的重要表征。
首先是对底层“分层”现象的注意。在将农民工、贫困农民、下岗工人的悲剧故事作了穷形尽貌的描绘后,“底层叙事”显然亟需寻找新的意义生长点,晓苏的极富象征意义的短篇小说《我们应该感谢谁》可以看作是这种寻找最好的注脚。从“油菜坡”乡村来到城市的兄妹三人将瘫痪的父亲送回乡下交由村长尤神照顾。父亲过世后,兄妹三人为表示感谢送给村长尤神一台电视,而喇叭手钱春早则告密说其实是自己的老婆在照顾老人,他才应该得到感谢,但最后兄妹三人却发现这不是真相,真正应该感谢的人是哑巴金斗。表面上这是在寻找恩人,其实更应该看作是在寻找真正的底层,是对底层的一次“分层”发掘。在已成为城里人的大树三兄妹看来,“油菜坡”乡村的一切均在底层之列,因而无法分辨谁才是真正应该感谢的人,谁才是真正的底层。这样一种以俯视的姿态看待乡村,当然只能看到乡村的平面图,也是很多底层作家对乡村认识的局限,但真正的乡村立体雕塑需要置身其中才能看到,小说展现出作家力图审视底层横截面的努力。作品中村长尤神、喇叭手钱春早和哑巴金斗构成了乡村结构的三层,真正的最底层是哑巴金斗。作者别具匠心地将金斗设计成哑巴,使他甚至不能像钱春早那样悄悄告密,说出事实的真相,它象征着真正的底层已经丧失了话语能力,不能表达自己。
贾平凹的《高兴》也涉及底层“分层”的问题,揭示出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底层状态。如收破烂这一底层行业中,竟然存在着复杂的层级关系,分为五等人事:提着口袋翻垃圾的,拉着架子车或蹬个三轮车走街过巷的,分包居民小区不再跑街的,负责一个大区域得进贡的,最后是独霸城市一方收行业费的“大拿”。这样的分层是显明的、外在的、容易判断的,但有一种更为隐蔽的层级关系却让人习焉不察,如小说里餐馆小工欺负收破烂的五富,五富又看不上游手好闲当乞丐的石热闹。他们都是社会的底层,彼此分处不同的行业,这种行业身份虽然名义上没有高低贵贱,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却形成了共同的上下指认,所以餐馆小工才觉得欺负收破烂的五富理所当然。这种无法排除的而又无处不在的意识层面的默契是怎样形成的,无疑与社会文化心理有关,但由于《高兴》的主要切入角度并不在此,对这一题旨的挖掘并不深入。
其次是对底层“流动”问题的探讨。任何社会如果没有阶层的流动将是不可想象的,必将是缺乏活力的,是一潭死水,某种程度上说阶层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底层不是静止的,底层的人们无不渴望脱离贫困,脱离底层,向更高阶层迈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依靠自己的才干,付出艰辛的努力,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幸运,积累了一些财富,但并未真正脱离底层,正在底层的边缘向上挣扎攀援着,他们是底层的上层,是上层的底层,身处二者的夹缝之中,成为了一种“底层边缘人”。这类人物沉浮上下的故事和精神履历是社会阶层流动变化的最好见证,对他们的书写是底层写作空间拓展的一种尝试。
在王十月的《国家订单》,罗伟章的《变脸》、《大嫂谣》等作品中,“底层边缘人”形象已初见端倪。王十月《国家订单》中的小老板,从一个提着蛇皮口袋走出乡村的农民工,到拥有一家小型厂,似乎已经从底层的泥淖里拔出。但“港商”赖查理卷款潜逃一下就让他的工厂面临破产。他准备卖掉设备给工人发工资,表现自己源自底层的善良。可为了逐利,他又让工人连续加班,成了“黑心老板”。为走出底层,他不得不失去底层中某些闪光的东西。最终,走投无路的小老板还是走向了“高压线的铁架”。可见,底层向上的“流动”是异常艰难的,他们要面对赖查理、周城(律师)一样的上层,向上寻找着自己的去处;他们更要面对和自己一同走过来的打工仔,回顾着自己的来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所承受的痛苦甚至多于处于底层本身,他们必须有应对生活的两副面孔。
这一点以写底层著称的罗伟章观察得更细致,《大嫂谣》中对包工头胡贵的描写已见出作者对底层向上挣扎命运的关注,只是未及详尽展开,而到《变脸》中这一形象便丰满起来。小说通过乡村人陈太学一步步变为城市人陈老板的故事,准确地再现了“底层边缘人”的夹缝生存状态及演变轨迹。贫苦农民陈太学来到城市奋斗成为一个小包工头,从最初不得已的赖掉工人工钱到想方设法的克扣,再到在项目经理面前所受的屈辱,“陈太学震动的地方感觉迟钝了,更不像当初赖掉冉老头他们的钱时那么心痛了”。“变脸”本是川剧的一种绝活,在这里作者借此有意强调它的“绝活”意义,通过对变脸的熟练掌握,陈太学越来越富了,也越来越不“底层”了。但在通向阶层上游的路上,真的只能以尊严、良知、道德的失落为代价吗?显然,将陈太学由底层向上路途中的“变脸”全部归因于没有退路、身不由己未免武断,作者指给他们的道路略显单狭,他们理应有更多的选择。
底层的流动有向上的攀移,也有向下的滑落,方方的《万箭穿心》可以视作一个城市妇女由衣食无忧的中产者重新回到贫困底层的故事。主人公李宝莉因为当厂办主任的丈夫而有着优越的生活,但丈夫外遇,李宝莉报警捉奸致其自杀,突然之间赡养公婆、抚养儿子的责任落在李宝莉的肩上。没学历、没经验、年龄大的李宝莉只好干起了最为底层的苦力“扁担”,经历了底层所能遭遇的一切苦难,如体力的付出、流氓的欺负,甚至是卖血供儿子上学等。由于小说着力于李宝莉的一种赎罪和还债情结,因而对其由中产者坠落到底层的心理变化和情感历程表现得还不够充分。
最后,是对底层“变异”叙事的尝试。在“底层叙事”中,还存在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变异情况,那就是底层人物与动物关系的透视,这或许是作家无意识的共同倾向,但同时也可认为是由于“底层叙事”题材的过于单一所致。动物叙事是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这类作品大多数的最终落脚点都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主题,而这里提到的底层动物叙事则着力于开掘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下,底层的人与动物在社会学层面的紧张关系。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作品,都选择了与人的社会生活更为紧密、更具情感关联的“狗”作为叙事对象,如陈应松的《太平狗》、罗伟章的《狗的一九三二》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民进城”成为新世纪小说最为炽兴的故事类型,然而陈应松的《太平狗》并没有淹没于这滚滚洪流中,这主要得力于作者独辟蹊径,让一条乡下的狗随着主人进入城市,由此故事一分为二、不再单薄,人与狗各自的命运相互映衬,使小说的意义含量稍显厚重。山区农民程大种进城打工,他的狗“太平”悄悄地跟着,因为碍事,程大种对纠缠不休的狗大打出手,将之驱逐。小说里程大种的遭遇与大多数进城农民的命运并无二致:投靠城市里的姑妈遭到白眼,忍受城市人歧视干着工钱极少却最苦最累的活,最后被骗到黑工场,凄惨地死去。如果仅此而已,这将是“底层叙事”平淡模式的又一个,然而狗的存在却使文本的意蕴得以丰富。“太平”作为一只乡下土狗进入城市,它的遭遇与程大种如出一辙:电车上遭到围攻;与城市里洒着香水的苏格兰牧羊犬的对比;在价值二十万的藏獒前被城管队长唤作“×狗”,四处流浪。最终狗找到程大种,在危境前二者重又不离不弃。显然,作者的用心是将人与狗在城市的命运进行对比并交织在一起,喻指“乡下人”和“乡下狗”一样在各自的种群中都属于底层,而在陌生的城市最终只有二者才能彼此忠诚、相互依靠。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即使作者力图使故事情节更为复杂曲折,叙事表达上更加立体多元,然而故事的内核却依然延续着典型的底层苦情模式。
在罗伟章的《狗的一九三二》中,虽然故事时间向前延伸至1932年,可由于故事发生地老君山的封闭自足性,作品中对自然环境的强调屏蔽了社会环境和时间因素的干扰,使事件更具穿越性,从而获得了当下意义,同样可以视为一个“底层叙事”文本。与《太平狗》不同,这里作者没有将人与狗进行同构,使之同一化,而是着力展示在生存困境中人狗关系的紧张、松弛、对峙、和解,挖掘其中隐藏的人的动物性及狗的“人”性。由于战争和饥荒,老君山的陈德明、陈召父子受到死亡的威胁。在饥饿面前本来亲密的人狗关系陡然面临严峻的考验,人的生存必须要以狗的牺牲为代价,在求生本能的拷问下原本善良的底层在面对更弱势也更为底层的动物时,人性最为隐秘的罅隙开始暴露。陈召不顾父亲的反对,杀死了两只小狗,母狗老黄带着幸存的小狗小黄逃离陈家。最终陈德明饿死,陈召将之葬在屋后的空地。老黄独自回来准备献身,与来掏陈德明尸体的群狼搏斗被吃掉,显示出狗极具“人”性的一面。灾荒过后,长大的小黄也回到陈家报恩,当所有人都为狗的忠心所感动并认为陈召理所应当地会好好对待小黄时,陈召却设计慢慢地将小黄绞死——理由很简单,就是它曾经背叛过自己。这里,作品不再将上层对底层的剥夺与施压作为重点,而是通过自然的饥荒抽离出一个完全绝对化的生存困境,在这一境地中对习惯中的善良底层的精神底里进行查探、拷询与显形,揭示出底层内部的伤害与分裂。
三
从以上对“底层叙事”流变的追踪与分析可以看出,作家对“底层”自身的书写更加全面和深入,对“底层叙事”的简单重复有所自省,也试图形成多样化的创新图景,寻找更具表述可能的意义生长点。然而,整体上看,新世纪十年来“底层叙事”的多样化丰富化的创作图景还并未出现,无论是“分层”、“流动”,还是“变异”,更多的都是叙述对象与书写形式的变化,其精神品格与审美格调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与创新。“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多样化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价值尺度、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的多样性,也就是作家艺术地掌握生活的方式的多样。”④ 因此可以看到,在新世纪十年中段的巅峰期之后,2008年“底层叙事”的汹涌潮流开始稍显乏力。这可以从以现实主义为办刊宗旨,力推“底层叙事”的大型文学刊物《当代》上发现端倪,在2008年全部6期《当代》的主打长篇小说中,涉关底层的作品已难得一见,同时以“底层叙事”为议题的学术会议也日渐稀少。读者与评论家的逐渐退场,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底层叙事”有淡出新世纪文学的中心、走向衰落的危险。
究寻“底层叙事”疲态尽显的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题材单一雷同、艺术乏善可陈外,更为重要的是精神资源的缺失。这种缺失与后现代消费主义语境下大众文化的兴起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作为消费主义社会重要特征的大众文化迅速膨胀,对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造成挤压、覆盖,占据了文化思潮的中心舞台。原本高雅、严肃和深刻的纯文学,为适应大众文化对文化商品化、审美平面化的要求,必须不断修正自己的创作路向。我们看到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出现了“寻租写作”、“改编写作”、“新闻写作”等倾向。为实现被改编成影视剧的“最后一跃”,小说更强调故事的完整性、可读性和传奇性。“底层叙事”由“小说月报”走向“故事会”,文学的经典意识荡然无存,“平面化”的叙事大行其道,追求短暂、即时性的美学趣味使文学摒弃了对深度意义、永恒价值、理性蕴涵的探索。在这样一种整体性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底层叙事”成为新世纪中国小说主潮实属不易,在某种程度上,它表现出中国作家在“后现代”语境中力图为当代文化建设注入活力的一种姿态,也体现出“底层叙事”与消费文化相冲突、相抗衡的一种努力。然而,从另一向度上看,仍然作为“纯文学”面目出现的“底层叙事”又势必受到消费文化的剥蚀与挤压,使其原本就缺少深厚文化底蕴的叙事又不能不迎合消费时代大众的阅读趣味,适应市场的需要(也可说一定程度上作家在消费主义逼迫下放弃了精神资源的寻找)。由此可见,“底层叙事”正是在这样一种“悖论”式的语境中持守着所谓纯文学的最后防线。今天,自觉抵御消费时代的种种诱因,不断充实现实主义的精神血液,坚守面向民众的写作姿态,仍然是“底层叙事”最切要的价值立场选择与文学承担意识。
另一“悖论”还表现在,过于“贴近生活”也影响了“底层叙事”在更高层面看取当前中国社会现实,并对之进行解读和审美创造的可能。毫无疑问,“底层叙事”对现实社会特别是当下生活的干预是其最有价值的部分,但同时这也造成了一种困境,那就是由于与生活贴合得过于紧密,从而缺乏必要的审美距离,使作品呈现出的生活是原生态、展览式、没有经过艺术处理的“生存现场”。陈应松曾说:“因为‘生存’是最大的、最鲜活的,充满了动感、实感,有血、有泪、有感情参与的一个词,‘生存’对于许多人特别是底层人来说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你这样的现场所获得的一定是十分厚重的、沉重的,充满了分量的东西。作家所写的东西一定是双向选择,双向感动。你选择了沉甸甸的东西,你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是轻飘的轻佻的。”⑤ 显然,陈应松是将“生存”当成了唯一有价值的书写内容,而不以此为内容的作品必然是“轻飘”、“轻佻”的,也就是说作品必须呈现底层人物的生存景观才是“充满了分量的东西”。我们不怀疑书写“生存”的意义,它展示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底层民众所承受的苦难与阵痛,寄寓着作家深切的同情,并由他们发出了底层自身不能发出的呐喊与吁求,以期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这是“底层叙事”赢得尊重的关键所在。这种“平民化”的视角和对“平民精神”的追求,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其书写显然还缺少阔深的文化视野的烛照以及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启蒙精神的高度。我们看到无论是陈春贵、鞠广大,还是来泰、刘高兴,他们的苦难都来自乡村的贫穷和城市的歧视;而贫穷和歧视又似乎是兀自挺立,不知所由。作品并未给我们指出它们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只是满足于呈现或复制现象,而对现象背后的人性构成、道德判断、精神取向、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并无追问。某种意义上看,“底层叙事”又是一种“苦难叙事”,它以表现人在生活中的苦难为满足,把引得读者掉下一捧同情的眼泪作为目标。然而“悲剧中的怜悯绝不仅仅是‘同情的眼泪’。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由于突然洞见了命运的力量与人生的虚无而唤起的一种‘普遍情感’”⑥。因此,这样的苦难只是“生活的悲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悲剧”。它没有足以触动人心的悲剧力量和审美震撼,更谈不上悲剧精神了。阎连科谈及《受活》创作目的的一番话或许更有所启发:“《受活》对我个人来说,一是表达了劳苦人和现实社会之间紧张的关系,二是表达了作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那种焦灼不安、无所适从的内心。”⑦ “穷苦人与现实社会之间紧张的关系”正是目前我们大多数作品都拥有的,即是作品中人物现实的生活苦难;而真正缺乏的是“现代化的进程中那种焦灼不安、无所适从的内心”,即是在这一历史阶段内人的不可逆转的现代化焦虑。如果作品将悲剧的维度指向当前中国人无法回避、必须承受的现代化阵痛,试图反抗而又无力反抗的悖论性处境,也许能有更多的收获。
当然,如果说作家对此完全无知无觉,并不是事实的真相。早在20世纪末,王安忆就对文学创作缺乏与生活的“距离”有着清醒的认识:“像我们目前的描写发展中城市生活的小说,往往是恶俗的故事,这是过于接近的现实提供的资料。”⑧ 而贾平凹在《高兴》的后记中也说:“这个年代的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⑨ 贾平凹的话实际上更多是透露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尴尬和无奈,或者说这种无奈背面隐含着作家对社会历史“使命承担”的避让与不负责任。当代小说的两位扛鼎者,尚且对文学“大精神”的缺失有着这样的困惑与悲叹,难道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叙事”真的只能提供一份当下生活的社会记录而已吗?“底层叙事”应向何处寻找那些可供滋补的精神资源呢?
实际上,“底层叙事”并非当代作家的独创,它其实是“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新世纪的延伸。“底层叙事”完全可以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庞大深厚的根系中获得丰富的精神滋养。“五四”以来的现代启蒙精神无疑并且应该成为“底层叙事”极需补充的钙片。由鲁迅开创的“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现代启蒙精神为核心价值构成,他对底层民众的书写,既有知识分子的道德同情与怜悯,更不乏清醒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而后者则是新世纪“底层叙事”最为缺乏的。在“底层叙事”中,作家虽然能够发现底层民众生活贫困、漂泊无依的苦难,但只能在“纯悲悯”的漩涡中打转。他们没有办法解读这些问题,更谈不上开出“药方”;对于来泰、刘高兴们的不幸,他们只能随其所便、听其所怨,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无力感。正如吴玄《发廊》中的叙述者“我”一样,尽管考上大学在城里当了教师,但面对妹妹方圆在城市中不断恶化的悲剧命运却毫无办法,只能发出一声长叹:“我这么没用,能帮方圆什么忙?”——这事实上可以看作是整个底层作家面对描述对象时的无奈感喟。
要冲出这样的困围,需要一种清醒的现代“理性批判”精神的介入。这种理性批判精神要求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当前中国人特别是底层民众的命运与前途,而不能只纠缠于生存窘境的展示与堆砌,止步于无奈的怜悯与同情。作家不能只根据某些生活的表象草率地作出真假判断、善恶指认,而应该深入表象背后的底里,分析传统与现代交织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与民族文化心理,反映、揭示病灶的所在,这样才能对人民真正有所助益。同时,这种理性批判精神更应灌注到对底层人物的主体选择、主体价值的审视中去。我们看到的“底层叙事”中主人公的困境、绝境,无一例外地由外部生存压力所导致,而作为人的主体选择、精神力量却无关紧要,对主人公的行为起不到丝毫作用。作品中的人物被作者所制造的一个又一个物质困境所挟持、绑架,精神取向极为匮乏,没有任何自主能力,都走向了似乎是非此不可的道路。而对当代社会中由于物欲的泛滥、价值的散佚、观念的模糊、精神的贫困等所造成的人性的堕落、道德的沦丧、人性恶的膨胀等种种现象并无深入的挖掘。因此,鲁迅那种峻切地深度追问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精神在当下更显得弥足珍贵。
“底层叙事”因“贴近生活”而过于“现世”,使其作品以无批判的暴露为主色调,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生活中的冰冷与疼痛、叹息与麻木,是人与人之间的撕裂与伤害,而那些呼唤爱、表现美,看取光明、引人向善的具有正面精神价值力量,能给人希望与振奋的暖色调作品却难得一见。因此,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叙事”只是匍匐于纯客观化的叙事表面,对生活困境的机械复制只能使读者陷入生活的绝望,无法给人以艺术的感化与熏染,同时也导致了自身创作艺术想象力的匮乏,像20世纪80年代的《哦,香雪》、《老井》一样带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品再也难觅踪迹。真正要为底层拨开乌云,透出阳光,撷取生活的亮色,并将之呈现出来,给灵魂以抚慰,给精神以支撑,必须要有理想主义光芒的烛照。这在更深层次上关涉现代文化精神的建构问题。新世纪正处于一个多元价值观交相碰撞、多种文化精神拉锯反复的非常时期,当人们在迷惘观望的时候,作为当代文化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理应有这样的历史冲动和使命感,从民族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文明意识的价值选择和更新中塑造崭新的现代文化精神。
新世纪以来从“身体写作”、“美女写作”,到“80后写作”、“打工文学”等等,各类名称层出不穷,眩人耳目。然而无论披着何种名号的外衣,文学最终必须以作品证明自身。那些曾经喧嚣一时的各类名目下的作品今天还能让人想起多少,并说这是一部值得再次阅读的作品呢?其实,“底层”从来就是现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创作资源,而“底层叙事”早已构成了新文学的优良传统,鲁迅笔下的“鲁镇”世界、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以及一大批乡土作家的作品,无一不是以最为底层的劳动人民为描写对象。既然文学对底层的关注早已有之,为什么直到新世纪才有“底层叙事”这样颇为含糊的命名呢?这其中有命名的快感和评论的需要,但更为深层的原因是这一命名契合了公众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化的担心与恐惧,因而“底层叙事”才迅速得到大众的认可与接受。其实,如何命名倒无关紧要,如果“底层叙事”能够自拔于现象的泥潭,撇弃对大众的审美预期和心理需求的一味迎合,加强对底层自身精神缺陷和人性弱点的反思,承继“五四”以来启蒙文学之国民性批判的主题深度以及“鲁迅式”的自省精神,它应该和可以避免陷入到概念化的写作路径中。如最近引起较大反响的青年批评家梁鸿的“非虚构文本”《梁庄》,就在放低知识分子的姿态后,结合社会调查、口述实录、访谈等不同的体裁,“突破了‘从文学到文学’的内在循环”⑩,呈现出一个真实而又发人深省的中国乡村世界,为“底层叙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向度。当下,“非虚构”文本已非个别现象,而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为徘徊中的“底层叙事”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它打破了小说叙事的固化模式,以“纪实”性叙事充实文本的内在层面,在关注民生、切合时弊方面,也显示了更为强大的能力;但它能否突破报告和纪实的局限而获得真正文学性,却也正是“底层叙事”同样面对的问题。
十年回首,无疑“底层叙事”以其显眼的声势已经在新世纪的文学版图中牢牢地圈定了自己的疆域,但它能否作为具有坚实作品支撑的文学创作潮流持续深入地发展下去,而不仅仅是以现象本身进入文学史,这还需要通过更多更精的作品来证明,我们期待着。
注释:
① 陈应松、李云雷:《“底层叙事”中的艺术问题》,载《上海文学》,2007(11)。
② 曹征路:《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2)。
③ 刘继明:《我们怎样叙述底层?》,载《天涯》,2005(5)。
④ 雷达:《论创作主体的多样化趋势》,载《小说评论》,1991(3)。
⑤ 陈应松:《文学的突围》,载《上海文学》,2008(1)。
⑥ 朱光潜:《悲剧的心理学》,第108-10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⑦ 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新尝试》,载《读书》,2004(3)。
⑧ 王安忆:《生活的形式》,载《上海文学》,1999(5)。
⑨ 贾平凹:《我和刘高兴——长篇小说〈高兴〉后记》,载《美文》(上半月),2007(8)。
⑩ 李云雷:《我们能否理解“故乡”?——读梁鸿的〈梁庄〉》,载《南方文坛》,2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