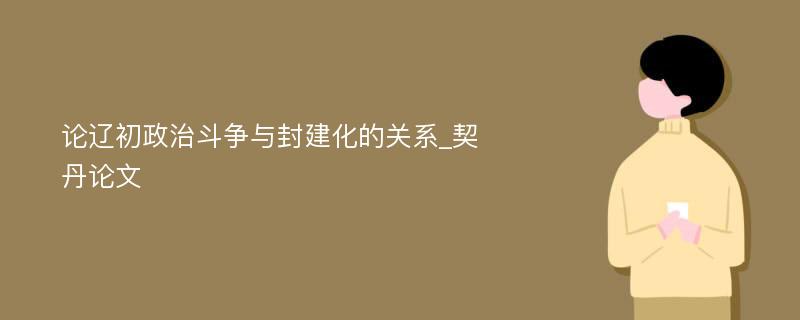
试论辽朝前期的政争与封建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建论文,试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2)03-0105-04
(一)
辽宋金时期,我是历史上由唐末五代的大分裂到元代大统一的一个过渡阶段,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时期,辽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能在短时期内从落后的社会形态和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崛起,与强大的中原王朝并立达数百年之久,重要的原因即受到了中原王朝政治结构和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并吸纳了唐、宋及历代汉族王朝的各种传统。辽朝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也就是契丹族与汉族频繁交往并接受其影响的过程。辽朝自太祖草创,世宗以降的发展,国家体制开始纳入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轨道。至景圣时期,基本完成了封建化改革。他们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更新和向外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追溯契丹族的历史,他们是我国北方古老的东胡族系鲜卑族的一支,长期生息在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一带,过着氏族部落的游牧生活,北魏时已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但直至公元6世纪后期才形成部落联盟,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契丹族才由氏族部落进入奴隶制,逐渐成为与中原汉族封建政权相对立的北方一大强国,迅速地向封建制过渡。关于阿保机所建辽政权的性质问题,这里说几句。对于此问题,学术界各执一说,迄今无定论。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第六册认为:阿保机政权是在氏族公社基础上建立的奴隶制国家,杨树森著的《辽史简编》[1]、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纲》亦持此观点;但华山、费国庆《阿保机建国前契丹社会试探》、[2]张博泉《略谈对契丹社会的看法》[3]及尚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就认为契丹族由原始氏族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我们认为阿保机创建的是一个奴隶制国家,虽然建立国家的模式是从中原汉制承袭而来,但国之根本是部族,农耕人口不占绝对数字,正如陈述在《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指出的:“阿保机的汗国(帝国)是以奴隶占有为基础的各部落联合”,就社会生产方式看,游牧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奴隶制是主要的。对财产与奴隶的无限贪欲促使阿保机不断发动对邻族的战争,而这种为争夺人口与土地而发动的战争,正是奴隶制社会的显著标志之一。据《辽史·兵卫志》记载,阿保机曾对幽云地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战争,如阿保机即位“六年春,亲征幽州,东西旌旗相望,亘数百里。所经郡县望风皆下,浮获甚众,振旅而还”;神册元年(916),“攻蔚、新、武、妫、儒五州,俘获不可胜纪,斩不从命者一万四千七百级”,这也是奴隶制本身不可克服的顽症。我们认为阿保机建立的国家是奴隶制政权,并不否认在契丹社会里存在着封建经济关系,事实上在阿保机建国前后,这种封建因素已经产生。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汉城”。何谓汉城?指的主要是汉族人居住的地方,《辽史》卷60《食货志》记载:“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滑盐县也。”《通鉴考异》引宋白话:“阿保机居汉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龙门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韦二界相连之地。其地滦河上源,西有盐泊之利,则后魏滑盐县也。”《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又载,“天佑末,阿保机乃自称皇帝,署中国官号。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楼邑,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城南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其实,汉城应理解为类名而不是专名,姚从吾先生在《契丹汉化的分析》[4]一文中指出:“据辽史(卷三七——三九)地理志,上京临潢府的南城,东京辽阳府的外城,中京大定府的新城,中京道建州旁的新城,均名汉城。当时契丹人利用汉俘,难民建置的州县,就《辽史·地理志》约略估计即有38处。上述汉城的特色,‘市中有鼓楼,下列市肆。有孔子庙,文昌阁,城隍庙,祖先祠堂,佛寺道观。’”汉城里的汉人“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5]姚先生认为:“汉城即汉人所居之城之义,辽初所建之汉城,为汉人所居者,为数不胜枚举,不限定在滑盐县之一城。”[6]傅海波先生(德)认为:“汉城不是被奴役的殖民地,也不是流放犯的居所,而是变成充满活力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城中的许多汉人居民不是俘囚,而是从混乱的和受压迫的中国边疆各镇自愿跑来的流民。这些居民,不管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对契丹的建国有很大的帮助。”[7]的确,在草原上广建汉城,汉族先进的文化传入了北方。而汉人却没有成为部民或牧奴,封建制度存在于汉城中,这就加深了中原王朝对北方少数民族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种封建因素的出现及长期积累,加速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为以后走向封建化开拓了前进的道路。但是就当时阿保机建国后整个国家社会状况而言,辽国还是以畜牧经济为基础的奴隶制政权,契丹社会虽已有封建制成分,但封建制生产关系还不能战胜奴隶制,阿保机虽在政治方面采取了一些汉化措施,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在经历了太祖、太宗等五代皇帝共半个多世纪的统治,至圣宗时期阶级关系真正发生了重大变化,辽朝才进入了封建社会,并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也就是说,到辽朝中期,特别是圣宗时代,辽朝才全面确立了封建制度。
这里顺带说一下辽朝的分期。辽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统治的70多年,史学界视之为辽朝中期。将中期以前的80年看为初期,初期又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是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德光统治时期,认为这段时期是繁荣的奴隶社会;后段是世宗耶律阮、穆宗耶律景、景宗耶律贤统治时期,认为这一时期处在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之中。把道宗耶律洪基、天祚帝耶律延禧统治时期视为辽朝后期。[8]这种划分不无道理,但我们立足于辽朝封建化进程,提出另一种分法。在总体上我们仍把辽朝的历史划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在具体分段上,我们主张将景宗、圣宗和兴宗在位期间的历史视为辽朝中期。我们认为,景宗以来,人人望治,经过景宗的社会改革,辽朝实际已在向封建社会过渡,故景宗的统治可视为辽朝中期的前段,也就是说把景宗在位期间的历史看作辽朝中期的前段;辽圣宗继位后,辽代逐步进入了政治、经济稳步发展时期,特别是圣宗的一系列封建化改革,使封建因素由增长而达到高峰,因此我们把圣宗朝的统治视为中期的中段;兴宗继位后,继续推行封建化措施,使封建制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而结束了封建化历程,故兴宗一朝的历史可视为辽朝中期的后段;道宗以后辽政权开始逐步由盛世走向衰落,辽朝进入了它的后期阶段。
总之,辽朝封建化进程曲折复杂,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过程,特别是辽朝前期围绕皇位继承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这与契丹历史上形成的家族世选制有密切关系,但其深层的原因乃是封建制与奴隶制的深刻矛盾所导致。因此,探讨一下辽朝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些问题,能更好地学习研究辽史。
(二)
阿保机死后皇族内部展开了复杂激烈的权力之争,史载:“自太祖之世,刺葛、安端首倡祸乱,……李胡而下,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难,与国始终。”[9]辽初皇族内部为什么会多次发生内争?继承权所反映的社会性质变化如何?此问题是辽初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辽初皇族内部的斗争,首先在耶律倍和耶律德光两大支系间展开。前者主张发展尊孔重儒的汉文化,而以述律后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势力则坚持保持契丹化。述律后是一个守旧的代表。《辽史》卷71《淳钦皇后传》载,“太祖崩,后称制,摄军国事。及葬,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于柩。”《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四》记载,阿保机卒于夫余城,“述律后召诸将及酋长难制者之妻,谓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问曰:‘汝思先帝乎?’对曰:‘受先帝恩,岂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见之。’遂杀之。”《契丹国志》卷13《太祖述律皇后传》载,“太祖之崩也,后屡欲以身为殉,诸子泣告,惟截其右腕,置太祖柩中,朝野因号为‘断腕太后’”。“先是,后任智用权,立中子德光,在其国称太后。左右有祭黠者,后辄谓曰:‘为我达语于先帝。’至墓所,即杀之。前后所杀以百数。”最后,平州人赵思温当往,思温不行,太后曰:“汝事先帝亲近,何为不行?”对曰:“亲近莫如后,后行,臣则继之。”太后曰:“吾非不欲从先帝于地下,顾诸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往耳。”述律后“乃断一腕,置墓中,思温亦得免。”《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第二》载:“述律为人多智而忍……左右有过者,多送木叶山,杀于阿保机墓隧中。大将赵思温,本中国人也,以材勇为阿保机所宠,述律后以事怒之,使送木叶山,思温辞不肯行。述律曰:‘尔,先帝亲信,安得不往见之?’思温对曰:‘亲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从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国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断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谏之,乃断其一腕,而释思温不杀。”参照诸史,我们可以看出,述律后断腕可信而“欲以身殉”并不可信,当时,“国中多故”,正值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述律后岂会轻易地退出这场权力角逐的斗争?这只是她表面上做做样子而已,她以“我今寡居”、“思先帝”为借口,对于“难制者”、“左右黠者”、“左右有过者”一律杀之,不难推测这些人大多是她政治上的反对派,至少是不愿与她合作者,述律后借机排斥异已,消灭政敌,对于赵思温“亲莫如后,后何不行?”的发问,述律以“顾诸子幼弱,国家无主”为自己申辩,又不惜用以腕代身自残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心意,也借此来证明奴隶制杀殉风气的合理性,这一切都是述律后极力维护旧制度,为自己今后的统治扫除障碍而做的准备工作。两种对立的政治倾向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耶律倍迫于形势,不得不“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10]述律后因势利导,谓诸臣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德光……遂立之。”[11]天显二年(927)十一月,举行了传统的柴册礼,耶律德光即皇帝位,是为辽太宗,耶律倍被称为“让国皇帝”,守旧派战胜了进步势力。
太宗继位后,因“见疑,以东平为南京,徙倍居之,尽迁其民。又置卫士阴伺动静。”[12]这位昔日的东丹王受猜忌和监视后只好“帅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13]临行刻了一首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据《契丹国志》载,在此之前,东丹王已有一次南逃的举动,因“为逻者所遇,后不罪,遣归东丹。”述律后不罪的原因并非出于亲子之爱,而是因为当时耶律倍在政治上既无实权可言,又未掌握实际的军马大权,故述律后才不予追究。耶律倍奔唐,可想见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已十分紧张。耶律倍初奔后唐时,后唐局势尚好,有“年谷屡丰,兵革罕用”[14],“生民实赖以休息”[15]的小康局面,耶律倍也受到种种优厚待遇,但终究不免有寄人篱下之感,故“虽在异国,常思其亲,问安之使不绝。”[16]当后唐政局混乱时,特别是明宗的养子李从珂发动政变后,由于他不善处理与臣下的关系,和石敬瑭之间“心竞,素不相悦。”[17]侍臣人人自危,耶律倍也不例外,故才秘密向契丹请兵,密报太宗:“从珂弑君,盍讨之。”[18]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和耶律德光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说契丹皇族内新旧两种势力之间的对抗性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耶律倍与耶律德光两大支系的斗争,最终以耶律德光取代耶律倍的皇位继承权而告终,这说明辽国当时虽已具有一定的封建因素,然而这种新生的力量在契丹社会中还极其微弱,守旧势力处于优势地位。再联系契丹社会的传统习俗对人们头脑的禁锢作用,就不难理解耶律倍虽被立为皇太子,而不得不“让国”的原因了。这里说一下契丹旧制。《资治通鉴》卷266载:“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与约,推一人为主,建旗鼓以号令诸部,每三年则以次相代。”阿保机遂久不代,自然引起诸部的不满,反对者首先来自迭刺部,以阿保机“诸弟”刺葛、安端等为代表,诸弟反对阿保机,因为“他进一步破坏了古老的氏族部落组织,日益走向建立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破坏了部落世选制,日益走向建立君主世袭制。”[19](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见《辽金史论文集》)他们发动了三次叛乱,史称“诸弟之乱”,直到公元912年才得到平息。从中可看出,当阿保机成为奴隶主势力改革派的代表后,就遭到了保守派的顽强反抗,他们企图保持部落的固有状态。反对旧势力的斗争从一开始就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就连述律皇后及其子耶律德光也是守旧势力的代表,他们都是传统观念很深的人,虽然太祖后来统一契丹八部,述律皇后有定策之功。迭刺部的守旧势力被击溃后,其他七部中的反对派又联合起来,将阿保机“劫之于境上,求如约。阿保机不得已,传旗鼓,且曰:‘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别自为一部’。七部许之”。这当然是阿保机的权谊之计。陈述先生在《契丹政治史稿》中指出:“支持突欲者犹不免对方毒手,何况突欲?或谓突欲既被迫奔唐,党突欲者也不免刑戮,何以突欲之子兀欲还留在契丹?应当了解,德光被选和突欲落选,用旧俗看来很平常。即令突欲为大汗,也不必是父子传袭。相反的,德光以后的大汗,兀欲仍然有一定的资格或机会,故突欲奔唐,而兀欲仍得不奔。”
契丹统治阶级内部掀起的第二次斗争是在太宗病死栾城后,斗争的双方是耶律倍子永康王兀欲与其叔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李胡。由于李胡“残酷骄盈”,已失众望,惟述律后“溺爱之。”[20]“常嘱意欲以天下传李胡”,[21]而贵族们“万口一辞,愿立永康王。”[22]形势对兀欲极为有利,在直宿卫耶律安搏,军队实权派南院大王耶律吼和北院大王耶律洼等有权势的贵族支持下,兀欲于大同元年(947年)四月,在行军途中的镇阳被诸将拥立为帝,是为辽世宗。皇位由德光系转归倍系,守旧派首次遭到失败。然而守旧势力并不甘心失去政权,李胡举兵夺权但泰得泉一战失败而归,最后世宗与李胡各率军队驻扎潢河横渡,几乎再度兵戎相见,幸得耶律屋质在其间斡旋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撕杀,《辽史拾遗》引《陷北记》:“兀欲及述律后战于沙河,述律兵败而北,兀欲进至独树渡,遂囚述律于扑马山。”最后达成“横渡之约”,述律后只得许立世宗,但斗争并未结束,述律后和李胡仍有“异谋”,以致被迁至祖州后软禁。述律后的失败反映了辽朝新兴力量的发展不可抗拒。但宫廷斗争远未平息,即便世宗在位的五年间也如此,世宗本人也于951年被其堂叔察割所害,据《辽史》卷112《耶律察割传》,是年七月,“帝幸太液谷……群臣皆醉。察割归见寿安王,邀与语,王弗从。察割以谋告耶律盆都,盆都从之。是夕,同率兵入弑太后及帝,因僭位号。”寿安王是耶律德光的长子,这里寿安王虽“弗从”,但仅表明自己不愿参与的态度而已,这或许正是寿安王的高明之处,因为他对察割的言行既未严加制止,更没去举报,反而听之任之,才会出现“察割反,帝遇弑”[23]的情况,这也足见皇族内部斗争的复杂性。
察割之乱被平定后,寿安王耶律璟登上皇位,是为穆宗,政权又转入德光系手中,此后契丹皇族内的斗争更趋激烈频繁,谋反事件此起彼伏,(应历)二年春正月,“太尉忽古质谋逆,伏诛。”六月,“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瀚等谋南奔,事觉,诏暴其罪。”七月,“政事令娄国、林牙敌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谋乱就执”,八月,“眉古得、娄国等伏诛,杖李澣而释之。”(应历)三年(953)十月,“李胡子宛、郎君嵇干、敌烈谋反,事觉,辞逮太平王罨撒葛、林牙华割,郎君新罗等,皆执之。”九年十二月,“王子敌烈,前宣徽使海思及萧达干等谋反,事觉,鞫之。”十年七月,“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等谋反,伏诛”,十月,“李胡子喜隐等谋反,辞连李胡,下狱死”[24]诸如此类,甚多。尽管穆宗的高压政策使得“朝臣多以言获谴”,[25]但这也未能阻止耶律倍一系的再次夺权斗争,世宗的次子耶律贤始终与韩匡嗣,耶律贤适、女里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据《辽史·景宗纪》“穆宗酗酒怠政。帝一日与韩匡嗣语及时事,耶律贤适止之。帝悟,不复言。”这当中帝“悟”些什么,“悟”有多深是不难想象的,还未等耶律倍系的皇族采取行动,穆宗就遇弑了。据《辽史》卷10《穆宗纪下》,十九年二月,“近侍小哥、人花哥、疱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穆宗被弑,《辽史》认为是因他“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其实这只是其一,事情的另一面仍然是皇族内部两大支系斗争日益激烈和表面化的结果。这以后景宗继位,耶律倍一系又一次掌握了契丹统治权。景宗即位,由于思想上早已接受了立长立嫡的观念,故当其病危时,做好了传位准备与防范夺权的措施。“易置大臣,敕诸王各归第,不得私相燕会,随机应变,夺其兵权。”[26]圣宗才得以顺利即位,以后兴宗、道宗二帝即位,都是父子世袭,立嫡立长的封建宗法制度才从此确立下来。
(三)
综观辽初统治阶级内部围统皇位继承问题而引起的政局混乱,可以说与其封建化过程相联系,因为从根本上看是新旧两种势力的对抗,是倾向革新还是倾向保守的斗争,而这些斗争使得契丹在政治上的汉化日益加深。虽然这些争斗与阿保机建国前就已存在的“旧制”有很大关系,具体看是因当时“制度未讲”[27]而这又与旧时推选大汗的“世选”制度分不开,赵翼曾说:“辽初功臣无世袭,而有世选之例。盖世袭则听其子孙自为承袭,世选则于其子孙内量才授之……世选官本契丹旧制,不自辽太祖始也……辽代世选官之制,功大者世选大官,功小者世选小官,褒功而兼量才也。”[28]类似的现象元朝也有,赵翼还对这一现象有过比较,“按辽之世选官,与元时四怯薛相同。如木华黎子孙安童,哈刺哈孙,累世皆为宰相。阿鲁图自言我博尔术后裔,岂以丞相为难得耶。是元时丞相多取于四怯薛之家,与辽之世选宰相,大略相同也。”这反映了旧习惯、旧传统长期以来所具有的影响力。这种“世选”习俗到景、圣时期尚留有明显痕迹,更何况辽初呢?史载:“景宗保宁时,耶律思温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仍命世预其选,圣宗统和九年七月诏有没于王事者,官其子孙,时耶律谐理伐宋,获其将康保威,以功诏世预节度使选,宰相韩德让贵宠,萧敌鲁杀旨,言德让宣赐国姓,籍横帐,由是世预大医选,子孙入官者众,兴宗重熙十六年二月,诏世选官译有才能者用。”[29]我们认为契丹汗位世选传统的影响固然是引起皇位纷争的重要原因,它无疑加深了契丹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矛盾,但这不是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应当是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政见迥异所致,旧习俗不过是被巧妙利用作为争斗的工具罢了。变乱争权中两种势力斗争之激烈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倾向革新的势力有时并不是要明确地放弃旧有制度,但他们的种种做法已引起了守旧贵族的强烈不满,史载:“契丹主(兀欲)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轻慢诸酋长,由是国人不服,诸部数叛,兴兵诛讨,故数年之间,不暇南寇。”[30]这种互相之间的摩擦必然会随着契丹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加深和扩大,最终也必然发展为两个支系间势不两立的斗争,这种斗争往往激烈而残酷,有时呈以妥协的方式暂时得以调和,如“让国皇帝”的让国,但新旧势力之间的对立依然没有改变,因为从根本上看两种政治势力都要为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特权而努力,由谁来执掌辽政至关重要,这涉及到契丹社会中各方面的问题,诸如对中原地区的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对汉人的态度及信赖程度该怎样,先进的生产方式能否得以推行、吸收汉人先进影响的程度怎样,凡此种种都贯穿于两种势力斗争的始终,要求掌权者必须作出不容置疑的回答。这一系列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实质反映了契丹贵族政治上的分歧,即辽朝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是继续保持奴隶制,还是推行封建制的问题。这种守旧与革新的矛盾和斗争以及皇族内部两种势力在不同时期的较量和消长,推动着契丹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程,推动着辽朝实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