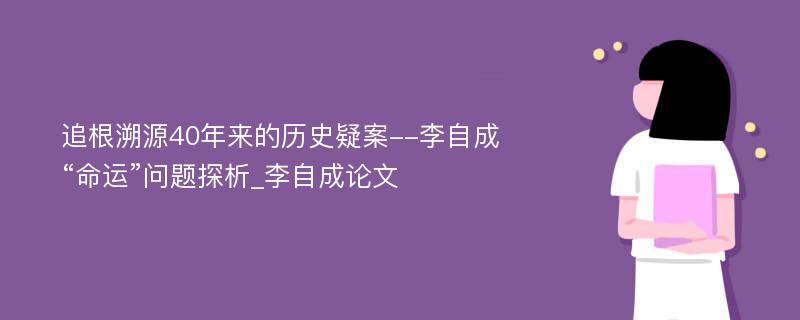
四十年来历史疑案追踪——谈谈李自成“归宿”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疑案论文,归宿论文,四十年论文,历史论文,李自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关于晚明民变领袖李自成的生死问题,我的兴趣和存疑是很早的。1955年毕业分配到历史研究所,我被指派在明清史研究室工作。先读《明史纪事本末》,再读《明史》,同时做《皇明经世文编》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目录提要。当然也尽量涉猎当代人撰写的明清史事的论著,其中包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及李文治先生的《晚明民变》等等。对于明末农民起义的基本史实和李自成的死,我只有个粗略的印象。1956年由于《历史研究》尚归历史研究所主办,和编辑部同在一个不大的院落里。建所伊始,规模不很大,研究人员也不多,又大都是青年人,整天在一起。我听说关于李自成的死,有位姓申的先生寄来一篇文章,论证李自成并未死于通城、通山,而是兵败后入湖南石门夹山为僧而终。年青人好奇心重,总想待发表后以先睹为快,但当时的编辑部大概以申的观点与郭老相左而终未刊用。
当时我并没有想去探索此事,一是对明末史事知道的太少了,不具备这个能力;二是在工作学习之余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到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里,撰写了关于牙人牙行的探讨文章,并予以发表。
事也凑巧,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被正式调入郭沫若主持的《中国史稿》编写组,第一次分工就指令我写好明末农民起义一章。不必讳言,那时参加《史稿》组,被当作一种荣誉和领导的信任,焉敢不努力钻研,以求表现自己。为此,我整整花了三年的功夫。
因为脑海中很早就有个感兴趣的问题,即关于李自成之死的不同说法,因而在读书和查找资料时,自然更加留心。时间日长,材料日多,我发现“战死说”,不论是在通城还是在通山都非常混乱、矛盾和漏洞百出,飘忽不定,令人难以适从。正如徐鼒所云:“自成之死,传闻异辞”。在李自成生死的各种记载里,年月互异,有四五种说法;死地也有四五处之多,而死的方式竟达九种以上,却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材料。
《明史》的编纂,前后将近60年,集中了大批优秀学者。关于明末史事,当然算不上年代久远,一切所需书籍与资料自然一览无余。《明史》是一部公认的严谨史书,凡属重大历史问题都是经过撰写者相互讨论以至争辩然后裁定。譬如:关于严嵩该不该入奸臣传的问题,就数次争论,而且十分激烈。对于李自成究竟是死还是生?众说虽然纷纭,但分析结果,得出的结论只有“终无实据”而已。张文贞公是奉旨监修《明史》的官员,同时也是学者,他的这句话始终对我印象很深。传闻毕竟是传闻,代替不了事实。但写史写书总不能没有个说法,总得从其一说,故史馆诸公裁定了“通城说”,而其死的方式,亦未有定论。
我认为《明史》裁定通城绝非撰史者的疏忽,他们都是当时学术界的佼佼者。我不相信这些连《明史·地理志》都撰写得那样详细的人,竟不知九宫山指何处。竟连明修《寰宇通志》都无人看过,可能吗?我倒觉得是解放后的寡闻学者做了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多余考证!在我看来,史馆诸公在几经斟酌之后认为通山说漏洞、硬伤太多,不及通城说较为稳妥。
通城、通山说虽均无实据,但对夹山说,也仅是文字记载而已。虽似言之凿凿,我也未敢轻信。正如徐鼒所言:“为僧之事,固无足据”。都是文字对文字,缺乏可信的依据和实物印证。
《中国史稿》的说法,当然要以主编郭老的意见为根据,这是不能含混的。同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我不想也不愿意有别的想法。农民起义领袖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为理想而奋斗牺牲,豪气千秋,何其壮烈!说他遁迹法门,总脱不了“逃跑主义”,有损于“伟大形象”,故宁信其死而不信其生。然而满脑子的问题和疑惑,常想若有机会与郭老能谈谈。三年困难时期终于有了这个机会,郭老把《中国史稿》编写组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一是研究问题;二是改善一下生活。其间,我把自己的疑惑和感兴趣的问题简短地告诉了郭老。其实,我的言外之意是想说郭老不该根据两三学者以考辨“九宫山”所在,而定自成死地,也不必于1956年发表声明更改“通城说”。他边走边谈,大意是说要彻底搞清这个问题,还得新材料的发现或者有实物的印证。郭老指出的是一条研究问题的方向,并不涉及谁对谁错,其态度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不像现在有些人对不同意见就一概骂倒。毕竟是大师风范为学子树立了楷模。
那个时期,由于各种原因,“自成生死”并不多么重要,谁也不去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前再打这种无谓的“笔墨官司”。文革之后,“凡是论”被实事求是所取代,李自成归宿这个从未解决的悬案,重新被提了起来。往日的疑惑和兴趣,使我密切注视着通山遇害说和夹山为僧说的论战。
对此问题,我的态度从来就是谨慎的,本着一个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审视和探索一切历史事件,从未想过要反对谁,维护谁。四十年来,若断若续地追踪着李自成归宿问题的史料与文物。尽管如此,在1985年的通山会议上以及将近十年之后的夹山讨论会上,我都没有轻易谈自己的看法。如今有了新材料,有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和不少文物的出土,就不能不对李自成之死重新加以探索论证了。
二
有人说李自成被杀于通山县九宫山,已经定论。这简直像痴人说梦!若非缺乏常识,则是别有用心!此说证明何在?一无首级二无信物,这是当时的结论。据《东华录》所载,英亲王阿济格前后奏报本身就互相矛盾,均未落实。顺治二年七月己巳“摄政王赐阿济格军谕”曰:“尔等先称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贼兵尽皆剿除。后又言自成身死是真,战败贼兵共十三次。则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见在江西,此等奏报情形,前后互异……尔等之意特以奉命剿除流寇,如不称流寇已灭,自成已死,则难以班师,故行欺诳耳。尔等虽行诳称,其谁信之。”作为一个前线指挥,不仅先后奏报不一,对李自成究竟是死是活,始终闪烁其辞。以顺治二年闰六月奏报看,云“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自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可亡,俟就彼再行查访。”此段文字,实不敢推敲,“降卒”所言,既非二十人之一,何以知之?“素识”者往认,何不能辨?除非死者非其人。再说从闰六月到七月受多尔衮责罚,时隔两月,阿济格派人“就彼再行查访”,并无下文,显然没有眉目,得不到证实。文字记录在案无法更改,于是有人心生奇巧,以为能证明阿济格曾被再度起用过,便可推翻“欺诳”之过。既是缺乏常识,又是形而上学之最。军事倥偬之际,戴罪立功者多矣,不等于没有前罪。且看《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之阿济格传乾隆的批谕,“谕曰:朕览实录载英亲王阿济格秉心不纯,往追流贼,诳报已死,又擅至沿边索马,且向巡抚嘱托公事,过迹昭著。虽前次亦有微功,究不足以抵其罪。黜爵实由自取。其子孙前俱降为庶人。削其宗籍。”这便是一记有力的耳光!
据统计,明末清初记李自成事者,史、志、稗、乘大致有六十种左右,但正如徐鼒所言:“自成之死,传闻异辞”。说李自成被打死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么死的,谁打死的?异说纷纭,矛盾百出,且都得不到可信的验证。说法那么多,明清之季的学者也作了一些分析,最后也只能从其一说而已。对于关键问题,即死者是否是李自成,结论还是“终无实据云”。其所谓的“考证”,只是用一种无实证的材料去论证另一种无实据的说法,得出自己倾向的观点,仅此而已。所以有人说:“李自成死于通山,清初已成定论”,清末已“考证清楚”了,简直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在讥讽嘲笑别人的同时,自己竟然连文章也读不懂了!
问题从一开始,一再追查的就是李自成究竟死了没有?九宫山死者究竟是谁?说他是李自成,凭据何在?这是清与南明两个王朝特别关注的事情。而最早文献就是阿济格与何腾蛟的两个奏报。两疏歧异矛盾之处,暂且勿论,一个共同点都是听来的,“空口无凭”。而且都受了各自朝廷的责备。尽管二人为自己竭力辩护,但终归没有“实据”。若有人企图用传闻的记载作“引经据典”的文章,那我还可以告诉他《石匮书后集》等书记载将自成首级献给了何腾蛟,而《程氏宗谱》等书,亦有献首军门佟的记录。一首二献,岂不更加荒唐可笑么!
老实说,迄今为止根据各种记载综合判断,只有一件事是真的,那就是九宫山的确死了个“贼人”。但死者究系何人,并没有解决,或者有人怀着各种目的不愿意承认。阿济格、何腾蛟以及官方人士异口同声,说那就是李自成,是因一保乌纱帽,二怕获罪。而现在有些人,却不正面研究问题,在枝节上大做文章,纠缠不清,实在非论史者所当为。
事实上,根本的问题在于死于通山县九宫山的并不是李自成,而是农民军中一个叫李延的人。在所有的数十种书籍记载中,应该说据有可信性最强的是当事者,当地或当时的人的各种记述了。
通山《程氏宗谱》载:程安思,字九伯“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
《世思堂程氏宗谱》亦云:程九伯“于顺治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
《金氏宗谱》云:“一柏(九伯外甥)一同,追剿闯贼于牛迹岭下”。
其他如《朱氏宗谱》、《王氏宗谱》、《余氏宗谱》等书的记载均可印证此事。
康熙庚午举人谢延树是当地人,著有《诗古文集》,其中有“小月无题”一诗,云:“天剿李延贼,凶魂乃帝催”。
通山发现的新资料,手抄本《九一宫志》(于道观经卷中发现)共十一则,千余字,时间从顺治二年到康熙二十年。其中有“阴访李延墓六则”,这六则并未全部披露,只引了一条自认为对己有利的材料,只说九一道尊于顺治年间接待来自夹山的两位出家人,前来寻找李延死于何处,葬于何地。最后未找到,走后九一道尊捡了一首“红绫诗”。诗云:“顾庐恶梦烟灰灭,华堂已毁躏铁骑。壮士捐躯怀前志,小子残生泄君机。妄言轻信离情起,良谋屡进几度依。难忘恩义凭山吊,莫让随流世外疑”。作为资料果然重要。通山派认为这是藏头诗,乃顾君恩所作,这一观点可以接受,但他们以此断定夹山为僧者乃顾君恩,却是错了。因为去通山找李延墓的是两个僧人而非唯一的一个。从诗意中回味,作者的确泄露了不少“君机”。道出失败的原因、捐躯的“壮士”,只好依从“良谋”,最后提醒人们不要“随流”瞎说,且用了耐人寻味的“世外”二字。这岂不是透出一点消息,即“禅隐”和谋士顾君恩很有关系吗?自成谋士,兵败中被杀的杀降的降,记录均在,唯顾君恩不知下落,此人每在关键时刻,始见于记载,确为自成出了“良谋”度过了多次难关。此诗又一次证明了这点。
通山说的学子,常指责别人不以科学态度对待史实,以至谩骂讥讽别人,对别人竭尽污蔑之能事。而他们不仅否认史实,且编造历史,假造《弋闯志》,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编造假《家谱》。相反,对一些有价值能说明问题但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如《九一宫志》等等,竟然采取了掩盖封锁的手法。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已经说明了真相所在么?
通山死者乃李延,即使《通山县志》上,也赫然写着:“九宫山北有李延墓”。
据通城派学子所写《通城说新探》一文云:六十年代初在通山县九宫山一道观内,曾发现过清乾隆年间该观道士曾为李延立了一块“李延将军墓碑”,大意记述了李延在当地活动时军纪很好,与道士们相处颇为融洽。像这种珍贵资料,通山说者为什么长期尘封,秘而不宣?
这些资料充分说明了通山九宫山死难的是有名有姓的李延其人。通山说者众口一辞,说打死者为程九伯与其外甥金一柏,那么程、金二氏自是当事人,则程、金二氏之宗谱,当然是确证无疑的第一手材料。那么,二氏既非农民军内部人,何以知其死者是李延呢?显然和他们宗谱中所记之“得珠冠、龙袍、金印”分不开(是龙袍还是蟒袍?两者差异甚微,一般人很难区分。珠冠不等于皇冠。珠冠、蟒袍,宠臣、大臣均可服用)。许多官修志书如《湖北通志·武备志》,亦不讳言“剥其衣得龙袍金印”。道理很简单,也十分明显,金印上刻着的就是李延。不然程氏之流是不会知道的。如果印刻“李自成”三字,宗谱上亦不会编出个“李延”二字来!宗谱与志书都说此物献于“军门佟”,先不管这个佟是谁(因当时清高级将领中有两三个“军门佟”的人),倘是“李自成”三字,“军门佟”焉敢匿藏不报,而此实物信证,足可平息各种风波,也不会有这个三百五十余年的历史疑案了。这个道理三岁孩子也明白。
通山说的解释漏洞太大了,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硬伤,怎么办呢?只有胡说一通了。童书业先生在此根本问题上道是本本分分写着“也许”、“或者”、“假定是否事实”,有待进一步研究,等等,其实事求是的态度,与那些强词夺理者实不能同日而语(见《李自成死事考异》)。
李延根本就不是李自成,连博学的童书业先生也未敢说是“自成别名”。1984年5 月在通城县发现的《彭城堂金氏宗谱》康熙丙申谱序说:“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狂,其烧毁民居也不殊秦火之虐焰”。这是当地人记当地事,而且正是李延烧了他们的金氏宗祠,刻骨铭记,不会错录。标明了俨然两个不同的人。
还有一个印证,据申悦庐先生引《半窝杂记》云:一道者言“闯王知大事已去,抽身而隐。有一义儿,受恩最厚,代统其众,不料至九宫山为村民所杀,出于意外也。”此又与通山《九一宫志》之“阴访李延墓六则”相互印证。
遍查《延绥镇志》、《延安府志》、《米脂县志》,他如《绥寇纪略》、《罪惟录》、《后鉴录》、《鹿樵纪闻》、《明季北略》、《甲申传信录》、《怀陵流寇始终录》等等,记自成乳名、字者多矣,唯独无“延”字。李自成也根本不可能叫李延,谁都知道李过乃自成之侄,据李宝忠《永昌演义》,其侄辈除李过,尚有李通、李遵、李迪(迪、廸通用)等等,米脂县闯王纪念馆馆长申长明先生调查表明:自成侄辈皆以“辶”命名,辈分有别。在封建宗法社会中李自成绝对不可能又名李延。
栾星先生(通山派)曾寄我所著《李岩之谜》一书,拜读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李延的信息。他说60年代初,在李岩故里调查李岩事迹,在县委招待所碰见米脂县两位干部,同居一室,便聊了起来。当自己说到是来调查李岩时,米脂的干部便脱口说,我们县里也有他的后代,我在李氏家谱中看到过李延的名字。栾星认为这不可能,显然把同音异字弄错了。后来我写信请申长明先生追查米脂《李氏宗谱》,可惜文革之火焚后,文物幸存甚少,已无原物,实在遗憾,但亦是可印证李延实有其人的。
有人曾想以顾氏《明季实录》之附录《酉阳随笔》之“闯贼名自成,一名炎,米脂人”这条记载,企图用谐音附会,且不说南北音读甚远,其所引曹应昌《上高汇旃先生书》云:“且闻其(自成)更名李兖,以应孩儿兑上之谣”。明言乃“据之传闻”。传闻再加上猜测,和《酉阳随笔》如出一辙,分明是传闻之误。
明明是李延,为什么非要指鹿为马说成是李自成,始作俑者是谁呢?有人对费密的《荒书》评价颇高,其价值在于所记较为详细,但引用者却取其所需,弃其不利。其实恰巧是这部记述较具体的著作,道出了其中蕴含之实情,揭示了一个苦衷和隐秘。
李自成对南北两个朝廷来说都是大敌。阿济格初报“自成已死,贼兵已灭”,双方朝野为之振奋。清王朝为此祭了天地,告了太庙。结果自成生死却得不到证实。朝廷为此感到难堪,便下令追查,英亲王也保证“就彼再行查访”。在此种形势与气氛下,地方官自然压力很大。行查的文书急如星火,县官自然如坐针毡。《荒书》写得明白:“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程九伯为什么不敢出认?以他为首打死的,尸证物证都是李延,封建专制时代他岂不知“冒功领赏”是要砍头的。所以有公文榜谕他也不敢张冠李戴。只有县官亲自跑来,当面说了被杀的是李自成,他才敢走进官府去领赏。这不是把原委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么?这件事完全说明把李延说成李自成,是阿济格谎报在前,而通山县令谎证在后。但还是“终无实证”而无法结案。
非常明确,把李延说成李自成是县官在上级追查的情况下亲口说的。如果说打死人的时间在四五月间(因时间说法不一),除去公文函件的往返时日,“行查到县”的时间不超过七八月间。理由很简单,任何史、志、稗、乘关于此事的记载,也不会早于这位县令的信口雌黄。县令指鹿为马,自有苦衷,但从此传了开去,关于李自成死于通山的记载(通城另当别论)都是这样误传造成的。自县令亲口说谎之后,有两种现象可发人深省。以后所有官修志书如康熙间之《湖广通志》、《湖广武昌府志》、《通山县志》以及后修之《湖北通志》、《九宫山志》等等,均直书死者为李自成(当然偶然也出现矛盾,如《通山县志》载九宫山北有李延墓)。而在当地的宗谱里,尚未贸然违背事实,一般成谱早者依然写着李延,随着时间推移,概律为李延即李自成,最后干脆全是李自成了。
尽管县令因时势所驱,不得不指鹿为马,混乱视听,但毕竟还是拿不出凭据,朝廷当然不信,从未行文予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军门佟”手里所掌握的“龙袍、金印”自然更不敢拿出来上交了。因为一旦证实不是李自成,便是欺君杀头之罪,阿济格就将被处极刑。这个重要的“实证”自然也就因此而灰飞烟灭了。
总之,谎报加谎言,使不少学子莫衷一是,也是使不少学子信以为真。更有个别自以为是者,摆出了“教师爷”的架势,对不从通山说者,不烦冗文,拿着大刀长矛费劲地乱杀乱砍,其实早已无异于唐·吉珂德,把一切都看错了。那种强说为项,洋洋大论的文章不就都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么!
三
关于李自成未死于九宫山的另一种说法,即夹山为僧说,在十年前我也未敢轻信。但也没有理由和凭据对之加以断然否定。研究历史要求实、重材料、讲证据。若怀杂念、主观、偏执以至抱有某种情绪,把不利于“我”者,是资料则断章曲解;对不同意见者则口诛笔伐以期骂倒,那便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
李自成“为僧说”,真正有学问的人虽不相信,不予肯定,但亦未断然否定,斥为荒诞。譬如徐氏《小腆纪年》引了江昱所言之后,按曰“为僧之事,固无足据”。此文句本来浅显,有人竟一叶障目,连“足”字的含义也不懂了。童书业先生是饱学之士,以科学态度,大家风范,讲道理,谈依据,不装腔作势,谩骂别人。尽管他为通山说而“考异”,但结束用辞也不盛气凌人,只云通山说“是比较可靠的”。而对李延、李自成“变”的关键问题,没解决就是没解决,直书曰:“自然还待继续研究”。决不像有的人那样愣是生拉硬扯,自以为是,妄下断言。童先生不否认为僧说“言之凿凿”,只是由于偏信通山而认为越说得“详细”,“所以考据家多不相信”。其实这也不尽然,若说“其世愈晚,传说越繁”是规律,那么通山说之纷纭何尝不是如此呢?这话在五六十年代,甚至80年代我也认可。但那些有名有姓,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详细记载,一旦得到某些实物的印证,就会更显得“言之凿凿”的可贵了。倘若单是记载对记载,文字对文字的扯淡,永远也扯不清,结果必然是各取所信。所以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有实物加以证明,即要拿出“实据”来才能敲定。
有人承认“何璘对历史事件是求真求实的”,却又指责何璘编造出了“禅隐”说,岂不自相矛盾,逻辑混乱。李自成夹山为僧在小范围里早就有传闻,何璘只不过做了“求真求实”的亲身考查,然后以董狐之笔记述罢了。此事先有张琮伯亲身经历于前(康熙初年赴任途中路过夹山与奉天玉和尚面谈甚洽),歙县江昱“特至夹山”眼见于后(亲去夹山见到石塔、遗像,又访问了寺中老僧,认为“奉天玉”是李自成“自寓加点以讳之”),又有张琮伯子孙《半窝杂记》可证。怎么说是“何璘说他当了和尚”。一个隐秘逃命出家的人,能大张旗鼓地张扬吗?即便是在小范围里被个别人窥知,也只能在他死后才渐渐地传了开去。这种极为浅显的道理,竟然有人大作形而上的文章,高明还是拙劣,自有行家去公断。更有人挖空心思在“奉天”二字上不吝笔墨,但“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的石塔,赫然耸立,不止一人见过,只能诠释其由而不能否认其实。岂可以常规律之。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之《流寇琐闻》摘录了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陕西延安府米脂县塘报中一段话,曰:“闯贼名李自成,幼曾为僧,僧名黄来僧”(《广阳杂记》与此略同)。李自成“小名黄来儿”(见《罪惟录》、《绥寇纪略》、《鹿樵纪闻》等书)。当地米脂县塘报,自然不诬。起码印证失败遁迹空门之可能。由于自幼当过和尚,庙中佛事司空见惯,所以再次当起和尚来,自是行家里手,便于隐秘,不易露出破绽,且能够充当“高僧”。这大概是他生前未被察知,瞒天过海,竟然寿终的原因之一。虽未遭宋代李顺为僧而被捕之厄运,却也被当地政府砸毁坟墓,几乎鞭尸。
这些资料在无物印证情况下,并不显眼,只是文字的一说而已。但是近十年来,石门夹山出土和发现了许多重要文物,是可以与文字记载相印证的凭据,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难道不该正视和重新探讨么。我相信倘郭老在世也会去看的。在发现的许多文物中,我以为“西安王马铃”、“梅花诗残版”、“奉天玉诏”以及奉天玉墓的发掘,葬式、墓志铭等尤为重要。墓葬的发掘证实其葬式与陕北米脂一带习俗的一致,墓志铭说明并非一般和尚,隐讳之词不同一般,更说明身份之特殊。“塔铭”,证实奉天玉确有此僧,不只是传闻和文字虚载,也证实何璘亲身考察所写《书李自成传后》之不诬。“西安王”马铃证明乃自成跨骑之物,据《小腆纪年附考》云: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李自成自称“西安王”,故农民军内部是不能随意盗用的。其“梅花诗残版”于夹山寺院残壁中的发现,更证明章太炎先生根据民初民间长期留传的“梅花诗”,考定为李自成所作的确切性。而他对《明史》李自成走死九宫山所提之“六不可信”,增添了事实的依据。尤其是“奉天玉诏”的发现,为奉天玉和尚的身份定了性,非为帝者,焉敢用诏。这些经过国家文物局鉴定是真的文物,否认是徒劳的。把这些点串连成面,加经综合分析,李自成的影子不是从沉淀而浮出水面了吗?对此夹山说者多年做了很多研究(请看《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一书),虽然欠缺之处也有,但也说明了许多问题。文章俱在,自不待我赘言。历史研究常常需要综合分析和考察,在无直接资料简单说明时,需要各种材料或实物综合印证,以究其是非。不能以己之偏见,拒史实于不顾,一味吹毛求疵,这是作为史学研究者不应持有的态度。
就目前通城、通山、石门三家争论来看,关于李自成究竟死在何地,通山说最不可信,而石门夹山说较为可靠。尽管通山说千方百计否认“为僧”史料,割裂夹山出土文物,大肆攻击、造谣,以至无中生有,但都抹杀不了实物的存在,愈来愈多的学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改变了以往的看法。虽然夹山说尚存不足之处,对资料、文物探究不深、不细,但迷雾毕竟近于消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