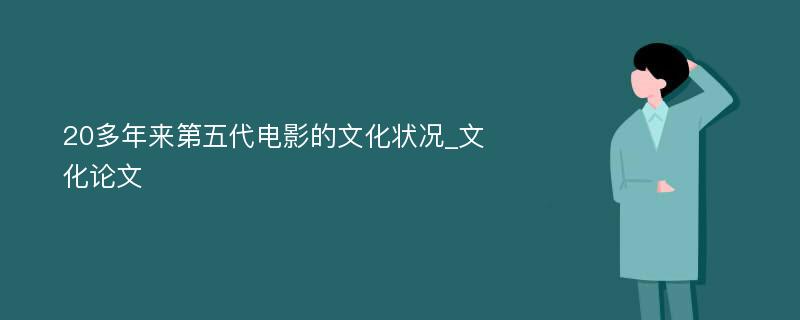
“第五代”电影20年来的文化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势论文,第五代论文,年来论文,文化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2-0116-05
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中国第五代电影”绝不是偶然的勃发,而是应运而生的必然文化产物:天时、地利与人和,它无不一一占到。因之,它“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也便绝非咄咄怪事。然而,任何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化艺术,只能应运而生,不能人为造作;而若要长久发展与进步,则必须有自己坚实健康的根基而“与时俱进”,绝不应“与世浮沉”甚或“随风俯仰”。这正是本文反思中国第五代电影的要旨。
一、第五代导演第一阶段创作的文化体现:“与时俱进”
任何以确切的年代数字截然划分某种文化阶段,都不可能确切,只能是相对的参照。在这里,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延至90年代初期)视为第五代导演创作文化的第一阶段,也如是。
以“文革”结束为时代表征,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文化主导是——批判专制,解放思想,张扬被长久压抑的人性,摆脱捆绑身心的束缚,渴望现代健全的国家体制,追求健康积极的生命实现……对传统文化全方位的检查与反思,对现代人文思想的又一轮接触与体味,其结果便是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人们的观念,进而推动了社会改革、开放的进程。
第五代电影导演整体,作为“一代”艺术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应运而生,并以其特定的艺术传媒手段发挥了应有的文化作用,可以说“不辱使命”。
我们看一下在这阶段中第五代导演代表性的创作:
陈凯歌《黄土地》84、《边走边唱》91,张艺谋《老井》86、《红高粱》86、《菊豆》90、《大红灯笼高高挂》90、《秋菊打官司》92,田状状《猎场扎撒》85、《摇滚青年》89,吴子牛《晚钟》87、《大磨坊》90,李少红《血色清晨》90,夏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88,何群《寡妇村》88、《出嫁女》90,王小列《顽主》88……等。
在上述作品中鲜明地体现了一种整体的文化品格:通过或寓言或传奇、或写实或概括的艺术形象体系,都蕴含着严肃的形而上的社会反思与生命觉悟。《黄土地》以诗意的镜像语言,传达着厚重深沉的人文思考,《边走边唱》则承载着近乎宗教层面的对生命与人生的终极拷问;《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则以寓言体的传奇,张扬着千百年来被压抑、被束缚的健康人性,颠覆着“从来如此”、“天经地义”的专制文化与病态人生;《老井》、《秋菊打官司》之类,或挖掘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生存艰难以及因之产生的人性变异,或准确把握当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与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晚钟》、《大磨坊》等,则通过对历史事件刻骨铭心的剖析、审视,使人们在难以言说的沉默中,体味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清醒的痛悟”;而《血色清晨》、《寡妇村》与《出嫁女》等,则以强烈的民俗色彩,极具震撼性地展示出当代民俗深处的文化蒙昧、畸型、弊端与病变,进而呼唤着清醒、健康、积极、自然的人性境界与生命觉悟;至于《摇滚青年》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等作品,则以热烈的音像语言直接宣泄人文观念的前卫与新潮,或以调侃、戏谑、灰色幽默的方式,表露着对传统、规范、正经的社会法则与个体人生的嘲讽、冲击乃至反叛……
这其间,当然并不排除张艺谋以及其他导演如《代号美洲豹》(88)、《古今大战秦佣情》(89)等另类的影片——或偶走商业路径或试验纯艺术品格——但就总体而言,第五代影片在这个时期的文化主潮则是在“应运而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对社会文化的历史性进步,起了应有的推波助澜作用。也正因此,我们应该说:作为当时社会精英文化的艺术体现者,第五代电影导演们“不辱使命”了。
二、第五代电影第二阶段的文化体现:“与世浮沉”
这第二阶段大致可视为上个世纪的90年代。
这阶段中国文化的总体状态是:消沉与泛滥并生,退隐与寻求同在:回避时代的个性消遣与疏离现实的学术把玩遥相呼应,形而上的拘谨与形而下的放纵相安无事,物质世界的无序活跃与精神领域的低迷平庸“相得益彰”;徘徊而不乏摸索,探寻又往往茫然;在文化多元化的纷纭表象中,则显现着根基的飘游与定向不稳。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化分化现象显得突出、明显。如果说80年代的社会文化有一种整体根基与基础走向的话,90年代社会文化在初期的暂时沉闷之后,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分化——可以说是文化多元化的体现,也可以说是文化散漫化的状态。只就精英文化而言,便呈多种态势:如退隐化、边缘化、皈依化与世俗化(当然也残存着种种潜在的抗争与顽固的坚守)……等等。所谓退隐,就是一定程度的失语;所谓边缘,就是不再作黄钟大吕的主音;所谓皈依,便是回归注解与阐述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职能;所谓世俗,就是索性放下精英者的自命,在“适世”的标榜下追求“适己”的现实。
第五代导演中,确有文化思维的中坚人士,但也难免且自然地在这总体的社会潮流中,产生分化。这期间的种种分化中,有沉沦,有苟且,更多的则是在“现实生存”的前提下,探寻、摸索、试验、开拓,以求中国电影的种种突围与超越,欲为当代电影开掘或保留一道生存之途——只是与80年代主要致力于形而上的文化使命相比,此阶段渐渐向形而下的层面作汗漫的转移。
第五代电影此期的主要创作有:
陈凯歌《霸王别姬》93、《风月》95、《荆轲刺秦王》98,张艺谋《活着》93、《西楚霸王》94、《摇啊摇,摇到外婆桥》95、《有话好好说》97、《一个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99,吴子牛《南京 1937》95、《国歌》99,李少红《红西服》98,张建亚《三毛从军记》92、《绝境逢生》94、《开心哆来咪》97、《紧急迫降》99,夏钢《大撒把》90、《与往事干杯》95、《伴你到黎明》92,何群《凤凰琴》93、《混在北京》95,霍建起《赢家》96、《那人·那山·那狗》99,冯小宁《红河谷》96……等。
这些作品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它们没有了上一阶段的共同根基,而是以各自的人文观念与艺术品格,顺随时世地进行着东行西走、南探北寻——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其间孜孜以求的意念,也不能完全无视其不同品格的艺术营造。
陈凯歌一向以自己强烈表现欲的艺术风格著称,《霸王别姬》中,将古老的京剧艺术与极具现代观赏诱惑的同性恋相混合,浓艳的镜像,精致的造型,委曲的情节,复杂的人性,畸型而真纯的情感,美丽而悲哀的故事……无论被斥为“只为满足西方评委的东方猎奇”,还是被誉为“电影大师级的经典之作”,它自身勿庸置疑的“艺术存在”确是铁定的事实。《荆轲刺秦王》则以更大气的制作、恢宏的场面、极具感官冲击力的镜像语言,掀起了一次“与民共舞”的观赏浪潮。张艺谋的《西楚霸王》也走《刺秦》的路径:构图的精美,故事的曲折,人物脸谱化的张扬,历史艺术化的改写……题材不俗,手段强悍,确有某种“大家气势”。然而,这些作品的人文内涵该怎样评判?它们究竟要在即时的社会生活中传达怎样的文化意识?这种意识又与时代的历史进程有怎样的关系?是张扬一种霸气?是表现某种委曲?是唤醒新时期的人文意识?还是只为“好看”而为之的退守性镜像传奇?
张艺谋的《活着》倒是有些别致的空灵,但与余华的原作相比,过多社会背景的关涉,多少降低了本来涵蕴的形而上悟觉,给观众的感受便只有苦涩的现实性感慨了。而他的《梦醒时分》、《有话好好说》,更与其前期作品的文化内涵迥异,分明体现出人格精神与处世态度的变格与疲软。李少红的《红西服》、夏钢的《大撒把》、《与往事干杯》、何群的《混在北京》等作品则是对芸芸众生的生态扫描,传达、渲泄着,艰难而自强、或惆怅而温婉、或愤世而无奈的种种现实情绪……这类作品是真实的,同时又是散漫的。与前面的传奇自然不属于同一层面,而自身内部的人文取向,也不大(或大不)相同——其林林总总与纷乱不群,被某些评论者视为当代生活与人文心态的“跟拍”与“录相”,不无一定道理。
其它影片更其纷繁:《一个不能少》强调“原生态”,但又明显是趋时的造作;《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我的父亲母亲》、《那人·那山·那狗》均特意传达着既定的人生情境,但其疏离现在、回避当前的潜因,也只能使人产生文化层面的惆怅与迷茫。其它,如吴子牛、冯小宁此期作品中鲜明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张建亚影片的商业化追求,夏钢镜像间都市小人物平凡境况的展示……等等,我们从中既可以感到在总体“适世”、“合时”的影像体系探索寻求中,在导演之间各显身手的比拼,又明显看到每个导演自身的文化游移、变化乃至悖反。
所有这些,恰恰可视为90年代社会文化状态的一种“写实”。
三、新世纪以来第五代电影的“随风俯仰”
此阶段以世纪之交为始。就世纪之交的我国文化态势而论,既有着旧世纪末的失落、悲酸乃至恐惧,又有着新世纪初期的迷茫、惶惑与无所适从。在这种社会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潜意识下,被冠以“大众文化”之名、蕴涵着某种后现代意味的文化思潮的涌现:消费文化的扑涌,世俗欲望的膨胀,不要终极精神的文化快餐,只看“现在”、只要“活着”而不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即时性”享受,满足平面化与肤浅化,只图感受不要觉悟,沉溺于无所用心的轻松情境而拒绝与摒除形而上的悲剧意识……等等,虽不能说已完全占据社会思潮的主流,但其甚嚣尘上的态势,其文化覆盖面之广泛,则勿庸置疑。
在上述文化背景与时代氛围中,如果说,前一时段第五代电影还有着东冲西突、南试北测的文化寻求、探索、期冀的潜意识,那么在此阶段,便基本上只为“活着”而“随风俯仰”,为纯粹形而下的市井消费而终归商品化了。此期间第五代的主要电影作品有:
陈凯歌《温柔地杀我》00、《和你在一起》02,张艺谋《幸福时光》01、《英雄》02,田壮壮《小城之春》22,夏钢《玻璃是透明的》01、《向水倾诉》01、《一见钟情》02,何群《飞虎队·澳门》99、《无声的世界》00,霍建起《九九艳阳天》00、《蓝色爱情》01、《生活秀》02,冯小宁《黄河绝恋》00、《紫日》01,麦丽丝《天上草原》02,以及宁赢的《夏日暖洋洋》01……等。
此阶段电影可细分为三种。第一种:倾心竭力地追求极致之美,以超级感官愉悦(相对于国内影片而言)获得观众青睐,《英雄》是其集大成的代表。以三千万美元的“大手笔”,精心刻意地欲问鼎奥斯卡奖,欲振兴大陆电影票房的濒临危亡,应该说,其动机可嘉,其手段(制作、宣传、营销等)也有力,其经济效果与商业经验更值得重视。但从文化角度审视,且不究其意识形态的传达与20年前正相悖反,只就当前的社会文化效应而论,它不过是适应乃至趋从“世俗消费”而已。其它如《黄河绝恋》、《紫日》、《小城之春》、《天上草原》以及虽非电影但出于张艺谋之手的豪华歌剧《图兰朵》等作品,尽管从审美角度看,均有不坏的体现,但就其文化品格的肤浅、陈旧、平泛与疏离而言,也只能归入“适世”与“适时”的典雅型消费文化一类:镜像表层的“典雅”之下,仍埋藏着商品化的基因。
第二种:以贴近时下小人物的普通生活为标榜,用近乎写实的风格,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力图达到某种“清明上河图”的意蕴。此类影片以《和你在一起》、《生活秀》、《玻璃是透明的》为代表。应该承认,这类作品确实是对时下百姓生态与心态的某种展示,所以能获得部分观众的认可。但因只停止在生活表层的扫描,而没有更重、更深地触及时下百姓内心主弦与集体意识(与集体潜意识),也没有蕴含真正“审时度世”的文化启悟,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现实表现,而只是带有现实风格的世俗摹写,是一种疏离的写实、仿实,因而受到某些人的“伪现实主义”之讥。
第三种则是纯粹商业追求的制作。这类影片当然以世俗的消费需求为唯一对象,其文化层面的“随波逐流”更是自然而然。其间,宁赢的《夏日暖洋洋》倒是对当下社会无根状态的展示,对人生片断的零碎扫描。从观赏角度说或许并不“好看”,其特意为之的叙述方式也不见得高明,但从文化意识看确有意走出新路,而并不随风。这就比一味地沉溺世俗、趋从时潮、满足平浅的大众消费而全然失去“文化自我”来,显得有价值与意义。
但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文化主导取向是屈从大众消费需要的“随风俯仰”。
四、近20年中国文化流变的当前审视
纵观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创作,本文这里要强调:“与时俱进”不应混同于“与世浮沉”,更不能变质为“随风俯仰”。真正的“与时俱进”应奠基在清明认知社会文化的历史大趋势与时代大背景之上,致力于社会文化的健康进展。“与世浮沉”只根据时政与世事的即时需要而生而动,缺乏或暂无一己定向的人文寻觅而漂泊;至于“随风俯仰”则属于只追风潮、全失自我的沉沦。
我国当前的人文态势,正处于大的历史转型时期,总体上可使国民认同、信守的文化,即包括生命意义、人生态度、社会觉悟、国民意识、世界观念,以及与现实有关的各种价值取向、各种机制建构等等所组合的当代健康的主流文化,应该说尚未清醒、稳定地形成,而尚在徘徊、探索、角逐乃至拼争之中,尚在更新、重构前的一时消沉与迷茫中。在这种特定的文化时段,如果我们的文艺作品只停止在杂乱浮泛的现实表层作“适俗”乃至“媚俗”的再现与传达,那么,对现代国民精神的科学建构、对健康昂扬的中华民族的生命,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
当然,生活不能没有平浅的轻松,不能没有休闲的愉悦,不能没有原始的放任,但也不能没有理性的深刻,不能没有思辨的过程。文化不能过于“沉重”让人难以走出压抑,过于沉重决不应该成为文化消费的结果,而消费文化的轻松也决不应该以浅薄为基础让人轻浮,堕入轻浮毁掉的会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构造。
一个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个人,不能没有主导其生存发展的文化灵魂。就社会的文化组成而言,官方文化、大众(民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三足鼎立,才能构成稳定的文化结构。而就三种文化的分工与职责而言,任何时代的精英文化均应处于时代前沿的引领与召唤位置。
第五代电影导演当然不全是文化精英,也不能因其明星、大腕、名人的传媒身份便成了精英文化的天然体现者。但因他们的创作演变,确可窥得近20年来中国文化流程之一斑,也可从反思中对真正怀有时代与历史使命感的文化精英们有所启示。第五代电影导演尽管过了其最辉煌的时运阶段,继他们之后的新人、新作已经破土而出、显出顽强的生命力。但我们还是怀着某种恋旧情结,不无期冀地问一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勿庸置疑,具有一定“后现代基因”的大众文化在当代已经出现并日益泛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国文艺如何因历史与时代特定的文化使命而“定岗、定位”?
有学者借用西人“大众文化”理论,在讲述“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必然产生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因其平面性、消费性与世俗娱悦性的本质,必然要求文化产业(或产业文化)与之相适应……”等等之后,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或运作),便作出如下判断:
“大众的规则就是市场……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要取消。艺术不仅是要贴近生活、走入生活,而且艺术就是生活。艺术在大众社会里转变了性质,在电视里艺术不再是高于生活的个体创造,电视节目应是集体共同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消费品……
“要让他们(指大众)欢快,让他们掌握话语权。这是一个人人参与行动、享受文化、追求娱乐、平等交流的时代,是失去权威、中心话语的时代,是超级民主胜利的时代。”(注:陈默《影视文化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的确,当代电视(或曰现代传媒)文化确已成为大众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消费品。但这绝不等于说:我国当代的文艺创作与运作,就应完全以适应“大众(世俗)文化”的消费需求为终极目的。甚至也不能仅仅以展现带有某种后现代意味的社会生活物像为终极标准——尽管它们可能有某一层面的对社会状况、时代风貌的认识价值。至于所谓“超级民主”之类乌托邦想象、至于不要任何权威与中心的时代臆造、至于完全能够“人人参与行动、享受文化、追求娱乐、平等交流”的政治伊甸园,都只能是纯书斋中的学术性空想。即使是大众文化成为主流的社会,也不可能没有任何权威,只不过没有了惟我独尊且强迫大众接受的专制性权威;中心也还是要有的,只不过不再有唯一的中心,而是多中心的不同形式的有机组合。
所以,对待当前大众文化消费的正确方针应是:在“适应”的基础上对其作进一步升华,在“平等”的交流中对其作自然的推举。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符合历史文化进步大趋势的“奉天承运”,而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随波逐流”。否则,在欢呼“大众文化”终于到来的一片喧嚣与沉溺中,难免会走向自身的反面。
在当代中国,表现“大众文化”这一特定对象的艺术作品,应在一种新的“意义基础”与“价值准则”及“历史引领”的内蕴中,再去展示“社会状态的无意义、无价值与无历史”。或曰:在“无意义”的形像系统的艺术展示中,使观众或读者获得某种反思后的意义的重新定位与价值的新层面的奠基。否则,对象既已经呈“无意义”状态,你再以“无意义”的表现再现之,到底让观众在这一头雾水中得到什么?艺术创作之于社会
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便莫名其妙了。
另外,现在人们所说的“后现代文化”,虽然绵延至今已经几十年或更长,但从世界文化数千年历史流变的大背景来看,毕竟只是一种过渡文化(或曰文化的过渡)。它绝不是、也不应是一种终极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相对于“现代主义文化”的“后文化”,又同时具有孕育期间的健康的新世纪多元组合文化的“前文化”态势。真正的现代主义之后的“后现代文化”,应是在上述变态、剧痛之后的重新融合:多元展示在健康的总体新价值与新意义基础上的文化共舞。
对学界而言,既要理解后现代产生的背景及现时的状态与意义,又要有历史主义的宏观审视与时代把握。一味宣扬、恣意展览而不加节制与必要的把握,无异饮鸩止渴。但也要注意“过犹不及”的弊端:若不能审时度势地一味长久恶治,以“后现代主义”的极端性反叛、否定、打倒、推翻一切维系世界、社会与人间的道理、规则与理念,唯求大破,不思新立;只要瓦解,不思整合;只要混沌的天然,弃绝清明的理念……那也绝非济世良方。
